| 學達書庫 > 賈平凹 > 秦腔 > |
| 九十九 |
|
|
|
竹青把情況反饋給了夏家的五個兒子,只說男人家有主意,沒想慶玉先躁了,罵道:「一個子兒都不給他!」慶金嘟嘟囔囔,一會兒說爹愛管閒事,現在出了事啦兩委會沒一個人來過問,一會兒又怨恨狗,如果不是狗去咬,哪兒會有這事。慶滿和瞎瞎也罵狗,說爹把狗慣得沒個樣了,在爹眼裡,狗倒比兒子強。正恨著狗,來運就進了門,來運是和夏天義去七裡溝的,已經走到半路,夏天義發現忘了帶吃捲煙的火柴,讓來運回家去取。來運先跑到夏天義家,院門鎖了,二嬸是害怕書正媳婦再來而到俊奇娘那兒,來運就跑到了慶滿家。來運一進慶滿家,見屋裡坐了夏家五個兒子,尾巴搖了搖,從廚房灶臺上叼了一盒火柴要走。慶玉說:「瞧瞧,這狗真是成精了!」瞎瞎就一下子先過去關了院門,逮住了來運就打。可憐來運被夏家的五個兒子按在地上用腳亂踢亂踩。夏天義在路上等了一個時辰,不見來運,擔心來運沒聽懂他的話,就返身自己回家來取火柴,在巷中忽聽得慶滿家有響動,順腳進來,才發現來運被打得趴在地上,口鼻裡往外噴血。夏天義氣得渾身哆嗦,吼道:「這是打狗哩還是打你爹哩?!要打就來打我吧!」五個兒子都松了手,呆在那裡。夏天義還在吼:「打呀,來打我呀,你們不打,我自己打!」舉了手打自己的臉。兒子們嚇得一哄散了,來運才嗚嗚嗚地哭起來。 慶金跑出門,趕忙往四叔家去,慶金著實是慌了,他要搬夏天智來勸爹,但到了夏天智家門口,才醒悟夏天智去省城了,沒有在家。那日的天上黑雲密佈,秦安的媳婦在伏牛梁上的地堰上割酸棗刺回來當柴火,聽見了老貧協和我爹又在吵鬼架,嚇得跑回來,把鐮刀都丟失了。染坊裡的大叫驢莫名其妙的不吃不喝,腹脹如鼓。而放在劉新生家的樓頂上的牛皮鼓卻自鳴起來。 夏天智是在省城呆過了十天返回清風街的。孫女的手術很成功,割開了封閉的肛門,只等著傷口痊癒後大便就正常了。夏天智滿懷高興,等到白雪娘帶著慶玉的小女兒去照管白雪和孩子,他自己就帶著一大包買來的秦腔磁帶先回來了。清風街發生的事,是他回來後知道的,他就去萬寶酒樓向夏雨要了一千元,謊稱向出版社再購一部分《秦腔臉譜集》,把錢悄悄送去了書正家。書正見夏天智拿了錢來,從炕上下來一瘸一瘸地走著去倒茶水。夏天智說:「你給我走好,直直地走!」書正說:「走不直麼,四叔!狗日的趙宏聲整我哩,現在我走到哪兒路都不平!」端來了茶,茶碗沿一圈黑垢,夏天智不喝,罵道:「這碗噁心人不噁心人?你還講究在鄉政府做過飯哩!」書正說:「清風街上我最服的就是四叔了,四叔做事大方,你就再罵我,我心裡還高興哩!」卻又說:「四叔人大臉大,去鄉政府再做飯的事,還求四叔給說話哩!」夏天智說:「你別給個臉就上鼻子啊!你去鄉政府問過了?」書正說:「我讓我媳婦去過,人家不肯再要了,嫌我是跛子。」夏天智說:「我咋聽說是嫌你不衛生,還慶倖斷了腿是個辭退的機會。」書正說:「那些幹部官不大講究大哩,鄉長要筷子,我好心把筷子在衣襟上擦了擦給他,他倒嫌我不衛生,我衣襟上是有屎呀?!」夏天智當然沒有去鄉政府給書正說情,書正的媳婦倒自個去找鄉長,鄉幹部一見她,先把大門關了,敲了半天敲不開。她說:「當官的這麼怕群眾呀!」門還是不開。她就大聲喊,喊她來取書正的一雙鞋的,難道鄉政府要貪污群眾的鞋嗎?隔了一會兒,門上邊撂出來一雙鞋,是破膠鞋。 書正的媳婦提著破膠鞋往回走,走到磚瓦場旁的土壕邊,一群孩子用棍子抬著連了蛋的來運和賽虎,孩子們哄地散了,這婆娘就拾了棍打來運。來運拖著賽虎跑,又跑不快,被木棍打得嗷嗷叫。鄉政府的團幹從街上過來,奪了棍子,說:「狗也是一條命,你就這樣打?!」婆娘說:「我沒打賽虎,我打來運。」團幹說:「來運是賽虎的媳婦,你打來運是給鄉政府示威嗎?」婆娘說:「噢,狗是夫妻,鄉政府才護著夏天義呀!」團幹說:「你這婆娘難纏,我不跟你說!」拿了棍子回鄉政府了。書正媳婦又用腳踢來運,來運已經和賽虎分開了,立即發威,咬住了她的褲腿,她一跑,褲子嘩啦撕開一半,再不敢踢,捂著腿往家跑。 夏天義卻在這天夜裡添了病,先是頭暈,再是口渴,爬起來從酸菜甕裡舀了一勺漿水喝了,再睡,就開始發燒,關節裡疼。天亮時,二嬸以為人又起身去七裡溝了,腿一蹬,人還睡著,說:「今日怎麼啦,不去七裡溝?」夏天義說:「我是不是病了?」二嬸從炕那頭爬過來,用手在夏天義額上試,額頭滾燙,說:「燒得要起火呀!你喝呀不?」夏天義說不喝。二嬸說:「是不是我把老五的媳婦叫來,送你去宏聲那兒?」夏天義說:「誰不害頭疼腦熱,我去幹啥?恐怕是頭髮長了,你讓竹青來給我剃個頭。」二嬸摸摸索索去了慶堂家,竹青把理髮店的小夥叫來。夏天義的頭皮松,剃頭時割破了三處,都粘著雞毛。夏天義想出來活動活動,但走了幾步,天轉地轉,面前的二嬸是一個身子兩個頭,他又回來睡在了炕上。到了下午,後脖子上暴出了個大癤子。 夏天義沒有想到一顆癤子能疼得他兩天兩夜吃不成飯,睡也睡不好!二嬸害怕了,這才告知兒子們,兒子們都過來看了,把趙宏聲請來給貼膏藥。慶金說:「啥病你都是一張膏藥?」趙宏聲說:「我耍的就是膏藥麼!」慶金說:「為啥這樣疼的?」趙宏聲說:「癤子沒熟,就是疼。」慶金說:「還有啥藥吃了能叫人不疼?」趙宏聲:「那就得打吊針消炎。」慶金說:「打吊針。」趙宏聲說:「這膏藥我就不收錢了。要打吊針得連續打五天,我就貼不起藥費了。」慶金就去和幾個兄弟商量,得給老人看病,慶滿的媳婦問:「這得多少錢?」慶金說:「現在藥貴,幾百元吧。」慶滿的媳婦說:「不就是個癤子麼,貼上膏藥慢慢就好了,還打什麼吊針?」慶金說:「老人年紀大了,啥病都可能把人撂倒。」淑貞說:「人老了就要服老哩,再說人老了不生個病,那人又怎麼個死呀?!」慶金啪地抽了老婆一個耳光,罵道:「這都是你說的話?」淑貞一把抓在慶金臉上,臉上五道血印兒,說:「你還打我呀,你們人經幾輩就是能打人麼,不打人也不至於落到病成這樣!我不孝順,你孝順,你給你爹去各家要錢治病麼,看你能要出個一元錢來,我都是地上爬的!」慶金不言語了,氣得去河灘轉,肚子鼓鼓的,一邊揉一邊說:「氣死我啦!唉,氣死我啦!」又覺得自己窩囊,傷心落淚。轉了一會兒,心想幾個弟媳婦肯定也是不會掏錢的,他不願再給他們說,可他自己又沒錢,便去了西山灣的血站賣了血。 慶金沒想到給他爹只打了兩天吊針,夏天義是忽閃忽閃著又緩和過來了,而他卻從此面色發黃,見葷就吐,一坐下來便困得打瞌睡。光利去了新疆後所經營的供銷社關了門,卻一直欠著承包費,人家最後清算,以商品抵債,把他又叫了去。原想著把那些積壓商品拉回去還可以辦個雜貨攤兒,現在全抵了債還不夠,人一急,眼前發黑,就昏倒了。醒來尋思什麼病上了身,趁機在縣醫院做個化驗,結果是肝硬化。慶金問醫生:這病要緊不要緊?醫生說:當然要緊,往後再不得生氣,熬夜,喝酒,好生吃些保肝藥就是。慶金沒有去買藥,回來也沒給任何人說,只是再聚眾喝酒時堅決不動杯子。 眼看著到了臘月十幾,慶金坐在夏天智的院子裡曬太陽,太陽暖暖和和。夏天智吃了一陣水煙,見慶金耷拉個腦袋,來運也臥在那裡不動,就說:「提提神吧!」放起了秦腔。慶金不懂秦腔,問放的是啥調?夏天智說:「你連苦音慢板都聽不來?」順嘴就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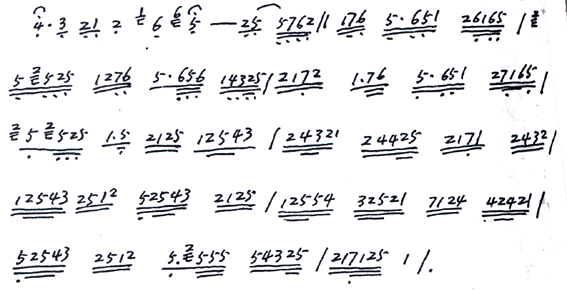
|
|
|
| 學達書庫(xuoda.com) |
| 上一頁 回目錄 回首頁 下一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