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達書庫 > 賈平凹 > 秦腔 > |
| 六十二 |
|
|
|
夏天智被張八哥請去給他的堂兄弟分家,堂兄弟是中街困難戶,分家本不該請夏天智,但中街組長主持分了幾次,兄弟倆都嫌不公平,要求重新分定,中街組長和張八哥就請了夏天智出面。兩個兄弟一個剃了個光頭,一個頭髮長得繡成了氈片,把所有的家當都搬了出來,老二說老大有媳婦而他沒有,就該把那個大板櫃分給他,老大說,不行,家裡他是主事的,憑啥他分不到大板櫃?老大的媳婦叫羞羞,是個弱智,一臉的傻相,只是嘿嘿嘿地笑。老二就主張,要分就把羞羞也當一份家產,要羞羞的不要大板櫃,要大板櫃的不要羞羞。夏天智就罵道:「你說的屁話!舊社會都沒有這種分家法!」夏天智一罵,兩個兄弟都不吭聲了。夏天智說:「房一人一半,老大東,老二西,廁所給老二,屋後的大榆樹給老二,老大拿大板櫃,老二拿三個甕再加一把頭一個笸籃,紅薯窖共同用。有啥分的?就這樣弄,今天就刀割水洗,分鍋另灶!」說完坐在中堂吃他的水煙了。中街組長說:「就這樣定。四叔,那些雜七雜八小的零碎呢?」夏天智說:「這還用得著我再給分呀?」中街組長和張八哥就提一個小板凳給了老大,提一個搪瓷盆給了老二,老大老二不時地有異議,夏天智就哼一聲,他們又再不敢爭執。破破爛爛的東西堆成了兩堆,夏天智說:「我該走了!」才要起身,門裡進來了狗剩的老婆和她的兒子,大聲地說:「四叔,聽說你過來了!」狗剩死後,夏天智承包了禿頭兒子的學費,這禿頭兒子在學校期中考試得了九十八分,狗剩的老婆摘了一個南瓜,領著兒子來給夏天智報喜的。夏天智情緒立即高漲了,也不說再走的話,當下把考卷看了,說:「不錯,不錯,我的錢沒打水漂兒!」卻發現考卷上還有一個錯別字老師沒批出來,就拿筆改了,又讓禿頭小兒在地上寫,寫了三遍。狗剩老婆說:「四叔待我們的恩,我們一輩子不敢忘的,他要以後學成了,工作的第一個月工資,一分不少要孝敬你哩!」夏天智哈哈笑著,說:「我怕活不到那個時候吧?來,給爺磕個頭吧!」禿頭小兒趴在地上嗑了個響頭。夏天智說:「這瘡沒給娃治過?」狗剩老婆說:「男娃麼,沒個羞醜!」張八哥說:「現在小不知道羞醜,長大了就該埋怨你了!你弄些苦楝籽、石榴皮和柏朵子,熬了湯,每天晚上給娃洗。」夏天智說:「別出瞎主意,明日去找趙宏聲,就說我讓來治的,不得收錢!」有人梆梆地敲門扇,門口站了慶金,給他招手哩。夏天智說:「啥事?」慶金說:「家裡有事,得你回去哩!」夏天智說:「啥事你進來說!」慶金進來卻只給他耳語,夏天智臉就陰沉了,說:「你就從來沒給我說過一句讓我高興的話!」站起來就要走,卻又對中街組長和張八哥交待:「把事情處理好,甭讓我下巴底下又墊了磚!」 回到家,慶滿、慶堂、瞎瞎已經在等著,夏天智在中堂的椅子上坐了,說:「到底是咋回事,你爹就去了七裡溝?」慶金說:「他先前讓我和他一塊去,說他慢慢修地呀,我以為他隨口說的,沒想真的就去了。」夏天智說:「一把年紀了,他倒還英武啥哩?!」慶金說:「就是呀!他幹了一輩子,啥時候落個人話,可這一半年不知是咋啦,總不合群,自己糟踏自己的名聲。四叔你要給我爹說哩!」夏天智說:「我說是我說,你們做兒子的,出了這事,我想聽聽你們的意見。」瞎瞎說:「我覺得丟人!外人已經對他說三道四的,他這一去,唾沫星子還不把人淹死!」慶滿說:「爹只管他逞能,從不為兒子們著想,上次替種俊德家的地,我們就一臉的灰,現在又到七裡溝,知道的是他要去給清風街修地呀,不知道的又該咬嚼我們對老人又怎麼著啦。」慶堂說:「他修什麼地,做愚公呀,靠他在那兒就是呆二十年,能修出多少地?!他是咋去的?」慶金說:「娘說是新生給蓋的棚子,啞巴和引生廝跟著的。」慶堂說:「引生是瘋子,那啞巴是幹啥吃的,讓他呆在爹跟前照顧老人,他倒是瞌睡來了就給送枕頭!不說修地,就是住在那裡,得下個風濕病了,是啞巴負責呀還是誰負責?」慶滿說:「誰負責?事情說事情,別胡拉被子亂扯氈!」夏天智說:「又吵開呀?咱還笑話張八哥那兩個堂弟爭哩吵哩,咱也這麼吵呀?要吵就不要來尋我!」夏天智一說畢,慶金就拿眼睛瞪慶堂,慶堂說:「我說的不是實情?怎麼就胡拉被子亂扯氈?!」慶滿說:「自己把自己管好!」慶堂說:「我咋啦,我又咋啦?」慶金氣得發了恨聲。夏天智喊:「把茶給我拿來!」四嬸忙端了茶杯。夏天智見是上午喝剩的陳茶,呼地把茶杯往桌上一放,說:「新茶呢,那新茶呢!」四嬸又沏了新茶,夏天智喝了一口,又放下茶杯了。屋裡一時安靜,屋簷上的水刷刷地響。夏天智說:「說麼。」卻都沒有再說。夏天智說:「全撮口啦?」慶金說:「你說咋辦呀?」夏天智一下子火了,說:「咋辦呀,他的墳不就在那兒嘛,讓他就死在那兒吧,咋辦呀?!」慶金頓時瓷在那裡,嘴裡吐不出個完整的話。瞎瞎起了身就往門外走,一邊走一邊說:「說啥哩,不說了,逢上這號老子,他願意幹啥就讓他幹去!」慶金說:「老五你給我坐下!」夏天智說:「走吧,走吧,既然他要走,你也走,我無能,我二哥也可憐,他還英武啥哩嘛,甭說村人怎麼待他,兒子都是這樣麼!你走,你們都走!」把慶金往門外推,推出了慶金,又把慶滿慶堂推出了門,門隨即哐?關了。兄弟四個站在院裡讓雨淋著,慶玉就也打了一把傘來了,說:「四叔是啥主意?」瞎瞎說:「碕!」夏天智在門裡聽著了,破口大駡:「日他娘的,我說話都是碕了?!」四嬸說:「你好好給他們說,發的啥火,人家又不是夏風夏雨。」夏天智說:「你瞧瞧這成了啥門風!咱二哥做人失敗不失敗,他講究一生在人面前英武要強哩,倒生了一窩啥東西!」慶金在院裡罵了瞎瞎,瞎瞎不做聲了,五個兒子就商量了先把爹叫回來再說,當下就去了七裡溝。 我在木棚裡陪夏天義喝酒,夏天義沒醉,我卻醉了,就昏睡在床鋪上,做了一個夢,夢見我爹也在木棚裡坐著。夢裡我還想,我爹不是已經死了嗎,怎麼又在這裡坐著?我爹始終不和我說話,他是拿了個小本本給夏天義說七裡溝的地形,他說七裡溝是個好穴位,好穴位都是女人的×,淤地的堤應該建在×的下邊。說這話的時候,木棚角背身坐著的一個人罵了一句,身子一直沒有轉過來,而我知道那是俊奇的娘。我也奇怪,俊奇的娘來幹什麼?似乎我爹和夏天義為著一個什麼方案又吵起來了,夏天義指頭敲著我爹的腦門罵,而我爹一直在笑,還在對俊奇娘說:你怎麼不說話?你怎麼不說話?我正生氣爹的脾氣何必要那麼好,爹卻突然跑出木棚,跑出木棚了竟然是一隻大鳥!我叫著:爹,爹!就被瞎瞎踢醒了。五個兒子跪在木棚裡求夏天義回去,夏天義歎息著兒子們不理解他,但也念及著兒子們畢竟還關心著他,就同意先回去,瞎瞎便拿腳把我踢醒,說:「回村!回村!」我醒過來極不情願,看見來運已經被慶滿吆進棚來用繩子拴著,而棚外三百米遠的一塊青石上站著那只大鳥,就是曾經撞進棚裡的那只大鳥,黑頂紅嘴的鳳。我說:「住在這裡多好,為什麼回去?」瞎瞎說:「你是野的,你不回去了就和那鳥過活去!」我說:「我認得那鳥哩,那是我爹!」慶金說:「這瘋子胡說八道!」我說:「我爹說七裡溝是好穴位,好穴位都是女人的×形。天義伯,我爹是不是這麼說的?」瞎瞎又踢了我一腳。夏天義看著我,又朝溝裡看,他是看到七裡溝也真的是溝口窄狹,到溝腦也窄狹,沿著兩邊溝崖是兩條踏出來的毛路,而當年淤地所築的還未完工的一堵石堤前是一截暗紅色的土坎,土坎下一片濕地,長著蘆葦。整個溝像一條船,一枚織布的梭,一個女人陰部的模樣。夏天義往溝裡看的時候,我也往溝裡看,我也驚訝我爹說的話咋那樣準確呢?夏天義說:「引生,你懂得風水?你爹給你說的?」我說:「我爹說的!」夏天義說:「你爹啥時給你說的?」我說:「剛才不是給你和俊奇他娘說的嗎?!」夏天義說:「誰,還有誰?」我說:「俊奇他娘麼。」夏天義怔了一下,他還要問我什麼,嘴張開了沒有出聲,就把捲煙叼著,使勁地擦火柴。瞎瞎說:「爹,你和瘋子說啥的,他的話能信?」夏天義默默地吸了幾口捲煙,煙霧沒有升到棚頂,而是平行著浮在棚中,他走過來摸我的頭,說:「引生,要回都回吧,今日下雨,睡這兒要患關節炎的。」我說:「我就睡在這兒。」夏天義說:「還是回去睡吧。」我說:「睡在哪裡還不是都睡在夜裡?」新生說:「回,回!辛辛苦苦倒是給你蓋了棚子?!」我們就是那樣離開了七裡溝。溝口外的312國道上,雨還是一半路是濕的一半路是幹的,他們都走在乾路上,我讓雨淋著。 夏天義要住到七裡溝的計劃被限制了,清風街的人大多已知道夏天義去住七裡溝又被兒子們叫了回來,議論著夏天義在清風街活得不展拓,在家裡也不滋潤,有些可憐他,也有些幸災樂禍。夏天智用手巾包了幾塊生薑去看他的二哥,但他並沒有直接進屋去,而是坐在塘邊的柳樹底下,打開了帶著的收音機,放起了秦腔戲。正好唱的是《韓單童》:「我單童秦不道為人之短,這件事處在了無其奈間。徐三哥不得時大街遊轉,在大街占八卦計算流年。弟見你文字好八卦靈驗,命人役搬你在二賢莊前。你言說二賢莊難以立站,修一座三進府只把身安。」柳條原本是直直地垂著,一時間就擺來擺去,亂得像潑婦甩頭髮,雨也亂了方向,坐在樹下的夏天智滿頭滿臉地淋濕了。二嬸坐在雞窩門口抱著雞,用一根指頭在雞屁股裡試有沒有要下的蛋,聽見了秦腔,就朝著窗子說:「天智來啦!」窗子裡的炕上直直地坐著夏天義。二嬸說:「你出來轉轉麼,天智來了你也還窩在炕上!」二嬸說這話的時候,夏天義已經從堂屋出來,又向塘邊走,但有著雨聲,二嬸竟然沒聽見,她放下了雞,拿拐杖篤篤地敲窗櫺。 夏天智感覺身後立著了夏天義,卻始終沒有回頭,任收音機裡吹打「苦音雙錘代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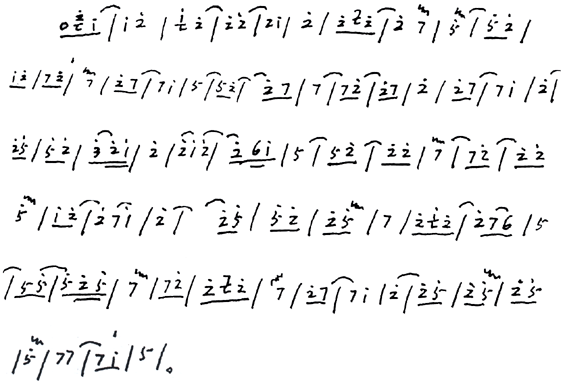
|
|
|
| 學達書庫(xuoda.com) |
| 上一頁 回目錄 回首頁 下一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