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達書庫 > 賈平凹 > 秦腔 > |
| 五十六 |
|
|
|
夏天智見四嬸為白雪端了飯,在院子裡對四嬸說:「你真輕狂,你給她端什麼飯?你再慣著她,以後吃飯還得給她喂了不行?!」四嬸說:「你知道個啥,她身上有了!」夏天智說:「真的?」四嬸說:「我可告訴你,你再別在家和我吵架,也別板個臉,連雞連狗都不得攆,小心惹得她情緒不好。」夏天智說:「你給我取瓶酒來!」四嬸說:「你要喝到外邊喝去!我再告訴你,再不要吆三喝五地叫人來家抽煙喝酒!」夏天智說:「在家裡不喝酒了行,可我總得吸煙呀。」四嬸說:「癮發了,拿煙袋到廚房裡去抽!」白雪在小房裡聽見了,只是嗤嗤地笑。 白雪原準備趁劇團混亂著要去趟省城,四嬸是堅決不同意了,她認為懷有身孕的兒媳不可以坐長途汽車,這樣會累及白雪和白雪肚子中的孩子。她還有一條沒有說出來的理由,就是白雪若去了省城,小兩口見面哪裡會沒有房事,而這個時候有房事對胎兒不好。白雪聽從了婆婆的意見,沒有去省城,只給夏風打了電話,告訴了她懷孕的事。在白雪的想像裡,夏風聽到消息會大聲地叫喊起來,要不停地在電話裡做著親吻的聲,但白雪沒有想到的是夏風竟然說讓她打掉孩子。要打掉孩子?白雪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連著說:「什麼,你說什麼?」夏風說:「打掉,一定要打掉!」夏風的意思是怎麼就懷上孩子了?!白雪生了氣,質問:「怎麼就懷不上孩子?你懷疑不是你的孩子嗎?」夏風的語氣才軟下來,說他不是那個意思,他是嫌在這個時候懷上孩子是多麼糟糕,因為他已經為白雪聯繫了工作單位,如果人家知道新調的人是個孕婦,那怎麼工作,生了孩子又是二三年哺乳,人家不是白白要養活三四年,那還肯調嗎?白雪說:「我啥時候同意調了?!」夏風說:「難道說我結婚就是為了兩地分居嗎?」兩人在電話裡吵起來,夏風就把電話掐斷了,氣得白雪流眼淚。四嬸問了情況,給夏風重撥電話,說白雪不能打胎,也不能去省城,她口氣強硬:「你回來,你給我回來!」但是夏風就是沒回來。 我又是兩天沒瞌睡了,因為我見到了白雪。每一次見到白雪我都極其興奮,口裡要汪很多的口水,得不停地下嚥,而且有一股熱東西從腳心發生,呼呼地湧到小腹,小腹鼓一樣地漲起來,再沖上手掌和腦門。陳星曾經驚呼我的臉像豬肝,說他看見過一次槍斃人,行刑前一個罪犯的臉就是這個顏色,結果一聲槍響後,別的罪犯一下子就不動了,那個罪犯倒下去,血還在咕嘟咕嘟冒,只得再補一槍。我罵陳星拿我開涮,但我也知道我渾身的血流轉得比平常快了十倍。人的大腦會不會像打開了後蓋的鐘錶,是一個齒輪套著一個齒輪的,那麼,我的齒輪轉得像蜂的翅膀。這一次白雪回清風街,我最早看見是在丁霸槽家門口,然後又在小河邊,記得白雪把棒槌丟失嗎?那就是我使的壞。她在小河邊洗衣裳的時候,我就在河下游的柳樹下,我說:來一場大暴雨吧,讓河水猛漲,把白雪沖下來,沖不下白雪就沖下一件衣裳。這麼念叨著,想起了那次偷胸罩的事,我害怕了,改口說:「把棒槌沖下來吧!」河水沒有漲,棒槌竟然真的就沖了下來。我撿起了棒槌,尋思哪一片水照過白雪的臉,河水裡到處都有了白雪的臉。我掬了一棒,手掌裡也有了白雪的臉。我那時是喝了一捧水,又喝了一捧水,直到白雪離開了小河,我才把棒槌別在褲腰裡回的家。從那以後,我兩天兩夜沒有睡。 說老實話,我在炕上抱著棒槌是睡不著的。我把棒槌塞在褲襠裡,褲子撐得那麼高,那該是長在了我身上的東西。我開始唱秦腔,秦腔是你在苦的時候越唱越苦,你在樂的時候越唱越樂的傢伙。我先是唱《祭燈》:「為江山我也曾南征北戰。為江山我也曾六出祁山。為江山我也曾西域弄險。為江山把亮的心血勞幹。」唱過了,還覺得不過癮,後來就一邊唱一邊使勁地擊打炕沿板。我擊打「慢四捶」:  又擊打「軟四捶」: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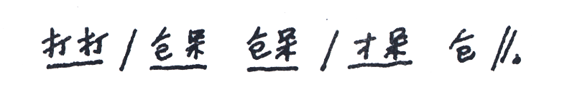 再擊打「硬四捶」:打 還擊打「倒四錘」和「四擊頭」「大菜碟」「垛頭子」,一遍比一遍擊打得有力,而口裡也隨著節奏狼一樣地吼叫。在我擊打了「慢一串鈴」: |
|
|
| 學達書庫(xuoda.com) |
| 上一頁 回目錄 回首頁 下一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