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達書庫 > 賈平凹 > 秦腔 > |
| 五十三 |
|
|
|
慶玉在新房僅僅獨住了兩天,淑貞就看見黑娥從地裡拔了青菜蔥蒜給慶玉包素餃哩。淑貞把這事告訴慶金。慶金在小河畔的沙窩子裡拾地,已經刨出了席大的兩塊,趁歇息,和慶堂、瞎瞎在地邊賭起撲克。賭注是二元四元的,慶金輸了,不肯掏錢,慶堂和瞎瞎就不依,說:「哥是掙工資的,還賴呀!」淑貞正好去,當下不高興了,說:「你哥有啥錢的,前天給娘買了件衣裳,又買了三斤鹽,他還有啥錢!」慶金說:「說這幹啥?」淑貞說:「咋不說,爹娘生了五個兒子又不是你一個?!你講究是有工資的,兄弟五個中除了你,誰沒蓋了新屋院!」慶堂和瞎瞎見嫂子話不中聽,起身走了,說:「哥,你可是欠我們賬哩!我們走呀,你好好拾地,工作了一輩子,退休了就當農民,這地肥得很,種豆子收豆子,種土豆長土豆,再種些錢給我嫂子長出個金銀樹!」兩個弟弟一走,慶金說:「我們在一塊玩哩,能賭多少錢,你就攪和了。」淑貞說:「我在屋裡給你煎餅哩,怕你肚子饑,沒想你倒在這兒賭錢,這糞籠大一塊地你弄了幾天了還是這樣?」慶金說:「我還害氣哩,工作了一輩子,拾掇這些地還不夠旁人恥笑哩,不弄了,不弄了!」淑貞見慶金上了氣,就蹴下身,說:「你在家閑著,是爹讓你尋個事幹的,又不是我逼的。今天累了,不幹了,明日再說。你知道不知道黑娥和慶玉過日子啦?」慶金說:「他的事你少管。」淑貞說:「我看這離婚是預謀了的,這不,晌午黑娥就在慶玉那裡雙雙對對包著餃子吃哩!」慶金說:「別是非啊!一堆屎嫌不臭,你還要攪騰?!」 淑貞憋住了一天沒再說,第二天就憋不住了,說給四嬸,又說給竹青。夏天義就把慶玉叫去,問:「你是不是想娶黑娥?」慶玉說:「想哩。」夏天義一抬腳就把蹴在對面的慶玉踢倒在地,罵道:「我以為你們鬧一陣子就和呀,你卻是早把心瞎啦!」慶玉的嘴撞在地上破了,血也不擦,說:「離就離了還有啥合的,我們三天兩頭吵嘴打仗你又不是不知道?她娘家舊社會經幾輩都是土匪,有什麼家教,嫁過來給我家做過一次針線,還是給你洗過一件衣裳?」夏天義說:「那黑娥就孝順啦,她是給武林他娘洗過衣服還是做過飯,他娘臨死的時候,吃到炕上屙到炕上,她做兒媳的收拾過?武林是老實人,啥事不聽她的,她還和你糾纏不清,她在武林家和你好,她嫁了你就不會和別人好?」慶玉說:「一物降一物,我不是武林。」夏天義看著慶玉,長長地籲氣,就掏出了捲煙。慶玉忙擦火柴來點。夏天義把捲煙又放下了,說:「你也是有兒有女的人了,文成是男娃不說了,臘八來我這裡哭哭啼啼幾場了,她給我說她走呀,出去打工呀!把孩子傷害成那樣,你知道不知道?我再給你說,你不合婚了也行,婚姻也不是兒戲,說離就離說合就合的,可黑娥取不得,你一口否定和黑娥沒那事,你卻要和她結婚,那又怎麼說?清風街人又該怎麼看夏家?」慶玉說:「我是和黑娥沒那事。就是有那事,我們一結婚也證明我們真有感情,外人還有啥說的?」夏天義說:「你給她應允過,要一定娶她?」慶玉不言語。夏天義說:「是她現在粘上你啦?粘上了的話,我讓你幾個兄弟去嚇唬她,熱蘿蔔還粘在狗牙上抖不離了?從這一點看,她就不是個好女人?」慶玉說:「是我要娶她。」夏天義說:「真的是你許了願!」氣又堵上喉嚨,掏捲煙叼在嘴上,手抖得擦不著火柴。慶玉說:「爹,爹……」夏天義強忍著,說:「你四十多歲的人了,我原本不管你的事,可我沒死,你不要臉了,我還有臉啊!你給武林戴綠帽子了,他沒尋你魚死網破就算燒了高香,你再把人家的媳婦弄來做你屋裡人,娃呀,那武林還怎麼過?一個村子,抬頭不見低頭見,他又不是階級敵人……」夏天義不說了,一會兒又問:「黑娥和武林能離婚?」慶玉說:「他願意不願意都得離。」夏天義說:「你放屁,你是土匪呀!我苦口婆心給你講道理,你就一點也聽不進去?!」又是一腳,把慶玉再次踢倒在地上。慶玉這回很快爬了起來,扭頭就走。夏天義吼道:「你滾!」自己卻從凳子上跌下來,窩在那裡半天不得起來。 後來的事情就熱鬧了:是夏天義再也見不得慶玉;是黑娥和武林開始鬧離婚,武林死都不離;是慶玉三天兩頭在河堤上或伏牛梁的背窪地約會黑娥。我那時全當是在看戲哩,碰著了慶玉,就高聲唱:「沒有你的天不藍,沒有你的日子煩,沒有你的夜裡失眠,沒有你的生活真難……」我用秦腔的曲調唱。慶玉拾了塊土疙瘩要擲我,我繼續唱:「什麼時候才能擁有你啊,我心愛的錢!」我說:「我說錢哩!你擲?你擲?!」慶玉笑道:「你狗日的讓錢想瘋啦!」遇見武林,我給武林出主意:「你沒好日子過,你也要讓慶玉過不上好日子!」武林說:「就是,是。婆娘再不好,畢畢,啊畢竟還有一個婆,婆娘。離,離,離了婚,我就,啊就,光碕打著炕,炕沿子了,響了。」我讓武林對黑娥殷勤些,武林果然殷勤,從田裡勞動回來,又做飯,又洗衣,掃地抹桌子,但是黑娥仍是不正眼看他,睡覺不脫褲子,還只給他個脊背。黑娥用香皂洗脖子,說這香皂是慶玉給她的,換上一雙新鞋,又說這新鞋是慶玉從縣城買的。黑娥說:「你不離婚,我就住到慶玉家不回來!」武林來尋我,問咋辦呀?我說找他慶玉,吃屎的還把屙屎的雇住啦?找他夏慶玉!武林卻要我陪他去。我陪他走到慶玉新房前的土場邊,我說你去吧。武林吸了一口氣,走到新房門口,看見慶玉坐在門檻上,武林不敢走了,繞到了屋後。那裡有新修的水尿窖,慶玉在牆裡蹲坑了,武林搬了塊大石頭丟進尿窖,髒水從尿槽口沖上去,濺了慶玉一身。慶玉還沒出來,武林先跑開了。我氣得再不理了武林,武林就去找夏天義。夏天義關著院門,武林說:「天義叔,天義叔,我有話給你說呀!」夏天義在家裡不吭聲,等武林走了,就捶胸頓足,罵慶玉要遭孽。 夏天義哪能想到,自己正熱心為七裡溝換魚塘的事抗爭著,慶玉卻出了醜,待到再不理了慶玉,又操心起三踅告狀的事怎麼沒個動靜?院門外的水塘裡漂了一層浮萍,原本是綠色的,卻一夜間都成了鐵紅。文成和啞巴將青柿子埋在塘中的黑泥裡暖了三天,刨出來了,在那裡啃著吃。給了夏天義一個,夏天義說:「柿子還沒熟哩,能暖甜?」咬了一口,柿子上卻沾著了一點紅,忙唾了幾口唾沫,發現是牙齦出血。竹青匆匆忙忙地從塘邊小路上過來,說:「爹,你吃啦?」夏天義說:「河灘地都收完啦?」竹青說:「最北頭還有幾家沒收。爹牙齦出血了?」夏天義說:「沒事。你要到後巷去,就讓栓勞他娘快把栓勞叫回來,出去打工總不能誤了收莊稼麼!」竹青說:「晚上了我去他家,現在君亭通知開會哩。」夏天義說:「組長也參加……研究啥事呀?」竹青說:「不知道。」夏天義突然覺得一定是鄉政府干預了七裡溝換魚塘的事,他說:「那你快去吧。」便進了院裡拿了煙葉搓煙捲,然後叼著蹴在院門口,看文成和啞巴在水塘游泳。啞巴只會狗刨式,腳手打著水花,把夏天義的煙頭都濺滅了。 兩委會的確是召開了會,研究的卻是魚塘的管理。管理條例一共有五條,又明確了在農貿市場專設一個鮮魚攤位。但是,誰來管理,意見不統一,有的說讓三踅繼續經管,有的說水庫之所以能以魚塘換七裡溝,也有三踅在幾年裡不繳代管費的原因,而他管的磚場還欠村上兩萬元,還有一萬元的電費也收不回來,如果再讓他管魚塘,那等於用七裡溝給三踅換了個私人魚塘。君亭見意見分歧,提出大家投票,誰的票多就讓誰幹。當下提了五個候選人,投票結果是金蓮票最多,金蓮也便簽了承包合同。開完會,竹青並沒有將會上的事說知夏天義,但三踅在丁霸槽家門口當著眾多的人大罵金蓮。 我不同情三踅。但我知道金蓮承包了魚塘,就是說七裡溝換魚塘板上釘釘的事了,就可憐起了夏天義。我本該立即去看望夏天義的,而很快又把這事遺忘了,因為我看見了白雪和四嬸往供銷社去。我承認我對不住夏天義,可我管不住我。我當時哇地叫了一聲,驚得站在旁邊的吃蒸饃的王嬸嚇了一跳,牙就把舌頭咬了。我說:「回來啦!」丁霸槽說:「你咋啦,?」我說:「我給你幫忙搬石頭!」丁霸槽的酒樓已蓋到第二層。我沒有從梯子上去到二樓,而是抱著腳手架的那根木杆子往上爬,我爬杆有兩下子,手腳並用,不挨肚皮,像蜘蛛一樣,刷刷刷地就爬上去了,上到杆頂還做了個「金猴探海」。我「金猴探海」是趁機往供銷社門口看,下邊的人喊:「引生,來個『倒掛金鉤』!」四嬸和白雪在供銷社門口說話,四嬸手裡拿著買來的兩袋奶粉。這奶粉一定是買給白雪喝的。但白雪的身子看不出是懷了孕,腰翹翹的。她們從供銷社往回走了,走過了丁霸槽的屋前,白雪抬了頭往正蓋的酒樓上看了一眼。我突然地嘿了一聲,雙腳倒勾在杆上,身子吊在了空中。眾人一哇聲叫好。傻樣!我哪裡是為他們表演的呢? 我在丁霸槽那兒幹了兩個鐘頭,沒吃飯,沒喝一口水,天麻麻黑了往回走,卻遠遠看見夏天義戴著石頭鏡坐在書正媳婦的飯店裡吃涼粉。夏天義一吃涼粉,肯定是他已經知道了金蓮承包魚塘的事,我現在再過去見他,就有些不好意思。我躲開了他。夏天義是吃完了一盤,又吃一盤,大清寺裡白果樹上的高音喇叭就播放了秦腔。夏天義說:「這個時候播的啥秦腔?」書正媳婦說:「金蓮管著喇叭的,她高興吧。」夏天義粗聲說:「再給我來一盤!」高音喇叭上開始播起了《鑽煙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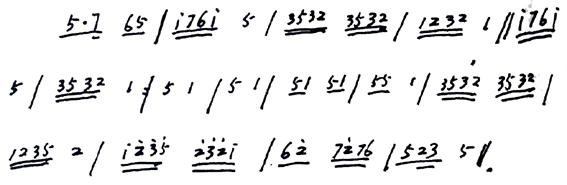 |
|
|
| 學達書庫(xuoda.com) |
| 上一頁 回目錄 回首頁 下一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