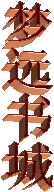
第三章
「見了鬼,」丁壽松嘟噥著,覺得自己做錯了什麼事似的。
什麼地方有翻翻窣窣的聲音,好象在誰在搗鬼,又像是搓紙的聲音。聽著叫他
更感到寂靜,更感到自己是孤孤單單的,好象這屋子裡那些人——壓根兒就不知道
添了一個客人。
那位老陳一會兒回到門房裡來,一會兒走出去——不知道忙些什麼。可是走起
來總是慢慢的,輕輕的,似乎拼命要叫他那只瘸腿踏穩當了——拐得像樣些,他一
直沒跟丁壽松說一句話,也沒看一眼。
丁壽松想要曉得別人到底看不看得起他,他故意想出些話來問:
「呃老陳,真的,你在這塊幹了七年吧?」
過了好一會兒,那個才冷冷地瞅他一眼:
「哪裡止!」
「哦,九年哩,怕有?」
他沒等著回答。於是又問:
「九年,可是啊?」
「沒得。」
這位客人有點不舒服,他一定要知道這回事才放心。他緊瞧著老陳的背影:
「那麼幾年呢?」
沉默了十來秒鐘,老陳說:
「八年還欠兩個月。」
丁壽松聽了歎了一口氣。不知道他是對光陰生了點感慨,還是因為坐著的床鋪
太高了叫他不舒服,他右腿擱上了左腿,兩腳就淩了空,腿子疊得發酸。可是他沒
把腿子放下來。
他一直沒移動他的視線。老陳背著臉在忙著兩隻手,在那裡縫補著什麼。丁壽
松可打不定主意——要不要再跟這位門房大爺攀談幾句。這麼沉默著很叫人不好受,
一開口他可又怕別人那副愛理不理的勁兒。
等到老陳一拐一拐地走了出去,他於是對自己說:
「嗯,真是的,老陳還是這個老脾氣。他對二少爺也都是這個樣子。真有趣!」
本來他還打算從老陳那裡打聽點什麼,現在才知道辦不到。這公館裡上上下下
的腳色——他丁壽松都摸熟了他們的脾氣,只有這個老陳有點特別。
「哼,一個門房!」——他才用不著去看一個門房的臉色哩。他從前進城來隻
是跟上房裡打交道,跟老陳沒有來往過。
他站起來舒舒腿。把包袱放到床上,撥空這張椅子讓自己坐上去。
太陽光漸漸射了進來,當窗的桌子上畫出一個耀眼的平行四邊形。影子在發著
抖,發光的一塊在閃爍著,好象桌面上給炙出了油——油星子還輕輕地在那裡跳動。
天空藍得沒有底:打這門房裡的窗口望去,叫人會不落邊際地想到老遠的地方,
想到老遠的事,連自己都不明白自己到底呆在一個什麼世界裡。一些白雲浮在前面,
帶著躊躇的樣子慢慢流著,好象給那些屋脊擋住了過不來似的。
那些屋脊顯得格外高,格外驕傲,看來竟要俯視全城一切的房子。
這麼高大的屋子可有五進。廳上總是掛著些灰撲撲的字畫,陳設些笨重的桌椅,
就叫人覺得這屋子更加大,更加空洞,走過的時候聽著自己的腳步子,聽著嗡嗡地
起了回聲,簡直有點害怕,一面忍不住要羡慕。
可是丁壽松每逢到這公館裡來,就不得不穿過這些陰森森的廳子,主人們住的
是後面幾進。他還記得大太太跟二少爺住的兩進——有幾扇房門一直鎖著,還貼上
二少爺親手寫的封條。打門縫裡張去,黑黝黝的隱約辨得出那裡堆著許多箱子:唐
家收藏的骨董字畫原是很出名的。
丁壽松歎了一口氣。唉!真是!唐老二本來用不著稀罕他那個印花稅分局的位
置。
他筒著兩手放在桌上,再把下巴擱上去。右眼眨呀眨的呆看著天上,一面細細
聽著這公館裡有什麼響聲。
四面很靜,連麻雀在院子跳——都覺得聽得見。偶然大門外面有車子拉過,松
了嵌的大石板格咚叫一聲,就簡直叫人嚇一跳。有時候聽見了步子響,他就得把腦
袋抬起點兒,看看是不是溫嫂子出來喊他去見他家姑奶奶。
他家姑奶奶今天可要到娘家去,還在打扮著。
「見了鬼!」他失望他說。他感到什麼事都不順當,都故意跟他作對。肚子似
乎塞滿了什麼東西,脹得他很難受,只要打個飽嗝就得翻出來的。
一個蚊子嚶嚶地在耳邊叫著。於是他狠狠地在自己臉上一拍,那個小東西哼了
一聲就蕩開了。
他生氣地想:
「唐老二——哼,搞得好好的又要交卸!」
他似乎怪別人事先沒跟他商量。接著他又隱隱覺得自己上了當:二少爺仿佛早
就知道他要來謀事,就故意辭掉了那個差使。並且趁著他來到的時候——二少爺趕
著過江去。
肚子裡的東西翻了一下,要嘔又嘔不出的樣子。他知道他對二少爺的那些敬意,
那些奉承的話——全落了空,照他自己說來,那就是「偷雞不著蝕把米」。於是他
把左眼角皺了起來,右眼眨得快了些。他想到大太太的那些話,又想起溫嫂子對二
少爺的那種賣弄勁兒。
他覺得這屋子忽然一亮,這些舊家具一下子變得鮮明了許多。他憑他自己的經
驗,憑他那種對別人身分高低的特別感覺,他領悟到自己這回做人做得太欠仔細。
「嗨,我怎麼不打聽一下的!」他在肚子裡叫。「見了鬼!——文侃當了什麼
秘書長,我還睡在鼓裡哩!」
他把包袱放到床下的網籃裡,決計去問問他家姑奶奶洗完了臉沒有。他心跳得
很響:連自己也不知道這是快活,還是害怕。一面他記起自己平素對丁家的那種冷
漠的樣子,那副看不起的臉嘴,就感到犯了什麼罪似的。這回——准是人家看他犯
了罪,才不大敢惹他,才叫他睡在門房裡,連老陳都哼兒哈的不十分理會。
他用謹慎的步子走到廚房裡,走到那些下房裡張望一會兒。隨後又到大少奶奶
屋子外面聽著。
溫嫂子在裡面伺候著,還聽見她們小聲兒在談呀笑的。
屋子外面的這個忽然有點嫉妒起來:
「溫嫂子到底憑什麼本事嘎,個個都歡喜她!」
這個堂客可在這裡吃了十多年閑飯。自從她那個男人嫖呀賭的敗了家,把八九
十畝田蕩光,她就走進了唐家——客人不象客人,老媽子不象老媽子。她幫著做做
針線,帶帶小孩,做起事來還露出那排黑牙笑著,好象她幹這些是為的她感到興味。
……
忽然屋裡面響起了腳步聲。丁壽松趕緊走了開去。他把下唇往外面一兜:哼,
別那麼神氣!——她一來一曆他都明白!
可是溫嫂子的能幹他也明白。真是的!別瞧她那雙眼睛朦朦朧朧瞌睡著的樣子,
看起人來可真看得准。柳鎮唐府上沒分家的時候就是大太太當家,溫嫂子就一直貼
在大太太的身邊,時常很俏地撮起嘴唇——在她耳邊嘰裡咕嚕的。一提到大少奶奶,
她嘴唇可就往下一撇:
如今——她可一天到晚跟著大少奶奶。
丁壽松不知不覺回進了轎廳,一半認真一半挖苦似地咕嚕著:
「嗯,不錯!嗯,不錯!」
不過——他搔搔頭皮——不過他家姑奶奶怎麼一來會相信她的呢?他有點不大
服氣,好象溫嫂子這件事辦通了,就是他丁壽松的失敗似的。
他轉身又蜇到廚房裡去:溫嫂子到那裡去打水的時候他可以碰見她,並且他還
打算把這件事探聽一下。他這就用種老朋友的口氣跟廚子桂九談了開來,轉彎抹角
扯到了大太太,然後很不在意地問到那個女人——他認為他家姑奶奶不會怎麼相信
溫嫂子。
「哪裡!」桂九叫,一面拿圍身中擦擦油膩膩的手。「大少奶奶才相信她哩,
什麼事都要她做。」
「怎麼呢?」
「怎麼!她叫她做的嘛。」
那位廚師傅又告訴了些不相干的事:大少奶奶房裡的椅子凳子只准溫嫂子坐,
大少奶奶回娘家的時候總是帶溫嫂子去。他說得很起勁,連臉都發了紅。一住了嘴
就用手去揉那些斬肉,不一會又想起一句話來,就重新在圍身巾上擦擦,打起手勢
來。
丁壽松咽下一口唾涎。唉,沒得法子:做人總是這麼麻煩的。他現在得從頭做
一番功夫,另外結一批朋友。真是的:這是很明白的事。
這裡他脖子一挺,牛頭不對馬嘴地答著別人的話:
「是啊,是啊。嗯,對哩。」
他不管桂九有沒有說完,就用種閒散勁兒踱出熱烘烘的廚房,仰起臉來吸了一
口氣。他覺得身子輕鬆了些,還消遣地瞧著屋簷上跳著的麻雀,它們側著腦袋看看
他,呼的一聲飛跑了。他不禁在臉上浮起了一絲微笑。
這世界似乎變亮了些,變好了些。他覺得從此以後——他反倒容易做人。他再
也不會引起那些閒話,說他看不起同宗倒去討好外姓了。仗著是一家人,開起口來
也容易得多。於是他嚼著東西似地磨磨嘴巴,興奮得心頭都發起癢來。
「唉,我們這位奶奶真是!洗臉還沒有洗好!」
一直到一點半鐘——他才由溫嫂子帶著去見了大少奶奶。
這回他拜年拜得很快,仿佛怕給別人瞧見。不知道是因為溫嫂子在旁邊吃吃地
笑,還是他自己跪得太吃力,起身的時候——顴骨上有點發紅。
他家那位姑奶奶呢——竟很客氣地把身子避開點兒,回答著「萬福」。腰板彎
得不大靈便,全身折成一個鈍角,仿佛她那漿過的硬領子箍得她不能動。她一直繃
著那張有點浮腫的臉子,等到別人盡了禮就仰了起來,給淡綠色的窗檔子映得發青。
屋子裡剛才洗過地板,還有點潮濕,桌子椅子都發亮,叫人摸都不敢去摸一下
——怕留下一個螺印來。到處都彌漫著一種說不出的香味,聞著就感到自己身子給
什麼軟綿綿的東西裹住了似的。
「坐吧,」大少奶奶嘴上閃了一下微笑的影子。
這位客人趕緊陪著笑——他家姑奶奶可又繃起了臉。他給搞得十二分局促,垂
著視線偷偷地往牆腳掃了一眼——不知道自己應該坐到什麼上面去,兩腳膽小地移
動一下,很怕踩髒了地板。
於是溫嫂子端著那把藤墊椅子過來——靠門邊放著。
這是規定了給客人坐的一把。坐墊上沾著點兒油漬,還有些地方去了漆,脫漆
的森砂底子上糊著灰和髒印。靠背上畫出了一個不成形的「唐」字——大概是祝壽
子用小刀子刻的。
唵,原來這孩子還是這麼個老脾氣。他媽媽房裡的木器件件都洗摸得又光燙又
乾淨,絕不准他破壞。於是他只好對這幾樣家具做起功夫來:反正是安排來招待客
人的,做母親的也就不怎麼禁止他。衣櫃旁邊那張骨牌凳可更加刻得花裡剝落,眯
著眼看去——簡直是一幅山水畫。不錯,這是指定給高媽她們坐的。
丁壽松把屁股頓上那把椅子的時候,莫明其妙地感到了一點兒驕傲。他一面問
候著丁家那些腳色,一面把脊背往後靠過去。
大少奶奶背著窗子,挺得筆直地動都不動,似乎怕一個不留神會把臉上的粉弄
得掉下來。她鼻孔裡時不時發出一種響聲:聽來覺得她在那裡笑,又像是答允客人
的話——還帶點兒謝意的樣了。
「唉,真是的,」丁壽松一提到丁文侃就歎氣。「到底是我們丁家祖上積德,
侃大爺——嗯,如今到底……」
溫嫂子一直歪著身子靠著梳粧檯的,這裡趕緊插了上來:
「沒得談頭!——前些個日子人家還看他不起哩!」
「怎麼呢?」那個臉上有點發燙。
溫嫂子使勁把下唇一撇:
「丁家窮哎,唐家闊氣哎。闊氣嘎,闊氣嘎——噢,如今掉了差使還要找丁家
想法子!」
這位姓丁的可活潑起來,拿出那種跟自家人談體己話的派頭——歎著氣發著議
論。他認為一家人家頂要緊的是個氣運。他可不怕別人的白眼,到時候出了頭——
哼,你瞧著吧!
他輕輕拍著自己大腿,瞧瞧這個又瞧瞧那個,舔一下嘴角上的白沫。
可是大少奶奶在鼻孔裡哼了一聲。她好象全沒聽見別人的話,只顧自言自語似
地說了一句——
「我反正就是這個樣子。」
接著她對窗子那邊轉過臉去,皺了皺眉毛。她怕陽光照壞了她的眼睛,把窗檔
子拉嚴些。舉動來得很細巧,很小心,似乎她在拈一條蟲子。隨後還把手指撚幾撚
——去掉剛才巴在上面的灰塵。
她聽著丁壽松談了這麼分把鐘,她又對梳粧檯照照鏡子。
反映出來的臉子有點歪,右邊腮巴看來更加腫了些。可是看她那兩撇清秀的眉
毛,那雙明亮亮的眼睛,誰也不敢咬定她有三十七八的年紀。於是她稍微把腦袋側
一下,眼珠斜著對鏡子瞟了一瞟。
溫嫂子一面緊瞧著大少奶奶,一面嘴裡照應著客人。她好象不大相信他的,時
不時大驚小怪地叫著:
「真的啊?真的啊?」
現在她可忽然發現了什麼,一腳沖到梳粧檯跟前——拿起毛巾來細摸細抹地在
大少奶奶的嘴角上擦了起來。
丁壽松仍舊在報告他家鄉的情形。他說得很詳細,連他家用的帳目都背了出來:
仿佛他知道她倆向來就非常關切他這個自家人,他不能夠漏掉了點兒叫她們下放心。
因為怕別人沒注意他,他故意提高些嗓子發幾句問話。
「姑奶奶你看我有什麼法子呢?你看呢?」
照例——溫嫂子就跟著歎一口氣,瞧瞧那位奶奶,似乎問她這一手有沒有做錯。
那位奶奶說:
「真不行!怎麼搞的?——用呀用的玻璃就不平了。」
一會兒她又沖著丁壽松問:
「孩子不吵啊?」
「什麼?」那個一下子摸不著頭腦。
「哪,你說你家裡沒得吃的,你孩子餓著不鬧麼?」
丁壽松那個挺直著的脖子松了勁,跟手放了氣似地長歎一聲。
「是啊,」他說。「人家說起來:哦,家裡倒還有五十畝田哩。其實啊——唉,
姑奶奶你是曉得的。不出來找個事情何行嘎,你看?」
他聽見溫嫂子嘴裡「嘖嘖」響了兩聲,就轉過臉朝她看看——表示他這些是同
時對她兩個人說的。
那個仿佛代替他傷心得喪了元氣,身子軟搭搭地斜倚著梳粧檯:
「噯唷我的媽!真想不到你家這個糟法子!」
不過丁壽松認為現在有希望些:他早就料到侃大爺會做官,這回一聽見了這個
好消息——他就趕出來了。他說話的聲音越提越高,手勢也打得特別有勁,顯得挺
有把握的樣子:
「一筆寫不出兩個丁字,侃大爺總不能望著自己家裡人挨餓——呃可是啊?我
常跟家裡人說:我不管人家家裡怎麼有錢有勢,我是——唵,我姓丁,我只相信我
家丁家的人。我是——我是——我問侃大爺要口飯吃吃我倒說得出口,不比人家…
…」
丁家這位姑奶奶可總是有什麼放心不下:一會兒看看窗子,一會兒看看鏡子。
她視線一落到丁壽松臉上,就忍不住要去研究他那雙眼睛。
「左邊那只一定害過風火眼。」
於是她想到有一種很靈的眼藥,可是忘了叫做什麼。她眼睛往上翻了一會兒,
然後不安心地盯著自己的指甲。她這壞記性逗得她自己都不高興起來。
這時候耳膜上猛的給敲了一下似的——沖進了那個男客的話聲:
「我要去跟兩位老人請安。」
她剛集中注意力聽到了這一句,又從這上面轉開了念頭,把他下面的話全都漏
過去了。
丁壽松聲音發了啞。還是不住嘴的談著,喝著溫嫂子給他倒來的茶。
這回他覺得已經有了點兒落子:到底同是一個祖公下面的子孫——待他不同得
多。看來事情可以進行得很順手,什麼都湊得停停當當的。他告辭出來的時候竟透
出一口長氣,腳踩著的似乎是帶點暖氣的棉花。
他因為心裡太舒服了,就耐不住要多幾句嘴——到了房門口又轉身問溫嫂子:
「姑奶奶不等吃飯要回家吧?」
接著他重新提到那位在京裡做官的自家人,好象這回他順利得過了火,倒叫他
有點擔心,有點犯疑似的:
「侃大爺下月初一定家來啊?」
那位溫嫂子生了氣地把嘴一撮:
「噯唷你這個人!……快代我去喊小侯打車子!」
於是他吃吃地笑著走了出去,大聲使喚著車夫——那個剛送了二少爺到汽車站
回來,拿一塊灰黑手巾在抹著臉上的汗。
「快點個!快點個!」他瞪著眼叫。「哦,還要給溫嫂子叫掛黃包車哩。……
唉,你真不著急!」
一直等到大少奶奶到大太太那裡問了安,坐上了車子出門——他才放了心。
他還在大門口站著望了一會,顯然他捨不得分手。
小候跨著大步子跑開去了。用著包車夫常有的那種派頭——直沖到了大街上,
怎麼也想要趕上別的車輛。上面那個踏鈴不住地響著,一陣風似地在那些招牌旗子
底下掠了過去。街心裡那些石板給踩得空隆空隆吼起來。
溫嫂子帶著那包大少奶奶的衣裳,坐著雇車在後面跟著。她回頭對丁壽松媚笑
了一下,就挺著脖子,眼睛直盯著前面的天空。她覺得街上的人都在瞧她,於是撮
起嘴來做個俏樣子。
「要死嘍!」她在肚子裡叫。「噯唷,盡看著人家!——有什麼看頭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