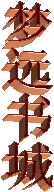
第二章
丁壽松一給帶到了裡面,他就覺得他這趟來得不大湊巧,唐二少爺今天要到對
江那個省城裡去。他知道他那位闊親戚還是那個老習慣:一個月裡面總得過江去次
把,並且四五天就回來的。不過他總感到有點失望,仿佛他碰到了不好的兆頭。
「去做什麼呢,真是!」
接著他又想:
「嗯,怕的又是有個雌貨迷住了他!」
他心頭竟有點酸溜溜的,可是他用種很感動的臉色跨進了那個書房。
這間房子很暗,一走進來就覺得一陣涼氣。四壁似乎要跟這有氣沒力的光線賭
賽——那些字畫發著灰黃色,看去只像是牆上的黴斑。
那位啟昆二少爺正把上身伏在桌沿上,一個人在那裡喝稀飯。他嘴裡哪一絲肌
肉都在跟滾燙的流質掙扎著,搏鬥著,把他那張長方臉攪得動著扭著。一面發出唏
唏噓噓的響聲,好象他什麼地方受了傷。
唉,唐二少爺比先前老了點兒:腦頂上多了幾根白頭發。不過那抹斬齊的鬍子
還是又黑又有光澤,氣色也不壞,實在看不上四十幾歲。並且他仍舊吃得很多,用
他全力使勁著筷子——仿佛這兩根銀棒很有些斤兩。他把一塊蔥油燒餅整個塞到了
嘴裡,又夾起油滴滴的肉包子來。他神色很認真地嚼著,把一雙有點紅絲的眼睛盯
著那盤鹽水豬肝,腮巴肉扯動得很起勁。看來他簡直是在盡什麼神聖的義務:他生
到世界上來就只為的這個。
那位客人駝著背走進來的時候,二少爺好象怕給分了心似的,只隨便瞅了他一
眼。
可是丁壽松用激動的聲音叫了起來:
「二少爺!你發福啊!」
接著把包袱捧寶似地放到一張紅木椅上,他就施起本地頂隆重的禮節來。他哼
了一句——「拜年!」一面用種挺熟練的手法跪了下去。
二少爺稍微躊躇了一下,就認為自己可以不必站起身來。他只用手擺了幾擺,
又像是表示不敢當,又像是嫌別人打攪了他的用飯。嘴裡不方便地響著:
「呃呃,呃!」
他瞧著別人伏下身子去,一面皺著眉,似乎嫌那個的姿勢不大好。
因為跪著的地方離他太近,丁壽松磕頭的時候不得不把脖子縮著點兒,脊背就
更加駝了些,看來顯得格外恭敬,格外有那種「小人該死」的樣子。於是二少爺覺
得自己仿佛又給墊高了許多,臉上放著紅光。並且忍不住想要挑出對方的錯處來似
的,擺出副討厭的臉色來瞧著客人——等他先開口。
丁壽松早就摸熟了主人的脾氣:他知道二少爺一輩子看得頂要緊的是一個娘,
還有一個寡嫂。於是他開頭就提到對方的母親。
「大太太康健?我去給她老人家拜年。」
「呃,等下子!」那個把臉用力地一晃。「她老人家沒有起來。」
那位客人可還打算往外走:
「那我們那位姑奶奶……」
「早哩早哩!……你坐罷!你坐罷!」
說了就送一塊蘿蔔頭到嘴裡,慢慢地嚼著。他看看丁壽松,又看看那些碟子—
—似乎怕人搶去。
牆上的掛鐘拖下一個很長的擺——重甸甸地搖著,替他的嚼聲打著拍子。有時
它格達響了一下,人家當它會敲起來,可是偏偏沒有聲音。好象它知道它自己活在
這唐家裡不是為的要報時辰,只是讓它塗金的雕花在這裡給客人們欣賞欣賞的。
天上大概有雲在流著。這屋子裡一下發了點亮,一下子又暗了下去。於是那些
紅木家具時不時在變著顏色——一會兒淺,一會兒深,象二少爺的脾氣那麼捉摸不
定。
丁壽松為了特別客氣些,他不去坐那些光燙的椅子。只把半個屁股擱在一張骨
牌凳上,腰板稍微挺直了點兒。
「大太太——她老人家——」他感慨地說,一面咽了一口唾涎,「唉,真是的!
她老人家真好,福氣!……她老人家——她老人家——那個背疼的毛病可好點個了?」
那個瞅了他一眼,校正他一下:
「膀子疼。」
照丁壽松平素的脾氣——准得有一場爭辯。可是他忍住了,只表示了有點驚異,
右眼睜得大大的:怎麼,膀子啊?接著可又不放心起來,很仔細的問著疼得怎麼樣,
有沒有貼膏藥,好象他是個醫生。最後他屏住了呼吸,焦急地等著別人回答他。
「唔,今年沒有發,」唐老二很不經意的樣子。連眼睛都沒抬起來。
「丁壽松總想要別人轉過臉來,可是等個空。他臉上皮肉縮緊了些。右眼就睜
得有點費勁。怎麼搞的呢——唉,他那位親戚沒往年那麼看得他起了。其實自己在
家鄉里也有五十畝田,也穿著長衫受人尊敬,並且那些泥腿子常常有事情請教他的。」
「人家還說唐老二是孝子哩!」他在肚子裡嚷。「哼,問起他的娘來——他倒
他倒——不相干似的!」
倒還是他丁壽松關切些。他問:
「她老人家背脊——呃膀子——一點不疼啊?什麼膏藥貼好的嘎?」
等到他聽說並沒有用藥,只是在天慈寺許願許好了的——他就快活得全身都晃
動起來,右眼眨呀眨的流眼淚的樣子。他一面提高嗓子發著感慨,一面歎著氣。
唉,大太太是——菩薩當然保佑她老人家。不過他認為二少爺的功勞更加大些。
「二少爺你老人家——唉,孝心感動上天:我曉得的,我曉得的。」
那個把嘴唇包著,嚼得輕了點兒。掛鐘敲起來的時候——他還嫌它吵似地皺皺
眉,可是它滿不在乎慢慢響了十一下。
丁壽松活潑了起來,話也漸漸來得流利了。他打著手勢,腿子也在桌下動著,
輕鬆得連骨頭都脫了節。嘴裡反反復複談著啟昆二少爺的孝行,好象生怕對方不知
道。他又歎氣,拿手背抹著濕祿祿的下唇。
未了——他還舉出別人的話來做佐證:
「他們都說嘛:唐家二少爺真是!好心有好報,怪不得如今當大官哩。孫少爺
呢,書又讀得好:常是考第一,他們說。」
「哪個說的?」二少爺拼命裝出副平淡的臉色。
「哪個啊?……都是這個樣子說。小火輪……唵,大家也談的。」
原來船上的人——一個個都在談著唐二少爺:那麼個好人出現在世界上,出現
在城裡,真好象是個菩薩落凡。唐家全家的人又都那麼出色,跟那位二少爺配得很
得當。至於他丁壽松呢——他只歎氣,唉,真是的!他在這三四年裡面沒有一天不
想著他這房親戚,沒有一天不跟家裡人談起:
「唉,我這一輩子就只靠二少爺。真是!二少爺待我們真好。說話要捫捫心,
真的!」
他並且還細細地告訴他那兩個種田的兒子:他要叫他後代都記得這位好人。
那位二少爺慢慢吃完了飯,慢慢向客人轉過身來。他臉上有點發紅,氣色顯得
更加好。他自己也不知道這到底是喝了稀飯之後身上發熱,還是有一種輕飄飄的快
樂感覺熏得他這樣。
隨後他用種很溫柔的聲音叫高媽打手巾把子給他。他挺舒服地靠在椅上,打一
個小木盒子裡掏出一件精緻的小銀器來:這還是四五年前的那根牙籤——用銀練跟
耳挖子吊在一起的。他很周到地剔著牙,還用小指去幫著挖呀刮的。他時不時插句
把問話:
「怎麼呢?……怎麼說的,他們?」
反正現在去趕公共汽車還嫌太早,他就打算讓客人談完了再走。他覺得了壽松
這人還不討厭。可是有時候他臉上忽然感到一陣熱:他看著對方那副過於謙卑的樣
子,過於小心的樣子,反倒叫他起了點疑心。到底是說正話還是說反話呀,那傢伙?
全屋子都靜悄悄的,表示著一種大公館的莊嚴。只有丁壽松一個人在咭咭呱呱,
似乎四面還起了嗡嗡的回聲。他嗓子發幹發嘎,好象破竹子在空中甩著的聲音。他
求救地瞅了一眼茶几——可是那些聽差老媽竟忘記了替客人倒茶。
未了他提到了他這趟的來意,他要請二少爺賞他一碗飯吃。
「二少爺待我好,我只要跟二少爺做事。……」
他哭喪著臉盯著對方的眼睛——等著別人表示一點什麼。
二少爺那雙眼睛中間隔著一座寬鼻子,叫人疑心他的視線不會有焦點。那上面
塗著一些紅絲,好象老是睡不夠似的。不過它還發出又威嚴又同情的光來。丁壽松
總覺得那雙眼珠子生得不大平正,可是仔細瞧去,又不知道它的毛病到底在哪裡。
「怎麼的呢?」二少爺問。「你們鄉下也搞得這麼糟法子?」
「是嘎,是嘎,唉!三五十畝的人家——唉,真不得了!一年水一年幹的。還
要鬧土匪。」
「你們那塊也有土匪?」
「怎麼沒得呢。唉,如今世界好人少,沒得吃的就搶。」
他還想往下說,可是外面有腳後跟頓著磚地的響聲。連二少爺也注意地望著門
口。他們瞧見那位溫嫂子拎著個紅漆木桶——要打外面廳子穿過。
那個女人仍舊是那麼副俏勁兒。太陽穴上貼著頭昏膏藥,眉心裡扭瘀扭得一撮
紅的。眼睛永遠是那副朦朦朧朧的樣子,還對書房這邊瞅了一眼。她沖著丁壽松扭
扭脖子打招呼的時候——很俏地笑了笑,露出那排整齊的黑牙齒來。
二少爺巴望著什麼似地問她。
「大少奶奶起來了吧?」
「沒有哩!」——那個看不起地答一句,撇撇下唇走掉了。
這叫丁壽松嚇了一大跳,連神經也緊張了一下。怎麼,溫嫂子現在伺候大少奶
奶,溫嫂子——嗯,奇怪!她竟沒把二少爺瞧在眼裡!怎麼搞的呢,這是……然後
他從男女事件上面去著想:唐老二只管是個好人,在這方面可招人說了許多閒話。
這回——說不定是溫嫂子故意賣俏。
於是他沒那回事似的,苦著臉又回到原來的話題。
唐啟昆想起剛才那回情形給別人瞧了去,就瞪著眼對著他的客人——看看那個
的臉色。可是對方什麼表示都沒有。
「混蛋!」他暗暗地罵。他不相信那個姓丁的就這麼麻木,越是故意裝做不懂
事的樣子,故意不露出什麼神色來,他就覺得他越可惡。
然而最後他還是答允替那個傢伙設法,並且還問:
「你有地方住沒有?」
「哪裡有呢。客棧住不起,我……二少爺賞一個臉,給我……」
「好好好!你就住在公館裡罷!……小侯!小侯!——打車子!」
他出門之前還是照著他平素的禮數——到嫂嫂房裡去叫一聲問安,還到母親那
裡去告辭。隨後戴上那副茶色平光眼鏡,挾著一個肥泡泡的黑皮包,坐上包車叮叮
當當地走了。
只留下丁壽松在大太太房裡拜年。
這回丁壽松沒多說話:大太太老不停嘴,叫他沒機會開口。他只應著——「是,
是。」他在這裡竟聽到了一些意外的消息:原來他那本家丁文侃的確當了什麼秘書
長。唐二少爺的局長位置呢——交卸了!
他脊背上流過一道冷氣,又流過一道熱氣。他覺得坐著的椅子晃動了起來。
那位大太太可沒住嘴的意思:想不到一位六十二歲的老太太——還這麼有力氣
說話。她把一雙手擱在茶几邊沿上,看去像是用鹽醃了許多時日的,又幹又白,跟
她那張皺巴巴的臉一樣。那兩片薄嘴唇很快地一下子縮緊,一下子掀開,發出嘶嘶
嘶的聲音:顯然她那排假牙沒鑲得妥貼,一說起話來就會透風。
「他們真是希奇巴拉的,」她把腦袋湊過去點兒,仿佛告訴他一件了不起的機
密事。「當秘書長有什麼稀奇嘎!——比印花稅分局長還小一品哩。你們二少爺連
這個局長都不情願玩,硬辭硬辭才辭掉的。嗯,真的也難怪他。人家當局長賺錢,
你們二少爺呢——還賠本。再玩下去——家裡田都要賣光了哩。……你們二少爺說:
做官沒得玩頭。你看看嘎:你們二少爺當局長的時候——今兒個縣太爺請酒,明兒
個商會請酒,他還嫌煩哩。今年自正月裡初二起,一直到——到——」
這裡她轉過臉去問她孫女五二子:
「到十幾啊,那回子?」
那個十一歲的五二子正在挑著花。客人進門的時候她打量了他一下,又低著頭
去做她的事,這時候她就很快地答:
「到十九。」
「唔,十九。你看!一直到十九都有人請,他一直沒在家裡吃過一頓安穩飯。
……搬到城裡來總是應酬大:人家總要請你們二少爺管管事。早就說要下鄉找管田
的說話,總沒得工夫。鄉下這幾年也真是!……哦,真的,你兩個兒子呢?還好不
好?」
「他們……」
「你們二少爺啊——辭了局長還是忙。真的。丁文侃那個秘書長——還是你們
二少爺幫忙才玩成的哩。你們那個本家,你曉得的,從前五塊十塊的常是來告幫。
那回子我家那個親家太太來借錢,說是——說是——」
她掀著嘴沒有了聲音,用詢問的眼色看看她孫女。於是五二子微笑著,口齒很
清楚地報告了那句話:
「她說,『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她說,『親家太太哎,做做好事嘎。』
……」
大太太就格格地在嗓子裡笑著,她那孫女用光閃閃的眼睛瞧著客人,愛笑不笑
的——似乎表示她從前小時候就認識他,又仿佛要看破他裡面的心事。
丁壽松可笑得很忸怩,他決不定要不要走出去,肚子裡老反復著那個疑問:
「怎麼搞的呢?怎麼搞的呢?」
以後大太太的話——他幾乎沒有聽進去。大概她談到了城裡的一些情形,又談
到了公館裡的開銷。
「我呢——還是柳鎮住得慣點個。柳鎮真是個好地方。你到那塊去的那年……
哦,真的,你是哪年到過那塊的啊?」
這位客人驚醒了一下:
「柳鎮啊?——我是……」
「柳鎮什麼都好,就只是有些個壞人不得了——搶東西放火他都來。你們二少
爺才不放心我哩,硬要接我到城裡來住。也是天照應:要是我還在柳鎮的話,那場
倒頭的大水就逃不過……」
忽然——五二子好象感覺到了什麼,猛的抬起了臉。她把挑花繃子往桌上一放,
躡腳躡手走到窗子跟前,掀開一小角窗擋往外面張了一張。
「怎幹?」她祖母吃驚地問。
那位孫小姐搖搖手,對窗子那邊努努嘴,又拿兩隻手指指自己的太陽穴。
於是大太太提高嗓子問丁壽松餓不餓,還叫韓升照拂這個遠客去吃早飯。等別
人挾著包袱要出房門的時候,她又大聲說:
「你這回還沒看見你家姑奶奶吧?——去看看嘎!」
因為大少奶奶還沒洗好臉,丁壽松就在門房裡等了一個多鐘頭。他的住處是給
安頓在這屋子裡的,跟老陳拼鋪。他把包袱放在一把快要散了的太師椅上,這才坐
上吱吱叫著的床沿——老遠地想了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