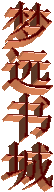
第二節 八字腳文化之子
世界上有許多湊巧的事情那都是大意。讀者諸君當然知道我是說史兆昌。史兆
昌不是想在上海結識幾個人麼?哪,胡根寶。
史兆昌還是前年,不,大前年,他大前年在漢口認識了胡根寶。他那天在江漢
夫那兒散步,三五個穿藍短衣的傢伙圍著一個穿夾袍的人要動手。穿夾袍的說好話,
打躬作揖,可是還吃了一個嘴巴子。史兆昌走了過去把那三五個藍短衣推開:
「滾!再動手老子剝你們的皮!」
「關你麼事!」那些傢伙叫。「這姓胡的賣了我們,他……」
「敢動!」——馬上他擺了個馬步,站好樁子。
不用說,這些下等人裡面沒有好傢伙。
記不上有沒有交手,還是巡捕來了,總而言之給那穿夾袍的解了圍。
「真正是大恩人,」穿夾袍的打躬。「要不是您家來了,我性命都危險。……
您家貴姓?」
「不敢。敝姓史,」他拱一拱手。
「我請您家去洗個澡,您家賞不賞……」
「不敢當。打抱不平是我應分的事。」
「真正是大俠客。現在這世界……」
這麼著就跟穿夾袍的做了朋友,那就是胡根寶。可是他們做朋友沒有做多久:
一會兒他爸爸派了人來接他回北平去了。
「呵,在這兒遇見了。真想不到!」
人行道上那些男男女女忙著走著,從他們身邊擦過。一些賣晚報賣小報的孩子
瘋了似地嚷著。
史兆昌還一直站著,告訴胡根寶他打的主意。
「上海你熟不熟?」
「我是老上海,」胡根寶笑得滿臉都是皺紋。
「我想在上海找一個……」
「找一個小館子吃飯罷。您家沒吃過飯吧,我來做個小東。」
「噯不,」史兆昌斬鐵截釘地把手一揚,他認為他這回總得花幾個本錢。「我
請。」
胡根寶的腰漸漸伸直,透過一口氣來。
「是是。您家愛吃哪家館子?……這兒有一家浙江飯店。」
「好罷。」
喝著酒,胡根寶就告訴史兆昌:他有許多熟人。
「並且還有個頂了不起的。」
「武功好,是不是?」
「武功?哼,武功好到天上去也鬧他不過。」
許是什麼劍仙。許是個有道行的。可是史兆昌怕希望得太大會失望,就鎮靜地
又說:
「最多是個有內功的吧。」
可是胡根寶搖腦袋。怪有禮貌地輟了一小口酒,把尖臉上的肌肉抽動了幾下。
史兆昌的眼睛盯著胡根寶的眼睛:媽的這傢伙賣關子。
胡根寶用手剔了一下牙,把嘴里弄乾淨,到底說了出來:那可不是個尋常人。
那個跳了起來,差點兒沒把桌子掀翻:
「啊!?」
一個茶房恭恭敬敬地站到了房門口。
「怎麼,」史兆昌叫「那是……那是……呵!」
「有的。不過要現蒸,」茶房說。
「什麼,我們說我們的,不幹你的事!……老胡,到底是……?」
史兆昌全身都飄了起來。胡根寶說了怎麼一個人,到底是?
「要是太極真人到上海來……」
「當然我會給您家介紹。他還說這一個月內有個人會來拜他做師傅,這人有宿
根,他還說,是從北方來的。」
「他麼,他麼,他麼?」史兆昌興奮得幾乎昏過去,一屁股坐到椅子上,臉紅
著。「你怎麼會拜識太極真人的?」
「我是,」那個用手背揩一下嘴邊的油,「我是在一個乩壇裡拜他做師傅的。」
「你……你……怎麼,你也是他的徒弟?」
「上半年才拜他師傅的。他教我道術。要不要放點胡椒?太極真人是……鴨子
不吃會冷的。」
史兆昌瞧著胡根寶的嘴——鴨子湯沒全吞下去就說話,湯水帶著泡沫似的東西
沿嘴角流到下巴上。這胡根寶在學道。可是太極真人說的有一個人要來拜他做師傅。
那是誰,那是誰?——
「我正是想要學道術,劍俠都要懂道術的。」
「太極真人會的。」
「還有土遁……」
「他都會,他都會。」
突然史兆昌站起來,一大步跨到胡根寶跟前,作了一個揖:
「假如你……假如你……你瞧不瞧得起我?」
「什麼!我……」那個嚇了一跳,站起來退了一步。
「你要是瞧得起我,我……我……咱們拜把!」
茶房送手巾把子來,拜把的事就給耽擱了會兒。
他倆走出那家館子的大門,胡根寶就打著嗝兒,趕著史兆昌叫二弟。
「二弟,大世界去好不好?二弟,我吃得真飽。嘔!二弟,明天我們去……嘔,
明天去……到商務印書館買金蘭譜。……你搬家的時候我來幫忙,我是……嘔!二
弟,師傅不久會來,二弟你等著。師傅是……」
「唔。」
史兆昌焦急地等了個把星期。
「大哥,太極真人准得來麼?」
「不要性急。師傅是說來就來的。」
「大哥,你瞧太極真人肯不肯收我?」
「二弟你放心,包在我做哥哥的身上!」拍拍胸脯。
「大哥你學著什麼功夫,可不可以說一點兒?」
「唔?唔。唔!我還才學,」那位大哥伸手到一個煙罐子裡拿煙,可是已經空
了。
「劉福,買一聽煙捲來。劉福!」
胡根寶瞧瞧牆上一副石印的清道人的對子:一個個字像藤似地扭著。中間掛著
一幅從什麼地方拓下來的「岳鄂王遺像」。胡根寶又仰起那張尖臉瞧瞧天花板。
「二弟你們這幢房子多少錢一個月?」
「好像是七十五兩吧。我可弄不明白。」
「這房倒不錯,」胡根寶瞧瞧窗外。「你們一家夠住了吧?」
史兆昌想再談點兒學道術的事,可是大哥老釘著問這幢房子有沒有洗澡間,有
沒有抽水馬桶,仿佛大哥打算要在洗澡間裡煉丹似的。
老問這些幹麼呀。總而言之已經住下一幢房子,三層樓,七十五兩。他們是前
五天搬進來的。
「兩個亭子間都住著人麼?」大哥問。
突然樓下客廳裡一聲響:嘩啦!
史兆昌把兩個嘴角往下彎著:
「哼,又是打牌。假如中國人全是這些個人可就糟了。」
「我應該去拜見拜見伯父哩,」那個伸個懶腰。
「不必罷。可不是什麼客氣。你是大哥,我不瞞大哥說,我們家裡……」
他告訴大哥:他有個家等於沒有家。他親生媽在他三歲上死去,八歲上他爸爸
討了個女人生了兆武,他就是個孤零零的人了。親生媽是精明的人,瞧到了這一點,
臨死就叫他丈夫給兒子存一筆現錢。當然老家裡還有一筆錢,可是那兒有土匪,靠
不住會到手。
「現在我跟我家裡的關係就只是這麼一筆錢,其餘的全跟我沒關係。」
「錢有多少?」大哥滿不在乎地問。「這筆錢隨你自己用麼?」
「唔。我已經是大人了,這筆存款就隨我怎麼使。款子可不多,只是三千零點
兒:我可沒動它,我預備著一番事業。」
「伯父對於你……」
「呃,不用提了罷,」史兆昌噓了口氣。「他本來是個好人,可是入了魔道。」
老實說,他對他爸爸簡直是有點兒仇似的。爸爸和繼母他們站在另外一邊捉弄
他,鬥他幌子。他知道爸爸那位填房太太對他不懷什麼好心:巴不得他死——她親
生兒子就得獨自個兒接過爸爸那筆產業來。
瞧瞧罷,連自己家裡人都用這種心眼兒!
「呃,這年頭兒好人可真太少!」
可不是麼,瞧見的聽見的都是些個歹人害好人的事。那些個大帥們拼命逼錢糧。
洋鬼子動不動殺幾個中國老百姓玩玩。有錢人販洋米來使中國米賣不出價錢。佃戶
愈來愈不聽話,簡直跨到了東家腦袋上。這些個受得了麼,媽的?近幾年來家鄉還
鬧著土匪,還有××鬼子!
他史兆昌可得做個好漢:自個兒受的,別人受的,他都得出口惡氣。自個兒吃
了虧,也想到了別人吃的虧。
「是呀,得做個好漢。」
爸爸從前的話是挺對的:
「你的八字是個大將的八字。你要學好,懂吧,要學好。不要做個平常人。」
誰也說他的八字裡註定了他得做一番驚人的事業。
「來,」爸爸常是這麼拖他到自己跟前去,「告訴我:你將來做個什麼人?」
「做關公。做嶽飛。」
「好小子!」拍拍他。「將來爸爸也有面子。」
他看過嶽傳。接著他看了七俠五義,七劍十三俠,他就開始練起武來。這還是
小時候的事。可是他一直沒變:還是想著自己的將來,還是拜師傅學著拳。
可是現在他爸爸把希望寄到兆武身上,不相信大兒子了。
「哼,我總得頂天立地的……我總得……這是命裡註定了的。這就是宿根。」
做一個英雄,就得相信自己,得苦苦地修煉,得立下大志。
去年他過二十四歲生日的那大他找到一個破關帝廟裡發過願,他對那位紅著臉
皺著眉毛的菩薩跪著:
「我要修道煉成一個劍仙。我要削盡世界上的歹人,打抱不平。我要征服全世
界。我要消滅世界上的邪道——那些不信菩薩的,不遵聖賢之道的,廢孔的,沒上
下尊卑之分的,提倡公妻的,那些個妖孽。我要殺盡土匪,要捉盡世界上的賊。…
…」
這裡他想了一想,看可說漏了什麼沒有。於是又加了一句:
「我要使我們家鄉安居樂業,穀子賣得起價錢,下等人都入正道,都知道個上
下,都知道自己的身分,都相信天命。我要使世界太平。我史兆昌發了這些個宏願,
決不變志:請關公……請關老爺……請關二爺……關關關……」
他一下子不知道要怎麼稱呼。
怎麼,忘了麼,關二爺不是死了之後封了帝的麼?
「請關帝!」他趕快說了出來。「我史兆昌請關帝轉奏,保佑我成功。……我
史兆昌誓死要修成這麼一個劍俠。」
這些宏願其實早就有了的,不過一直到那天才正式在菩薩面前宣了誓。於是他
努力要找個有道行的人拜他做師傅,一面找了個國術大家教他打形意拳。
「這種拳只是個初步功夫,」史兆昌開著剛買來的一聽煙,嘴裡說著。「我還
學過許多拳哩。」
他背履歷似地一口氣告訴他那位大哥還學了些什麼拳,於是拿一支煙插到嘴巴
上:須至履歷者。
胡根寶又瞧著天花板。
沉默。樓下的牌聲和笑聲。
史兆昌在房裡一上一下地踱著:用了戲臺上老生武生的那一副八字腳步子。他
老把眼瞟著那衣櫃的大鏡子:瞧瞧自己走的姿勢對勁不對勁。
這種八字腳步子也是小時候他爸爸給他的教訓。
「正派人走路有正派人的走法,不要毛腳毛手。」
爸爸就用八字腳步子走個樣子給他瞧瞧:
「走路要這樣規規矩矩地走。古來的聖賢,帝王,卿相,大將,都是這種走法。
和尚道士做法事的時候就用這種步子。你只要去看如今那些有道學的人,走起路來
也這麼一規一矩的。走路雖是小事,也要注意注意,這也是我們中國禮儀之邦的一
種那個,一種……一種……總而言之這種儀態是代表我們的文物的。」
的確正派人走起路是這種步子。古來那些大英雄大俠客雖沒瞧見過,可是從戲
臺上,從繡像畫裡,可以看得出:關公,岳爺爺,花木蘭,武松,薑大公,十三妹,
一塵子,諸葛亮,甘鳳池,太上老君,都是這麼一雙八字腳,還有許多許多了不起
的人也都是。
太極真人可不知道是不是這麼一雙腳……
史兆昌的眼睛從那面大鏡子上滑下來,溜到那位太極真人的徒弟那雙腳上。
那雙腿在疊著,瞧不出。
「大哥,太極真人走起路來是什麼樣子?」
「什麼?」那個摸不著頭腦。
「唔,沒什麼。我不過是……」
突然樓下有個小女孩子哭了起來:
「媽,媽,二哥揪我的頭髮……媽……」
史兆昌馬上跑出了房門。
他是去打抱不平的,是不是。
不。那女孩子是繼母生的第四個小妹妹,和兆武鬧彆扭,只到她娘跟前告狀而
已。這是常事。
可是樓下客廳裡又有奶媽控告二少爺:
「太太您瞧,二少爺搶走了我一條褲子,給扔到垃圾桶裡。二少爺還揍我,您
瞧,太太您瞧。」
太太的聲音:
「什麼,你的褲子?」
打著牌的男男女女就大笑起來。
讀者諸君還沒見過那位太太,還得讓我介紹一下哩。請下樓去瞧瞧熱鬧罷。
哪,那位太陽穴上有個紫色疤的就是史伯襄老先生的太太,史兆昌的繼母。年
紀瞧去不到四十歲,眼睛是紅的。她後面坐著史伯襄老先生在瞧她的牌。
奶媽站在她跟前,左手抱著不滿周歲的五小姐,伸出右手腕上一塊青的給她瞧。
「你的褲子怎麼會給他搶去的?」太太把笑出了淚來的眼睛盯在自己的牌上。
「我在房裡折著衣裳,二少爺跑進來一搶就跑,把我的褲子扔到了垃圾桶裡。
我要來告訴太太,二少爺就揍了我一拳。」
太太輕輕地皺著眉毛:
「你這個奶媽也真糊塗:怎麼連自己的褲子都管不住!……二少爺的脾氣你們
是知道的,你應當自己小心呀。你這個人真是!」
這裡太太歎了口氣:
「兆武這孩子真是淘氣,雖然人家管不住自己的褲子,你也不該把它扔到垃圾
桶裡呀,垃圾桶……碰!七萬碰!三條。你吃一個吧。三條真是好張子:我拆對打
給你的。不要?這好的張子不要?真是淘氣。真氣死我。垃圾桶裡的褲子……怎麼
劉太太你就和了麼,嗨!伯襄你點支煙給我。我一定要罰兆武一頓,兆武!兆武!
……二少爺什麼地方去了,喊他來……兆武!」
「打二哥!打二哥!」四小姐叫,可是給洗牌的聲音蓋住了。
七八分鐘之後太太又長長地歎口氣:
「兆武這孩子真淘氣。十五歲了呀。啊呀,這張中風虧你打!真是個好炮手,
哈哈哈!雖然說尚武精神是要提倡的,你也不該打奶媽呀——打傷了還有奶麼?褲
子搶去也何必扔到垃圾桶裡呢。這孩子真氣死我!……」
史伯襄老先生謹慎地給太太點了一支煙,安慰著太太:
「兆武這孩子的確淘氣。但是你也不能管得太嚴:十六歲他當了師長,還不是
你當老太太享兒子的福麼?」
「雖然是不錯,可是這時候總叫你有點慪氣呀,是不是。現在我總是……自摸
平和!四七條我聽了許多時候了。上家聽了沒?我等四七條等了許久哩。我當是等
不著了。不錯,等著做老太太享福,可是現在太淘氣,做娘的心裡當然不舒服。…
…」
太太把煙放在煙灰盤上,讓手來洗牌。嘴裡往下說著,告訴大家兆武的八字是
十六歲得做師長。
「當師長是很苦的,當師長可沒工夫玩了,所以我現在隨便一點,對他。十六
歲當師長當然太早了點兒,可是有什麼辦法呢。不過古時候也有十二歲當一品宰相
的。……兆武今年十五歲了,能玩的日子可不多了,就讓他玩玩。到臘月他就走完
了懵懂運。明年做起正經事來,要玩也不能玩,不能再……再是那麼……他志向是
在武的一方面。可是……可是……我總覺得十六歲當師長,總是一樁苦事。別人十
六歲還是個小孩子哩,呃,是不是,劉太太?」
史兆昌從樓上送他的大哥下來,站在門外聽了會兒。他很重地吐口唾沫:
「哼,十六歲當師長!他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