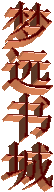
第一節 到了上海
睡著的城市。靜靜的夜。
突然!轟隆!
炮響!
炮彈劃過黑色的空氣,像吹哨子似地叫著。接著——嘩啦!
××兵工廠裡炸開了一個大窟窿。這是太陽牌的炮彈。
接著第二炮。步槍響。第三炮。第四炮。第五炮。
睡著的人跳了起來:
「怎麼!……」
「又是什麼實彈演習吧。」
「不像。」
「老是實彈演習!」
「聽!」
有人在叫喊。屠殺已經開始。
「××鬼子呀!」
「咱們的兵幹麼的?」
可是××調完了!
這消息馬上傳了開去。每個角落裡都抽痙似地震動了起來。牆上貼滿了壁報。
街上叫著「號外!號外!」空氣裡蕩著緊張的談話。
「馬上就得打到天津!」
「北平也有點兒彆扭哩。」
「跟鬼子幹一傢伙!」
「大亂子就來了!」
「幹麼要退兵?」
世界像一根拉得緊緊的橡皮帶,稍為碰一下,就得嗒的一聲斷了的。
「遲早總得有這麼一手的。」
「咱們民族得找自己的出路!」
學生子又活動了起來:拿著旗子在東單牌樓走著;喊著。街上的人覺得這回的
學生子比往日有點不同:這回的事是連自己也有點關係的。
「好傢伙!」
「大家幹呀!」
有些人在跑來跑去打聽消息:
「究竟這兒北平要緊不要緊?」
「說不定。」
「我想搬回南方去。銀行裡提款還提得出吧?」
他們都輕輕地談著,仿佛聲音一大了點兒就得給鬼子兵聽了去似的。他們呼吸
得怪費勁的:空氣是早已經凝得像漿糊那麼厚了。
「史伯翁,你聽見的消息如何?」
「靠不住。走為上策。」
「極是極是。我還去到銀行方面聽聽消息看。」
銀行裡忙著對付存戶提款。拍賣行一天總得到兩打人家裡去估價那些帶不走的
笨重的家具。車站裡來著電話,來著慌張的臉嘴,要定頭二等的臥車鋪位。
「好了,都弄停當了。」
於是許多車輛從前門擁出來,停到東車站西車站門口,卸下肚子的東西:太太,
姨太太,鋪蓋,蜜棗匣子,老爺,小姐,皮箱,少爺,獅子貓,罐頭餅乾,男人用
人,藤包。
一坐到洗澡堂子似的臥車裡,就透過一口氣來。
「這放心了。」
「可是天津呢?說不定天津鬧了亂子,那可糟糕。」
坐定了的人抽著煙,靜靜地瞧著別人擠上車。搬運夫給皮箱什麼的壓得歪著腦
袋,吃力地喊著:
「借光,借光!」
搬運夫後面緊跟著那些皮箱什麼的主人,焦急地四面瞧著只要兩條腿稍為一停,
後面的鋪蓋就沖到自己的脖子上。
「借光借光!」
「快,快,車要開了!」
誰都找好了自己定的鋪位,安靜地等著開車,大家就都拔起一雙八字腳,踱出
臥車那扇小門,在過道裡走著。誰也得在這車上遇見個把朋友的。
「史伯翁!」
「喔,劉六先生!」
「請進來坐坐。」
那位留著三四根鬍子的所謂史伯翁跨進一扇小門。
「到上海麼?」劉六先生一面在個綠色洋鐵罐子裡掏出一支煙捲來給那位史伯
翁。
史伯翁點點腦袋,把那支煙捲塞到嘴裡,去湊劉六先生手裡的火。
「寶眷呢?」劉六先生又問。
那個趕快抽了幾口煙,把煙拔出了嘴,讓嘴來答話:
「都一同來了。」
這臥車廂裡除了劉六先生還有一位四十上下的胖子,一個勁兒微笑著瞧著史伯
翁。劉六先生瞧了那胖子一眼,就覺得自己還得做一件事:
「你們二位見過麼?……這位是史伯翁,史伯襄先生。這位是……」
「久仰久仰,」那位胖子搶似地說。「史伯翁在北京住了很久吧?」
「甲辰,乙巳……唔,差不多三十年。」
大家忽然給震得一搖,火車就動了起來。
史伯襄老先生抽煙,可是煙熄掉了火。
「大世兄也一同來了麼?」劉六先生嘴裡問史伯襄老先生,眼向各處找著,像
在找那位大世兄。他找到鋪位下面,找到地上,又拿手去掏口袋。
「唔,也一同來了。」
劉六先生找到了一盒火柴給史伯襄老先生點火,眼對著那位胖子:
「史伯翁那位大世兄武功很好。他是……他是……叫做什麼派的,有一個派名。
是不是少林派?」
那位史伯翁微笑一下:
「我也弄不清楚那些名目。他是——叫做什麼內功吧?」
「現在還天天練麼?」
「他愛玩那麼一套,我也不大管他。他好像在那裡運什麼氣。胡鬧,簡直是!」
那位胖子把個肚子挺了起來,大聲地告訴史伯翁:武功裡面頂了不起的是運氣
這步功夫。
甘鳳池就是運氣的,甘鳳池!他聲音提得很高:他怕火車的響聲掩住了他的話。
「只要肯用功,沒有練不好的。令郎有沒有拜師傅?」
史伯襄老先生張一張嘴要答,可是胖子又搶著問了下去:
「令郎台甫是什麼?」
「兆昌。不吉之兆的兆。昌……昌……昌是——沒有女傍的。」
「讓我們見一見好不好?」
那位胖子似乎對這些事怪內行的。史伯襄老先生在那張腫了似的肥臉上盯了一
眼,就踱出去到自己臥車間裡把他大兒子史兆昌叫了來。
史兆昌比他爸爸高上半個腦袋。大概二十五六歲。眼角往上翹,像一個戲子。
臉紅紅的。有點胖。胸部挺發達,可是他拼命把胸部吸進,讓背駝著。
這年輕人對劉六先生和胖子作一個揖,坐到鋪位上,背就更駝了。
胖子把眼盯著史兆昌:
「世兄近來練什麼功夫?」
「形意拳。」
「練得久了吧。」
「半年,」史兆昌接著劉六先生給他煙捲。「這倒還不怎麼難。老師說的,練
功夫全靠天生的有根底,不然是,怎麼用功也練不好的。這話挺有道理。」
胖子點頭。他又想問內功練得怎樣,可是他弄不明白形意拳到底算是外功,還
是內功。他瞧瞧窗外:野景在向後面飛去。他自言自語地:
「內功很要緊。」
史兆昌一震:唔,這胖子說不定懂得一手兩手!他試探地說:
「我也練著運氣的功夫。」
胖子回過臉來,把肚子挺一挺,又大聲地說到甘鳳池:
「氣功練得到甘風池那樣就好了。甘鳳池真是了不起的。譬如……譬如……」
他先瞧瞧大家有沒有在聽他,然後說了一件甘鳳池的事。
「甘風池在雍正皇帝面前,試過本事的:他拿一根絲線……一根頭髮……一根
……一根絲線……唔,是一根絲線……」
不錯,是一根絲線。他說這根絲線有十五丈長。他說甘鳳池拿著這根絲線,運
一運氣,他把肚子又挺一挺,他說絲線就豎了起來,像一根筆直的竹竿——十五丈
長。
「這還不算,」胖子站起來,打著手勢。「在那絲線的頂上面,就是十五丈高
的上面,絲線上面,還拿一個五千斤重金元寶放上去。呵,這功夫!」
史兆昌拍拍煙灰問:
「五千斤的金元寶?」
「是呀。是雍正皇帝的。然而——」這裡忽然胖子改成了心平氣和的聲氣,屁
股也坐了下去。「然而還不算什麼。後來甘鳳池叫雍正皇帝所有的力士來,叫他們
用力拉那根絲線。就有五百個力士來拉。……」
當然是拉不動。於是那位胖子勝利地微笑起來。
史兆昌長長地吹了口氣,一肺的煙向胖子臉上噴了過去。這口煙吹得有幾分用
力,他就瞧瞧對面那張胖臉——看那張臉給他的煙打得在發疼沒有。
可是胖子滿不在乎,又挺起肚子說了個運氣的故事。……
史伯襄老先生可和劉六先生談到了時局。
「上海不知道有沒有問題哩。」
「那不會有什麼,」劉六先生放心地。
史伯襄老先生扔掉了手裡的煙屁股,又從綠色洋鐵盒子裡掏出一支。他疊著腿
子,背靠到壁上,這麼把自己坐得很舒服之後,就長長地歎了一口氣:
「中國人真是不爭氣!你看,自從……自從自從……自從這個……」
劉六先生似乎想不到別人一下子會發感慨,他愣了一會兒才知道別人所談到的
題目。
「是呀, 」 劉六先生瞧了史伯襄老先生一眼,把眼睛移到一個小藤包上面。
「這回再那麼醉生夢死可就真要亡國了。所謂……所謂……然而……但是像是……
大家都覺得這個國不是自己的。」
那個也會心地微笑一下:
「你我都是手無縛雞之力的。白拼命是沒有用的。我們還是……倒是……唔,
明哲保身。而且……而且……」
突然他兒子興奮地叫:
「不對不對!」
史伯襄老先生嚇了一跳,就「而且」住了。
可是那位胖子很安靜地說:
「我當然比你知道呀。」
唔,他們倆在爭論什麼。
史兆昌紅著臉往下說:
「有劍術的人比普通俠客要厲害得多。呂四娘當然是劍客,是劍仙,她是……
假如她是個普通俠客,她可殺不了雍正。她是吐劍殺了雍正的。」
「你記錯了,」胖子慢慢地一個字一個字在咬著「呂四娘的本領是飛簷走壁,
不會吐劍。她是個俠客,不是劍客。」
「哪裡!我看見書上……」
「我當然比你明白呀,」打著手勢叫別人別嚷。「我當然比你知道得清楚些。
呂四娘的事我最明白。呂四娘同我還有點親戚關係哩。」
史兆昌的心一跳,張大了眼盯著胖子。
胖子用手拍自己的膝頭,發音很正確地說出那親戚關係:
「呂四娘的嫡堂侄兒的表侄的曾外孫女婿,是我一個族兄的舅公公的一個內侄
的連襟的姑表兄弟。所以我最明白呂四娘的事。她並不是劍仙。」
「要是劍仙,那就得更……」
「劍仙當然更厲害,」胖子搓搓手。
「總得學到這一地步才不冤枉做一輩子人,」史兆昌瞧著窗子。「做劍仙是非
學道術不可的。」
史伯襄老先生插了進來:
「這可得要有宿根的人才行,你配麼?」
那年輕人橫了他爸爸一眼,咽下一口唾沫。
劉六先生把手擱在那年輕人肩上:
「你看那些……」
史兆昌全身有點發熱。他心跳得很響,差點兒沒震碎了胸膛。
「沒武功救不了中國,」他說得有點氣喘。「只要一個!……還怕鬼子麼?—
—……劍術是非練不可!」
史伯襄老先生可記起呂純祖降乩壇說的那些話:中國亡不了,有個救國的大英
雄已經長大,馬上得做出一番偉大的事業來。
這大英雄是不是他的大兒子史兆昌?
他沒這麼想。要是這大英雄真出在他家裡,他希望這大英雄是他第二個兒子史
兆武——這小子倒有宿根。他不大關心大兒子。
史兆昌瞧了他爸爸一眼,使勁地把手裡的煙捲往洋鐵痰盂裡一摔。他知道那老
頭不大相信他大兒子。自從繼母生了兆武,這大兒子馬上就成了個可有可無的人。
老頭覺得大兒子不會有什麼了不起的出息。可是史兆昌對自己的前途當然比那糊塗
老頭明白得多。
「哼,瞧著罷!」
他又瞧瞧他爸爸。他爸爸掏出一塊折成長方形的手絹,用種滿不在乎的勁兒揩
著嘴上那三四根鬍子。自從討了繼母之後,這爸爸的臉子忽然變成了討厭樣子:嗯,
瞧瞧他那邪裡邪氣的眼睛!
這是入了魔道,這是!其實這老頭兒人倒是挺好的。可是爺兒倆一回到自己的
臥車間裡,老頭兒就教訓史兆昌:一個人總別自己誇口。
「誇口是不會長進的。」
「我可誇過口了麼?」史兆時眼睛不對著爸爸。
「譬如剛才你在劉六先生那邊……」
「一個人總要有志氣,」兒子大聲說。「說自個兒的志氣可不是誇口。」
史伯襄老先生愣了會兒。
「志氣……」老頭反著手嘟噥著。
「爸爸,您別老跟我鬧彆扭,我知道您是……呵,不說了罷。」
「怎麼?」聲調怪和氣起來。
「二弟那麼昏天黑地的您倒不教訓教訓他。」
「你二弟是正交著懵懂運,我有什麼辦法。」
「呵,懵懂運,」兒子笑了一下。
老頭兒就只相信二弟。八字先生說二弟十六歲會當師長,老頭兒就把二弟當太
歲看。
「哼,十六歲當師長!」
命裡註定了十六歲當師長倒並不是奇事,只是史兆昌信不過他二弟會這麼著:
二弟不夠料。
晚上他睡不著。火車空隆空隆響著。火車上不好練功夫,今天沒做晚課。
幹麼要逃到上海去,那麼怕?
在上海找得到一個師傅麼?可是那些劍仙和有道術的人在上海是呆不慣的。那
些人總得在昆侖山上,躲在一所陰暗暗的屋子裡煉丹,運氣。再不然就是峨嵋山。
……
史兆昌歎口氣,起來點了一支煙。
「得想法子到峨嵋山去求道。」
據說到峨嵋山去,上海可比北平近些。學了道他得花上一天工夫把土匪剿乾淨,
於是去打回東三省,還收服了××國。休息了一會,再去征服別的什麼國:俄國,
英國。還有什麼爪哇國。
「美國呢?」
他考慮了好一會:美國是跟咱們中國挺要好的。……呃,到那個時候再說罷。
那個時候誰也知道有個史兆昌。中國人家家給他立長生牌位,燒著香對他磕頭。
他得有個愛人,像十三妹那麼一個女子。他和那愛人一塊兒立功。
史兆昌狠狠地抽口煙。
上海許找得著十三妹那樣的女人。有部書叫……叫……
「叫什麼呀?」
叫……不錯,叫做什麼什麼因緣的。可不是,在天橋兒還找得著哩。天橋兒他
去過,可沒找著:那些賣武藝的全是些男子漢。只有一處有個女的,那是個六七十
歲的老婆婆。媽的,像十三妹那麼個人,天橋只有一個,只有書上說的那麼一個。
嗽!
幾天幾晚他老打算著這些事,跟誰也不開口。老頭兒不懂得他。繼母跟他壓根
兒合不來。兆武是暈頭。他只是一個人抽著煙,躺著,計劃著到上海第一件事幹什
麼。
「上海地方我可不熟。」
他從沒到過上海。他那位把兄老住上海的,可又走了。這回他總得結識幾個人。
坐了幾天火車他可一點不累。別人紅著眼睛,瞌睡似地跨下車,他就嘟噥了一
句什麼,挾一個小皮箱就跳到月臺上,搶到別人前面。
月臺上螞蟻似的人。
這許多人裡面可有沒有夠他做朋友的?
呵,上海!
這天的晚上,史兆昌就跨出旅館門,在愛多亞路的人行道上踱著了。
他手握著拳,嘴閉得緊緊的。重重地在水門汀上踏著八字步子,睜著眼注意著
每張臉子。
「啊呀,」忽然有個尖臉向他打招呼,「大恩人!大俠客!您家怎麼到洋涇浜
來了?……什麼時候來的,您家?」
可是史兆昌忘記這尖臉是誰。
「不認得了麼?」那個打躬似地彎著腰說。「我是胡根寶呀。……您家公館打
哪裡?……」
「呵,真巧!」史兆昌眼睛放光。「我住在這裡一家湖南人開的旅館裡。明後
天就得搬家。……你近來怎麼著?你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