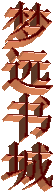
秋天的憤怒 四
十幾年前,他們曾經手挽手地涉過蘆青河;往西,穿過密林,不為人知地走了幾百里;又折向南,入山。
在大山裡面,李芒找到了他的一個朋友。朋友以介紹副業師傅為名,把他和她介紹到了一個又小又窮的山村裡。這麼年輕的兩個師傅,山民們看了很驚奇,也很喜歡。可就是沒有住的地方:這是二十歲左右的一對子,給他們太窄巴的地方不行。他們一年、也許是兩年的時間,就會添出一口來。
後來有人想起有幢房子鬧過鬼,倒是又空閒又寬敞。
李芒問:「怎麼個鬧法?」
村領導說:「房子三間。最東邊一間盛了乾草,大躍進那年裡面吊死一個人,以後常年鎖著。到了半夜的時候,鎖著的門就響,鎖、鐵環子,都哢嚓嚓響……」
「就是哢嚓嚓響嗎?」
「就是這麼響。」
「沒出來過什麼東西麼?」
村領導搖搖頭:「沒有。」
「那就住在那裡吧。」李芒這樣說。他想,只是哢嚓嚓響,危害不著他們的生活。這使他想起自己村裡那個老寡婦:每到夜深的時候就哭,開始人們聽了都害怕,後來也就不怕了……
他們把用來居住的正間和西間認真地裱糊了一番。在土炕的圍牆上,還貼了粉紅花紙。這一天他們一生也不會忘記的。他們忘不了那麼疲乏地走了幾百里路,路的兩旁那麼荒涼,顏色單調,山的岩石是鐵樣的青灰色。他們躲閃著行人,躲閃著田野裡的歌聲。他們好不容易翻過了最後的一座山,接近了朋友,接近了他們將要落腳的這個山村。於是世界的顏色開始變換了,變為嫩綠和淺黃,變為石竹花的那種紅色,又變為土炕圍牆上的那種透著暖意的粉紅色了。
天色將晚,粉紅色被霞光映成了大紅色。小織的臉也紅了。
她穿了件學生藍制服。這衣服剪裁得特別合身。頭髮黑亮而柔軟,用橡皮筋在腦後紮成兩個彎彎的毛刷刷。此刻,這兩個毛刷刷安靜地垂著,末梢兒往裡曲著,像小貓那兩隻永遠握不緊的拳頭。她安詳而羞澀地坐在炕沿上,手裡掐弄著她的淡黃色的小手帕,臉像被染過了一樣,臉上有一層非常細小、非常規整、又淡又勻的白絨毛。這使她顯得很稚嫩。她剛剛才十九歲。十九歲的姑娘就跟上一個男子跑出來了,她多有激情啊!此刻,她把一切都壓抑在心底,不動聲色,微微抿著嘴角。紅紅的嘴唇,下唇翻得略重一些,顯得有些頑皮。她不看站在屋子裡的李芒,她看到的只是環繞她的一片粉紅色。她很自信地等待著,她什麼都能等得到:幸福、焦慮、喜悅、煩悶、惆悵。一個有過這種等待的人才知道她此時的心緒是多麼美好、多麼豐富而奇特。她實在是一個勇敢的人,在周圍的一片凝固的空氣裡,在一個板著沒有血色的面孔的世界裡,她不是表現了可嘉的勇氣麼?這勇氣誰給的她也不知道,大概是站在一邊的這個好棒的小夥子吧。
這個小夥子可不簡單。可這個小夥子的爺爺是地主。
當時他沒有上高中的權利。上高中的學生都是貧農和下中農推薦的。這個小夥子從小長得挺拔,像個運動員似的。人們以為他特別需要在農村裡鍛煉和改造,就讓他扛麥包、抬大筐什麼的。抬來扛去,他並沒有彎腰縮背,也沒有長成一個短粗胖子。他悄悄藏起了對這種勞動的厭煩和焦躁,質樸可愛。第三年,上高中可以推薦和考試相結合了,他幸運地上了學。
他做了學校運動員,穿著漂亮的運動衫。有一次他在一個運動會的比賽場上推鉛球,鉛球落下時,有個特別靈巧的女學生激動不安地走過去插了個小鐵旗子。女學生插下的這個小鐵旗子再也沒有誰超過,她很自豪。
後來他們一同畢業回村了。她穿了洗得發白的黃軍衣,也背了個同樣顏色的挎包。他看到她常常想:這樣的姑娘真不多見啊!
再後來他們就好起來了……
天色越來越暗淡了,霞光一束束從窗上收走。小織還是默默地坐在炕沿上。她突然說:
「李芒,咱走了多遠,怎麼一點也不累?」
李芒說:「我剛才還累,現在不累了。」
「半夜的時候,等著鬧鬼吧。」小織說。
李芒不答話。他找了截紅色的粉筆,在那個鎖起的門上劃了一個大大的×。他說:「把這個鬼槍斃了吧!」
小織笑了,笑得沒有聲音。
停了會兒她說:「今夜就睡在這兒嗎?」
「可不是就睡在這裡唄。」李芒咬了咬嘴唇。
小織流出了淚花。她說:「可是,可是……」
李芒想安慰他的新娘子,可是找不到合適的話。
小織一個人哭著,哭過之後更美麗了。她像個小孩子那樣大仰著臉兒看他。他看到了她那齊整整的一溜兒眼睫毛。她說:「李芒,你不知道我有多麼害怕……」
「誰不害怕?我也害怕,可是……」
李芒鼓勵著她。他這聲音若斷若續,表現了他那顫顫的幸福的心情。
天黑了。他們點起了一根蠟燭。
「這個大山裡的村子我以前想也沒想過……啊啊,……鬧鬼的屋子……啊啊……小織!你睡著了嗎?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