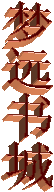
楊爭光 買媳婦
一
根蘭的肚子在後村人的眼皮底下一天一天往外鼓,鼓圓了。那天,村長天泰和
玉柱扛著纖繩從河灘上往回走。天泰不時瞄著玉柱,想和玉柱說幾句有關根蘭肚子
的話,硬是沒說成。因為玉柱的眼睛不和他對光。雖然玉柱的心思也在根蘭的肚子
上,可就是不和他對光。玉柱一直把頭仰在脖子上,看著遠處的天。人在得意的時
候就會這樣,眼睛看著遠處,自個兒和自個兒說話。到村口了,天泰的手在玉柱的
脖子上搧了一把。天泰說,瞧你那毬眉眼想和你說幾句話你瞧你那眉眼。玉柱縮了
一下脖子,眉眼一折,就把一臉的得意折成了笑,呵呵,呵,玉柱看著天泰。天泰
說,你甭給我笑你的喜也是咱後村人的喜根蘭撒腿的那天你可得意思意思。
玉柱臉上的笑沒了。
「咋?難道你想悄兒沒聲地讓根蘭給你下崽?沒個響動?」天泰說。
玉柱吭哧了半晌,臉憋紅了。
「要是,要是……」玉柱說。
「要是個毬!」天泰說。
「要是再生個……」
玉柱又憋住了。
天泰明白了玉柱的心思。根蘭生過一胎,沒落住,玉柱的心有些虛。可是,村
長天泰很快就緩過神來,找到了說辭。他把眉毛一擰,教訓了玉柱幾句。天泰說你
還是六尺男人!天泰說蛇咬了你一口連麻繩也怕了,難道說……咹?天泰覺得底下
的話不便說出口,就打住了。他看見玉柱緊閉著嘴唇,用力一吸,嘴唇像柳葉一樣
發出來一聲響。
「哎!哎!」有人朝這邊喊。是村長的婆娘。她總這麼叫村長天泰。天泰聽見
了,卻不回頭,依舊看著玉柱。難道咱不能往好處想?他說。
玉柱說嫂子叫你哩。
天泰說咱不能……咹?
嫂子叫你哩!玉柱說。天泰說聽見了,毬眉眼,去去,回去摸根蘭的肚子去。
玉柱要走。天泰說哎,問你話哩。玉柱又站住了。
「多少天了?」天泰說。
「不知道。」玉柱說。
「你扳著指頭算麼,」天泰說,「從種上那天起,二百八十天。這跟種莊稼一
樣,八九不離十。難道你不知道哪天種上的?」
玉柱說:」這又不是種莊稼眼睛瞅著往犁溝裡埋種子。」
天泰踩著腳說哎嗨!你真是個哎嗨!
玉柱說:「再哎嗨!也不能把這事和種莊稼混在一起,天天晚上都種,誰知道
是哪天晚上種上的。」
「你問根蘭嘛。」天泰說。
玉柱還是不懂。天泰的婆娘又喊了。天泰比玉柱年長幾歲,是種孩子的把式,
婆娘進門五年,下了四個崽。天泰說這事給你一時半會兒說不清,我婆娘又喊叫了,
去,摸根蘭的肚子去。
天泰聳聳肩膀,把纖繩挪挪好,走了。
根蘭是老梅從貴州領來的,和村長天泰的婆娘一樣,也是個漂亮女人。每天晚
上,玉柱都要摸根蘭的肚子。只有玉柱知道根蘭的肚子有多好。他感到根蘭肚子裡
的孩子不是一天天長大的,是他一天天摸大的。他躺在根蘭的臂彎裡,把一隻厚重
有力的手放在根蘭的肚子上,眼睛瞪著屋頂上的木椽,一聲不吭,像捂著一樣不小
心就會弄壞的東西。根蘭的肚子沒大的時候,他天天晚上騎她。他有使不完的力氣。
他愛聽根蘭在他的身子底下給他呻吟,難過得像一灘軟泥。他說根蘭你難受了?根
蘭說不,不,根蘭把他抱得更緊了。根蘭的臉像發燒的柿子。現在,他摸根蘭。根
蘭像一隻貓,安靜地躺著讓玉柱摸她。根蘭感到玉柱的手把一股溫熱的東西傳給了
她。根蘭說玉柱你天天這麼模咋就摸不夠。玉柱說唔唔我也不知道咋就摸不夠。根
蘭說我的肚子就這麼好?玉柱說我覺著好越摸越好不信你摸。玉柱拉過根蘭的手讓
根蘭摸。根蘭沒摸。根蘭把手抽走了。根蘭說我摸不出好來。玉柱說這就怪了我咋
摸咋好你咋就摸不出來?根蘭掩嘴笑了一下。根蘭笑的時候老愛掩嘴,其實根蘭的
嘴很好看。玉柱說也許自個兒的肚子自個兒摸不出好來要別人摸,女人的肚子要男
人摸才能摸出好來吧。根蘭說那你就摸,你覺著好我也就覺著好了。玉柱說根蘭快
了吧?根蘭說快了。玉柱說我聽天泰說能算來日子。根蘭說我心裡算著哩。玉柱說
狗日的天泰。根蘭說天泰咋啦?玉柱說不咋他幹活是能手養孩子也是能手,一種一
個准他狗日的。根蘭又要笑。玉柱說根蘭你這回……根蘭立刻捂住玉柱的嘴不讓玉
柱往下說。根蘭說你甭說本來我就害怕。玉柱說不怕不怕你生個雞蛋我也認。玉柱
想起天泰的話。玉柱說狗日的天泰教訓我讓我往好處想。根蘭說你看你人家天泰是
好心你罵人家。玉柱說我沒罵我是感激他狗日的。根蘭不再說什麼,把手放在玉柱
的手背上。就這麼,根蘭捂著玉柱的手,玉柱的手捂著根蘭的肚子,一直到他們睡
過去。
幾天以後,根蘭喊肚子疼。玉柱沒忘記天泰的話。他讓他哥金梁去找天泰。
「你就說咱給村上叫一場電影。」玉柱說。
金梁大玉柱五歲,是個光棍。他娶過一房,死了,所以成了光棍。玉柱比金梁
有主意。其實金梁也是個有主意的人,死了女人後有些蔫了,顯得沒主意,脾氣出
奇的好。
根蘭在裡屋的炕上一聲一聲叫喚。金梁說我找天泰你去叫二女。二女是個單身
女人,會接生。玉柱說根蘭你給咱堅持住我去叫二女。金梁和玉柱都從大門裡跑了
出去。根蘭咬著牙根,躺在炕上,眼睛瞪得像死魚一樣。
二
「玉柱想叫一場電影。」金梁給天泰說。
村長天泰正蹲在炕上,嚼白蘿蔔鹹菜吃粥。他把脖子一擰,說:撇腿了?根蘭
撇腿了?
金梁不好答話。
「噢噢,」天泰說,「你是他哥不能胡說走走到鎮上去。」
天泰叫了幾個船夫,和金梁一起去了鎮上。鎮上有一台放映機。
這時候,單身女人二女已經坐在了根蘭的炕上。手跟前放著水盆和剪臍帶用的
剪刀。根蘭撇著腿,挺著肚子,叫喚著,呻吟著。二女用毛巾擦著根蘭頭臉上滲出
的汗水珠子,教導著根蘭,讓根蘭鼓勁,用力。
「這是力氣活,根蘭,」二女說,「生娃沒有不出力使勁的。」二女說,「有
人生娃前要飽吃一頓,為的就是生娃的時候出力,你吃飯沒?」
根蘭使勁點頭。
「那你就得使勁,甭惜力氣。」二女說。
玉柱蹲在屋門外。二女不讓他進去。二女說生娃不是親嘴,用不著男人。玉柱
幾次想進去,因為根蘭的叫喚聲猛一下就很揪心,二女還是不讓。二女說你要進來
你就給接生。玉柱覺得二女的話比根蘭的叫喚聲更嚇人,就只好蹲在門外。他咬著
嘴唇,黑著臉,好像根蘭不是要給他生娃,而是在給他上吊。
根蘭整整叫喚了一天,硬是沒讓二女的水盆和剪刀派上用場。根蘭每叫喚一聲,
玉柱都想沖進去搧二女一個耳光,然後把手塞進根蘭的肚子,掏出那一塊遲遲不肯
出來的東西。當然他沒有沖進去,他只是想。他知道生娃和在雞窩裡掏雞蛋不一樣。
天麻黑了。金梁和天泰扛著絲繩從門外走進來。他們已經把放映機和放映員一
起放在了村委會的院子裡。他們朝緊閉的屋門看了一眼,挨玉柱蹲下來。他們知道
事情有些麻煩,沒和玉柱打招呼。玉柱像害牙疼一樣。金梁從耳朵背後取下一支卷
好的煙捲,遞給玉柱。玉柱沒接。金梁把煙捲叼在嘴裡,在衣袋裡摸火柴。天泰已
點著了煙,把火遞給金梁。金梁搖搖頭,繼續摸著,到底摸了出來,正要劃,屋裡
突然傳出一聲喊叫。三個男人立刻揚起脖子,朝屋門看去。
沒有嬰兒的哭聲。
很興奮。銀幕已掛起來。放映機支在人堆裡,旁邊豎著一根竹竿,吊著一隻電
燈泡。放映員是個年輕的小夥子,正在教光棍漢萬泉發電。萬泉把一截麻繩纏在發
電機輪子上,拉了幾次,沒成。萬泉並不氣餒,反而覺得好玩,一次次纏著,拉著。
孩子們等得沒耐心了,喊著:放!放!
「放你媽個腿!」萬泉說,「沒電咋放?再喊叫把你們扔到房上去。」
孩子們不吱聲了。他們都怕他。光棍萬泉娶不到媳婦,肚子裡有火,燥氣了會
真扔的。
「去,到玉柱家看去。」萬泉給孩子們說,「他婆娘一生,就立馬回來報告。」
一夥孩子們跑走了。萬泉又一次把麻繩纏上輪子,用力一拉,發電機響了。
竹竿上的電燈泡嘭一下亮了。
「咋樣?」萬泉一臉得意,看著放映員。
「關了先關了。」放映員說,「掏錢的人沒給話不能放。你先把繩子纏上,放
的時候再拉。」說著,就要關發電機。
萬泉不悅意了。萬泉說關了發電機燈泡就滅了。放映員說就是不讓燈泡亮才要
關燈泡亮著費電。萬泉說天黑成毬了你讓大夥兒亮亮堂堂的多好。放映員說看電影
又不是看大夥兒的臉要看臉叫我來做什麼關了關了。
幾個孩子從門外跑進來。
「生了?」萬泉問。
「生著哩。」孩子們說。
萬泉說你媽的腿我知道生著哩去去再看去讓她快點生。
孩子們說二女把擀麵杖都用上了在根蘭肚子上擀哩。
放映員說這事還麻纏關了關了。
又一夥孩子從門外跑進來說生了生了!
「你看,你關不成了。」萬泉給放映員說。
「關不成就放。」放映員說。
咋啦啦啦,放映機轉動起來,放映員說萬泉你往銀幕上看你看我做什麼電影又
不在我臉上。
電燈滅了,一道光束朝銀幕射過去。萬泉和滿院的人都像雁一樣伸長了脖子。
「關了關了!」有人失眉吊眼地喊著跑進院子。
是金梁。他撥開人堆,堵在了放映機前邊。
「關了!」金梁說。
放映員眨矇著眼。他沒關放映機,因為他省不過神來。放映機咋啦啦啦轉動著。
那束光全在金梁的胸脯上。「關了。」金梁說。
「為啥?」放映員說。
「孩子死了。」金梁說。
放映把眼睛大張了一下,又縮小了。他咽了一口唾沫,很為難的樣子。
「你看,你把錢都交了,不放咋辦?」放映員說。
金梁的胸膛上放著光芒。要不是他的胸膛,光芒就會在銀幕上放射。
「咋辦個毬。」天泰從人堆裡擠過來,嘭一下拉亮了電燈。「不放就不放了,
還咋辦?都回家睡覺去,聽見了沒有?」
滿院的人都站起來,提著椅子板凳往外走。萬泉屁股底下坐著一摞磚頭。他抬
起腳,朝它們踹過去。磚頭倒了。
「小心你狗日的腳腕子!」天泰沖萬泉罵了一句。「你婆娘生個死娃你放不放
電影?」他說。
「我要有婆娘我給村上唱大戲!」萬泉說。
「有一頭母豬給你,你回家躺在炕上等著去。」天泰說。
萬泉不敢回嘴,但萬泉的樣子很傲氣,手背起來,胸脯一挺,從大門裡走了出
去。
「毬眉眼。」天泰說。
放映員一直愣著。天泰說你還愣什麼把你這一攤子收了去。
當天晚上,金梁和玉柱在村外的野地裡挖了一個土坑,埋了死嬰。他們在那裡
蹲了很長時間。
「玉柱……」金梁說。
他想安慰他兄弟幾句,卻找不到合適的話,顯得比玉柱還熬煎。
「玉柱……」他說。
他這麼說了幾次。
後來,老梅就來了。
三
河水從深山大嶺中噴湧而出,到平緩的地帶後就變得溫和起來,不緊不慢地隨
山勢蜿蜒,向遠處流去。陽光照下來,給水波里弄出一塊塊閃光,也給河灘的沙石
裡揉進一層淡漠的紅色。
後村人除了種莊稼,也吃這條河。他們不撈魚。河裡沒魚。他們給山上送貨。
山頂上有座古塔,突然熱鬧起來,許多人去那裡燒香,還有許多人去那裡看風景。
後村人用船把貨從山後的河水裡運上去換錢。他們踩踏著河灘上的沙石,拖著木船
逆流而上。船上裝著食品和日用百貨。船夫都是青年男人。他們送完貨物點完錢之
後,有婆娘的就各口各家,沒婆娘的光棍們無處可去,就跟在村長天泰的屁股後頭,
到天泰家去吹牛聊天。他們不缺胳膊不少腿,誰知道咋弄的,就是找不到女人。沒
女人的男人一個人呆著太犧惶,也著急,所以,他們都去天泰家。
那些天,他們總說根蘭,說著說著,就說到他們自己了,然後就想起了老梅。
天泰的婆娘坐在炕上補衣服褲子。她有補不完的衣服褲子。她的臉上總有一種滿足
的笑。天泰也很滿足,蹲在炕沿上抽旱煙。他不太插嘴,只聽光棍們張嘴胡說。
是玉柱不會弄,還是根蘭不會生?兩個了,都是死的。他們想不通,所以,他
們每一次都從這兒說起。然後就有人反駁:娃在根蘭的肚子裡,根蘭撇腿生哩,咋
能怪玉柱叩B不能掂個臭嘴胡說吧。然後——
「我看也不全是胡說,老梅弄來的女人都是外地的,不保險。」有人這麼說。
萬泉也在。他瞄著天泰婆娘說:「咱嫂子也是老梅弄來的,咋生一個成一個?
難道是咱村長會弄?讓村長給玉柱教教。」
天泰婆娘說:臭嘴。依舊是滿臉笑。她不到三十歲,身段很好。她是老梅領來
的女人中最好看的一個。
「老梅狗日的眼裡有水哩,撿好的給村長。」有人說。
萬泉不同意。萬泉說老梅眼裡有水能看見漂亮不漂亮可老梅再能也不能看出會
不會生娃吧?
光棍們說那不一定,說不準老梅就有這眼力,母馬能不能下駒牲口販子一搭眼
就能看出,老梅弄這事多年沒這點眼力還能是老梅?讓村長說。
天泰不說,只是個笑。
呼啦啦,門外撞進來四個光葫蘆,一個比一個矮一點,清一色長牛牛的。他們
都是村長天泰的光榮。最高的一個挪過一條板凳站上去,把手伸進吊在屋樑上的饃
籠裡,抓出一個饅頭,又抓出一個,再一個,分給幾個兄弟,然後給自己抓了一個,
跳下板凳,又呼啦啦跑了出去。
光棍們正在想著老梅。他們突然想起,老梅好長時間沒來村上了。
「老梅咋這麼長時間不閃面了?」他們說。
「咋?都把錢攢夠了?」萬泉說,「錢夠了就在本地找嘛,明媒正娶,一不操
心跑,二不怕像根蘭一樣光生死娃。」
一個光棍撇撇嘴,說:「錢是屁股流油磨豆腐一樣一分分掙的,不是在路上撿
的。這賬我可算過了。找本地的女子,從訂婚到娶進門,至少也得這個數,」他用
指頭比劃出一個六,「六千塊。」他說,「從老梅手裡買,最多也就三千。」
其實,這筆賬光棍們都算過,所以,腰裡的錢差不多了,就會想起老梅。
「找本地的知根知底嘛。」萬泉說。
「買到屋裡過一段日子就知根知底了。」光棍們說。
「問村長,看他知不知嫂子的根底。」他們讓天泰說。
天泰還是個笑,不說。
幾天後,他們就知道了老梅進村的消息。他們送完貨收了船,從河灘上往回走,
二女把他們堵在了村口。
「老梅來了!」二女說。
他們愣了一下,有些不信。
「來了?」他們說。
「來了真來了。」二女說。
二女的臉上泛著紅色,像下完蛋的母雞。老梅每次來都住在二女家。老梅說二
女乾淨。也許他們還有別的事,要不老梅一來,二女就像吃了喜娃他媽的奶一樣,
連大腿上的肉也興奮得發顫。
「三個。」工女說。
光棍們「嗷」地叫了一聲,撒腿向村裡跑去。
「老地方。」二女沖著他們的背影說。
他們很快就看見了老梅,看見老梅領來的三個女人。
他們沒想到玉柱也會來。
四
老梅是獵戶,女人就是兔子。老梅是釣戶,女人就是魚。他總能打到兔子或者
釣到魚。他把她們弄到一起,然後再弄到後村,分配給這裡的光棍們。這就是老梅。
老梅知道什麼叫商品經濟。老梅說商品經濟就是做買賣。買啥賣啥?老梅說啥
賺錢買賣啥。在多的地方買,在缺的地方賣;在價錢低的地方買,在價錢高的地方
賣。這就是商品流通。
「我流通女人。」老梅說,「你們這兒缺這東西。」
就是就是,光棍們說,咱這地方啥也不缺就缺女人你多給咱流通些。
老梅說這事情越來越難做了。過去叫牽線紅娘現在叫人販子弄不好要坐班房。
光棍們說放娘的狗臭屁說這話的都是有女人的人讓他們打十年光棍看他們還說
不說。買媒人的就合法買人販子的就犯法了?媒人就近找人販子從遠地方弄就是個
遠近的不同啥是個遠啥是個近?一百里二百里?一百里以外犯法你就給咱在九十九
裡的地方弄。
當然當然,老梅說,讓緊箍咒箍住的話就不是老梅了。老梅吸了一口煙,又吐
出來,歪著頭,眯著眼,讓吐出的煙霧,從鼻子前邊一直飄浮上去。
這就是老梅。
這回,他弄來了三個。他給她們說找工作,先去煤礦做飯,然後做統計員。因
為她們裡邊有識字的。他們走了許多天,女人們不放心了,要回去,老梅的同伴就
變了臉。老梅有一個樣子很凶的同伴,是個青年男人,臉上有一塊刀疤。刀疤說誰
也走不成,領你們逛世界來了是不是?一路上坐火車汽車蹦蹦車還有住宿吃喝的花
費你們掏是不是?想回去就留一條腿,他說。老梅沒有變臉。老梅說別生氣別生氣
她們沒出過遠門想家了這也是人之常情對不對?女人們害怕了,給老梅直點頭。老
梅說就是嘛跑這麼遠的路哪能不工作就回去。老梅也有變臉的時候。老梅一變臉就
讓女人脫衣服,然後自己也脫。然後,老梅的同伴就會壓住女人,讓老梅和女人幹
那事。老梅也壓女人。老梅壓女人的時候,幹那事的就是刀疤。老梅覺著這麼弄女
人沒意思,他覺著二女好,所以他壓女人,讓刀疤弄。他把心情要留給二女。這也
是老梅。他知道怎麼能把女人的毛撫順,讓不聽話的聽話,讓聽話的更聽話。
二女說的老地方是她家的一間空房子。老梅和刀疤把女人們推進去,讓她們脫
掉長衫長褲,挨著牆壁站好,讓光棍們看。
「看吧,」老梅說,「看仔細些。」
蹲在另一面牆壁底下的光棍們立刻睜大了眼。
「高矮胖瘦臉面身材胸脯屁股胳膊和腿都在這兒了,」老梅說,「你們隨便看。」
現在,女人們已經明白了,後悔了,可是也來不及了。她們站在一排光棍們的
面前,努力收縮著自己,捂著臉,抽泣著。她們頭頂的牆面上,用白粉筆寫著她們
各自的價錢。年齡最小的一位,價錢最高,三千五。
「她叫小艾,」老梅說,「是縣城的高中畢業生。」
。光棍們開始盤算挑揀了。有的被價錢嚇了回去,決定不買了,就品頭論足。
「這麼高的價,是金子?還是銀子?」一個說。
「價高不一定實用。咱花錢買的是女人,不是繡花枕頭。」另一個說。
「我看三千五那個,也許是頭不會生養的騾子。」另一個說。
玉柱就是這時候走進來的。他輕輕推開門,蹲在一個光棍的跟前,給老梅點點
頭,然後,把目光放在了三個女人的身體上。
「你來弄啥?想買二房啊?」光棍說。
玉柱不吭聲,專心地審視著女人。
萬泉從始到終沒說一句話。他是光棍們裡邊看得最認真最細心的一個。經驗豐
富的老梅知道,這才是真正的買主。他笑吟吟走到萬泉跟前,掏出一根紙煙遞過去。
「萬泉,別把眼看花了。」他說。
光棍萬泉擋過老梅遞過來的紙煙,站起來,朝年齡大一點的女人走過去。女人
立刻把臉埋到了手裡。
「我是結了婚的人,」女人說著要哭了,「我有男人,有娃。我被人騙了。」
女人真哭了。
萬泉沒有詫異,也沒有生氣,好像沒聽見女人的話。他上下打量著,然後,把
女人撥過身去,又打量了一陣,然後退回來,看著女人,思量著。
「咋樣?」老梅說。
這回,萬泉接了老梅的紙煙,點著,吸了一口,噴出一股白煙。
「這個我要了。」萬泉說,聲音不大,卻擲地有聲。
「二千五的我要!」一個光棍喊了一聲,好像怕喊遲了別人會搶走。
老梅一臉得意,掃視著光棍們。
緊挨玉柱的光棍,用胳膊捅捅玉柱說:剩一個了,再不拿主意就遲了。
玉柱把下巴殼抵在搭起的胳膊上,思考著。
「錢不順手的,過幾天也行。」老梅說。
玉柱還在思考。
那天晚上,玉柱不停地翻身。他睡不著,好像被什麼難纏的事情糾纏住了。他
哥金梁早就睡實在了,鼾聲不時地往玉柱的耳朵裡鑽。他坐起來,在黑暗裡瞪著眼。
膨,燈亮了。根蘭也坐起來,給玉柱披上衣服,擔心地看著玉柱。她不知道玉
柱為什麼睡不著。她已經恢復了許多,額頭上綁著一塊紅布,怕受風。
「咋啦?」她說。
玉柱愣著眼,一動不動。
根蘭摸摸玉柱的額頭,不燒。
「喝水不?我給你倒水去。」根蘭說。
玉柱皺皺眉頭,很煩躁的樣子。根蘭不敢再問。玉柱又躺下了。根蘭給玉柱掖
好被子,關了燈。她沒躺在被窩。她側著身,用手支著頭,在黑暗裡看著她男人。
玉柱又翻了幾次身。根蘭在心裡歎了一口氣,無可奈何地縮進了被窩。她實在太困
了。
第二天清早,玉柱穿好衣服,勾上鞋,又去了一趟二女家。他好長時間沒有開
口說話。他坐在炕沿上,仔細地卷著煙捲,好像不是來說事情,而是來捲煙卷的。
老梅也不開口。他抽著紙煙,耐心地等待著。
玉柱到底卷好了那支煙捲。他掐了紙頭,卻並不點燃,歪過頭,定定地看著老
梅。
老梅剛吐出一口煙。煙霧彌漫了老梅的臉。
「你抹下來一千,我立馬交錢領人。」玉柱說。
老梅在煙霧裡思量著。
「行不行你給句話。」玉柱說。
啪啦一聲,老梅把半截紙煙扔在了地上。
「就這了,你取錢去。」老梅說。
天大的事情,一下決心就簡單了。就這麼,玉柱買走了小艾,年齡最小的那個。
「縣城的高中畢業生。」老梅說。
五
劈哩啪啦。玉柱用竹竿挑著一串鞭炮,挑得老高,炸出一團團五顏六色的紙花。
金梁穿著一身新衣服,站在他弟玉柱的身後,笑著,說不清是羞澀,還是幸福。幾
個孩子撿拾著落地未響的爆竹。另幾個孩子在遠處朝金梁喊叫。
「金梁,圓房。金梁,娶媳婦。」
玉柱把竹竿朝孩子們掄過去。孩子們跳開去,又轉過身,齊聲喊著。
金梁只是個笑。
玉柱一直沒給金梁說買女人的事。玉柱把小艾從二女家領回來的時候,金梁直
眨矇眼。玉柱把小艾交給根蘭,然後說:「哥你別眨眼,你來,我有話和你說。」
金梁還在眨眼。玉柱把金梁拉進屋。
「咋樣?」玉柱一臉笑,問他哥。
「啥咋樣?我不懂你的話。」金梁說。
「女人,你看那個女人咋樣?」玉柱說。
金梁還是不懂。
「我把她買了。」玉柱說。
金梁更不懂了。
「二千五,從老梅手裡買的。」玉柱說,依然是一臉的笑。
「再把她賣出去,是不是?」金梁不高興了,以為玉柱想當二道販子。
「你咋就不明白?咱家缺個女人,你咋就不明白?」玉柱說。
「噢噢,」金梁明白了,「你是給我買的?」
「咋樣?」玉柱說。
「不咋樣。」金梁說。
這回,該玉柱不明白了,急了。
「縣城的中學畢業生,老梅親口說的。」玉柱一著急,說話就像打槍一樣,
「人剛才你見了,不咋樣?」
「嗨嗨!」金梁跺了一下腳,「我不是說人不好。我還能談嫌人?我是說,這
麼大的事,你該和我商量商量。」
「噢噢,」玉柱有些放心了,「現在和你商量也不遲。」他說,「你總不能一
輩子不要女人吧?」
「是啊是啊。」金梁說。
「那還有啥商量的?錢我已經交了,人你也不談嫌,還有啥商量的。」
「你看你,你讓我把話說完嘛。」金梁說。
「不商量了。」玉柱說,「根蘭給你把屋子收拾收拾,明天就辦事。」
玉柱走了。
金梁抱著頭,在地上蹲了很長時間。他感到事情有些突然,然後,就為他兄弟
的用心感動。玉柱啊玉柱,他在心裡說,你哥咋能一輩子不要女人呢。他像吃了一
塊熱豆腐,熱乎乎要流出眼淚來了。
那天晚上,他們兄弟倆說了半夜話。他們感到他們比世界上所有的兄弟都親。
「一定得保住這女人。」玉柱給他哥說。
「讓根蘭好好養身子。」金梁給他弟說。
「得放一串鞭炮。」玉柱說。
「你說放就放。」金梁說。
劈哩啪啦,鞭炮放響了,響得村莊好像要跳起來一樣。那時候不是清晨,而是
黃昏。他們兄弟倆商量好了,爆竹一放完,金梁就進屋,和女人圓房。
金梁的屋子已經收拾過了。根蘭拿著幾件新衣服讓小艾換,小艾不換。小艾坐
在炕上。根蘭的屁股擔著炕沿。
「咋說也是個喜慶的事,換件新衣服,圖個吉利。」根蘭說。她把同樣的話已
說過許多遍了。
小艾一聲不吭。
「是女人,遲早都得過這一關。」根蘭說。
爆竹放完了。玉柱和金梁關了大門。
「根蘭!」玉柱朝屋裡吼了一聲。
「哎。」根蘭應了一聲。
「出來!」玉柱說。
根蘭對小艾說:以後就是一家人了,我該叫你嫂子。
「根蘭!」玉柱又吼了。
「來了來了。」根蘭說。根蘭把手裡的新衣服放在小艾跟前,對小艾笑笑,說:
「我走了。」
根蘭剛一出屋,玉柱就把站在門口的金梁推進去,咣啷一聲,拉上門,拴上了
門栓,又掏出一把鎖,哢嘣一聲,鎖上了,然後轉過身,對根蘭說。回去。
根蘭看著上了鎖的屋門,很不放心。玉柱不耐順了,一把抓住根蘭的胳膊,朝
他們的屋裡拽去。
玉柱一直把根蘭拽到炕跟前,一用力,根蘭順勢就坐在了炕上。玉柱返身關了
屋門。
「你看你。」根蘭伸著手腕讓玉柱看。她的手腕讓玉柱抓疼了。
「誰讓你磨蹭。」玉柱說。
「我擔心金梁哥……」
「有啥擔心的?脫你的衣服。」玉柱說。
「聽聽嘛,聽聽金梁哥他們。」根蘭說。
「聽啥?能扳倒她就成了。脫。」玉柱說。
「啥話也能慢慢說,聽你的聲,開飛機一樣。」根蘭親呢地白了玉柱一眼,開
始解衣扣。
玉柱已脫光了。
「真是個二楞。」根蘭說。
根蘭的衣服還沒脫完,玉柱已等不及了。他扳倒了她。她澳地叫了一聲,抱緊
了玉柱。他們拉滅了燈,糾纏在一起。他們都很投人。玉柱拱著根蘭的身子,喘著
氣。根蘭輕輕呻喚著,讓玉柱拱。
「啊!」玉柱叫了一聲。
「哦!」根蘭也叫了一聲。
他們就躺平了。他們張著眼,喘了一會兒氣,然後就豎著耳朵,聽金梁屋裡的
動靜。玉柱的一隻手放在根蘭的肚子上。他們一聲不吭。
六
金梁沒有扳倒小艾,那個縣城的高中畢業生。
小艾的媽媽是縣衛生局的副局長,是那種精明能幹又厲害的女人。她爸在一所
中學教音樂,會拉手風琴,並有一副嘹亮的嗓門。可在精明又厲害的女人跟前,他
就成了窩囊的男人。小艾討厭她媽的精明,也瞧不起她爸的窩囊。她媽說小艾你考
衛校。小艾說我為什麼非要考衛校。她媽說你考大學考不上考其它學校我說不上話。
小艾說我的事為什麼非要你說上話。她盯著副局長。副局長端著磁化杯正在喝水,
不喝了。她把磁化杯嘭一聲放在茶几上,扭過頭對廚房裡的音樂教師說:把你那東
西給我停了。音樂教師正在拉《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他總愛拉那首歌,一邊走一
邊拉,拉到了廚房去了。
停了!副局長說。
手風琴不響了。音樂教師走出廚房,卸著手風琴。怎麼啦怎麼啦我剛拉出點味
道這不是你愛聽的歌嗎?音樂教師的笑臉幾乎要挨著副局長冷峻的鼻子了。
小艾越來越不像話了非要跟我對著幹,副局長說。
音樂教師說小艾你不能跟你媽對著幹對著幹對你沒好處。小艾說我沒想和誰對
著幹我討厭你們這麼一唱一合的口氣!小艾出門走了。副局長也是精明的女人,和
音樂教師也是窩囊的男人倆口子對瞪著眼,對瞪了好長時間。他們想不到小艾會出
遠門。他們想她吃晚飯的時候就會回來。
小艾沒回來,小艾出了家屬院,拐進了巷子,從她家樓前過的時候,她聽到了
音樂教師的手風琴聲,還是那首《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小艾感到噁心,就一直往
前走,一直走到了汽車站。後來,就碰上了老梅。
現在,她坐在了金梁的炕上。她順著眼,燈光把她的身子投在牆壁上,拖成一
團巨大的陰影。根蘭給牆上貼了幾張畫,使這間屋子透露出一些新房的氣氛。
金梁不是玉柱。他沒有硬扳。他想女人要是願意,你不扳她自己就會倒,女人
不願意,你就是硬把她扳倒,也弄不成事,所以他沒硬扳。他倒了一盆熱水,放在
炕跟前,看著小艾。
「你洗洗。」金梁說,「你們念書人講衛生。」
小艾沒想到,金梁會這麼慢聲慢氣地和她說話,慢聲慢氣中還有一種關切。她
抬起臉,看著金梁。
金梁一臉誠懇,迎著小艾的目光。
洗就洗。小艾這麼一想,就抬腿下炕了,端過臉盆去洗臉。她也實在該洗一次
臉了。走了上千里路,洗臉是有次數的。
金梁坐在炕沿上,看著小艾洗臉,心裡突然湧動起一種溫熱的情感。他的屋子
裡有一個女人在洗臉。他看著她。就這麼,他的心裡湧動起一種溫熱的情感。
小艾洗完臉,端著臉盆想出門倒水,拉拉門,這才想起門被反鎖了。金梁也想
起來玉柱把門鎖了,剛才看小艾洗臉,心裡忽兒忽兒的,就忘了鎖門的事。他跳下
炕沿,接過臉盆,給小艾笑了一下,笑得很不好意思。
「我來。」金梁說。
金梁順著門坎,往外倒臉盆裡的水。小艾走到衣櫃跟前,對著鏡子梳理頭髮。
衣櫃上嵌著一塊玻璃鏡。金梁倒完水,轉身來,小艾已坐在炕上,紮好頭髮了。她
看著金梁,洗過的那張臉像杏一樣,看著想吃,吃著又覺得可惜。
金梁的心格噎響了一聲。
小艾又順下眼去。她聽見金梁一步一步朝炕跟前走。走到跟前了,坐在炕沿上
了。
啪啦,一隻鞋掉到了地上。
啪啦,又一隻。
金梁要轉身上炕。小艾突然失聲叫起來。
「別上來!」小艾揚起頭來,叫了一聲。羞憤和驚慌,使那張杏一樣的臉變成
了一枚柿子,紅得要噴發出血來。
金梁被嚇了一跳,愣了,一動不動地看著小艾。
「你別……」小艾要哭了一樣。「你別碰我。」她說,「我才十七歲,我是被
老梅騙來的,他說他給我找工作,他騙了我,我要走,我不會給你當媳婦。」
金梁不知該怎麼辦了。
「你下去。」小艾說。
「你不能讓我在地上呆一夜吧?」金梁說。
「你下去。」小艾說;
「我不動你,不行?」金梁說。
「我害怕。」小艾說。
金梁搖搖頭,在地上找鞋。
「好,我下去。」金梁說。
金梁倒了一茶缸開水,順衣櫃靠著。
「你睡。」金梁說。
「我不睡。」小艾說。她心裡寬鬆了一些。
「我喝水,你睡。」金梁說。
金梁喝了一口,水太燙。金梁吹了幾口氣,又喝。
小艾拿過根蘭送給她的衣服,嘶一聲,撕成了兩半。金梁不喝水了,看著小艾。
小艾繼續撕著,把衣服撕成布條,然後用布條紮褲腰和褲腿。金梁感到他的心打顫
了。他趕緊喝了一口水。小艾紮好褲腰和褲腿,又順著眼,坐在炕上一動不動了。
金梁心裡很焦渴,一口一口喝著,喝完了茶缸裡的水,還在喝,喝著茶缸裡的空氣。
突然,他不喝了。他的眼睛盯在了牆角的一口瓷甕上。
「小艾。」金梁說。
小艾受了一驚,揚起頭。
「你睡不著,是不?」金梁說。
「我不睡。」小艾說。
「我給你頂缸。」金梁說。
小艾不懂金梁的話。金梁說你見過要雜技的頂缸沒?我給你頂缸。說著,就放
下茶缸,朝那口瓷甕走過去。瓷甕裡有幾條麻袋。金梁把麻袋取出來,抓住瓷甕一
用力,嘿一聲,瓷甕沿兒就落在了金梁的頭頂上。金梁伸開胳膊,搖擺著身子,努
力平衡著,不讓瓷甕掉下來。他齜牙咧嘴,滿臉漲紅,大張著眼,想看頭頂上的瓷
甕,又想看小艾。
小艾被金梁的舉動驚呆了。
金梁很想笑一下,可頭上的瓷甕顫悠悠晃動著,不讓他分心。金梁說小艾你看
我有的是力氣我沒地方使我給你頂缸耍。金梁說這話時,眼眶裡溢滿了淚水。本來
他想笑,不知為什麼溢出了眼淚。
「小艾你看,你往我這兒看。」金梁說。
金梁又用了一下力,嘿一聲,瓷甕蕩起來,轉了一下,又落下來。金梁用頭去
接,想接往另一邊的甕沿兒。
他沒有接住。瓷甕結結實實地從金梁的頭頂上扣了下去,扣住了金梁。
小艾抱住頭叫了一聲,不敢往過看。她想金梁會被瓷甕砸死的。
沒有。金梁被砸暈了一會兒。沒多長時間,他就從瓷甕裡爬了出來,又靠著瓷
甕蹲下去。
他睡著了。
七
玉柱把鑰匙塞進鎖孔,打開鎖,取下門栓。門被拉開了,金梁從屋裡走出來。
他睜了一下眼,陽光猛烈地刺進他的眼睛。他擠擠眼,朝茅廁走去。昨晚上喝進肚
子的水,全變成尿水了。玉柱又拉上門,掛上門栓,要鎖。根蘭說不鎖了,我和金
梁哥都在家裡,還看不住一個女子。玉柱就不再鎖門,把門鎖裝在了衣兜裡。
金梁從茅廁出來了。
「你不去河上了。」玉柱給他哥說,「你給咱鑿個石臼,砸辣面子調料面子用。」
金梁看著玉柱,有些意外。
「石頭我找好了。」玉柱說。
院子裡真有一塊石頭,上邊放一把鐵錘,一把鐵鑿子。
「人跑了,錢就白扔了。」玉柱說。
「噢噢。」金梁說。
玉柱去了河灘。金梁就坐在院子裡,鑿那塊石頭。根蘭給小艾端了一盆洗臉水,
然後掃院子。掃完院,小艾也梳洗過了,根蘭就拉小艾去廚房做飯。根蘭淘米,小
艾燒火。小艾不會拉風箱,很彆扭。根蘭說拉幾次就好了。她往爐膛裡添了一把硬
柴。
小艾很快就拉得順手了。她從來沒拉過風箱,覺得很新鮮。根蘭給她說很多村
上的事情。根蘭說的事情也很新鮮。根蘭說這村上有許多外地女人。光棍們一有錢,
就想媳婦。他們都願意從老梅手裡買。村長的婆娘也是從老梅手裡買的。我也是。
根蘭說,我娘家在貴州,被人騙出來,經老梅跟了玉柱。
「我跑過幾次,都給抓回來了。」她說,「後來我就不跑了,就認了。我跑啥
呢?女人嫁給誰不是一輩子?在爹媽也是賣,和老梅賣有啥兩樣?這麼一想,我就
安心了,也覺著玉柱是個好男人了。」她說,「玉柱脾氣不好,不如金梁哥。女人
能攤上個好脾氣的男人,也是福氣。我現在啥也不想了,就想著給玉柱生個孩子。」
根蘭像在講別人的事情一樣。
「我命苦,生了兩胎,都失了。」根蘭說。她說這話的時候,眼圈兒好像紅了
一下。也許是水蒸氣撲了眼。水開了,她揭開鍋,吹著升騰的蒸氣。
「水開了待會兒再燒。」她說。
小艾停了風箱。根蘭灌了兩壺開水,然後往鍋裡搭米。小艾覺得根蘭很能幹,
人也好。
能聽見金梁在院子裡鑿石頭的聲音。其實金梁人也不壞。小艾這麼一想,就偏
過頭,想看一眼院子裡的金梁。金梁在前邊院子的牆根底下,在灶窩裡偏偏頭是看
不見的。
金梁一下一下鑿著那塊石頭,很認真的樣子。其實,他的心思不全在石頭上。
他想著昨天晚上的事。他感到有些窩囊。他想他不頂缸就好了。他想他就該上炕,
把小艾紮褲腰褲腿的布條撕了,然後再撕她的衣服。小艾就是喊叫起來,也不要緊。
小艾的喊叫就是讓全村的人聽見,也不要緊。我又沒撕別人的衣服,我撕我的女人
的衣服與別人毬不相干。我要能撕掉她的衣服就好了。我抓她的奶奶。我怎麼也能
抓她的奶奶吧?你要真抓住了女人的奶子,撕了她的衣服,情況也許就會是另一個
樣子。金梁一邊鑿著,一邊這麼想。他越想越後悔,恨不能讓時間倒回去,倒回到
昨天晚上去。
萬泉就是這個時候蹲到金梁跟前的。
萬泉輕輕推開頭門,閃進來,又輕輕合上門,蹲到了金梁跟前。他朝廚房那裡
看了一眼,一臉神秘的表情。
「咋樣?」萬泉問金梁。
金梁沒吭氣。
「昨晚上,咋樣?」萬泉又問了一聲。
金梁還沒吭氣。他不會給萬泉撒謊,可他也不會給萬泉說他頂缸的事。所以,
他不吭聲。
「沒成?」萬泉說。
金梁有些噁心,想用手裡的鐵錘敲萬泉的頭。
「你是咋弄的嘛!」萬泉說,「給她個下馬威嘛。」他說,「我那個女人也是,
咋說也不願意,我就給了她一個下馬威。我說今晚死都成,不讓睡,萬萬不成。我
說完就把她壓倒了。」
金梁一下一下鑿著。
「女人一到男人身子底下,就不由自己了。」萬泉說。
「不信你照我說的試試。」萬泉又說,「萬事開頭難,頭一開,往後就順溜了。
就看你能不能橫下心。」
金梁不鑿石頭了。可金梁也沒看萬泉。他看著那塊石頭。萬泉以為他的話起了
作用,直來精神。
「你是有過女人的人嘛,是不是看她嫩,可惜?再嫩也是女人嘛。放到炕上的
女人還睡不了,算毬啥男人!」萬泉說。
金梁把手裡的鑿子在石頭上敲了一下。萬泉這才看見金梁的臉色有些不對。
「我說錯了?」萬泉說,「難道我說錯了?」
金梁開口了。金梁說你再胡說我就敲你狗日的。
「你看你看,我教你成事你還是這態度。我胡說了?難道我胡說了?」萬泉說。
「出去!」金梁說。
萬泉有些害怕,站起來。看著金梁。
「這熊是不是病了。」他說。
「滾!」金梁吼了一聲。
萬泉跳開了,然後往大門跟前退。他很擔心金梁手裡的鐵鑿子,也許金梁會把
它朝他的頭甩過來。
「這熊病了。」萬泉咕嚕了一句,從大門裡跳了出去。
金梁舉起鑿子,朝石頭狠狠地摔下去。鐵鑿子發出一聲脆響,彈起來,蹦出去
老遠。根蘭和小艾聽見響聲,跑出廚房,看著金梁,不知他怎麼了。
幾天後,金梁就給了小艾一個下馬威,然後,和玉柱打了一架。
八
小艾不和金梁睡,金梁一點辦法也沒有。小艾和根蘭一起掃院,一起做飯,甚
至臉上也有了一點兒笑,可一到晚上,就紮褲腰褲腿,並且全紮成死結,看得金梁
真想大哭一場。
「哥,你就真拿她沒辦法了?你就不能來點硬的?」玉柱朝他哥這麼吼著。他
比他哥還著急。
「繩呢?刀呢?你就不能用上一樣!」玉柱喊著。
那天晚上,金梁把繩和刀都甩在了櫃蓋上。
咣啷一聲。是鑿石頭的那把鑿子。
小艾正在紮褲腿。褲腰已紮好了。她停住手,抬頭看著金梁。金梁一臉鐵青,
像一頭準備咬人的獅子。小艾的手從腳腕上邊鬆開來,目光慌亂了。
「金梁叔……」小艾膽怯地叫了一聲。
「誰是你叔?」金梁的眼睛裡要進出血來,咆哮了,「我是你男人!聽見了沒?
男人!」
小艾的身子立刻縮小了,打著抖。
「脫衣服還是死,你選一樣。」金梁說。
小艾把身子縮得更小了,像一隻恐懼的羊羔。
「脫!」金梁說。
小艾害怕地搖搖頭。
「脫!」金梁聲嘶力竭地喊了一聲,喊出了滿肚子的羞憤和酸楚,淚水立刻模
糊了他的眼眶。
金梁怎麼也沒想到,他這麼一喊,把小艾從恐懼中驚醒過來了。小艾的身子慢
慢鬆開來,眼睛裡射出一種堅定的目光,盯著金梁。
「我不願意死。」小艾說,「也不願給你做女人。你實在要我死,你就把我殺
了。」她說。
金梁愣了,眼裡的淚水又滲了回去。
「你殺吧。」小艾說。
他們互相盯著,一動也不動。金梁感到身子裡聚集起來的氣力正在一點一點消
退,骨頭正一點一點變軟。
蹲在院子裡的玉柱跳了起來。他一直蹲在院子裡,聽著屋裡的動靜。
「窩囊廢!」他叫了一聲。
屋裡悄無聲息。
玉柱提起一條木凳,朝屋裡砸過去。
「窩囊廢!」他又叫了一聲。
他跑到門跟前,使勁踢了兩腳,又抓住門栓搖著。他急了。
「金梁!」他叫著他哥的名字,「你炕上的女人是用咱的血汗錢買來的!」
根蘭跑過去,拼力拉走了玉柱。
「金梁!」玉柱還在叫。
咣當一聲,根蘭把他們的屋門關上了。
「玉柱你別這麼,哥的事讓哥慢慢辦。」根蘭給玉柱說。她把玉柱推到炕上,
給玉柱解著紐扣。「快睡快睡,」根蘭說,「我的熱身子還堵不住你的嘴。」
這時候,金梁身子裡的力氣已經泄盡了。他蹲在牆根底下,兩眼瞪著一個地方,
好像在發呆。坐在炕上的小艾仰著頭,看著牆上的畫兒,不知想著什麼。
金梁好像咕嚕了一句什麼。
小艾扭過頭,看著金梁。
「你走吧。」金梁說。他不看小艾,話音輕,卻很清楚。
小艾實在不敢相信,金梁會說這樣的話。
「我沒養女人的命。」金梁像給自己說話一樣,「我娶過一房媳婦,死了。玉
柱看我孤單,就花錢,買了你。都怪我糊塗。你走吧。」他說。
金梁說得很痛苦,也很誠懇。小艾反而不知該說什麼了。她支吾了好大一陣。
「我,我讓我爸媽還錢給你。」她終於想到了一句合適的話,「你要信不過,
我就寫封信去,讓我爸媽拿錢來領我。」
「錢不是你爸媽拿的,憑啥讓你爸媽還?我認了。」金梁說。
「那,那你就人財兩空了。」小艾說。
「你這個樣,硬不讓你走,我比人財兩空還難受。」金梁說。
「金梁叔,你是好人。」小艾說。
「狗屁。」金梁說,「我不願當這種好人,是你逼著讓我當。你別叫我叔,叫
得我心口疼。」
小艾想不通,金梁為什麼說是她逼他當好人的,可她不敢多說,她怕金梁突然
又變了主意。
金梁沒變主意。第二天半夜,他輕輕抬開一扇門,把小艾領出去,朝縣城方向
走了。到縣城汽車站,天還沒亮,小艾就靠在候車室的長木椅上睡了。金梁蹲在賣
票的窗口下打盹,到賣票的時候,他就會站起來,第一個買票。
他沒想到會出什麼意外,卻偏偏出了。沒等他把話說出口,玉柱的拳頭,就重
重地砸在了他的臉上。他攥著車票和找的錢,從人堆裡擠出來,想搖醒睡在長木椅
上的小艾,就看見玉柱領著一夥人,從外邊湧進來。他的頭裡邊「嗡」地響了一聲,
身子站直了。小艾正揉著眼。玉柱和那夥人圍了上來。小艾清醒了,想把身子縮在
金梁背後。
「拉上去!」玉柱說。
那夥人把小艾拉到了車站門口的手扶拖拉機上。
「你……」金梁張著嘴,話沒出口,玉柱的拳頭就掄起來,照直朝金梁的臉砸
過去。金梁聽見鏘的一聲,立刻感到了一陣辛辣。他呻吟了一聲,險些倒下去。他
又張張嘴。鏘!又一聲。玉柱的那只拳頭又一次擊中了他的臉。他叫了一聲,栽倒
了。玉柱並不罷手,他拳腳相加,在金梁的身上踢打著。他不說一句話,只是瘋狂
地踢打著。
金梁沒有反抗。玉柱不知走了多長時間了,他才慢慢爬起來,搖晃著朝車站外
走去,沾在身上的塵土紛紛跌落著。他走到一家飯館裡買了一盆水。飯館的人問他
吃不吃飯。他說我先洗臉。他洗了臉,飯館的人問他吃不吃。他說吃。飯館的人說
早說吃飯就不要水錢了。他說要吧你要吧無所謂現在你給我上飯菜。飯館的人說要
酒不?
「要。」他說。
晚上,他搖晃著回來了。他從玉柱手裡要過屋門上的鑰匙,打開鎖。他抬起腳,
朝門扇踢過去。門栓「嘩啦啦」掉了。他橫進去,關上了門,然後,屋裡就傳出來
小艾的叫喊聲和激烈的廝打聲。
他強暴了她。
小艾平展展躺在炕上,眼睛大張著,看著屋頂。
「金梁,你把我毀了。」她說。
金梁歪倒在一邊,打著呼嚕,嘴角上掛著笑。
然後就到了冬天,下了一場大雪。
九
大雪下得無聲無息,停得也無聲無息。山啦,河岸啦,村莊啦,雪把一切都變
成了一種顏色。雪剛停,孩子們就在村外的野地裡打雪仗了。能看見他們追逐著扔
雪團,也能看見雪團打在他們的身上碰開的樣子,可聽不見他們打鬧的聲音。他們
的打鬧聲,被鬆軟的雪吸收了。天氣很寒冷,但寒冷中有一種安祥。
玉柱搶著斧頭,潛心地劈著一截樹樁。
院子的雪已經掃過了。根蘭用鐵鍁攢著散雪。小艾把雪堆堆成了一個雪人。她
想讓它更好看一些,便用凍紅的手指頭,在雪人的眉眼上摳著,摳幾下,退兩步看
看,呵呵手指頭,走過去再摳,然後,從雪人頭上取下早已做好的鼻子,安上去。
她做得很投人。
金梁推著一個大水桶從大門外走進來,用小木桶把大水桶裡的水往廚房裡的水
缸裡倒。
「哥,我把打井的找好了。」玉柱給金梁說。
「唔,哪兒的?」金梁說。
「官村的社會。」玉柱說。
「噢噢。」金梁說。
「價錢也說好了,」玉柱說,「一口井二十八塊錢。人明天就來。」
「哄哄。」金梁說。
聽他們這麼說話,看院子裡的情景,不知底細的,會以為這是一個美滿和睦的
家庭。
街上突然響起一陣雜亂的腳步聲。
「抓回來了!」有人喊著。
根蘭和小艾支楞著耳朵,聽著街的上動靜。
「萬泉媳婦昨晚上跑了。」金梁說。
有人慌慌失失沖進門說:「萬泉媳婦被抓回來了,給褲襠裡灌涼水哩!」說完,
又慌慌失失跑了。小艾還沒反應過來,根蘭已抓住了小艾的手。
「看去看去。」根蘭說。
金梁想阻攔,根蘭已拉著小艾出門了。他不放心地看了玉柱一眼。玉柱說去嘛。
金梁放下木桶跟了出去。
萬泉家的院子裡圍滿了人,積雪被踩踏得不堪入目。人們臉上的表情比看電影
還強烈。萬泉媳婦被圍在中間,又羞又怕,面如死灰。她的褲腿已被紮住了。萬泉
提來一桶涼水,放在女人跟前,伸手要解女人的褲帶。女人躲閃了一下,擋著萬泉
伸過來的手,一臉乞求。
啪啪!兩聲清脆的耳光偏上了女人的臉。女人痛苦地捂著被搧過的地方,不再
躲閃了。
萬泉很容易地解開了女人的褲帶。他舀起一勺涼水,朝女人的褲襠裡灌下去。
女人不禁涼水猛烈地刺激,叫了一聲,身子立刻挺直了,烏青的嘴唇顫抖起來。
嘩,又一勺。
「活該!」有人說。
「給她灌出點記性來。」有人說。
萬泉一語不發,在桶裡舀著涼水。
嘩。涼水往女人的褲襠裡繼續灌著。
「她跟你是不是一個地方的?」根蘭問小艾。
「不是,」小艾說,「半路上聚在一塊的。」
「就說麼,說話不一個口音。」根蘭說。
女人滿臉烏青了,渾身打抖,隨時都會栽倒。
「咱走吧。」小艾捅捅根蘭。
「咋啦?」根蘭問小艾。
「不咋。」小艾說。
「看會兒,再看會兒。」根蘭說。
她們又看了一會兒。
那天晚上,金梁脫衣服睡覺的時候,看見小艾坐在炕上發愣,以為小艾還想著
萬泉媳婦的事。金梁說別想了萬泉狗日就不是個人。小艾好像沒聽見金梁的話。金
梁說睡吧,明天打井的要來打了井吃水就方便了。說著,就鑽進自個兒的被窩裡先
睡了。他們睡一個炕,但不睡一個被窩。除了那一次,金梁再沒動過小艾。他甚至
有些後侮,儘管小艾沒對他說過一句怨恨的話,可他還是有些後悔。小艾好像什麼
事情也沒發生過一樣,和根蘭一起做飯掃院,也收拾屋子,給金梁端洗臉水,有時
還和根蘭說幾句笑話,讓金梁看著心裡暖乎乎的。可是,一上炕,小艾就紮褲腰和
褲腿。這時候,金梁的心就像貓爪子在抓一樣難受。小艾就這麼讓金梁一忽兒暖乎
乎一忽兒像貓抓一樣。
以後的幾天裡,金梁沒鑿石頭,他幫著打井的匠人社會打井。根蘭小艾合夥做
飯。玉柱在河灘上修船,送貨的船壞了。玉柱中午不回家,讓根蘭給他送飯。
事情就出在送飯上。
打井的社會是個怪人,二十五六歲的樣子,剃著光頭。冬天也剃光頭。我這人
火氣大,他說。他有一台黑白電視機,到哪兒打井就把它背到哪兒。從井裡上來,
渾身都是泥土,卻不急著收拾,先去開那台電視,然後才洗臉洗手。我愛看新聞,
他給根蘭和小艾這麼說。根蘭說大白天哪有新聞讓你看。她嫌浪費電,要關。社會
不讓。
等會兒等會兒也許一會兒就有了,他說。他一邊吃飯,一邊固執地瞅著電視機。
這時候,根蘭就該給玉柱送飯了。
「你們吃,我給玉柱送飯去。」根蘭說。
根蘭送了兩天。第三天中午,根蘭剛說完你們吃我給玉柱送飯去,小艾就放下
飯碗說,我也去。根蘭有些為難,卻不好拒絕,就看了金梁一眼。小艾知道他們不
放心她,就端起飯碗,沒再說話。根蘭更為難了。
「去吧!想去就一起去。」金梁說。
小艾覺得很沒意思,說她不去了。根蘭很尷尬,拉起小艾說,不是我不想領你
去我怕金梁哥捨不得讓你出門走走金梁發話了咱就走。根蘭硬拉著小艾走了。
沒出什麼事。小艾和根蘭一起去,又一起回來了。金梁放心了,也有些羞愧,
然後,就有些激動了。他借了一輛自行車,騎了幾十裡地,到鎮上的商店裡買了幾
盒方便面和一瓶罐頭,晚上,把它們一樣一樣掏出來,放在櫃蓋上,讓小艾吃。
「你吃不慣這兒的飯,你調調胃口。」他給坐在炕上的小艾這麼說。
然後,又掏出來兩本書,和那幾樣東西放在一起。
「我跟小學校的老師要了幾本書。你是念書人,心煩了就念念。」他說。
小艾朝那兩本書瞄了一眼,想笑,又繃住了嘴。
那是兩冊小學二年級的課本。
「這地方偏僻,沒幾個念書的人。」金梁說。
金梁上炕了,小艾卻沒像往常一樣紮褲腰褲腿。那幾條布帶在炕頭上放著,金
梁看見了它們。金梁的心好像被螞蟻咬了一下。沒多咬,就咬了一下。他把布帶扔
給小艾,然後脫衣服。
金梁要鑽被窩了,小艾還一動不動地坐著,不知想著什麼,也許什麼也沒想。
金梁張張嘴,想說句什麼話,一出口,卻變成了另外一句。
「你把罐頭吃了吧。」他說。
小艾還那麼坐著,沒動。
「我先睡了。」金梁說。
每天晚上金梁都要這麼說一句,然後再睡。只有金梁知道,這句話一點也不多
餘。他並不想先睡。他想他要能跟小艾一塊睡多好。他想也許有一天,小艾會接過
他的話,和他說句什麼。沒有,小艾沒有接過他的話。他總是心情淒涼地鑽進他的
被窩,然後再淒涼好長時間,再睡去。
現在,他又這麼說了一句,心情淒涼地往被窩裡鑽進去。他知道,鑽進被窩以
後,他還會心情淒涼的。可是——
小艾叫了他一聲。
「金梁……」小艾這麼叫了一聲,雖然很輕,他還是聽見了。他有些不相信,
以為他聽錯了。
「金梁……」小艾又叫了聲。
這回,他聽得真真切切。他把鼻子從被窩裡抽出來,看著小艾。
是小艾。她叫了他一聲。她沒看他,但她確實在叫他,聲音依然很輕。
他不知道他該不該回答她一聲。
「你,你叫我?」他說。
小艾把頭轉了過來。小艾臉上的表情讓他摸不透她的心思。小艾定定地看著他。
「你不想要我的身子了?」小艾說。
金梁立刻慌了。他沒想到小艾會說這樣的話。小艾的目光讓他心裡發毛了。他
想起了那一夜,舌頭上像纏了頭髮一樣。
「那一次,我喝醉了,我心裡難受。」他說。
他躲開了小艾的目光。
「我再也不會那樣了小艾。」他說。
「金梁……」小艾又叫了一聲。
金梁抬起頭,看著小艾的臉。
「今晚上我願意。」小艾說。
小艾說得很誠懇。但金梁不信。
「小艾,你別戲弄我。」他說。
「我沒戲弄你,」小艾說,「我願意。」
「你想通了?」金梁說。
小艾點點頭。
金梁愣了半晌。然後,金梁胳膊一挑,就把被子掄到了炕牆裡邊,抬起身一躍,
就跪到了小艾跟前,抓住了小艾的手。
「你,」他說,「想通了?」
小艾又點點頭。金梁激動地叫了一聲小艾,就變成了淚人。他抱著小艾,流著
淚給小艾說了一串話。他說小艾我咋能不想你的身子我沒一天不想把心都想幹了。
他把他的淚臉埋在小艾的懷裡嗚咽著,他說小艾我一想你和我睡一個炕你不願給我
做女人我的心就像刀子割一樣我都想去死。那一夜,小艾和所有柔順的女人一樣,
讓金梁在她的身子上躁來攘去,使盡了氣力。金梁一聲聲叫著她的名字,恨不能把
他整個兒化進小艾的身子裡邊去。
他怎麼能知道,小艾為什麼要這麼待他呢!
他很快就明白了。
十
根蘭提著送飯的竹籃子,拉著小艾的手從溝邊走,邊走邊給小艾指東道西,說
著周圍的山名地名。
「你看,那就是駝鳥峰。說是像個駝鳥。我沒見過駝鳥,誰知道像不像。這條
溝叫抵角溝。咱走快點,我怕玉柱等急了,有你看的時候。這地方偏,可看著好看,
比電影上照的那些山啊水啊的好看。」根蘭說。
小艾好像有些目不暇接,東看西瞅,一臉好奇。
突然,她停住了腳步,看著溝底。根蘭以為小艾看見什麼新奇的東西,也停下
來,往溝底下看。
沒什麼好看的。
「溝底下能有啥好看的,想看,啥時候讓金梁哥帶你……」
根蘭話沒說完,小艾突然推了她一把。她叫了一聲,扭過頭,沒看清小艾的模
樣,就落下去。竹籃子像雀兒一樣飛起來,又落下去,和根蘭一塊兒往下滾。
小艾看著往溝底下滾著的根蘭,臉上的表情像木頭一樣。
「根蘭姐,我跟你不一樣。」她說。
她就這麼說了一句,然後轉過身,撒腿跑了。
根蘭還在往下滾,像一件包著東西的衣服。
當玉柱和天泰幾個人把血嗞糊啦的根蘭抬回家的時候,金梁像被誰在頭上敲了
一問棍,眼睛立馬直了,身子立馬僵了。玉柱說小艾跑了她把根蘭推到溝裡自己跑
了我去追她。玉柱說完就和一夥人火急火燎地開著手扶拖拉機走了。出門時又給金
梁扔了一句話哥你別怕根蘭死不了小艾也跑不了。玉柱的眼裡噙著淚花。人急了不
光會紅眼,也會氣出眼淚,玉柱就氣出眼淚了。
玉柱他們一走,院子裡就安靜下來。有人在屋裡給根蘭清洗著傷處。
打井的社會在井底下喊了幾聲,不見動靜,就從井裡爬上來。他很快就知道發
生了什麼事情。他用手抹抹光頭上的泥土,走到臺階那裡收拾他的電視機,要走的
樣子。
「幹啥!」金梁突然吼了一聲。他一直像木樁一樣站著。他突然朝社會喊了一
聲。
社會說走啊你家出了這麼大的事我想這井打不成了。
「放你的狗屁。」金梁說。
「噢噢還打啊。」社會說。他不收拾電視機了。「你說打咱就打井打個半截工
錢難算。」他說。
金梁不吭聲了。金梁一臉兇狠,把手慢慢攥成拳頭,越攥越緊,要打人一樣。
他沒打人。他叫了一聲,把那只拳頭砸在了自己的臉上,鼻血嘩一下流了出來。
他知道他流鼻血了,但他不管,好像他鼻血太多,有意要放一些出來。社會看不下
去了,在牆上摳下來兩小塊硬上,塞進了金梁的鼻子。
「血再多也不是這麼個流法啊。」社會說,「我看你得睡一覺,人心焦的時候
蒙頭睡一覺就會好一些。」社會把金梁推進屋,拉了門。
金梁真睡了一覺。一覺醒來,他像換了一個人,不氣也不急了。
那時候已是第二天早上,小艾被掀回來了,在根蘭的炕跟前跪著。她沒逃脫,
在通往縣城的路上,被玉柱他們追上了。他們揪著她的頭髮,拳腳相加打了她一頓,
然後把她扔上了手扶拖拉機。她渾身是土,臉上一塊青一塊紫。有人給玉柱出主意,
讓扒光小艾的衣服遊街,有人說斷她一根懶筋讓她一輩子拉著腿走路,不影響給金
梁暖被窩給金梁一個熱身子,也不影響生娃。玉柱沒吭聲。他把小艾揪在根蘭的炕
跟前,讓小艾跪下。小艾撲嗵一聲跪下了。玉柱說根蘭挑筋斷腿你說句話。他覺得
怎麼處治小艾,應該讓根蘭決斷。根蘭搖搖頭,讓玉柱出去,她說她想和小艾說幾
句話。根蘭的頭上手上都纏著紗布。她看著小艾,好長時間沒有吭聲。小艾有些受
不住了,先開了口。
「根蘭姐,我對不起你。」她說。
根蘭的眼睛濕了。她拉住小艾的手說:小艾,你真是一塊鐵石頭。
「你讓他們弄死我吧。」小艾說。
根蘭沒接小艾的話茬。根蘭說你走了我摔死了讓金梁哥和玉柱咋活嘛。根蘭說
他們活得不容易他們人看著粗其實心腸都不壞。根蘭說我咋也得給玉柱生個娃我原
想你也許會給金梁生一個生在我的前頭。
「有了娃在院子裡跑來跑去,這個家就圓滿了。」根蘭說。
小艾也一臉淚水了。可是,小艾的心思和根蘭不一樣。
「我要走。」小艾說。
根蘭說你走不了,處治萬泉媳婦你是親眼看見了的。這世上有幾個人能想咋活
就咋活?由不了你,隨不了你的心。
小艾抱著根蘭的胳膊哭了,哭得很傷心。
「金梁哥的命裡也許沒女人。」根蘭歎了一口氣,「看來,金梁哥難拴你的心
了。」她說。
金梁和玉柱在院子裡蹲著。他們都聽見了根蘭和小艾的談話。他們不知道該怎
麼辦了。
社會端著一杯熱茶,朝他們走過來,蹲在他們跟前。
「我看,」社會咽了一口茶水,「這女人你們怕是留不住了。」
玉柱用紅絲絲的眼睛瞪著社會。他想在社會的嘴上摘一巴掌,或者把茶杯奪過
來,把那杯熱茶水連茶葉一起潑在社會的臉上。
社會好像沒看見玉柱的臉色,又咽了一口茶水。
「我看是留不住了。」社會說。
「呸!」玉柱給社會吐了一口。
社會躲了一下,沒吐上。社會並不生氣。
「玉柱,我說的是實在話。人不愛聽實在話,這是人的毛病。」社會說。
玉柱還要吐,被金梁攔住了。金梁說玉柱你別和社會較勁他沒說錯,留不住就
讓她走吧。
玉柱眉頭一跳說:你就知道個走!人走了,錢呢?
金梁不吭聲了。
「錢呢?」玉柱說。
社會又開口了。社會說的話是金梁和玉柱都想不到的。
「如果願意,你們把她給我,我給你們錢。」
玉柱和金梁眼睛直了,看著社會。社會不像說耍話。他一臉誠懇的表情。
「這是個商量的事。」他說,「她要走,你們又治不住她,到頭來就是個人財
兩空的下場。」
「我打斷她的腿,讓她躺在炕上,我養著。」玉柱說。
「這何必呢,」社會說,「看著是你和她過不去,其實是你自己和自己過不去。」
「打你的井吧你,這事和你無關。」玉柱說,「我們治不住她你就行?你有日
天的本事?」
「也許我就真有日天的本事。」社會說。
「做媳婦?」玉柱說。
「這你別管。」社會不願露底,「你拿你的錢,錢子兒不少給你。你要不放心,
咱讓你們村長當個證人,咋樣?這兒不好說話,咱去村長家說。說說總行吧?你不
撒手,有你的人在,你怕啥?」
事情竟越談越真了。
開始的時候,玉柱連想也不願想。金梁說玉柱我已經死心了也許社會說的也是
一條路。玉柱鬆動了一些。玉柱說要談你談去我不去我咽不下這口氣。金梁說我去
你也去該咽的氣再難咽也得咽。玉柱說你真的不想留她了?金梁說我想留可留不住
她是個人又不是貓狗能拴住。玉柱不再說話了。
第二天一早,他們和社會一起找了一趟天泰。村長天泰說留不住就給社會算毬
了。不過這事可要想好接了社會的錢就不能反悔。社會說為了以後不麻煩咱寫個合
同。金梁和玉柱都沒反對,天泰就寫了一份合同。天泰把合同念了一遍,問行不行。
他們都說行。天泰說行了就按手印。他取出一盒印色,讓他們一人在合同上按了一
個紅手印。天泰說行了行了社會你交錢。社會說村長你是證人也得按個手印。天泰
說對對我忘了這茬兒我按我按。天泰按完手印又說,我再把村委會的章子給你們蓋
上章子比手印氣派。他們都覺得天泰的主意好。天泰又給合同上蓋了公章。天泰說
社會你現在該給金梁點錢了。社會說事太急不順手差一千塊過幾天給。天泰問金梁
和玉柱行不。玉柱說不賣了。社會看著天泰。天泰說金梁我看這個小艾是不行了等
老梅來了再找合適的啥胳膊配啥袖子就給社會算毬了。天泰說社會又不是跑戶走戶
再說還有合同差的錢就緩幾天吧。金梁接了社會的錢。
當天晚上,社會就把小艾扶上了一頭毛驢,又把那台電視機遞給小艾,讓小艾
抱著,走出了後村。小艾問拉她去哪兒。社會說先到我家住一夜明天送你去縣城。
小艾以為社會要送她回家。小艾說你的心咋這麼好?社會說爹媽給的沒辦法。小艾
問金梁和玉柱為啥會放她走。社會說我給了他們一點錢。小艾說我一回到家讓我爸
媽給你寄錢來。社會說寄不寄無所謂錢是人身上的垢癡。小艾說我沒騎過驢老覺得
要摔下來。社會說你可要抱好我的電視機摔碎了我的損失可就大了。
一到社會家,幾個人就把小艾挾起來,裝進了一條裝糧食的口袋。社會已下井
了。社會家後院裡有一口水井。「往下溜。」社會在井底下喊著。
他們把口袋拴在井繩上,溜了下去。
十一
井底下有一孔窯,是放紅薯用的。現在,窯裡鋪著一堆乾草,乾草上鋪著塑料
布和被褥。被褥上坐著小艾。社會說小艾實話給你說吧我從金梁手裡把你買過來了
當然是給我做媳婦我跟金梁一樣打了多年光棍了,說完就把小艾撲倒在被褥上,撕
小艾的衣服。小艾把兩隻手伸成鷹爪樣,在社會臉上狠抓了一把。社會叫了一聲,
跳開了。社會的臉上立刻現出來幾道指印。他摸摸臉,疼得直咧嘴。
「流氓!」小艾喊著。
「是啊是啊,」社會說,「不流氓,咋能把你弄到這兒來,到底是念過書的人,
罵得很准。」
井上邊的人問社會上不上井,他們等得不耐煩了。社會把頭朝土窯裡伸出去朝
井上喊了一聲:你們走吧我自己能上去。井上邊的人走了。社會又轉過頭,對小艾
笑著。
「這是我家的井,」他說,「打井的時候就挖了這窯,放紅薯的,沒想到會放
媳婦,連我都覺得有些稀奇古怪。」
「你放我出去。」小艾說。
「要出去就得跟我睡一個炕。我媽把房子和炕都收拾好了,眼井底下比天上地
下。」
「不要臉你。」小艾說。
「要臉就要不到媳婦,這個賬我還能算過來。」社會說,「只要你給我做媳婦,
你天天叫我不要臉都成。我把名字改成不要勝也成。」
小艾說不出話來了,一下一下出著氣。社會往小艾跟前湊了湊,小艾的手立刻
伸成鷹爪。社會不湊了。社會說你是不是又想抓我不動你了你想不通我就是把衣服
剝光也弄不成事這又不是往牆上釘木橛子。小艾說把你的臭嘴弄乾淨些。社會說鄉
下人的嘴肯定不如你們城裡人乾淨鄉下人不刷牙嫌刷牙麻煩。社會說你要願意的話
我可以天天刷牙。小艾又不說話了,她感到社會太不要臉,不要臉到這種地步。說
什麼也是白費口舌。
但社會還想說。社會說我不是金梁,金梁那一套我看不上,我有我的手段。我
這手段是給金梁家打井的時候突然想出來的。我給你在這兒鋪上毛氈塑料布褥子被
子我看你往哪兒跑除非你往水裡紮。
小艾的頭要破了一樣。小艾抱住頭嘶聲叫了起來:
「你放我走!」
兩串淚珠豌豆一樣從小艾的眼眶裡滾了出來。
「那你哭一會吧,」社會說,「有時候哭也能哭走一些傷心。我媽傷心了就一
個人哭,哭完了該做啥還做啥。」
小艾真哭了,把頭埋在胳膊裡,哭得很傷心。社會在一邊蹲著,很有耐心地聽
著小艾哭。
「要哭就好好哭一回。」社會說。
小艾哭了一會兒,止住了聲。
「不哭了?」社會說,「不哭了咱繼續說。其實也沒啥說的,你跟我圓房,我
就讓你上井。」
「我肚子餓了。」小艾說。
「噢噢,我肚子也餓了。」社會摸摸肚子,「我上去吃點東西,下來再和你說
話。當然,我不會給你帶吃的,也許餓你幾天,你就會想著跟我圓房的。」
社會嬉皮笑臉地又說了幾句,就從井筒子裡爬上去了。他胡亂吃了一頓。他媽
和他爸問他這辦法行不行。他說這種辦法過幾天才能見效,一時半會兒還不行。他
媽做了兩個荷包蛋,讓社會給小艾送下去。社會說,媽,你這是毀我的事情哩,她
有吃有喝有住,還能跟你娃成事嘛你。他把那兩個雞蛋吃了。他媽看看他爸。他爸
說就聽他一回吧。
第二天早上,他們沒給小艾送飯。中午也沒送。晚飯的時候他媽不依了,端著
飯碗朝社會喊叫了社會你想餓死她是不是?社會說媽你說錯了餓死她我到哪兒弄媳
婦這種機會可不是想有就能有。社會他媽說餓死她你讓鬼給你做媳婦去。社會說我
在一本書上看過人七天七夜水米不沾牙才能餓死。社會他媽說放屁我今兒非要給她
送飯。社會她媽讓社會他爸把她往井下送。社會他爸拿出那條口袋,拴在井繩的鐵
鉤上,讓社會他媽坐進去。
「我來我來。」社會看他媽動真的了,要自己下井。社會他媽給社會吐了一口,
讓社會他爸把她往下溜。
「毀了。」社會把頭仰在脊背上,朝天說了一句。
「毀了。」他又說了一句。
「溜。」社會他媽說。
社會他爸搖動了轆轤。
事情確實毀了,但不是因為小艾吃了社會他媽送下去的飯,而是另有原因。先
是社會他媽發現小艾犯噁心,想嘔吐,再是金梁到社會家來了一趟,後來又加進了
鎮上派出所的趙所長,幾個原因攪和在一起,就把事情鬧大了。
社會他媽是在另一次下井送飯時發現小艾犯噁心想嘔吐的。她問了小艾幾句話,
然後就驚慌失失讓社會他爸把她吊上去,一上井就說:小艾懷孕了。她不知道她在
井下邊和小艾說話的時候井上邊發生了什麼事情。
「小艾懷孕了!」她說。
話一出口,才看見金梁也在井臺邊上站著。
他們都愣了。
一十二
金梁來社會家,是因為鎮上派出所的趙所長。
那天,趙所長把他那輛破三輪摩托騎到了後村,還沒到村長天泰家就熄了火,
怎麼也發動不起來。那輛摩托常犯這種毛病,說不定就會在哪兒停下來,給趙所長
添點麻煩。也多虧是趙所長,不知有什麼手段,最終總能讓它重新動彈起來。所以,
到什麼地方去,他都要騎著它。
「天泰,天泰,快叫幾個人給我推推摩托。」他站在天泰家門口喊著。他大概
有五十歲了,有一口滿是茶漬的黃牙。
天泰走出門,朝街道兩邊看看,沒人。
「走走,我給你推。」天泰說。
他們把那輛摩托推進天泰家。天泰婆娘端上了茶水。四個娃要坐摩托,被天泰
趕走了。
「去去,這摩托不敢動,動壞了你爸賠不起。」
「天泰你別諷刺我。」趙所長邊收拾摩托邊說。
天泰說我沒諷刺你我怕那幾個熊娃胡動真弄壞了耽誤你的事。說完,嘿嘿笑了
兩聲,蹲在摩托的另一邊。
「你也是,所長都當了幾年了,也不換個新的。壞到我這兒好說,咋也得給你
管飯,你慢慢修。壞到半路上咋辦?」天泰說。
「能有油讓我跑就不錯了,還換個新的。上個月的工資還拖欠著哩。」趙所長
說。
「那你還給他跑毬個啥?」天泰說。
「你以為我愛跑?我整天盼退休哩,年齡不到嘛,不跑咋辦?」趙所長說。
「你沒事肯定不來。」天泰說。
「廢話。」趙所長說,「你們村又買了幾個外地媳婦是不是?」
「沒有啊。」天泰說。
「你這毬人還跟我耍花子。你們村買了那麼多外地媳婦,我問過沒有?其它事
沒人說,我也會管,這號事找不到我門上,我不會管的。」
「咋啦?」天泰多少有些緊張。
「裡邊是不是有個叫小艾的?」趙所長說。
「咋啦?」天泰說。
「她父母找到縣公安局了,你說我管不管?」趙所長說,「我不管,上邊找我
的麻煩。」
「沒這麼個人。」天泰說。
「我這回可是認真跟你說話哩,天泰。」趙所長說。
「我們村肯定沒這個人,你要是找出這麼個人來,我跟你坐牢去。」天泰說,
「不信你找去。」
「我也沒說一定就在你們村。我這個行當,就是個捕風捉影。」趙所長說。他
遞給天泰一根紙煙,自己也叼了一支。天泰湊過去,給他點火。
「你啥風不能捕啥影不能捉偏要捕捉人家的媳婦?」天泰說。
「你這村長當的,連個法律都沒有了。法律把這叫拐賣婦女哩。」趙所長說。
「法律也是人定的嘛。」天泰說。
「人定的是人定的,可不是你跟我定的,對吧?」趙所長說,「總不能讓人家
父母天天在公安局哭喪吧?」
「你把女人捕捉走了,買女人的光棍漢也一樣全家哭喪。」天泰說。
「你這人咋沒一點人情味兒?」
「你這話就說得不對了。不是我沒人情味兒,是咱倆的人情味兒不在一個地方。」
天泰說。
「這話也對。」趙所長說。他站起來,拍拍手。
「修好了?」天泰說。
「試火試火。」趙所長說。
一試火,真好了。趙所長騎上去,要走。
「不吃飯了?」天泰說。
「吃。」趙所長說,「我出去蹓一圈。你給咱準備飯。」說著,人和摩托一塊
兒出門了。
他到金梁家聊了一趟。根蘭一個人在家。他說金梁玉柱呢?根蘭說河灘去了。
他說噢噢,邊說邊瞄著幾個屋子。根蘭說找他們有事?他說沒事沒事。根蘭說不坐
了?他說不了不了你咋啦頭上纏那東西?根蘭說不小心摔到石頭上了。他又噢噢了
兩聲,走了。他到天泰家吃了一頓飯,說了幾句閒話就回鎮上去了。
當天晚上,他又轉了回來,還領著幾個派出所的人。他們敲開了金梁家的門。
他們沒找到要找的人。
「人呢?」趙所長問金梁和玉柱。
「兩個都在你跟前站著,另一個是我婆娘,在被窩裡,要看?」玉柱說。
「哎你個玉柱,你婆娘咋了?你以為我不敢看?我偏要看你領路。」趙所長說。
屋裡確實只有根蘭一個人。
「對不起對不起。」趙所長說。
「說個對不起就行了?」玉柱說,「半夜三更打門叫戶,沒看我只穿了一件單
衣服,感冒了咋辦?下回來帶些感冒藥,反正你是公費醫療」
「行啊行啊。」趙所長說。
他們沒找到小艾。他們去了萬泉家,把萬泉媳婦弄上摩托車帶走了。萬泉像挨
刀一樣嚎叫了半夜。
第二天,金架起得很早。他說他一夜沒合眼,他想看看小艾,他不放心。
「社會不是個正經人。」他說。
「你是沒事找事。」玉柱說。
根蘭說想去就讓金梁哥去向社會要欠的一千塊錢。她知道金梁在為小艾擔心。
「這錢不能要了。」玉柱說。
「看看也不成?」根蘭說,「金梁哥你去你的。」
金梁就去了社會家,就知道了社會把小艾溜到了井裡。他說社會你咋能把人弄
到這種地方?社會本來就對金梁來他家不高興。社會說弄到啥地方是我的事與你無
關。金梁說你把她弄上來。社會說你出去。金梁伸手就給了社會一耳光。社會閃開
了,摸了一根棍說:金梁你想打架是不是?金梁說你把人弄上來。社會說我不要打
架你就別往跟前來。這時候,社會他媽在井底下搖著井繩,要上來。
就這麼,金梁知道了小艾懷孕的事。
十三
金梁紅脖子漲臉一口氣跑回家,抓住玉柱的胳膊直搖晃,半晌沒說出話來。
「咋啦咋啦?」玉柱緊張了。
「小艾懷孕了!」金梁說。
根蘭立刻從廚房顛出來。
「小艾懷孕了!」金梁說。
吃過飯,金梁和玉柱又去了社會家,和社會進行了一次激烈的談判。社會他爸
也在。他們說話都很直接,一點彎兒不拐。
「是是,我是差你一千塊錢,我不賴帳,我給。」社會說。
「我不要錢了我要人。你的錢我退,我帶錢來了。」金梁說。
「這錢我不接。咱是訂了合同的,想要人找你們村長去,讓他來要。」社會說。
「村長來也不行。」社會他爸說。
「他敢來?我k他耳光!」社會說。
「她懷了我的孩子。」金梁說。
「憑啥說是你的?我跟她也睡了。你紅口白牙可不能胡說。人在我家裡,咋能
懷上你的孩子?再胡說,我可就不客氣了。」社會說。
「你敢!」金梁說。
「人急了啥事都能做出來。」社會說。
「王八蛋!」金梁說。
社會蹭一下站起來,被他爸拉住了。
「坐下坐下。」他爸說,「咱不跟他吵,不跟他鬧,咱湊錢,明天就把錢送過
去。」
「我不要。」金梁說。
「那就是你的事了。」社會他爸說。
金梁氣得渾身打著抖。
「金梁,這不是生氣的事,這是個講理的事。」社會他爸說。
玉柱一直沒吭聲。他一直盯著社會和社會他爸的臉。他知道說不下去了,就站
起來。
「回。」他給金梁說。
金梁說:「事情沒說倒,咋能口?」他不回。
「回!」玉柱朝金梁吼了一聲。
「還是玉柱明智。」社會他爸說,「明天一早,我讓社會把錢送過去。」
「你等著,我會來取的。」玉柱說。
「不要錢!」金梁說。
玉柱拉著金梁的胳膊往外走。
「我不會要錢!」金梁扭過頭又喊了一聲。
當天晚上,社會和他爸就把錢湊夠了。第二天早上,他們哪兒也沒去,等著玉
柱和金梁來取錢。快吃早飯了,還沒等來。
「他們不會來的。」社會說。
「再等一會兒。吃過早飯還不來,咱就送過去。」他爸說。
「媽你做飯。」社會給他媽說。
砰一聲,大門被撞開了,有人跑進了院子,喊著:
「社會你快!金梁、玉柱領著人來了!」
社會一步就跳到院子裡。
「在哪兒多少人?」他說。
「快到村口了,一大夥人都拿著傢伙。」那人說。
社會的臉立刻變白了。社會他爸把錢塞進炕洞,也從門裡跳出來。
「叫本家戶族的往村口走,能上的全上。」他爸說。
社會應了一聲,取下屋簷下的鐝頭提著,跑出去叫人去了。
社會和本家戶族的人湧到村口的時候,玉柱金梁帶領的一群人剛好趕到。他們
還抬著擔架,準備運送傷員。
社會和他爸並不怯火,等著。
金梁、玉柱他們到跟前了,停了下來。兩邊的人互相看著,緊握著手裡的傢伙。
「還看啥?」玉柱突然說了一聲,「上!」
打鬥就這麼開始了。他們立刻攪和成一片。鐝頭、鐵鍁、棍棒,帶著風聲,朝
對方的頭部腰部腿部掄去。石頭、磚頭和拳頭,拍砸出各種結實的聲響。勞動的工
具一旦成為戰鬥的武器,勞動的軀體也就不是軀體了。是肉。是一種堅韌或者脆弱
的東西,承受著襲擊。也只有在這種時候,強壯的肌體才會煥發出一種非人的瘋狂。
本來他們是互相認識的,見了面會親熱地打招呼,以後也還會親熱地打招呼,但這
會兒,他們是戰鬥者。他們只想著打倒對方。打!打他們這些狗日的!他們打昏了
頭,打花了眼,有人竟把傢伙掄到自己人的身上。這時,被打的就會跳起來罵一聲:
你狗日的昨往我身上搶!
有人用堅硬的牙齒,咬住了對方身上的一塊肉。
很快就有了呻吟聲,因為有人已躺在了地上,不知什麼地方流著血。
玉柱的對手是社會。他很快打倒了他。他騎上去,揪住社會的兩隻耳朵,往地
上磕社會的頭。社會說玉柱你放開我咱有話慢說。玉柱不放。玉柱知道他一放開社
會就會跳起來說不定會把他弄倒然後磕他的頭,所以他不放。他一下一下磕著。他
感到抓耳朵磕不如抓頭髮磕,但社會是光頭,只能抓耳朵。
金梁一開始就瞄準了社會他爸。社會他爸知道不是金梁的對手,就跑,邊跑邊
喊人過來對付金梁。所以金梁一直沒打上他。金梁一定要打上他,放倒他。金梁到
底沒把社會他爸放倒,有人掄了金梁一棍,打在了腿彎處。金梁腿一軟,跪了下去。
社會他爸笑了一下,正要往金梁跟前撲,一塊磚頭有力地拍在他的肩膀上,他呻吟
了一聲,也跪在了地上。
如果不是社會他媽,打鬥還會繼續下去。可是,社會他媽來了。
「別打了!別打了!小艾讓公安搶走了!」她朝打鬥的人群失聲喊著。
打鬥的聲音小了。
「小艾讓公安弄上摩托開走了!」社會他媽說。
打鬥聲沒了。
金梁玉柱和社會社會他爸都從地上爬起來,瞅著社會他媽。然後,就互相瞅了。
「肯定是趙所長。」金梁說。
「就是就是從後街走了。」社會他媽說。
「咋辦?」社會看著金梁和玉柱。
「還不快起來,追!」社會他爸說。
「追!」玉柱說。
能爬起來的人都爬起來,提起各自的傢伙,跟著金梁玉柱和社會跑了。他們合
成了一個群體。
「抄近路!」社會他爸朝他們喊著。
他們很快就看見了那輛三輪摩托車。
十四
趙所長像狗一樣,很快就嗅到了小艾的下落。他激動了一會兒,然後發動了他
的那輛三輪摩托,把它開到了社會家。他沒費一點周折,因為社會他媽一看見他,
牙齒就打顫,沒等問話,就供出了小艾。她取出那條口袋,拴在井繩鉤上溜下去,
和趙所長合力把小艾從井底下弄了上來。
「趙所長他們在村口打仗哩。」社會他媽說。
「噢噢。」趙所長說。
「你讓他們別打了,你是所長說話管用。」社會他媽說。
「噢噢。」趙所長說。
他沒去村口。他從後街走了。他想把小艾送到鎮上,然後再回來管他們。他小
看了他們的膽量。也忽視了他的那輛摩托車。摩托車在不該壞的時候壞了,怎麼也
發動不起來。他睜著眼,看著金梁玉柱社會和一大群人從溝坡上滾下來,提著各式
各樣的傢伙。越來越近了。他蹬酸了腳腕,硬是沒讓他的三輪摩托叫喚一聲。他知
道一時半會兒沒法讓它跑起來,索性不蹬了,點了一根煙,等著人群往他跟前跑。
小艾焦急地叫了幾聲所長。趙所長說:「你別怕,咱是正義的一方,咱有法律,他
們不敢把你咋樣。」他擦了一把頭上冒出的汗水珠子。
呼啦啦一陣腳步,他就被圍住了。最前邊的金梁玉柱社會憤怒地盯著他。他想
給他們做個笑模樣,做出的卻是一個哭笑都不是的表情。
「把人放下。」社會說,口氣很硬。
「為啥?」趙所長儘量讓他的聲音綿軟一些。
「她是我花錢買的。」社會說。
「你看是這,」趙所長說,「我是奉命行事,沒辦法,有話咱到鎮上去,慢慢
說。」
「少廢話,不交人,我們就動手了。」社會說。
「你們這麼弄要犯法的。」趙所長說。
「我們顧不得了。交人不交?」社會說。
「不交。」趙所長從皮帶上解下一副手銬,「誰跟我胡來,我就銬誰。」他說。
「搶!」玉柱喊了一聲。
趙所長舉起手銬喊著:「不准動!」
「打!」社會喊了一聲。
人群發出「噢」的一聲,把趙所長和他的摩托車還有小艾,一起淹沒了,拳腳
從各個方向砸向趙所長,把他的正義和法律砸得沒了蹤影。
「別打骨頭,打殘廢就麻煩了!」社會給人群喊著。
沒人打他的骨頭。他們只是把他打倒了。他們從他身上雜遝過去,架走了小艾,
然後又掀翻了那輛摩托。趙所長從地上爬起來,人群和小艾不見了,只有他的那輛
不爭氣的三輪摩托倒在一邊,正燃燒著。不知誰把它點著了。他看著燃燒的摩托車,
終於做出了一個笑模樣。剛才他想給他們做,做得不好。現在他做出來了。他感到
額頭上有些疼,摸摸,那裡腫了一個包,一摸更疼。他想起他給小艾說的話,覺得
很可笑。
這時候,小艾正在金梁和社會的中間。他們一人拉著小艾的一隻胳膊。他們發
生了爭執。
「小艾不能去你家。」金梁說。
「也不能去你家。」社會說。
「不管去哪兒,也不能讓趙所長知道。」玉柱說。
「對對,」社會說,「小艾暫時歸咱兩家管,把事情說倒,該去誰家就去誰家。」
這一次他們沒吵,也沒打。他們暫時達成了一致意見。他們把小艾安置在一個
隱密的地方,又開始了談判。
談判是在金梁玉柱家進行的。根蘭做了幾個下酒菜,讓他們邊吃喝邊談。他們
沒動筷子。他們的心思不在酒菜上。
金梁幾乎要哀求社會了。金梁說社會你就把小艾讓給我你比我年輕有的是機會。
社會不同意。
「我是比你年齡小,可我爹媽年齡大了,我娶不下女人,他們睡覺不塌實。」
社會說。
「就非要跟我爭一個女人?」金梁說。
「沒辦法,咱們遇上了。」社會說。
「她懷了我的孩子。」金梁說。
「你咋又說這話?」社會很不高興了,「這風傳出去,將來生下娃,我咋面對
世人?人都說社會的娃是金梁的,你讓我咋往人面前走?」
「總不能把一個女人撕成兩半吧?」玉柱說。
「我也是這話。」社會說。
「說啥我也要小艾。」金梁說。
「我跟你一樣。」社會說。
他們談了一個晚上又一個白天,事情說不倒。
「咱有合同嘛。」社會突然想起了那份合同,「咱拿合同說。」
「拿合同就拿合同,合同是兩家訂的,黑白不由一家說。」金梁說。
他們叫來了村長天泰。天泰說你們這官司難斷我斷不了。社會急了。社會說天
泰你好賴也是個村長你不能這麼做事簽合同的時候你咋說的?天泰說我當初也是為
了你們兩家好現在好不了你讓我咋說?社會說那咱就去鎮上。天泰說這也是個辦法
鎮長官比我大也許他能斷這個官司。
「去鎮上不能少了你。」社會說。
「當然當然,我跟你們一起去,該我說話我就說。」天泰說。
他們怕趙所長找事,但他們很快就不怕了。小艾在我們手上,他能找個啥事?
他們就去了鎮上。
十五
事情進行得很快。這是他們沒想到的。
鎮政府文書把他們讓進一間屋子,給他們每人倒了一杯水,說:鎮長讓你們等
會兒,縣上來了幾個人正談話哩。
「啥人?」社會說。
「我沒問,你們等等。」文書說。
文書閉上門出去了。一會兒,門又開了。進來的不是鎮長,也不是文書,而是
趙所長。趙所長額頭上的包已經下去了,留著一塊紫顏色。
「聽說你們要來。」趙所長說。
趙所長一說話,金梁玉柱和社會就不緊張了。天泰站起來想跟趙所長握手。他
一到鎮政府,見人就握手。
趙所長沒和他握。
門大開了。進來幾個公安,每人手裡提著一副手銬,把金梁玉柱社會銬了。把
天泰也銬了。
他們都瞪圓了眼睛。
「這是咋麼回事趙所長?」天泰說。他比金梁他們經多見廣,很鎮靜。
「你這是官報私仇!」社會朝趙所長叫喊起來。
「你們都參與了拐賣婦女,犯了法。」趙所長說。
「我也是?」天泰想不通。
趙所長對天泰點點頭。
「這怕是冤枉我了。」天泰說。
「治了你的罪,你就知道了,」趙所長說,「村委會的公章不是耍貨,想往哪
兒蓋就能往哪兒蓋。」
「噢噢。」天泰似乎明白了。
趙所長端過一杯茶水,不慌不忙地喝著。
「等把小艾接來,就送你們去縣上。」趙所長說,「這回弄得陣勢很大,公安
局長也來了,還領著小艾的父母。小艾的母親把咱鎮長教訓了好大一陣。那是個厲
害女人,說話像刀子一樣。你們這地方這麼落後,她說,普法教育搞了幾年了,群
眾連一點法律常識都沒有,你這鎮長也有責任。鎮長的臉直發燒。鎮長說當然當然,
不過說句心裡話,在這種地方,讓省長來也出不了彩,說不定還不如我哩。鎮長不
服氣。小艾母親說我心疼女兒,更氣你們這兒的人賤踏法律。那狗日的女人。
趙所長像拉家常一樣,和幾個戴銬子的人這麼說著。
院子裡開進來幾輛摩托車。小艾被接來了。小艾撲在她媽懷裡哭了很長時間。
然後,他們看著公安們,把金梁玉柱社會和天泰一個一個押上了一輛麵包車。
「小艾。」有人叫小艾。
是根蘭。她不知什麼時候來了。
小艾走到根蘭跟前,想說什麼,又說不出來。她拉住根蘭的手,叫了一聲根蘭
姐。
「你看你,害了多少人……」根蘭說。
小艾直想哭。
麵包車開動了。小艾她媽叫小艾上摩托車。小艾就上了摩托車。
金梁坐在麵包車裡,一直看著前邊摩托車廂裡的小艾。他沒想他們會怎麼處治
他,他想著小艾。
「你們要把小艾咋辦?」他問趙所長。
趙所長覺得這話問得很可笑。
「你沒看人家父母來了?」趙所長說。
「她懷著我的孩子。」金梁說。
趙所長覺得這話更可笑。
「懷你的孩子是懷你的孩子可孩子是非法的肯定得打掉。」趙所長說。
「放屁!」金梁站起來,漲紅著臉。
「你坐下,你坐著,車一搖把你閃倒了。」趙所長說。
金梁慢慢坐下去,低著頭,一聲不吭了。
到縣城跟前了。摩托車拉著小艾和小艾父母,要去縣政府招待所,拉金梁他們
的麵包車,要去看守所。金梁突然一躍而起,從車門裡拉出去。
「小艾!」他撕心裂肺地喊了一聲。
摩托車廂裡的小艾扭過頭來,看著金梁。金梁被摔倒了,從地上爬起來,跌撞
到小艾跟前。
「小艾,你懷了我的孩子。」金梁說。
小艾點點頭。她突然覺得金梁很可憐。她感到她心裡有一種複雜的感受。她不
想欺騙他。
「你要弄掉它,是不?」金梁眼巴巴地看著小艾。
這回,小艾沒點頭,也沒搖頭。她不願傷害金梁。她想給他說幾句什麼話。
摩托車突然叫了一聲,開動了。
「小艾!」金梁絕望地叫著。
「你不能……」他喊著。
兩個公安架起金梁,往麵包車上拉。金梁固執地擰著脖子,看著那輛越跑越遠
的摩托。
在看守所,他們見到了老梅和二女。老梅掏出一盒紙煙,給他們散發著,很輕
松的樣子。玉柱和社會抽了老梅的煙。金梁沒抽,他還想著小艾和小艾肚子裡的孩
子。天泰也沒抽,他憋了一肚子冤枉,一個人蹲在一邊,一點一點嚼著,連話也不
願說。
一個月以後,他們被判了罪,勞改去了。老梅最重,是五年。二女三年。金梁
玉柱和社會各一年。最輕的是天泰,半年,監外執行。
一年後,金梁玉柱和社會三個人背著行李捲,一塊兒走出勞改農場的大門。金
梁不願跟玉柱和社會回去。他說他要去找小艾。玉柱知道攔不住,就沒吭聲。社會
說金梁你就把心收了吧。金梁什麼也沒說,一個人走了。
他真找到了小艾家。小艾認出了他。小艾給金梁倒了一杯水說:金梁你坐我沒
想到你會來。金梁不坐。金梁說我的孩子呢?小艾低下頭,順下了眼。小艾說金梁
我對不起你。正好小艾她媽推門走進來,一看見金梁就往外趕。金梁說我要我的孩
子來了。小艾她媽說出去出去趕快出去我們家沒人認識你。金梁給小艾她媽笑了一
下。小艾她媽說別跟我嬉皮笑臉的肯定是在勞改場學來的。金梁的臉突然變了。他
從行李捲裡抽出一把刀子,捅進了小艾她媽的肚子。
「這也是從勞改農場學的。」金梁說。
小艾她媽大張著眼,捂著肚子往下倒著。
金梁沒再捅。金梁轉臉對小艾說:小艾,我每天都看見你的模樣在我眼跟前晃
來晃去。我沒辦法。
小艾抱著頭,尖叫了一聲。
金梁又被判了罪。這一次是十五年。玉柱和根蘭去監獄看他的時候,他說現在
我心裡乾淨了再不用想著弄媳婦的事了你們好好過日子吧。玉柱給金梁點著頭。根
蘭不停地擦眼淚。
這時候,老梅已經出獄了。他使了錢,減了刑。他想改行,改了幾次,都覺著
不順手,就繼續做老營生,流通女人了。當然,他沒去後村,他把地方挪在了更北
邊的一個省份,所以,他不知道金梁又一次被判刑的事。他又弄了幾個女人,要領
著她們北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