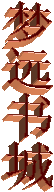
楊爭光 我的簡歷及其它
楊爭光
1957年,我出生於陝西乾縣。1964年,我在我出生的村莊上小學。兩年後,是
世界矚目的文化大革命。我記憶最深的課文是「小貓釣魚」和「年四旺狠鬥私字一
閃念。」四年級,我作為全縣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被老師吊在褲帶上,在縣
城裡招搖了好多天。1974年底,我從一所農村中學畢業,回鄉種地,並染上抽煙的
惡習。1978年,我考人山東大學中文系,學習漢語言文學。我買最便宜的牙膏,抽
廉價的劣質煙草。我讀了一些書,知道了托爾斯泰和海明威。知道了魯迅不是世界
上惟一的偉大作家。1982年,我被分配到天津市政協工作。這一年,我見到了漂亮
的抽水馬桶,在出了許多洋相之後,我感到了屁股的高貴。也是在這一年,我到北
京走了一趟。北京的街道使我淚眼模糊。轉過年,我便娶妻養子了。
1979年,我發表了第一首詩。1980年,我發表了第一篇小說。那時候,我想當
詩人。我對詩產生過十多年的迷戀。1986年,我在陝北的一個小村裡住了整整一年。
這一年的經歷對我產生的影響非我所料。我和小說結下了不解之緣。其後的幾年中,
我寫的小說大多收在我的第一本小說集——《黃塵》裡。
1989年底,我調到西安電影製片廠任專業編劇。和電影的交情又一次帶給我一
些運氣。我寫了《黑風景》、《賭徒》、《棺材鋪》、《老旦是一棵樹》等幾個中
篇小說。細心的讀者一定會發現它們和電影的某種關係。在西影的兩年中,我寫過
七個電影劇本,有兩個拍成了電影。其中《雙旗鎮刀客》獲得日本夕張國際驚險與
幻想電影節大獎。據說電影是導演的藝術,我自然不宜多嘴。
在我寫作的過程中,許多人給我無私的幫助;我的每一篇作品的編輯,都為我
付出了勞動。我對他們滿懷感激。
中國的小說,我喜歡《紅樓夢》和《創業史》。
在作家中,我喜歡列夫·托爾斯泰和魯迅。
契訶夫的機智和海明威的簡潔使我絕望。偉大的小說家,以他們的天才,使小
說的寫作荊棘密佈,險象叢生,令人望而卻步。可惜的是,天才和普通人一樣也會
死,而不斷發展的時代又不能沒有小說藝術。要不,他們寫,我們讀,那該有多麼
愉快。
是的,小說是一門智慧的藝術。問題在於,操作是一回事,是否具有操作的智
慧,是另外一回事;寫出幾篇可看的東西是一回事,寫成一個真正的小說家,又是
一回事。
然而,契訶夫沒有因為列夫·托爾斯泰和莫泊桑的存在而改行。大狗叫,小狗
也叫,各用各的聲音叫,他這麼說。後來的事實證明,他和他們叫得一樣好聽。
既然這樣,那就甭管那麼多。想叫就叫幾聲——
我迄今為止的小說,多以農村為背景。我這樣做是基於兩方面的原因:一是我
熟悉他們;其次,我以為,中國是一個農民國家,中國的城市是都市村莊。中國農
民最原始最頑固的品性和方式,滲透在我們的各個方面。愚昧還是文明?低劣還是
優秀?這只是一種簡單的概括。它是靠不住的。
他們遇到了一些事情,他們按他們的方式做了。我就這麼寫。這也是我最感興
趣的。當然,我得按我的方式和語言去說,去講述。
我有意和我所寫的東西保持著距離。我以為這樣做,我就可以平靜一些,儘量
避免受自己的欺騙。
我想說的一切,都在我的小說裡。如果是一個故事,它就在故事的過程中;如
果是幾個人物,它就在人物的行為裡。小說只能是小說。小說之外的話,只能在小
說之外去說。
當我感到我的小說用幾句話就可以說清楚,我就會考慮把它撕掉,然後吹幾聲
口哨,或者找人聊天去。我覺得這樣做,可能比寫那篇小說更有意思。
我沒有文思泉湧的時候。我寫得很苦。
優秀的小說是由優秀的小說家和優秀的評論家、優秀的讀者共同創造出來的。
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說,小說的鑰匙不一定在小說家的手裡。
優秀的小說,可能掛滿了鎖。它需要鑰匙。
但是,真正的評論家不僅僅是一把鑰匙。他有自己的話要說。小說是他說話的
材料。世界上沒有萬能的鑰匙。對每一位作家的作品都有興趣說話的評論家,是可
疑的。為評論而寫的小說,肯定乏味;看小說家的臉色而作的評論,同樣乏味。小
說和評論都需要一種勇氣。好的評論不僅要觸動小說家,也要觸動眾多的讀者。
但我是真誠的。只要我還寫小說,我就需要評論的關注。也正因為我還寫小說,
我希望我能讀到令我心動的評論,不管它評論的是哪位作家,哪篇作品。
我寫得很少。我還有幾個東西要寫。我希望我能寫好它們。除此之外,我還希
望我能有一套房子,把我從地下室那間十幾平米的屋子裡解放出來。那裡終年不見
陽光。我一家三口在那裡已住了整整八年,恰好和常寶裝啞巴的時間一樣長短。
當然,這僅僅都是希望。
1992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