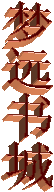
楊爭光 雜嘴子
一
他們嫌我話多,叫我雜嘴子。
最先叫我雜嘴子的是黑三。他是個木匠。他和他的兒子們像老鼠一樣,把一根
又一根帶皮的圓木從他家的大門裡叨進去,在院子裡沒日沒夜地啃,把它們弄成門
窗或者桌椅或者箱子櫃子,有時,也會弄成一口棺材。我媽說黑三的手藝是祖上傳
下來的。黑三的幾個兒子也跟著他爸學,看樣子還要往下傳。
那天,我看黑三做活,看著看著,嘴癢癢了。
「三爺,你家的木頭哪來的?」我說。
「買的麼。」黑三說。
「我聽村長在喇叭裡說,水渠岸上的樹讓人偷了,我看你和二叔在水渠岸上轉
悠過幾回,怕是偷來的?」
黑三把脖子擰過來,臉上像抹了一層醬。
「去,去,」黑三說,「你這熊娃咋是個雜嘴子,掙著掙著說話。」
吉祥村的人把憋屎憋尿屙不下硬使勁叫掙。
後來,黑三到處給人說,張清林家的二窩子是雜嘴子,話比屎還多。後來,有
人見了我就叫雜嘴子。我把兩隻賊圓的眼睛撲問了半晌,然後撒腿往家裡跑。
「媽!他們叫我雜嘴子!」我對我媽喊叫著。
「誰叫你往誰臉上吐。」我媽王玉梅給我這麼說。
我真吐了幾次,但不管用。
「媽,我吐了,可他們還叫!」我給我媽說。
我媽把手攥在圍裙裡看了一會兒天。我媽說叫就叫巴掌捂不住眾人嘴,誰讓你
老多嘴多舌?讓他們叫去,雜嘴子就雜嘴子,雜嘴子又不是三隻手不丟人。
就這麼,我成了雜嘴子。
我媽不管,我也就不管了。其實聽慣了並不刺耳。我依然愛說話,想說的時候
嘴就癢癢。
後來,他們突然不讓我說話了。
二
那些天,我發現我哥群生總和鄰村一個叫燕麥的姑娘幽會。他總是在我睡下後,
不聲不響地溜出去。那天晚上,我把腳從被窩裡伸過去,沒找見他的大腿。我立刻
想到了村外那座廢棄的磚瓦窯。被窩裡彌漫著一股濃重的汗臭味。我陶醉在無邊的
想像裡。我想跟蹤他。我很快就把腳從被窩裡抽出來,蹬上了褲子。
我爸張清林和我媽王玉梅正在上房屋裡說胡話。
我怕門軸太響,便提開門坎,把我的頭從門底下送出去。夜色裡的村街像一幅
陳舊的佈景,傾斜著橫在我的眼睛跟前。一片樹葉像碩大的汽球,朝我顛過來,發
出一陣滋啦滋啦的響聲。沒有一個人影。雞不叫,狗不咬。
我一縮身子,從門底下爬出來。貼在大門旁邊的牆壁上,那片樹葉正好在我的
腳跟前。它不像汽球了,也不再滾動。
我順牆根朝城門溜過去。我沒走城門道。我從城門旁的殘牆上翻了過去。
我感到腳上的幾根筋麻了一下,然後就聽見我跌倒的聲音從屁股底下鑽出來,
又伸出去,水漂一樣漂成一溜。我用眼珠子追尋著那一溜響聲,一直到它沉役在黑
暗的盡頭。
我很快來到一個空場跟前。那裡堆著許多草垛。月光很亮。我像一隻靈巧的貓,
在草垛之間閃著、嗅著。我選擇了一個最合適的草垛爬進去。草垛裡有一個草窩,
是我事先堵好的。
一股乾燥的草味和土味撲過來,拐線蟲一樣鑽進我的鼻眼。我險些打出幾個噴
嚏。我趕緊捏住鼻子,往鼻根那裡使勁,把噴嚏堵回去,然後,我又攪了一陣舌頭。
我感到殘留在鼻腔和喉嚨裡的土味和草味被我攪出來的唾沫濡濕了。我放心了一些,
把眼睛對準了不遠處的磚瓦窯。
我正好看見敞開的窯口。
窯口黑乎乎的,什麼也看不清。但一會兒就看清了。我看見兩個黑影一點一點
從黑框裡顯現出來。
我的胸膛裡像飛進了一隻歡快的麻雀。我憋了一會兒氣,讓它跳騰得小了一些。
我把眼珠子固定在眼眶的正中,讓它們一動不動。
那兩個黑影也一動不動,像兩個鼓硬的口袋,一高一低,一粗一細,直直地站
著。他們不吭聲。好長時間他們一聲不吭,就那麼直直地站著。
他們在喘氣。
我聽見了他們喘氣的聲音。他們喘氣的聲音越來越大,身子裡好像有一個吹氣
筒。人在渴極了的時候才會這麼喘氣。他們焦渴了?
突然,我看見高大的黑影向低矮的黑影撲過去。低矮的黑影發出一聲短促的呻
吟。我沒聽過這種呻吟。我媽腰疼的時候也呻吟。我媽呻吟的聲音和我這會兒聽到
的不一樣。我媽呻吟的時候我心煩,也難受。可這會兒,我心裡有一種說不清是恐
慌還是激動的感受。那一聲呻吟像受了驚嚇的母鴨子發出來的,聽得讓人憐憫。
他們糾纏在一起了。他們撕扭著,抖動著,發出一陣更大的喘息聲。他們好像
要掙脫,卻糾纏得更為緊密。他們的腳像撒歡的牛犢,踩踏著地上的磚頭,叭叭亂
響。高大的黑影好像要幹什麼,低矮的黑影卻一下一下彎曲著,躲閃著。
「燕麥,哦,燕麥……」高大的黑影痛苦地叫著。
「哦,群生,哦,不……」低矮的黑影比高大的黑影更為痛苦。
我被他們奇特的扭打著呆了,渾身的骨頭像硬柴一樣。哢啦一聲,我壓斷了胳
膊底下的一根玉米杆。我聽見玉米杆的斷裂聲像鴿子一樣從草窩裡飛出去,在夜空
裡拍打出一串啪啦啦啦的脆響。我恨不得把它抓回來,捂進我的懷裡。
「誰?!」一聲威嚴的喝問從窯口傳過來。
我看見他們猝然分開了。高大的黑影也挺成了一根硬柴。我緊緊盯著他。我想
他也許會走過來。
沒有。他們諦聽了一陣。
「貓。也許是誰家的貓。」高大的黑影說。
「回,我得回了。」是燕麥的聲音。她好像有些害怕了。我看不見她的模樣。
我能想見她害怕的樣子。
「坐。」群生說。他搬了兩塊磚頭。
他們坐在窯門裡邊了。他們好長時間沒有說話。月光裡的磚瓦窯像一塊安靜的
石頭。
我看不見他們的影子,也聽不見他們說話。一會兒,一股熱乎乎的睡意從遠處
向我飄過來。我瞌睡了。幹草葉蝴蝶一樣紛紛矚落,落在我的臉上,身上……
三
早晨是從村口那根木杆上的高音喇叭開始的。
「啪噠」一聲,喇叭開了,然後是一陣滋啦滋啦的聲響。然後是村長吹話筒的
聲音。
「嘭嘭。喂。嘭。注意了,咹——我說個事情。劉存道家的羊丟了,咹,誰看
見了,就給人家送回去,咹,一隻羊富不了日子。為一隻羊動嘴動手打個血嘴青鼻
子不划算,咹,就這。」
「啪噠」,喇叭關上了。
我就是這時候醒來的。我的腳不知怎麼伸到了草窩外邊,我感到腳有些濕涼。
我知道露水濕透了我的布鞋。我把腳動了動,又動了動。然後,我往腰上使了使勁,
坐了起來。我看見落在我身上的草葉像開放了一樣,猛烈地飛起來,又慢慢落下來。
我很快就想起了群生和燕麥。
在窯門裡邊,我看見了兩塊豎著的磚頭。它們面對著面,很滑稽的樣子。
窯裡邊裝著鬥窯的廢磚。
我撓著頭頂上髒亂的頭髮,對著那兩塊磚頭笑了一聲,然後,又笑了一聲。
它們不理睬我。
我走過去,伸出一隻腳,撥倒了左邊的那一塊。我瞅著它們。我伸出腳,撥倒
了另一塊。
我把它們胡亂撥了一陣。
一會兒,我就走在田野上了。
太陽還沒出來。霧像姑娘脖子上的紗巾,這裡一塊,那裡一塊,展著,神著,
不往上升,也不往下落。已經有人下地了,在霧裡動彈著,影子一樣。
「撲踏。撲踏。」有人拉著架子車,在路上不緊不慢地走著。
「唰——唰——」是揚糞的聲音。
有人拼力咳嗽著,清理著淤積了一夜的喉嚨。
剛剛醒過來的早晨像一碗清湯麵。
我走得很不安分,在田野裡斜著走。我險些滑了一跤。我以為踩上了髒物。吉
祥村有好多人清早起來不願上茅房,愛在地裡屙。你不小心,就會踩上一堆新屙的
髒物。
不是髒物,是蔓菁。我蹲下去,飛快地揪了幾把,塞進褲腰裡。我感到蔓菁上
的露水濕上了我的肚子。
「早上有霧,後晌捶布。」我蹦著,顛著,走出了蔓菁地。我從城門道裡走進
去。我看見典典媽和幾個女人頭挨著頭,鬼鬼祟祟地說著什麼。典典媽是個臃腫的
女人,套衫下總是露出一截花布棉襖,紐扣拼力扣在一起,把她勒成一個鼓脹的棉
花包袱。
「啵嘰啵嘰。」我聽不清她們說的話。
她們看見我走過來,嘴巴像突然凍住了一樣。
「啵嘰啵嘰。」我朝他們拌拌嘴。
她們像幾隻母羊,突然甩開蹄腳跑散了,眨眼功夫,就竄進了她們的家門。
我想不通那些母羊們。
一隻貓竄了過來。是王婆家的那只米貓。我一彎腰,就抓住了米貓尾巴。米貓
尖利地叫了一聲,臥進了我的懷裡。我立刻就忘了那些母羊。
我感到我的嘴癢癢了。
沒進王婆家的大門,我就喊叫了:
「王婆,你家的米貓跑了!」
王婆顛著一雙小腳從二門裡搖出來,一臉驚慌。她是吉祥村最後一個小腳女人。
那雙腳像兩個堅硬的餃子。
「跑哪了跑哪了?」王婆只顧著急,沒住我懷裡看。
「我逮住了。」我說。我得意地在貓的脊背上撫著。
王婆提起肩膀,從嘴裡放出一口長氣。
「看你這娃,我當貓真跑了。」王婆說。
「不是我逮住,就跑到後街了。」我說。說話的時候,我的嘴和吃肉一樣愉快。
「後街的娃壞,逮住貓光拔貓鬍子,貓沒鬍子就迫不住老鼠了。有繩繩沒有?我給
你拴住它算了。」
我把膝蓋並在一起,夾緊,從褲腰上抽出一條髒兮兮的褲帶,咬在嘴裡,一撕,
褲帶分成了兩條。我用褲帶在貓脖子上套了一個圈,又在後腿上挽了一個環。
「你要勒死它!」王婆叫起來了。
「勒不死!」我說。
「唰啦」一聲,什麼東西掉在地上了。
「你偷蔓菁菜!」王婆的眼珠子險些滾出了眼眶。
我只顧拴貓,忘了褲腰裡的蔓菁。
「噢麼,」我說,「我給我家豬揪了幾把。我在草窩裡睡了一夜,揪些蔓菁菜
回去我媽就不罵我了。給你貓。」
我把拴貓的繩頭塞給王婆,在她的手指頭上纏了幾圈。
「拴到你家柱子上。」我說。
我系好褲子,拾起蔓菁葉,塞進褲腰,走了。
「你拴在我手指頭上了!」王婆頓著那兩隻餃子一樣的小腳,在我後邊嚷嚷著。
我沒理王婆。我想立刻見到我哥群生。我沒想到他會揍我。他一翻身就抽了我
一個耳光。
四
我隨手把蔓菁葉扔進豬圈,進了群生和我睡覺的屋子。群生平展展趴在炕上,
好像睡著了。我又想起他和燕麥扭打的情景,還有那兩塊磚頭。
我跳上炕,坐在群生的頭跟前。他的兩隻耳朵直直地挺著,長滿了茸茸的細毛。
我在他的耳輪上撥了一下。
他沒動。
我又撥了一下。當我彎曲著手指頭要撥第三下的時候,群生像打別蟲一樣,突
然從炕上彈了起來。我沒看見他的巴掌是怎麼偏過來的。我聽見了一陣疾促的風聲,
那只粗大的巴掌就貼在我的耳朵上,啪一聲。然後,我的耳朵裡就像鑽進了一隻馬
蜂。
他打得太狠了。他從來沒這麼打過我。我感到我的耳朵變成了一隻醬紅的辣椒。
我捂著半個臉,恐懼地看著群生。一會兒,我的眼珠子裡就迸出了火星。
「你打我!」我說。
群生看也不看我一眼,像木樁一樣倒下去。這回,他沒趴。他仰面躺著,眼睛
大張著,看著屋頂上的木椽。
我在挨打的那只耳朵上揉捏了一陣,把目光從群生的臉上移上去,也看了一會
兒屋頂。我憤怒了。
「你打我!」我喊叫了一聲。
群生連眼毛也沒動一下。我從炕上跳下來。
「你敢打我!」我又喊叫了一聲。
我看見了炕倉裡的兩把笤帚。我提著它們,雙手搶開,朝群生的大腿掄過去。
「你打!」我大叫著越掄越狠。
笤帚在群生的大腿上歡快地跳著。有幾下打在了膝蓋上。群生燥氣了,肚子一
縮,從炕上跳下來。
我們對打起來了。
「媽你來看我哥打人呢!」我喊著。
我媽沒像過去那樣跑過來,用笤帚敲群生的頭,給他吐唾沫。群生把我夾在腰
裡,夾到後院的井跟前,用腳踢開了井蓋。
「媽!」我感到我要尿褲子了。
群生沒把我塞進井裡。他把我甩在了井跟前,回屋去了。我真想追過去,在群
生的小腿肚上咬一口。一
我沒有。我朝井口裡看了一眼。我聞見了一股涼水的氣味。我知道井很深。
「媽!」我仰著脖子,朝上房屋裡喊著。
我媽王玉梅從屋裡走出來,看看我,半天沒說話。我看見她把兩隻手捂在了臉
上,一會兒,肩膀就劇烈地抽動起來。
「嗚哇!」我媽王玉梅突然放聲大哭了。
本來我想哭。我想用眼淚水誇大群生打我的後果。我想說群生要把我塞進井裡
淹死。我想我媽王玉梅看見我坐在大張著口的井跟前,就會尖叫一聲,就會變成一
只憤怒的母雞,撲進屋去,在群生的腦頂上撲打,一直把群生打出屋,再從院子裡
打到村街上去。
可是,我媽王玉梅哭了,劇烈地抽動著肩膀。
我很快就知道我家發生了重大的事情。我爸張清林被一輛三輪摩托車帶走了。
一副鐵銬子銬住了我爸的手腕、他把縣上撥下來的修路款借給了王三。王三進了幾
次賭場,屁股一拍跑了。我爸成了貪污犯。
我媽王玉梅又一次哭軟了身子。她還在哭,眼淚水從她的指縫裡往外滲。我媽
哭了整整一天。
我感到我的心裡像塞進了一截潮濕的木頭,正生長著黴菌。我一會兒感到肚子
餓,一會兒又想吐。
我哥群生煩躁得像一隻刺蝟,不是碰倒這個,就是撞翻那個,人到哪裡,哪裡
就會發出一陣稀裡嘩啦的響聲,要不,就幹幹地坐著,一下一下咬牙根。
第二天早上,我媽讓我和她去鄉上看我爸張清林。我媽說他們要把我爸帶到縣
城的監獄裡去。
五
我媽挎著一個小包袱。我們走了很長的路。快到鄉政府大門的時候,我媽停住
了腳步。她看著我的臉。我感到我媽的目光沉重得像鐵。
「管住你的嘴。」我媽說。
我沒聽懂她的意思。
「甭亂說。甭哭。記下了?」我媽說。
我點點頭。
「要不我撕爛它。」我媽說。
我又點點頭。我抿了抿嘴。
我媽說話和她生孩子一樣簡潔有力。她生了五個孩子,傷了三個。我是最後一
個。生我之後,我媽給我爸張清林說:「不生了吧?」我爸想了想,說:「不生就
不生了,由你。」我媽就不生了。我媽一天一天發胖,成了一個胖女人。但我媽決
不臃腫。
我點了兩次頭,我媽還不信任,眼睛直直地盯著我的嘴。我又點點頭。這回,
她好像放心了。
鄉長和鄉幹部正在一個大屋裡開會。我媽拉著我在門外等著。我聽見鄉長在講
話。他是個粗喉嚨大嗓門的人,每一次到吉祥村,都要來我家吃擀麵條。他看見門
外有人,便探出身子,給我媽點點頭,又折回去,繼續講。
「不抓緊春灌,小麥就分不好蘖。」他說,「你們下去,要協助村長,再發現
有人在村上死吃大喝,我就讓他背著鋪蓋卷回家。散會。」
我嘴癢了。我沒管住它。我突然產生了一種說話的欲望。我要給鄉長說句話。
鄉長把我媽王玉梅和我領進他的屋,搬過一把椅子給我媽說,坐。我媽沒坐。
我媽眼紅了。鄉長倒了一茶缸水。我媽說鄉長你甭倒了我不渴。鄉長說你看清林這
人當了半輩子出納當糊塗了怎麼能把錢借給王三?王三說做生意你就信?那是個賭
棍嘛。狗能改了吃屎?鄉長說到了這地步鄉上也沒辦法,那是法律一進局子就成了
法律的事。
我插不進嘴。人想說話又插不進嘴的時候很難受。我的喉嚨裡好像鑽進了一隻
螞蟻,螞蟻的腿殘缺不全,它在我的喉嚨裡掙扎著,要爬出來。
「我想看看人。」我媽說。
「嗨!你看。」鄉長一副遺憾的樣子,「你來早一些就好了。他們把人弄到縣
上去了。」
我媽哭了。人哭的時候臉很難看。
鄉長說:「甭哭,哭也沒用,等著判吧,在縣監獄會受些罪,判了就好了,現
在的勞改農場不像過去。」鄉長的話沒止住我媽的眼淚。鄉長的兩根手指頭在辦公
桌上敲著。
我終於把那句話吐了出來。
「我看見劉幹事在我們村喝酒了。」我說。
「嗯!」鄉長扭過頭看著我。他好像沒聽清我的話。
「死吃大喝。」我說。
我媽突然抬起腳朝我踢過來,踢在我的腳彎上。我險些跪在地上。
「真的。」我說。
鄉長笑起來,「哈哈哈哈!」他仰著頭笑。
我媽抓住我的胳膊,把我從屋裡掄出去。我媽說:「走。」
我媽沒見上我爸。我說了一句話,我媽踢了我一腳。這就是那天在鄉政府發生
的事。
六
我媽突然就會愛我一下。我剛學說話的時候,我媽抱著我給我指太陽,讓我說
蛋。
「蛋。」我說。
我媽立刻會驚叫一聲,一張臉會興奮地紅成雞冠。我媽大聲說「你爸,你聽你
兒說太陽是雞蛋,你聽。」沒等我爸回聲,我媽就在我的臉蛋上吞一口。「愛死了
愛死了,」我媽說,又吞一口,恨不能把我再吞回肚子裡去。
現在,我說一句話,她就給我一腳。
「你千萬把我的話聽一些民生。」我媽說,「咱家和人不一樣了,要忍著,甭
說話,別人往臉吐也甭還嘴。」我媽說這些話的時候一臉痛苦。我媽恨不得給我下
跪。
「一句話也不能說?」我問她。
「少說。」我媽說。
一個多月後,我爸張清林被判了五年刑,到一個叫馬欄的地方勞改去了。聽他
們說我爸趕到風頭上了,要是平常,最多判兩年。我不懂什麼是風頭,只記住了馬
欄和五年。我覺得馬欄叫起來很順口,也好聽。
我媽一聽見馬欄兩個字就滿臉難堪。她很少說馬欄。她總把馬欄叫那地方。
那天,典典媽抱著一堆衣服布料給我媽說:「燕麥她爸要退婚。燕麥她爸是倔
熊人這媒說不成了。」她說。我媽給典典媽化了一茶缸糖水。典典媽喝了一口,說:
「咱有胳膊就會配上袖子。」我媽搖搖頭,沒說話。
我用粉筆在地上畫了一個圈。
「燕麥她爸是個驢糞蛋!」我說。我看著典典媽。
我看見典典媽瞪圓了眼。她看著我,又看著我媽。我媽說:「出去!」我在圓
圈上吐了一口,又踩了一腳。
「我又不是燕麥她爸。」典典媽說,「我說媒說出晦氣來了,我走呀。」
典典媽剛要抬腳,我哥群生堵在了門口。典典媽以為群生要打她。
「群生,呵呵……」典典媽說。
群生走到炕跟前,抓起一塊布料。吱啦一聲,布料被撕成了兩截。吱啦吱啦,
群生一下一下撕著。一會兒,布料全變成了布條。
群生把它們全扔進了豬圈裡。我和群生站在圈牆外邊,看著豬一下一下拱著那
些布條。我聽見典典媽咕咕嚨嚨從我們身後出去了。
「啥人嘛,不尿泡尿水照照。」典典媽出門的時候說。
群生要找燕麥。我媽說你甭去。群生說我要找。我媽說你甭給我丟人。群生說
我的事你甭管。我媽說我要管。群生一甩門走了。
「咦!這狗日的。」我媽說。
我想往外溜。我媽眼尖手快,揪住我的耳朵。
「呆著!」我媽說。
「我要屙屎!」我說。
群生把燕麥叫到一個土壕裡。群生說燕麥你爸是個小人。燕麥順著眼不敢說話。
群生說我給你說話哩!燕麥抬眼瞄了一下群生,瞄得很小心。
一我聽著哩。」燕麥說。
「小人!」群生吼了一聲。他像一隻發狂的野獸,來回走著。「你說,」他逼
到燕麥跟前,「你爸是不是小人?你說。我要你說!」
燕麥的眼裡突然湧滿淚水。
「你甭罵了群生哥。」燕麥說,「我願意跟你好我都快急死了。我是偷著來的,
我爸知道我和你見面會打斷我的腿,有話你快些說。」
群生沒話了。
燕麥捂住臉,身子一擰,跑了。
「燕麥!」群生叫了一聲。燕麥沒回頭。
我從麥地裡爬起來,看著我哥群生。他像霜打了一樣。他也看見了我。他沒說
話。
「我拔草哩。」我揚著手裡的草給他說。
七
我家的大門緊緊閉著。村街上有人放爆竹。
群生在前院不聲不響地擦著他的手扶拖拉機。那些天,他很少動它。村上有人
風傳說要收繳,抵我爸張清林的貪污款。群生一直等著他們把它開走。
我媽王玉梅像螞蟻一樣,一會兒從廚房出來,一會兒又走進去,一臉焦灼。她
夾著菜刀,提著圍裙。
群生輕蔑地瞟著我媽。
我知道我媽的心思。她等著娶媳婦的人家來請她,請她去幫忙。她在鍋臺上是
一把好手,村上有人過事情都要請她。
街道上的爆竹聲和吵嚷聲沒有了。我媽還不死心,不時地朝虛掩的大門那裡瞄。
群生扔掉沾滿油污的棉紗,陰著臉朝我媽走過來。「噌」一聲,他把我媽手裡
的圍裙撕過去,手一揚,圍裙鳥一樣飛出去,搭在了晾衣的鐵絲上。
「燒了去!」群生說,「快把它燒了去!」
我媽沒說話。她木然地看著鐵絲上的圍裙搖來擺去。
「再也沒人請你了,你記著。」群生說。
群生扭身往前院走。我媽的臉一點一點漲紅了。
「我是你媽,群生!」我媽拍打著胳膊吼叫起來,「你管起我的事來了?我在
村上活不了人,在家也不行了?你去把我的圍裙燒了,你試試看。你敢!」
「我看著難受!」群生說。
我媽急了,順手抓起抬水棍朝群生掄過去。群生要躲幾下,我媽就不打了。可
群生不躲。我媽沒臺階下,就一個勁打。群生被打到疼處,就抓住木棍。我媽使勁
往回抽,抽不動,就鬆開手,一頭朝群生撞過去,然後,就張開嘴,要放聲大哭的
樣子。她沒哭,她怕被人聽見,就把哭改成出氣。她張著嘴,一口一口出長氣。
那些天,我哥群生和我媽王玉梅就這麼慪氣。慪完氣,他們就安靜一些,各自
做各自的事情。我們家的門日夜閉著。沒有人來我們家。
後來,他們不太慪氣了。我發現他們總背著我咕咕噥噥說什麼,他們總用一種
怪異的目光看我,好像我是一個小怪物。再後來,我媽王玉梅就把我的嘴撕了一回。
那天,他們在屋裡又咕噥了一陣,然後叫我進去。
「你知道你爸把錢借給王三了?」我媽說。
我搖搖頭。我不知道我媽的心思。「你把你爸的事給人說了,得是?」我媽說。
我眨矇了半天眼。
「說。」我媽說。
我又搖搖頭。
「你說不說?」我媽撕住了我的嘴。
「我沒有!我不知道!」我叫了起來。
「村上有人說是你說出去的。」群生說。
「狗!」我叫喊著。
我媽一用力,就把我的嘴唇撕長了。我疼出了眼淚。
「狗!」我喊著。
我媽鬆開手,看著我。我跳了一下。
「為什麼撕我?」我說。
我媽說不管是不是我害了我爸,撕我的嘴沒什麼壞處,嘴疼了就會少說話。
八
吉祥村小學在後街西頭,很簡陋。一間小屋是老師的臥室和辦公室。小屋旁邊
搭了一間草棚,有些簡單的炊具,老師嫌派飯不可口,就自己做一頓換換口味。一
間大屋是教室,四個年級三十多個學生共用。教室後邊是羊圈,養著幾隻羊,由學
生輪換拔草餵養。羊賣來的錢買笤帚粉筆墨水,不給學生家攤派。老師說這叫勤工
儉學。羊圈也是茅廁,男女學生按時分別使用。老師給村長說專門堵個女茅廁。村
長說鼻嘴娃懂個什麼不夠麻煩的工夫。村長扛著犁正要下地。老師氣得肚子疼。村
長一抬腳,老師就罵了一句:「牛蛋。」村長扭過頭說:「就辦?」老師說:「牛
蛋」,村長說:「噢噢,我會小心的,戳了一輩子牛屁股,還能毀了牛蛋。」
老師叫王文凱,是個半土不洋的人,走路大大咧咧,愛喝幾盅酒,是個吃商品
糧的,和燕麥一個村。
那天,他給我們講溫暖那一課。他說他喜歡啟發式教學法。他一邊講,一邊掐
粉筆頭,打那些做小動作的學生。他總能打到他們的額頭,嘭一聲,很准。
「下雪的時候,你的手凍紅了,腫了,冷吧?」他像背書一樣,在講臺上走來
走去,「你把手塞進熱被窩裡試試,什麼感覺?溫暖!這就叫溫暖!明白嗎?」
「明白!」我們齊聲說。
「嘭。」粉筆頭打中了。
「你凍得渾身打顫顫,牙齒格抖抖響。你從鍋裡摸一個熱紅薯咬一口,熱紅薯
從喉嚨裡往下滑的時候,什麼感覺?」
「溫暖!」我們已懂了。
「對!」老師說,「這也是溫暖。我剛才講的溫暖一樣也不一樣,一個暖手,
一個暖肚子。世界上有各種各樣的溫暖。你對一種溫暖有體會,其他溫暖就好理解
了。我們課文上講的溫暖是另外一種。」
「嘭。」又打中了。
「把課文念一遍,一,二!」
我們齊聲念起來。老師在教室走了幾個來回,然後走出教室看屋簷下太陽的影
子。
「下課。」他朝教室裡喊了一聲。
教室裡立刻亂了。有人叫喊著急急地鑽進了羊圈。
我又想說話了。我看見典典和根舍幾個人正要出教室門。他們一走,教室裡就
沒幾個人了。
「不對!」我喊了一聲。
典典幾個人站住了,看著我。「手凍腫了塞進被窩一點也不溫暖,是癢癢!」
我說。
根舍仰著脖子想了一會兒,說:「是癢癢。」典典在根舍屁股上踢了一腳,說:
「對個屁。」
典典輕蔑地看著我。
「你把手凍腫試試,塞到被窩裡試試。」我說。
「不許你說話。」典典說,「你敢說老師的壞話。」
「我沒有。」我說。
「你爸是貪污犯!」他說。
「你爸是豬!」我說。
「把他綁了!」典典說。
根舍幾個人嗷地叫了一聲,撲過來,扭住了我的胳膊。
「審判。」典典說。
我伸腿朝後瞪了一下。根舍叫喚了一聲,抱著肚子倒在了長凳上。
「把他勾倒。」典典說。
一隻腳伸過來,把我勾倒了。根舍爬起來,騎在我身上,像搧打葫蘆一樣打我
的頭。我一下一下閉著眼睛。
「老師來了!」
典典喊了一聲,從門口跑了出去。根舍鬆開我,也要跑。我恨不能咬他一口。
我抓過一把小板凳,朝根舍甩過去。我聽見根舍哎喲了一聲,然後就看見他抱著腦
頂蹴下去。我站起來,咬著牙齒。我想根舍要過來,我就咬他一口。
根舍沒有過來。他的腦頂上起了一個大包。
九
根舍一見他媽就嗚哇一聲哭了。他媽說咋啦咋啦。根舍說雜嘴子打我了。他媽
一下就摸出了那個肉包。他媽驚叫了一聲,就拉著根舍上街上了。
「看呀!」根舍他媽在街道上大聲野氣地喊著,「是貓是狗也欺侮人呢嘛哎……」
我媽王玉梅站在院子裡聽著。我看見我媽的臉越來越難看。我抱著書包坐在台
階上,不時往我媽的臉上瞅一眼。根舍他媽的唱揚聲越來越大。我感到根舍他媽是
世界上最醜惡的女人。
街道上一定圍了許多女人。
「多險,再重點就砸透了。磚頭?石頭?」一個說。
「砸透了可了得。是誰?雜嘴子?噴噴。」另一個說。
我媽聽不下去了。她朝我走過來。
「他先打我。」我站起來,往後退著。我怕我媽撕我的嘴。我臉上的表情一定
很可憐,要哭了一樣。
我媽的手朝我的嘴伸過來了。
我媽的手又停住了。我媽走到豬石槽跟前,取出攪食用的小木板。
「拿著。」我媽說。
我不敢不拿。我顫悠悠接過攪食板。我的眼一直看著我媽的臉。
「自己搧。」我媽說。
「不。」我給我媽說。
「你搧不搧?」我媽說。
我遲疑著,不知該怎麼辦。
我媽轉身走了。我媽走到了井跟前。
「搧。」我媽說。
「媽!」我叫了一聲,撲過去,抱住了我媽的腿。
「不怪我,媽。」我說。我感到我的眼裡湧滿了淚水。
「搧。」我媽說。
我鬆開我媽的腿,慢慢站起來。我看著那個小木板。它有兩寸寬,一尺多長,
上邊沾滿了豬食。
淚水從我的眼眶裡流出來,蟲子一樣往下爬著。
我把攪食板抬起來,朝我的嘴搧過去。我沒閉眼睛。我聽見「啪」的一聲,然
後就感到一陣火燒一樣的疼痛。
「啪!」我又了搞一下。
「我恨你!」我對我媽喊著。
我更恨根舍他媽。我想了許多整治根舍他媽的辦法。我想在她家門口挖一個深
坑,讓她出門的時候踩進去,折歪她一隻腳。我還想養一隻狼狗,我要訓練它,讓
它專咬根舍他媽。
十
在以後的許多天裡,我沒說過一句話。我經過憋屎憋尿的滋味,也經過吃得太
飽憋胃的滋味,我感到憋住話不說比憋屎憋尿憋肚子更難受。我的喉嚨裡像塞了一
把豬毛。我常常想吐。我一吐就會吐出胃裡的酸水。我常常發呆。有人問我什麼,
我就愣愣地看著他,然後搖搖頭,然後走開。我媽說抱些柴禾來,我就抱些柴禾。
我媽說抬桶水,我就跟她抬桶水。我媽說脫衣服睡,我就啪嘰啪嘰蹬掉鞋爬上炕脫
衣服,鑽進被窩睡覺。那些天,群生早出晚歸,開著手扶拖拉機跑小生意。我不說
話,家裡就只有我媽一個人的聲音了。開始的時候,我媽還有些高興,後來,她就
擔心了。她問我是不是病了。我搖搖頭。我能看出她心裡有些難受,可又實在不想
讓我說話。她歎了一口氣,說:
「民生,不是我不讓你說話,你爸的事把媽嚇怕了。媽再也經不起折騰了。你
一句話說得不是地方就會惹事。你就憋著吧,你實在憋不住了就對牆說,就一個人
自言自語。屎尿能憋死人,話憋不死。世上的啞巴一層一層的,還活人呢。」
每個星期天,我都出去投豬草。草籠拔滿後,我就坐在楞坎上自言自語。一股
風從我的鼻尖上吹過去,我就說,這是夏天的風,夏天的風涼快,要是冬天的風,
就該叫寒冷。涼快和寒冷是不一樣的。遠處的山根下有一片電網,遠看著和蛛網沒
什麼兩樣,我就說,那不是蛛網,那是秘密工廠,在地下哩。
有時候,我也和地裡的草談話。我說:「你看你多好,你沒有嘴,你不為嘴發
愁。」和草說話很安全,想說什麼就說什麼。
回家的時候,我就說:「再見了,下個星期我再來。」我看見滿地的莊稼和草
在風裡搖擺著。如果天上飛過一隻鳥,我也會給它說:「再見。」
一到村口,一碰見人,我就憋住了。
「話憋不死人,」我媽王玉梅說,「啞巴還活人哩。」
我不是啞巴。我到底沒有憋住。
十一
那天放早學回來,我看見群生正給手扶拖拉機加油,加完油,又開始擦車。他
擦得很仔細,擦得手扶拖拉機通體透亮。我知道他要去永壽縣給豬販子拉腳,豬不
通人性,又屙又尿,擦車箱是白擦。可群生連車箱也擦。我張張嘴,想問他,又把
話憋了回去。
「站這不嫌腿困?去!」群生趕我走。他忙乎了好多天,沒掙到幾個錢,心裡
窩火,說話像吃了火藥一樣。
我媽王玉梅正在廚房燒火做飯。她好像沒看見我進來,仰著脖子,一下一下拉
著風箱。我蹲在她跟前,看著爐膛裡的火。火裡的碳像一塊塊紅透的金子。風箱單
調地響著,一聲,又一聲。
「村長來咱家了。村長把手扶車給了黑三家。」我媽說。她依舊仰著脖子,像
自言自語。人在無可奈何的時候,就會這樣。
我立刻想起了我哥群生擦車的樣子。買車回來的時候,群生把我和我媽抱上車
箱,在村外轉了兩圈。他太愛那輛車了。我感到他太可憐了。他正在前院裡擦車。
「醜娃一會兒來開車。」我媽說。
我心裡有些發熱。我想看看群生。
群生已加完油。他仰面躺在手扶拖拉機的肚子底下,用扳手上著一顆螺絲,滲
滿汗水的臉上滿是油污。我看著他,心裡很難過。我很想給他說幾句什麼話。
他用油污的手背擦了擦鼻子上的汗,又撓撓臉,繼續上螺絲。他很用力,一下
一下咬著牙。
醜娃就是這時候從我家大門裡走進來的。他拿著一把玉米花,一邊走一邊吃。
他不用嘴在手裡吞。他一顆一顆往嘴裡扔,扔一顆,嚼一陣子,再扔。
「群生,村長給你說過了?」醜娃給群生說。
群生沒說話。他上好螺絲,從拖拉機肚子底下爬出來,提著扳手,得愣地看著
他剛剛收拾一新的車。醜娃走過去,在車頭上摸摸,拍拍車把。
「你還擦它?還值得擦?」醜娃說,「村上讓我掏三千元,我思量了幾個晚上,
實在不想要它。這可是心裡話。」
我真想在醜娃的臉上搧一把。
群生一抬手,把扳手扔進車箱裡。他沒理睬醜娃的話。
「我把車收拾了一遍,你試試。」群生說。
醜娃把手裡的玉米花全塞進嘴裡,拍拍手,坐在車座上,搖搖車把,拉拉離合
器,一副懂行的模樣。
「你看這離合器,不靈光了。這間,你看這閘,還管用麼?」醜娃說,「我敢
說這車開不了幾天就會變成一堆廢鐵。群生,你把它發動著,我聽聽聲音。」
群生沒動。群生的眉毛跳著。
「噢,我明白,」醜娃說,「我知道你心裡難受。其實我心裡也不塌實。可又
一想,做木匠活買木頭送貨,弄輛手扶也好。三千塊就三千塊,一咬牙的事情。世
上的許多事就是個一咬牙,一咬牙也就辦了。」
群生臉上的肉抖起來了。我想群生會撲過去,揪住醜娃的頭髮,把他從車上揪
下來,再從門裡踢出去。
群生沒有。群生看著醜娃,一下一下咬著牙根。
醜娃在車座上顛屁股晃著。
「你看這,到底不如新車,像臭毬老漢的尻子,沒彈性了嘛。」醜娃說。
塞在我喉嚨裡的那一把豬毛一點一點變硬了,長了,要從我的嘴裡長出來一樣。
我想喊。我想對醜娃說一句刻毒的話。
「呀!」我怪叫了一聲。
醜娃和群生被我突然的怪叫聲嚇了一跳。他們扭過頭來,直直地看著我。
我肯定說了一句什麼話。在我的那句話惹禍以後,我怎麼也想不起我說了什麼。
但我肯定說了。我的話使醜娃大丟臉面。然後,我就發出一串乾笑。我笑出了眼淚,
笑酸了肚皮。我好像要笑傻了一樣。
「嘻嘻嘻嘻……」我笑著。
「哈哈哈哈……」我還在笑。我故意這麼笑。
我看見醜娃的臉色紅了,又白了。我媽從廚房跑出來,在我頭上拍了一把。我
立刻止住了笑聲。這時候,醜娃的臉已板了起來。他把脖子朝群生扭了過去。
「群生,」他說,「你兄弟倆想把我當猴耍,得是?難道我是猴?不是我非要
這車不可,是村長三番五次來找我嘛。你不願給,我還不稀罕這爛熊東西呢!」
「咣」一聲,醜娃提著攪把,在車頭上敲了一下。
「甭敲!」群生說。
醜娃拖長腔哎了一聲,說:「現在這車是我的了,我愛敲就敲。我把它敲成一
堆爛鐵由我哩。你屙屎球動彈甭鼓那閑勁。」
「你,你甭欺人太甚。」群生說。
醜娃揚揚手裡的攪把,越說越刺人:「群生,我不欺你,我讓給你敲,咋樣?
你給村上拿出三千元錢,你把它破爛就由你了。咋樣?」
群生的臉變成了豬肝。群生突然轉過身,從豬圈後掂一把鐝頭,朝手扶拖拉機
搶過去。他像一隻張開翅膀的大鳥。
「群生!」我媽王玉梅悲慘地叫了一聲。
鐝頭重重地砸在手扶拖拉機的頭上,「哐嚓!」那裡立刻出現了一個難看的坑,
油漆碎片飛蹦起來,又紛紛跌落。「哐嚓!」又一聲。
群生一下一下砸著,手扶拖拉機迅速地改變著形狀。眨眼的工夫,那輛擦得油
光鋥亮的手扶拖拉機就真的變成了一堆廢鐵。
我感到群生砸得很痛快。我甚至也想提一把撅頭和群生一塊砸。我還想,車要
是醜娃的腦袋就好了。
砸!砸!我在心裡叫著。
鐝頭聲突然停止了,群生大口地喘著氣。
群生掄鐝頭的時候,醜娃大睜著眼,鼓著眼珠子一動不動。這會兒,他眼珠子
慢慢收進了眼眶裡。
「好。」醜娃說,「你砸得好。三千塊錢聽了幾聲響,好。」他說,「這與我
不相干。你砸,接著砸。我走呀。」
醜娃一邊說一邊從我家門裡退了出去。
群生一甩手,鐝頭飛到了牆根底下。他回屋去了。
我媽王玉梅變成了一截木樁。她愣愣地看著那堆廢鐵。院子裡突然沒了一點聲
音。
我有些害怕。我感到一股冰涼的東西在我脊背上爬動。我朝我媽跟前靠了靠。
我媽的身子抖了幾下,又抖了幾下,然後,我媽渾身的肉都抖索起來。
我媽突然抓住我的頭髮,尖叫了一聲:
「怪你!」
我的頭皮收緊了,一陣陣疼。我的鼻眼裡像塞進了一根辣椒。我的眼向上翻著。
「怪你!」我媽又叫了一聲。
我憤怒了。我恨不得踩我媽一腳。
「他砸的,賴我!」我也叫了一聲。
「你……你!」我媽王玉梅的舌頭好像缺了一塊,咬不清字了。她鬆開我的頭
發,風一樣刮進二門,回屋了。
我懵了。
十二
我在院子裡站了整整一天。沒人搭理我。
早飯沒有吃成。中飯我媽沒做。我媽和群生一直關在各自的屋裡。他們一聲不
吭。傍晚的時候,我看見我媽進了廚房。飯好了,我媽和群生吃飯。群生拖著鞋,
慢騰騰從屋裡出來,蹲在小木桌跟前,抱起粗瓷大碗呼嚕呼嚕喝粥,不時夾幾根鹹
菜,格噌格噌嚼著。
我定定地看著我哥群生和我媽王玉梅。我的腸子裡時不時滾過幾個氣泡,咕咕
響。我站了一天,又累又餓,我希望我媽和群生叫我進去。我想他們不管誰叫我一
聲,我就會走進去抱起粥碗。可是,他們不叫我。他們看也不看我一眼,好像家裡
根本就沒有我。他們喝著,吃著。稀溜,格噌格噌,稀溜。他們不管我。
天很快黑下來。群生又進屋了。我媽喂過豬,把圍裙搭在鐵絲上,也進屋了。
我的心裡突然生出一股仇恨。我恨群生,也恨我媽。他們是故意的。我想站死
在院子裡。我想我能站死就好了。我想我真的站死了他們就會後悔,就會哭。我想
出許多我站死以後的情景。我想我媽會哭得像淚人一樣。哭,你哭。你一輩子會哭
的。
屋子裡沒有一點響動。
我想弄出些響聲來。我要讓他們聽見。我咬緊牙叫喚了一聲。我攥著拳頭在我
的頭上胡亂打。我狠狠抓著我大腿上的肉。我撕著我的嘴,撕得老長老長,讓喉嚨
擠出一聲聲痛苦的叫喊。我想我媽和群生一定在聽。
屋裡還是沒有響動。我看不出他們會把我叫進去的一點點跡像。我已折騰得很
累了。我停下來,只一聲一聲呻吟著。我把頭放在脊背上呻吟。
「群生。」我媽在屋裡喊著。
我立刻停住了呻吟。
「二門關了沒有?」我媽的聲音很平靜。
「沒有。」群生在另一個屋裡說。
一陣響動後,我看見我媽披著衣服走出來,站在二門跟前看著我,好像問我進
去不進去,不進去她就關門。
我什麼也不說,可我真怕她關門。她真關了門,我就是怎麼折騰也不頂用了。
我媽王玉梅合上了一扇門,又要合另一扇門。
我再也堅持不住了。我感到我的腿突然軟了。
「媽!」我大叫了一聲,跪下去。
「媽!」我叫著,「我再也不多嘴了!啊,啊,啊……」我哭喊著朝我媽王玉
梅爬過去,頂住了沒合上的那扇門。
「啊,啊啊……」我哭著,淚如雨下。
十三
我撕嘴的時候並沒感到怎麼疼,可第二天就感到了,我照鏡子一看,才知道我
的嘴腫得翻了起來,像遭了馬蜂。
我沒去學校。
我一個人在村外的水渠岸上溜達著,踢著渠岸上的爬地草。我踢斷了許多根。
後來,我不踢了,我順著水渠胡亂走,不知怎麼就走到了那個堆草垛的空場跟前。
我在我曾經睡過一夜的草垛邊上坐了一會兒,然後,走進了那座破瓦窯。
我站在窯裡,看著那些爛磚頭。我突然產生了一種奇怪的欲望。我想把磚頭刻
成人的模樣。
我一連刻了好多天。每天放學回家,我都要去磚瓦窯,坐在那裡刻磚頭。我刻
了一大堆。我把它們放在我的周圍。它們圍繞著我。我也不知道我為什麼要這麼做。
那天,輪我們班給學校裡的羊拔草。我知道一個草多的地方,很快就拔滿了草
籠。正要回去的時候,我看見典典和根舍提著草籠朝我走過來。自從那次打架以後,
我沒和他們說過話。我不想理他們。他們走到我跟前了。
「雜嘴子,」典典看著我草籠裡的草,「知道這裡草多,為什麼不叫我們?」
「砸了我一板凳,還沒還你哩。」根舍說。
我看著他們,不說一句話。
「把你的草分我們一點。」典典說。
「不給就搶。」根舍說。
「把他的嘴糊上,甭讓他喊叫。」典典說。
根舍從衣袋裡掏出一卷黑膠布。典典伸出一條腿,放在我腿後,把我推倒。根
舍撕開膠布,往我嘴上貼。
典典和根舍分了我草籠裡的草。根舍說給他留點吧。典典說不留,讓他再拔去。
典典朝我的草籠尿了一泡尿水,說:「甭給老師告我們。」
他們走了。我沒再拔草。我一條一條撕著嘴上的膠布。我聽膠布離開我的嘴皮
時發出一種「吱吱」的聲音。
我把它們捏成了一個圓疙瘩,放在手心裡看了一會兒。我提起空籠朝磚瓦窯跑
去。我好像瘋了一樣跑著。
我站在窯門口,看著我刻好的那些磚頭。我哭了。我的眼淚悄兒沒聲地往下淌
著。我想給那些磚頭們說些話。我想求求它們。它們用各種表情看著我。
突然,磚頭們在我的周圍動彈起來,它們不是磚頭。它們變成了許多人臉。它
們都是我認識的人臉,我媽,我哥,還有典典和根舍,也有王老師和燕麥。它們朝
我圍攏而來。
我不停地咽著唾沫。我感到我的喉嚨很幹。
我抱起一塊磚頭。「你為什麼不讓我說話?」我說。我挨個兒問它們。我聽不
到一句回應。它們又硬又澀。
我把手裡的磚頭使勁甩了出去。磚頭砸在其它磚頭上,發出一陣空洞斷裂聲。
「嘩啦啦啦——」我推倒了一排磚頭。
「嘩啦啦啦——」又一排磚頭倒了。
我在窯裡亂砸著。磚頭們倒塌著,碎裂著。我已經筋疲力竭了。我趴在磚頭堆
上喘了一會兒氣。後來,我慢慢閉上眼睛。我感到從窯頂洞口射進來的陽光悄悄向
我移過來,落在我的脊背上,又從我的脊背上滑了過去。
我媽找見我的時候,已是半下午的時辰。
「你一個人鑽在破窯裡做什麼你?」我媽說。
我眯著眼,不說話。
「我問你話哩!」我媽說。
我用舌頭舔著嘴唇,依然沒說話。我媽拽著我的胳膊,一直把我拽到飯桌跟前。
我沒動筷子。我不想吃。
「給你留了半天了,不吃等我給你喂呀,得是?」
我站起來,走進屋,頭朝炕牆躺下。我媽跟進來,在炕跟前站了一會兒,又出
去了。
「咋啦?」群生問我媽。
「看牆哩。」我媽說。
我媽沒說錯。我一直看著炕牆。我緊盯著一塊地方。一會兒,那裡就會現出各
種各樣的圖畫,不停地變換著。也許是一張臉,也許是一頂帽子,也許是一棵樹,
甚至是貓的一條尾巴。我就這麼看著炕牆上的一塊地方。我感到我身體裡的水分正
一點一點流失。我的肚子裡空空蕩蕩。
後來,他們說我病了。
十四
群生和燕麥又見了一面。群生說醜娃日他媽腰裡有錢口氣大,粗話太傷人,我
受不了,我把手扶機砸了。燕麥說你看你一點氣也不受,還能收拾不?群生說我把
它砸成一堆廢鐵只能拆零件賣了。燕麥說你看你真是的。群生說一砸,我就後悔了,
本來,是給我爸頂帳的,幾鐝頭就砸沒了。燕麥說那咋辦那可咋辦?群生說我出去
打工呀。群生仰頭看著遠處,喉節一動一動,一臉悲壯的神情。燕麥看著鞋尖半晌
沒說話。群生說沒啥難腸的我不連累你。燕麥急了,毛毛眼上閃出幾星淚花。燕麥
說你就會說這種話傷我的心。群生說你爸沒找你的茬?燕麥說他要給我找婆家,讓
他找去,找下了,讓他跟人家去。群生說我不能娶你了,我得出去掙些錢,掙點錢
再說。燕麥說這我管不了你反正我死活是你的人。群生放心了。第二天,他去外縣
的一個水泥廠打工去了。
群生是天麻亮的時候走的。我媽王玉梅給他烙了一袋面餅。我媽說錢難掙屎難
吃,遇事嘴軟一點。我媽還說甭死心眼兒,傷了身子骨是一輩子的事。
我跳下炕,提著書包一直追到村外。群生已走遠了,像一個黑皮球,在水一樣
波動的莊稼上邊漂搖著,越漂越遠,不見了。我想像著群生背水泥時的樣子。我為
他傷了一會兒心,我在城壕邊上轉了一陣,然後拐進了學校。我感到頭有些疼,沉
甸甸的,像在鹽水缸裡泡過一樣。後來,我感到我不只是頭疼,腿也有些酸軟,渾
身發困。我很想在什麼地方睡一覺。上自習的時候,我不停地打盹。我感到有人走
到我跟前了。我努力地睜著眼。我睜不開,我的眼皮又重又澀。我脖子一軟。頭碰
在了木板凳上。
「哄」一聲,滿教室的人笑起來。
我抬起頭,張大眼睛看著他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
「咳,咳。*王老師在我身後咳嗽了兩聲。
我站起來,等著挨批評。
「咋啦。」王老師說。他沒罵我。
「我,我困。」我說。
王老師皺了一會兒眉頭,說:「你回去吧。」
正是做飯的時候。我媽王玉梅在院裡抱柴禾。她看見我提著書包站在門口,立
刻把眼睛瞪成了圓環。
「你,逃學了?」她說。
我順著眼。我感到我的脖子像軟面一樣。
「說!你,逃學了?得是?」我媽說。
「我因……」我說。
我媽放下抱著的柴禾,摸摸我的頭,又用嘴唇在我的額顱上貼了一會兒。她總
是用這種方法看我是不是發燒。如果我發燒,她就會驚叫一聲。
這回,她沒有驚叫。她眨了幾下眼。
「不會是怪病吧?」她說。
「我困。」我說。
我媽眨著眼朝天上看著。然後,我媽給我請了兩個人。
十五
先請來的是村上的醫生殷涼亭。
我困乏極了,可躺在炕上怎麼也睡不著。我的頭裡邊塞滿了許多稀奇古怪的東
西。恍惚中,我好像走進了一條長街。那是我從沒去過的一條街。街道上擁滿了人。
他們的臉上沒有表情。他們不說一句話。他們排成隊在街道上走著,看不見頭,也
望不見尾。他們像衣服架子。衣服的擺動是街道上惟一的聲音。
我被我看見的情景驚呆了。我很害怕,我突然產生了一種想尿尿的感覺。
「啪噠!」什麼東西掉在我頭頂上了。
是鳥屎。一隻黑色的鳥從我的頭頂上飛過去。它沒有鳴叫。衣服架子的隊伍還
在街上無聲地走著。
「民生,民生。」有人搖著我的肩膀。
我睜開眼,殷涼亭已坐在炕沿上了。他正從藥箱裡取針盒子。
「倒水。」殷涼亭說。「針管要消毒。」
我媽倒了一碗開水。
殷涼亭取出針管,又取出一支體溫計,夾在我的腋窩裡,然後拉過我一隻胳膊,
把兩根手指頭壓在我的手腕上。我感到我手腕上有一條筋在殷涼亭的指頭底下蹦蹦
跳著。
「張嘴」
我張開嘴。
「啊——」殷涼亭說。
我啊了一聲。殷涼亭說再啊。我又啊了一聲。
「舌頭。」殷涼亭說。
我伸舌頭。殷涼亭看了一陣,說:「嗯。」
「屙屎不?」他說。
我搖搖頭。
「屙屎硬不?」
我又搖搖頭。殷涼亭嗯了聲,做出一副沉思的樣子。
「沒胡吃?」殷涼亭問我媽。
「沒有,沒有麼。」我媽說。
殷涼亭取出體溫計,舉在空中看了一陣,又嗯了一聲。「沒病。」他說。
我媽一臉狐疑張了張嘴,想說什麼。
「沒病。」殷涼亭說。他把取出的針管又裝進了盒子。
「娃說他因。」我媽說。
「春天麼,人都發困。這叫春困。」殷涼亭說。「我也發困哩。」他已背好藥
箱。「沒打針沒吃藥不給你要錢了,你把碗裡的水倒了去。」
殷涼亭背著藥箱走了。我媽抄著手想了一會兒。
「能看病,能看個熊。」她說。
她出去不長時間,就請來了王婆。
十六
王婆看也不看我,一進門就說:「倒水倒水。」
「水早倒好了。」我媽說。
王婆說噢噢取筷子去。
我媽取來一雙筷子。王婆說:「香,香。」我媽從牆壁上的鏡框背後取出一把
香,吹吹上面的灰土。
「一根。一根就夠了。」王婆說。
王婆從懷裡取出一張折疊成三角的紙,用香挑起來,在我的頭上繞圈子,嘴裡
啵嘰啵嘰念著什麼。
門口一黑,王老師從門外走進來。他給我媽擺擺手,不讓我媽招呼,怕打攪王
婆。我媽給王老師挪過一把椅子。王老師從口袋裡摸出一個紙條捲煙卷。
「娃沒去啥地方?」王婆問我媽。
「去磚瓦窯了。」我媽說。
「噢噢。」王婆說。她爬上炕,兩隻小腳碰了幾下,抖掉小鞋上的土,爬到炕
牆跟前,挑著那張三角紙在牆壁上劃圈子。
「啵嘰啵嘰啵嘰……」
劃著劃著,那張紙竟粘在了牆上。
「你看你看,」王婆說,「娃的魂跑得老遠了。你看娃蔫了嘛,蔫成啥了嘛。
火。」
我媽把火柴遞給王婆。王婆燒了那張紙,然後跳下炕,把那根筷子豎在水碗裡,
又啵嘰啵嘰念起來。
「立住。立住。」王婆給筷子說。
筷子竟直乎乎立在了水碗裡。王婆說:「你看你看。」我媽說:「就是就是。」
王婆撥倒那兩根筷子,橫放在碗上,說:「西邊小鬼東邊神,放了我家小人人,騎
上驢,跨上馬,想上天就上天,想人雲就人雲。」「好了。」王婆說。
「我給咱做飯。」我媽說。
王婆說不了不了。這時候,她才和王老師打了一聲招呼。王婆說:「你們識字
人不信這。」王老師說:「信,咋不信。」他們笑了幾聲。我媽說:「你看這事,
把你整的,我給你化缸子糖水喝。」王婆說:「不了不了,我家那只米貓總往外溜,
貓不是狗誰給它吃它就愛誰。」我媽說:「你看你,一口水也不喝。」王婆說:
「姓要緊,你看娃,不送了我能回去。」說著,小腳就蹺出了門坎。我媽說:「送
送,送送,看你說的。」
王老師蹴在椅子上抽煙。他到人家裡聊天的時候總愛這麼蹲在椅子上。我一直
在炕上躺著,瞪著眼,一會兒想那條長街和長街上的衣服架子,一會想那滴鳥屎。
「啪噠」一聲,滴在我的頭上。那是一隻黑鳥。
我媽一進門就給王老師說:「殷涼亭看病總沒個長勁,請王婆來撚弄撚弄,也
許會項些事。」
「哦。哦。」王老師點點頭。
「許是娃心累了。」我媽說。
「哦。哦。」王老師說。他好像琢磨著什麼。
我媽說:「民生,你看你整了多少人,老師也來看你。」王老師說:「沒啥,
我沒啥,快考試了,娃沒病就好,我也走。」王老師把煙把兒扔在地上,用腳蹭蹭。
他看了我一眼,走了。
我怎麼也想不到,許多天以後,我會像一頭暴怒的獅子朝王老師軟活的肚子接
過去。
十七
我依舊憋著,不說一句話。
那天,王老師在講臺上發考卷念分數。我很緊張地盯著王老師的臉,等他念我
的名字。
「劉勝利,81分;趙典典,49分……」
學生們領過考卷,都到院子裡去了。教室裡的學生越來越少。我感到我的心一
點一點往喉嚨眼蹦著,越蹦越快。早該念我的名字了,可王老師沒念。他看也不看
我一眼。
最後幾個學生走出教室,只剩下我一個人了。我的心猛烈地跳著。王老師收拾
著粉筆盒,要走的樣子。
我不知道我的考卷出了什麼事情。我支撐不住了,從座位上站起來。我感到我
臉上的皮一陣陣發緊。我張著嘴,想問王老師一句什麼,又想不出要問的話。我想
哭。
「放學了放學了。」王老師朝院子裡喊了一聲。
學生們轟一聲湧進教室。又轟一聲湧出去。
我直直地站著。我不知道我該怎麼辦了。這時候,王老師才對我說了一句:
「到我屋裡來。」
我來到王老師的那間小屋。王老師好像並不急著和我說話。他慢騰騰收拾著桌
上的東西,然後倒了半盆開水,開始刮鬍子了。他給鬍子上抹上肥皂,坐在椅子上
一下一下刮著,刮得很仔細。他不看我。學校裡很安靜,偶爾能聽見幾聲羊叫。
王老師刮到一半的時候,突然開口說話了。
「你說,你考得好不好?」
我想不到他會提這麼個問題。我不知道該怎麼回答。他突然的問話使我拿不准
我自己了。
「說麼,好不好?」王老師問一句,刮一下鬍子。
「嗯……啊……」我說。
「好?你說好?」王老師站起來。
我搖搖頭。
「不好?」王老師的聲高了,又朝我跟前逼了一步。
我不吭聲了。我感到我的心裡正聚積著什麼東西。
「想想,想好了再說。」
王老師又刮他的鬍子了。他在折磨我。我到底受不住了。我的臉憋得快要漲破
了。
「我不知道!」我突然沖著他吼了一聲。
王老師愣了一下。他走到我跟前,在我的屁股上踢了一腳。我趔趔身子。他又
踢了一腳,又踢了一腳。他看著我的臉。我的眼眶裡滲滿了淚水。
「嘭!」又一腳。
豁出去了!豁出去了!我咬著牙,在心裡喊著。
王老師定定地看著我。
我鼓足力氣,一頭朝王老師撞了過去,撞在他的肚子上。他經不住我突然的一
撞,朝後退了幾步。刮胡刀從他的手裡飛出去。
我咬著嘴唇。我想他再踢我,我還要撞。
他沒踢。我像貓逗老鼠一樣。
「來,再來一下。」他說,「有膽量就再撞。」
撞!撞!我一低頭,又撞過去。我撞著,踢打著。我一聲不吭。王老師躲閃著,
瞅空子在我的身上拍一巴掌。
就這麼,我們打起來了。我們從屋裡打到屋外,一直打到羊圈裡。後來,我們
都沒了力氣,我們趴在羊圈裡互相瞅著,喘著粗氣。我們趴了好長時間。
「噗——」王老師吹著氣。他沒刮完鬍子,像怪物一樣,給我笑著。
「噗——」我也吹著,像一隻小魯。我不笑。
「民生,」王老師上氣不接下氣,「我告訴你,噓,噗,你考得很、很好,噓,
是你們班最好的,噗,最好的一個。」
然後,他放聲笑了。
「哈,哈,哈哈哈哈……」他翻過身,仰面朝天,笑出來一串聲音。
我感到我臉上的皮一點一點松了。我咧開嘴,也笑起來:「嘿,嘿,嘿嘿嘿嘿……」。
我感到我心裡有什麼東西正在開放。
我爬起來,跑了。
王老師還在笑:「哈哈哈哈……」
我一直跑到北坡上。我的心裡裝滿了幸福。我平展展躺著。我把一塊碎玻璃放
在眼睛上看天。天又高又遠。太陽很亮。幾隻雁在天上飛著。伸著翅膀。
我聽見了幾聲牛叫。我產生了一種奔跑的欲望。我跳起來,掄著布衫朝一群牛
跑過去。
我爬上一頭牛的脊背,在牛肚子上砸了一拳。牛猛地一下揚開蹄子奔跑起來。
「下來!下來!」
我聽見有人失眉吊眼地喊著。我不管。我又在牛肚子上砸了一拳頭。我在牛背
上噢噢叫著。
一群牛跟著我奔跑。我們跑上了另一道山坡。
土坡下是一片又一片麥田。麥子在金燦燦的陽光裡起伏著,搖動著。
「嘿嘿,嘿嘿。」我對著麥田笑著。我不知道我為什麼那麼高興。我真想跳進
麥浪裡打滾。
我真感激王老師。在以後的許多日子裡,我都懷有一種溫馨的心情。
十八
我媽王玉梅在地頭掐了個麥穗,兩手揉了幾下,吹去麥殼,手心裡就滾出十幾
顆金黃的麥粒。我看見她臉上的喜色沒爬上眉梢梢,又退了下去。
已經有人開鐮收割了,能聽見麥壟裡嚓嚓的鐮聲。
「再不割就搭不住鐮了。」我媽憂慮地看著滿地的黃麥,又看著遠處。突然,
她的眼睛直了。
「民生你看,那是不是你哥?」她說。
我順著她的目光看過去。我看見群生扛著一把大掃帚從遠處的土坡上走下來。
「民生,是你哥。」我媽王玉梅變成了一隻肥胖的雀兒,「回,咱回,讓你哥
甭來地裡,回家去。」
晚上,群生把屋裡的燈掛在了窗櫺上,照得院子通亮。我媽王玉梅把收割打碾
用的農具全翻騰出來,擺了半個院子。我給群生端來一碗涼水,蹴在他跟前看磨鐮。
我媽站在門後一張一張數著群生打工掙來的錢。她數了好幾遍。她揭開箱子,把錢
夾在包袱裡,給箱子上掛了一把鎖。然後,又翻騰出幾個麻袋,坐在臺階上補縫老
鼠咬破的小洞。她一邊補縫,一邊問群生背水泥的事情。群生說他有些不想去水泥
廠了。我媽看了群生一眼,說:「一月掙二三百塊錢,咋不去了哩?」群生說:
「這麼掙,幾年也還不了爸的欠帳。」
「那咋辦?在屋裡呆著一分錢也沒有。」我媽說。
「有人卷花炮掙了大錢,發了財。」群生說。
我媽想了一會兒,搖搖頭,說:
「那是個危險事情,不成。」
「出死力不危險可掙不了錢。人喝涼水也會噎死哩。」群生說,「人家咋就不
怕危險?」
我媽又想了一會兒,說:「人家是人家,咱是咱。」
「我就這麼說說,」群生說,「卷花炮要買火藥買紙還有其它東西,咱也沒那
麼多錢。」
「就是麼。」我媽說,「咱沒那麼大肚子就甭吃那麼大的饃。」
群生沒再說話。我媽縫好了一個麻袋,蹦一聲咬斷了線。
然後是收麥,運麥,打碾。學校放了十天忙假。
割麥的時候,群生在前邊割,我媽在後邊捆麥捆。我提著草籠撿遺落的麥穗,
找黃鼠窩,用瓦罐提水灌黃鼠。
揚場了。群生用木鍁揚麥,我媽戴一頂大草帽,用群生買回來的那把大掃帚掠
著麥堆。麥殼被風吹走了。麥粒像珠子一樣落下來,在我媽的草帽上、麥堆上蹦跳
著,發出一陣陣散亂的脆響。我提著一把小笤帚,把蹦到遠處的麥粒掃回麥堆。我
不時地看著我媽和群生。我感到他們勞動的樣子很好看。那些天,我們全家人的頭
發眉毛和耳朵鼻眼裡都沾滿了灰土,每次都會洗出一盆黑水。我媽蹴在臉盆跟前,
用浸滿水的毛巾在脖頸上拉著。水像愉快的小蟲子一樣從她的脖子上淌下來,一直
淌過胸脯。群生洗臉的時候總是胡吹氣,噗哧噗哧,很響。群生的頭髮又黑又厚。
他洗完頭不用毛巾擦。他用手捋幾下,然後像狗一樣使勁搖頭,搖出一圈又一圈水
花,很氣派。
然後是交公糧。那天清早,村長把吉祥村交公糧的人集中在一起,拉著挑著推
著,還動了幾輛手扶拖拉機,浩浩蕩蕩出了村子,朝王樂鎮糧店去了。我一直跟到
城門外。我想我哥群生也在裡邊,有我家的糧食,我的心裡就一熱一熱的,直想淌
眼淚。
十九
我到南仁村去了一趟。群生讓我找燕麥。
「民生,你給哥到南仁村跑一趟,叫燕麥今晚去磚瓦窯,我有話給她說。」他
這麼給我說了。
「她爸打我咋辦?」我說。
「你甭讓他撞見。」他說。
南仁村離吉祥村不遠,二裡地,抬腳就到了。
我沒撞見燕麥她爸。我從燕麥家的後牆上翻上去,看見燕麥正在後院裡簸麥。
撿麥子裡的土坷垃。我朝她扔了一個土塊,正好打在她懷裡的簸箕上。她嚇了一跳,
抬起頭看我。我給她笑笑,用手劃了一個大彎。一會兒,我們就坐在了村外池塘邊
的柳樹上。
「你爸呢?」我說。
燕麥掩住嘴笑了。
「你這麼大個人還你爸呢?好像你是個大人。」燕麥說。
「我哥不讓我撞見你爸。他讓你去磚瓦窯,」我說,「老地方。」
燕麥又笑了。「你哥給你說是老地方了?」
「我哥沒說。我知道我哥總讓你去磚瓦窯。」我說。
「格兒,格兒。」燕麥笑得很好聽。
「你甭笑,你死活得去,我哥明天就去水泥廠。」
那天晚上,我沒去磚瓦窯偷聽。我躺在炕上想著他們說話的情景。我媽在廚房
烙面餅,讓群生帶著路上吃。後半夜,我被尿憋醒了。我起來撒尿,看見我媽已睡
了。自從我爸張清林走了以後,我就和我媽一個屋睡。我不知道群生回來沒,就到
他的屋門口聽了聽。裡邊有群生睡熟的呼吸聲。
天還沒亮,我就被一陣驚慌的砸門聲驚醒了。我看見我媽王玉梅忽一下坐了起
來,邊穿衣服邊問:
「誰?來了來了。我的爺呀,不知又出了啥事。」
我媽跑出屋,朝群生屋喊著:群生起來快起來我聽像是燕麥。
門剛開了一條縫,燕麥就急急地撞進來,她披著一頭亂髮,滿臉蠟黃。她說她
和群生見面的事讓她爸知道了。她爸打了她一頓,要找群生鬧事。燕麥說完了就哭。
我媽也有些怕了,看著群生,說,這可咋辦?這可咋辦?群生陰著臉,半晌沒說話。
「你可不能打他,再說他也是我爸。」燕麥說。她怕群生管不住性子揍她爸。
二十
燕麥她爸一腳就踢開了我家的門,一把就揪住了群生的頭髮。他是個五十多歲
的男人,又瘦又小,手上的勁卻很大。我媽說:「親家,有話慢慢說,你把娃放開。」
燕麥她爸說:「屁,誰和你是親家,我揪的是搶人的土匪。」群生說:「六叔,你
放開我,人看見了笑話。」燕麥她爸說:「你還怕人笑話,你勾引我女兒還怕人笑
話?怕人笑話我就不來了。」
燕麥她爸揪得更緊了。群生貓著腰,疼得直閉眼睛。
「我就是要揪著你看你咋辦,」燕麥她爸說,「彩禮退給你了,你憑什麼還勾
弓哦女兒?你還算不算人?」
群生說:「六叔你這麼揪著我直不起腰我沒法和你說話。」
「我和你沒話說,我要和吉祥村的人說,走,咱到街上去。」燕麥她爸把群生
往大門外揪。
群生往後使著勁,說:「我不去。」
「我揪著你去。」燕麥她爸說。
燕麥急了,從屋裡跑出來,要拉她爸的胳膊。
「走開!」她爸說,「不走開就蹬你一腳!」她爸橫著眉毛。
我媽拉住燕麥,說:「你甭言語你回屋去。」燕麥不回。
「爸,你放開他,你把他的頭髮揪掉了。」燕麥說。
「我要揪!我要把他揪成禿子!」她爸說。
燕麥她爸到底把群生揪到了村街上。
「吉祥村的人哎!」他大聲野氣地喊著,「你們給我個公道哎!吃屎的把屙屎
的困住了,吉祥村的人哎!有沒有說公斷直的人!」
村街上很快圍了一堆人。燕麥她爸揪著群生的頭髮不鬆手,喊得嘴裡泛著白沫。
我媽把我拉到一邊說:「快去學校喊王老師,小廚房冒煙哩許是來了。他們是
一個村的人,也許能息事。」
要不是王老師,誰也說不準燕麥她爸會鬧到什麼時候。王老師走出拐巷就高聲
嚷起來:
「大清早誰在街道上喊叫哩咹?」
人們給王老師讓開一條道。
「是馬六啊,」王老師說,「有啥事屋裡說不成,得是?大街上這麼喊怕人不
知道你馬六喉嚨高嗓門大,得是?」
「你是教書先生你來說說,」馬六說,「社會主義治不治勾人拐人的?」
王老師說:「社會主義也不興揪人頭髮,你趕緊把人放開。」
「我不放。」燕麥她爸馬六說。
王老師說:「你在咱南仁村撒潑沒人管,可這是吉祥村,你再這麼揪著不放,
吉祥村的人就不答應了。」
馬六愣住了。王老師的話真有些管用,人群裡果真有人說話了:
「把人放開!」
「叫村長去!」
村長就在人群裡站著。他不能不出來說話了。
「馬六,」村長說,「你把人先放開,有話給我說。」
「你給我保證讓他不勾引我女兒我就放開。」馬六說。
「我保證不了。」村長說,「社會主義興結婚自由,娘老子也不能強扭,國家
有法哩。」
人們哄笑了。燕麥她爸撲閃著眼睛。
「我給他甩人命!」他跳著叫了一聲。
村長走過去,摘著馬六的手指頭:「為這事你就是上吊也沒人管你,你快鬆開。」
馬六一步就跳到了上堆上。
「我要在他家門口碰死!」他喊著。
「群生,把你丈人叫到屋裡去喝碗水消消氣。」村長說。他給群生擠著眼。
群生拍打著頭髮,看了馬六一眼。
王老師走上土堆,拉住馬六的胳膊說:「走,到我那裡去,我給你熬茶。」
王老師拉著燕麥她爸走了。
二十—
燕麥她爸一鬧,倒把群生和燕麥的事鬧成了。
主意是王老師出的。他說:「群生,你跟燕麥結婚算毬了。」群生和燕麥都吃
了一驚。王老師說:「把生米做成熟飯,燕麥她爸就沒轍了。」
事情就這麼定了。群生和燕麥領了一張結婚證,一人買了一身新衣服。我媽縫
了一床新棉被,給群生屋的窗子上糊了一層紙,貼了一個紅喜字。結婚那天,群生
請王老師給他們舉行了一個儀式。我媽炒了幾碟菜,一家人圍著小桌吃了一頓。吃
著吃著,我媽流了淚。
「這麼大的事,也沒給他爸說一聲。」我媽說。
王老師往喉嚨裡灌了一盅,看了我媽一眼。
「六二年把人餓糊塗了。」王老師說。他給我們講他去北山換糧的事。
「我推著車去北山換糧,」他說,「端端地就碰上了一隻狼。那時候到處都有
餓死的人。狼也餓,它跟上我了。我走它也走,我停它也停。走著走著,我燥氣了。
我說狼你吃我沒意思,我身上沒幾兩肉。我說話的時候,它蹲下了。它給我叫喚了
兩聲。我心想這驢日的狼還通人性哩。我這麼一想不生氣了。我給狼說,咱都是可
憐人,一路走就一路走,做個伴兒。我這麼一說。它站起來,給我搖搖尾巴,走了。
你說怪不怪。它一走,我推著車撒腿就往山外跑,險些跑斷了腸子。那次狼要吃了
我,今天這酒就喝不成了。」
王老師張開嘴,又灌了一盅,咯一聲,從喉嚨裡滾了下去。
「我就是那年娶的媳婦。」王老師說。「我媳婦一進門就倒了。我以為她太激
動。我想我也得有個表示,就趕緊抱住她。後來才知道她不是激動,是餓昏了。」
「格格!」我笑了,笑得很響。
「現在你們看去,我媳婦身上的肉足有二寸厚。」
「格格格格。」我笑得肚皮疼。
「看這娃,笑傻了。」我媽說。她也笑。
我很長時間沒這麼開心地笑過了。
第二天,群生和燕麥硬著頭皮去南仁村回門。燕麥她爸把他們推到門外,關住
門不讓進去。他們在門外站了很長時間。他們聽見燕麥她爸在犀裡哭。
「哎嗨呀嗨,我馬六上輩子虧了人哎嗨。」他這麼哭著,很傷心。燕麥她媽把
門開了一道縫,說:「你們快走、你爸哭哩,我不敢讓你們進屋。你爸就是這號人,
過一陣子就好了。抱個外孫回來,看他認不認。」燕麥臉紅了,說:「媽,那我走
了。」燕麥她媽說:「好好過日子。」
群生沒去水泥廠。他決計要卷花炮掙錢。王老師給他寫了張條兒,讓他去信用
社找人貸款。他選中了那個磚瓦窯。他找村長,村長說你弄去,磚瓦窯廢了村上要
它沒用。群生和燕麥把窯裡的爛磚頭搬出來,把它收拾成了一個卷花炮的作坊,然
後,他就聯繫著買火藥,騎著自行車轉村子收購廢書廢報紙。
那年秋天,我上了四年級。他們好像不怎麼管我的嘴了。我說話漸漸多起來。
不知為什麼,我總愛和燕麥說話。我叫她燕麥姐。我媽說叫嫂子。燕麥說就叫姐,
叫姐聽著親。
二十二
我媽王玉梅到馬欄農場看過我爸一次。我媽說:「我想去馬欄看看你爸。」我
說:「我也去。」我媽說:「念你的書。」燕麥說:「家裡有我哩,你放心去。」
群生說:「要不我去。」我媽說:「你忙你的。我去。」燕麥給我爸炒了一袋面餅
豆豆。
那天下完課,王老師問我卷花炮的事。我說:「我哥收廢紙哩。」王老師噢噢
點著頭。我說:「我媽要去看我爸。」噢噢,王老師又點點頭。晚上,他拿來兩盒
金絲猴煙,讓我媽給我爸帶去。「清林愛抽這煙。」王老師這麼說。
我媽走了七天。回來的那天晚上,我們全家坐在炕上,聽她講馬欄農場的事。
我媽的氣色很好,我媽說:「你爸在農場受了優待,不幹重活,一個人在一個地方
看場子,沒人管制他。」我不知道什麼是場於。我媽想了一會,說:「我也不知道。
一間大本房裡堆著許多大木頭。大木房隔了一間小屋,是你爸睡覺的地方。你爸自
己做飯吃。」
「遠麼?」
「遠死了,坐兩天汽車哩,還要倒車。」我媽說。
「他們不打人?」
「你爸說只要不逃跑不胡生事就不打。」我媽說,「有個犯人想逃出去,腿上
挨了槍子,又給拖回去了。我給你爸說,你可甭弄傻事情,家裡好好的,你安心地
改造。他們那裡把勞動叫改造。改造就改造,不給人家改造咋辦?」
「我爸見你高興死了,得是?」我說。
「你爸一晚上就抽了兩盒煙。你爸聽了群生和燕麥的事,高興得直抽煙,一邊
抽一邊咳嗽。我說你少抽些行不。你爸說我一高興就想抽煙。他把王老師給的兩盒
煙抽完了。」我媽說,「你爸讓我悄話給你們,卷花炮要小心。你爸看的那個場子
在大溝裡,一到晚上很安靜。白天也安靜,看不見狗大個人影。」
馬欄,馬欄。我感到馬欄的名字很好聽。我想像著那條大溝。我感到那地方很
神秘,也很嚇人。
在冬天的頭場雪到來之前,我用竹竿挑著一長串鞭炮走上磚瓦窯頂。那是我哥
群生卷出來的第一串鞭炮。鞭炮聲響亮乾脆,開的紙花像五顏六色的羽毛紛紛飄落。
我挑著爆響的鞭炮在窯頂上轉著圈子。我感到我不是在窯頂上,而是在雲上邊。我
感到鞭炮的響聲像歡樂的鳥叫,離我很近,又很遙遠。
吉祥村的人都聽見了那一串響亮的鞭炮聲,看見了紛紛揚揚的紙花。他們感歎
著我們一家人過日子的心勁。
典典和根舍跟我套近乎。典典說:「雜嘴子,咱和好。」我不信任他們。我想
起他們給我嘴上貼膠布的情景。典典說:「真的,我和你拉勾。」他不管我願意不
願意,就把指頭勾在我的指頭上搖了幾下,然後給我嘿嘿笑。根會說:「我也和你
拉勾。」他學著典典的樣,和我拉了勾。他們都很真誠。典典說過年的時候你把你
哥的花炮偷些來,咱到城外放。我說行。我一直以為我一輩子也不會理他們。我恨
他們,現在我才知道,我需要他們的友情。
然後,就是那場大雪。
二十三
雪下了幾天幾夜,等太陽從雲裡掙扎出來的時候,地上的一切都變得臃腫了。
田野啦,房屋啦,水渠岸上的樹啦,都裹著一層綿乎乎的白雪。遠處的北山好像遠
了,在柔和的太陽光裡蹲著,像一群穿著翻羊皮襖的老頭。
上課的時候,我就感到肚子餓。王老師一說放學,我就第一個跳出教室,踩著
厚厚的積雪朝家裡跑。我想我媽要是蒸饃饃就好了,我一進門就抓兩個熱乎乎的軟
蒸饃吃,如果噎住,我就喝開水。
我家的門上掛著一把鎖。
那些天,群生和燕麥沒日沒夜在磚瓦窯裡卷花炮,一進臘月就能賣了。我媽有
時候也去磚瓦窯給他們幫幫手。
「騰騰騰。」典典媽端著一盆髒水人她家門裡出來,朝街道上潑去。
「你媽在桂蓮家裡。」她朝我喊著,「桂蓮兄弟娶媳婦,請你媽幫忙去了。」
村上又有人請我媽王玉梅過事情了。
桂蓮家的院子裡又熱鬧又忙亂。竹笛子搭成的棚下擺著幾個大方桌,娘家客正
在吃喝。廚房門口盤著土爐子,兩口大鍋裡燴著肉菜。鼓風機嗚嗚叫喚著。
「來了!油!」有人端著盤子朝棚裡去了。
新房門口圍著一堆人,吵嚷著要耍新媳婦。
我媽和幾個婦女在廚房裡蒸饃饃。蒸好的饃饃又白又軟,在蒲籃裡冒著熱氣。
一籠蒸好了,她們抬著倒進蒲籃,再搭一籠。桂蓮遞給我媽一茶缸紅糖水,我媽喝
水的時候看見了我。「出去,快出去,這裡忙,」她說。桂蓮一把拉住我,在蒲籃
裡抓了兩個熱饃饃,說:「甭走,給你夾個肉夾饃。」我媽說:「甭夾,娃們家不
能慣毛病。」
我想吃,又不敢要。
「我哥呢?」我說。
「在窯上哩,要去你就去。」我媽說。
桂蓮夾好了肉讓我吃。我媽說你先給你哥送去回來再吃。桂蓮說也成。桂蓮把
夾肉饃饃放在一個細瓷碗裡,說:「叫你嫂子甭做飯了,來這兒吃。」
夾肉饃饃本來是我的,轉眼又成了群生的。
我端著兩個夾肉饃饃朝磚瓦窯走著。我太想吃它們了。我的舌頭底下直往上泛
酸水。我聽見我的肚子裡有什麼東西往下滾著。咕,咕,滾一截就這麼叫喚一聲。
我揭開一頁饃饃,我看見那幾塊肉片很大,肉香味直往我的鼻眼裡鑽。只要我一伸
嘴,它們就會鑽進我的嘴裡,再從喉嚨鑽進我的肚子。
吃一個吧。我想。
我抬頭看看磚瓦窯,不遠了。
走五十步我再吃。我想。
我一步一步數著,數到五十了,離磚瓦窯還有一大截。
吃吧。我想。
我想走十步咬一小口,到磚瓦窯一定能給群生剩一個。我只吃一個。
我拿起一個夾肉饃饃。我朝磚瓦窯看了一眼。然後,我在夾肉饃饃上咬了一口。
我沒想到一咬就收不住了。我幾口就吃掉了它。
我接著吃掉了另一個。我神長袖子擦擦嘴,大步朝磚瓦窯走去。我端著空碗。
「哥!」一進窯門我就喊了一聲,「媽叫你和燕麥姐去桂蓮家吃飯哩。」
燕麥看看我手裡的空碗,又看看我的嘴說:
「怕是讓你送飯吧?看你嘴上的油。」
「我吃了兩個肉夾饃。我餓了。」我說。我沒說那兩個肉夾饃是給群生的。
群生正在卷炮。群生給燕麥說:「你去吃,我不餓。」燕麥說:「一塊去,吃
了再來。」群生說。「不去。」燕麥說:「你不去,我也不去。」
我吃了兩個夾肉饃饃,肚子裡滋潤了許多、我說:「不去,不去我也卷」
「別動!」群生說,「小心炸了你。」
「走不走走不走?」我燥氣了。
燕麥說:「兄弟,你別惹他,他和我剛吵了幾句嘴。」燕麥伸伸懶腰,看著群
生。
「我心裡咋瞀亂得很,一塊走吧。」燕麥說。
「你這人咋啦羅囉嗦嗦真是個婆娘!」群生瞪眼了。燕麥並不生氣。她沖我擠
擠眼,說:「好,好,我是婆娘,我是婆娘,兄弟咱走,讓他一個人呆著,狼吃了
他。」
出窯門的時候,燕麥又看了群生一眼,張張口,想說什麼,又怕群生嫌她囉嗦,
把要說的話咽了回去。
群生跟我們一塊走就好了。他沒有。
二十四
我和燕麥在雪地上走著。我挨她很近。我喜歡跟燕麥在一起。我喜歡看她,喜
歡和她說話。喜歡聽她格兒格兒的笑聲。燕麥的身上有一股香味,我以為是雪花育。
後來我才知道不是。她從不抹東西。我不知道那股香味是從哪兒來的。
「燕麥姐,我就愛和你一起。」我說。
「格兒,格兒。」燕麥笑了,「為啥?」
「你好。」我說。
「格兒,格幾。哪兒好?」
「不知道。」我說。我確實說不出哪兒好。
「你比我哥好。」我說。
「格兒格兒。」燕麥笑得更響了。「你哥看著凶,其實心眼不壞。」她說。
「我看你比他好。」我說。
燕麥又笑了。她摟住我的脖子,看著遠處。
「明天早上姐帶你去落雁灘打雁去。」她說。
「打雁?」我不信,「我又沒土槍。」我說。
「不要槍。」她說,「把地上的雪掃開,潑上水,雁落下來,到第二天早上,
雁毛就凍在地上,咱拿木棒去,悄悄溜過去,總能打住幾個,打回來燉雁肉,喝雁
湯。」
我看著遠處的落雁灘。那裡鋪著厚厚的白雪。我想著打雁的情景。雁撲閃著翅
膀,很好看。
「哥去麼?」我說。
「不要他。」燕麥說。
「我也不想要他。」我說。
「格兒格兒。」燕麥又笑了。
就是這時侯,我們聽到了那聲巨響。
「轟!」一聲。緊接著是一陣歡快激烈的鞭炮聲。不是一串是許多串。劈劈啪
啪。劈劈啪啪。
「轟!」又一聲。
我看見燕麥的身子猛烈地抖了一下,突然定住了。
一股濃煙夾雜著磚頭的碎片從磚瓦窯那裡面空而起。僅僅是一眨眼的功夫。磚
瓦窯不見了,沒有了。
我懵了。我瞪大眼珠子朝磚瓦窯那裡看著。我感到我的手被燕麥甩開了。我看
見她像瘋了一樣朝磚瓦窯跑去。
我沒有跑。我還沒想清楚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我好像在夢裡一樣。我茫然四
顧。我看見田野啦,村莊的房屋啦,水渠岸上的樹啦,仍舊裹著一層綿乎乎的白雪。
世界很大很大。北山是一群穿著翻羊皮祆的老頭。它們一聲不響。照在雪地上的陽
光很安靜,也沒有聲響。
可是磚瓦窯沒有了。
一群人叫喊著從村口奔跑出來。我看見跑在最前邊的是我媽王玉梅。她挽著袖
子,胳膊上沾滿了面這。
全村的人都湧到了磚瓦窯。那裡已成了一片廢墟。我媽王玉梅和燕麥趴在廢墟
堆裡,一塊一塊刨著磚頭。那時候,硝煙還沒有散盡。偶爾有一聲鞭炮從磚頭縫裡
蹦出來,啪,一聲,啪,又一聲。
傍晚的時候,他們刨出了我哥群生的屍體。
他們都走了。我一個人在那堆廢墟跟前站著。這時候,我才發現我一直拿著那
只空碗。那是一隻白色的細瓷碗,碗邊上有幾朵精巧的花。
我想起了那兩個肉夾饃。我看著那只細瓷碗。兩行眼淚水從我的眼眶裡流出來。
「哥,我把你的肉夾饃吃了。」
我給那堆磚頭說。
二十五
我媽和燕麥給群生糊了許多紙衣服,還有紙鞋和紙帽。她們糊得很仔細。
「吱扭」一聲,門開了。是典典媽。她悄兒沒聲地坐在我媽跟前,和我媽一起
糊。
桂蓮來了。根舍媽來了。許多女人都來到我家。她們都不說話。她們和我媽和
燕麥一起糊紙衣。
王老師也來了。他在院裡站了一會兒,又走了。
只有村長一個人說了一句話。他坐在門坎上抽了一鍋旱煙。他歎了一口氣,站
起來,在鞋底上蹭掉煙灰,說:「可惜娃了。」
燒紙衣的那天,我媽王玉梅在我哥群生的墳頭放聲大哭了一場。
燕麥沒哭。她就那樣坐著,像凍僵了一樣。
我跪在那堆紙衣跟前,看著燃燒的紙火。我又想起了那兩個夾肉饃饃。
王老師用鐵鍁把墳堆拍了一圈。他用手托著腮幫,像害牙疼一樣。
「哎嗨嗨嗨……」我媽的哭聲傳得很遠。
典典媽搖著我媽的肩膀說:「二嬸,你甭哭了。他能狠心合下你,你還哭他做
啥……」
典典媽捂著嘴,到底沒忍住,吼著吼著哭起來,眼淚水一溜兩行。
從此以後,我很少說話。不是他們不讓我說。我沒話說。我總會想起炸藥和火
藥把磚瓦窯掀上空中的那副情景。鞭炮劈劈啪啪地響著,磚頭和瓦礫紛紛跌落,埋
沒了我哥群生。那時候,太陽正照射著白雪,沒有一點聲息。
我覺得那一切好像一個虛幻的故事。
但群生真真的沒有了。
燕麥的臉上像抹了亮油,閃著淒慘的淚光。她不再格兒格兒的笑了。她說話的
聲音很弱。我老偷偷地看她。我很想給她說點什麼。我沒說。
群生過二七那天,我們從墳地燒紙回來,燕麥和我媽走進廚房做飯。
「你歇去,我做。」我媽說。
燕麥沒說話,提著水桶出去了。
「民生,拿棍跟你姐抬水去。」我媽給我說。
我拿著抬水棍走進後院,看見燕麥扶著轤轆把兒,要吐的樣子。
「媽,我姐吐哩!」我喊了一聲。
我媽跑過來,扶過轤轆把兒,看著燕麥的臉色。
「找殷涼亭看看去,甭耽擱出大病。」我媽說。
燕麥看了我媽一眼,想說什麼,又沒說。
我媽的眼睛突然放光了。
「燕麥,你有身子了?」
我媽好像很激動,忘記了吊在半井裡的水桶。她撒開手,抱住燕麥的肩膀搖著。
「你有身子了,燕麥!」
噠噠噠噠,轤轆飛快地轉著。「通」一聲,水桶落在井底了。
我看著我媽和燕麥,愣了一會兒。一股熱乎乎的東西在我的身子裡猛地衝撞起
來。我想哭。我想放聲哭一次。
我跑到前院的牆拐角。我往牆拐角跑的時候就抽噎了。我對著牆,肩膀抽動著。
「嗚!嗚!」我仰著脖子。我感到喉嚨裡很堵。
我抹了一把淚水。我感到我的眼淚是熱的。
我媽聽見我哭,在二門口看了一會兒。
「好好的哭啥?」她說。她不知道我的心思。
「嗚!嗚!」我哭著。
我媽沒有再問。那些天,一家人的心都像燒化的蠟燭一樣,說不定誰突然就想
哭。想哭就哭了。
晚上,我媽王玉梅翻來覆去睡不著。她坐起來,披上布衫,兩隻手托著臉想著
什麼,想一會兒又躺下,躺下又坐起來,一直折騰到後半夜。
她終於受不住那種熬煎了。她拍我,輕聲喚著:
「民生,你睡了沒?」
我一骨碌從被窩裡坐起來。我沒睡著。我一直聽著她翻騰的聲音。
「你輕點聲,媽想和你說說話。」她說,「披上布衫,甭著涼了。」
我披上布衫,等著她說。她沒點燈。我和我媽王玉梅坐在黑暗裡。
「你燕麥姐懷孩子了。」我媽說。
我點點頭。我以為她還要說什麼。她歎了一口氣,歪低著頭,不說了。我們坐
了好長時候,她把布衫取下來,放在炕頭,說:「睡吧。」
她抻抻被子,躺下了。
我猜不透她的心思。後來,我發現她老打量燕麥姐,好像要從燕麥的臉上看出
什麼異樣來。
二十六
幾天後,我媽王玉梅和我哥的媳婦燕麥談了一次話。
我媽站在燕麥的屋門口猶豫了一會兒,終於鼓起勁,挑開了門簾。
「媽,你坐。」我聽見燕麥說。
「嗯,坐,我坐。」我媽說。
我媽的口開得很艱難。
「燕麥,媽想和你說件事。」我媽說。
「媽你說,我聽著哩。」燕麥的聲音弱弱的。
「群生,群生去了,」我媽說,「這家裡留不住你,你遲早也得找人……媽不
是不明事理的人。你要走,我不攔擋你……」我媽又頓住了。突然,提高了聲音:
「你看在媽的老臉上,把肚子裡的娃給我生下來。我要這個娃。我一定得要這個娃
呀,燕麥!」
我媽哭了。我媽和燕麥哭成了一團。
又過了幾天,燕麥突然說她想回娘家看看。我媽愣了一下,說:「看看你爸你
媽,散散心。去,你去,媽的心大著哩。!,又說:「讓民生送送你。」
「不,不用。」燕麥說。她好像有些慌張。
我媽一直把燕麥送出大門。
我脫下一隻鞋,朝天上拋。鞋像鳥一樣,在空中劃出一道弧線。「上是男,下
是女。」我說。
「啪噠。」鞋落下來,鞋口朝上。
「男娃!」我叫了一聲,「媽你看,鞋口朝上,我燕麥姐一定生男娃。」
我媽沒看鞋。她皺著眉頭。
「民生,快穿上鞋,跟你燕麥姐去。」
我不明白我媽為什麼要這樣。
「去,甭讓她看見你。她進了南仁村,你再回來,知道不?」我媽說。
燕麥沒去南仁村。她拐上了另一條路。她匆匆走著。
她在鄉衛生院門口站住了。她猶豫著,一臉痛苦。
「燕麥姐!」我喊了一聲,從牆拐角背後朝她跑過去。
燕麥吃了一驚。她沒想到我會跟著她。
「你?……」我看著她的臉。
燕麥蹲下來。她拉住我的手,可憐巴巴地看著我。
「兄弟,」她說,「姐也不願走這步路……」
「我,我恨你!」我想甩開她的手。她死抓著不放。
「姐沒辦法啊,」她說,「姐不能要這個娃,生一個沒爸的娃,太可憐了。姐
還要活人。娃要受人的白眼……」她流淚了。「甭給媽說,她知道會受不了。」她
說。
她站起身,朝衛生院的大門走進去。
我沒動。不知為什麼,我沒動。我看著她往裡走。
我一口氣跑回家。我媽問我:「去南仁村了?」
「嗯。」我說。
「你看著進了南仁村?」
「嗯。」我說。
「咋去這麼長時間?」
「嗯。」我說。
天快黑的時候,燕麥回來了。我媽有些詫異。
「我呆不住……」燕麥說。
我緊張地看著,心裡咚咚跳。
「回屋快回屋甭累著了。」我媽給燕麥說。
我松了一口氣。燕麥感激地看了我一眼,進屋。
「啊噢!」我叫了一聲,把一隻鞋朝天上拋去。
第二天,我媽就知道了燕麥墮胎的事。
我媽做了兩個荷包雞蛋讓燕麥吃。燕麥不敢看我媽的臉。她說她不想吃。
「掙著也要吃。不為你,也得為肚子裡的娃。」我媽說,「吃,趁熱吃。」
燕麥吃得很痛苦,像吃藥一樣。
我媽拿著一件衣服,坐在炕沿上。她要把它改成小孩的衣服。她一邊做,一邊
給燕麥講她的經驗。
「女人生頭一個都害怕,」她說,「其實沒啥怕的。我生群生的時候和你這會
兒一樣,害怕得吃不下飯,睡不好覺。我生了五個,傷了三個,是過來人。有我在,
不會讓你吃虧。」她說,「老天爺造女人,就是讓她生兒育女。」她說,「懷著娃,
不能氣著,累著,也不能餓著。要多吃。娃的衣服褲子我給你弄,你甭操心。」
燕麥一口也咽不下去了。
門簾嘩啦一聲被挑開了。典典媽像一隻紅臉雞,憤怒地盯著燕麥。她來得很突
然。
「二嬸,你還給做好吃的?你該給她吃老鼠藥!」
我媽王玉梅茫然地看著燕麥。燕麥低頭一聲不響。
「二嬸你咋這麼糊塗,她把肚子裡的娃刮了!」典典媽說。
我看見我媽的身子搖晃了一下。
燕麥撲通一聲跪在地上,抱住我媽的腿。
「媽呀!」她哭叫著,「我對不住你啊,啊啊……」
我媽閉上了眼睛。
「我傷了兒子,又傷了我的孫子,孫子……」我媽王玉梅像說夢話一樣。
「啊,啊,啊……」我媽的喉嚨像卡進了什麼東西。她抽搐著身子,朝後倒下
去。我媽的手碰倒了櫃蓋上的雞蛋碗。碗跌在我媽彎曲的膝蓋上,翻下去。那兩個
荷包蛋在地上蹦跳著,像兩個活物。
二十七
一個月以後,燕麥去了南仁村。我看見她在群生的墳跟前站了好長時間。她彎
下腰,朝墳堆磕了一個頭,走了。她什麼東西也沒拿。那時候是清晨,風吹得墳地
裡的樹枝吱吱響。
她再也沒有回來。從來到走,只有多半年的時間。
兩年以後,我考上了縣城的一所重點中學。
我爸刑滿釋放後,在家呆了三個月,便患肝癌去世。我從學校趕回來,他已躺
在了棺材裡。我看了他一眼。他穿著一身整齊的衣服,戴著一頂帽子,很安詳。
借我爸錢的王三看過我媽一次。他發了財。我媽給他的臉上吐了一口。王三說:
「嫂子你吐,我害了你們一家,你就是用刀砍,我也不躲。」王三給我媽掏出一疊
錢。我媽把錢塞進王三懷裡,說:「你走吧。」我媽的臉上佈滿皺紋。她老了。
就在那一年,我考上了外省的一所大學。臨走前,我突然想看看燕麥。我看見
她的時候,她拉著一輛架子車,車上裝著許多南瓜,還坐著一個三四歲的男孩。燕
麥眨了好大一會兒眼,才認出是我。「這不是民生兄弟麼,你看我個笨眼,聽說你
考上了大學?」她說。我點點頭。車上的男孩喊著鼻,鼻。燕麥在他的鼻子上捏了
一把,把鼻甩出去,在衣襟上擦擦手指頭,說:「媽好麼?」我說:「好,好著哩。」
燕麥說:「拿幾個南瓜給媽吃,自家種的,成實了。」我沒拿。她拉著架子車走了。
我看著她的背影。我感到她說領我去落雁灘的話好像是上一輩子的事。
我媽堅持要把我送到北坡,還要送。我攔住了。我媽用渾濁的目光看著我。
「民生,你爸的事不是你給人說出去的?」她突然說了這麼一句。
我不知道怎麼回答她。
「管住你的嘴。」她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