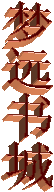
楊爭光 扭
——快樂家園第二
婆子媽又回來了。她在前房裡,坐在炕上。她不停地扭胳膊扭腳,蹾屁股。徐
培蘭能聽見她蹾屁股的聲音,就那種「騰、騰」的聲音。她也能聽見她在地上尿尿
的聲音,塌啦啦啦。婆子媽老撅著屁股尿。婆子媽在炕上屙,她把屎蛋蛋包在手巾
裡,放在炕頭上。太陽光一旺,她就靠在門框那裡,給徐培蘭笑。徐培蘭看得清清
楚楚,就是十年前那麼一種樣子。
「你……回來了。」徐培蘭說。
婆子媽不說話。她給徐培蘭笑。屋裡一滿是爛紅薯的氣味。徐培蘭聞見屋裡滿
是爛紅薯的氣味。她知道是怎麼回事。可那時候她不知道。那時候也這樣。爛紅薯
的氣味讓她翻腸倒肚。她想吐。她吐不出來。
那天傍晚,她站在前門口避煙。前門口有幾棵桐樹,她就站在桐樹底下。她把
兩個炕洞裡的柴禾一起點著了。往常她只燒一個炕,婆子媽的炕羊村姐燒,羊村姐
沒來,所以徐培蘭就把兩個炕洞裡的柴禾一起點著了。她擰過脖子猛搧了一陣。她
看見煙從煙囪裡卷出來,往地上撲。煙囪在半牆上。煙不往高處走,往地上撲,撲
了一層,軟軟的白。一會兒,徐培蘭受不住了,她把扇子一扔,往門外跑。她憋住
氣不咳嗽。她知道一咳嗽就會吸氣,就會把煙吸到肚子裡。
她聽見婆子媽在前房裡摳炕席。那些天,婆子媽總摳炕席。燒炕的時候,她不
出房子,她坐在白煙裡。她不煙。誰知道她怎麼的不怕煙,她坐在炕上摳炕席。席
蔑斷裂時,就發出嘭啪嘭啪的聲響。徐培蘭能聽見。徐培蘭知道婆子媽已經把炕席
摳爛了一大片。
「做什麼你摳炕席?」徐培蘭朝屋裡吼。
屋裡全是白煙,有一些正往半空裡飄。婆子媽不說話。她想不出婆子媽坐在白
煙裡是個什麼模樣。
炕席不響了。
「你摳炕席?」徐培蘭說。
「煙嗆我。」婆子媽說。
婆子媽的吼聲從白煙裡鑽出來。婆子媽好像有些氣憤。婆子媽一氣憤,徐培蘭
心就有些舒坦。有時候,她就想讓婆子媽氣憤。
「嗆你就摳炕席?」徐培蘭說。
「就摳。」婆子媽說。
「嗆你就摳?」徐培蘭說。
「我愛摳。我媽生我愛摳。」婆子媽說。
「你是老鼠。」徐培蘭說。
「日你媽,你媽是老鼠。」婆子媽說。
徐培蘭閉了閉嘴。煙散了許多。她聽見婆子媽的手指頭不太用勁了。
「嫖客日的。」徐培蘭說。
「你媽遭了罪,讓我服侍。」她說。
她朝著羊村的方向。她想起了羊村姐,所以她朝著羊村的方向。
桐樹上吊著幾片葉子,就吊著那麼幾片。冬天快過去了,可它們還吊在樹上。
她瞅了整整一個冬天,它們沒落。它們卷著,風一吹幹響。
「還落過雪呢。」徐培蘭想。
它們就是不落。她瞅著它們想了一陣。後來,她抽了抽鼻子。沒煙了。再後來,
她又抽了抽鼻子,她就聞見了爛紅薯的味道。她看見照順往她跟前走。照順背著書
包。
「照順你吃紅薯來?」她說。
照順站在糞堆那裡眨矇眼。那裡有個糞堆,是富士家的。
「吃唻就吃唻。」她說。
「我沒吃。」照順說。
「你眨矇眼。」她說。
「我沒吃。」照順說。
「沒吃哪來的味兒?」她說。
「我沒吃。」照順說。
「日怪了。你沒吃就日怪了。」她說。
「我沒吃做什麼日怪了。」照順說。
「你問。」她說。
照順抽抽鼻子。
「我沒吃。」照順說。
「沒吃算了,你回。」她說。
婆子媽靠在門框那裡。婆子媽不知什麼時候出來了。她趔趔身子,讓徐培蘭進
門。
「你看我!」她朝徐培蘭吼了一聲。
「我沒看你!」徐培蘭說。
「看就看唻。」婆子媽說。
「你香你稀罕看你。」徐培蘭說。
「你眼黑我。」
「我沒眼黑你。」
「我要吃。」婆子媽說。
「我餓了我要吃。」婆子媽說。
夜裡,徐培蘭醒來幾次。她聽見婆子媽又屙了。她睡不著。她感到屋裡的紅薯
味越來越大。早沒紅薯了,可屋裡有紅薯味。她想人總會有些事情。人真日他媽的。
那是一種甜絲絲的氣味。她想是爛紅薯的味,要不氣味就沒這麼大,這麼撓人。
那天,羊村姐來了。她看見徐培蘭剛從井裡鑽出來。徐培蘭鼻子上沾著濕泥,
手上也有,膝蓋上也有。
「嘎。嘎。」羊村姐趔著肚子。
「我下紅薯窖裡唻。」徐培蘭說。
「屋裡有一股紅薯味。」她說。
「窖裡沒紅薯。我知道沒有。我看過幾次了。屋裡有一股紅薯味。」她說。
羊村姐抽了幾下鼻子。
「你聞。」徐培蘭說。
「怪怪的。」羊村姐說。
「是爛紅薯。」徐培蘭說。
「沒紅薯麼,這會兒沒紅薯麼。這會兒誰還會有那東西。」羊村姐說。
「噢麼。」徐培蘭說。
「你說是紅薯?」羊村姐說。
「怪怪的。你也說怪怪的。」徐培蘭說。
「這可不好。屋裡有味可不好。」
「噢麼。」
「讓人知道了可不好。」
「人都知道了。」徐培蘭說。
「花香知道了。」她說。
徐培蘭有些想哭。吃早飯的時候,她端著碗去前門口曬太陽。前門口太陽旺,
暖和。她看見花香也端著碗。花香在糞堆裡。花香使勁往她碗裡看。花香拐彎抹角
和她說話。
「雁過留聲。」花香說。
「不一定。我說不一定。」她說。
「一定。」花香說。
「人死留名。」花香說。
「誰知道他八輩子爺叫什麼名?」
「甭想糊弄人。」花香說。
「說話要說清。」
「紙裡包不住火。」花香說。
「說話要說清,我說。」
「你們家有紅薯。」花香說。
徐培蘭正往下嚥一口飯。她沒咽下去。她感到它們硬硬地堵在她喉嚨眼那裡了。
「我都聞見了,富士也聞見了。」花香說。
「日他媽的有紅薯。」徐培蘭說。
「有就有。」花香說。
「甭讓你家的氣味撓人。」花香說。
「我說誰家有紅薯誰日他媽。」
紅薯窖打在井筒上。她怕她沒看好。她又下了一回井。她知道她有眼病,她用
手摸。她咬著牙。一咬牙,她就感到肚子裡有些憋。她想她遲早要和婆子媽吵一架。
她突然這麼想。
那是一種甜絲絲的味道。
二
婆子媽總斜著眼看她。婆子媽不知道怎麼的老斜著眼看她。
「你偷吃紅薯!」她說。
那天,她跳了一下,她跳進婆子媽的屋裡。她把頭一直伸到婆子媽的鼻子底下。
她感到脖子上的筋繃得很硬。
「我說你偷吃紅薯。」她說。
「騰。」婆子媽蹾了一下屁股。
婆子媽不穿褲子。婆子媽穿一件又寬又大的夾襖。她看見婆子媽兩條幹腿從夾
襖底下伸出來,腿上邊像撒了一層麩子一樣的東西,有一條腿不停地扭著,抖著。
「你把我捏死。」婆子媽說。
婆子媽又蹾了一下屁股。
「你瞞不了我。」徐培蘭說。
「你來把我捏死。」
婆子媽蹾著屁股往前挪。婆子媽把頭埋在胳膊裡,往徐培蘭懷裡鑽。徐培蘭又
跳了一下,從門裡跳出來。她看見婆子媽的腿正從炕沿上往下伸。
「你弄了一屋子怪味。」徐培蘭說。
「日你媽我偷吃紅薯。」婆子媽說。
「你看你弄的怪味。」徐培蘭說。
婆子媽從門裡邊挺出來,靠在門框上。婆子媽斜著眼珠子。那天,太陽有些旺。
桐樹影影打在婆子媽的臉,有些神裡鬼氣。她沒吼,她看著徐培蘭笑。這是徐培蘭
沒想到的。
婆子媽就這麼有些神裡鬼氣。太陽一旺,她就站在前門口。她穿著那件夾襖。
夾襖底下直直地挺出來兩條幹腿,有一條不停地扭著,抖著。有一隻胳膊也不停地
扭,在她的胸脯那裡扭著花子。
「我不知道她身子裡正爛東西。我以為是爛紅薯的氣味。」
那天,徐培蘭給蓋子叔這麼說。她看見幾星唾沫濺到蓋子叔的臉上了。
「你看我唾沫濺你臉上了。」她說。
「她好好的。太陽一旺,她就在門口曬暖暖。她不穿褲子。我看她好好的。我
不知道人快死了就有味道。」她說。
「人死了都有味道。」蓋子叔說。
「快死了也有?」她說。
「人不是說死就死。人一點一點死。」蓋子叔說。蓋子叔不抬頭。蓋子叔坐在
柴禾窩裡捉蝨子吃。
「看著好好的,能吃能睡。」徐培蘭說。
「人和紅薯一樣,爛一點就有味道。」蓋子叔說。
「你看這。」徐培蘭說。
「她年輕時可動人哩。」蓋子叔說。
徐培蘭眨矇著紅眼皮,往蓋子叔臉上看。她看見蓋子叔的臉皮緊了一下,又松
了。
「她的腳好看。」蓋子叔說。
「村上的女人就她腳小。」蓋子叔說。
「我不信。我不信你這話。」
「她讓一村的女人沒了光彩。女人們不和她來往。她借不到鹽醋。後來,她就
沉著臉,像鬼一樣。誰知道她心裡想什麼。沒人見她笑過。」蓋子叔說。
「給我阿公爸也不笑?」徐培蘭說。
「這可沒人知道。你阿公爸沒給人說這事。」蓋子叔說。
「噢麼。」徐培蘭說。
「早了。這事早了。」蓋子叔說。
「我不信她沒給人笑過。」徐培蘭說。
「她不和人說笑。」蓋子叔說。
「她給我笑。怪怪的。」徐培蘭說。
「誰知道她做什麼給你笑。」
那天沒風,太陽也很旺。他們說得很融洽。儘管他們一個不太看一個,可他們
很融洽。
「穿壽衣那時辰,你記得不?我給她褲襠裡塞布。」蓋子叔說。
「記得,記得麼,是舊褲子。我心裡慌失了,找了個舊褲子。」徐培蘭說。
「我手挨著她的大腿。一層皮,就一層皮,裹著幾根幹骨頭。這我可忘不了。」
蓋子叔說。
「我婆子媽死得貧氣,像個死貓。我看著像個死貓。」徐培蘭說。
「有人死得貧氣,有人福泰。」蓋子叔說。
「我聽見騰一聲。我想不到。」
「人死如燈滅。」
「就是的。我看就是的。」徐培蘭說。
她聽見前房裡響了一聲。那時候,院子裡黑糊糊的,她聽見響了一聲。照順睡
著了。她搖照順。她讓照順喊,照順不喊。她說照順你不喊我心裡慌,照順就喊了。
婆子媽不應聲。她說照順快穿衣服。照順害怕。照順說媽我怕。她說照順你驢日的
我也怕。後來,他們推開婆子媽的房門,他們看見婆子媽睡在地上。她說做什麼你
睡在地上?她看見婆子媽好像給她笑了一下。她說你看你還笑,婆子媽就不笑了,
婆子媽的眼珠子往上翻。她說你甭翻眼珠子,你這麼翻我害怕,我沒主意了。她說
照順你快去叫人,快去。
第二天,羊村姐來了,草谷村的姑也來了,還有蓋子叔。他們把婆子媽抬在一
張木板床上,給她換壽衣,因為她只剩一口氣了。
「我想不出。我以為是爛紅薯。」徐培蘭這麼給人說。
三
「我不想死。」婆子媽說。
這會兒,她靠在門框那裡。她往徐培蘭臉上看。
「我不知道我會摔下來。」她說。
那天,她肚子有些脹。她動不動肚子就有些脹。她想尿一泡。她這麼一想,就
有什麼東西順著大腿往下流。她想站到地上。她一挺身子,就從炕上摔下來。她聽
見徐培蘭讓照順喊她。她聽見徐培蘭朝前房這裡跑。她看見徐培蘭像黑影一樣立在
她腳跟前。
「做什麼你睡在地上?」徐培蘭說。
她給徐培蘭笑了一下。
「看你還笑。」徐培蘭說。
「我要死了。你看我要死了。」
她想這麼說。她沒說出來。她感到她的眼珠子往額顱裡邊擠。她鼓鼓勁,她不
想讓它們擠到那裡邊去。她想它們真擠進去就不好了。她想它們遲早會擠進額顱裡,
再也不出來,可現在她不願意。她想看看她的胳膊和腳。她想看看它們這會兒還扭
不扭。她就這麼想著,往眼珠子上鼓勁。
「死了我就和你較不上勁了。我不想死。」婆子媽說。
「我知道你和我較勁。」徐培蘭說。
「我看出來了。」徐培蘭說。
徐培蘭記得,那些天,她像母狗一樣,出來進去抽鼻子。
「你母狗樣。我就愛看你母狗樣。」婆子媽說。
「嗚。嗚」
徐培蘭一抽鼻子,喉嚨裡就發出一種粘粘糊糊的聲音。婆子媽靠在門框上,看
徐培蘭在牆角那裡搗騰。那裡放了一堆臭鞋底鞋幫爛襪子。徐培蘭鼻子眼裡噴著粗
氣。
「難聞死了。日他媽難聞死了。」徐培蘭說。徐培蘭看了一眼婆子媽。
婆子媽不出聲,就那麼給徐培蘭笑。太陽光照著她的兩條腿,照在她的頭頂上。
她沒幾根頭髮,就那麼幾根白絲絲,像搭了幾條白線,順著腦頂搭過去,在腦勺那
裡挽了一個紐扣那麼大小的疙瘩。
「做什麼你笑,做什麼你老笑?」
她笑。她笑的時候,眼睛就凹進去,胭脂骨就突出來。
「貓。」徐培蘭說。
「我說你是貓。」徐培蘭說。
「看你腳像個搗蒜錘。看不扭死你。」徐培蘭說。
「難受死我了。你這麼笑難受死我了。」徐培蘭說。
「你不說話你光笑。你又沒吃喜娃他媽的奶。」徐培蘭說。
「我受夠了。咦。我受夠了我。」
徐培蘭蜷在牆角裡抽肩膀。她手裡捏著一隻爛鞋底。她使勁捏它。她使勁閉她
的紅眼皮。她好像擠出來幾星淚水花花。婆子媽抿著嘴笑。
「我沒吃紅薯。我知道紅薯味是我肚子裡的。我肚子裡有什麼東西爛了,我知
道。我打嗝的時候嘴裡就有一股爛紅薯的甜味。這我知道。我不給你說。我做什麼
要給你說?我想看你的母狗樣。我坐在窗子跟前吐氣。」婆子媽說。
「我讓你聞。」她說。
那些天,婆子媽感到她精神很大。一到晚上,她就坐在窗子跟前。
「噗——」她吐氣。
「噗——」她這麼吐。
她張著嘴,下巴一下一下朝前伸。她感到滿屋都是她口裡吐出來的那種怪味。
她很興奮。她聽見徐培蘭不停地在炕上翻身。徐培蘭知道她正往院子裡吐氣。徐培
蘭知道她把嘴對著徐培蘭的窗口。
「噗。」
「噗——。」她就這麼和徐培蘭較勁。她感到她渾身發熱。她們較了一輩子勁,
她還沒這麼熱過。民民他爸死了以後,她不知怎麼的就想跟徐培蘭較勁。她看不慣
徐培蘭。徐培蘭老和民民在他們的屋裡說笑,他們咕咕噥噥像貓念藏經一樣,所以
她看不慣徐培
「格兒。格兒。」徐培蘭老給民民這麼笑。「格兒。格兒。」
「騷情。」她說。她一個人在前房裡說。
「她勾引他。」她說。
「她勾弓哦娃。」她說。
「她狗日的奶子大。」
她想起民民光屁股娃的時候,民民總是精光光偎在她懷裡。民民嘴裡噙著一個
奶子。民民像豬娃一樣拱她。民民一拱,她就幸福得想流眼淚。民民手裡還攥著一
個奶子。民民總這麼吃奶。
「格兒。」徐培蘭這麼笑。
「她驢日的奶子大。」她說。
她能想起民民抓她奶子時候的樣子,可她想不起民民在徐培蘭跟前的作態。
「她欺侮我娃。」她說。
早上起來,她總能看見徐培蘭臉上紅撲撲的。一看見徐培蘭的臉紅撲撲,她心
裡就有些怪,她就感到她臉上的汗毛噌噌響。
「騷。」她說。
「民民。」她喊。
「民民你睡。你驢日的睡到吃飯。」她這麼喊。
「你就這麼過日子麼?你驢日的。」
她聽見徐培蘭悄聲和民民說話。
「快起來你聽媽罵你哩。」徐培蘭說。
「格兒。」
她腦裡邊總有徐培蘭笑的聲音。
「沒見過男人的貨。」她說。
她這麼一說,心裡就來氣。她總能找出個什麼事情和徐培蘭較上勁。
後來,民民在大白溝修水庫挨了石頭子兒,頭上流出來一灘軟不拉嘰的東西,
死了。她們一塊難受了一陣子。
「我的兒呀麼啊啊。」她張大嘴哭。
埋民民的時候她也這麼哭。徐培蘭不哭。徐培蘭直著眼。後來,徐培蘭的眼就
成了紅絲絲雞屁股那種樣子。再後來,照順長大了。她看見照順一天天長大了。照
順一進門就叫喚。
「媽哎。」照順總這麼叫徐培蘭。
「哎。」
她看見徐培蘭把頭從屋裡伸出來。徐培蘭的臉上紅光光。徐培蘭咧著嘴給照順
笑。徐培蘭總要摸照順的頭。
「騷情。」她說。
「沒養過崽。」她說。
「那麼愛別生出來,一輩子裝在肚子裡。那麼愛有本事把他塞回去。」她說。
「我大腿裡夾過幾個。」她說。
「我男人不死我能夾一串。」她說。
後來,她得了那種怪病,扭胳膊扭腳。她不想扭,可她沒辦法。她管不了自己。
她眼看著她的胳膊和腳不停扭,她怎麼也使不上勁。它們在她的眼皮下扭來扭去。
再後來,她就在地上尿尿,在炕上屙屎。她把尿蛋蛋包在手巾裡,放在炕頭上。
「啊。」徐培蘭失聲了。
「啊。」徐培蘭的眼珠子在紅眼皮裡一動不動,一會兒,淚水水就像豌豆一樣,
從眼眶裡滾出來。
「你肮髒人呀麼啊,啊。」徐培蘭說。
「你屙你說一聲,你住手巾裡包呀麼啊,啊。」徐培蘭捏著鼻子哭。
後來,徐培蘭不哭了,也不管了。羊村姐三天兩頭來給她媽洗涮。羊村姐像棉
花包包一樣從大路上滾過來。羊村姐趔著肚子,她走路總把胳膊掄得很開。
「我不嫌棄我媽。我給我媽洗。」羊村姐給人這麼說。
「嘎。嘎。」羊村姐給徐培蘭笑。
夜深人靜的時候,羊村姐睡在她媽跟前,和她媽拉話。
「媽你屙屎,你給人家照順他媽說一聲麼你。」羊村姐說。
「我不給她說。」
「你看你可憐的。」羊村姐說。
「我就感。」
「看你可憐的人笑話哩。」
「我就屙。」
「嘎。嘎。」羊村姐看著屋頂笑。
「我媽活傻了哎。嘎。嘎。」
羊村姐這麼笑。羊村姐的笑聲震得屋頂上往下掉塵土。
「我遲早要把她娃捏死。」婆子媽突然說,「我讓她騷情。」她說。
「嘎。嘎。」羊村姐笑。
「我看她騷情。我看不慣。」婆子媽說。
「我媽說傻話哎,嘎。嘎。」羊村姐說。
「要不是我尿出來,我就捏死他了。」婆子媽說。
「我一鼓勁就尿出來了。」婆子媽說。
「看我媽可憐的說傻話哎。」羊村姐說。
四
那天,她在前房裡尿尿。她蹶著屁股。她知道她骨頭硬了,所以她不蹲,她蹶
著屁股尿。那時候她還沒尿出來。她看見照順在院子裡寫字。院子裡有個石礅,照
順就趴在那裡。
「媽哎。」照順這麼叫徐培蘭。
「哎。」徐培蘭這麼應。
「騷情。」她想。
「照順。」她叫照順。
照順擰過身子,朝她這邊看。
「照順你媽哩?」她說。
「你看你在屋裡尿尿。」照順說。
「我問你媽哩?」她說。
「我媽借小籮去了。我媽要籮辣面子。看你在屋裡尿尿。」照順說。
「照順你來。」她說。
照順走進來,站在她跟前。
「照順我扶著你。」她說。
她把手放在照順的肩膀上。
「你尿。你快尿。」照順說。
她把手往照順脖子那裡挪。
「你捏我脖子上了。」照順說。
「你扶我肩膀上,你甭捏我脖子。」照順說。照順的脖子動了動。
她給手指頭上鼓鼓勁。她還想鼓鼓勁。她感到她小肚子那裡憋得難受,她感到
她快管不住尿了。尿憋在小肚子裡像一包軟東西,一下一下往外脹。
「完了。」她想。
「我不行了。」她想。
她感到大腿那裡有些熱了。她大腿那裡一鬆勁,她就聽見一陣響。
「塌啦啦啦。」
她嚇了一跳。一股酸熱的眼淚水湧進了她的眼眶。她手上沒勁了,就鬆開了。
她聽見徐培蘭從門那裡走進來了。
「看你,捏我脖子。」照順說。
「媽,你看她捏我脖子。」照順給徐培蘭說。
「甭去她跟前。」徐培蘭說。
「塌啦啦啦。」
她尿了好大一陣。後來,她坐在炕上,她看見徐培蘭拉著照順朝廚房裡走。
「騰。」她使勁蹾了一下屁股。
「我要吃。」她吼了一聲。她梗著脖子。
那時候,她還沒穿夾襖,夾襖在箱子裡。她屋裡的櫃頭上放著一個箱子,民民
在大白溝放炮打石頭的時候,偷回來一個木箱,她不讓民民給徐培蘭,她說她要放
衣服,民民就給她了,放在櫃頭上。她用它裝棉衣服,夾襖也在裡邊。後來,她就
穿了那件夾襖。她一穿夾襖,徐培蘭就知道油的事情了。
夾襖上有一塊油污,徐培蘭一眼就看見了。徐培蘭的眼珠子和豌豆一樣。
「啊。」徐培蘭張著嘴。
徐培蘭的眼珠子一動不動,看著婆子媽夾祆上的那塊油污。
「是你偷了油。我以為是老鼠幹的。」徐培蘭說。
那些天,老鼠折騰得厲害。老鼠讓全村的人心神不安。
徐培蘭跳進婆子媽的屋裡。徐培蘭看見木箱子上也有油污。箱子背後有一個粗
瓷老碗,碗裡還有些油。
「啊。」徐培蘭說。
那天,婆子媽去廚房找饃吃,她看見幾隻老鼠圍著油罎子打轉。油罎子在牆角
那裡,光不溜秋,老鼠們找不到下爪的地方。
「她驢日的。」她想。
「她驢日的捨不得吃油。」她想。
「她和她娃偷著吃,一定。」
她一想,就伸手取了一隻粗瓷老碗。她把它塞進油罎子淹在油裡,又取出來。
她把油碗放在她的木箱子背後。她想來想去想到了那地方。後來,她就看見了那只
老鼠。老鼠忽閃著眼珠子往油上瞅。再後來,老鼠們一個跟一個,從洞裡爬出來。
它們順著相腿爬到油碗跟前。她能聽見它們喝油的聲音。它們喝油像吹哨子一樣。
再後來,老鼠們伸長脖子往碗裡湊。她知道油不多了。它們一湊,就踏翻了粗瓷老
碗。
「你做什麼偷油。」徐培蘭說。
「生油又不能吃。」徐培蘭說。
「就是的。」婆子媽說。
「那你偷。」徐培蘭說。
「就是的,我舀了一碗。」婆子媽說。
「你讓老鼠吃。」徐培蘭說。
「我聽響聲。我聽老鼠們喝油的響聲。」婆子媽說。
「你這麼整人。」徐培蘭說。
「它們白日黑裡喝。」婆子媽說。
十年前,她可不這麼和徐培蘭說話。她一聲不吭。徐培蘭像火星燒了大腿一樣
在院子裡跳。那時候,她有些樂。她坐在炕上,用夾襖捂著腿。她歪著脖子翻眼看
徐培蘭。她看著徐培蘭跳出了前門。徐培蘭端著那只粗瓷老碗。她聽見徐培蘭在街
道上給人說油的事。她感到她臉上發熱。她真想把徐培蘭的嘴皮撕下來,讓它吊在
下巴那裡。
「驢日的。」她說。
「她驢日的。」她說。
她想幹點什麼事。她下了炕。她看見徐培蘭借誰家的那只小籮放在案板上。她
知道那是徐培蘭借來的,徐培蘭沒顧上還人家。
「說去,你說你的去。」她說。
她在籮網上戳了一指頭。她聽見「嘭」一聲。
「驢日的說去。」她說。
「嘭。」又響了一聲。
這就是她幹的事。她盤腿坐在炕上,她一直聽著徐培蘭的動靜。她到底聽見徐
培蘭在廚房裡叫喚了一聲。
「啊」
就這麼一聲。
她想徐培蘭的眼珠子又和豌豆一樣了。徐培蘭一定張著嘴。
五
「噗——」
婆子媽坐在窗子跟前,她能聽見徐培蘭翻身的聲音。她甚至把頭伸到窗子外邊,
手按在窗臺上。她蹶起屁股。她一興奮就這樣。
「噗。」她這麼吐。
後來,她感到她頭裡邊有些暈乎。她想她鼓的勁大大了。她想她這麼吐氣熏不
死徐培蘭。她想她這麼吐氣會把她自己吐死。她知道她身子裡有什麼東西爛了。她
這麼一想就有些害怕。
「日他媽我不吐氣了。」她說。
她從炕倉裡翻騰出來兩隻爛鞋。她把它們穿爛了,埋在炕倉裡。這會兒,她想
起它們了。那是兩隻老女人穿的那種小鞋,鞋口那裡有兩條鞋帶。她把它們拴在一
起,拴在門環上。她想把它們拴在門環上,她就把它們拴在門環上了。徐培蘭看見
那雙鞋的時候,它們正在門環上打轉兒。
「你生事。你是生事精。」徐培蘭說。
她靠在門框上笑。她看見徐培蘭像風一樣旋在那雙鞋跟前,把它們攥在手裡。
她聽見嘭一聲,徐培蘭就把它們揪下來了。徐培蘭胳膊一掄,它們就像死雀兒一樣
飛上了屋頂。她看著屋簷頭,她想它們也許會滾下來。
它們沒有。
「我還拴。」她說。
她又拴了一雙。她天天拴。徐培蘭從門環上把它們揪下來,往屋頂上掄。她看
見徐培蘭腰一閃,鞋就上屋頂了。
「你拴我就掄。」徐培蘭說。
「你掄你就掄。我知道你要搶。你就是這麼不想讓我活。」婆子媽說。
「你活你活做什麼你拴鞋?」徐培蘭說。
「我想拴。我愛看。我愛看門環上吊鞋。」
她到底把她積攢的那些鞋拴完了。它們各式各樣大大小小在屋頂上擺了一片,
有小娃穿的,也有大人穿的。徐培蘭能認出來,有幾雙是她阿公爸穿過的。婆子媽
把它們都收拾著,壓在櫃裡。誰知道她做什麼收拾那些爛鞋。現在,它們都上屋頂
了。
徐培蘭和婆子媽都住屋頂上看。她們都仰著脖子。她們心裡都有些吃驚。後來,
她們就你看我,我看你。她們都有些累,她們大口大口出粗氣。
「呼,哧。」
她們像公雞一樣。那會兒村子裡什麼聲音也沒有,就和這會兒一樣,就她們兩
人出氣的聲音。太陽很好。
「我知道我身子裡爛東西了。我不想死。」婆子媽說。
「人都不想死。」徐培蘭說。
「你和照順都活著,你姑也活著,就我死了。」婆子媽說。
「人都不想死。」徐培蘭說。
「我劃不過。我一想就劃不過。」婆子媽說。
「那你要死。」
「我恨氣。」
「那你要死。」
「我沒辦法,又不是我想死。」
「人有時候就沒辦法。」徐培蘭說。
「你姑不讓你們哭。你姑說甭哭甭哭,等你媽走遠了哭。我氣恨你姑。」婆子
媽說。
「我知道你氣恨我姑。」徐培蘭說。
「我心裡鼓著勁,可我沒辦法,我就走遠了。我氣恨你姑。」婆子媽說。
「你姑來了總說她男人怎麼怎麼,我氣恨她。」她說。
「後來我不氣恨你姑了。她男人死了。她男人一死,我就不氣恨她了。」她說。
「這我知道,你說這話我知道。」徐培蘭說。
「你阿公爸睡覺愛咬牙。」婆子媽說。
徐培蘭住她臉上看了一眼。她不想往她臉上看。一想起她十年前就死了,她是
已死的人,徐培蘭心裡就有些怕。可這會兒她住婆子媽臉上看了一眼。她看見婆子
媽的嘴皮子不停動彈。婆子媽的嘴唇也乾癟了,就兩張皮,沒肉。
「我沒說過這事,我沒說過你阿公爸咬牙的事。他睡我跟前,他把牙齒咬得嘎
嘣響。」婆子媽說。
「你沒說過。我沒聽你說過。」徐培蘭說。
「我想起來了。我想起來了就說。」婆子媽說。
「他老擰我大腿,我受不了。我受不了我就想把他掐死。」婆子媽說。
「你看。你看這事。」徐培蘭說。
「後來他死了。我老想他擰我的事。他睡覺咬牙。我睡一覺醒來就摸他,我一
摸才想起他死了。那會兒。我就氣恨你姑了。」婆子媽說。
「我不知道這些。」徐培蘭說。徐培蘭打了個冷顫。其實那會兒沒吹風,天也
不冷。
「你看我不知道。」徐培蘭說。
「我就給你說哩。我又沒說你知道。」婆子媽說。
「你蓋子叔給我褲襠裡塞了一條爛褲子,這我可忘不了。你姑不讓你們哭。你
姑用手背在我鼻子上挨。我可忘不了。」婆子媽說:
「就是的。」徐培蘭說。
「你們圍著我,等我斷氣。你們不吭聲。等我一斷氣你們就哭。你們給我洗完
身子就等我斷氣。」婆子媽說。
徐培蘭心裡抖得厲害。她知道婆子媽說的是十年前的事。村子裡看不見一個人
影,就她們兩人。
「就是的。」徐培蘭說。
「就是的。」她說。
「你們給我穿上壽衣就等我斷氣。那會兒我睡在木板床上。我看不見誰在我腳
上刮,掰我的腳指頭。我看不見。」婆子媽說。
「你姑在我頭跟前。我閉著眼就知道你始在我頭跟前。她過一會兒,就用手背
挨挨我的鼻子。」婆子媽說。
這就是她們說的話。
六
草谷村的姑用手背在婆子媽的鼻子底下挨挨,就說:
「快給你媽洗。」
草谷村的姑拄著一根拐杖。她是個愛乾淨的老女人。她也是小腳。她另一隻手
裡握著一塊手帕。她總這樣手裡握一塊手帕。
那時候,她已經把婆子媽抬到木板床上了。徐培蘭掏空了炕洞裡的陳灰,她把
它們鋪在地上。陳灰蓋住了那股潮濕的尿臊昧。可爛紅薯的氣味遮不住,它攪和在
空氣裡。
羊村姐趔趄到櫃跟前。她從櫃裡取出來一個布包袱,婆子媽的壽衣在包袱裡。
徐培蘭端進來一盆熱水。屋裡的人都不吭聲。照順站在炕牆跟前,沒人看他,所以
他一直站在那裡。
徐培蘭把水盆放在床頭那裡。羊村姐給婆子媽頭上撩了些水,就用毛巾搓那幾
根白頭發。她用火柴梗在婆子媽耳朵裡掏了一陣,她把婆子媽的耳朵撕得老長。後
來,她就給婆子媽擦臉。她手上一用勁,婆子媽臉上的皮就抽扯,婆子媽就口張眼
裂。照順看見婆子媽的眼眶裡沒有眼珠子,全是白顏色。婆子媽的嘴張開來,照順
就看見了她嘴裡那幾顆肮髒的門牙。婆子媽的牙床說不上是紅還是白。婆子媽的脖
子那裡流著幾道髒水。
「輕些。你輕些。」姑說。
羊村姐的手就輕了些,慢了些。羊村姐把毛巾上的髒水扭到盆子裡。她很專心。
她不放過一點地方。她不停地吸鼻涕。她專心的時候,鼻子裡就往外流清鼻。
「弗。」
照順聽見她吸鼻涕的聲音很響。屋裡沒人說話,所以照順聽見她吸鼻涕的聲音
很響。
後來,羊村姐和徐培蘭一起給婆子媽洗身子。髒水從婆子媽的胸脯上流下來,
順著肋骨流下去。婆子媽的胸脯那裡也有兩個奶奶,像給那裡枯了兩片幹蘿蔔皮。
再後來,她就把婆子媽翻過來,給她洗背。再後來,她們就給她洗腿。照順一直看
著那些髒水,看著它們往下流。不大一會兒,髒水就把婆子媽瘦腿上麩子一樣的東
西和成髒泥了。羊村姐用手巾擦它們,把它們扭進水盆裡。
她們終於給婆子媽穿上了壽衣。婆子媽的壽衣又寬又大,烏黑閃亮。婆子媽縮
在壽衣裡,像一根幹柴禾。
她們給婆子媽穿上壽衣以後,就開始給她刮腳。婆子媽的腳趾頭撮在一起,撮
在腳心那裡。徐培蘭一個一個把它們掰開,往趾頭縫裡撩水。她從懷裡掏出來一把
剪刀,用刀刃在婆子媽的腳上刮。照順看見她刮下來一堆粘粘糊糊的東西。徐培蘭
用手指一抹,再把它們彈在地上。她涮涮剪刀,再刮。
她們不吭聲,也不咳嗽。她們都能聽見羊村姐吸鼻涕的聲音。
羊村姐從包袱裡取出來兩隻小鞋,套在了婆子媽的腳上。她又取出來一條白褲
帶,纏在婆子媽的褲腰那裡。蓋子叔按按她的手,她瞪著蓋子叔。蓋子叔給徐培蘭
點點頭,讓徐培蘭過來。徐培蘭把頭湊在蓋子叔的耳朵跟前。
「取塊布。」蓋子叔說。
「新的舊的?」徐培蘭說。
「舊的。」蓋子叔說。
徐培蘭找了一條舊褲子。照順看見蓋子叔把它塞進了婆子媽的褲襠。
「啊。」照順叫了一聲。
他們就看見他了。
「出去,這娃,出去。」蓋子叔說。
「甭走遠,一會兒你再來,叫你你再來。」蓋子叔說。
照順沒走。照順立在門外邊。他看見草谷村的姑又用手背挨婆子媽的鼻子了。
「還有氣。甭哭。你們先甭哭。」她說。
就這麼,他們圍著婆子媽。他們不說一句話。他們一個勁出氣。他們聽見空氣
裡有什麼聲音。沒人說話,所以他們能聽見。
草谷村的姑用手背又挨了。
「甭哭,讓她走遠點。一哭她又回來了。」她說。
「活著受罪哩,讓你媽走。」她看著羊村姐和徐培蘭。
羊村姐不吸鼻涕了。她感到鼻眼有些酸,眼眶裡也有些酸。她歪著頭,看著她
媽的臉。她順著眼皮。
徐培蘭的鼻子也有些酸。一到這光景,人的鼻子都會發酸。蓋子叔蹾在炕沿上,
往煙袋鍋裡裝旱煙。
「姑,你看我媽抖了一下。」羊村姐說。
「姑,你看我媽的褲子濕了。我媽尿了。」羊村姐說。
「哭。姑,我說哭。」羊村姐說。
草谷村的姑又挨了挨婆子媽的鼻子。
「哭。」姑說。
羊村姐像雁一樣伸了一下脖子。
「哎嗨嗨嗨媽喲。」羊村姐哭了。
「哎嗨嗨嗨媽喲。」徐培蘭也哭了。
「哎嗨嗨嗨把你的娃耶。」羊村姐說。
「哎嗨嗨嗨你把我耶。」徐培蘭說。
她們拖著長腔。她們像唱戲文一樣。她們的哭聲拐著彎,從前房裡拐出來,拐
了老遠。一會兒,她們就哭出了眼淚水。
「照順哭。」蓋子叔說。
照順跪在地上,蹶著屁股。
「啊。哈。」
照順哭了。照順的氣短,所以照順這麼哭。照順哭得很認真。
姑點著了一盞煤油燈,放在婆子媽的腳底下。
「哭哭算了。讓人報喪去。」她說。
「挖墓。」她說。
她搖搖徐培蘭的肩膀。她掉了門牙。她的嘴像一瓣枯萎的喇叭花。
徐培蘭不哭了。徐培蘭捏了一把鼻涕。
「啪。」
鼻涕從她的手指頭上飛出來,粘在了牆根底下。
七
「我不甘心。」婆子媽說。
婆子媽的眼珠子有些兇惡。她說著說著眼珠子就有些兇惡。
「我說我不甘心。」她說。
「你都死了你說這話。」徐培蘭說。
「黃鼠在我那裡打洞。」婆子媽說。
「我不懂。你說這話我不懂。」徐培蘭說。
「它們打到墓堂裡了。」婆子媽說。
「它們打了十年,它們一直打,就打到墓堂裡了。」她說。
「它們在那裡磨牙。」她說。
「黃鼠打洞我有什麼辦法。我讓照順塞過黃鼠窩。村上人都去亂墳灘那裡塞黃
鼠窩,他們怕水灌進去,他們怕墳堆塌了,裂口子,所以他們都塞。我讓照順塞過。」
徐培蘭說。
「它們要打洞,我有什麼辦法。」
「我聽見它們在我跟前磨牙。」婆子媽說。
「我不信。你說這話我不信。」
「棺材爛了。它們在爛木板上跑來跑去。」婆子媽說。
「總要爛。棺材埋在地裡總要爛。」徐培蘭說。
「我身上往下流水水。臉上也流。水水一流,我就剩骨頭了。它們舔我身上流
的水水。」婆子媽說。
「它們不放過我。」她說。
「後來,水水滲到土裡了,它們就舔土。」她說。
「黃鼠是吃草的蟲蟲。」徐培蘭說。
「後來,它們撥我的骨頭。它們把我的骨頭撥得噌楞響。它們叼著我的頭髮在
墓堂裡亂跑。」婆子媽說。
「你看。你說的我不知道。」徐培蘭說。
「她們跑來跑去。它們不停地叫喚。」婆子媽說。
「它們就這麼折騰我。」她說。
「我躺在棺材裡好好的。這你記得,我躺得好好的。」她說。
那天,蓋子叔招呼幾個小夥,讓他們打開棺材蓋。時辰到了。蓋子叔叫照順過
來。照順手裡拄著紙棍。
「照順你來。」蓋子叔說。
婆子媽的臉上蓋著一張紙,照順看不清她的模樣。照順有些害怕。照順看見蓋
子叔給婆子媽解開了褲子。他知道她的褲襠裡塞著一條舊褲子。他一直記著。他想
不到蓋子叔會叫他取那個東西。
照順往蓋子叔的臉上看。
「你取。你是孫子,你取。」蓋子叔說。
照順摸到了它。他感到它濕浸浸的。他聞到了一股嗆鼻的尿味。他把它撕出來,
扔在炕倉底下。他裝著滿不在乎的樣子。他甚至往那條舊褲子看了一眼。他看見屋
裡的人好像沒什麼事一樣,沒人看他。羊村姐等他扔了那件難聞的東西,伸手給婆
子媽緊好褲帶。
「抬。」蓋子叔說。
他們把婆子媽抬起來,往棺材裡放。草谷村的姑一直把在棺材上,她等他們放
好婆子媽,就用手巾給她擦了擦臉。她臉上邊落了一層塵灰。
「看著,看你媽一眼。」蓋子叔給徐培蘭和羊村姐她們說。
她們都往棺材裡邊看。婆子媽的眼窩四成了兩個圓坑。婆子媽躺在寬大的黑壽
衣裡,她的手從袖口那裡露出來一些。一隻手裡放了一塊手帕,另一隻手拿著一把
紙扇。她這麼顯得很福氣。
「一蓋上你們就哭。」蓋子叔說。
「蓋!」蓋子叔喊了一聲。
徐培蘭和羊村姐就哭了。照順看著蓋子叔爬上棺材蓋,在上邊跳了幾下,然後,
他從蓋子上砸進去幾個鐵釘。
「哭。」蓋子叔說。蓋子叔在照順的屁股上踢了一腳。
「啊。」照順哭了。
「哈。」照順拄著紙棍哭。
照順抹鼻涕時候,鼻眼裡鑽進來一股尿味。他知道是那條褲子上的,它們在他
的指頭上,還沒有散完。
「後來,就沒爛紅薯味了,得是?」婆子媽說。
「就是的。一出煞就沒了。我一進門就聞不見了。」徐培蘭說。
那時候是正午,他們都躲出去了,屋裡只放著那具棺材,空蕩蕩的屋裡就一具
棺材。他們給醋罎子、醬油罐子、門扇、板凳一類的東西上都貼了一片紅紙。他們
給那幾棵桐樹上也貼了。他們躲在隔壁的富士家。一會兒他們就聽見了屋裡的響聲。
「響哩。」他們說。
「你聽響哩。」
他們互相看。他們都張著眼。他們想不出那是一種什麼東西。他們叫「出煞」。
他們想也許是一股紫氣,它從棺材裡跑出來,把屋裡的東西沖得稀裡嘩啦響。他們
想死人身子裡都有這種東西。他們害怕它。他們沒有見過,可他們害怕,所以出煞
的時候,他們就躲出去。他們把門大開著。他們在隔壁富士家聽它在屋裡折騰。
「就這麼屋裡沒了爛紅薯的怪味。屋裡只有一股死人的味道。照順說他手指頭
上的臊味沒散完,他說他能聞到,他說洗不淨。徐培蘭說沒有沒有了照順你是心裡
病。徐培蘭把照順的手指頭放在鼻子底下,她抽抽鼻子。
「沒有,你聞。」徐培蘭說。
照順聞聞手指頭,沒說話。
那天,徐培蘭點了一堆火。她把婆子媽的夾襖褲子那一類東西架在火上邊燒了。
她把它們埋在糞堆裡。她埋灰的時候,才看見有一塊布沒燒完,她看不出是夾襖還
是褲子上的。好多天以後,她還想著那沒燒盡的布。她一直想著它。她記得火很旺。
她想不出為什麼沒燒盡,偏偏剩了那麼一塊。
「算了。」她說。
她燒了那些東西以後這麼說。她進了廚房。一會兒她提著菜籃子出了門。她去
亂墳灘送飯,幾個男人在亂墳灘那裡給婆子媽挖墓。那裡長著幾棵樹,老遠就能看
見。徐培蘭頭上戴著孝。徐培蘭的孝褂兒白白淨淨。徐培蘭的鞋上包了一層白布,
也白白淨淨。徐培蘭挎著菜籃子從街道上往過走,她看見村裡的女人們從她們的門
裡邊伸出半個身子看她。她們和她打招呼。她們壓著聲。
「死了?」她們說。
她們顯出關心的樣子。她們閃著眼珠子。
「噢麼。」徐培蘭說。
「入殮了?」
「澳麼。」
徐培蘭挺了挺胸脯。她突然感到她有些高興。她不知怎麼的感到有些高興。她
抬著下巴,從她們的眼皮底下走過去。她能聽見她走路的腳步聲。太陽光從西邊照
過來,照在她的臉上。她想太陽光這麼照著她也很高興。
「噢麼。」她說。
八
棺材停放在臺階那裡。她們記得婆子媽睡在裡邊的模樣。
「嘎嘎。」
羊村姐在炕上笑。她坐在炕上。草谷村的姑也坐在炕上。徐培蘭又鋪了幾次灰。
婆子媽的氣味小多了。婆子媽的櫃蓋做了靈台,兩根大蠟燭流著淚。燭光在她們的
臉上搖擺不定。
「我媽自在了。姑哎,我說我媽自在了。」羊村姐說。
羊村姐的頭埋在一堆肉裡。她越來越胖了,它脖子那裡的肉像發麵一樣。
「噢麼。」姑說。姑撮著瘦嘴。
「自在了,我說自在了。」羊村姐說。
羊村姐挪挪屁股。她把手塞在屁股底下。炕有些熱。徐培蘭靠著門,她正往嘴
裡塞饃。她們能聽見她拌嘴的聲音。
「明兒個一埋,我媽就沒氣氣了,我媽在這屋就沒氣氣了。」羊村姐說。
「人一埋就沒氣氣了。」姑說。
「人活一輩子一埋就沒氣氣了。」站說。
「姑,給我媽還做獻湯不?」徐培蘭突然說。
「做麼。做麼。給你媽最後一頓飯麼。」
「我給我媽做去。」羊村姐說。
徐培蘭看了羊村姐姐一眼。她手裡的饃還沒吃完。她往嘴裡又塞了一塊。她看
著羊村姐下了炕,從門裡搖擺出去。一會兒,廚房裡就有了聲響。
「你要掃墓哩。」姑說。
「我不想去。我一個人。」徐培蘭說。
「看這娃。」姑說。
「我一個人去亂墳灘害怕。」徐培蘭說。
「看這娃。要掃哩。」姑說。
「害怕也要掃?」徐培蘭說。
「規矩麼。老輩人立的規矩麼。媳婦掃墓,規矩麼。」姑說。
羊村姐端著獻湯進來了,清湯裡沉著幾條面片。她立在靈桌跟前,她把臉皮往
下拉。她一拉臉皮,看著就有些難過的樣子。
「媽,你吃,你吃你就動動筷子。」羊村姐說。她看著清湯裡的面片。碗上邊
放著一雙筷子。
「我一會兒再去。」徐培蘭說。
「你一會兒就一會兒。」姑說。
「還要掃墓。你看還要掃墓。」徐培蘭說。
「姑你看。」羊村姐叫了一聲。
「我媽動筷子了。」她說。
她們都往碗上看。羊村姐一說。她們就看筷子好像動了。她們好像聽見了筷子
動的響聲。她們知道婆子媽躺在棺材裡。她們記得她的模樣。
「筷子動就是你媽吃了。」姑說。
「我看是假的。」徐培蘭說。她感到她臉上的皮有些緊,像遭了風一樣。
「吃了碗裡的面片怎的就沒少?」她說。
「都是人憑嘴這麼說哩。」她說。
羊村姐張著眼睛,往徐培蘭臉上看。她好像有些吃驚。
「你看照順他媽說的話。」羊村姐說。
「你看照順他媽。」
「掃墓去,你掃墓去。」始給徐培蘭說。
徐培蘭把手伸進炕倉,取出來一把笤帚。她朝門外看了一眼。
「天這麼黑。」她說。
她感到風從門縫裡鑽進來,往她的脖子裡灌,一直灌到她褲腰那裡。
「誰立的這規矩,真想不出誰立的這規矩。」她說。
她往棺材那裡看了一眼。那裡也點了一根蠟燭。婆子媽和她隔了一層木板。
「她的眼成了兩個深坑。」她想。
「你沒掃墓。我知道你沒掃墓。」婆子媽說。
徐培蘭的眼珠子成了豌豆。徐培蘭這會兒老多了,可徐培蘭的眼珠子和過去一
樣,動不動就成了豌豆。
「你在野地裡尿了一泡就回來了。」婆子媽說。
徐培蘭夾著笤帚從街道上往過走。街道上沒有人,也沒有聲響。家家門口都長
著一棵樹,樹上也沒有聲響。徐培蘭聽見她的腳步聲從底下浮上來,一直浮到街道
那頭。一出街道,她就看見亂墳灘了,那裡掛著一盞燈籠。墓挖好了,挖墓的人給
那裡掛了一盞燈籠。
「她死了。棺材釘得嚴嚴實實。蓋子叔在上邊跳了幾下。」她想。
她感到她手心裡有些濕。她看著遠處的那盞燈籠。
「我出汗了。我手心裡出汗了。」她說。
她感到小肚子那裡有什麼東西在抽。她知道她想尿了。她想看看周圍有人沒有。
其實她一直看著那盞燈籠。她聽見什麼地方有流水的聲音。她聽著就越想尿了。
「我不掃了。我不想掃墓了。」她說。
她解開褲帶,蹲在路邊的野地裡。她聽見尿水像射箭一樣往土裡沖。她感到她
眼睛裡有些酸。她想尿把人憋急了人就會這樣。
她聽見誰咳嗽了一聲。
「康定。」她喊。她聽出是康定的聲音。
「澆地哩。我澆地哩。」康定說。
「我給我媽掃墓唻。」她說。
「噢麼。我說麼。」康定說。
她感到她身上的肉鬆了。她緊好褲帶,夾著笤帚往回走。
第二天清早起棺。女人們排著長隊,跟在棺材後面哭。走到尿尿的地方,徐培
蘭睜開眼找了一陣。她看見她尿在一塊瓦片上了。尿水衝開的土裡邊,正好埋著一
塊瓦片。
「你說我沒掃墓就沒掃墓,你又沒跟著我。」徐培蘭說。
「沒掃就沒掃。」她說。
她看了婆子媽一眼,婆子媽正給她笑,婆子媽一直是這麼個模樣。
九
婆子媽老回來,這是她沒想到的。屋裡一滿是爛紅薯的氣味。
婆子媽靠著門框和她說話。婆子媽說話的時候不停扭胳膊扭腳。她在炕上蹾屁
股,在地上尿尿。她弄得屋裡一滿是爛紅薯的怪味。
「受死我了。這屋裡受死我了。」徐培蘭說。她咬著被子。她用指頭擰胸脯上
的肉。她喉嚨裡有一種粘粘糊糊的聲音。
「嗚」
「鳴——」
後來,她蹬開被子,跳下炕,撒開腿往羊村跑。她一口氣跑到羊村姐那裡。她
們有十年沒來往了。羊村姐還是那麼個碌碡樣,走路像滾球一樣。
「你說死了就沒氣氣了。你說過這話。」徐培蘭說。
「嘎。」羊村姐笑了一聲。
「她和我說話。我受死了。這麼就受死我了。」徐培蘭說。
「嘎。」
「一屋裡紅薯味。」
「看我媽可憐的。」羊村姐說。
「受死我了。」徐培蘭說。
「嘎。嘎。」
「照順不在,我一個人在屋。我都想跑了去。」徐培蘭說。
「看你說的,自家屋裡你跑了去。」羊村姐說。
「嘎嘎嘎嘎。」
羊村姐笑出來一串響聲。
「看你說的。」羊村姐說。
「我一急身上肉就癢癢。」徐培蘭說。
「燒紙。到墳裡燒些紙。」羊村姐說。
「看我媽可憐的。」她說。
「她說她不甘心。她說黃鼠打洞,舔她的水水。」徐培蘭說。
「燒些紙。看我媽可憐的。」羊村姐說。
「不頂事。我看不頂事。」
「人不能讓尿憋死。」羊村姐說。
「有時候就憋死了。」
「看你說的,你把事情說得死死的。」
徐培蘭一回來,就朝著門框那裡吼:
「你真毒辣。你這人真毒辣。」
婆子媽穿著夾襖,夾祆上明光閃亮。徐培蘭想起她燒夾襖的時候,它就明光閃
亮。她想起了那堆灰。這會兒穿著它。
「日怪了。」她想。
「你就這麼神裡鬼氣。」她說。
「呸。」她吐了一口。
她看見婆子媽跳了一下。婆子媽就跳了一下,又靠在門框上。
「你讓我受死了。」徐培蘭說。
「噢麼。」婆子媽說。
「你不回來就好了。」徐培蘭說。
「噢麼。」婆子媽說。
「噢麼噢麼。」徐培蘭說。
「我想讓你扭胳膊扭腳。」婆子媽突然這麼說。
「我不想。我又不想扭。」徐培蘭說。
「我扭了一輩子。我難受我才扭。你阿公爸一死我就想扭,後來就真扭了。扭
了也難受。」婆子媽說。
「我難受,可我不想扭。」徐培蘭說。
「說不準哪天你就想扭了。」婆子媽說。
「我不想。」
「你總要扭。我說你總要扭。」
「我想進門裡去。你離開些讓我進去。」徐培蘭說。
徐培蘭把門關上了。她關門像抽筋一樣。她從門縫裡往外看。
「你走。我說你走。」她說。
後來,她從櫃裡翻出來一盒紙。婆子媽死的時候沒燒完,剩下幾盒。她把它們
放櫃裡了,她一直記著它們。天傍黑的時候,她點著了它們。她看見紙灰帶著火星
往上躥,在半空裡打著旋兒。
後來,她想好好睡一覺。她把被子蒙在頭上。她在被窩裡眨矇眼。她聽見她的
眼皮噌嘭噌嘭響。
「我睡不著。」她說。
她想哭。她想哭的時候,喉管裡就有一堆什麼東西往外擠。再後來,她就聽見
了敲門聲。那時候星星正稠。門環一聲一聲響。那時候沒風,那幾天一直沒風。她
知道是婆子媽。婆子媽沒走,她一直在外邊站著。星星稠的時候她就這麼敲門。
十
照順回來的那天,徐培蘭正挨著牆坐在炕頭那裡。照順那些天一直在一個叫武
威的什麼地方賣衣服。照順說那地方很冷。照順賺了一筆錢。照順已長過門扇了。
「媽我餓了。」照順說。
徐培蘭給照順做好飯,就坐在炕上看照順吃。照順吃著吃著不吃了。照順往徐
培蘭胳膊上看。
「媽你胳膊動哩。」照順說。
照順聽見他媽叫喚了一聲。
徐培蘭的胳膊像揭線蟲一樣。徐培蘭往胳膊上鼓勁,她不想讓它動彈。她把腳
從被窩裡抽出來,她看見她的腳也像拐線蟲一樣。
她叫喚了一聲。
「媽你別讓它動。」照順說。
「不行。照順不行。」徐培蘭說。
「照順你就讓媽扭。媽不想扭。媽沒辦法麼呀哎,哎。」徐培蘭說。
晚上,照順聽見他媽一個人在屋裡哭。
「哎嗨嗨嗨你把我耶。」她拖著腔。
「啊。啊。」她吸了兩
口氣。
「啊。」
她又吸了一口。照順想他媽這會兒一定仰著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