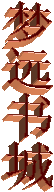
楊爭光 黃塵
——快樂家園第一
一
富士在牛屁股上抽了一鞭子,牛毛上冒起了一股煙塵。他看見他給那裡抽出來
一條白道兒。牛毛裡有上,所以就出來一條白道兒。牛縮了縮屁股,快走了幾步。
「哦。哦。」他這麼吆喝牛。
他光腳踏在犁溝裡。地有些熱,好長時間不下雨了。地就有些熱。富士一直等
雨,可等不來。富士挽著褲腿,他的腳底下也冒煙塵。地大幹了,富士知道。富士
不往下看,他抬著頭。他額顱上有幾道紋理,讓土填滿了。塵土在空氣裡飛來飛去,
看不見,可它飛來飛去,填在那些紋理裡邊,汗水一浸,就那麼粘在富士的額顱裡。
「哦。哦。」他這麼吆喝牛。
天不下雨,太陽就熱。什麼都熱。富士心裡像長了毛。他一低頭,就感到那些
毛在心裡頭往上長,所以他不低頭。他把頭放在脖子上,讓它胡轉,這麼,他就覺
不得那些毛了。他就這麼個樣子,就這麼吆牛,頭胡轉。有時候,他就把頭轉到煥
彩那個方向。煥彩在那裡挖玉米根。
煥彩家的地和他挨畔。煥彩貓著腰。他聽見煥彩的鼻子裡稀溜稀溜響,所以,
他有時候就把頭轉過去,朝煥彩那裡瞄一眼。
「哧——」
他聽見響了一聲。他看見煥彩在鼻子上捏了一把,就這麼響了一聲。煥彩手一
甩,她甩得真准。他看見煥彩手指頭上的鼻涕甩出來,像飛蟲一樣。它掛在一個玉
米根上了。
「哭哩。」他想。
「那女人哭哩。」
煥彩死了男人,沒人幫她收拾地。大忙天,人都顧自家,誰都顧不上誰。一到
忙天,煥彩就想援朝。援朝是她男人。以前,援朝開個拖拉機,手扶拖拉機,有一
次,他和它一塊栽到壕溝裡,就死了。援朝讓她下了兩個崽。這時候,那兩個崽坐
在地頭上,他們正罵仗。
「你媽鱉。」一個說。
「日你媽。」另一個說。
「媽鱉媽鱉。」
「日你媽日你媽。」
他們都坐著。離他們不遠的地方,放著富士的兩隻鞋。還有些人在地裡,他們
收拾他們的地。天不下雨,他們也收拾,野地裡散著他們的影影。野地裡很靜。
「媽鱉媽鱉媽鱉……」
「日你媽日你媽……」
他們比賽看誰的氣長。
煥彩穿件短袖衫衫。過去這時候早脫了,都是日他的不下雨。女人們都穿短袖。
煥彩的短袖衫衫上有一塊濕了,貼在脊背上,還有一塊也濕了。貼在胸脯那裡。那
裡圓鼓鼓的。
「軟的。」富士想。
富士突然這麼想。他聽見心裡頭「咚」一聲,他以為煥彩聽見了。
煥彩沒聽見。她貓著腰,那裡還是圓鼓鼓的。富士的胳膊裡有些癢癢,往手指
頭那裡癢癢。他把犁把緊捏了一下。
「那東西是軟的……」
他看見花香往他跟前跑。快正午了,富士想把地犁完,就讓花香回去給他取饃。
她一會兒功夫就來了。花香空著手,她的臉白煞煞,嘴裡往外噴氣。
「死了。」花香說。
富士有些腿軟。花香一這個模樣,他就腿軟。娶花香的那天晚上,花香的臉就
白煞煞的。花香把被子擁在脖子那裡,看著他。他用膝蓋往花香跟前跪,花香的臉
就白了,嘴張著。富士的腿就軟了,他一屁股軟在花香的身子跟前,一動不動。花
香搖了他半天。
「你咋啦咋啦?」花香說。
「我想騎你,騎你身上。」富士說。
「我腿軟了。」他說。
「你騎你騎。」花香說。
「你騎。」她說。
他沒騎成。以後好多天也沒騎成。花香費了好大勁,才讓他騎了。可花香就是
不能白煞煞臉,一白煞煞,富士就腿軟。
這會兒,富士感到他的身子往下溜,他想坐在犁溝裡,因為他腿軟了。
「死了。」花香說。
「徐培蘭家的貓死了。」她說。
富士愣著眼珠子,朝花香臉上瞅。
「你咋啦你看我給你說哩。」花香說。
「說哩說哩。」富士說。
「你說麼。」他說。
「徐培蘭家的貓死了。我一回去,就看見徐培蘭,我就往回折。她家的貓死了」
「噢。嗯。啊?」
富士緩過神來,他的眼睛張大了許多。
「你說那只貓,就是那只貓死了?」
「嗯啊。我看見徐培蘭抱著。」
花香個子有點矮,像軟乎乎的麻袋,說話時身子一搖一搖。
「走。走。」富士說。
「走。」花香說。
煥彩看著他們。那兩個崽不罵仗了,也看。富士走到地頭,光腳往前一攛,攛
走了那兩隻布鞋。
「哧——」
煥彩又甩了一把。她沒哭,可她甩了一把。這一回沒甩在玉米根上。其實,富
士沒看見,也沒聽見。
二
蓋子叔什麼也不知道。他坐在草垛旮旯裡。不知是誰家的草垛,那裡摞了好多
草垛。他們嫌草垛占自家的院子,他們像南山猴一樣,一個看一個的樣,都把草垛
摞在路邊。那裡是官地方。
蓋子叔就坐在那裡,他讓息娃子給他提布褂上的蝨子。他老了,可一時還死不
了。他這樣的人,村上已經不多了。
「我只捉一個。」崽娃說。崽娃一臉不情願的樣子。
「你捉喀。你提。」蓋子叔說。
「我都給你說了。我只捉一個。」
崽娃跪在蓋子叔跟前,拿著蓋子叔的布褂。
「娃家眼尖。娃家不能懶。」蓋子叔說。
他把頭窩在肚臍眼那裡,用手翻扯他的長褲腰。他沒幾根頭髮,就幾根雜毛。
雜毛裡塞了些土和柴草一類的東西。
「蝨子可靈哩,你穿上衣服它就出來咬你,你一脫,它就不見了,它鑽布縫縫。
它在布縫縫裡,你小心看。」他說。
他們都不抬頭。他們捉得很努力。
「爺說,六十年一個輪回,民國十八年就這麼旱。你看這天。時景到了,我說。」
其實他沒看天,他窩著頭。
「我只捉一個。」崽娃說。
「人沒吃的,吃草吃樹葉,吃光了。人隔肚皮能看見腸子,綠的。肚皮裡沒油
水就薄了,像燈籠紙,就能看見腸子。天旱,不長莊稼,草一個勁長。日他的怪。
爺不哄你。」他說。
他用舌頭潤潤嘴唇。
「你看這天。」他說。
「我都急了。你不讓我走。我都想尿了。」崽娃說。
「尿麼尿麼,這娃,你尿麼。人餓肚子的時候就沒樣子了,就急眼。我搶了染
坊三的饃。你不知道他,他早死了,你沒生出來他就死了。他攆我,我急眼了,我
把饃塞在牛糞裡,我說你攆你攆。他不攆了,往牛糞上看。他一走,我就刨出來吃。
不髒,髒什麼。人一餓就沒臉了,人沒臉就沒辦法。牛糞是草變的,髒什麼,不髒。」
他說。
「你看,爺捉了一個。」他說。
他讓崽娃伸開手。崽娃看著那個小東西從蓋子叔的手指頭上掉下來,在他的手
心裡不停動彈。
「我扔呀。」崽娃說。
崽娃手裡癢癢,一直癢癢到他心裡頭。他怕那個小東西從他的手心裡鑽進去,
鑽到他的肉裡邊去。
「不扔。人扔蝨子身上越出得多。」
蓋子叔伸長脖子,把那個小東西捏過去放在嘴裡。崽娃看見他嚼它。
「你吃蝨子!」崽娃叫喚了一聲。
崽蛙鼓著眼珠子,臉憋得漲紅,像屙屎一樣。
「吃蝨子沒什麼不好。蝨子是自個身上出的。你見誰扔蝨子沒?」蓋子叔說。
「你看這天。這熊天喀。」他說。
就他們兩個人在那裡說話。滿世界就好像只他們兩個人。蓋子叔挪屁股的時候,
柴草就發出些聲響。
後來,富士和花香走過來,他們看見了蓋子叔。他們把眼睛張大。
「八叔。」他們叫。
他們在面前不叫他蓋子叔,叫他八叔。蓋子是他的小名。
就這麼,他們給蓋子叔說了貓的事。
「死?啊?」
蓋子叔從柴草窩裡拱起來。花香看見他肋子那裡排著許多骨頭。
「你再說。」蓋子叔說。
蓋子叔看著花香,好像要把花香吃到他的眼窩裡。花香把頭一下一下往脖子裡
縮。
「徐培蘭抱著哩。」花香說。
「死了?」蓋子叔說。
「死了。」花香說。
蓋子叔把頭歪過來,朝富士臉上看。富士不說話,他的腳有些癢,他把它從鞋
窩裡拔出來,放在另一隻腳上蹭,蹭來蹭去,所以,他沒說話二
「怎麼死了?」蓋子叔說。
「就說哩。」花香說。
「你沒問她?」
「我看見她抱著。」
「你看把他的。」蓋子叔說。
「她說她娘家有個公貓,她說她去配。你看把他的。」蓋子叔說。
「死了。我看見的。」花香說。
「真真的?」
「真真的。」花香說。
花香拼命點頭。蓋子叔把褲帶勒緊,把胳膊塞進布褂袖筒裡。
「你看把他的。」他說。
蓋子叔前邊走。富士把腳塞進鞋窩,他和花香跟在後頭。息娃子在柴窩裡,朝
他們的背影眨矇著眼。
三
那是一隻母貓,他們都記得它。那些天,它老在樹上叫春,叫得人心神不寧。
玉米收了,人們都在等雨,他們一天一天等。它這時候叫春。徐培蘭家後院裡有一
棵樹,它就爬在樹上,三鄰五舍都能聽見它的叫聲。
它冷不丁在樹上叫起來,這是誰也想不到的事。
那天晚上,徐培蘭還沒睡,雖然她鑽在被窩裡,可她沒睡。照順爬在櫃蓋那裡,
正往本子上寫什麼。照順是她的兒子。修水利的時候,民民在大白溝放炮打石頭,
石頭片飛在他腦門上,給那裡撞了個黑窟窿,流出來一堆稀不拉嘰的東西,他就離
了人世。埋民民的時候,徐培蘭沒哭,連一滴鼻涕都沒流。她愣著眼看兒子照順,
看了整整一個晚上,眼睛就成了雞屁股那種樣了。後來,她的眼一直紅不絲絲,像
遭了風一樣。現在,照順上學了,能往本子上寫什麼了。徐培蘭老這麼鑽在被窩裡
看他。
後來,她就聽到了貓叫春的聲音。先叫了一聲,又叫,又叫。那時,夜晚很靜。
它一聲一聲叫,從喉嚨裡撕扯出那種聲音,說不清是什麼滋味。它就那麼叫著,一
聲一聲往人的肉裡頭鑽。
「嗚——哇啊。嗚——哇啊。」就這聲。
它把樹搖得撲啦撲啦響。
「民民。民民。」
徐培蘭聽見婆子媽在前房裡喊她。婆子媽不叫她的名字,叫她男人的名字。她
聽見婆子媽的聲音有些興奮。婆子媽得了一種怪病,不痛不癢,就一隻腳和一個胳
膊不停地扭。她喜怒無常,一個人住在前房裡。她在炕席上屙屎,在地上尿尿。她
把屎蛋蛋包在手巾裡,放在炕頭上。徐培蘭數說她,她就對著徐培蘭笑。徐培蘭一
走,她就把頭放在窗口上,伸長脖子沖著徐培蘭的脊背罵:
「你眼黑我得是?狗日的你眼黑我。」
她扭胳膊扭腳,她老這樣有事沒事罵一陣。她和徐培蘭像仇家對子。
這會兒,她的聲音有些興奮。
「民民你聽。」她喊。
「叫春哩。叫春哩。」她說。
徐培蘭聽見她在炕上蹾屁股。她一興奮就蹾屁股。
「貓和人一樣哩。」她說,「貓和人都懷春哩。人就是不喊,貓可不是人,貓
想了就叫喚。啊哈。啊哈。」
她把屁股蹾得騰騰響。
第二天清早,徐培蘭一出門,就碰見了許多詭秘的眼珠子。女人們掃院掃到門
外,她們都朝徐培蘭家門口看。她們不和徐培蘭說話,就看著她。
花香也看著徐培蘭。她提著笤帚。她和徐培蘭住隔壁。她也不說話。她們離得
很近。
「貓叫春哩。」徐培蘭說。
徐培蘭笑了一下。她原以為花香會說句什麼,花香也會笑一下,可花香沒有,
徐培蘭的笑就僵在臉上了。她不知道該怎麼辦。她看著那些女人們。她感到身上有
些冷。
「我家貓叫春哩。」她說。
「劈啪,劈啪。」
她聽見一串關門的聲音。女人們都跳進她們的門坎,把門關上了。她嚇了一跳。
就剩下花香一個人了。
「我家貓……」她說。
她很不好意恩的樣子,好像做了什麼虧心事。她還想說一句什麼話。她看見花
香把鼻子往上挽了一下。
「唰。唰。」
花香狠勁掃了兩笤帚,塵土飛揚。花香從門坎上跳回去。花香關門的聲音很重。
「咣當!」
徐培蘭感到一股氣從她的肚子裡邊憋上來,一直憋到眼窩那裡憋出了幾星淚水
花花。她把笤帚摔在地上。
「毬日的。」她吼了一聲。
「我又沒做虧心事。」她說。
「我家貓叫春,又不是我叫。」她說。
這時候,太陽從東邊那個村莊莊頂上升起來。徐培蘭站在門口,能看見它。它
剛升起來,沒多少光氣,就有點紅,像紅蘿蔔那種顏色。
她聽見門坎響。婆子媽不知什麼時候出來了,手把著門框,看著她笑。婆子媽
的臉也像紅蘿蔔那種顏色。昨晚上,她蹾了一夜屁股。
「噁心。腥氣。」徐培蘭說。
她看見羊村姐從大路上朝這裡走。
四
羊村姐像個碌碡,一滾一滾,從路上滾過來。她越來越胖了,看著不是胖,是
腫,好像有個人給她什麼地方插了個竹筒,往她身子裡吹氣。誰知道她吃什麼。世
上就有那麼一種人,喝口涼水也上膘。
沒到跟前,羊村姐就笑。她笑的時候,肚子一趔一趔。
「嘎。嘎。嘎。」
她不一下笑出來,她一聲一聲笑。
「媽又屬炕上了,得是?」她說。
一你看去。你一看就知道了。」徐培蘭說。
「嘎。嘎。嘎:」
羊村姐掄著胳膊,從門坎上滾進去。一會兒,她提幾件惡臭衣服走出來。她把
它們抖開,抖在太陽底下。太陽光好像都照在那些衣服上了。
「嘎。嘎。你看我媽呀哎。老糊塗了呀哎。嘎。嘎。」
她笑著,說著。她一個人。徐培蘭早進屋了,在廚房的鍋底下戳爐子,準備做
早飯。羊村姐一個人在外邊說著,笑著。後來,羊村姐蹾在太陽底下給她媽刷洗那
些尿衣服屎褲子。屎臭尿臊味一個勁沖她的鼻子。一會兒,鐵盆裡漂起來許多屎花
花。她把它們倒掉,換了水再洗。再一會兒,她就抽鼻子了,淚水水從她的大眼角
那裡往下掉。
她隔兩天就來給她媽洗一次。她總這樣。
「媳婦是銀錢買的,不親。女兒親。我給我媽洗。我不嫌髒。我媽上輩子遭了
罪。噗,噗。我不埋怨人家徐培蘭。噗,噗。」
她一個人自言自語,一個人抽鼻子流淚。後來,花香從門裡跳出來,叫了她一
聲:
「姑——」
花香叫她姑。
「姑你來了。」花香說。
「我給我媽行孝來了。」她說。
「你看我媽這褲子。」她說。
她把它從鐵盆裡提出來,抖了抖。
「嘎嘎」
她朝花香笑了兩聲。
「嘎嘎嘎嘎……」
她把脖子往外扭,一連笑出來一串。
「姑你知道不?」花香說。
「貓叫春哩。」她說。
「嘎。」
「真真的。」花香說。
「嘎嘎。」
「要出事哩。我看要出事哩。」
花香臉上的神色很嚴重。她一直把嘴湊到羊村姐的耳朵跟前。
「嘎嘎嘎嘎。」
羊村姐笑聲太大,花香嚇了一跳。她看見羊村姐把頭仰到脊背後頭,喉節笑得
一跳一跳。她還看見她用一根手指頭摳耳朵,就是她剛才用嘴對著的那只耳朵。
「就是的。」徐培蘭說。
她們看見徐培蘭從門坎裡走出來。
「媽很興奮。」她說。
「媽蹾了一夜屁股,騰騰響。」
徐培蘭知道花香在跟前站著。她瞄了花香一眼。她看見花香有些慌張,從門裡
溜進去,悄無聲息的。
「嫖客日的。」徐培蘭說。
「又不是我叫春。嫖客日的。」她說。
「呸。」
她朝花香家門口吐了一口。
羊村姐瞪著眼,不知道她們是做什麼。羊村姐這會兒成了一堆軟肉,堆在鐵盆
跟前。她囗蹴的時候就是這種樣子。軟肉裡有個硬疙瘩,眼窩就在硬疙瘩上邊,咕
咯咕嚕轉。
「嫖客日的。我是貓,得是?」徐培蘭說。
後來徐培蘭才知道,那一夜,村裡的女人們都沒睡。她們都支愣著耳朵,聽那
只貓在樹上叫喚。她們慌慌了一夜。她們感到貓叫喚的聲音很熟悉,她們感到好像
不是貓叫喚,是她們自己叫喚。她們說不出是害怕還是難受,就那麼過了一夜。
後來,就死了驢。
五
驢不是驢,是驢驢。驢驢小時候,提個竹籠賣麻花。他和他媽一樣,個子高。
他媽叫高山坎。他叫驢驢,村上人叫他驢。白天,他在街上賣,晚上在飼養室賣。
一夥人在飼養室耍錢。贏錢的人吃麻花,說:「吃鱉熊的。」輸錢的人也吃麻花,
說:「有輸的沒得吃的?吃他媽的個毬。」他們都吃。後來,驢驢媽死了。再後來,
他哥給他從遠地方領了個媳婦。她叫美裡。驢和美裡兩個人過活。
那天,驢給美裡說:
「我種呀。」他扛著耬。
「不下雨你種?」美裡說。
「天一下雨就出來了。」驢說。
「天不下燒死了你種。」美裡說。
「那你說怎麼辦?不種怎麼辦?」驢說。
「天不下我有什麼辦法。」驢說。
驢低著頭。驢是個厚嘴唇,一說話嘴唇呱噠呱噠響。驢一低頭像哭喪一樣。驢
喪氣的樣子讓人可憐。
「你種你種我不管。」美裡說。
驢就種了。他哥搖摟,驢用繩拉。驢沒有牲口。他不願意出錢雇別人的牲口,
所以他用繩拉接。驢使著全身的勁。天氣幹熱幹熱,驢身上冒虛汗。驢看見黃土地
從他的褲襠裡往後溜。驢感到那些黃土像乾枯的玉米葉子一樣,刷著他的眼珠子,
讓他難受。他想把眼睛閉上,他想閉上眼睛就會好受一些,可他不敢。閉上眼怎麼
看地畔子呢?閉上眼怎麼能走直呢?他不敢。
他把兩隻腳摳在地裡,腳趾頭勾起來的黃塵往上飛,鑽進他的鼻孔,鑽進他的
耳朵窟窿,撲在他的牙齒上。雖然天氣乾燥,可驢的嘴還有些濕,上塵撲在牙齒上,
就變成了泥,粘糊在那裡。
「兄弟你甭怕,你看我也使勁哩。」他哥說。他哥搖著耬。
「哥你甭使勁。你一使勁種子就不勻了。你搖你的,哥。」驢說。
美裡給驢和他哥送飯。晚飯在家裡吃。美裡在灶夥窩裡燒火。驢說他餓了,等
不及了。驢把紅薯塞了一肚子。幾天前,美裡蒸了許多紅薯。
「冷了你吃?」美裡張著眼窩。
驢不說話。後來,驢說他累了,想睡。他說睡就睡了。他沒脫衣服就睡了,就
死在炕上了。第二天,美裡扛著鐵耙耙去地裡,她邊走邊給人說:
「驢驢死了。」
沒人信她的話,可她說:
「驢驢死了。」
「那你還去地裡?」有人問她。
「我不管他。他死了連一句話也不給我說。我不管他。」美裡說。
「這熊人。」人們說。
「我不管他。」美裡說。
早飯時候,驢驢家湧了一院子人。幾個年齡大的人在炕跟前,他們把驢驢抬在
床板上。驢驢光著腳,硬梆梆挺著。他尿濕了褲子。人死的時候都要尿一泡,驢驢
也尿了。
「美裡,拿幾件衣服。」有人喊。
他們要給驢驢換幾件乾淨衣服。美裡說在櫃子裡。他們把櫃子打開,抖開了所
有的衣服,都是爛髒的。他們這才知道美裡是個懶婆娘。後來,驢驢他哥拿來幾件
衣服給驢驢穿了。驢驢挺著,任他們擺弄。
「他就那麼睡著,誰知道他死了。」美裡說。
女人們圍著美裡,聽她講驢驢死的事。
「我坐在炕上,挨著驢驢。我說驢驢你聽貓叫春哩,驢驢不說話。我搖他,他
不說話。」美裡說。
「我沒開燈,我搖搖他。貓叫得厲害,像娃娃哭一樣。我害怕,可驢驢不管我。」
美裡說。
「後來我就睡著了。」她說。
美裡一說,女人們都想起了貓叫春的聲音。她們都用眼睛找徐培蘭。徐培蘭在
人夥堆裡,美裡一說貓叫春的事,她就想走。這會兒,她從人夥堆裡往後縮。
「徐培蘭走了。」有人說。
人們都看徐培蘭。徐培蘭已退出門坎了,她不時回頭。她們看見她的腳絆了一
下,就跑起來。
「貓叫春,又不是我叫。」她說。
「我又不是貓呀啊嗚嗚。」
她們聽見徐培蘭哭了。
後來,許多人圍在徐培蘭家門口,叫徐培蘭出來。他們商量好了。
「徐培蘭你出來。」有人喊。
六
徐培蘭在茅房尿尿。她沒尿出幾滴。從驢驢家回來,她就想尿,老想尿,雖然
尿不出幾滴,可她想。茅房在前院的邊上,打了一圈矮牆。那時候,她就蹲在那裡
邊。她聽見有人喊她,聽見來了好多人,就提著褲子,把頭伸過矮牆頭。她看見他
們圍在她家門口,領頭的是蓋子叔。
「徐培蘭你出來。」蓋子叔說。
她能看得出,蓋子叔努力裝出沒什麼事的樣子。
「我不出來。」徐培蘭說。
她站在矮牆裡邊,看著他們。他們臉上冒著氣,汗水從額顱上滲出來,往下淌,
在他們的臉上沖出許多小溝。他們的臉太肮髒了。他們一口一口出氣,她能聽見他
們出氣的聲音。天很熱,所以他們一口一口出氣。
「有話你們說。」徐培蘭說。
「我不出來。」她說。
她看見羊村姐又從大路上滾過來。大路邊上栽著白楊樹,她就從那裡滾過來。
她越滾越慢,後來就停住了,縮在一棵樹背後,朝這邊看。她不知道娘家門口做什
麼圍那麼多人。徐培蘭看見她了。
徐培蘭聽見門坎響。婆子媽也出來了,靠著門框,一臉紅蘿蔔的顏色,腳和胳
膊還那麼不停扭,有時候扭得厲害,就打在門框上,打出「嘭嘭」的響聲。
「都來了。他們是商量好的。」徐培蘭想。
她感到這事很丟人。她眼睛紅不絲絲地看著他們。富士和花香也在人群裡。徐
培蘭瞧不起他們,他們肮髒。是人不是人都來了,所以她感到丟人。她恨不得鑽進
糞堆裡把自己埋了,恨不得跳出去把那些人都捏死。統統捏死。她想把他們的眼珠
子摳出來,讓雞吃了。
「這太丟人了。」她對他們說。
「我知道你們想做什麼。你們對付我一個人。這太丟人了。」她說。
「我不出來。」她說。
徐培蘭提著褲子,她想哭。他們只看見她半截身子,他們能看出她提著褲子。
「你家貓不能叫了。」蓋子叔說。遇到這號事,蓋子叔總出頭露面。
「大家說的。」他說。
「你看大家都來了。」他說。
那些人站在蓋子叔後邊,不停流汗水。
「你們想日鬼我。」徐培蘭說。
「日鬼就日鬼。」蓋子叔說。
「驢死了。你知道驢死了。大家說你家貓不能叫了。」蓋子叔又說了一句。
「驢死了就驢死了。我又不是貓。」徐培蘭說。
「誰知道呢。」蓋子叔說。
「那你說我是貓?」徐培蘭說。
「我沒說你是貓。我說誰知道呢。」蓋子叔說。
「誰知道就誰知道。」徐培蘭說。
「把它勒死。」蓋子叔突然說。
他們都往徐培蘭臉上看。他們一直看著她。他們看見她的眼眶裡好像有兩個核
桃,老大老大。
「勒死。」蓋子叔說。
「你們這些人。」徐培蘭說。
「勒死。」
「你們這些人。嗚嗚。」
徐培蘭哭了。她的嘴能圓能扁。她一哭,嘴就扁了,嘴唇打著抖。
「那你就讓它甭叫。」蓋子叔說。
「我又不是貓。」徐培蘭說。
「幹天火地的。叫它甭叫。」蓋子叔說。
「嗚嗚。」
「眾怒難犯。」蓋子叔說。
「嗚嗚。」
「要不燒你家房子。」
「嗚嗚。」
「說燒就燒。」
蓋子叔朝前走了一步。他看見徐培蘭臉色變了。徐培蘭死死盯著他。突然,徐
培蘭從茅房裡跳出來。他們都看見她跳出來,跳在他們跟前。
「我家有老鼠。」她說。
「大傢伙。我看見了。」她說。
「我家圍裡糧食下得飛快。」她說。
他們讓徐培蘭震住了。徐培蘭的臉色很害怕。蓋子叔不說話,朝徐培蘭眨矇眼。
「我看見了,像牛犢。」徐培蘭說。
那夥人開始來回動彈。徐培蘭看見一些人往外溜。他們互相瞅著,一個跟著一
個,都往外溜。他們心虛了。
「你們小心著。」徐培蘭朝他們喊。
蓋子叔也溜了。他一直眨矇著眼。
院子裡空蕩蕩的,只剩下徐培蘭一個人。到處都是太陽光。有一棵梧桐樹,葉
子啪噠啪噠響。沒風,可它響。婆子媽也溜回去了;
徐培蘭想起羊村姐。她伸著脖子看路邊的那些樹,沒人影。
「驢日的。」她罵了一聲。
「呸。」她吐了一口。
七
花香沒一點心思洗碗。那時候,天已經黑實了。富士吃了一碗開水泡饃,他說
他肚子餓。花香聽見他在廚房案板上掰饃,把碗弄得叮噹響。
「做什麼你?」花香說。
「我餓。我吃開水泡饃。我又沒吃別的什麼。」富士說。
「壺在房子裡你在廚房做什麼你?」她朝著窗子喊。
她聽見富士進來了。富士掰了一碗饃蛋蛋。她給富士倒水,她聽見饃蛋蛋們拼
命吸水的聲音,它們一點一點脹開來。她看見幾滴開水碰出來,濺在富士的手背上。
「噝——」富士叫起來。
富士端著碗,腿一個勁抖。他燙了手,可手裡端著饃碗,所以他抖腿,像兔子
一樣。
「噝——」
花香嚇了一跳。她看著富士的作態,心裡有些憐惜他。她有時候突然的對富士
就有這麼一種憐惜。
「噬——」花香也吸了一口氣。
花香很驚訝的樣子。
富士咽饃的聲音很大。他不嚼,他在嘴裡用舌頭一擺弄就往下嚥。他吃飯很認
真,這會兒也是。花香看著他,花香的嘴唇也動彈。後來,花香給富士說:
「我不想洗碗。」
花香坐在炕上,靠著牆。電燈光有些發白,把她和富士的影子映在牆壁上。富
士脫了鞋,坐在炕沿邊。他的腳有些癢,他用手在腳面上搓。他背對著電燈,所以
臉上有些黑。花香的臉對著電燈。
「放櫃蓋上,我明個洗。我沒一點心思。」花香說。
富士不說話,他一下一下搓腳。他不看花香,他知道花香對著電燈,臉白煞煞。
「這算做什麼。我沒一點心思。」花香說。
就花香一個人的聲音。富士出氣的聲音不算聲音。其實,富士出氣的聲音也很
大。他不停地搓腳。
「電燈太亮。我說電燈太亮。」花香說。
「富士你甭搓腳。」花香說。
花香拉拉被子。後來,他們就進了被窩。
「啪噠。」
他們都聽到了開關的響聲。他們都睜著眼。他們互相知道。
「我家有老鼠。」徐培蘭說。
花香想起徐培蘭了。不知怎麼的,花香就想起了她。
「像牛犢。」徐培蘭說。
「糧食下去飛快。」徐培蘭說。
「小心著。」徐培蘭說。
徐培蘭的眼窩紅不絲絲,想起來有些害怕。花香有些怕。
「老鼠是洞裡的蟲蟲。」花香說。
「龍生龍,鳳生鳳,老鼠兒子會打洞。」富士說。
「它會鑽到咱家來。它鑽到咱囤底下。誰知道。」花香說。
「你聽。」花香突然這麼說。
他們都支愣著耳朵。他們聽見什麼地方真有響聲,像老鼠的聲音。
「富士你去看。」花香說。花香的聲音有些緊張。
「你看你。你這麼說話,晚上了你這麼說話。」富士說。
「你去看。」花香說。
「誰知道是不是。誰知道它在什麼地方。」富士說。
「囤底下。肯定。」
「那你也去。都去。」
因在隔壁房裡。花香穿著短褲。富士什麼也沒穿,他睡覺不穿衣服,他總是把
衣服扒得精光。他們倆爬在囤底下瞅。囤台是土坯砌的,有幾個窟窿。他們就往窟
窿裡邊瞅,一人瞅一會兒。他們沒瞅見什麼,就站起來,互相往臉上瞅。花香的鼻
梁上沾著土。富士的鼻樑上也有。
「你聽。」花香說。
富士的腿抖了一下。他們站在那裡聽。
「日他的。我日他的。」富士說。
他們好長一陣沒說話。後來,富士說:
「花香你甭出聲。我弄些泥堵洞洞。把洞洞全堵住。」
他們整整幹了半夜。花香提著鐵鍁,不停地給富士鏟泥。他們和了一堆泥巴。
他們儘量不弄出聲,夜裡響聲大。花香跟在富士屁股後頭,他們齊齊地搜尋牆根。
牆那邊就是徐培蘭的家。富士用手抓泥巴,往那些洞洞裡塞。他們把一切可疑的洞
洞窟窿縫縫都堵死了。他們感到晚上做活很好,有精神。人想幹什麼的時候,人就
不累。他們不說話,但他們都這麼想。他們濺了一臉泥巴。
「看你臉上的泥。」花香說。
「看你臉。」富士說。
他們互相看著,很激動的樣子。富士想在花香身上捏一把。花香想在富士身上
什麼地方咬一口。人一高興就想好事。他們很高興,就想。後來,他們飛快地上炕,
鑽在被窩裡。當時,他們可沒想什麼晦氣的事。
八
富士抱著花香。富士總要先這麼抱抱她。「怎麼好怎麼來。」人都這麼說。富
士也一樣,他感到這麼好,所以他就先這麼抱抱花香。花香的身上熱烘烘。他聽見
花香出氣越來越粗。花香的身子不停動彈。
他們想好好睡一覺。他們都想。難得有這種好時候,因為他們總鬧彆扭,老不
順心,好心情總碰不在一塊。兩人都想睡的時候才能睡好,這他們知道。這會兒,
他們塞了好大一陣洞洞,心裡很痛快,他們的心思往一塊兒想,他們成了一個人,
所以,他們一個人想那事,另一個也想。
富士騎在花香身上了。燈黑著。窗戶外邊有星星,可還是黑。富士聽見花香在
他的腿底下張著嘴喘氣。他看不見,他能聽見。
「你聽。」花香突然這麼說。
富士愣了,他騎在花香身上愣住了。花香的聲音有些怪。他想起花香白煞煞的
臉,腿一軟,就愣在花香身上。
「有個洞沒塞。」花香說。
「你說的?」富士說。
「好像是。」花香說。
「好像好像。」
「回屋的時候我就想起來了。我想給你說,可我沒說。」花香說。
「那你不說。」
「沒塞。就是沒塞。」花香說。
「看你。看你這個人。」
「塞去。你塞去。」花香說。
「我想不來哪個洞沒塞。」
「你去,你去看。」花香說。
「我不想去。泥都幹了。沒泥了。我想不起來哪個洞。」富士說。
「我記得還有泥。幹了你沒點水,」花香說。她推推富士的胳膊。富士的胳膊
一直在炕上撐著。
「我不想去。」富士說。
「你不想澆水你就往泥上尿些。用不了多少水。」花香說。
「我不想去。我想不來哪個洞。」富士說。
「你聽。」花香說。
他知道花香說的是什麼。他感到他要流淚,喉嚨裡難受。他用手指在那裡捏了
一下。
他們沒弄成事。後來,富士蔫不拉嘰坐在炕沿上。他沒一點勁了。他光著屁股。
花香把頭伸過來,他感到她鼻孔裡的氣打在他大腿上,像羊舌頭一樣舔來舔去。
「我日他媽我!」
富士仰起脖子,沖著屋頂罵了一聲。
「我日徐培蘭她媽我、我、我……」
他們聽見後院雞架上「啪啦啪啦」響了一陣,然後就聽見雞叫聲傳過來。一會
兒,全村的雞叫成了一片。
花香縮了縮身子,縮進被窩。富士也縮了進去。
富士沒睡多大一會兒。他想屙屎,就爬起來。他能吃能做也能屙,他就是這麼
一個人。天有些麻亮。他蹲在茅坑上,聽見康定家院子裡有響動。康定家和他斜對
著屁股住,和徐培蘭家正對屁股。富士聽著有點鬼鬼祟祟,康定家兩口老愛幹些鬼
鬼祟祟的事。富士想看看,很想很想,人有時候就想看別人做些什麼事情。這會兒,
富士就想。
牆角有一根白楊木椽。富士緊好褲子,從椽上爬上去。他一下就看見了他們。
康定兩口子蹲在牆根那裡,康定手裡抓著泥巴。富士明白了,他有些想樂。他這麼
一想,身子就動了一下,蹭在牆頭的虛土上,虛上往下溜。
「涮一」
他聽見虛土往下溜。他看見康定媳婦朝他這裡看。他看見她用腳戳了戳康定的
屁股。康定抬起頭,歪擰著脖子。就這麼,他們六隻眼珠子碰在一塊,互相瞅。他
們都有些不好意思。他們沒說話。富士看見康定和他媳婦溜進他們的房子去了。
後來,康定媳婦給人說,那天晚上她胡做夢,她夢見徐培蘭變成了一隻老鼠,
兩隻眼像兩顆黑豌豆。
「我夢了。」她說。
「我也夢了。」康定說。
「徐培蘭是老鼠。」她說。
「嗯啊。」康定說。
「怪了。」她說。
「怪了。」康定說。
他們坐起來。他們聽見空氣裡有一種聲音,像過電一樣。
「(口營)——(口營)——」就這聲。
「我難受死了。」她說。
「我活不成了。」她說。
「嗚。嗚。」她就這麼哭了。
康定聽見她揉眼睛,她把眼睛揉得「嘭嘭」響。
那天,這誰都知道,村裡人都沒去地裡。他們都躲在家裡拼命地堵洞,塞牆縫。
村裡一滿是濕泥的味道。
九
貓到底逮住了那只老鼠。他們都看見了。他們以為沒治了,可到底逮住了。
「逮住了!」
他們聽見徐培蘭在她家門口失眉吊眼地喊。他們從門坎裡蹦出來,朝她湧過去。
徐培蘭多次給他們講述過事情發生的經過。那天,她站在案板跟前切蘿蔔絲,
刀拐了一下。她感到小拇指頭有些癢癢。她知道她挨刀了,就把小拇指頭放在嘴裡
吸。她不想讓她身上的血流到地上,血是糧食變的!不容易,所以她吸。她把指頭
蛋塞在嘴唇中間,用舌頭尖抵著癢癢的地方。她吸了一口,就感到有個小蟲蟲從那
地方往胳膊裡鑽,往她心裡頭鑽。婆子媽在前房裡折騰,不知是屙了還是尿了,能
聽見窸窸窣窣的聲音。
「我要吃。」婆子媽喊。
「狗日的,我要吃。」
婆子媽喊了這麼兩聲,就不言語了。她總是這麼毫無根由的喊兩聲,像乞求又
像威脅。徐培蘭早熟悉了婆子媽的這種伎倆,徐培蘭不在乎。起初,她聽見她這麼
喊,心裡著實慌了一陣。她怕鄰家聽見。她怕出什麼事。她恨不得抓一把土把婆子
媽的老嘴塞住。她感到婆子媽太惡毒了。
「你做什麼喊呀你。」她說,聽著像埋怨,委實是哀求。
「我要喊!」婆子媽說。她看見徐培蘭受難一樣的臉,就有些幸災樂禍。
「不給你吃了喝了你喊?」徐培蘭說。
「我要喊!」婆子媽說。
徐培蘭捂著臉,爬在櫃蓋上流淚水花花。她感到她完了。她模糊地看見以後的
日子,她感到她不得好過。可竟然過來了,過了許多年。婆子媽用心險惡,卻就那
麼一點伎倆,徐培蘭不怕了,她不在乎婆子媽那一套,她甚至感到婆子媽太可笑。
有時候,她有意日弄婆子媽,讓她上火,讓她那麼喊兩句。她總是上當。徐培蘭感
到這樣很好玩,心裡舒坦。
徐培蘭吸了幾口血,她聽見廚房裡什麼地方有一種響聲。她搜尋了一陣,才知
道是從糧囤底下傳出來的。糧囤在牆角那裡。響聲大得出奇,震得案板上幾個胡蘿
蔔一個勁滾。響聲不往她的耳朵裡鑽,往她頭上爬,刀子一樣刮她的頭皮。她用力
睜眼,把眼睛扯得像兩個口袋,要不是連著什麼,眼珠子就會從口袋裡邊滾出來。
她知道那是什麼響聲。
她的心越跳越快。心跳一厲害,人就有些憋氣。
「啊。」她哼了一聲。
「噢。」又哼了一聲。
她抬著腿,用腳尖勝出廚房,然後,她就像挨了棍一樣,往大門外飛跑。她跳
在大街道上,渾身亂顫。
「逮住了!」她喊。
「逮住了!」她喊。
她的聲音像撕破了一樣。她有些張牙舞爪的樣子,喊一聲,就用力氣縮一下身
子。
「逮住了。」她喊。
他們以為她瘋了,後來他們才知道她沒瘋,因為一會兒,他們就看見那只母貓,
它咬著一堆灰不溜秋的軟東西,從徐培蘭家的門坎底下鑽出來。它看見那麼多人圍
著它,嘴裡發出一陣叫聲。它很憤怒。
「嗚——嗚——」
它圓睜著眼,充滿敵意。
「啊。」他們失聲了。
「噢。」他們都這麼失聲了。
他們閃開一條路。他們看見它擺著頭,想找個縫隙跑出去,所以,他們給它閃
開了一條路。它一聳身子,就竄走了。他們看見它雄健得像一隻狼狗,朝池塘那裡
奔跑。村外有一個池塘,早乾涸了。那裡成了人們倒爐渣扔雞毛蒜皮破鞋底一類東
西的地方。
他們跟過去,他們亢奮了,和母貓一樣亢奮。
「哦,逮住了,哦。」
徐培蘭一個人自言自語。她看見他們朝池塘那裡湧,就跟在他們後頭,一邊走
一邊自言自語。她滿臉風光,激動不已。
她看見羊村姐來了。
「快呀你,姐哎——」她朝她揚胳膊。
「逮住了!」她朝她喊。
她看見羊村姐停一會兒,就滾起來,越滾越快。
十
他們圍在池塘岸上,看著那只母貓。它在池塘裡轉來轉去。它已經不怕他們了,
它有些大模大樣,邁著它的步子,嘴裡咬著那一堆灰不溜秋的軟東西。老鼠已經氣
絕了,四條腿耷拉著,尾巴拖在地上。母貓不時地停下來,摔打那只老鼠。它咬在
老鼠的脖子那裡,咬得很緊,老鼠咧著嘴,牙齒呲在外邊,好像在笑。母貓沒咬爛
它,它渾身於乾淨淨。他們能聽見母貓摔打它的聲音。老鼠一聲不響,任母貓擺佈。
「狗日的。」他們說。
「它不吃。」
「它玩哩,日他的,它和它玩耍哩。」他們說。
後來,母貓不走了。它呲著尖利的牙齒,使勁往老鼠脖子那裡塞,在那裡撕了
一下,然後,他們就聽見母貓的嘴裡發出一陣痛快的吮吸聲。母貓用前爪壓著那只
老鼠。
「它喝血哩。」他們說。
他們很安靜,很耐心,聽著母貓喝血的聲音。
「嗚哇——」母貓叫了一聲。
他們聽見它叫了一聲。母貓抬起頭,朝他們掃了一眼。他們看見它的牙尖上有
一層鮮紅的東西。
「嗚哇——」它叫了一聲。
它吃那只老鼠了。它跳舞一樣在地上蹦著圈子,不時發出「嗚嗚」的叫聲,說
不出是仇恨還是殘忍。他們看得驚心動魄,一會兒發冷,一會兒發熱。有幾個人不
停地用手摳脊背,他們感到脊背那裡癢癢。他們滿臉噴紅。
「啊。」他們說。
「噢。」他們說。
「你聽它狗日的。」他們說。
「咕嘰。咕嘰。」母貓嚼老鼠肉。
「格噌。格噌」母貓嚼老鼠骨頭。
它嚼得很痛快。有滋有味。它的嘴上粘著幾撮老鼠的灰毛。
「啊。」徐培蘭說。
「它真行。」她說。
徐培蘭太激動了。她攥著手,她攥得很緊,紅不絲絲的眼窩裡像放著兩個玻璃
蛋蛋。她感到她身上的肉突突跳。她的臉有些歪,臉色難看。人太激動的時候,臉
就成了這種樣子。
「啊。」她說。
「我都快暈了。」她說。
她情不自禁了。她的聲音有些大。他們都持過頭來看她。就這麼一忽兒,那只
母貓不見了,等他們回過頭來的時候,它不知從哪兒走了。他們看見池塘裡只剩下
一堆老鼠的皮毛。
「啊。」
「噢。」
他們騷動了。他們把徐培蘭圍在當中。
「徐培蘭。」
他們叫她。他們一臉討好的神色。他們不知道說什麼好,就這麼叫她。後來蓋
子叔說:
「配去。給母貓配去。」
蓋子叔雙手插在腰眼那裡。他沒扣紐扣,把布褂掀在後腰上,開著胸膛。
「讓它下兒子。」他說。
徐培蘭真想跳一下。她感到眼窩裡有幾滴眼淚水要往外掉。她吸了吸鼻子,脖
子仰了仰,眼淚水才沒掉下來。
「你看我真高興,我都要哭了。」她說。
她又吸了一下鼻子。
「要配。」蓋子叔說。
「我娘家有個公貓,很威風。」徐培蘭說。
「配去。你配去。不能讓你家母貓幹叫。」蓋子叔說。
「種瓜得瓜,種豆得豆。讓母貓給咱下崽。」他說。
「我真高興。」徐培蘭說。
她拉著羊村姐的手往回走。她們遠遠看見婆子媽站在門框跟前,扭胳膊扭腳,
臉上笑眯眯的樣子。回屋後,她們才知道,婆子媽沒尿也沒屙。
「姐哎你看,怪了。」徐培蘭說。
「嘎。嘎。」羊村姐傻不乎乎笑。
「她沒往炕上屙。她今天沒往炕上屙。」徐培蘭說。
「嘎。那我回呀。嘎嘎。」
羊村姐回了。徐培蘭一直送她到路口。她站在那裡,看著羊村姐走。走了一陣,
她朝她喊了一聲:
「姐哎!」
羊村姐回過頭。
「我真高興。」徐培蘭說。
「嘎。嘎嘎嘎。」
羊村姐掄著胳膊,她真的走了。
「怎麼會死?」
「不是配去麼?怎麼就死了?」
蓋子叔說。
「我倒要看看,怎麼就死了。」
他這麼說,邊走邊說。
十一
他們看見她了。她抱著那只母貓,就像花香說的那樣。太陽直照著她。那時候
是正午,她家門朝南開,她站在門口,所以太陽就直照著她,照在她臉上,黃黃的,
像土那種顏色。
蓋子叔把舌頭在嘴裡攪了好大一會兒。他咽了一口唾沫,沒有說話。本來他要
說話,可他一看見徐培蘭,就沒活了,就咽了一口唾沫。
徐培蘭把貓抱在肚子那裡。他們看見母貓的腿耷拉著,從徐培蘭的胳膊上耷拉
下來,一動不動。貓腿可能硬梆了,所以一動不動。他們看不見貓頭。
「它不叫喚了。」花香說。
花香聲音很輕,她拉了拉富士的手。富士的腳又癢了,不停地在底下蹭腳。他
們站在蓋子叔背後。崽娃子也在。
「死了。」蓋子叔說。
「徐培蘭心裡難過不?」花香說。
「看你說的。」蓋子叔說。
「我心裡覺著它沒死。」花香說。
「人有時候就是這麼的,死了,你想著沒死,人有時候就這麼的。」蓋子叔說。
「說不定沒死。」花香說。
「看你說的。」蓋子叔說。
「說不定它從徐培蘭胳膊上跳下來。」花香說。她又掐了一下富士的手。
「看你說這話。」蓋子叔說。
「說不定徐培蘭想唬弄咱哩。」花香說。
「甭說。徐培蘭聽見了。」
他們說這些話的時候,一個不看一個,他們都看著徐培蘭。他們離她還有一些
距離。他們就嘴動彈,什麼都不動。
他們看見徐培蘭紅絲絲的眼窩裡有淚水花花。後來,他們看見她朝池塘那裡走。
幾天以前,母貓在那裡吃老鼠,他們想起來就激動,他們都記得。
「啊——」當時,他們都失聲了:
「噢。」他們都這麼失聲了。
「狗日的。」他們說。母貓讓他們心情亢奮。
「嗚哇——」母貓咬著老鼠,它這麼叫喚。
「它真行。」徐培蘭給人說。
「我真高興。」她說。
「我真他娘的高興。」
當時,他們和她一樣,真他娘的高興。
他們都記得清清楚楚。
「哦啊!」
花香叫喚了一聲,她把富士的手捏疼了,像掐了一下一樣。
他們遠遠看見徐培蘭站在池塘岸邊。就是他們看母貓吃老鼠的地方,徐培蘭甩
開胳膊一搶,他們就看見那只母貓從她的手裡飛出去、撲了一下,在高空裡劃了一
個圓弧,落下去,然後,他們就聽見一聲悶響。
「嘭。」就這麼一聲。
花香就叫喚了一聲。
就什麼也聽不見了。
他們能想出徐培蘭的模樣。她的眼紅不絲絲的。他們也能想出那只母貓,它四
蹄伸開,花肚子亮在光天裡。死貓都是那一種樣子。它躺在爐渣堆裡,那裡還有一
些雞毛蒜皮臭鞋底子一類的東西。天還那麼熱。過一段日子,母貓就會腐爛,發出
一股惡臭味。再過一段日子,它就幹了,剩下一個乾巴巴的皮囊。
「日他的。」蓋子叔說。
「這熊天氣。」他說。他們都把頭仰著,朝天上看。富士的腳不癢了。花香聽
見他把腳往鞋窩裡塞。
那天晚上,徐培蘭睡得很早。她聽見婆子媽又在前房裡屙。她心裡一陣噁心,
就上了炕,拉開被子。照順爬在櫃蓋上寫作業。照順每天晚上都寫作業。她把被子
擁在脖子那裡,看著照順的後腦勺。
「我要吃!」婆子媽在前房裡叫喚。她越叫越凶。
「你聽著,我肚子餓了。」
她不一次喊完她的話,她一句一句喊。徐培蘭小聲給照順說:
「照順你說饃在廚房裡,你給她說。」
「饃在廚房裡。」照順朝外喊了一聲。
她聽見婆子媽進了廚房,裡邊稀裡嘩啦一陣響。一會兒,她聽到婆子媽爬在她
的窗子外頭。
「我不吃我鱉。我不吃我讓你和你娃好過?」婆子媽朝她吼,震得富紙響。
「吃死你,憋死你,整死人了你。」徐培蘭小聲說。
有兩滴眼淚水從徐培蘭的眼窩裡掉出來,順著胭脂骨那裡往下滾,灌進她的耳
朵。
十二
花香和富士也睡得很早。本來他們不想早睡。花香給富士說:
「聽聽,你去後牆上聽聽。」
富士順著那根木橡爬上去,要不是他看見康定家兩口站在牆根底下,他就不會
睡那麼早,可他看見了。他趕緊溜下來。
「日他的,晦氣。」他說。
「怎麼啦怎麼啦你?」花香說。
「日他的康定。」他說。
「怎麼啦康定?」花香說。
「像狗一樣,在牆根底下聽。他們也聽哩。」富士說。
他們都很晦氣,他們聽不成了。他們不知道徐培蘭家裡有什麼事。電燈明光光
的。
「睡。日他的睡。」富士說。
他們在被窩裡,他們身上都熱乎乎的。他們在被窩裡說話。
「母貓死了真不好。」花香說。
「死了就死了,沒什麼好不好。」富士說。
「你說徐培蘭睡了沒?」花香說。
「我又不是徐培蘭。」富士說。
「看你這人。老他媽的不下雨。」花香說。
富士不說話,睜眼看著屋頂。
「你說會不會下?」花香說。
「我又不是老天爺。」富士說。
「地還沒收拾好。」花香說。
「噢麼。」富士說。
富士這麼一說,就想起了煥彩。他只想了一下。
「軟的。」他想。
那時候,花香睡著了,聽她出氣的聲音,就知道她睡著了。富士往花香跟前蹭
蹭。他扳花香的腿。花香睡覺老蜷著腿。
「軟的。」他想。
他到底把花香扳平順了。他感到花香睜了一下眼。後來,他就騎上去,他鼻子
裡的氣打在花香脖子那裡。花香不動彈。
「煥彩。」他想。
他出了一身汗,渾身的骨頭像松了一樣。好長一段日子,他都冷不丁想起這個
夜晚,他問花香,花香說她不記得那事。
「我睡著了。」她說。
「我夢見下雨,真真的。是霖雨。」花香這麼說。
第二天,富士去地裡,他看見煥彩家地畔上圍了好多人。晚上,煥彩偷了人家
的牛。煥彩睡不著就來了氣。她心裡發急。人發急的時候就睡不著覺,越想越睡不
著。
「我日他媽。」她說。
她穿好衣服,摸到鄰村一戶人家裡,把人家的牛偷出來。她想用人家的牛犁地。
「丟人顯眼!」
富士聽他們罵煥彩。他們來了一夥人,把煥彩圖在當中。
「我又沒犁地。你看我沒犁,雖然我偷了牛,我不會犁地。」煥彩說。
「髒。」他們說。
「我不會套牛。我偷了,可我不會套牛。我原以為我會。」煥彩說。
「賊樣。」他們說。
「就算我偷了,可我沒犁地。」煥彩說。
那夥人商量了一會兒,他們就在煥彩家地裡來回跑,跑得塵土飛揚。他們要把
煥彩的地踏硬。他們這麼懲罰她。他們從路溝裡撿來許多碎石頭瓦塊,往煥彩的地
裡扔。煥彩站在一邊看著他們扔。後來,他們走了,煥彩就在地里拉那些瓦塊和石
頭。
人們都下地了。田野上亂散著他們的影影。他們不時地往天上看。到處都能聞
到幹土的味道和牛糞的味道。
「哦。哦。」
富士吆喝那頭牛。他把鞋脫在地頭上,光著腳。他心裡又長毛了。他要把剩下
的那一點地犁完。花香蹲在地頭那裡,朝天上看。就一個太陽,天上什麼也沒有,
也沒有太陽光。太陽把它的光都灑在地上了,就那種黃不拉嘰的太陽光。
「哦。哦。」
那是富士吆牛的聲音。
十三
後來,下了一場雨。
他們像瘋了一樣,往地裡塞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