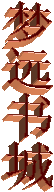
楊爭光 黑風景
一
事情開始的時候很簡單。其實後來發生的一切也很簡單。那天,種瓜人站在瓜
棚跟前朝瓜地裡看了一眼。太陽總是從東邊出來,然後從西邊落下去。西瓜又長大
了一些。沒有什麼東西能讓人激動或者不安。就這麼,他朝瓜地裡看了一眼。然後,
太陽就旺了。然後,他在地畔上找了塊地方,躺下去。
瓜地在峁上。一條土路像褲帶一樣搖晃著從兩邊搭下去。峁是掛那條褲帶的架
子。再就是西瓜。瓜棚邊的土坑裡有一些啃過的瓜皮。在這種地方,竟然長出來這
麼一片西瓜,讓人感到有些滑稽。西瓜確實豐收了,它們排列在那裡,不動聲色。
遠處,依然是那種溝壑梁峁一類的東西,直往人眼窩裡蹭,乾巴巴像塞滿了土。
那裡有一道楞坎。他剛好把頭枕在得坎上,臉上蓋著一頂草帽。他沒有睡著。
他感到小腿上有個什麼東西。他把腿抬起來。很熟練地在那裡搧了一巴掌。他立刻
感到一陣粘糊,很得意。
那是一隻飛蟲。
後未,他就聽見了一陣牲口走路的聲音。它們踩著那條褲帶悠然地往上爬著。
他突然產生了一種想吼一句什麼的欲望。
「來了,來了,又來了……」
他這麼唱了一句。他順著帽沿朝路上看了一眼,一群販牲口的人已停在地頭了。
那是一群面目肮髒的男人。他們穿著那種少顏無色的長腰寬腿褲子,紮一條線褲帶。
他們進了瓜地,貓著腰,挨個兒在西瓜上摸著,像摸著一樣可心的東西。
他聽見他們摸過來了。他沒看他們,他用耳朵聽著。一會兒,他感到一隻手摸
上了他的草帽。
「切個瓜吃。」
摸他的是一個長著茬茬鬍子的人。
種瓜人沒說話,也沒動,茬茬鬍子揭掉他臉上的草帽。陽光猛烈地刺進他的眼
窩。
「切個瓜吃。」茬茬鬍子說。
種瓜人依然未動。他正對付著猛烈的太陽光。茬茬鬍子把草帽放在屁股底下,
在他的頭跟前坐下來。
種瓜人聽見一聲西瓜破裂的響聲。
瓜地裡響起一陣西瓜破裂的響聲。
種瓜人斜著眼。他看見幾個牲口販子砸著西瓜吃,他們吃得很高興。種瓜人想
閉上眼,但又睜開了。他看見他們砸著西瓜耍鬧,看著看著,種瓜人變臉了,氣粗
了。他甚至誇張地吹了幾口氣。
又一聲西瓜破裂的響聲。
「這夥熊人。」他說。
他突然坐起來。
「甭砸!」他說。他鼓著全身的力氣,使勁搖著頭。
「甭砸!」他這麼說。
「給你錢。讓他們砸去。」茬茬鬍子說。他大口大口地啃著西瓜。
「甭砸!」種瓜人又喊了一聲。他好像很固執。他好像喊給自己聽一樣。他仍
然坐著。
牲口販子們愣了一會兒。
「我說甭砸!」種瓜人說。
瓜地裡響起一陣更激烈的破裂聲。
種瓜人看見一個販子抱著一個大西瓜,朝那個蹲著吃瓜的光頭頭上砸了下去。
西瓜砰然破裂。光頭上滿是破碎的瓜瓤。光頭動了動,依然吃瓜。
「甭砸!」種瓜人說。
那個販子並不理會。他把半個西瓜朝那顆光腦袋扣了下去。他感到他的喉嚨裡
很快就會顫抖出一陣笑聲。他沒笑,因為他感到有些不對勁。他扭過頭,種瓜人已
到他跟前了。他把那一陣笑聲給了種瓜人。他笑得很憨厚。
「我說甭砸!」種瓜人聲音小了,但語氣很硬。
販子又笑了一聲。販子笑得依然憨厚。
種瓜人突然掄起了切瓜刀。那是一把彎月形的切瓜刀。那一聲和西瓜破裂的聲
音很相像。這回,販子沒笑出聲,他使勁扭著身子,倒了,臉上浮著那種憨厚的笑
容。
販子們圍過來,他們看著挨了刀的同夥,然後瞅著種瓜人。
「你這熊人。」其中的一個說。
「我說甭砸,他要砸!」種瓜人說。
「你的瓜不賣錢得是?」
「不賣錢做甚?」
「那你殺人。」
「我說甭砸,他要砸!」種瓜人不明白販子說什麼,他眨矇著眼。他想,瓜賣
錢當然瓜要賣錢,可他做什麼要砸。
光頭上滿是碎瓜瓤的那位湊過臉來,仔細端詳著種瓜人的老瞼。他是個矮壯的
男人。
「你狗識的殺人。」光頭說。
「他砸西瓜。」種瓜人說。
光頭抓住種瓜人的一隻手往背後擰,一直擰到他發出一聲痛苦的喊叫。然後,
光頭把種瓜人的兩條腿扳上來,往鼻尖上折。種瓜人躺在地上,並不反抗,眼珠子
定定地看著他的兩隻腳,一點一點朝他的鼻子折了過來。
「這老熊筋還軟。」販子們說。
「就是。」
他們終於聽見了骨頭挫裂的梆梆聲。種瓜人又發出了那種痛苦的喊叫。就這麼,
他們擺弄著種瓜人。他們擺弄得很仔細,很認真。他們像做一件平常的事情一樣做
著這一切。後來,他們從瓜棚上取下來一條麻繩,拴在種瓜人的腳脖子上。他們把
他倒吊在椽上,用他的頭夯著鬆軟的土。再後來,他們把他的頭裝在褲襠裡,種瓜
人也穿著那種褪色的藍布大襠褲。他們到底把他弄成了一個圓球,吊了起來,吊在
了瓜棚上的木椽上。光頭一下一下拉著麻繩,圓球打著旋兒往上升著。
「狗識的還殺人,讓你殺,拿三千塊大洋來。送個沒開苞的女人來。七天不見
人影,就把村子洗了。」光頭說。
村子在溝坡底下,像隨便扔在那裡的一堆溫暖的舊衣服。
販子們把挨了刀的同夥搭在牲口背上走了。
他們是一群販牲口的土匪。
那時候,吊在瓜棚上的種瓜人像一件東西,悠悠晃動著。瓜地裡,有幾個西瓜
被豎了起來,在陽光裡閃著油光。
二
六姥是村裡最有魅力的女人,六姥家上房廳裡聚集著一群表情淡漠的男人。他
們在這裡商量著一件重大的事情。他們蹲著,坐著,靠著牆壁。他們聽著酸菜缸上
蒼蠅振翅的聲音。那裡排列著幾口大菜缸。
六姥靠著門框,手裡拿著半截紅蘿蔔。她是個愛吃紅蘿蔔的老女人。她形容枯
槁,一臉者皮,但牙齒很好。燈光從屋裡射出來,抹亮了六姥的半個瘦臉。另一盞
燈放在菜缸的缸蓋上。
他們剛剛吃完晚飯。他們的腳跟前放著一碟酸菜。有人伸長舌頭,努力地舔著
碗裡的飯粒,舌頭在瓷碗上拉出一陣悅耳的響聲。
「這麼大一個村子,找不出一個合適的,我不信。」有人說。
「拴牢。」有人喊了一聲。
拴牢抬眼盯了喊他的那人一眼。
「我家女子才十二歲,虧你說得出。」拴牢說。
「那你說誰家的女子合適?」
「我看存道家月桂合適。」拴牢說。
眾人都把目光放在了存道的腦頂上。
存道半晌沒說話。存道似乎觸到了傷心處。存道難受得什麼似的。存道說:
「事到如今,我也不護衛了。我家月桂跟人睡過了。就是那個補鍋的。他在我
家住了幾天,就出了丟人事。他把村上的爛鍋補好了,他把我家月桂睡成了爛女人。
我家月桂的肚子大了,不信到我家看去。他走的時候,沒給我家要補鍋錢。他不聲
不響就走了。他個狗識下的。不信到我家看去。」
存道泣不成聲了。
六姥不說話。她一直嚼著手裡的那半截紅蘿蔔。
「來米她爹。」一個年輕一點的戶主喊了一聲。他叫德盛。
他們把頭扭向牆角。來米她爹像沒聽見一樣。他沒有抬頭。
「你家來米合適。」德盛說。
「來米她爹你自己說。」
來米她爹一動不動。
他們看六姥了。他們的意思很明白:我們把合適的人選出來了,可人家來米她
爹不吭聲。
六姥眯縫著眼。她好像在笑一樣,其實她就這麼一副像笑一樣的模樣。她停止
了咀嚼,嘴巴不動了。她合往嘴唇的時候,嘴巴就像一朵枯萎的花。
「來米合適」有人說。
「讓六姥說。」有人說。
缸蓋上的蒼蠅們激動地振著翅膀。
來米她爹揚起頭,看著德盛。他看了好大一會兒。他突然站了起來。
「德盛。」他叫了一聲。
德盛狐疑地看著來米她爹的臉。
「我操你女人!」來米她爹說。
「我操你家女人!」他說。
他撥開人堆,從牆角裡走出來,走進了院子,朝大門口走去。半道上,又折過
身來。
「我操你女人!」他似乎跳了一下。
他們一直看著他出了大門。他拖著鞋,鞋底打著腳板,啪嗒啪嗒作響。
有人醒過神來,急急地跟了出去。
「甭走,哎,看這人,哎……」
一隻貓從門坎上竄出來,六姥一伸手,熟練地抓住它,朝屋裡的土炕上扔過去。
貓發出一聲尖厲的叫喚。
六姥嚼紅蘿蔔的聲音很響。
那時候,月光很亮。峁頂上,種瓜人吊在瓜棚的木橡上,像一樣東西。滿地的
西瓜像一個又一個活物,怪綠怪綠的。
遠處是山包子。還是山包子。
三
挑客憋娃背靠著碌碡,囗蹴在仁義家門口。他的脖子邊上插著一根小竹棍,竹
棍上拴著兩條紅布,這是他的職業標誌。他爹死的時候莊重地指著那根小竹棍說,
憋娃你甭小看那條紅布布,它是你吃飯的碗。憋娃就朝小竹棍看了一眼。他爹又跟
憋娃說,憋娃你把小竹棍插在脖子上,你就成了挑客,就有人求你高接遠送好吃好
待。憋娃給他爹點了點頭。憋娃爹從炕角裡取出一個油光閃亮的挑刀盒,把它塞進
了憋娃的裹肚兜裡。他爹說憋娃你下刀的時候手要狠,要用力氣,甭怕豬叫喚豬蹬,
甭怕血。憋娃又點點頭。後來,憋娃成了挑豬閉蛋的能手。
現在,挑客憋娃囗蹴在仁義家的門口。夾在他指頭上的煙捲已抽過一半了。仁
義家的院子裡傳出來了一陣淒厲的豬叫聲。
仁義兩手攥著一頭小豬的四條腿,從門裡碎步跑了出來。
「哪兒?在哪兒挑?」仁義說。
憋娃用腳尖在地上點點。「就這。」他說。他從掛在褲腰上的那個盒子裡抽出
一把鋒利的挑豬刀。他用膝蓋壓住小豬的後腿根,仁義揪著豬耳朵。豬拚命地掙扎
著。
「壓住頭。」憋娃說。
仁義看著憋娃的臉,他感到憋娃太有些不近情理了。挑豬就挑豬,用那麼大勁
做什麼?
「看你說的。壓住壓住,不是你家的豬得是?你輕點。」他看著憋娃的手。
憋娃不理他。他用挑豬刀在豬肚子上剔毛。那裡很快露出了一塊白皮。他在那
裡劃了一刀,豬皮裂開了一道白口,他又劃了一刀,豬皮透了。他把挑豬的刀咬在
嘴裡,然後把一根手指頭從刀口裡塞進去,在豬肚子裡揣摸著,另一隻手取下挑豬
刀,把帶勾的一頭順著那根血指頭塞進去,勾出來一團血肉模糊的東西。他掉過刀,
噌一聲,那團血肉就滑進了他的手心。他一甩手,那團血肉就飛上了街道。一隻狗
跑過來,舌頭一卷,那團沾滿泥土的血肉就進了狗嘴。狗牙之間發出一種咀嚼的響
聲。
「你割的口子太大了。」仁義說。
憋娃用針縫著那道口子。繩子穿過豬皮時也有一種響聲。
「我說你割的口子太大了。」仁義說,「這麼小個豬,你割那麼大口子。不是
你家的豬你不害心疼得是?」
憋娃看了仁義一眼。
「我看五個銅錢就行了,你還要七個。你割那麼大的口子。」仁義說。
「梆」一聲,憋娃把縫好的線割斷了。他站了起來。
「我不要錢了。」憋娃說。
仁義的眼珠子不動了。豬亂蹬著腿,他有些抓不住了。
「看你。你看你。」仁義說,「大了就大了,我就說說。你看你。」
「八個銅錢。」憋娃說。
「看你。」仁義要哭了一樣。
「八個。」
「看你,說好的七個。」
「八個。」
「八個就八個。」
「掏錢。」憋娃說。
「看你,我這麼大歲數還訛你。八個就八個。」仁義說。他從口袋裡摸出一把
銅錢。「看你,我能挑得起豬出不起錢?你把我看成什麼人了。」他說。
憋娃重新縫好了刀口。他們放開了那頭小豬。
「你挑淨了沒?」仁義突然說。
憋娃往盒子裡裝著挑豬刀和針線。
「沒挑淨讓你賠。」仁義說。
「呸!」憋娃給仁義的臉上吐了一口。他吐得很准。他走了。
仁義看著憋娃的背影,半晌沒回過神來。
「這熊人。」他說。
他拽過袖子,擦掉了臉上的髒物。他想起了那頭小豬。
「嘮嘮嘮嘮……」他叫喚著。
豬已跑得沒影了。他看見拴牢敲著鼓從街那頭走過來。
「籌糧了——」拴牢喊著。
人們扛著裝滿糧食的口袋從門裡走出來,朝來米家走去。一群踢瓦塊玩耍的娃
們哄鬧著,跟在大人們的屁股後邊跑。
四
來米家的院子裡堆滿了糧食口袋。人們蹲在自己的口袋跟前。口袋上寫著他們
的姓氏。他們不說話。他們已做出了明智的抉擇。他們愛糧食,可更想活下去。好
死不如賴活著,他們總這麼說。他們抽著旱煙。他們不時地把煙鍋嘴上的涎水吸進
肚子。他們豎著耳朵,等待廂房屋裡的來米她爹開口說話。
又有幾個人扛著糧食口袋從門裡走進來。那時候,來米坐在上房門口的臺階上
摘辣椒。她是那種單眼皮的姑娘。她身體很好。她似乎對她家院子裡發生的事情漠
不關心。她甚至大大方方地走進豬圈,在裡邊撒出一陣無拘無束的尿水聲,然後又
進行了一種痛苦而幸福的努力。她屙了一泡。她一邊緊著褲帶,一邊聽著那頭豬吞
食排泄物發出的暢快的聲響。她滿面紅光地走過院子裡的糧食口袋,坐在臺階上,
拿起了一串辣椒。
「來米她爹說話了沒有?」有人說。
「沒。沒呢。」
「他狗日的嫌少。」德盛說。他也蹲在一個糧食口袋跟前。
他們朝廂房裡看一眼。
廂房屋裡像死了人一樣,讓人透不過氣來。他們等待得太久了。他們仍然在等
待。他們有足夠的耐心。他們看著屋頂上的木椽,看著櫃蓋上的木紋。他們偶爾往
來米她爹的臉上瞄一眼。他們給他已說過很多話了。現在他們不吭聲。
來米她爹的一條腿伸在炕沿上,另一條腿吊著。他正編著一條線褲帶,他腰上
的那一條不太管用了。他想他在這時候編一條褲帶是很快活的事情。褲帶的一頭在
他的手裡,另一頭纏在他的腳趾頭上。他的表現是所有人中最自在的。他們在求他,
哎嗨!他背靠著牆壁。他一抬頭就可以從窗戶看到院子,但他不看。他編得很專心。
他好像胸有成竹一樣。人可不是什麼時候都能這麼胸有成竹。
院子裡的糧口袋越來越多。幾個娃們在口袋叢裡竄來竄去,拍打著數數:「十
七,十八,十九,二十……」另一夥娃們做著「打樁」的遊戲。
來米她爹真是來米她爹。他繼續編著線褲帶,似乎要編出世界上最光彩最氣派
足以讓他一輩子臉上生輝的一條來。能聽見空氣流動的聲音。屋裡的人都盯著他。
一種近似於憤怒的東西正在他們的身子裡爬動著。他們恨不得咬他一口。他們恨不
得奪過他手裡的那條褲帶,把它扔在豬圈裡,塞進屎尿裡。
德盛從門口擠進來,討好地湊到來米她爹耳朵跟前。
「你看行不?行不行你說句話。」他說。
來米她爹仍然編著他的褲帶。
「拿去。再拿去。把圍底騰了。」德盛站在門口給院子裡的人說。
「他想勒死村上人。」有人憤怒了。
「不給了。讓土匪來吊死算了。」
「看你說的,我可不想吊死。」另一個說。
「走,拿去。」
來米看了他們一眼。她摘好的辣椒已兩大堆了,一堆鮮紅,一堆墨綠。她把一
根紅辣椒放在鼻子底下喚著。她咬了一口。她禁不住辣椒猛烈的刺激,張大口哈著
氣,眼窩裡立刻湧出了淚水花花。有人扭頭看了來米一眼。
「給她嘴裡塞個驢毬才好。」他們說。
來米沒聽見。也許她聽見了。她張著口。
「你看嘛,你朝外邊看一眼。」拴牢給來米她爹說。
有人把盛著糜穀的鬥和升子一類的東西也擺在了院子裡。還有人拿來了幾籃子
雞蛋。
廂房屋裡的空氣已很緊張了。
「時辰到了。」來米她爹想。
他想往窗外看一眼。他把目光停在了門口。六姥不知什麼時候來了。她靠在門
框上。他們又聽到了那種嚼紅蘿蔔的聲音。
「啊哈!」來米她爹突然大動悲聲,嚎啕起來。
「我對不起她媽呀……她媽死得早呀嗎啊啊……到了陰曹地府給她媽咋說呀嗎……」
他淚流滿面了。
六姥走了。
人們大大松了一口氣。他們一個一個相跟著出了來米家的大門。
「啊,啊,啊……」來米她爹還在廂房嚎啕著。
來米愣愣地看著院子裡的那些糧食口袋。後來,她整了整衣服,在臺階上坐好,
坐成女人哭墳的那種姿勢,然後,嘴巴一張,就哭出一長串聲來:
「哎嗨嗨嗨嗨媽呀,你把我嗆——」
她拖著腔。那是一種真正的歌哭,抑揚頓挫,暗合陰陽,說不出是歡樂還是悲
痛。那是一種敘述式的詠歎,把敘事和抒情完美地結合在一起。她吸了兩口氣,對
著滿院的糧食口袋繼續歌哭。她吸氣的時候,喉嚨裡也有一種聲音。
「你把我……」
來米的歌哭在空氣裡顫動著。
五
仁義和他婆娘拌了一天嘴。仁義婆娘讓仁義送糧,仁義不送。
「我不出糧。」他說。
他婆娘斜了他一眼。他婆娘是個肥胖的女人,粗腿大屁股,胸脯上嘟嚕嚕一堆
肥肉,看著讓人眼饞。
「都出哩你不出,你能的。」女人說。
「我就能的。」仁義說。
「你不出糧就得去騾馬寨子,土匪不殺了你才怪。」女人說。
「我不出糧,我也不去騾馬寨子,我管毬他。」仁義說。
「能麼。你能麼。」女人說。
「噢麼。」仁義說。
「村上就出了你這麼個能豆豆。」女人說。
「我沒糧。」仁義說。
「我把糧都裝好了。」
仁義的眼窩張大了一點。他看見牆角蹲著一個裝滿糧食的口袋。他擰過頭,往
婆娘的臉上瞅。婆娘太日髒了。
「日你媽。」仁義說。
女人張了一下嘴。
「做什麼你裝糧?」
女人仍然張著嘴。仁義朝她走過來,揪住了她的頭髮。她知道仁義要接她了。
仁義總這麼接她。仁義揪著她的頭髮,使勁一拉,她的臉就仰起來,對著屋頂。她
的眼珠子鑽進了額顱裡,眼眶裡剩下兩窩白東西。她的身子朝後彎著,肚子腆起來,
胸脯上的那兩堆肥肉鼓鼓的要繃出來。可仁義不動這些地方。仁義把另一隻手順著
她的肚子往下塞,一直塞進她的大腿間。仁義的五根指頭一抓,就會抓住一把肥肉。
然後,仁義就往手指頭上使勁。然後,女人就感到了一種鑽心的滋味,說不出是疼
痛還是興奮,眼眶和鼻眼裡就湧出來一股酸水。女人就淋漓地叫喚一聲,露出兩排
肮髒的牙齒。
這會兒,仁義就這麼抓著女人大腿上的一塊肉,往指頭上使著勁。
「日你媽。」仁義說。仁義狠著臉。
女人齜著牙,正忍受著那種鑽心的滋味。
「你把糧食給我倒到圍裡去。」仁義說。
「我不。」女人說。
仁義又使了使勁。女人叫喚了一聲。「我不。」女人說。
「倒不倒?」仁義說。
「倒。」女人說。
仁義鬆開手。女人摸著大腿上那塊肉,呻吟了幾聲。仁義看著女人把糧食倒進
了圍裡。
「他們會讓你去騾馬寨子。」女人說。
「誰敢讓我去?吃了豹子膽!」仁義說。
「看麼。」女人說。
「看麼就看麼。我管毬他。」仁義說。
「我不出糧,我也不去騾馬寨子。」他說。
後來,他們就聽見了來米的歌哭。他們靜靜地聽著,都有一種想尿尿的感覺。
「我管毬他。」仁義說。他看著屋頂上的木橡。
六
來米一直哭到了天黑。來米沒挪地方,還坐在白天欲哭的那地方,還是那個姿
勢。她的單眼皮有些腫脹。
院子裡的糧食口袋已少了許多。來米她爹把它們騰空了,倒進了囤裡。圍裡的
糧食已冒尖了。他把倒空的口袋從屋裡扔出來。他給門外邊扔了一堆空口袋。
「甭難過了。」他給來米說。
「是女人總要找男人。」他說。他要開導開導來米。
「這窮熊地方有好男人?你說。你見過?土匪也是人,也是吃五穀雜糧的。土
匪就不娶老婆了?」
「土匪吃人哩得是?土匪是吃人哩,看吃誰哩。你好好地順著他,他吃你?不
就是讓你給他當老婆嘛,是不是?你說是不是?」
他又扔出來一條空口袋。他總是拖著鞋。他從來米跟前走過去。
「讓你幫個手你不幫。」他說。他又抱起一袋糧食。「不幫就不幫,緊你爹我
一個人往死裡累。你的心就這麼硬?真是,女人的心比石頭還硬。你媽的心就跟石
頭一樣。我說你不能死你得活著,你死了讓我和來米咋辦,她眼睛一閉腿一蹬就死
了。心比石頭還硬哩。」
他又站在困臺上了。
「這不比種地強?這不叫種糧食,也不叫收糧食。這是往圍裡倒糧食。你長這
麼大啥時候有這麼多糧食。這是糧食我說娃喲,不是土,也不是牛糞。你悄悄地坐
著,你爹我把什麼都想到了。你爹我能讓你吃虧?你說。你想和他過了你就和他過,
不想過活了你再回來,他強扭你不成?人心是能強扭的?扭了一月扭不了一年,扭
了一年扭不了兩年,強扭的瓜不甜。土匪也不是吃草屙料的,他不知道?你看這糧
食。你回來了咱坐在家裡慢慢吃。吃這東西不會壞肚子。你看你看,給你說你還不
愛聽。看你難受的樣,好像你把糧食給人家了一樣,哎嗨。」
來米抬起屁股,進了另一間屋。來米她爹歪著脖子,看著來米關上了門。
「模樣,看你那模樣。」來米她爹說。
來米吹滅了屋裡的燈。院子裡滿是月亮光。來米她爹背著手,在月亮光裡踩踏
著,似乎在試試能不能把月亮光踩碎。後來,他豎著耳朵聽了一會兒。來米的屋裡
沒有聲響。他躡足走過去,掛上了門栓,又從身上摸出來一把鎖子,鎖上了門。
「來米你睡。」他對著門扇說。「好好養養神,村上選好人,你們要上遠路呢。
睡,你睡。」
「我也睡,」他說,「剩下的活我明天做。我這人活了一輩子,一輩子是個閑
不住。」
來米她爹進了那間廂房屋。他一眼就看見了白天編好的那條線褲帶。他抽掉了
褲腰上那條;日的,把它從門裡扔了出去。布條正好搭在豬的木欄上,搖來擺去。
他一口氣吹滅了燈。
院子裡只有月亮光了。像鋪了一層水。沒顧上倒的幾個糧食口袋浸泡在清水一
樣的月亮光裡。不知什麼地方傳來幾聲夜鳥的叫聲,直往人頭皮裡鑽。
來米她爹挪挪脖子底下的枕磚,睡了。
七
拴牢又敲鼓了。鼓聲不緊不慢,像報喪一樣,給人一種不祥的預感。
全村的人都聚集在六姥家門前。他們堅七豎八歪擰在那裡。他們總是一臉晦氣。
那裡有幾棵樹,還有一個草垛,一堆糞土。幾隻雞不避人,在草垛和糞堆跟前扒食,
雞爪不時揮動,彈蹦著士粒和碎草。一隻豬在街道的路溝裡拱土,也許就是仁義家
挑過的那只小豬。
門前的木桌上白花花放著幾錠銀洋,還有一隻女人用的針線籃子。這會兒,那
裡放著許多麻紙團。
那時候是正午,太陽光裡有種揉斷乾草一樣的響聲,讓人心裡直發毛。
六姥坐在門坎上,眯縫著眼。她沒吃紅蘿蔔,她抱著膝蓋骨。
沒人往木桌上看。他們不知道在看什麼,也許什麼都沒看。他們的眼窩像核桃
砸出來的兩個圓坑。
有人咳嗽了一聲,從人堆裡站起來。
是拴牢。
「仁義。」他叫了一聲。
仁義沒動。他翻了拴牢一眼。
「你沒出糧,得是?」拴牢說。
「我沒糧。」仁義說。
拴牢把頭轉向眾人。
「仁義沒穀子,也沒豆子,也沒錢,幹蘸油葫蘆不成。送來米他去。」拴牢說。
仁義慌失了。
「我不去,我腿不好。」他說。
「不去不行,」拴牢說,「有錢出錢,有力出力,這是老規矩。」
「仁義你站過去!」拴牢說。
人們都看著仁義。仁義不敢不站過去,他一邊斜著身子一邊給拴牢說:
「我不去,咋說我也不去。」
拴牢向大家宣佈:「還得一個人,沒人願意去,咱就抓鬮。」
「不准挑挑撿撿,手指頭蛋碰到哪個就拿哪個。」
「我不抓。」來米她爹從人堆裡走出來。他很有些自得的樣子。他走到六姥跟
前,挨著六姥囗蹴下去。
「抓就抓。」
人們紛紛站起來,朝木桌擁過去。
「一個挨著一個。」拴牢說。
人們就排好隊,一個挨著一個。
仁義蹲在桌子旁邊。他很不服氣。
「我不去。日他媽誰愛去誰去。」他說。
來米她爹顛著屁股,欣賞地看著人們抓鬮的神態,仿佛他是世界上最自在的人。
他想人日他媽就應該這麼活著。他突然想起了來米。他想他應該把來米的情況給六
姥說說。
「六姥,」他說,「您安安地把心放在肚子裡,我把來米在上房屋裡鎖著哩。
我給她送飯,她死不了,也跑不掉。」
六姥沒說話。六姥眯縫著眼。
抓完了,沒人報告他抓著了。
「誰抓著就報名。」拴牢說。
人們憤怒了。
「誰抓著了站出來,別耍賴。」他們說。
「肯定是鱉娃。」有人說。
鱉娃抱著頭在一邊一聲不吭。
「送人都不願去,那來米呢?心甭太黑了,我說。」來米她爹說。
「毬!」鱉娃站起來。他把手裡的紙團撕成了碎米花。
八
拴牢和鱉娃站在仁義家門口。
「仁義。」拴牢喊。
仁義從屋裡走出來。
「我不去。誰愛去誰去。」仁義說。
「我家出糧,我家現在就出。」仁義婆娘說。她從仁義脊背後邊腆出來。
「不成。早些做什麼去了?」拴牢說。
「我不去。」仁義說。
鱉娃抓得很准。他一把捏住了仁義褲襠裡的那一堆東西。仁義叫喚了一聲,跪
在地上,肚子使勁往後縮著。
「你甭動彈。」鱉娃說。
仁義跪直身子,一動不動。
「你躺下。」鱉娃說。
「我不。」仁義說。
鱉娃用了用力,仁義疼痛難忍,又叫了一聲。「我躺,我躺。」他說。
仁義朝後仰面躺下。他看著鱉娃的臉。
「你去不去?」鱉娃說。
「我不去。」仁義說。
鱉娃從腰裡掏出了那把挑豬刀。
「拴牢,你把這狗熊的褲帶解開。我把他用了去。」鱉娃說。
仁義婆娘叫喚了一聲,朝鱉娃撲過來。她使足勁在鱉娃身上蹬了一腳。鱉娃沒
動,女人反而被彈了回去,一屁股坐在地上。
「不活了,不活了。」女人哭嚎著。
「脫,把狗日的褲子脫了。」鱉娃說。
拴牢解開了仁義的褲帶。鱉娃晃晃那把挑豬刀。仁義沒動,一副任人宰割的模
樣。
挑豬刀扶上了仁義的皮肉。一陣冰涼的感覺,仁義的腿抖起來。他知道鱉娃會
真下手的。鱉娃真能把他的那東西割下來喂狗。
「我去。」他給鱉娃說。
「不去不是娘生父母養的。」他說。
鱉娃鬆開手,把挑豬刀裝進了盒子。仁義站起來,拍著身上的土。
「看把你能的。挑豬挑得眼花了你還挑人呀,得是?」仁義說。
「呸!」鱉娃照著仁義的額顱吐了一口。
「呸!」仁義又聽見了一聲唾。仁義婆娘照著仁義的臉也吐了一口,吐在了仁
義的下巴上。仁義沒說話。他看了婆娘一眼。
那天晚上,仁義和鱉娃一起蹲在六姥家的門坎裡邊。仁義順溜多了。六姥從腰
裡掏出來一堆銀洋,放在櫃蓋上。
「這是你們路上的盤纏。」六姥說。
他們朝那堆銀洋看了一眼。
「吃了飯就走。」六姥說。
出門的時候,六姥說:
「把老眼殺了。」
他們像受了驚嚇似地回過頭來。
「把他殺了。」六姥說。
六姥靠著木櫃。六姥像瞌睡了一樣。那只貓臥在土炕上的棉被窩裡。
六姥又吃紅蘿蔔了。他們出了門,還能聽見那種清脆的咀嚼聲。
九
瓜棚上的種瓜人不再晃悠了。沒有風。距瓜棚不遠有一道上樑。
一陣咯吱咯吱的木輪聲。
土梁的豁口處,出現了鱉娃、仁義和來米。來米坐在一輛單木車上。車上鋪著
一床棉被。還有一床棉被在來米的脊背後頭,卷著當靠背。仁義推車,鱉娃跟在後
頭。
來米穿一件紅布衫,像紅辣椒。她歪著頭,順著眼,任單輪木車顛著,搖著。
鱉娃背著手,邊走邊觀景。鱉娃的脖子邊上插著他挑豬閹蛋的標誌。
他們看見了種瓜人。他們停了下來。他們聽見對面山上有人唱歌。
「來了,來了,來了」
「花花大門進來了……」
他們朝對面山上望了一眼。仁義咽了一口唾沫,心裡有些虛慌。
「坑人哩!」仁義突然喊了一聲。
「憑什麼讓我去?坑人哩!」
仁義跳了一下。木輪車又響了,他們走下了溝坡。
他們要走一段很長的路程。
他們走到溝底了。一條小河從幾塊大石頭上摔下來,順著溝流過去。來米一伸
腿,從單輪車上跳下來。她要喝水。
「喝就喝,都喝。」仁義說。
仁義和鱉娃跪著,把嘴伸進水裡吸著。來米喝完水,靠在土坎上解辮子。她把
辮子解開,然後再編。鱉娃和仁義坐在石頭上,聽著來米解開辮子的聲音。
「這回該你推了吧?一人推一程。」仁義說。他看著鱉娃的髒臉。
「人不能耍賴,不能得寸進尺。我可不是你鱉娃雇來趕腳的。讓來米說。來米
你說。」
來米編著辮子。來米很超脫。來米是坐車的,誰愛推誰推。所以,來米不說話。
來米繼續編著辮子。編好了,來米朝脊背後頭一甩,來米甩得很好看。來米一伸腿,
又坐在了本輪車上。
鱉娃攥住本輪車把。鱉娃推著,仁義拉著,他們過了小河。河上留下了幾個鮮
活的濕腳樣。仁義看看那幾個濕腳樣,就跟在車子後頭了。他把手背起來。他想他
應該把手背起來。人有時候是孫子,有時候就是爺。當孫子就得有個龜孫樣,當爺
也得有爺的氣派,所以,他也要一邊走路一邊觀景。
「就這。哎嗨。」他想。
後來,他想起了來米她爹。他想和來米說幾句話。
「我說來米,你爹可真行,成咱村上的財東了。」他說。
「你爹這會兒在家裡蒸白饃饃吃哩。你信不。」他說。
車上的來米一顛一顛的,眼睛一動不動。
「信不信由你。我要是你爹也蒸白饃饃吃哩。哎嗨。」仁義說。
他眯著眼看著遠處。他似乎成了來米她爹。他聞到了一股白饅頭的香味。
兩邊都是山。路窄長窄長,在山溝裡胡亂拐著,拐著。
他們在路上走著。他們三個人。
十
來米家很熱鬧。來米家從來沒這麼熱鬧過。來米她爹想好好收拾收拾家。現在,
他有這個力量了,也有這個心情了。他請了存道、拴牢和德盛幾個人給他打牆。他
給他們熬罐罐茶。他把熬好的茶水倒在碗裡,讓他們喝。
「喝,」他說,「甭急,喝了再打。有你們吃的喝的。」
「噢,噢。」德盛幾個人對來米她爹笑著,看著他提著菜罐走開。
「心真黑。來米她爹的心黑透了。」存道說。
「他成咱村上的富戶了。」拴牢說。
「糧食都給了他,咱喝西北風。」德盛說。
「我就想把這碗摔了去。」存道說。
「摔了去。」德盛說。
「給驢日的摔了。」拴牢說。
「咣當」一聲,存道手裡的茶碗碎在了一塊半截磚頭上。存道一臉誇張的表情。
「看你。」德盛和拴牢說。他們都看著來米她爹。
「沒抓牢,日他的沒抓牢。」存道說。
來米她爹看了地上的碎碗一眼,他沒過來。
「毬一個碗,毬。」來米她爹說。德盛他們都感到肚子憋。
「這不成。他一人好過,這不成。」存道說。
「我婆娘和我鬧翻了,」德盛說,「我一進門,她就抓我的臉,罵我是鱉旦,
抓了我一把就回娘家去了。」
德盛臉上真有幾道指印。
「總得想個辦法。」存道說。
「就是。」德盛說。
「找六姥去。」拴牢說。
他們放下手中的活計,相跟著朝村裡走。來米她爹以為他們想屙屎撤尿。
「我家有豬圈。」他說。
「這夥熊人。」他說。他似乎有些不滿。
就是這時候,德盛發現有人在他家偷雞。不知道這人的名字,就叫他溜溜吧。
他進了德盛家的門。他一邊往進走一邊說:「大叔大嬸爺爺奶奶給點吃的。」他背
著一個布褡褳。窗臺上有一雙洗過的布鞋。他飛快地把它裝進了褡褳裡。「大叔大
嬸爺爺奶奶……」他這麼叫著。後來,他看見那只母雞。半牆上有個雞窩,母雞正
在窩裡下蛋。他把它抓了出來。他擰著脖子想把它擰死,然後裝進褡褳。
「賊!」德盛站在大門口吼了一聲。
溜溜嚇了一跳。他把一根手指頭飛快地塞進了雞屁股。
「有蛋哩。真是個母雞。我摸著有蛋哩。呵,呵呵。」他一臉賴皮的模樣。他
對德盛笑著,想往外溜。
「放下!」德盛說。
溜溜放開母雞。母雞搧了幾下翅膀。
「我看它有蛋沒蛋。有哩,我不騙你。」溜溜說。
「看你賊眉鼠眼的。」德盛說。
「閃開!」溜溜突然變了臉,喊了一聲。趁德盛發愣的功夫,他貓起腰朝德盛
沖過來。他沒有成功。德盛一把撕住了他的耳朵。他歪著脖子轉了一圈。
「我沒偷。我看它會不會下蛋。」溜溜失聲喊了起來。
德盛把撕耳朵的那只手往上一提,溜溜就踮起了腳尖。他們就這麼出了門,上
了街道。一碰見人,溜溜就放開嗓子幹嚎,沒人的時候就求饒。
「你放了我。我一輩子不來你們村了。誰哄你是四條腿。我把你叫爺。爺,大
爺。」溜溜給德盛說。
德盛把渾身的力氣都用在了手指頭上。他撕著溜溜的耳朵。
十一
六姥盤腿坐在土炕上,她抽著旱煙。那是一根長杆銅頭煙鍋。除了吃紅蘿蔔,
六姥還愛抽旱煙。那只貓臥在六姥的懷裡。
除了拴牢和存道,還有許多人。他們都來找六姥要主意。
「日子沒法過了。」拴牢說。
「他不仁,咱不義。」存道說。
「六姥你拿個主意。」拴牢說。
「把他做了。」有人說。
六姥敲掉了煙鍋裡的煙灰。她抬起一隻胳膊取櫃蓋上的那半截紅蘿蔔。
他們聽見了溜溜的喊叫聲。一會兒,他們就看見德盛撕著溜溜走進來。
「他偷我家雞。」德盛說。
「沒有。我看它會不會下蛋。」溜溜說。
德盛使勁擰了一下。溜溜踮著腳叫喚。德盛的手塞進溜溜的褡褳裡,取出來一
只鞋。
「他還偷鞋。」德盛說。
「叭!」德盛用鞋底在溜溜臉上搧了一下。
「把狗識的綁了。」有人喊。
他們把溜溜綁在門前的樹上。
「取刀去!」有人說。
「剁了他!」有人說。
溜溜不叫喚了。他閉上眼。
「死了吧,死了吧。」他說。
人們有些詫異。他們感到事情有些不好辦。賊娃子不怕死,你能有什麼辦法。
六姥從人堆後邊走出來。
「放了他。我有話和他說。」
「溜溜睜開眼,瞪著六姥。拴牢給溜溜鬆開繩子。溜溜活動活動胳膊,很輕蔑
地掃了眾人一眼,跟著六姥進了屋。
後來就發生了溜溜給來米她爹剃頭的事。
來米她爹用熱水洗完頭,把毛巾圍在脖子上,在那條單人木凳上坐下來。看著
溜溜磨剃刀。溜溜磨得很利酒。
「你說你能剃頭?不像。」來米她爹說。
「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鬥量。」溜溜說。他用指頭試試刀刃,朝來米她爹走
過來。
「弄這事多年了,最拿手的就是剃光葫蘆。」他說,「你又不是沒見。德盛,
拴牢,都是我剃的。你又不是沒見。」他說。
「怎麼看也不像。」來米她爹說。
溜溜一手按在來米她爹頭上,一手舉著刺刀。他朝門外邊看了一眼。他想這事
情事關重大,得穩住神。
「嗞——」來米她爹的腦頂上出現了一道白皮。一堆毛髮順著剃刀卷下來。溜
溜的手好像抖了一下。
「嗞——」溜溜挨著白茬又剃了一刀子。又一堆毛髮卷了下來。溜溜的臉嚴肅
得有些怕人。來米她爹很有些無所謂的樣子。他想起了村上人噁心的嘴臉。
「他們眼紅我呢!」來米她爹說,「我日他媽讓出了閨女,他們出了什麼。閨
女是好養的?我早後悔了,他們還眼紅我。黃花閨女換糧食,我吃多大的虧?你說
是不?」來米她爹斜過臉,翻眼看著溜溜。
溜溜心虛了,手抖得厲害。他又朝外邊看了一眼。他知道他們在外邊等著他。
「你剃,剃。」來米她爹說,「我看你的手藝還湊合。聽刀子的聲音就知道。」
「嗞——」剃刀挨著白茬又一次劃過來。溜溜已經滿臉汗水了。有人在什麼地
方咳嗽了一聲,又咳嗽了一聲。他們都聽見了。
「吃白石灰了。狗日的吃白石灰了。」來米她爹說。
「嗞——」
「嗞——」
刺刀的速度越來越快。後來,溜溜手上的剃刀閃了一下,就在來米她爹的脖子
上劃出一道口子。來米她爹叫喚了一聲。溜溜從門裡跳出來,跌跌撞撞跑上街道。
街道上黑壓壓蹲著許多人。他們突然站起來,看著溜溜。溜溜從人夥堆裡撞了
過去,一直跑出村子,跑上那座土峁。種瓜人還吊在瓜棚上,像一件東西。
「啊,啊。」他叫喊著。他不時地看著身後。沒有人追他。他們用不著追他。
來米家廂房屋也有一種「呵呵」的叫喚聲。那是從來米她爹的喉嚨裡發出來的。
後來,人們就看見他從門坎上爬出來半截身子,脖子上的刀口冒著一種粉紅色的泡
沫。
人們屏息靜氣地看著他。他們圍在他的跟前,直到那些紅色的泡沫一個一個破
滅淨盡。
「死了。」他們說。
拴牢把來米她爹的頭轉過來。他們看到了一雙怕人的眼睛。眼珠子從眼眶裡掉
了出來,沾滿了土,圓鼓鼓地對著他們。
人群一陣騷動。人們向糧囤擁過去。來米她爹倒完糧食後扔掉的那些空口袋堆
在上房門口的臺階上。他們翻騰著,找自己的口袋。
拴牢從布衫口袋裡掏出一個麻紙本。
「還有規矩沒有?」他說。
「一家裝了一家裝。」他說。
他照著麻紙本念了起來:
「劉存道,穀子三鬥,小麥二鬥。」
劉存道提著口袋走向糧囤。
「王德盛,穀子八鬥。」
他們排著隊,挨個兒裝糧。一會兒,來米她爹曾經撫摸過的糧囤就空了,像一
只空洞的眼窩。
院子裡安靜下來。來米家的豬不知什麼時候拱開了木欄,在院子裡吃著撒落的
糧食,一直吃過門坎,吃到糧囤跟前。
十二
他們在一孔土窯跟前停了下來。天已麻黑了,他們想歇歇腳。他們看著那孔窯。
「你進去看看。」鱉娃給仁義說。
「你去,你去喀。」仁義說。
那是一孔攔羊人廢棄的空窯洞,很大。裡邊有些乾草一類的東西,好像有人睡
過。鱉娃把乾草往一塊踢踢,踩平。
「就睡這。」他說。
「怎麼睡?」仁義看著乾草說。
來米已在最裡邊躺下了、鱉娃從木輪車上取下鋪蓋卷。他伸手進去摸了摸,裡
邊有銀洋的響聲。它們在。他把鋪蓋卷放在頭底下當枕頭,緊挨著來米躺下去,邊
上留出來一溜乾草。仁義知道那是給他的地方。他想說什麼,又憋了回去。他坐在
乾草上,脫鞋,倒鞋窩裡的土,然後躺下。
窯裡一滿是乾草和羊糞的氣味。
月亮光從窯門口照進來。他們都張著眼窩。
「睡不著。日怪了,想睡睡不著。」仁義說。他聽見來米的身子動了一下,他
突然想起了什麼,兩隻胳膊一用力,把半個身子撐起來。他看看來米,又看看鱉娃,
然後看他們之間的空檔。來米和鱉娃的身子快換在一起了。
「我睡不著。」仁義說。
「咱換換地方。」仁義給鱉娃說,「我這人躺在門邊上睡不著。」
鱉娃一動不動。仁義又躺了下去。
「睡不著,真日怪了。」他說。
他感到他身上有一樣東西正在起著變化。他立刻就想起了他那位肥胖的婆娘。
一到晚上,他總要想起她。他想起她的時候,就會聞到一股纏人的怪味,他身上的
什麼東西就會變化,硬挺挺的讓他難受,他就想幹一件什麼事情。他就這麼想著,
難受著。
鱉娃真是個鱉娃。鱉娃早睡著了。他想沒沾過女人的男人都這麼貪睡。他這麼
一想,就有些模模糊糊了。
他聽見了一陣乾草的聲音。他看見來米站起來,從他的腳跟前走過去,出了窯
門。他推了推鱉娃。
「來米想跑。」他說。
鱉娃跟著來米出了窯門。他看見來米在一塊石頭背後蹲了下去。他感到身上什
麼地方被觸動了一下。他看著那塊石頭,聽見了一串尿水聲。仁義站在他後頭,和
他一起聽著。來米一站起來,就看見了他們。來米沒說話。來未動了動眉毛,從他
們身邊走過去。
「你看人家來米尿尿!」仁義說。他感到鱉娃很無恥。
「你真不要臉。人家一個大姑娘。」他說。
來米好像聽見了仁義的話。來米沒回頭,她進了窯門。鱉娃一直看著她。
「我看你存心不良。」仁義說。
「好啊你個鱉娃!」他說。
鱉娃瞪著仁義。鱉娃的臉讓仁義感到害怕。
「好吧好吧我不說了,愛看你看去。看還不是幹看,哎嗨!」仁義說。
他們沒有進窯。他們在石頭上坐下來。山溝裡很安靜。
「你說咱能殺了老眼?」仁義說,「他們都是殺人的貨,咱能殺了他?你說。」
「咱不弄那事。咱把來米送到就走。咱管毬他。」仁義說。
「他們會把咱怎麼樣?咱把來米和錢給他們送到手,他們能把咱怎麼樣?」仁
義說。
「不知道。」鱉娃說。
「來米呢?他們會把來米怎麼樣?他們把來米……」仁義說。
「不知道。」鱉娃說。
「咱跑。咱不去了。」仁義突然說。他看著鱉娃的臉。
「咱手裡有三千塊大洋。咱滿世界浪去。咱浪出個什麼眉眼就什麼眉眼。」仁
義說。
鱉娃不吭聲。
「要不你讓我走。我的腿有病,你給我分點,咱各走各的。」仁義說。
「行不?」仁義說。
「我割了你。」鱉娃說。他突然變了臉。
仁義聽見鱉娃褲腰上的挑刀盒響了一聲。
「看你看你,」他說,「不跑就不跑。我還有老婆娃哩。不跑就不跑。」
窯裡傳來一陣哽咽聲。他們聽了一會兒。
「來米想他爹了。」仁義說。
他們一進窯門,看見來米坐在乾草上抽泣。來米沒想她爹。來米不知道她這是
怎麼啦。來米壓根就沒想這事。來米想你讓我坐單輪車我就單輪車,你讓我去騾馬
寨子就去騾馬寨。來米想往前的路是黑的。來米有時候會想起她媽。她記不得她媽
的模樣。她想她媽可能是個比她年齡大的女人。她一想她媽,心裡就有些不是滋味,
就想流些眼淚什麼的。她感到這很怪。人有時候就有這麼一種很怪的感覺。
天麻亮的時候,來米出了窯門。仁義看見來米出了窯門。他沒驚動鱉娃,悄悄
跟出去。他看見來米下了溝坡。他有些慌失了。
「來米跑了!」他朝鱉娃的腿骨上踢了一腳。鱉娃一骨碌爬起來。
「我看著她從溝坡那裡下去了。她跑了。」仁義說。他沒跟鱉娃出去。他從鋪
蓋卷裡取出了裝銀洋的布袋。他沒想到鱉娃會折回來。他愣了一下。
「看什麼?人都跑了你還看什麼?我說她要跑你還不信。」仁義說。
「一人一千五,咱各走各的。」仁義說。
鱉娃沒動。
「你想多分?那不成。一人一半。」仁義說。他解開了布袋上的繩子。
他們聽見了腳步聲。來米從溝坡那裡走上來,來米的懷裡抱著一抱山果。來米
不知道他們要幹什麼。她看著他們。
幾塊銀洋從解開的布袋裡掉下來,在地上滾了幾圈,像仁義張大的眼睛。
「這熊人。」仁義說。他給鱉娃笑了一下。
來米坐上單輪車。他們又起程了。來米把一顆鮮紅的山果放進嘴裡,嚼了幾下。
後來,他們就碰上了溜溜。
十三
溜溜在溝裡坡裡胡竄了幾天幾夜,就忘了他給來米她爹剃頭的事。他感到肚子
很餓。他看見了在溝底下行走的鱉娃他們。他想他應該把他們截住,也許能弄點吃
的。他掄開胳膊,從峁頂上栽爬下來。
鱉娃他們一上溝,就看見了溜溜。他們不認識他。他坐在路邊的楞坎上。在這
麼個很難看見人影的地方突然看見了一個人,他們都有些驚奇。他們想和他打個招
呼,但沒打。他們從他跟前走了過去。他們甚至沒有回頭。
溜溜一直看著他們。他感到他們太沒道理,有這麼見人不打招呼的麼?
「嗨!」溜溜喊了一聲。
鱉娃和仁義回過頭看著溜溜,等溜溜說話。溜溜不言語了。仁義感到沒什麼危
險,就朝溜溜走過來。
「你喊啦?」仁義說。
「我喊啦。」溜溜說。
「你做什麼喊?」仁義說。
「我說嗨!」溜溜說。
「你吃多了?」仁義說。
「我餓啦。」溜溜說,「我幾天水米沒沾牙了。」
「餓了你還喊?」仁義說。
「我說嗨!」溜溜說。
「我摸摸你肚子。」仁義說著就要摸。
「摸女人的肚子去。」溜溜說。他看了來米一眼。
「你狗日的真會想。」仁義說。他突然伸出手在溜溜的脖子上偏了一巴掌。溜
溜跳了起來。
「你打人。」溜溜說。
「我想卸你的腿。」仁義說。
「你敢打人。我幾天水米沒沾牙,你敢打人。你看你,你還卸我的腿。」溜溜
一邊說一邊往後退,一直退到本輪車跟前。他掃了來米一眼。他愣住了。來米的臉
很美,紅是紅白是白。他給仁義笑了一下。
「你們送新娘,得是?」溜溜說,「我跟你們混口飯吃。」
「我推車。」溜溜又看了來米一眼。
「你知道我們去哪兒?」鱉娃說。
「我管毬。該不是殺人去?」溜溜說。
「還真讓你說著了,哎嗨!」仁義說。
「我推我的車,我管毬。」溜溜說。
「到時你就尿褲襠。」仁義說。
「牆縫裡看人哩。我也弄過那號事。剃頭刀子一抹,就是一個血脖子。你不信?
我溜溜走南闖北,什麼事沒經過?」他又看了來米一眼。
「我給咱推車吧。」他說。
「一路上都推?」仁義說。
「看你說的。給點吃的。」溜溜說。
鱉娃給溜溜一張玉米煎餅。溜溜推著來米在前,鱉娃和仁義背著手相跟在後。
就這麼,他們收留了溜溜。
後來,他們碰到了一棵樹。那時候太陽正熱。他們在大樹下睡了一覺。
十四
來米沒睡。來米在離他們不遠的一塊石頭上坐著。來米看著遠處的什麼東西。
那時候太陽正熱。空氣裡有一種幹上的氣味。
仁義睜開眼睛,正好看見了來米繃緊的屁股蛋。他好像想起了一樣重大的事情。
他看看鱉娃和溜溜。他們正睡得一塌糊塗。他爬起來,走到來米跟前,挨著她坐下
來。
「你要小心鱉娃。」仁義說。「我看他心懷鬼胎。他想打你的主意哩。」仁義
說。
來米好像沒聽見,身子一動不動。
「給你說你還不信?」仁義說。
溜溜睜開眼,在鱉娃身上蹬了一腳。
「挑豬閉蛋的沒好人,我說。」仁義繼續給來米說著,「你可不能讓他把你弄
了。」仁義說得很誠懇。
仁義聽見了一陣響動。他回頭一看,鱉娃不知什麼時候站在他背後了。仁義有
些難堪。
「來米真會找地方。這兒有風,涼快。」仁義站起來,給鱉娃說,「不信你試。」
鱉娃沒動。他想搧仁義一個耳光。
「你們談,你們談。」仁義說。他從鱉娃跟前側了過去。
溜溜遠遠看著他們。他飛快地從鱉娃當枕頭的鋪蓋卷裡摸出錢袋,取出兩塊銀
洋,塞進鞋窩,然後穿好。
那時候,鱉娃改變了搧仁義一個耳光的主意,他想往仁義臉上吐一口。他感到
仁義這樣的人只能吐給一口唾沫。他側過頭,他感到唾液已爬上舌頭尖了。可他沒
吐。他看見溜溜正在偷錢。
「你們談,你們談。」仁義這麼說。
鱉娃沒吐出那口唾沫。
來米轉過頭來了。她看著鱉娃。來米的眼睛好像大有深意。她挺著繃緊的胸脯。
鱉娃心裡有個什麼東西動了一下。
然而,鱉娃轉身走了。來米看著鱉娃的背影,眼睛一點一點順下來。她走到單
輪車跟前,一伸腿,又一伸腿,坐了上去。溜溜很麻利地駕起了單輪車。他心裡正
燒著一團火,因為他的鞋窩裡有兩個光閃閃的銀元。
「妹子,你坐好。」他給來米說。
「我要快走了。」他說。他把拌繩在肩膀上挪挪好,手上運了運勁。車子果真
快了。
「什麼好,女人的大腿好。」
溜溜聽仁義給鱉娃這麼說。
「妹子,你聽見沒?」溜溜已滿頭大汗了,他問來米。他看著來米的脖子。
來米在本輪車上一顛一顛的。
溜溜想幹一件什麼事。他剛幹了一件,那兩塊銀元在鞋窩裡正美好地磨著他的
腳掌。他還想幹一件好事。好事多了不累人,也不遭罪。誰不想多幹好事,誰都想
不停地碰到好事,讓好事淹死。溜溜這麼想著。他不停地回過頭看被他越甩越遠的
鱉娃和仁義。
「女人的大腿好。我不信。」溜溜想。
溜溜終於下了決心。溜溜一下決心,木輪車就翻倒了,來米驚叫一聲,從車上
摔下來。溜溜飛快地湊到來米跟前。
「摔著了?我看我看。」他捏著來米的腳脖子順腿往上摸。
「這兒疼?這兒?」他捏著,問著。
「這兒?這兒?」溜溜的手又順著來米的大腿往下捏。
「怎麼啦?怎麼啦?」仁義喊著。
「絆倒了。石頭把車子絆倒了。」溜溜也喊著。他在來米的大腿上狠狠捏了一
吧。
來米看了溜溜一眼,溜溜駕起車轅。他給來米笑了一下。
「我有銀元。」溜溜突然說。
「我晚上給你看。」他說。他又笑了一下。
鱉娃和仁義趕上來了。
「你狗日的怎麼推車?」鱉娃說。
鱉娃拽著溜溜的胳膊,把他從車轅裡揪出來。溜溜打了個趔趄。溜溜很得意。
「你推得好。」來米給鱉娃說。
溜溜看著仁義的後腦勺,很不服氣的樣子。他想教訓仁義幾句。
「你說女人的大腿好?」溜溜說。
「咋啦?」仁義說。
「我看沒什麼好。」溜溜說。
「你知道個毬。」仁義說。
「我捏過。」溜溜說。
「你知道個毬。」仁義說。
仁義根本不把他溜溜放在眼裡。
「你見過幾個女人?你那不叫見,叫看。你聞過女人的肉沒?你騎過女人的肚
子?你知道個毬。」仁義說。
溜溜瞪圓了眼珠子。他想一掌把仁義搧倒。仁義不知道溜溜的心思。仁義背著
手,頭仰得老高。
溜溜沒搧。溜溜吸一口氣,又吐了出來。他看著來米的背影又下了一次決心。
他想他無論如何也要聞聞來米的肉。他想他聞了來米的肉還不行,他還要好好教訓
教訓仁義。他不想騎來米的肚子。他想女人的肚子沒什麼好騎,沒什麼意思。還是
聞肉好。那時候,他感到腳掌一陣陣疼。他知道是那兩塊銀元在鞋窩裡作怪。他想
來米不讓他聞肉的話,他就把銀元送給來米。兩塊銀元哩,她還不讓聞?
那天晚上,他們歇息在崖畔底下。那天晚上沒有月亮,溜溜枕著他的那雙鞋躺
了一會兒。然後他趴在來米耳朵跟前給來米說:「來米我想聞聞你身上的肉,我有
銀元你讓我聞聞。」
來米搧得真准。她掄圓胳膊,手掌重重地落在溜溜的臉上。溜溜想喊叫一聲。
溜溜捂著半個臉,沒喊出聲來。他沒想到來米會搧他。他感到事情太突然了。他輕
輕地叫了一聲來米。來米不說話。她好像什麼事也沒做過。她好像快要睡著了一樣。
溜溜聽見了一陣金屬敲擊的聲音,然後又聽見「啪嗒」一聲,一雙鞋飛過來,
摔在他的腳跟前。溜溜立刻想壞了壞了。他擰過頭一看,鱉娃不知什麼時候坐起來
了。鱉娃手裡拿著兩塊銀元,一下一下敲著。溜溜急了。溜溜想發作。他感到鱉娃
太不要臉了。
溜溜沒發作,他要哭一樣,把那雙鞋放到他頭底下睡了。一陣尖厲的疼痛正從
的腳掌上往他的心裡鑽。
那時候他們都沒了瞌睡。他們在黑暗裡張著眼窩。他們突然感到了一種沉重的
東西。
「再五十裡,就到騾馬寨子了。」鱉娃像自言自語。
一溜土從崖背上溜下來,發出一陣「滋啦!,的聲音。他們都聽見了。
「要下雨了。」仁義說。
天上的雲確實越來越重了。
來米走到鱉娃跟前,看著鱉娃黑乎乎的臉。鱉娃不知道來米要幹什麼。
「我命苦。」來米說。
來米轉過身,半個屁股坐在單輪車上。那時候天還沒亮,他們又上了路。
十五
那是一座野店。周圍什麼也沒有,獨獨這麼一座野店。店門緊緊地閉著。
「過了這個店,就是騾馬寨子。」仁義說,仁義的聲音很虛弱。
他們一路上都沒想騾乃寨子。現在他們不能不想它。他們要到那裡去。他們的
獨輪車上推著一個女人和三千塊大洋。
「把老眼殺了。」六姥嚼著紅蘿蔔給他們說。
鱉娃臉上的皮動了一下。他看見來米正看著他,目光有裡有一種讓人憐惜的期
待。一股風吹過來,撩起那根竹棍上的兩條紅布。紅布條在風裡甩出一陣響。然後
就是一陣雷聲。然後就大雨如注了。雨點猛烈地砸在他們的肩膀上,砸在本輪車上。
地上積水橫流。
「鱉娃你狗日的說句話。」仁義噴著滿嘴的雨水朝鱉娃喊著。
「要走你一個人走。」仁義說。
仁義踏著雨水,跑到店門跟前,用力一推,門開了。
院子裡沒有人。幾間屋子的門關閉著。除了雨水,什麼聲音也沒有。這裡一定
發生過什麼事情。
他們聽見了一陣劈劈剝剝的聲音,是從伙房裡傳出來的。一個蓬頭垢面的男人
靠著牆壁,臉埋在胸脯上,好像睡著了。灶膛裡的火已滅了,灰堆裡不時爆出一陣
響聲。鍋裡不知道煮著什麼東西。
「哎。」仁義對那個人喊了一聲。仁義上前撥了一下。那人直直地倒了下去。
仁義看見了一張結滿血癡的髒臉。
他早已死了。
仁義叫了一聲。仁義像瘋了一樣在院子裡跑著,尋找著什麼東西。他終於找到
了一塊石頭。他朝自己的腳踝上砸了幾下。
他的手被鱉娃緊緊攥住了。鱉娃把他從泥水裡拽起來,惡狠狠地盯著他。
「叭!」鱉娃打了仁義一個耳光。
「叭!」鱉娃又打了一個。
仁義愣愣地看著鱉娃。鱉娃手一松,仁義又一屁股坐在了泥水裡。他看著鱉娃
進了一間屋子。
「我不去。我死也不去。」仁義突然放聲哭了起來,「老眼會殺了我們,啊,
啊……」他痛苦地捂著臉。
雨小多了。天急劇地黑下來。他們沒走。他們在野店裡住了一夜。
來米坐在一間偏房的土炕上梳理頭髮。溜溜蹲在牆角,瞅著黑洞洞的炕門。他
不時抬頭看看來米。來米梳頭的時候總有一種頭髮的聲音。一會兒溜溜就靠著牆根
睡著了。來米把梳好的辮子甩到脊背後頭,出了門。
鱉娃在另一間屋。他躺在一堆乾草裡。那是一間堆乾草的屋子。他不知道在想
著什麼。
「鱉娃。」來米在門口叫著。來米從門口走進來,她看著草堆裡的鱉娃。
「你們不會活著回來。」來米說。
「我不是黃花閨女。」來米說。
鱉娃好像沒聽懂得來米的話。
「我和男人睡過覺。」來米說。
「和我爹,我不騙你。」來米說。
鱉娃的臉色劇烈地變化著。
「母狗!」鱉娃突然跳了起來。鱉娃臉上的肉突突跳著。鱉娃抓著來米的肩膀。
鱉娃的眼睛睜得老大。鱉娃的目光慢慢變得複雜起來。鱉娃甚至有些溫柔了。
「來米……」鱉娃這麼叫了一聲。鱉娃的聲音很輕,只有來米能聽見。
來米迎著鱉娃的目光。鱉娃感到來米的胸脯正一點一點膨脹著,讓他不能自已。
不知怎麼的,他把來米扳倒了。
「噢。」來米驚叫了一聲。來米驚叫的那一聲和呻吟一樣。
就這麼鱉娃弄了來米。鱉娃喘著氣,來米呻吟著,來米像蛇一樣扭著身子。後
來,他們都軟在了那堆乾草裡。
「鱉娃……」來米說。
「來米……」鱉娃說。
「你娶了我。我跟你走。」來米說。
鱉娃躺在來米跟前。鱉娃不說話。
「我知道你不會娶我。」來米說。來米站起來,扣上衣扣。她穿的是那種大襟
布衫。
「我再也不坐你的車了。」來米說。
來米出門的時候,看見仁義站在門口。仁義等來米一走,就發瘋一樣撲進來,
撲向鱉娃。他想騎在鱉娃身上,劈頭蓋臉打他一頓。他沒打,鱉娃的目光把他嚇住
了。他伸出手做了一個要打的架勢。
「鱉娃你起來。」仁義說。
鱉娃站起來。
「你別動。」仁義說。
鱉娃沒動。
「我要打你。你讓我打。」仁義閃著巴掌。
後來,仁義放下了手。他在屋裡走來走去。他很激動。他狠狠地教訓了鱉娃一
頓。
「好你個挑豬的。」他說,「你敢睡來米。有你這麼傷天害理的人麼?就算她
不是黃花閨女,她是你能睡的麼?你鱉娃手捂著胸口想一想,哪個女人不能睡,你
偏偏要睡來米……」
十六
騾馬寨子真是騾馬寨子。騾馬寨子有許多馬房。馬房裡拴著馬、驢和騾子一類
高足牲口。土匪們以販牲口為職業。騾馬寨子是他們聚居的老巢。他們把牲口從內
蒙古販回來,然後在騾馬交易會上賣給當地人。他們像走親戚串門一樣在內蒙、山
西和甘肅一帶做著牲口生意。他們愛牲口如命。他們都是些殺人不眨眼的貨色。他
們就是這麼一夥人。他們有他們的活法。他們給牲口刮毛、配種、鏟蹄子、釘掌。
他們熟悉牲口像熟悉他們的腳趾頭一樣。
他們也是吃五穀雜糧的。來米她爹這麼說。
那天,他們和往常一樣在馬房裡忙碌著。他們說著各種各樣的笑話。他們的說
笑夾雜在牲口的叫聲裡。驢叫聲是這裡最嘹亮的聲響。有人在伙房裡做飯。
石頭塚是騾馬寨子最高的地方。上面有許多窯洞,那是販子們睡覺的地方。老
眼住在最中間的那孔窯裡。窯前邊蓋了一截木房。
一條大路從馬房跟前伸出來,一直伸到遠處。那裡有一道石頭壘成的矮牆。過
了那道矮牆就下山了。
鱉娃、仁義他們就是從那裡走上來的。那時候,一匹小公馬從遠處跑進了馬房,
跑到一匹母馬跟前。正給母馬鏟蹄的土匪說:該騙這狗日的了。然後,他們就聽見
了一陣木輪車的咯吱聲。然後他們就看見了鱉娃他們。
鱉娃他們站在那道矮牆跟前,肮髒的臉上佈滿了太陽光。他們看著土匪們。土
匪們看著他們。他們都有些疑惑不解。
土匪們以為那幾個人走錯了路。他們又各幹各的事情了。可是鱉娃他們眼睜睜
朝馬房這裡走了過來。
「老眼呢?」鱉娃說。
沒人回答。一個矮個子土匪不知從哪裡追出來一隻狗。狗拼命地跑著,叫著,
狗叫聲像刀子一樣。快追上了,矮個子土匪靈巧地伸出一隻腳,朝狗的後腿上踏過
去。
「哢嚓!」狗的一條後腿斷了。
狗打了一個滾,翻過身子,更淒厲地叫了一聲,拖著一條斷腿跑著。
「哢嚓!」又一聲。
另一條狗腿斷了。
仁義的腿打抖了。仁義閉上了眼睛。
矮個子土匪像戲耍一樣,把狗提起來,提到伙房跟前。那裡有一口鍋,水已燒
開了。土匪取過刀子,朝狗的脖子抹過去。
土匪剝下狗皮。他把狗皮掛在了伙房的牆上。狗頭沒有割斷,連帶在狗皮上,
塗滿了鮮紅的狗血。矮個子朝馬房裡的土匪們笑了一下。他把狗肉放進了鍋裡。
沒有人搭理鱉娃他們。
仁義的身子像篩糠一樣。他圓瞪著雙眼,撲通一聲跪在地上。
「他要殺人!」仁義突然喊叫了一聲。他指著鱉娃。
「他殺人來啦!」仁義喊著。
鱉娃好像迷糊了一會兒。他聽見土匪們哄一聲笑了起來。
土匪們以為仁義是個瘋子。
仁義慌失了。仁義慢慢爬起來。他折過身,撒腿跑了。誰知道呢?人有時候就
會這樣。
「殺人啦!殺人啦!」
仁義一邊跑一邊喊著,一直跑過了那道矮牆。沒有人追他。
「老眼呢?」鱉娃又問了一句。
溜溜一直沒放下車轅。來米也沒下去。她感到鼻眼裡有些難受。她把小拇指塞
進鼻眼裡掏了一會兒,掏出來一塊鼻癡。她吸了兩下鼻子,然後彈了一下指甲蓋兒。
她感到好受多了。
「老眼呢?」她聽見鱉娃這麼說。
老眼正給一匹馬灌藥。老眼五十多歲,戴一副茶色石頭鏡,穿一件白布褂,寬
腿褲。他不像土匪頭,像一個經紀人。以後鱉娃就會知道,其實老眼不壞。老眼挺
好。來米也會這麼說。
馬痛苦地扭著脖子,藥很難灌進去。
溜溜把木輪車直推到老眼跟前。來米下了車。來米下車的姿勢很好看。
鱉娃解開錢袋,把一堆銀元倒在地上。老眼看也沒看。
「耍哩,耍笑哩,你們就當真了。」老眼說。他到底把藥灌進了馬嘴。他朝來
米的臉上看了一眼。
「耍哩。」老眼說。
鱉娃氣歪了臉。他沖著老眼大吼了一聲:
「我操你媽!」
鱉娃的眼眶裡湧滿了淚水。
「村上人快讓你們整死了。」鱉娃說。
老眼一點也不生氣。
「人總要有點什麼事。無事生非哩。你沒聽人這麼說?」老眼說。他又看了來
米一眼。
「走,咱們走。」溜溜說。
「哎,」老眼說,「來了就住幾天。」
他們住下了。
十七
鱉娃盤腿坐在馬房的土炕上。他們被安頓在這裡了。這裡拴著幾匹牲口。
「這地方不壞。」溜溜說。他賊眉鼠眼到處亂瞅。
鱉娃正卷著一根煙。
「吃狗肉了——」
他們聽見矮個子土匪喊了一聲。從炕牆上的窗口剛好能看到伙房那裡。他們看
見矮個子土匪揭開鍋蓋,用鼻子喚著冒出來的熱氣。他想取一塊肉嘗嘗。太燙了。
他趕緊拔出手,放在嘴邊吹著氣。土匪們夾著碗。圍在鍋跟前等著領肉。
「我也領去。」溜溜說。
土匪看了溜溜一眼。溜溜指指鍋裡。
「有福同享。」溜溜說。
土匪夾了塊肉,放在溜溜碗裡。
「吃。日他媽不吃白不吃。」溜溜給鱉娃說。他把狗肉碗重重地蹾了一下。
鱉娃沒動。鱉娃看著老眼的那座小木房。從馬房的門裡正好能看到那裡。矮個
子土匪端著一大碗上好的狗肉,敲著老眼的木門。他側耳聽了聽,給其他土匪們做
了個鬼臉。
門開了。老眼一身熱汗。
「把肉放門口。」老眼說。
老眼在木房門邊上尿了一泡。他端起肉碗,門又關上了。
「操他娘。」溜溜說。他有些憤憤不平。
溜溜開始吃肉了。他憤怒地對付著一塊帶肉的骨頭。
「什麼世道。不吃白不吃。」溜溜說。
「操他的媽媽。」溜溜又罵了一聲。
鱉娃掐滅了手裡的煙捲。煙頭上掉下來一溜火星。天黑了下來。
明月高照。土匪們已經入睡。幾排平靜的馬房裡亮著幾盞燈光。偶爾能聽見牲
口響界和挪動蹄腳的聲音。
溜溜脫著褲子,唱了兩句酸曲:
先解紐扣後解懷那個,
然後再把那個褲帶解,
奴和你玩耍來……
老眼的木門緊緊關閉著。鱉娃一夜沒睡。鱉娃一夜都想著來米和老眼睡覺的樣
子。溜溜累極了,一夜睡得很香。
天一亮,老眼就來找鱉娃。
「來米不是黃花閨女。」老眼說。
鱉娃板著臉,他看見來米提著一個空臉盆從木門裡走出來。她在伙房門口的甕
裡打了一盆水,又進了那座木房子。
「她和男人睡過。」老眼說。
「噢麼。」鱉娃這麼說了一句。
「你們在路上走了幾天,怕是和你睡的?」老眼說。
「沒。沒有。」鱉娃說。
「看你說的。」鱉娃又說一句。他好像給老眼笑了一下。
「大屁股,肥突突的。」老眼說。
老眼從屁股後邊摸出來一把鏟蹄刀。
「到馬房裡轉轉。」老眼說。老眼似乎忘了來米和男人睡覺的事。
「這些馬都是從蒙古買回來的。」老眼給鱉娃說。他很得意。他和鱉娃轉了好
幾個馬房。他鏟蹄的技術很老練,搬起腿噌噌兩下就鏟好了。他放開馬腿,在馬臀
上拍了兩下。
「純純的蒙古種,至少賺一半價錢。」老眼說。
就這麼轉了一圈,鱉娃不太彆扭了。他甚至忘了老眼是個土匪。他甚到感到老
眼是個能人。他想不通老眼怎麼會是個土匪。他想世上的事說到底沒個什麼道理。
「把老眼殺了。」嚼紅蘿蔔的老女人說。
十八
那天早上,鱉娃看見一群土匪往牲口背上搭馱子,好像要上遠路。「他們去定
邊城趕騾馬交易會。你要回去就跟他們一起走。」老眼給鱉娃說。
鱉娃沒準備回去,所以鱉娃半晌沒說話。
「不走住幾天也行。」老眼說。他的一隻手在一匹母馬的肚子上摸著。
「懷駒了。狗日的懷駒了。」他說。
那匹小公馬揚著蹄子從馬房跟前跑過去,鬃毛像水一樣顛簸著。
「該騙他狗日的了。」老眼說。
「我騙。」鱉娃說。
要上遠路的土匪們搭好了馱子。
「這回一定要賣個好價錢。」一個土匪說。
「順便去一趟蒙古。回來走山西。山西的女人奶子大。」另一個說。
來米從木門裡出來倒水。她提著臉盆,朝馬房這裡看了一眼。溜溜趴在一口大
缸跟前喝水。溜溜看沒人注意他,便放下馬勺,朝木房子溜過去。
「來米。」他執在窗口往裡看。木房子的偏牆中有個窗口。
來米已坐在炕上了。
「老眼把你怎麼啦?我問你話哩。」溜溜一副不要臉的樣子。
「呸!」來米隔窗朝溜溜臉上吐了一口。
「你讓我進來,我有話跟你說。」
來米開了門。溜溜和太陽光一起跨進來。
「行啊來米。」溜溜在凳子上坐下,自在地翹起一條腿。桌子上有吃剩的狗肉。
溜溜拿過來一塊塞進嘴裡。
「老眼這地方不壞。」溜溜說。
來米正在清點一疊皮貨。她對它們好像很滿意。她好像沒聽溜溜的感歎。
「你看這,三個月的羔皮。」來米說。
「老眼從蒙古弄的。」她說。
溜溜好像發現了一件重大的秘密。他一下一下瞪圓了眼睛,他使勁把那口狗肉
咽下了喉嚨。
「我說來米,你還真跟老眼過一輩子呀?」溜溜說。
那時候,鱉娃正要騸那匹小公馬。老眼和幾個土匪把小公馬綁在一根木樁上。
鱉娃騎馬的技術和挑豬一樣熟練。他在那裡割了一刀。那一刀和挑豬很相像。他把
帶血的刀子在褲腿上抹了兩下。
溜溜給來米講了他剃頭的事。
「他還以為我給他剃頭哩。」溜溜說得眉飛色舞,「剃著剃著,我就剃到他脖
子上了。我手這麼一劃拉,他就成了血脖子。你不信?我說的你不信?」
「他是我爹。」來米說。來米沒抬頭。
溜溜的眼睛又瞪圓了。
「你爹?你說他是你爹。」溜溜說。
「你把我爹割死了?」
「看你來米淨說笑話。」溜溜說。
老眼從門裡進來。老眼一邊走一邊問來米:
「誰把你爹割死了?」
「沒有。來米說笑哩。嘿嘿,呵呵。」溜溜有些不會笑了。他往外走。
「殺你爹就是殺我岳丈大人。」老眼笑著給來米說。
「來米你可別胡說。呵呵,你們在,你們在。」溜溜順手拿走了吃剩的那碗狗
肉。他退出門坎,撒腿就跑。
溜溜在土崖邊上找到了鱉娃。
「來米不走了。這裡好吃好喝,她不想走了。」溜溜說。
鱉娃一臉鐵青,不知道想著什麼。溜溜把那碗剩狗肉推在鱉娃跟前。
「吃。我在老眼屋裡偷的。」他說。
「她要和老眼過活。」他說。
「沒看出來。真不是個貨。」他說。
「爛髒女人。」他說。
鱉娃一聲不吭。鱉娃咬著牙根,腮幫子一鼓一鼓的。
「你說咋辦?」溜溜說。
「日他的!遇到這號事情。」他說。
他看見鱉娃把什麼東西塞進嘴裡嚼著。
「你不管?這麼大的事你不管?你還是男人呢!他還睡過人家來米呢!」溜溜
說。
溜溜終於看清了,鱉娃往嘴裡塞的是土坷垃。鱉娃不緊不慢地嚼著。他又撿了
一塊。
「你吃上?」溜溜說。
溜溜有些害怕。溜溜的臉扭成了一堆難看的肉皮。
「啊哈,你吃土?」溜溜突然尖聲叫喊起來。「他吃土呢!他狗熊吃土呢!」
鱉娃已經是滿嘴濕泥了。
遠行的土匪們上路了。
牲口隊走過馬房,走上大路,一直走過了那道矮牆。
「他吃土呢!」溜溜喊著。
溜溜回到了馬房。他跪在炕上,想著鱉娃滿嘴濕泥的樣子。
十九
天還沒大亮,老眼就來喊鱉娃,叫鱉娃和他給牲口鍘草。老眼說人上了年紀瞌
睡就少。鱉娃說人不上年紀有時候也睡不著。老眼說就是就是,咱鍘著草諞著閒話
我還愛和你偏。鱉娃說走,鱉娃蹬上了鞋。
一間馬房跟前有一個幹草垛。鱉娃扳鍘刀,老眼遞草。他們都是鍘草的把式。
他們鍘得很老練。他們都很認真。
「嚓——,嚓——」
那時候天邊慢慢有了幾道紅色,像棗刺劃破的血印。那時候來米和幾個沒出門
的土匪肯定還在睡覺。那時候騾馬寨子只有老眼鱉娃鍘草的聲音。溜溜睜眼看看鱉
娃的被窩,以為鱉娃尿尿去了。他又閉上眼,嚼著唾沫翻過身睡了過去。
「嚓——」
鍘刀有力地切割下去,被鍘斷的碎草向一邊翻卷著。鍘刀抬起來的時侯,刀口
那裡就齊刷刷亮出一道白茬。老眼的膝蓋壓在乾草上,一下一下遞著。鱉娃扳著刀
把,一抬一壓,一起一落。
「嚓——」鱉娃狠狠地壓下去。他把鍘碎的草朝旁邊撥了一下。
「我看你這人不壞,留在騾馬寨子算了。」老眼說。
「弄我們這營生沒什麼竅門。你到蒙古去,沒錢不怕,你借,你借蒙古人的。
第一回少借點,惜二十塊,還的時候你還三十。他巴不得你再借。再借你就借他三
百,借了你就走人,走得遠遠的,你再買馬。天下那麼大,他到哪兒找你?找個毬!」
老眼說。
「你不要怕事,也不能怕死。人不怕死,什麼事情都能幹成,要什麼有什麼。」
老眼說。
老眼說得不緊不慢,像講著一件平常的事情。他埋著頭,沒看鱉娃。他知道鱉
娃在聽他說話。
鱉娃的臉色有些難看,嘴很幹。鱉娃的嘴唇上炸起了一層白皮。鱉娃鬢角上的
青筋鼓了起來。鱉娃的眼窩像兩個土坑。
「把老眼殺了。」六姥說。
「我日他的媽媽。」鱉娃在喉嚨裡咕嗜了一聲,不知道是罵六姥還是罵老眼。
老眼沒聽清。老眼遞草的手停下來。他伸著下巴看著鱉娃的臉。他不知道他的
手正放在鍘刀底下。
「嗯?」他說。
鱉娃使勁把鍘刀壓了下去。他聽見一聲手骨斷裂的響聲。他看見老眼的兩隻手
離開了手腕,從鍘枕上掉下來,在白花花的碎草裡動彈著。
老眼沒感到疼。老眼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他張著嘴,看著鱉娃。他以為鱉
娃要說一句什麼話。後來,他終於感到疼了。他叫喊著蜷成了一團,在地上滾著。
鱉娃愣了好大一會兒。他想他應該幹點什麼。他想他得把這件事幹完。他跑進
了馬房,在馬房裡尋找著。他找到了一把鐝頭。他操起它,朝蜷曲著叫喊不已的老
眼跑過來。
他用銀背在老眼頭上砸了兩下。他感到鐝頭砸在人頭上和砸在硬土塊上差不多。
就這麼他砸死了老眼。老眼的茶色石頭眼鏡斷成了兩截,鏡片上沾著幾滴粉紅色的
液體。那時候太陽正一下一下在雲層裡往上拱著,雲層裡有一種擠破東西的味咋聲。
二十
溜溜下了村外的土坡,就失眉吊眼地喊起來:
「殺啦!殺啦!」
他連滾帶爬地跑進村街,在街上來回奔跑,驚得雞飛狗叫。
溜溜從來沒有這麼光榮過。全村人跟他來到村口,圍著他,聽他講述世界上最
讓人驚訝的事情。他們張著眼窩,眨著眼窩。他們都渴極了一樣,想被深深地驚訝
一次。
「殺啦?」拴牢的脖子和雁一樣。
「給我水喝。」溜溜說。
別人給溜溜一碗涼水。他一飲而盡。人們盯著他的嘴,等著他開口說話。
「來煙。」溜溜說。
有人把正抽的煙捲遞給溜溜。他狠狠地咂了兩口。
「殺啦?」仁義說。仁義也來了。
溜溜鄙棄地瞄了仁義一眼。
「人頭遍地……」溜溜說。
「啊。」人群騷動了。
「遍地?」人們說。
「遍地……」溜溜說。
「遍……」
「屍堆如山……」溜溜說。
「如山?」
「如山。」
「山……」
「血流滾滾……」溜溜說。
「滾滾?」
「滾滾……」
「滾?」
溜溜像喝醉酒了一樣。人們激動得滿臉通紅。他們不知道該怎麼才好。
「來了。」有人突然說了一聲。
人們鴉雀無聲了。他們齊刷刷把頭扭過去。他們看見了鱉娃。他站在坡頭那裡,
脖子上飄著兩條紅布。他站了一會兒,然後下坡,向村口走過來。
鱉娃走到跟前了。
鱉姓看著他們。他們看著鱉娃。他們突然都有一種陌生的感覺。他們都硬在了
地上,一動不動。後來,鱉娃就看見有人想往回溜。
「回來啦。」拴牢說。拴牢很不自在的樣子,臉上的肉動彈了幾下。
「嘿嘿。」拴牢友善地笑了兩聲。
「回去拖娃去。」仁義在他婆娘的屁股上踢了一腳。婆娘腆了一下肚子。
再後來,人們一個跟著一個散了。溜溜左顧右盼。溜溜不知道這是怎麼啦。溜
溜的眼珠子咕嗜咕嗜滾著。
「嘿嘿。」溜溜給鱉娃笑著。
溜溜也走了。
鱉娃一個人立在村口,鱉娃滿臉幹土。沒有人知道那時候鱉娃心裡想一些什麼。
那天,村上人給鱉娃燴了幾大碗菜。拴牢和存道幾個人陪著鱉娃吃喝了一頓。
村上順便炸了幾鍋油餅,全村人在六姥家門口吃了一次「大戶。」拴牢又敲著鼓在
街道上走了一趟。他一邊敲鼓一邊喊:「吃大戶了——」
「鱉娃,這是專意給你弄的。」拴牢指著那幾碗菜給鱉娃說。
鱉娃像倒髒水一樣往喉嚨裡灌了一瓶酒。
「吃!」鱉娃說。
鱉娃叉開筷子,照準一碗肥肉片插了進去。
後來,人們看見鱉娃搖搖晃晃地從六姥家走出來。他一臉喜色,邊走邊唱:
來了來了又來了
披紅掛綠過來了
來了來了又來了
花花大門進來了……
他們看見他搖進了他家的那道土門。他家門口有許多土坯,整整齊齊地壘成幾
個方塊。人們突然想起來,挑豬閉蛋的鱉娃好像說過,等他有了女人,就蓋幾間大
房。
二十一
六姥臉上像塗了油一樣,泛著那種油光。六姥的櫃蓋上有一串油餅,用筷子串
著,像個小塔。六姥家上房屋裡光線很暗,人們的臉埋在陰影裡。
「不能留這種人。」有人說。
「留不成。誰知道會出什麼事。」仁義說。他蹲在最不顯眼的角落裡。
「他殺了老眼,土匪饒不了咱。」他說。
「等著看麼。」他說。
「殺了老眼,不知還殺誰呢!」仁義又說了一句。
六姥一聲不吭。六姥的手越過那串油餅,摸出來一根紅蘿蔔。他們看著六姥。
他們肌肉緊張,精神亢奮。他們聽見那種不詳的嚼聲又響起來了,直往肉裡鑽。
那天晚上月光很亮。不知誰家的狗叫了幾聲。許多人從門裡閃了出來,急匆匆
穿過街道。他們來到鱉娃家的土門跟前。他們好像要商量什麼事情。他們沒有說話。
鱉娃歪倒在土炕上正沉沉大睡。一根粗壯的大紅蠟燭蹲在半牆上的木楔子上。
鱉娃挑豬的職業標誌胡亂扔在炕頭那裡。鍋臺上有一個盛水的黑瓷盆。那是一種連
著土炕的鍋臺。
「鱉娃。」一個男人的聲音在門外叫著,很溫柔。
「鱉娃開門。」
鱉娃沒醒。
「開門!」聲音大了起來。
鱉娃醒了。他感到有點渴。他抱起鍋臺上的黑瓷盆灌了一氣。
有人敲門了。敲門聲越來越大。門扇猛烈地顫動著。鱉娃感到有些不對勁。鱉
娃甚至聽見一聲窗紙破裂的聲音。他看見一根手指頭。
「嚓——」從紙洞裡戳了進來。
窗紙被撕爛了。鱉娃看見了幾個人頭。鱉娃沒見過這種事。他想找一件什麼東
西提在手裡。他聽見「嘩啦」一聲,然後就看見一堆人從門裡擁了進來。
誰也不知道他們是怎麼弄死鱉娃的。那天晚上,許多人都聽見了鱉娃家那一陣
可怕的響動。許多人坐在他們的土炕上,他們睜眼靜靜地聽著。
那夥人離開鱉娃睡覺的那間屋的時候,門沒有合嚴。他們看見一股血水從門坎
底下爬出來,順著門縫裡射出的那道光亮爬著,像遊蛇一樣。他們才知道人身上的
血能像箭一樣往外射,還能像蛇一樣地在地上往前爬。
他們在鱉娃家院子裡和了一堆泥。他們挽褲腿,在泥堆裡踩著。他們想把泥和
得勻一些。他們看著那股血水。
「年輕人的血旺。」他們說。
他們排成一行,一直從土門外排到流血的那間屋門口。他們一塊一塊遞著土坯。
仁義拿著泥刀,把土坯砌在門框裡。仁義砌得很認真,他甚至不放過一件拳頭大小
的窟窿。
他把窗戶也砌上了。
他給砌好的土坯上抹了一層泥皮。
「唰——」他用泥抹子抹著,泥皮越來越光滑。他一直抹到天亮的時候。
「唰——」仁義還在抹著。
仁義抬頭往亮天的地方看了一眼。他看見山包子像他婆娘的奶子一樣。他想他
婆娘這會兒還在炕上睡著。他想他現在回去還來得及。他想他婆娘要是不願意他就
在她的肥腿上擰一把,一擰她就願意了。他離開鱉姓家的時候,看見還有幾道風乾
的血水沒有蓋住,他抓了一把泥,摔在上面。
他到底聽見了牲口走路的聲音。那是許多天以後。那時候也是天剛亮的光景。
村上人都聽到了。一夥騎牲口的人包圍了村子。
他們是騾馬寨子的土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