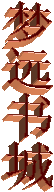
楊爭光 棺材鋪
一
楊明遠在蛤蟆灘襲擊了一隊做絲綢生意的商人之後,回到了老家新鎮,敲開了
他弟楊明善的門。那時候天剛麻亮,街道上沒有人影。他在他弟的破門上敲了幾下。
新鎮前後兩條長街,中間一條馬道相連,他弟楊明善就住在馬道裡。他聽見他敲門
的聲音像豌豆一樣滾出去老遠,然後,他聽見了幾聲咳嗽。他弟楊明善光著腳,拉
開一道門縫,仰著脖子,從門縫裡看著他的髒臉。他弟小時候害過一場病,以後的
四十多年裡沒怎麼長個子,就成了現在這麼個矮男人。他弟的眼珠子偏偏長得很大,
從鼻樑的兩邊掙出來,時刻都會從眼眶裡蹦出去一樣。他眨眼的時候,就會眨出一
陣「啪嘰啪嘰」的響聲。
這會兒,他仰著脖子,神情認真,從門縫裡「啪嘰啪嘰」看著他哥楊明遠。
「你回來做甚?」他說。他沒有讓他哥進門的意思。楊明遠當了土匪以後,他
們兄弟之間很少來往。
「你讓我進去。」楊明遠說。
「你說,你說你回來……」
楊明遠把手伸進門縫,張開五根粗硬的指頭,箍在他弟楊明善的腦頂上,一使
勁,楊明善的頭就從脖子上轉了過去。楊明遠擠身進門,把一包袱白花花的銀子放
在櫃蓋上。楊明善的女人正在炕上穿衣服,她從來沒見過這麼多的銀子,身子立刻
軟了,嘴巴攝成了一截竹筒。
「噢!」她呻喚了一聲。
楊明善一臉鄙夷的神色,瞄了他女人一眼。他感到他女人太有些見錢眼開了。
「順牆靠著我說,悄悄的別出聲,別給我丟人顯眼。」他說。
然後,他把臉轉向他哥楊明遠。
「我不要你的錢。」他說。
「我不要來路不明的錢。」他說。
女人用鼻子哼了一聲,聳聳肩,緊好褲帶,順炕牆坐了下去。她覺得她男人像
一塊生薑疙瘩。
後來,楊明善就知道了那一包袱銀子不是給他的。他哥楊明遠要收心洗手,回
新鎮當一名規矩的鎮民。
「我不想在外邊胡跑了。」土匪楊明遠說。
「跑麼,你跑麼,」楊明善說,「我又沒拉你的腿。」
「咱可是一個娘褲襠裡倒出來的。」他哥說。
「你聽你說的話,一個娘褲襠!」楊明善說。
「你給我弄一塊地皮。」他哥說。
「地皮?我為什麼給你弄一塊地皮?」
「你是鎮長。」
「我可不是你的鎮長。」楊明善說,「我是個毬不頂的鎮長。」
「毬頂毬不頂你給我弄一塊地皮。」楊明遠說,「一筆寫不出兩個楊字。」
「新鎮可都是規矩人家。」鎮長楊明善說。
「我不給你惹事生非。」他哥說。
「這可是人話?」楊明善說。
「人話!」他哥說。
楊明遠的身子背後傳出來一陣溜吸鼻涕的聲音。楊明善的女人又呻喚了一聲。
她看見楊明遠的身後站著一個髒兮兮的鼻嘴娃,進門的時候她竟然沒看見。
「我的後人。」楊明遠說,「我和你嫂睡了一覺就有了他,好歹是楊家的種,
我留了他。」
「噢。」女人說。
「你嫂命不長,死了。」楊明遠給弟和弟媳婦笑了一下,把他的後人坎子,從
身子背後撥到他弟跟前。
「叫叔。」他給坎子說。
坎子叫了一聲叔。
「叫嬸。」
坎子叫了一聲嬸。楊明善的女人從炕上跳下來,摸著坎子的頭。
「多乖。」女人說。她朝櫃蓋上的包袱瞄了一眼。
「你給我照看坎子幾天。」楊明遠說。他給櫃蓋上留了一把碎銀,提著包袱走
了。
女人興奮得像一隻下了蛋的母雞,她飛快地收起銀子,包好,放在一個牢靠的
地方。
「他留了我就收,我不嫌來路不明。」女人說,「我不嫌少。坎子,你好生在
嬸子這裡呆著,嬸子給你烙油餅吃。」
鎮長楊明善眨巴了一陣眼睛,沒說什麼。
許多天以後,土匪楊明遠在新鎮城外蓋起一座深宅大院,做起了棺材生意。人
們看見一截截帶著樹甲的圓木從馬車上卸下來,抬進了楊明遠家漆黑的大門,出來
的時候,就變成了一口口嶄新的白木棺材,散發著一股木香味,老遠就能聞見。楊
明遠成了新鎮的三家富戶之一。他沒惹事生非。他和新鎮的人來往很少,棺材鋪成
了新鎮最神秘的地方。新鎮人不知道楊明遠是怎麼用棺材發財的,他們猜測了很久,
有人說,楊明遠的棺材是給隊伍上的,隊伍上用那些白木棺材給挨了槍子的士兵收
屍,這種猜測設有得到證實。後來他們又為楊明遠一直不娶女人的事嘀咕了一段時
間。再後來,他們什麼話也不說了,他們想楊明遠還會發財。他們沒想到楊明遠的
棺材會有賣不動的時候。他們更想不到,楊明遠非要把賣不動的棺材賣給新鎮的人。
鎮長楊明善到那座深宅大院裡看過他哥一次。他老遠就聽見了鑿子、鉋子、鋸
子和木頭接觸的那種「叮叮噹當」「劈劈啪啪」的聲響。他踩著滿地的刨花,從一
群潛心做活的夥計中間走過去。他看見他哥楊明遠坐在一把黑漆木椅子裡,手裡焐
著泥茶壺。他哥的臉刮得白白淨淨,白淨得讓他有些接受不了。他哥給他笑了笑。
他感到他笑得有些怪模怪樣。他沒和他哥說生意興隆不興隆的事情,他覺得一個正
派人談生意很下賤,和一個生意興隆的人談生意的事情,更下賤。「他很得意,他
肯定很得意,我偏不和他說他得意的事情。」他一路上都這麼想。
他和他哥說了幾句娶不娶女人的話。
「你不給你弄個女人?」他說。
他哥往喉嚨裡灌了一口茶水,沒有說話。
「嗯?不弄。」他說。
「女人傷身子。」他哥說。
「說發你就發了。」他朝那些做棺材的夥計們看了一眼。
「噢麼。」他哥說。
「看你得意的,我可不是眼紅你。」他說。
「噢麼。」他哥說。
「你還要發,得是?」他說。
這回,他哥沒說噢麼,他哥端著泥茶壺看了一會兒天,他們好長時間沒有說話,
他們聽了一陣鋸子切割木板的聲音。後來,他聽他哥說:「棺材賣不動了。」
「做生意都有賣不動的時候。」他說。
「我可不想讓我的棺材賣不出去。」他哥說。
楊明善「啪嘰啪嘰」眨了一會兒眼睛。他覺得他哥有些可笑。
「棺材可不是什麼好東西,你總不能硬往別人家裡抬吧?」他說。
「我可不想讓我的棺材賣不出去。」他哥又說了一句。
「熊話。看你說這熊話。」他說。
他哥扭過臉又給他笑了笑。他哥往喉嚨裡灌了一口茶水。他哥咽茶水的聲音很
響。他哥仰著脖子,他看見他哥的喉節滑動了一下。他哥的喉節很大。
那時候,鎮長楊明善和新鎮所有的人一樣,沒有多想。
「啪嘰啪嘰,」他眨著眼。
二
事情發生得有些蹊蹺。那天傍晚,楊明遠端著那把泥茶壺出了他家的黑門,他
想出去走走。最近一段時間,他總愛這麼端著泥壺出去走走。離他家不遠處有一個
土壕,一會兒,他就蹲在了土壕邊上。他看見坎子和另外兩個一般大小的孩子在土
壤裡「過家家」。他認識他們,一個是地主的兒子大頭貴貴,另一個是當鋪掌櫃的
女兒花花。他們和坎子一樣,都穿著開襠褲。他們玩得很潛心。坎子當轎夫,「抬」
著新娘花花忽悠忽悠走了一陣,然後,新郎貴貴扶新娘下轎。
「親一口,貴貴,要親一口。」坎子說。
大頭貴貴愣眼看了坎子一眼,突然轉身抱住花花,在花花臉上親了一口。他讓
花花躺下,花花不躺,花花說地上有土。
「你是新娘,新娘要上炕。」貴貴說。
貴貴把花花扳倒,然後騎上去,竟躡著小屁股晃了起來。花花不讓貴貴晃,她
說貴貴你晃我就不和你玩了。貴貴說新郎都這麼晃,不信你問坎子。坎子說就是就
是。花花不說話了,任貴貴一下一下晃著。上壕岸上的楊明遠笑失了聲。貴貴一抬
頭,看見有人笑他,便受了鼓舞似的,小屁股晃得越上心了。當鋪的女傭人劉媽來
喊花花吃飯的時候,貴貴正晃在了興頭上。
「嗨哎!嗨哎!」劉媽喊叫著從土坡上顛了下來。
「他們玩耍哩。」楊明遠說。
劉媽沒聽見楊明遠的話。劉媽一直顛到大頭貴貴跟前,在貴貴一晃一晃的屁股
上搧了一把。
貴貴扭過頭,很不服氣地看著劉媽。
「你搧我?」貴貴說。
劉媽擰著貴貴的耳朵,把他從花花身上提起來。
「你擰我耳朵?」貴貴說。
劉媽本來想笑,可她沒笑。
「小小年紀就知道弄這種事,誰教你的?」劉媽說,「我看看你的牛牛有多長。」
劉媽說著,就從貴貴的褲襠里拉出貴貴的小牛牛,貴貴挺著肚子,一臉英雄氣
概。
劉媽在貴貴的小牛牛上捏了一下。
貴貴叫喚了一聲。
貴貴把頭仰在脊背上,斜眼看著劉媽。劉媽拽著花花走了。
「你捏我!」貴貴捂著褲襠喊了一聲。
劉媽沒有回頭。劉媽怎麼也想不到,她會捏出事來,會把貴貴的小牛牛捏腫。
第二天早上,地主李兆連的女人貴貴他媽讓貴貴下炕,貴貴不下,女人以為兒
子戀炕,便揭了被子。
「下去下去我要掃炕。」女人說。
女人突然瞪圓了眼珠子,她發現她兒貴貴的兩隻手非常可疑。一撥開貴貴的手,
她就失聲了,貴貴的小牛牛腫得像棒槌一樣,直乎乎豎在兩腿之間。
貴貴哇一聲哭了。
「她捏我。」貴貴說。
「劉媽捏我,她說她看看我的牛牛有多長,她就捏我。」貴貴看著他媽的臉,
他怕他媽揍他。
貴貴媽半晌沒有喘氣,她突然叫了一聲,像挨了戳的雞一樣從門裡奔了出去,
喊叫著,跳著,滿院子轉。
「啊哈,她捏我娃!啊哈,她捏我娃牛牛!」女人的眼淚像斷了線的珠子。女
人拍著屁股,打著臉。
地主李兆連正在馬房裡調理牲口,他是個四十多歲的瘦男人,長得像個書生。
他以為他女人讓開水燙了肚子,女人讓開水燙了肚子的時候才會這麼喊叫。他和幾
個長工從馬房裡跑過去,他甚至給一個長工說:「去油房舀些清油。開水燙了肚子
抹點清油就好受了。」女人一見李兆連,立刻止住了哭聲。
「貴貴的牛牛腫了。」女人說。
李兆連松了一口氣,說:「我當是開水燙了你的肚子,聽你那腔調。」
「驢!」女人跳著喊了一聲,「你去看,貴貴的牛牛讓人捏腫了!」
李兆連和長工們跑進屋,圍在炕跟前,要看貴貴的牛牛。貴貴樂了,從來沒有
這麼多的人對他的牛牛這麼關心過。他們說貴貴你甭捂你把手放開讓我們瞧瞧。貴
貴放開手,躺平身子,讓他的腫牛牛直直豎進他爹李兆連和那幾長工的眼睛裡。
開始的時候,李兆連並沒有把這件事放在心上,腫了就腫了,過幾天就會好的,
可沒多長時間,他就不這麼想了。貴貴的牛牛被當鋪女傭人劉媽捏腫的消息驚動了
李家戶族的男男女女和許多佃戶,他們提著雞蛋瓜果一類貴貴愛吃的東西,成群結
隊地來到貴貴家看望貴貴,這陣勢使四十多歲的地主李兆連突然產生了一種激動的
情緒。他越想越覺得劉媽捏得太不是地方了,他越想越覺得事情有些嚴重。當他想
到他只有貴貴這麼一個寶貝兒子的時候,他渾身的血好像燒開了一樣,在他的身子
裡「咕咚咕咚」直冒泡兒。他感到劉媽的那一捏簡直是個陰謀。
「叫去,」他給幾個長工說,「叫戶族裡的人都來看看。」
更多的人來到了貴貴家,他們都懷著激動的心情。貴貴平展展躺在炕上,啃著
人送來的好東西,聽他們激烈地談論他的牛牛。李兆連的女人已平靜了許多,她趴
在貴貴跟前,一臉憐愛的神情。
「貴貴你尿不?」
貴貴搖搖頭。
「疼不?」
貴貴搖搖頭。
「媽知道你疼,疼也要尿些,你不尿就會讓尿水憋死。尿不?」
貴貴還是搖搖頭。
「多可憐。」有人說。
「她怎麼敢捏娃的牛牛!」有人想起了劉媽。
「她那麼大的膽!」他們憤怒了。
就這麼,地主李兆連產生了一種激動的情緒。他想他要幹一件什麼事情。他想
他在幹這件事情之前應該到棺材鋪去一趟。
「我問問楊明遠去。」他說。
楊明遠知道李兆連會來找他,一看見李兆連從門裡走進來,他的眼珠子就亮了
一下,然後,就做出一副沉重的樣子。他把手裡的泥壺遞過去,讓李兆連喝茶。李
兆連不喝。楊明遠歎了一口氣。
「我說兆連,一口氣好忍。」他說。
他看見李兆連的瘦臉拉長了。
「你沒做什麼對不起當鋪家的事吧?」楊明遠問李兆連。
李兆連沒吭聲。
「劉媽下手也太狠了,」楊明遠說,「她怎麼能下那麼重的手。」
「他當鋪家想讓我李兆連斷子絕孫。」李兆連說。
「重了,重了,話說得重了。」楊明遠說。
「他胡為想讓我李兆連斷子絕孫。」李兆連又說了一句。
「傭人是傭人,不敢往人家掌櫃的身上扯。」楊明遠說。
「他胡為眼黑我。」李兆連說。
「牛牛是根,怎麼能捏人的根嘛。」楊明遠把目光從李兆連臉上移開,看著遠
處,像自言自語,「放在誰身上,這口氣也難忍。」
「忽——」李兆連吹了一口氣。
「忽——」李兆連又吹了一口氣。
「我日胡為他媽的腿!」李兆連突然跳起來罵了一句,走了。
楊明遠看著李兆連的背影,往喉嚨裡灌了一口茶水。夥計們停了手中的活,聽
他和李兆連說話。楊明遠把手裡的泥壺朝他們揚了揚。
「做你們的活去。」他說。
鉋子、鑿子、斧子一齊動了,棺材鋪一片熱鬧的響聲,一直響到深夜。
三
那天晚上,鎮長楊明善被請進了李兆連的家,他看見院子裡站著許多人,大都
是李家的長工,他們提著鐝頭鐵鍁一類傢伙,手裡點著火把,臉上佈滿激動的神情。
「我要砸胡為的當鋪。」李兆連說。
楊明善的心在胸膛裡顫了一下,他沒想到李兆連會這麼幹。他看著李兆連的臉,
眼睛啪嘰了半晌。
「我給你招呼一聲。」李兆連說。
「啪嘰啪嘰。」
「我不能蔑視政府。」李兆連說。
「差矣!」鎮長楊明善終於想出了一句合適的話,「差矣!」他說。
「我現在就砸。」李兆連說。
「差矣!」楊明善說。
沒等他再說什麼,砸當鋪的隊伍就呼啦啦出了大門,上了鎮街,空蕩蕩的院子
裡只剩下楊明善一個人。
「差矣!」他喊叫了一聲,追出門去。
當鋪掌櫃胡為正躺在炕上抽煙。有人把李兆連要砸當鋪的消息傳了過來,他不
信。他想劉媽捏牛牛的事與他胡為沒有干係。牛牛是劉媽捏的,我沒讓她捏,李兆
連不能胡拉被子亂扯氈,找我胡為尋事,他這麼想。他想,捏腫了又不是捏死了,
沒什麼大不了的,他想實在不行把劉媽辭退就結了,劉媽手腳不淨,老偷東西,他
正想辭了她。他很快就想出了結束這件事的辦法,他覺得事情很簡單,用不著大驚
小怪,所以,他沒把件事放在心上,他一直躺在炕上抽煙,他用六根手指頭捏著煙
槍。他一隻手上長了六根指頭。當鋪的生意紅火起來以後,他老感到,是那根多餘
的指頭給他帶來的運氣。高興的時候,他總要用舌頭舔舔那根與眾不同的指頭,它
像一根彎彎擰擰的樹根一樣,從大姆指的旁邊伸出來,緊緊貼著,顯出一種乖巧而
又多情的樣子。抽煙的時候,他喜歡用那只六指頭的手捏煙槍,不為別的,就因為
他喜歡。
「咣」一聲,門開了,一個夥計從門外撞進來。那時候,胡為剛在那根可愛的
指頭上舔了一下,沾在指頭上的唾沫水還沒幹。
「來了。」夥計說。
胡為瞪著夥計,一臉不高興的神氣。他最討厭的就是舔指頭的時候有人打擾。
「他們打著火把。他們叫你出去哩。」夥計說。
胡為躁氣了。
「你給李兆連說去,就說我不出去。」
「他們說,你不出去他們就砸。」夥計說。
「他敢!」胡為說,「他敢,」
李兆連和長工們圍在當鋪門口,火把在空氣裡燒出,陣陣「嘩嘩啪啪」的響聲。
當鋪夥計跑出大門,給李兆連說:「我家掌櫃不出來,我家掌櫃說你敢!」李兆連
也躁氣了,他指著當鋪的木板門說:「砸!」提傢伙的長工們一擁而上,木板門立
刻發出一陣歡快的呻吟,然後就破裂成許多碎片。長工們擁了進去。
「砸!」李兆連指著當鋪裡的櫃檯說。
當鋪夥計不敢攔擋,在一邊來回跳著:「你敢!你敢!」
「砸!」李兆連說。
又一陣歡快的呻吟之後,當鋪的櫃檯變成了一堆廢物。當鋪夥計不跳了,他看
看被砸倒的櫃檯,又看看李兆連。「好,」他說,「好,」他一下一下抖著下巴殼,
「你砸得真好。」他突然扭過頭,撒腿跑了回去。
「差矣!差矣!」鎮長楊明善甩著兩條短腿從街道上跑過來,他還想說一句
「差矣,」他猛地收住腿,看著被砸倒的一堆東西,把最後一個「差矣」和唾沫一
起咽進了喉嚨。他歪過頭,在人堆裡搜尋著李兆連。他看見李兆連領著砸當鋪的隊
伍越走越遠,他能聽見火把在空氣裡劃過的那種忽啦聲。後來,他又聽見了一陣腳
步。當鋪夥計領著胡為從屋裡走了出來。他想胡為肯定咽不下這口氣,胡為也不是
省油的燈。
胡為沒和他打招呼。胡為跨過被砸成碎片的木板門,在當鋪裡轉了幾個圈子。
他聽見胡為笑了一聲。
「日他的。」胡為說。
楊明善有些糊塗了。他猜不透胡為的心思。他沒想到胡為會笑。
「一口氣好忍。」他給胡為說。他想探胡為的深淺。
「我沒氣,」胡為說,「他李兆連就砸了我一扇門嘛,就砸了我一個櫃檯嘛,
我以為他要砸我的過活哩。」
鎮長楊明善興奮得兩眼放光了,「哎嗨!」他叫了一聲,「我沒看出你的股量,
你胡為日他媽真算個人!我以為你也要砸李兆連家的什麼哩。」
「我不砸,」胡為也為自己表現出來的大度感動了。「又沒人捏我家誰的牛牛,
我砸他我吃多了得是?我不砸。」他說。
「你知道,我就怕你也砸李兆連家的什麼,我就怕你們兩家你砸我我砸你砸得
拉不住閘,砸得昏天黑地的,你知道,儘管我毬不頂,可也算個鎮長,好壞得管點
事。」
「我不砸,」胡為說。
「你真好。」楊明善說。
鎮長楊明善和當鋪掌櫃胡為在一瞬間溝通了。他們越說越高興,越說越投機。
開始的時候,楊明善不斷地吹捧胡為宰相一樣的股量,後來,他們就互相吹捧。他
們吹得渾身發熱,吹紅了眼。他們感到站在街上這麼吹沒有意思,他們手拉著手進
了胡為的家。胡為讓夥計熱了一壺酒,他們對著酒壺繼續吹,一真吹到了天亮。眼
看著要發生的一起毆鬥,就這麼讓他們吹得煙消雲散了。鎮長楊明善很有些得意,
他感到他一個晚上沒有自吹,要不然,嗨嗨,胡為叫上一幫子人往李兆連家一沖,
日他媽這鎮上就得死人!
「胡掌櫃你看,天亮了。」楊明善說。
「噢麼。」胡為說。
「說亮就亮了。」楊明善說。
「天亮了你就走我睡一覺。」胡為說。
「你睡。我出去走走。」楊明善說。
楊明善邁著兩條短腿從胡為家搖了出來。鎮街上空落落的,風從街口灌進來,
撲在楊明善的額顱上,像年輕女人纖巧的手指頭,像母貓軟乎乎的舌頭。出門的時
候,他想他應該回家睡一覺,可這會兒,他突然感到在這麼好的時辰,把頭蒙在肮
髒的被窩裡,有些不划算。他沒有回家,他順著街道走了出去。
他聽見了一陣叮叮噹當乒乒乓乓的響聲。
響聲是從他哥楊明善的那座深宅大院裡傳出來的。夥計們在那裡製造著白木棺
材。
「日他媽真是越富越貪。」他想。
他朝他哥家的那扇大黑門搖了過去。他想和他哥隨便聊幾句什麼。人不是什麼
時候都有好心情,人心情好的時候,就想和誰隨便說幾句什麼話。
他哥家的黑門敞開著。他哥家有一灘豬屎正等著他,這是他想不到的。
他甩著兩條短腿搖過來了。
四
棺材鋪老闆楊明遠一夜沒睡。地主李兆連領著長工在胡為的當鋪一開砸,楊明
遠就來了精神,他把已躺進被窩的夥計們叫起來。他說不出幾天鎮上就會有一場好
戲,李兆連和胡為要開火。他們都是鎮上的大戶,他們一打起來就會死人。他說要
趕緊把棺材準備好。他說這幾天大家都少睡點覺,工錢嘛不會虧了大家。他把那把
黑木椅子搬進了工房。
「我和你們一起熬眼。」他結夥計們說。
他給工房的梁上吊了一盞耀眼的汽燈。
「把活做得精細些。」他說。
鉋子、鋸子、斧子叮叮噹當響了起來,他每天都能聽到這種響聲。他感到過去
的這種響聲沒有今天的好聽。他感到他很興奮,興奮得想流淚水。日他媽人興奮得
想流眼淚水的時候就知道什麼是幸福。日他媽這就叫幸福!他想。
「我不是想掙錢。」他說,「我覺得用我的棺材裝死人有意思,要不我就不開
棺材鋪了。」他說。「做什麼都能掙錢,掙不來錢你就去搶,去偷。那沒意思。」
他說。
「我還沒親眼見過用我的棺材裝死人哩。」他說,「我想親眼看看。」他說。
天亮的時候,他感到有些困,他想在椅子裡打個盹。他弟楊明善從大門裡走了
進來。他打了個激淩,呼一下從椅子裡坐直了身子。
「要來事了。」他想。
他沒說話。他直直地看著楊明善朝他走過來,他想他一定會給他說點什麼,他
等著他開口說話。
楊明善一臉得意的神色,什麼也不說。
楊明遠有些狐疑了。
楊明遠拿過他哥的泥壺,美滋滋呷了一口茶水,囗蹴在他哥的木椅跟前。
「日他的,喝了幾盅酒,口渴的很。」楊明善又呷了一口茶水。
「你忙你的,我沒事,我來轉轉。」楊明善說。
楊明遠看著他弟楊明善的模樣,想把他一腳踢倒。
「我不想喝酒,胡為說喝喝,這麼好的時辰有酒不喝是傻蛋,我就喝了,喝了
一夜。」楊明善說,「酒喝多了口渴。」
「胡為呢?」楊明遠問。
「胡為?在他家睡覺哩,」楊明善說,「那驢日的真是宰相的肚量,我以為他
要和李兆連開一火哩。」
「不開了?」楊明遠問。
「不開了不開了,我和他說了一夜話,我把他勸住了。我剛才給你說你就沒聽,
我和他喝了一夜酒,你聞。」他努起嘴,朝他哥吹了一口氣。
「你狗咬耗子。」他哥說。
楊明善覺得他哥的話說得有些怪。
「關你什麼事?」他哥說。
「啪嘰啪嘰」。楊明善飛快地撲閃著眼,「你這話說得就不對了,我是鎮長,」
他說,「我是鎮長我不管?你要是鎮長你管不管?」
「你是個毬。」他哥說。
楊明善好像不認識他哥一樣站起來,朝後退了一步,啪嘰啪嘰。
「你罵我?做什麼你罵我?我該你罵,得是?」他對他哥吼著。
「我看你該吃些豬屎」他哥說。
「憑什麼?憑什麼我該吃些豬屎?」
楊明遠不吭聲了,他歪著頭,在他弟的臉上掃瞄著,人又氣又沒辦法的時候,
就會有這麼一副古怪的神氣。楊明善有些膽怯了。他不知道他哥想幹什麼。
「你看我做什麼?」他說。
「給你吃些豬屎。」楊明遠說。
「憑什麼?」楊明善說,「真是天知道。」
楊明遠把臉轉向那些夥計:「過來,過來兩個人。」
兩個拉鋸的夥計走過來。楊明善的眼睛不再撲問了,他看著他哥。
「你看你,你還能把事弄成真的?」他說。
他往大門口退著,他想他只要能退到木門跟前,就轉身撒腿跑。
「甭讓他走。」楊明遠說。
一個夥計走過去,擋住了楊明善的退路。楊明善慌失了,你感到他腿上的關節
正在皴裂。
「真是天知道!」楊明善喊了一聲。
「去,到豬圈弄些豬屎來。」楊明遠給另一個夥計說。
夥計很樂意幹這件事,這比鋸木板有意思多了。他飛快地拐了幾個彎,進了豬
圈,又飛快地跑回來。楊明善看見他的手裡真抓著一把粘稠的東西。夥計的袖口高
高挽著。
「哥。你怎能這麼幹!」楊明善又喊了一聲,他還跳了一下。他看見他哥端起
泥壺回屋去了,他哥頭也沒回,他哥不給他一點希望。他感到這豬屎非吃不可了。
擋他退路的那個夥計抱住了他的胳膊,拿著髒物的夥計正一步一步朝他走近。他咬
緊牙關,憋住氣,他知道他們要掰他的嘴,他知道要掰開他的嘴唇是很容易的事,
而牙齒不容易,所以他使勁咬著牙關。他閉著眼。他聽見夥計說鎮長你就忍著點你
哥讓我們給你吃這玩貨我們當夥計的沒辦法這不怪我們。他想反駁夥計幾句,他想
說去你媽的甭給我說客氣話要弄你就快點弄。他沒說,他想他不能張嘴。他想他們
給他說客氣話也許是為了惹他開口,他一開口他們可就好辦多了,所以他沒說話,
他感到有一根手指頭在他的嘴上抿了一下,把那種髒東西抿進了他的嘴裡。然後,
他們放開了他。
「噗噝——」楊明善朝上吹了一口。
「呸!」他彎下腰,朝地上吐著。
「噗——呸!你想讓鎮上死人得是?你日弄人哩!噗——」他感到他嘴裡的髒
物怎麼吐也吐不淨。他看見他哥從裡屋出來,手裡端著泥壺,站在臺階上看著他。
他哥臉上的皮肉平順多了。
「你還算個人!」他對他哥喊著。
「以後你少管閒事。」他哥說。
「你還算個人!」他說。
他甩著胳膊,從大門裡搖出來。
「你還,還算個人!」他扭過頭又喊了一聲,然後進了城門洞。
已是早晨的時光了,他看見當鋪門口有幾個人在清理那些被砸爛的東西。他從
一邊繞了過去,他不想和他們打招呼。他感到他的牙齒上還有些那種黑綠色的髒物。
他很快拐進了家門,在廚房門口的甕裡舀了一馬勺涼水,認真地涮了一會兒口。這
時候,他才想起他一夜沒有合眼,真有些累了,他走進屋,看見他女人直乎乎在炕
上,頭髮像一堆乾草,衣服半開著,胸膛上吊著兩個肉葫蘆。女人一臉憂鬱的神色。
「你才起身?」他問。
「我沒睡。」女人說。
「沒睡?」他顯出吃驚的樣子。
「我睡不著,你不回來我睡不著。」女人說。
「我去當鋪喝酒了,」他說,「後來我去棺材鋪轉了一趟。」
「你哥沒留你吃早飯?」女人說。女人朝窗戶上看了一眼,太陽光已照到窗紙
上了。
「沒,沒有,我不吃他的飯。」他說。他蹬掉兩隻鞋,爬上炕。「睡,咱睡一
會兒。」他說,「脫了,脫了睡舒服。」他在女人的兩個肉葫蘆上撥了一下。
他們一塊鑽進了被窩裡。他沒給他女人說豬尿的事,他覺得給女人說這種事不
好,男人不一定把什麼事都告訴女人。
五
地主李兆連每天早晚都要去馬房看看。馬房單獨一個院子,拴著幾十頭牛馬騾
子一類牲口,由兩個長工飼養。早上下地的時候,牲口們就搖著尾巴從圈裡出來,
隊伍一樣走過新鎮的街道,在地上踩出一陣結實的蹄腳聲,晚上,它們再排著隊走
回來,踩出的蹄腳聲同樣結實。李兆連喜歡聽這種聲音,他感到自在,熨貼,日他
媽的,好聽!所以,他每天都去馬房。貴貴的牛牛腫了以後,他被耽擱了幾天,現
在,貴貴的牛牛消腫了。胡為當鋪也砸過了,他想他該去馬房看看。窮人愛娃娃,
富人愛騾馬,這是胡話,李兆連是新鎮的富人,他可是娃娃馬都愛。那天早上一醒
來,他給他女人說我去馬房呀。女人摟著貴貴,在被窩裡哼了一聲。他蹬上鞋,穿
著那件白布褂,邊扣紐扣邊往外走。
他沒看見他的牲口們。馬房的院子裡圍了一堆人,正嘈嘈著什麼。他們看見李
兆連走進來,就閉住嘴,朝他臉上看。他們給他閃開一條路,他看見了那兩個長工。
兩個長工一臉沮喪,手裡提著兩截韁繩,可憐巴巴的,要上吊一樣。李兆連心裡咯
噔響了一聲。
「日他媽出事了。」他想。
兩個長工叫了一聲「東家。」
「牲口沒了。」長工說。
李兆連感到他大腿上的肉好像被剃頭刀子割了一下。
「有人割斷了韁繩,把牲口全放跑了。」長工說。
李兆連的眼前立刻出現了一幅情景:有人趁長工睡覺的時候溜進牲口棚,用刀
子割斷了韁繩,把牲口們一頭一頭趕了出去。李兆連的腦袋裡忽一下亂成了一鍋粥。
李兆連的腦袋裡忽一下又變成了一盆清水。
「日他媽還不給我找去!」他朝長工們吼了一聲。長工們像受驚的野兔一樣從
門裡跳了出去。一會兒,新鎮方圓幾裡的溝岔和河灘上就響起了長工們吆喝牲口的
喊聲。
事情太明顯了。李兆連想也沒想,就走進了馬道,推開了鎮長楊明善家的門。
楊明善在豬圈裡正給他家的豬逮蝨子。那是一隻老母豬,剛下了一窩豬崽。它
功臣一樣躺成一個自在的姿勢,把它的十幾個奶亮給它的兒女們,讓它們肆意拱著。
它似乎很舒服,不時發出幾聲幸福的哼哼。
李兆連站在楊明善的跟前了。李兆連的臉像一枚青茄子。
「我給豬逮蝨子哩。」楊明善說。
「逮個毬!」李兆連說。李兆連脖子上的筋硬成了兩根筷子。
「咋啦咋啦?」楊明善說。
「有人放跑了我家的牲口!」李兆連說。
「笑話。」楊明善又要逮蝨子了。
李兆連往前走了兩步,抬起腳,朝那頭豬踢過去。豬叫喚了一聲,從楊明善的
手底下跳了出去,豬蹄子刨起的糞土花甩了楊明善一臉。
「你怎麼踢我家的豬?真是,不是自家的就不心疼。」楊明善心疼地看著那母
豬在糞堆上哼哼著轉圈子。「真是,要是你家的豬你踢不踢?」他說。
李兆連抓住楊明善的胳膊,把他從門里拉了出去。
「你甭拉你甭拉,大清早起來就踢我家的豬,還拉人,有沒有個天理良心!」
楊明善說,「你鬆開我。」
李兆連不鬆手,一直把楊明善拉進了他家的馬房。
「你看看,你睜眼看看。」李兆連說。
幾間牲口棚空蕩蕩的。
「你聽,你聽聽。」李兆連說。
楊明善豎著耳朵。長工們吆喝牲口的聲音像風箏一樣從鎮子外邊飄了過來。
「少一頭牲口,我和他胡為完不了。」李兆連說。
楊明善沒吭聲,扭身走了。
「我和他胡為唱火炮戲!」李兆連朝楊明善的背影吼叫著。他追出門,看見楊
明善拐過馬道,進了當鋪家。
胡為的心情看上去很好,他正在火爐上溫酒,心情好的時候,他總喜歡把酒溫
熱喝。他已經喝了好大一會兒了。他一見楊明善就說:「好,鎮長,好。」他的臉
紅堂瓜水的,他說熱酒上臉,可熱酒不傷胃。他給楊明善倒了一盅。
「來,喝一盅,熱酒不傷胃,我不騙你。」
楊明善沒接胡為遞過來的酒盅。他覺得胡為很噁心。
「你這人真噁心。」他說。
「我心裡高興。」胡為說。
「我以為你真是宰相的肚量哩,你這人真噁心,」楊明善說,「我不喝你的酒。」
「你不喝我喝。」胡為說。胡為把酒盅貼在嘴上,一揚脖子,那盅熱酒全進了
喉嚨。他放下酒盅,咂咂嘴,哈了一口氣。
「有本事你和人家李兆連明著來,你做什麼日弄人家的牲口?」楊明善說。
「我日李兆連他先人哩!我日弄他家的牲口!」胡為說。
「李兆連說你把他家的牲口放跑了,」楊明善說,「你聽,李兆連家的長工滿
河灘吆喝著尋找牲口哩。」
「我聽見了,我就是聽見了我才熱酒喝哩。我管毬他,我沒放他家的牲口。」
胡為說。
「李兆連說是你放的。」
「他愛說他說去,我沒放。這是報應,他砸了我家櫃檯,這是報應。他家的牲
口全跑丟了才好,跑丟了我就熱一老甕酒喝。」
「他要和你唱火炮戲!」楊明善說。
「嫖客日的放他家牲口。」胡為說。
「李兆連把長工佃戶都叫到他家裡了,在石頭上磨刀子哩。」楊明善說。
胡為不喝酒了,他覺得事情有些不對頭,他把眼睛瞪成了兩個酒盅,臉上的皮
肉顫著,顫著。他突然從地上跳了起來。
「他李兆連欺侮人哩!他憑著他有長工有佃戶欺侮人哩!」他說。
「我沒放他家的牲口!婊子養的放他家的牲口!」他說。
「那你給他說去。」楊明善說。
「我不說!我胡為的玩貨在我胡為的大腿根長著哩,軟硬由我自己。」
胡為搶開胳膊,把手裡的酒盅朝牆壁上摔過去,一聲短促的碎裂聲,酒盅變成
了許多瓷片。胡為的鼻尖和耳朵也變紅了。
「火炮戲就火炮戲,我沒長工沒佃戶可我能叫鎮上的光棍地痞二流子。他李兆
連磨刀子,我就磨鐮!」胡為說。
楊明善沒想到胡為會突然變臉,他看見胡為像一隻憤怒的公貓,從門裡跳了出
去。
「差矣!」楊明善說。
「日他媽,弄!」胡為說。
人真是怪物,說起性就起性了。胡為動了真格的。沒多大工夫,二十多個光棍
地痞二流子就聚進了當鋪掌櫃胡力的家。胡為神氣得像個將軍。
六
光棍地痞二流子們推舉出一個叫稀泥的人當他們的頭目,稀泥聽胡為的,他們
聽稀泥的,免得打起來的時候亂陣腳。他們每人手裡真提著一把鐮刀,在院子裡喊
叫著,一臉好事的神情。
「稀泥,問掌櫃的怎麼個弄法。」
「要弄就乾脆些。」
「把人弄死了誰承擔?」
「好,我給咱問去,你們等著。」稀泥說。
稀泥進了胡為的屋子,眼睛直勾勾看著胡為。「弟兄們等你說話哩。」他說。
「磨鐮!」胡為說。
稀泥把脖子伸出門外,朝院子裡喊了一聲:「掌櫃的說了,磨鐮
「進來一個撂倒一個。」胡為說。
「進一個撂一個——。」稀泥說。
光棍地痞二流子們吆喝著紛紛尋找石頭瓦片,一會兒,院子裡就響起了一陣酣
暢的磨鐮聲。事情鬧大了。
胡為突然有些後悔了。他本來沒想把事情鬧這麼大,只是和楊明善攆話,攆出
了一肚子火氣。院子裡吆喝聲和磨鐮聲不時從窗口灌進來,塞滿了他的耳朵。他不
時地朝院子裡看一眼,他想他實在有些冤枉,不知是哪個龜孫兒子放了李兆連家的
牲口,早不放晚不放,偏偏在李兆連砸了當鋪櫃檯的時候放。他想他得給院子裡的
那夥光棍地痞二流子們管飯,還要發兩塊大洋,要是打死一個兩個,還要辦後事。
他越想越覺得後悔。他想人日他媽說不定什麼時候就會碰上倒黴事,人倒黴的時候
喝涼水也會中毒。他心裡亂極了。他想打退堂鼓,想讓光棍地痞二流子們各回各家。
他想李兆連他娘的一定是吃錯了藥,他想咬李兆連一口;他想他只能有尿沒尿撐住
尿了。
「李兆連,你驢日的把我害苦了。」他對著牆壁這麼說了一句,他一肚子晦氣
怨氣恨氣。
「日他媽磨鐮!」他說。
「進來一個撂倒一個。」他說。
「往脖子上擼!」他說。
他踩著摔碎的酒盅碴兒走了幾個來回。他聽見光棍地痞二流子們提著磨利的鐮
刀湧到前院去了。他抬起腳,在他溫酒的小火爐上踢了一腳,然後,倒在炕上睡著
了。稀泥撞開門喊他起來的時候已是傍晚的光景了。
「來了!」稀泥說。
他呼一聲從坑上直了起來,他看見稀泥的臉上沒了一點血色。
「你狗日的害怕了!」他說。
「來了!」稀泥說。
他跟著稀泥跑進前院。他看見光棍地痞二流子們緊攥著鐮刀,眼睛圓嘟嘟睜著,
從大門裡往外瞅著。
「來了?」他問。
「來了。」有人說。
他聽見一陣牲口的蹄腳聲。
「進來一個撂倒一個。」她說。
他看見一頭牲口從他家門口的街上走了過去。又一頭。又一頭。牲口們排著隊,
搖著尾巴。李兆連家的一夥長工跟在牲口隊的後邊,一邊走一邊說著笑話,很輕鬆
的樣子。
他們把牲口找回來了。
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
光棍地痞二流子們空緊張了一陣,他們你看我我看你,互相看著,一臉迷茫的
神色。後來,他們就把目光放在了胡為的臉上。
胡為長長地出了一口氣。「楊明善把我哄了,」他說,「楊明善說李兆連讓長
工們磨刀子,要和我唱火炮戲。」
光棍地痞二流子們把攥濕的鐮把兒別進腰裡,等著胡為說一句他們想聽的話。
「回,你們都回家,這裡沒事了。」胡為說。
他們沒有走的意思。他們看著稀泥。
稀泥給胡為笑了一下。
「日他的,害我們等了整整一天。」稀泥說。他又笑了一下。
「就是,日他的,你們回。」胡為說。
「你看這……工錢。」稀泥說。
「楊明善把我哄了。」胡為說。
「哄是哄了,可工錢……」稀泥說,「人說不定什麼時候就會遇點麻煩事,你
說是不?」他把頭轉向他的同夥們:「你們說,是不?」
「是,當然,」胡為說,「看你稀泥說的,我胡為還能做虧人的事
他看著稀泥他們每人拿著兩塊銀元走了。他在那只火爐上又踢了一腳,他聽見
火爐呻吟了一聲。他飛快地抖抖腳,他用的勁大了些,踢疼了腳趾頭。然後,他讓
夥計把碎的酒盅碴兒掃出去,他覺得它們惹眼。他想李兆連要是一個酒盅就好了,
他就把李兆連摔碎,摔成瓷碴碴,然後掃出去,扔在城壕裡。李兆連偏偏不是酒盅。
他想他說不定什麼時候會捏死李兆連。他想像著他的手掐在李兆連脖子上的情景,
李兆連蹬著腿,李兆連的眼珠子鼓著鼓著就從眼眶裡蹦出來,掉在鼻子兩邊,像兩
個軟軟的麻雀蛋。他想那時候他什麼話也不說,咬住牙往手指頭上用勁就行了。他
把他捏人的情景想得很疹人。他出了一頭汗。人想這種事的時候,渾身都用著力氣。
「他驢熊哄了我。」他又想起了楊明善。他想他再見到楊明善就給他臉上吐一
口。
楊明善沒有說錯。地主李兆連真讓人磨了幾把刀子,他說如果找不回牲口他就
割當鋪掌櫃胡為的耳朵。他一直守在馬房的院子裡,等著牲口的消息。
「胡為說牲口不是他放的。」楊明善說。
「我不管。」李兆連說。
「人不能這麼弄事。」楊明善說。
「少一頭牲口我也和他弄事。」李兆連說。
牲口們一頭接一頭回來了,李兆連氣消了大半。牲口們沒跑遠。
「你看,牲口找回來了。」楊明善說。
「一頭不少。」長工說。
「胡為叫了一屋光棍漢,是些不要命的貨。」楊明善說。
李兆連看著長工們給牲口飲水,拌草,然後,又聽了一陣牲口嚼草的聲音。
「算了,牲口都回來了那就算了。」李兆連說。他出了馬房院子,進了家門。
「算了。」他給跟過來的楊明善說。
李兆連把門關上了。
楊明善以為李兆連會留他吃晚飯,李兆連把門一關,他才知道他想錯了。他聽
見他肚子裡有一種咕咕的響聲。
「日他媽人越富越貪。」他說。
他順著街道來到當鋪家門口,他想進去看看,搖搖門,也關了。
「日他媽人……」
天黑了,街道上一隻狗也看不見。他回到家,摸進廚房,吃了一碗涼水泡饃。
他感到那些被水浸泡過的饃在肚子化開來,變成了一股又一股熱乎乎的東西,順著
他的身子流開去,流過胳膊和腿,一直流到指頭梢。他感到他很快就有了力氣。他
貓一樣跳上炕,鑽進被窩,抓住了他女人胸脯上那兩個百捏不厭的肉葫蘆。女人睜
開眼看看他,又閉上眼,嘴裡發出一聲聲輕微的呻喚。他伸開一條腿,順著女人的
肚子搭過去。
「日他媽還是自己的女人好。」他想。
七
棺材鋪老闆楊明遠從來沒這麼揹運過。他不太喝茶水了。他常常坐在那把黑木
椅子裡,看著做棺材的夥計們發呆。夥計們做工的熱情已明顯不如以前。有幾口棺
材已經做好,整齊地排列在工房裡,散發著一股木香味,直往人心裡去。
他們沒打起來,狗日的。
那天,他又搬出了那把木椅,坐了進去。他看看夥計們,夥計們也看看他,都
沒有吭聲,他們已懶得吭聲了。
「瞿——」使鉋子的夥計在一條木凳上沒滋沒味地刨著,木花從刨眼裡卷出來,
像褲帶。
「哧——哧——」是鋸子切割圓木的聲音。拉鋸的兩個夥計面無表情,身子一
傾一仰地拉著,鋸屑順著鋸齒掉下來,落在他們的腿上,腳上。
「叮,叮叮。」是鑿子。他聽得有些心煩。好多天以來他心裡一直很煩。他想
去鎮街上走走,他甚至想去當鋪和地主家轉轉,他感到他已經沒有耐心等待了。每
天早晚,街道上都會響起李兆連家牲口們上地或下地的蹄腳聲。當鋪門前說不上紅
火,但總有人去典當東西,也不能說冷清。他們沒打起來,他們都平靜地做著他們
各自的事情。他們就這麼不動聲色地折磨著棺材鋪老闆楊明遠。他弟楊明善也有好
長時間不來棺材鋪了。
一進鎮街,楊明遠立刻有了一種掃興的感覺。鎮街上幾乎沒有人影。那時候是
正午,太陽正旺,人們都躲在自家屋裡的晾房裡睡覺歇響。幾隻狗臥在牆根底下的
陰涼處,伸著舌頭喘氣。遠處走過去一個人,一會兒,又走過去一個,一樣無精打
采,好像被太陽曬軟了。他認不出他們是誰。
當鋪的門大開著,被砸倒的門面和櫃檯早已修復起來,兩個夥計正枕著胳膊在
櫃檯上打盹,有一個抬起頭,看了楊明遠一眼,又把頭埋進了胳膊裡。
「如果打起來,也許他們已裝進我的棺材裡了。」楊明遠遠遠看著那兩個夥計
這麼想。他這麼一想,立刻就想起了排列在工房裡的那幾口白木棺材。
狗日的他們沒打。
他來到了李兆連家的馬房院跟前。他從門裡往進瞅了一會兒。一個長工從牲口
棚出來,在大水缸裡提了一桶水,又走進去,把水倒進牲口槽。他能聽見他倒水的
聲音。
他又想起了那幾口白木棺材。
他想他得把他們裝進去,他想他一定要這麼做。他很快走完了兩條街道,從西
城門走出去。他要從城外繞回棺材鋪。
和所有的鎮子一樣,新鎮城牆外也有一圈護城壕。楊明遠就是在護城壕裡看見
地主李兆連的兒子貴貴的。他一看見貴貴,心裡就咯噔響了一聲。他以為他花眼了。
陽光太旺的時候,人頭腦發熱,眼光容易繚亂。他搖搖頭,仔細看了看:是貴貴。
貴貴在城壕的群坎上刨一種叫做小棒槌的東西吃。
他想和貴貴說幾句話。他突然產生了這種欲望。他叫了一聲貴貴,朝貴貴走過
去。
「貴貴」
貴貴沒有抬頭,繼續用手指頭在土裡剜著。
「貴貴,你不和我家坎子玩了?」
「我媽不讓我和別家的娃們玩。」貴貴說。
「你的牛牛好了?」楊明遠蹲下來,朝貴貴跟前湊了湊。
「我媽不讓人動我的牛牛。」貴貴說。
「我不動。」楊明遠說。
「我剜小棒槌哩。」貴貴說。
「你剜,你剜你的。」楊明遠說。他扭著脖子朝周圍看了一圈,狗大個人影也
沒有。
「你一個人出來了?」他問貴貴,他看著貴貴剜土的手指頭。
「嗯。」貴貴說。
「唰——」貴貴剜著。
「唰——」
貴貴的手指頭像蟲蟲一樣,在土裡伸屈扭動著。貴貴剜土的聲音很大。楊明遠
咽了一口唾沫。他感到貴貴剜士的聲音正壓迫著他。
「唰——」
他感到胸口憋得慌。貴貴剜土的聲音越來越響,越來越急。
「唰——」
他又一次想起了那幾口白木棺材。他的手朝貴貴的脖子伸過去。
「我先把這小狗日的裝進去。」他說。
貴貴沒聽清他說什麼,想扭過頭來。他沒讓貴貴扭,他掐住了貴貴的脖子,把
貴貴的頭塞進了土窩裡。他感到貴貴的脖子一下一下鼓著,好像要咳嗽一樣,他給
手上加了點力氣。貴貴到底沒咳嗽出來。貴貴的手被壓在了身子底下,貴貴只能蹬
腿。貴貴使勁蹬著,蹬掉了一隻鞋,腳趾頭弓著,努力往土裡摳進去。後來,貴貴
的身子發冷似的猛抖了一陣,抖出了一泡尿水,就一動不動了。
他鬆開手,他感到他身子裡的血急劇地向他的手指頭上湧過去。他抬起頭朝天
上看了一眼。他坐在貴貴身邊,等貴貴的身體一點一點涼下來,然後,他撿起貴貴
蹬掉的那只鞋給貴貴穿好。他感到時辰差不多了。
他抱起貴貴的屍體,朝鎮子裡邊走進去。他想他必須這麼做。他一直走到地主
李兆連家門口,一腳踢開了門。
「兆連!」他叫了一聲。
他站在院子裡,等李兆連出來。
「兆連!」
他聽見了一陣呱嘰呱嘰的聲音。李兆連拖著鞋從屋裡走出來,站在階上朝他這
裡看著。李兆連看了好大一會兒,才看出他懷裡抱的是貴貴,他以為貴貴在哪兒睡
著了。
「不讓他狗熊出去,他偏要出去,睡著了得是?」李兆連說。
「你狗日的睜眼看看!」楊明遠說,「有人把他掐死了!」
李兆連的身子硬在了臺階上,然後,李兆連就像鷂子一樣朝楊明遠撲了過來。
「貴貴!」李兆連慘叫了一聲。
「我的兒啊!」李兆連的聲音像被風撕開的布條。
李兆連的女人穿著一件薄綢衫,出門沒走幾步,就像掉進水裡一樣,胳膊揚了
揚,搖晃著軟了下去。
後來,李兆連家門裡門外湧滿了人,屋裡屋外亂成了一鍋粥。有人在上房廳裡
支了一架木板床,把貴貴放了上去。李兆連的女人被抬進了裡屋,幾個女人在她身
上搓著,揉著,用指甲掐著人中,想讓她呼出一口氣來。李兆連坐在臺階上,眼睛
直直地看著前面,沒有人敢動他,敢和他說話。
「啊,啊——」裡屋的女人終於呼出氣來了,然後是一長串悲痛欲絕的哭嚎聲:
「哎嗨嗨嗨嗨……」
「啊,啊,」李兆連受了感染似的,脖子一揚一揚,人們以為他的喉嚨裡堵了
一口痰,都緊張地看著他,等著他把那口痰吐出來。
「啊——」李兆連拖長腔叫了一聲。人們看見兩股眼淚水從他乾巴巴的眼窩裡
湧了出來。他喉嚨裡沒有疾。
「我就這麼一個兒啊!」李兆連說。
「可憐死了。」人們說。
「我娶了三個女人,我四十歲才有這麼一個兒啊……」李兆連說。
李兆連的腔調像唱歌一樣。
八
棺材鋪老闆領著兩個夥計,把一口白木棺材抬進了地主李兆連的家。他勸說了
李兆連幾句。李兆連像霜打了一樣。
「人死不能復活,給貴貴辦後事要緊。」楊明遠說,「棺材錢我不要,貴貴死
得太可憐了,那麼小點年紀,還不懂世事哩。」
李兆連家又響起了一陣悲痛的哭聲。哭聲小一點的時候,楊明遠又感歎了一句:
「大人的事有大人在嘛,狗日的對小孩子下這黑手。」
有人給楊明遠端來茶,楊明遠不喝,他看著李兆連紅腫的眼窩說:「我不喝了,
你家裡有事,我走呀。」
「走。」他給兩個夥計說。
這時候,楊明善在棺材鋪裡正等著他哥楊明遠。楊明遠一進門,就看見楊明善
坐在他的那把黑木椅裡,一臉怪眉怪眼的神氣。
「大清早你來做甚?」楊明遠說,「你坐在我的椅子上像個人一樣。」
楊明善不說話。楊明善朝他哥撲閃著眼睛。
「啪嘰啪嘰。」
「看我做甚?看我不認識我?」楊明遠說。
「你掐死了貴貴!」楊明善突然說了一句。
那天早上,他女人端屎盆去豬圈倒尿,剛進去就叫了一聲:「豬死了!」他沒
聽清,女人又喊了一聲:「豬死了!」他慌慌失失跑進豬圈,看見糞堆頂上躺著一
只死豬崽。
「看你大聲野氣的,死了一個我以為全死了。」他說。他感到女人太有些大驚
小怪了。「一窩十幾個豬崽還能不死一個兩個?」他說。
「你快把它埋了去我看不得死豬。」女人說。
「埋糞堆裡得了,漚糞。」他說。
「不成不成我一進豬圈就想糞堆裡有死豬我害怕。」女人說。「你不想讓我屙
屎尿尿了,得是?」
「那就埋咱的樹根底下,樹能長旺。」他說。
女人叫得更急了:「不成不成晚上我睡不著你不想讓我睡覺得是?去,埋城壕
裡去。」
他同意了,可他不同意現在就去。他說不急不急吃了飯去,我走到城拐角手一
掄就會把它掄到城壕裡,你去做飯。
他還沒掄,就看見了他哥掐死貴貴的情景。他被他看見的那一幕嚇壞了。他趴
在一個樹坑裡一直看完了整個過程。他感到他大腿上的肉像遭蟲蛀一樣。他張著眼
窩一動不動,一直看著他哥楊明遠抱著貴貴的屍體進了鎮子。他坐在樹坑裡揉了好
大一會兒眼睛。他攥著拳頭在頭頂上砸了一下,又伸開巴掌在臉上搧了一下,他才
知道他不是在做夢。然後,他走到他哥掐死貴貴的地方看了一會兒。他看見了幾截
小棒槌和一堆零亂的濕土。
「呀咦!」他咬著牙從喉嚨裡擠出來一聲短促的怪叫。
他感到他不是在跑,而是在飄。他從他家門裡飄了進去,眼睛直直地看著他女
人。女人光著上身,正在屋簷底下陰處洗脖子。女人一眼就看見了他手裡提著的那
只死豬崽。女人的眼睛也直了。
「你沒扔?」
女人的濕手停在脖子上,一股髒水從她的指縫裡流下來,又順著奶頭之間的肉
溝裡流了下去。
「呀咦!」他又擠出了一聲。
他飄到水缸跟前,一頭紮進去,使勁吹了起來,水缸裡響起了一陣激烈的水泡
聲。女人一臉迷惑,鵝一樣伸著脖子,看看他蹶起的屁股,又看看扔在院子裡的死
豬。
「這囗人瘋了。」女人說。
他從水缸裡拔出頭來,使勁搖了幾下,搖出了一圈水花。
「呀咦!」
女人看見他從屋門裡奔了進去。
「瘋了。」女人說。
女人沒理他,繼續洗她的脖子。女人倒髒水的時候又看見了那頭死豬。死豬躺
在陽光裡,很惹眼。她想她一定得讓他把死豬扔到城壕裡去。
她進屋一看,才感到事情有些麻煩。她看見楊明善像死了一樣,平展展躺在炕
上,眼睛和嘴大張著。女人慌了,她在楊明善的額顱上摸了摸。
「你病了。」女人說。
「難怪,這麼熱的天,你病了。」女人說。
楊明善平展展一直躺到晚上。女人給他做了兩大碗飴饣各面,他吃得通體冒汗。
然後,他在院子裡轉了好長時間,然後,又躺在了炕上。他的臉從來沒這麼嚴肅過,
嚴肅得像一堵牆。他感到他臉上的汗毛像操練的士兵一樣,噌噌噌倒了,又噌噌噌
豎了起來。女人守在他跟前,不時在他的額顱上摸一下。
「可憐的人。」女人說。
「你看,眼睜睜瘦了一圈。」女人說。
早上一醒來,他就提著院子裡的那只死豬崽出了門,很輕鬆地把它搶進了城壕
裡。後來,他就坐在了他哥楊明遠的那把黑木椅子裡。
「你掐死了貴貴。」他說。
「我沒有。」他哥說。
「我看見了。」他說。
「我的棺材不能白做。」他哥說。
「是你掐死了他。我要給人說。」
「起來,你起來,你坐在我的椅子上像個人一樣。」他哥說。
「起來就起來。總有一天我會給人說。」
「沒人信你的話。」他哥說。
「土匪。」他說。
「我不過想賣幾口棺材。」他哥說。
「看麼。」他說。
「看麼。」他哥說。
這回,他哥沒讓夥計給他喂豬屎。
九
老闆楊明遠又開始喝茶了。他到當鋪掌櫃胡為家去的時候就端著那把泥壺,邊
走邊往嘴裡灌著茶水。胡為坐在涼房底下搖著扇子。他多少有些詫異,楊明遠從來
沒來過當鋪,可他往進走的時候就像進他自己的家一樣,搖搖擺擺就進來了。楊明
遠一落座,就說了一句讓胡為瞪眼睛的話。
「胡掌櫃,你做得也太蓋不過眼了?」楊明遠這麼說。
「什麼我做得蓋不過眼。」胡為說,「你這人真怪,到我家來給我說這話。」
「李兆連家貴貴死了。」楊明遠說。
「死了死了去。」胡為說。
「他們說是你掐死的。」楊明遠說。
胡為急眼了。他已聽到了一些風言風語,他最怕人說這句話。
「扯他媽的閑蛋!」胡力說。
「鎮上人都這麼說哩。」楊明遠說,「你說過你要殺李兆連全家的話,得是?」
胡為的喉嚨像塞了半截胡蘿蔔,喉節滑著沿著,半晌沒說出話來。楊明遠的話
太噎人了。楊明遠神裡怪氣地看著胡為。
「我說是說過,那時候我在氣頭上,可我沒殺。」胡為說。
「你看你看,這事非鬧大不可。」楊明遠說,「你怎麼能說殺人家全家的話。」
「那天中午我一直在家裡睡覺,你知道天一熱人就害瞌睡,我在我家炕上掐他
家貴貴?」胡為說。
「你看你看。」楊明遠說。
「我說過我要殺他家全家,可我沒說我要掐他家貴貴。」胡為說。
「你看你看。」楊明遠說。
「你老說你看你看,你說這話是什麼意思?我不想聽你這話。」胡為心裡發毛
了。
「你看你看。」楊明遠說。
「你說我掐死貴貴了?我告訴你,我沒掐。我為什麼要掐死他家貴貴?」胡為
說。
「這話你得給李兆連說去。」楊明遠說。
「我不去,我不說,你走,我不想和你說這些話。」胡為說。
「我知道你心裡亂。」楊明遠說。
「我不亂。」胡為說。
楊明遠一走,胡為就坐不住了,他像吃了蒼蠅一樣。他發現這幾天鎮上的人一
直用一種怪異的目光看他,當鋪的夥計們總背著他竊竊私語。他想他一定要和李兆
連說清楚,他想他和李兆連不說清楚他心裡憋得慌,他睡不踏實。這可不是捏腫牛
牛,這是人命關天的事。那天吃罷晚飯,他提了幾盒燒紙去了李兆連家。
李兆連家的院子裡掛著一盞汽燈,亮得耀眼。貴貴已經入殮。那只白木棺材上
了油漆,停放在一個竹箔搭起的棚裡,棚裡設了靈堂,點著幾排蠟燭,看樣子,地
主李兆連要大張旗鼓地給他兒子貴貴辦喪事。
送燒紙的人很多,他們排著隊,一個執事的人在方桌上登記禮單。胡為一聲沒
吭,悄悄跟在隊伍後邊。
有人看見胡為了。
「我給貴貴送幾盒燒紙。」胡為說。他感到他頭上正在冒汗。他在額顱上抹了
一把。
「天真熱。」他說。他覺得在這種境地裡說什麼話都不合適,他恨不得地上裂
開一條縫,讓他縮進去,他想為人不做虧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門,可有時候人不做
虧心事鬼偏偏要來敲你的門。
「胡掌櫃來了!」有人喊了一聲。
胡為的身子顫了一下。他看見院子裡的人都把頭朝他扭過來,他們好像看見一
只狼。胡為在額顱上又抹了一把。「呵,呵呵。」他給他們做了一個笑模樣,揚揚
手裡的那幾盒燒紙,「我給貴貴送幾盒燒紙。」他說。
登記禮單的人從二門裡跑進去,一會兒又跑了出來。
「東家不讓收你的燒紙。」那人說。
胡為急了:「為什麼不收我的?我不是新鎮的人,得是?」
「東家讓你回去。」那人說。
「我不回,我和你東家有話說。」
「東家說等辦完喪事他和你慢慢說。」
胡為傻眼了,院子裡沒有一個人說話,只有汽燈發出的那種噝噝聲。
「貴貴不是我弄死的!」胡為突然說了一句。胡為的臉憋得漲紅。
「這裡正辦喪事,你甭打攪。去,把他攙出去。」
兩個人朝胡為走過來,攙住了胡為的胳膊。
「那天中午我在家睡覺,我能在我家炕上掐死貴貴?」胡為說。兩個人攙著胡
力的胳膊往外走,他們把胡為扔在門外,「咣」一聲插上了門關。
「李兆連你聽著!」胡為把頭仰在脊背上,朝天上吼著,「我沒弄死你家貴貴!」
胡為低著頭想了一會兒,又抬起頭。
「李兆連,你想弄事咱就弄,我胡為日他媽豁出去了!」他說。
胡為把那盒燒紙扔在了街道上。他搖晃著往回走,長長的鎮街上響著胡為的腳
步聲。他沒想到事情會弄到這種地步。他想他說不清楚了,他想他就是說爛舌頭李
兆連也不會相信。滿世界的人都說貴貴是我胡為掐死的,那一定就是我胡為掐死的,
人舌頭上有毒哩,人能把假的說成真的,人真他媽的不是東西。他恨死了李兆連。
他想一腳把這個鎮子踢翻。他真踢了一腳,鎮子一動沒動,他沒踢翻它,他踢起了
鎮街上的幾片樹葉。
後來,他去了稀泥家。
「我說不清楚了,我也不想說了,我要留一手。」他給稀泥說,「你把你那夥
人叫到我家來,我一天給你們三塊銀洋。」
光棍漢稀泥在胡為肩膀上拍了一巴掌:「人活一口氣,人不能當孫子。」
「就是就是。」胡為像遇到了知己一樣。一會兒,他就把心裡的煩惱一掃而光
了。
那時候,棺材鋪的鉋子、鑿子、斧子聲響得正歡,又有幾口白木棺材做好了。
「就這麼弄,」楊明遠給夥計們說,「到時候把棺材抬到街上去。」
十
地主李兆連不露聲色地給他兒貴貴辦著喪事。他好像忘記了貴貴是怎麼死的。
他好像給他兒貴貴做生日一樣。他很捨得花錢。他甚至親手做一些具體的事情。他
不像幾天前那麼悲痛傷心了。他雖然不太說話,但臉上偶爾會出現一點笑容。他一
句也沒說起過當鋪掌櫃胡為。幾個長工用憂慮的口吻給他說胡為又把鎮上的光棍地
痞二流子叫到當鋪商量事情的時候,他也沒有吭聲,他甚至連頭也沒抬,依舊做著
手裡的事情。人們對這個長得有些文弱的地主投注了巨大的同情,他們不時地朝這
個穿著白布褂的不幸的男人臉上看一眼,他們總覺得他肚子裡埋著一顆炸彈。他們
賣力地為他忙碌著。
「看著麼。」他們私下這麼說。
「看著麼。」他們說。
一隊和尚敲著木魚在停放棺材的棚子裡整整念了一天經文。李兆連坐在旁邊聽
他們念,他聽得很認真,他把兩隻胳膊交叉著放在膝蓋上,把頭放在胳膊中間,一
動不動地看著那些唔唔啦啦的和尚。
「你看,他眼珠子動也不動。」人們說。
後來又來了一隊樂人,在李兆連家整整吹了一天。人們看見李兆連和前一天一
樣。把下巴頦放在胳膊上聽樂人們唱「祭靈」:
營帳外三軍齊掛孝
白人白馬白旗號……
他們一直唱到夜深人靜的時候。樂人們收拾傢伙準備歇息了。人們看見李兆連
不聲不響進了他和他女人睡覺的那間屋子。這些天,李兆連的女人一直躺在炕上,
沒有出門。
女人明顯瘦了。女人的眼眶裡沒有水份。女人總乾巴巴地看他。他坐在炕沿上,
拉住女人的一隻手。他想給女人說明天一大早就起喪,可他沒說。
「你給我再生一個兒子。」他這麼說。
他看見女人的眼眶裡有了些水一樣的東西,好像不是自己流出來的,而是別人
給裡邊滴進去的。
「我生不成了。」女人說,「我傷心透了。」
「叭嘰」一聲,「叭嘰」又一聲,他退掉了兩隻鞋,從女人身上爬過去,挨著
女人睡了。他們再沒說一句話。
所有的佃戶和長工以及李家戶族的男男女女都參加了貴貴的葬禮。他們把那口
棺材放進墓坑,用土填起來,給那裡堆了一個墳堆。嗩呐聲在黎明的空氣裡歡樂地
叫著。李兆連沒有動手,他一直站在旁邊看著。墳堆堆起來的時候,噴呐聲嘎然而
止。李兆連把一張白紙放在墳堆頂上,壓好。人們把鐵鍁放到肩膀上,要回家了。
「等等。」李兆連留住了他們。人們看李兆連的臉紅得像女人的指頭蛋。
「你們都看見了,」李兆連站在他兒貴貴的墳堆跟前給人們說,「我李兆連沒
兒了,我李兆連快五十歲的人沒兒了。」
人們把鐵鍁插進土裡,屏心靜氣地聽李兆連說話。
「我李兆連就是有三十萬的過活沒人接香火半個錢的事也不頂。我李兆連對不
起李家的先人。」李兆連說。
「我要弄一場事。」他說,「我要和當鋪掌櫃胡為抗戰到底。我要把胡力的皮
扒下來扔在房頂上讓太陽曬乾。」李兆連咽了一口唾沫,繼續說,「長工伯戶你們
聽著,我把話說在明處,跟我幹的,我李兆連給他好吃好喝,打死了我給他買柏木
棺材做壽衣唱大戲給他送終,不願跟我幹的,就甭在我家裡幹活,甭種我李兆連的
地,就這。」
李兆連一甩袖子走了。
「哦!」人們叫了一聲。
「噢!」他們看著李兆連的背影。
那天晚上,地主李兆連在他家上房廳裡擺了一桌酒菜,請來李家戶族的幾位長
者。他覺得這是大事情,他得和他們通通氣,也許他們還能給他出些好主意。一杯
酒上去,幾位長者就心火上攻了。
「要弄事就往大的弄,弄出氣派來。」他們濺著唾沫星子給李兆連說。
他們確實想出了一個好主意。
「打兵器。」他們說。「大刀,長矛。」
他們覺得這主意不錯,並為此激動了一會兒。「每人發一把刀,或者長矛。」
他們說。
事情就這麼定了。幾天以後,人們看見李兆連家的大門口,支起了兩個鐵匠爐。
李兆連家的長工套了一輛馬車,從縣城請來了兩位打鐵的高手,他們把鐵砧鐵錘鐵
鉗和風箱一類的傢伙從馬車上搬下來,當天就點著了爐火。人們都聽見了鐵匠爐傳
出來的風箱聲和鐵錘撞擊鐵器的聲音。鐵匠爐跟前放著兩口大水缸。
「嗞——」鐵器在水裡發出一聲尖厲的呻吟後,立刻改了顏色。兩位鐵匠的功
夫確實不淺,動作熟練而有力。
鎮長楊明善知道李兆連支起鐵匠爐的消息以後,痛苦得一夜沒有合眼,他下決
心要阻攔這件事。
「這麼大的事你不和我商量?」他問李兆連,「嗯?」
「去,弄你自個的事去。」李兆連說。
「你不能這麼弄,這麼弄要死人。」楊明善說,「我雖然毬不頂,可好壞也算
個鎮長。」他說,「我不能眼看著鎮上死人。」
「貴貴已經死了。」李兆連說。
「你知道是胡為掐死了貴貴?」
「我不管,我就知道貴貴死了,我沒兒了。」李兆連說。
「這事裡有鬼。」
「有鬼沒鬼我不管,我就認准他當鋪掌櫃胡為。」李兆連說。
「我不能讓你支鐵匠爐,」楊明善說,「你把爐子拆了,讓鐵匠回去。你嫌話
不好說我去說,我讓他們走。」
「小心鐵匠把你做了。」李兆連說。
「哎!」楊明善在鐵匠爐跟前喊了一聲,「你們趕緊把爐子拆了,回你們縣城
去。」
鐵匠從爐堂裡夾出一件燒紅的鐵器,在楊明善鼻子底下晃了晃。楊明善朝後退
了兩步,說:「小心你手裡的東西,那可是燒紅的。」鐵匠沒吭聲,朝鎮街那頭指
了指。楊明善不明白鐵匠的意思,啪嘰啪嘰眨了一陣眼。鐵匠又指了指,楊明善這
才看見當鋪掌櫃胡為家門口,也支起了兩座鐵匠爐,兩個夥計正賣力地拉著風箱。
楊明善不眨眼了。
「亂套了。」他咕噥了一聲。
「他們瘋了!」他說。
胡為一見楊明善,就做出一副嬉皮笑臉的模樣。楊明善說:「你看你,還笑哩。」
「我說不清了,」胡為說,「這不怪我。」
「不怪你,不怪你把事情越弄越大了。你不動,看他李兆連能把你怎麼樣!」
楊明善說。
「你說的,李兆連扒我的皮不執你的,看你說的。」胡為說。「我還有好玩貨
哩。稀泥你過來,讓鎮長看看。」
稀泥和幾個光棍漢正擺弄著幾支火槍。
「啊!」楊明善叫了一聲。
「我花銀子從土匪手裡買的。」胡為說。
「噢!」楊明善又叫一聲,他用手捂住臉,痛苦地蹲了下去。
「當,叮叮;當,叮叮。」兩家的鐵匠像比賽一樣。
「嗞嗞。」是鐵器淬火的聲音。
新鎮彌漫著一種死亡的氣息。人們站在遠處,恐懼地看著鐵匠們手中燒紅的鐵
器。
「只要給錢,什麼樣的玩貨咱都能打。」李兆連家的鐵匠說。
「就是就是。」胡為家的鐵匠說。
許多住戶已悄悄地棄家遠去。
「當,叮叮;當,叮叮。」
「當——」
十一
那場痛快淋漓的打鬥是從黎明開始的。
「哐!」李兆連家的門打開了。
「哐!」胡為家的門打開了。
他們像商量過一樣。他們扛著嶄新的鐵器,潮水一樣從門裡湧出來,在馬道裡
相遇了。他們沒有急著開打。他們像兩群鱉一樣互相瞅著。黎明裡響起了一陣緊張
的喘氣聲。
「動手吧。」李兆連看著胡為說。
「動手吧。」胡為看著李兆連說。
鎮長楊明善從他家門裡跳出來。
「不能動手!」他失眉吊眼地喊了一聲。他滿臉噴紅,站在兩支隊伍中間。
「把他扔進去。」李兆連給長工說。
兩個長工走到楊明善跟前,把他抬起來,從門裡扔了進去。楊明善的女人不知
道外邊發生了什麼事,剛一探頭就叫了一聲爹,飛快地關上了門。楊明善爬起來,
還要出去,女人一把揪住了他的耳朵。
「沒看見他們拿著刀?」女人說。
「我要出去!」楊明善說,「你把我的耳朵揪疼了。」
女人不理他。女人抿著嘴,把他揪進了屋。
一個長工突然發現了稀泥手裡的火槍,他擠到李兆連跟前說:「他們有火槍哩,
你看。」李兆連說:「甭吭聲。」「火槍。」長工又說了一句。李兆連說:「顧不
得了。」
這時候,他們聽見一陣腳步聲。他們看見棺材鋪的夥計們抬著十幾口白木棺材
從鎮街口走了過來,在街道邊上整齊地排列成一排。楊明遠端著那把泥壺,坐在一
口棺材蓋上,朝馬道裡看著,他兒坎子扒在他爹的脊背上。
「他們唱戲哩,得是?」坎子問他爹。
「噢麼。」他爹說。
楊明善把女人美美地捶了一頓,他從女人的褲腰上抽下那條線褲帶,把她綁在
櫃腿上。女人老實了許多,他搬來一架木梯,爬上了他家的屋頂。他激動地在屋頂
上走了幾個來回,踏得瓦片梆梆響。
他一眼就看見了他哥楊明遠。
「就是他!」他指著他哥喊了一聲。
「就是他!」他又喊了一聲。
沒有人聽懂楊明善的話。光棍稀泥覺得楊明善有些討厭,便舉起火槍,朝楊明
善瞄了瞄。「叭」一聲,槍響了,楊明善一個前撲,扒在屋頂上,直著眼瞪著稀泥。
「他狗日的想打死我。」他說。
他順牆溜了下去,再也沒有露面。
稀泥的槍聲使所有的人都嚇了一跳,他們感到渾身的血突然停止了流動,又突
然在他們的身子裡奔跑起來,沖上了他們的臉。他們的頭髮像公雞毛一樣燥了,硬
了。
「砍了!」有人喊了一聲。
「嗷——」李兆連的長工和伯戶們叫喊著朝胡力的隊伍沖了過來。
「叭——」又一支火槍響了,鐵屑像無數個豌豆一樣從槍口噴射而出。跑在最
前邊的幾個長工踉蹌著栽倒了。李兆連猛地捂住臉,短促地叫了一聲。
「我的眼睛瞎了。」他說。
他彎曲著跪了下去。紅了眼的長工伯戶們從他的身邊呼嘯而過,勾倒了他。他
感到有一隻腳踩在了他的肋骨上,又一隻腳。他聽見了一陣肋骨斷裂的響聲。他沒
想到會死得這麼快,也沒想到他會這麼死。
馬道裡嘩啦啦一片鐵器戳穿肉體的聲音。一個光棍漢舉起砍刀朝一個長工砍過
去,「噗」一聲,砍刀深深切人了頭骨。光棍漢樂了。他感到砍刀砍透頭骨的聲音
和砍透水葫蘆差不多。他張開嘴,想笑一聲,一柄梭標從他的後背心戳了進來,他
很快又有了另一種感受。他感到梭標激進肉裡和把冰塊吃進喉嚨裡一樣,都有一種
涼嗖嗖的感覺。他沒笑出聲,他吭了一聲,搖晃著歪在了地上,他感到馬道裡的打
鬥聲離他越來越遙遠了。
稀泥蹲在牆根下急得滿頭大汗,他正往火槍裡灌火藥。這會兒他才感到火槍沒
有砍刀和梭標方便。他朝人堆裡看了一眼,他看見許多人已躺倒了,臉上血肉模糊。
他到底裝好了火藥和鐵屑,他想他馬上就可以站起來向人群瞄準。這會兒他又感到
火槍很可愛。「咣」一聲,他的臉上挨了一刀。「咣,」又一刀。他不知道是誰砍
的,兩刀砍得都很准。他沒有站起來。他抱著那杆火槍倒了,肥胖的臉被嚴重地改
變了形狀。
當鋪掌櫃胡力也挨了兩刀,一刀在大腿上,一刀在脖子上,他仰面躺著,好像
長了兩張嘴,上邊的一張嘴泛著青色,下邊的一張正頑皮地吹著氣,不時吹出來一
個又一個粉紅色的血泡。
打鬥進行了整整一個時辰,馬道裡擺滿了屍體。幾個活著的人扔下手裡的鐵器,
瘋了一樣嚎叫著跑出城門。那時候太陽正在上升,陽光優美地穿過空氣,從牆頭斜
射而下,落在馬道裡的那些屍體上,像一群抖動著翅膀的金色蝴蝶。沒有風。血腥
味無聲地盤旋著。
坐在棺材蓋上的楊明遠有些索然寡味了。他感到人殺人並不像他想得那麼好看。
他眯著眼朝馬道裡看著,他知道那些屍體們正在一點一點變涼,變硬。他想像如果
有一具屍體突然坐起來對他開口說話,他就不會感到乏味了,他也許會大吃一驚。
他真大吃了一驚。他看見有個什麼東西在死人堆裡蠕動著。他突然張大了眼睛。
是坎子。
坎子不知什麼時候跑進了死人堆,像兔子一樣跳著,跳過許多屍體,跳到了牆
根底下,那裡是稀泥倒下的地方。坎子看中了稀泥手中的那杆火槍,他搖著,抽著,
把槍從稀泥手裡拔了出來。他不知道火槍為什麼會發出一聲脆響。他親眼看見它放
翻了幾個人,他感到它比砍刀神氣多了。他摸著它,用手指頭摳著。他把一隻眼睛
貼在黑洞洞的槍口上,想看看裡邊是個什麼樣子。
楊明遠突然感到了什麼,他撕心裂肺地喊了一聲:「坎子!」
他聽見了一聲沉悶的槍響,坎子像驚飛的鴿子一樣扇著翅膀,向空中一躍,又
跌了下去。
無數個鐵屑全部從坎子的眼睛裡射了進去,又從腦後飛了出來。火藥熏黑了坎
子的眼眶。
「坎子。」楊明遠跪在他兒坎子跟前叫了一聲,這一聲叫得很輕。
他把目光從坎子的臉上移開,穿過馬道。他看見他的那些白術棺材,它們整齊
地排列在那兒,散發著一股奪人的木香味。
夥計們不見了。
陽光如柱,它永遠都是那種金黃的顏色。
十二
幾天後,楊明遠敲開了他弟楊明善的門。楊明善和他女人正往一輛獨輪車上裝
東西,好像要出遠門的樣子。
「我走呀,」楊明善說,「我不在這兒呆了,你呆著吧。」
東西捆綁好了,女人坐了上去。豬圈裡傳出來一陣豬的哼哼聲。楊明善朝豬圈
那邊看了一眼,手抓起獨輪車把。
「你離開點,讓我過去。」他給他哥說。
楊明遠挪挪腳,靠邊了一些。
「我豬圈裡有一窩豬還活著,你要覺得難受你把它們也弄死算毬了。」楊明善
說。
楊明遠看著他弟推著女人出了門。他知道他弟再也不會回新鎮了。他弟沒有回
頭,也沒給門上掛鎖。
那時候,新鎮已成了空鎮。楊明遠挨家挨戶推著門扇。他好像老了許多。
「收屍啊!」他叫著。
又推開了一扇:
「收屍啊!」
街道很長,遠遠看去,他像一隻螞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