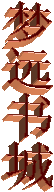
08
兩人總算是一笑言和,然而櫻桃的態度還是謹慎的,在一定程度上,她是一個
沒有依靠的人,她有自己的一套觀念。一失足成千古恨,她得慢慢地觀察——畢竟
就青春而言,她已是一個遲暮的人,她輸不起,除非小陳表明給她看較為優厚的條
件,保證她離開端敬之後的出路,否則她決不輕易付出更大的犧牲。因了這個想法,
櫻桃與小陳之間的關係忽冷忽熱。正在捉摸不定之際,端敬一日卻忽然回來了。
櫻桃接了端敬從車站打來的電話,叫了車一起去接他,一路上頗有些忐忑,但
自忖自己與小陳之間在公共場所頗為檢點,即使有些許風聲吹入端敬耳中,他也找
不出什麼證據。想著又理直氣壯起來。一路上端敬臉色如常,她一顆心才真正放了
下來。
端敬簡單道了一些香港的風土人情,林媽和車夫驚詫不已。櫻桃笑道:「香港
這麼好玩,等打完仗我們搬到香港去住算了,反正這裡也沒什麼勁。」端敬拍拍她
的手笑道:「小孩子氣,這麼性急,聽說好就恨不得馬上飛了去。現在那邊人太多,
都恨不得到大後方來呢。」轉頭含笑注視著櫻桃:「怎麼這裡不好玩麼?我不在的
時候你都幹什麼了,我知道你是懶得寫信的,不然一定懷疑你是不是把我這個孤老
頭子給忘了。」櫻桃心中一跳,臉不由得紅了起來,故意道:「幹什麼去了?陪人
跳舞去了,做壞事去了!」因為心虛,笑得格外高聲些。端敬用手指點點她,佯怒
地瞪了一眼,道:「伶牙利齒。」一番插科打渾,櫻桃才自在過來。
半夜裡櫻桃是被風吹門窗的聲音驚醒的。沒有燈,臥室裡彌漫著夜的氣息,又
像浸在顯影藥水裡,慢慢地顯出家具的輪廓來,迷迷濛濛的夜色像是一種咖啡凝重、
溫吞的氣蘊,伴隨黑白分明的鋼琴聲的凝重的咖啡的氣蘊。櫻桃躺著,聽通往陽臺
的門被風唏溜一下吹開了又輕輕一聲合上了。她這邊剛微一動,忽聽端敬輕道:
「你醒了嗎?」櫻桃應了一聲,端敬續道:「人老了,到時候就睡不著了,把你也
給吵醒了。」櫻桃道:「怕是一路上累著了吧?」端敬道:「說什麼累不累的,慣
了。」語調頗為落寞,櫻桃不禁心中一動。端敬道:「以前也這樣,忽然一件事就
得動身,那時候一個人,也沒什麼交待不交待,拔腿就走……現在不一樣了,在外
老覺得不放心——有個人在家裡等著,在外也就不能安心。」櫻桃笑道:「怎麼會
是一個人呢,以前有夫人、孩子……」她心裡這樣想,順口就講出來了,也忘了
「夫人」是自己平日頂忌諱的。
端敬一伸手替櫻桃掖掖被角,方道:「那不一樣,他們,我是放心的,他們頂
能照顧自己。你不一樣,這裡你孤孤單單一個人,又年輕,件件事情你還不大清楚。
我知道你那個爭強好勝的性兒,得罪了人都不知道。這世道,像我這樣在裡面打了
一輩子滾的人都一不提防就要吃虧呢。」櫻桃難得聽見這貼心貼意、知疼著熱的話,
心下一酸,不覺眼睛都濕了。她枕著的是一種藕合色蘇繡金風凰的枕頭,帶著寬寬
大大的荷葉邊,黑夜裡看不清楚,只有臉頰枕著風凰的輕微的凹凸感,可她知道那
鳳凰一定是濕了,羽毛像是灰敗了一層。人,總要老的,可是像端敬這樣,老得並
不可惡罷,這一點在嫁端敬之前便已知道,只是到現在才發覺,他真是這麼一個細
心的人。她哽咽了兩聲,只是伸手過去隔著被子偎著他。端敬也仿佛受了震動一般
低聲道:「櫻桃,你,你能陪陪我這個老頭子,我,我謝謝你,原來我以為這輩子
真是沒指望了。誰承想,老了竟還能遇見你,竟還能享一點清福……」櫻桃百感交
集,種種事驀地兜上心來,忽然她低聲道:「我們到成都去住一段時間吧。你不是
在那邊有幢小房子嗎?你把這兒的工作擱一擱,你都做了幾十年了,歇一歇吧,我
陪你。」一番道來,卻似早已有計劃的一般。端敬道:「歇,能歇得了多久呀,這
仗……情形看樣子不好。可是,也罷,依了你,等我把這邊的事情安排一下,你也
收拾收拾,你先過去。」櫻桃自忖自己在那邊人生地不熟,諸多不便,因道:「我
們一起走罷,省得你在這,我在那,兩個人都不放心。」端敬沉吟了一下道:「也
好。」
接下來的兩天裡,櫻桃忙著打點行李,三三四四地歸了幾大箱籠,竟不像是度
假。她自嘲:「我是窮過了的人。這世道過了今天不知明天,我可不能胡亂糟蹋東
西。」她現在不怕人家說她了。然而言語行動間總有一股豁出去的狠勁兒,似乎一
個被捆綁的人一下子被松了綁,運動幅度特大,可是腳還是木木的,至於心理上許
久以來的捆綁烙印更是歷歷在目,林媽笑道:「太太,你這手忙腳亂的樣子倒像是
在逃難。」櫻桃在心中震一震,不覺低語道:「不是逃,可是和逃又有什麼分別呢。」
她心中也未始沒有懷疑這一次急於離開重慶與小陳有什麼關連。
櫻桃本不想四處告別,可是小何太太,楊小姐等幾個朋友消息靈通得很,相約
來替櫻桃餞了行。櫻桃暗忖:暫時離了這地方也好,不然,也是危險——不定她們
怎麼對端敬造謠。到一個新的地方,成都,到一個沒有人知道她,知道她身份的地
方,或許……,或許什麼,她自己也是茫然,猜不到的——無論如何,該好一點罷。
可是她知道這希望也是渺茫得很,——從這兒連根拔起,不帶一些泥土,植到一方
完全陌生的土地中去,不帶這兒的一絲氣味,縱然冷漠一些——然而這是不可能的,
端敬做不到,她也做不到。再說,成都畢竟不是遠在千里之外。她討厭她所處的那
個圈子,可是離了它也不行。然而,她仍是懷著這樣一個渺茫的想法。
櫻桃終究還是一個人先去成都。一切準備妥當,車票都已訂好,端敬忽然接到
上海托人帶來的家信,端敬本在英國留學的女兒馨聲近日已回國,將輾轉至重慶來。
端敬一時頗費躊躇,自己成都是去不成了。然而櫻桃呢,馨聲此番到來,父女間必
定有許多話要說,櫻桃夾著其中,一定尷尬。端敬一時覺得在外七年的女兒忽然間
變得生疏起來,他還不知道馨聲會以怎樣挑剔的眼光看她父親的這一段婚姻。他是
一個謹慎的、顧家的男人,一直都是,一個好丈夫,一個好父親,所以他有理由要
分外謹慎些。櫻桃卻也識趣,到了日期,一徑上車先行了。
櫻桃意外地在成都碰見了好幾個在上海時的熟人,鄉音盈耳,張口便是吳音軟
語,這個時候櫻桃卻也安下心來,每日混在幾個熟人裡遊山玩水跳舞看戲。
如此過了兩個星期,櫻桃給端敬去信,但回信全無,櫻桃初時還篤篤定定,打
仗嘛,什麼都不方便,或許他有什麼要緊事要處理。又等了一星期,端敬還是沒信
寄來,櫻桃日日跑到山下的郵局去打聽,總懷疑或許郵局出了什麼差錯。
櫻桃到郵局去的時候,每次都遇見一個瘦瘦的女人,臉龐長長,眼睛是偏近灰
色的,乍一看,像盲人的眼睛,那一種空洞的沒有希望的顏色。肌膚是白的,但那
也是一種不正常的白,令人想起肅穆的醫院裡接近死亡的、閃著手術刀冰涼光澤的
那種白,還有一個胖男人,穿著古銅色綢長衫,他面前的桌子上擺著一副象棋殘局,
一副「天下無敵手」守株待兔的模樣。幾次不期而遇,櫻桃有一種尷尬的感覺,下
次再去的時候,有意和他們分開來。但也有例外的時候,比如現在,櫻桃一腳踏進
郵局,便見他們兩個端端正正地坐在椅子上,嚴肅的神態,不像是在郵局,倒像是
在就診,胖男人像醫生一些,而那個女人像一個局促不安的病人,犯了病,還輸了
理,「誰叫你不當心的」,心甘情願地挨醫生聲色俱厲的責怪。櫻桃和那女人並排
坐下,那場面便成了一個舊式人家的老小姐在女伴的陪伴下初次赴男人的約會,忸
怩不安,故作矯情的場面。櫻桃一坐下去才覺得不對,然而馬上站起來又顯得突兀
了些,只好硬著頭皮坐著。
那女人向她一笑,手絹一擺,給她打招呼,一開口便是天然姑蘇風韻。就在這
時,那胖男人卻忽然瞥了櫻桃一眼,櫻桃心下頗覺詫異。
那女人向她親熱地一笑,湊過來故意壓低了嗓音道:「你也是一個人住在這裡
嗎,我知道你。」櫻桃怔一怔,只見她灰色的眼珠子閃閃發亮,像燒白的二粒小煤
屑,她靠得大近,可以看見她瘦筋筋的脖頸像一個被吸盡了肉汁的水果,她穿陰灰
色夾紫紅色葉子的袍子,從袍口裡蒸騰上來的是一種熱熱的氣味。櫻桃下意識地往
後退讓,那女人不依不饒又向前湊近些重複道:「你是從上海來的嗎,我過去也在
上海住過的,我媽媽,我弟弟。我上次聽見你說上海話。」她熱切的臉上堆著皺皺
的笑紋,操著不很熟練的上海話:「書清和我,住在霞飛路……書清說他會來接我
的,我媽媽和弟弟都在上海被日本人炸死了,我只有書清了,我不能沒有書清,他
常常安慰我,秀文,你不用擔心,等打完仗,我們一起回上海,好好過日子……」
她的話到後來急促起來,一急起來便一個接一個地打嗝,她的煙白色的臉頰死一樣
地白,兩顆顴骨卻泛出兩團不正常的紅暈,她的手是痙攣的,下死勁地握著櫻桃的
手,像溺水的人抓住唯一的希望。
櫻桃有點怕了,一迭聲叫道:「太太,太太。」一邊用眼光向旁邊的那個胖男
人求救。那個男人騰地一下站起來,伸出粗圓的手臂去格開那個女人,那個女人仍
回過頭來,急急地道:「我的書清不會拋棄我的,他會回來的,他到香港去了,他
是我丈夫。」那個胖男人不耐煩地對櫻桃道:「你這樣一個太太,平時也不要輕易
與人搭訕,她,一個癡子,你知道她是什麼,你一與她搭仙,她就興奮起來,出了
事體你要負責的。」
櫻桃經他這一頓斥責,轉身走開。旁邊幾個知情的人,七嘴八舌他講給櫻桃聽。
原來,這個女人的丈夫是個銀行家,在成都另找個地方與他的秘書同居了,卻騙她
說到香港做生意去了。也不知道女人是真癡還是假癡,每天這個時辰總要到這裡來
等她丈夫的信,櫻桃忽然打了一個寒噤,那個胖男子狐疑地看了她一眼,試探道:
「你也是在這裡等信吧。」櫻桃衝口說道:「不,不。」一邊逃也似飛奔離開郵局。
她忽然明白,原來自己在這裡與那個瘋女人沒什麼兩樣。也許在那個女人眼裡,在
那個胖男人眼裡,在鄰居們眼裡,她同樣也是一個棄婦。這也不是沒有可能。如果
端敬聽說了有關她的風言風語,把她一個人撇在這異鄉異土,孤獨無依,她一個人……
或者,或者端敬有一個三長二短……她不敢想下去,這個世界充滿了不安定的動盪
因素。走,回重慶去,她當天就出去打聽車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