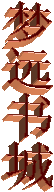
櫻 桃 紅
07
櫻桃那日沒有跳舞去。然而她此後在舞場裡一混就是一個星期,可是奇怪的是
小陳在這一些場合卻沒露面過。這個時候的重慶,雖然是戰爭時期,但聲色歌舞場
所卻比別的城市更厲害些,也比往日更繁榮。櫻桃雖是上海人,可那時候根本不出
去應酬,因此一星期以來玩得盡心盡致,感覺上重慶似乎比上海更為浮華。櫻桃的
朋友都說她的膽子比過去大多了,話裡的含意褒貶不一。櫻桃慢慢地結交了許多朋
友,對於和她相似身份的卻又抱了一層莫測的心理,不屑於搭理。正經的太太群中
對她的身份持有偏見,又嫌她的張狂,因此,櫻桃朋友多雖多,卻沒有一個知心的。
櫻桃又何嘗不知道這點,私下裡對人說:「我何嘗不知道,人情——薄如紙,這人
的心哪!我哪能管得了別人說什麼,端敬有錢,他願意讓我玩,關別人屁事。」她
沾上了許多習氣:抽煙、賭博、打麻將、逛戲園子、買首飾、跳舞……還有一樣捧
戲子。
有一日小何太太在西菜社請客,請的是兩個唱昆曲的,硬拉櫻桃作陪。櫻桃初
時在路上便猜出幾分,及到西萊社細觀小何太太的神情,果然有緣故。
她坐一坐,敷衍幾句,便找個藉口先走,小何太太卻也不甚留她。一路驅車回
去,她心下暗道:「看情形分明是小何太太看中了這其中的一個,只是沒有挑明,
只想扯了我充個數,擋了臉面,如此看來,小何太太竟也是個不安份的。亂世哪,
人人都是縱情享樂。這個仗一打,誰還顧得了誰,誰還顧得上什麼臉面呢。」不料,
第二天小何太太打電話來,有意無意間竟替她牽上了線。櫻桃只作不懂,小何太太
又不好明說,寒暄幾句,只得罷了。又隔一天,那一個唱昆曲的竟然親自登門造訪,
櫻桃意淡淡地,擋了回去。
林媽關了門回來,走到客廳裡收拾茶具,櫻桃正半躺在沙發上無聊地翻看一張
報紙。林媽向她看一看,搭訕道:「這位先生是先生銀行裡的嗎,以前沒來過罷,」
櫻桃嘴秀邊淡淡地浮起一絲笑容,懶懶地道:「那倒不是。」林媽也笑道:「我說
嘛,看著怪生的。」
櫻桃把報紙一丟,似笑非笑道:「告訴你,他還是我的情人呢,你信不信。」
林媽一下子抬起頭,忽又意識到什麼,訕訕地笑道:「哪能呢。」櫻桃瞟她一眼,
道:「究竟是不是,你不剛才都在門外聽到了嗎。」輕描淡寫一句話,把林媽堵了
臉紅脖子粗,訕訕地剛想分辯,被櫻桃擺一擺手止住了。櫻桃笑一笑,點上一支煙,
吸一口,才慢條斯理地道:「林媽,你記著,以後別這麼偷偷摸摸,讓人瞧見了,
說我們家幾句沒規矩倒也罷了,只是你這張老臉往哪兒擱——倒說在李家也做了幾
十年了,不知是哪個主子調教出來的,沒的讓人笑話!」
她老是覺得林媽在偷偷地監視著她。這個半老不老的女人,她一想起來就覺得
不舒服,尤其討厭她對端敬的殷勤模樣,她心下忽然起了一個念頭:她一直跟著端
敬,起碼端敬在重慶的這段日子裡,在她之前,她似有似無地充當著這個屋子的女
主人——她記得林媽是終身未嫁,一直侍候著端敬夫婦倆——那些漫漫的歲月,在
那些幾十年漫長的時間裡,她難道就對她的男主人沒有一點非份之想?而端敬對於
這個勤快整潔、有著幾份姿色的女傭……。她覺得胃裡有只手在蠕動似的噁心。她
知道這個念頭太過齷齪,可她仍不由自主地想。按她的脾氣,恨不得立時把她辭了
才算完。可是端敬很明顯地不會同意她,他甚至婉轉地暗示過,對林媽,要籠絡一
點兒。她知道是為她好,將來,一俟戰爭結束,端敬總是要隨著銀行遷回上海的,
他不能不考慮到將來如何安置櫻桃的問題。林媽是他元配的紅人,籠絡住她也算是
多點餘地的意思。可是他沒想過櫻桃的意思,她真的願意隨了他住進那個複雜的李
公館去,去做一房沒有地位的姨大太嗎?按她的心願,回不回上海尚無定論。她不
是沒有想過:別看今日風光,可仗一打完,局勢一明朗,她們這群抗戰夫人的地位
便發炭可危。可丟下重慶自由自在的日子再回頭去過那種低三下四的生活,那不是
瘋了?當然,留在重慶也不是沒有危險,特別是像她這樣的人,端敬萬一減少了對
她的經濟上的支持,她就不得不再過苦日子。她打定主意,真到了那一天,如果真
不能留在重慶,要去上海,端敬必須另置房子給她住。
因了這一層想法,櫻桃不得不對林媽有所顧忌。她自小在舊式人家中長大,那
種地位不穩的姨太太或是新少奶奶初進家門不小心便被年長資格老的傭人欺辱的事
見多了。端敬遠在香港,對於她在這邊的所作所為,只怕他還是信林媽的多一些,
可是也不能對她太客氣了,否則她倒以為她好欺侮。這一段時間櫻桃用心使出手腕,
恩威並用,總算是把林媽的氣焰壓下去了一點。
抗戰時期的重慶真是一個紙醉金迷的世界,人在這種地方墮落起來是很快的。
櫻桃學會了捧戲子,找男舞伴——但在關鍵時刻,她卻總是逃了,總是失了勇氣。
她也不明白自己。
這天林媽放假,櫻桃因昨晚上出去跳舞,起得很晚。一覺醒來,只見窗外一縷
陽光已穿過窗簾的縫隙在房間裡,灑了一大條一大條,像是誰不小心灑落的金粉。
竟是重慶少有的一個好太陽天氣。滿屋裡靜靜的,壁爐上方西洋自鳴鐘的聲音走得
單調和乏味,是一種空洞的,什麼都穿不透的聲音——碰到哪裡就從哪裡彈回來。
樓下的過道也很難得的沒有汽車駛過的聲音。也不知什麼時候了。
櫻桃胡亂揀了一點點心吃。一時興致拿起了水壺澆花,這花還是上次老王買來
的,有林媽天天照應著,居然長得生機勃勃。開的是一種深紫紅色的花瓣糾集在一
起的花,像是吐了一口血在上面。櫻桃澆著澆著忽然有些心煩,賭氣放了水壺,無
意間倚在窗前,她懶得去拉窗簾,只拈起了一角,怔怔地看著。
樓下是一條依山勢斜斜地鋪就的山路,她們這一幢樓是在地帶略高的地方,看
那低低的地方,總是先看見一個人的頭頂,滿頭烏髮的或是謝頂的,戴帽子的或是
不戴帽子的,接下去才依次是臉部、身體,像是膠捲浸在顯影液裡一樣,一點點不
慌不忙地顯出來。現在這條路上乾乾淨淨的,空無一人。過一會兒一輛人力車氣喘
吁吁地趕上來,坐在車上的那個男人穿著鐵灰長衫,車沒停穩便急衝衝地跳下來直
沖進樓裡。櫻桃原以為那個車夫要走了,不料,他卻蹲了下來,好像要歇歇腳,東
張西望地觀看,一邊從腰間掏出一杆煙袋來。使櫻桃覺得好笑的是,那個車夫明明
很年輕,不過十七八歲吧,卻老氣橫秋地持著這一杆煙袋。她不由地打量起這一輛
車與人來。剛才遠遠地看見車篷是油黃的,像黃油紙傘的那種,現在細細看,卻竟
然還是綢的,只是有點年代的髒與舊了。櫻桃以前從未想像過有這樣一種油黃得令
人詫異的綢緞,或許綢緞上織著小小的福字、壽字,充滿著了民間色彩的圖案。車
篷的邊上還繡著一圈棗紅的荷葉花邊,撲撲簌簌,過分肥大地在風中抖動,一切的
一切令人想起一個年代久遠的婚姻,一個齊刷刷的劉海的新嫁娘坐在這一團富貴的
喜氣裡,從一條路上丁了當當地過去了,自然,那時候這部車是完全新的,人也是
新的……如此濃厚的類似懷舊的氣息,使得這個年輕的車夫沒有任何準備,不加任
何化妝便出現在一個野草台班子的舞臺上,旁面的柱子上貼著大紅大綠《三娘教子》
《王寶釵寒窯十八年》的圖畫,而他在這種氣息中茫然無知。
櫻桃跟著車夫的目光轉:隔壁人家漆成白色的雕花鐵欄杆,對過人家大門上過
春節時貼的對聯,路邊一隻孤零零的貓,一個穿竹青布棉襖的老媽子拎著菜籃走過,
雙手怕冷似的籠在袖子裡,走過車夫旁邊時,慢吞吞地翻他一個白眼又不疾不徐地
過去了……看了半晌,櫻桃忽見樓下坐車的男子急急忙忙地沖了出來,空著兩手,
兩條胳膊半張著,有點氣急敗壞地奔到車邊又回頭看,卻是一個年輕女子抱著一個
孩子奔出來了。那個女的穿一件丹士林旗袍,短短的劉海,極鎮定的樣子。櫻桃猛
然記起來,原來這是樓下楊先生夫婦倆。楊太太先上了車,楊先生卻站著不動,和
車夫比手劃腳起來,從神情上看,大約是在講價錢。櫻桃猜想大概是孩子病了,不
由得微皺了眉,轉眼去看楊太太,只見她抱著孩子坐在車上一動不動,臉向這邊半
側著,沒有一點表情,眼光卻是無聊地東張西望,還是那些車夫方才看過的景致:
雕花鐵欄杆、破舊的春聯、貓……,仿佛對丈夫與車夫頗為吃力的討價還價感到厭
煩。倒是那個丈夫,一邊還價,一邊不住地拿眼瞟他太太,焦急的、無可奈何的神
情。櫻桃看到這裡,不由地想,不知她怎麼嫁給了他,不知他怎麼娶了她!看著只
是不般配。她模模糊糊記起不知哪兒看來的一句話,大意是說,婚前你要娶的那位
小姐是一個人,婚後你得到的太太是另外一個人。此話倒過來說同樣適合於男子,
大概婚前和婚後的人總要變的。
正在胡思亂想間,她忽然看見山路上慢慢駛來一輛白色的汽車,停在樓下。她
覺得車窗裡的人影有點眼熟,定睛一看,卻是小陳。她受了驚似的把手裡的窗簾一
甩,三步兩步退到沙發邊。自己也覺得有點兒失態。她把一隻手捂在胸口,在屋子
裡打了幾個轉兒,自己也不知道要幹些什麼。
門鈴響了的時候,她兀自在發怔。那鈴聲單調而悠長:鈴……叮咚,長得令人
厭煩,手一放,卻又冷不丁冒出一個「叮咚」的尾巴來,算是峰迴路轉。櫻桃本想
不開門,只作不在家算了,禁不得那門鈴執拗地一聲趕一聲地響著,焦躁不已,心
一橫,急步過去欲待開門,那鈴聲卻又戛然而止。她伸出去的手也不由得頓了一頓,
屏息靜聽,門外卻無聲無息,好像是走了。櫻桃不由得有些失望,終究是開了門欲
看個究竟,卻不防小陳一陣風似地從門外捲進來,順勢用腳把門抵上,靠在門上笑
吟吟地看著她笑道:「我只當你今天終究是不給我開門了呢。」櫻桃冷了臉,轉身
往裡邊走邊道:「我只當你從今往後再不登我這個門了呢,還以為哪個叫花子在門
外招人厭!」小陳夾腳跟進來,笑道:「你不希望我登這個門倒是真的,什麼叫花
子不叫花子的多難聽!」櫻桃霍地轉過身來,用手指著他的臉,冷笑道:「你嫌難
聽,我還嫌難看呢,你說,像你這樣賴在人家門前,一聲聲摁門鈴,你不怕閒話我
怕閒話呢。哦,是了,你巴不得人人都知道,人人都只當我被你騙了,你好乘機要
挾我。你以為我不知道你是多麼用心險惡的人。」小陳歎口氣,攤攤手道:「看,
人家巴巴地來看你,好心嘛,才說不上兩句話,又被你罵。作驢肝肺。」櫻桃冷笑
道:「你以為你說上兩句好話我就信了你。」小陳走上一步,在櫻桃跟前,緊緊盯
著她的眼睛,認真地道:「櫻桃,你真的以為我在騙你麼,你真以為我那麼壞嗎。
只要你說一句真心話,我馬上就走,以後再不來纏你。櫻桃,我是認真的。可是如
果你不相信我,如果你真的討厭我,我,……我只要你告訴我一句話。」
櫻桃不由地抬頭看他,她知道自己不愛他,可她還是擔心自己此刻會被他感動,
說出一些她自己都不能相信的話來,但……誰又能說得清呢,或許,或許她心裡是
對他有一點點愛,有一點點感情的,只是她自己不知道罷了。別人愛她不是重要的,
關鍵是要她能對別人有一點點愛,可那是多麼難……想到這裡,她的眼前慢慢虛無
起來,她的聲音也虛弱下來,道:「說什麼呢。我,我不知道。」她的頭不由地垂
了下去。他很快地捕捉到她這點變化,熱烈地道:「是的,你不會知道,可我知道,
我是說,我理解你,相愛的人都是最糊塗的,真的,連我自己都不太明白我自己,
我會這麼熱烈地愛上一個人——你,櫻桃。」櫻桃覺得自己已被逼到了牆角,可內
心仍不甘心輕易放棄,她掙扎地作出一點空洞的冷笑來:「我難道不曉得你不過是
順口說說罷了。」他道:「我們不要再談這些問題好不好,你總是不相信我。」櫻
桃忙道:「可不是,叫人怎麼相信你,一會要談,一會不要談,變得多快,更別說
男人的心了!」小陳笑了起來,搖頭歎道:「都說善變女人心,可世人不知道女人
的絕技還有一樣——倒打一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