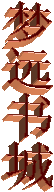
02
正笑鬧間,老媽子上來站在櫻桃身邊輕聲道:「都十二點了,可要先散了牌局,
端宵夜上來吃?」櫻桃扭起身來,伸手理了理散亂的鬢髮,一隻手臂停在空中,略
一思索道:「好吧,散了吧,我也累了。」老媽子賠笑道:「可不是,先生都在那
邊沙發上盹著了呢。」櫻桃「哦」了一聲,向那邊望去。老媽子悄聲道:「我才給
他蓋了一床毯子,怕著了涼。」櫻桃向四周人睃了一眼,笑道:「聽聽,我這個傭
人作得我一大半主呢,竟比我還關心他。」
楊小姐道:「你這女主人還好意思說。話又說回來,如今這樣忠心的下人可找
不大到,都是又笨又懶的。你不知道我那個小丫頭翠兒,人小鬼大,幹起活來又笨
得不開竅,費了我多少心思!」櫻桃托著頭髮半仰著臉,笑吟吟地道:「不於我事,
要說,我也沒那麼大的福氣呢。林媽是他從上海那邊帶來的舊人,用了三十多年了,
比我的年齡還長呢。」櫻桃的年齡從前也是相當忌諱的,可近來竟不那麼注意了—
—總是正得意的緣故,小何太太在心下暗忖,轉而又想到,既是舊人,想是服侍過
上海李公館的李端敬太太,也不知究竟忠心哪一個,搞不好,還是李太太在這邊安
插了一個耳目呢。只是李端敬和櫻桃的事不知有沒有傳過去。音訊不通,交通不便,
那面一時未必部曉,只是將來若曉得了,不知會怎樣。
櫻桃道:「在這家裡,我倒成了外人,竟還是他們主僕貼心。」似笑非笑地站
在當地看林媽走出房門去。小何太太嗤一聲笑起來:「難道你還吃這個老婆子的醋
不成。」櫻桃冷笑一聲,只不作一語,半晌,說:「你們看著好了,我這話不是白
說的。」
眾人一時無話,小何太太忽然驚道:「咦,小陳,你今天怎麼不說話,這麼老
實。」小陳手插在褲袋裡,背心抵在椅邊上,人往下溜,一雙腿抵住桌子腳,微笑
著道:「有你們說便夠了,我若開口豈不是煞風景。」小何太太喲了一聲,奇道:
「小陳怎麼今天連說話的腔調都變了,是被新女朋友甩了吧。從前可只有你甩人家
的。」小陳長歎了一聲,作憂戚狀:「一家有一家的苦處。今日裡眼見端公年近花
甲,仍是金屋藏嬌,豔福無窮,怎不令我輩羨煞。」一雙眼卻是瞅定了小何太太。
小何太太嘴一撇,道:「羨不羨的吧,你別在我跟前玩花樣,你那點伎倆,我看個
透。」說著憋不住笑起來。小陳笑道:「是嗎,我不相信女人竟會不上當。」轉頭
向櫻桃道:「李太太,你說是吧。」一句話問住了櫻桃,若是吧,她等於是承認她
上了李端敬的當;不是吧,又似乎不好,他分明是到她這兒求援來了。
正說間,林媽帶著一個丫環進來,託盤裡裝著幾碗銀耳湯,正好解了她的圍。
櫻桃趁機轉移話題,招呼眾人吃宵夜。
楊小姐數數桌上的籌碼,握住了在手心裡頓一頓,笑道:「今兒個竟然是我獨
贏了,改天請你們看電影罷。」小何太太道:「好個吝嗇的人,贏了我們這許多錢
去,竟是一場電影打發了去。不成,不成。」小陳道:「楊小姐起碼也該請我們到
天府樓去吃一頓館子。」櫻桃道:「不好,不好,還是找個上海館子。天府樓的川
菜我總是吃不慣;要不,廣幫的也行。」小何太太皺著眉頭,連連遙手:「廣幫的
也不行,他們菜吃得太下流、太噁心,什麼貓啊蛇啊的混在一起煮,不行不行,惡
心死了。」小陳笑著道:「這是廣幫極有名的一道名菜,叫龍虎鬥,總不成吃真的
老虎與龍吧,龍什麼樣子,誰也沒見過。獵呢,就是虎了,蛇當然就是龍了。一道
名菜呢!」櫻桃還未回答,這邊楊小姐一迭聲地嚷道:「我這主人還沒發表意見呢,
你們倒反客為主,合謀著怎樣花我的錢了。」
櫻桃微笑著看了一眼楊小姐,心下嘀咕:終究是小家子氣。楊小姐家世不如自
己,嫁得又不如自己,所勝的只是年輕。櫻桃常常有意無意間拿她來與自己相比,
比比又時常比出許多不平來——要是我還像她這般年紀……不過二十一、二歲吧。
她不知道自己如果像楊小姐這般年紀會怎樣,只是她斷言自己斷不會委委屈屈跟了
李端敬,做個地位不穩的「抗戰夫人」。現在的女孩子真是現實得很,在這兵荒馬
亂的年月,手忙腳亂給自己找個歸宿——只要有錢,能享福。櫻桃在人前一向是與
楊小姐平輩相稱的,但在背底裡總把她看作是與自己隔了一代的人。自己當然也算
是與楊小姐同一處境,但,至少有一點點不同吧——自己多少是帶點無奈的性質,
不像楊小姐,單純是為了享樂而「賣」了自己——她非常忌諱這個「賣」字,至少,
她哥哥對她的行為是默許的;至少,她嫁得還如人意;至少,不像楊小姐那樣時時
露出初入上流社會的窘迫來。這許多個「至少」其實並不那麼理由充足,櫻桃自能
自圓其說,但,有這一點點就夠了,就是沒有這一點點又怎樣?櫻桃無暇去想,端
敬的社交圈子是極其誘人的,是極其複雜的,多麼有趣。她都忙得有點手足無措了。
過了幾日,還是原班人馬,只少了端敬,依了櫻桃的主意,去了一家名為大上
海的菜館子,卻是櫻桃搶會鈔。小何太太向楊小姐使了個眼色,笑道:「你還是收
起來吧,你那點小錢,可憐!還不夠櫻桃買一支口紅的呢。」楊小姐一邊將錢放回
皮包,一邊笑道:「有人替我會鈔,我為什麼不肯。櫻桃,你現在有錢了,是該請
我們。」話雖是奉承,卻也不大入耳。櫻桃當下只裝沒聽見,吩咐車夫依舊送她們
去電影院。
她回去的時候已是晚上八九點鐘的光景,打了幾遍鈴,卻沒有人來開門。她不
耐煩起來,自己從手袋裡掏出鑰匙,門一打開卻聽見書房裡傳來留聲機的聲音,伊
伊呀呀,是京劇的調子,廚房邊的過道上有一雙男式皮鞋和端敬的手杖。他這天竟
是早早地回來了。櫻桃站了一會兒,聽見廚房那邊悄無聲音,大概林媽已洗涮完畢,
不知到什麼地方去了。
櫻桃意懶懶地,徑直到臥房去,經過客廳的時候,停一停,又決定轉到書房去。
他們家的客廳像舞臺上常見的佈景,四周分別有幾扇門通往臥室、書房、客房、
餐廳,浴室是與臥房連在一起的。她倚在門邊,看見端敬側面向著她,半躺在高背
皮沙發裡,閉著眼,她幾乎以為他睡著了,仔細一看,發現他原來沒有睡著,左手
手指輕輕在椅圈上打著拍子。房間裡鋪著一層厚厚的地毯,那鏗鏘的聲音被吸走了
一大半,越發細若遊絲,也像盹著了一般。
櫻桃輕輕地移過去,在另一端的大沙發上坐下,卻不言語,只管出神。唱片走
完了,發出沙沙的唱針的摩擦聲,端敬睜開眼,看見櫻桃,「咦」了一聲,笑道:
「你什麼時候回來的,我竟不知道。」一邊站起身來,趿了拖鞋去那邊的茶几上換
唱片。他穿了一件家常的睡衣,式樣簡單然而剪裁精緻,一個見過世面的有一點社
會地位和財富的平和的男人,介於中年與老年之間的,跟了這樣的人,生活總是平
穩一點吧。櫻桃這般思忖著。
端敬回轉身仍在櫻桃對面的高背沙發椅上坐下,微微笑著看她:「怎麼一聲不
響的,玩得開心嗎?」他的雙手閒適地交叉著,有著一點象牙白的膚色,修剪得整
整齊齊的指甲,有點鬆弛的然而還是一雙握權多年的男人的手,從這雙手上可以想
到他的整個人、他的為人以及他所代表的整個社會圈子——一個不失為合理的、有
所付出有所得的社會。一刹那間,櫻桃仿佛下了決心要抓住她目前有能力抓住的一
切。有一天,她也會老的,到那時,可都什麼也沒有了。櫻桃的臉上露著一絲若有
若無的微笑,支在沙發上撐住身體的一隻手卻慢慢地緊縮起來,怕冷似地悟在厚厚
的絲絨沙發裡。她看一看端敬,自己也不知為什麼笑起來,甩掉腳上的高跟鞋,盤
膝坐在沙發上,臉上卻是一副嗔怨的神情:「有什麼好玩,你又沒空陪我。」端敬
不作聲,只是微笑著看她。兩人相視而笑,櫻桃突然低了頭道:「以後再也不要和
他們一起玩了。」一隻手狠狠地劃著沙發上的絲絨面,一下,一下,發了狠似地。
端敬奇道:「不和誰一起玩啊。」櫻桃不作聲,端敬笑道:「看看,又耍小孩脾氣,
不出去吧,在家裡跟我鬧,說呆得慌;出去了還是這般無精打采的。」又道:「我
知道你的性格,人少了嫌孤單,人多了又嫌煩。不願意出去,明天就約了人到家裡
來玩吧,打麻將,跳舞,請客,隨你。要高興就多玩一會,厭了就早早散了。」櫻
桃道:「約了人來,也是麻煩,再說,你又不喜歡這些,上一次你還不是在旁邊睡
著了,害得我擔了好幾天心,怕你感冒。」說這些話的時候,臉上已微微有一些笑
影子。端敬道:「好個難侍候的小姐,自己怕麻煩,反賴在我身上。」櫻桃瞟他一
眼,道:「可是人家說的,好心沒好報,我倒是一片誠心為你打算,知道你愛清靜!」
說著過來坐在椅圈上,倚著端敬。
正說笑間,卻聽門一響,林媽邊用圍裙擦手邊走過來,端敬還沒怎麼著,櫻桃
飛紅了臉,忙不迭地坐起身來。林媽目不斜視地從他們跟前過去了,在桌邊收拾煙
灰缸子,倒了殘茶,又從櫃子裡取茶葉,泡了一壺碧螺春。房間裡一時沒人說話,
只聽見林媽走動時窸窸窣窣的聲音和偶爾杯盞相撞的清脆聲音,櫻桃兀自不放心,
又用手掠了掠頭髮,卻一眼瞥見端敬含笑瞅著她,眼裡不無挪揄之意。
林媽搭訕道:「這茶葉還是上海家裡帶來的呢,原想這仗不會拖得這麼長的,
所以大小姐沒叫多帶。一直放在這兒忘了,前兒打掃房間才發現了,先生你喝喝看,
味道很好呢。」櫻桃一時不曾會過意來,端敬皺著眉頭道:「林媽,我知道了,你
下去吧。」林媽不再說什麼,卻拉長了臉走出去。
房間裡的兩個人聽著腳步聲一路穿過客廳、廚房,一直走到陽臺上。大概剛才
在晾衣服,聽得見通往陽臺的門吱呀響了一下,兩人都被那門的聲音震了一震。端
敬似乎有點局促。櫻桃順口道:「你這大小姐好孝心啊!」端敬卻不回答,轉過臉
咳了一聲。這時留聲機裡已另換了一個女聲在唱,悲悲戚戚的:低——頭——離了
——洪洞縣——將身——來在——大街前……急急匆匆地訴說著什麼,卻是快慢得
當,條理分明,一個口舌伶俐的婦人。端敬依舊坐到這邊來,輕輕握住櫻桃的手,
轉過臉來道:「小時候頭一次我母親帶我去看戲,便是這出《玉堂春》。記得那時
好像是一個北平來的優伶,名喚作天香雪的……」他停了一停,聲音低了下來:
「人生在世,真是一轉眼的事,你看我,都是一個年近花甲的老人了。戲還是這出
戲,可聽戲的人已鬚髮皓白,青春是這麼易逝的……」櫻桃不禁變了臉道:「你別
這麼說。」端敬沒聽見,仿佛出了神。高大的寒冷的書房,裝飾著幾幅前朝的山水
畫,山是靜止的,水是靜止的,雲也是冷冷地凝固著的,只聽見留聲機裡的那個女
聲一句句冷靜的訴說著,櫻桃忽道:「林媽是陪嫁過來的吧。」話說得有點沒頭沒
腦。端敬頓一頓,微微一點頭,算是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