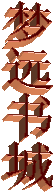
第二章
如今我對海島僅剩的記憶是將村落慢慢化為灰燼的天火,及在過亮的陽光中翩
然飛舞的白蝴蝶。
村落被燒毀的一年之後,我曾祖父的子孫被赦免結束長達七十一年的流放,允
許回中原居住。
是年父親45歲。一隻破落的白帆船停泊在岸邊,可是在父親眼中哀傷如招魂幡,
他覺得自己是一個客死異地的孤魂,被千里迢迢帶往海水另一邊的陌生故鄉。我和
母親默默跟隨其後。初來海島時,戴氏族人一百零三人曾使一隻中等海船充滿浩浩
蕩蕩的傷感。如今父親形單影隻。我的血脈中流著一半來自海島土著的母親的血。
此刻只有父親滿懷惆悵,那些淒慘的戴氏陰魂攀附在他的衣帶上,跟隨其後,心靈
相通惺惺相惜,他們把我和母親與父親隔開,他們欣欣然與父親共同回鄉。
我對母親說如果她不喜歡與父親相處,相信我們可以另外找到一個秘密深洞讓
她躲藏。我以我的方式安慰母親,可母親一笑了之。
當小島在海天交接處化為一個細如樹籽的黑點時,我忽然發現在黑點的左側有
一個白點,如同黑樹籽旁邊的白樹籽,我遙望半晌,忽然記起這是一個無人居住的
荒島,島上棲居著千百種姿態迥異的小鳥,它們在白天飛行,晚上歸巢,灰白的鳥
糞凝結在岩石上,像水晶一樣閃閃發亮,而後風吹日曬,化為塵上。我指給母親看,
問母親是甭還記得我和她曾一同到過這個白島去拾鳥蛋,母親認真地想了想,茫然
地笑了笑,她說記得。可我相信她已忘卻,對海島全然忘卻。
我與父母曾在家鄉一個叫琅琊的地方居住。
曾祖父曾有一個遠房親戚,如今他的子孫流落在江南蘇杭一帶。一日,我曾見
父親與兩個中年人在房中,後來知道,論輩份他們是父親的侄孫。他們看上去與父
親相仿,實質上更為年長幾歲。父親後來說原以為家人相見,雙方都會比較興奮,
實質不儘然,父親與這兩個身穿綢衣的中年胖男子相對無言,所以父親後來決定去
洛陽的時候內心頓時如釋重負。
我與母親隨父親搬至洛陽崇孝坊,洛陽對於父親是舊夢重溫,是他十五年海島
生活之後心裡真正的故鄉。他從未與洛陽謀面,可他與洛陽一拍即合,他對它懷著
真正的渴望與夢想。
我們起初依靠母親自海島帶來的首飾典了一出院子居住,頗大,房屋寬敞,我
喜歡屋子四周的木質走廊,我一生都酷愛這種建築風格。父親結交了許多朋友,深
夜歸家,我與母親自窗口看見馬車上衣著華美的女子的身影。奇怪的是父親在海島
時滴酒不沾,而洛陽令他中年時身心俱醉,如同遭逢一場浪漫豔遇。我與母親在他
身後的窗口邊品評那些女子的衣飾與容貌。只有在這樣的時刻,母親才喋喋不休。
家中雇傭了兩個下人和一個廚子,母親一向不善操持家務。我們在海島時的另
一個樂趣是她經常去採摘草藥,給島上人治病,而今母親雙手空空,大部分時間坐
在這間有木質走廊的屋子裡沉思冥想,有時自己對自己笑起來。我在院中走來走去,
隔著窗子看她,走一會兒又去看她。見她好好地坐在那裡便覺安心。
父親生日那天,母親大清早起來做準備,至傍晚時分,便開始沐浴焚香,梳妝,
並換上一件新制的紫色袍子。走廊上擺著一隻陶罐,裡面泡制著父親最愛吃的銀耳,
大朵大朵,潔白的像純淨的睡蓮。
那夜我靠在走廊的木框睡著,睡前猶見母親在燈下獨坐,睡蓮已蒼白,似等父
親等得乏了力氣。
次日清晨我被父親的高聲驚醒。原來母親大醉,父親和他的兩個朋友情晨回家,
看見這種情形,覺得十分丟臉,狂怒不止,順腳踢碎盛著銀耳的陶罐,水流了一地。
我起床後看見銀耳沾染塵埃,似殘花敗柳。母親酒醒後十分疲乏,只是叫頭痛,我
去斟一碗茶來給她喝,她似十分乾渴,一氣飲盡,末了,向我笑一笑,一夜之間她
已清瘦許多,只是無話。
這個春季母親被父親鎖在房內,甚至禁止與下人說話。母親不置一辭,唯一的
反抗是把下人送進去的一日三餐從窗口丟出來。自此我照顧母親的飲食,我學習煮
飯,裁縫。我最擅長的是製作一種叫「水晶糕」的南方點心,因為父親曾雇傭的一
任廚子是蘇杭人氏,他口中的蘇杭山水青綠,四季分明,宛若天堂。我閑來常陪母
親聊天,隔著窗子,我把廚子的話轉述給母親聽,一句一句,極為緩慢,極為詳盡。
母親和我商定,有一日要結伴去蘇杭。誰也不曾提起父親和洛陽。
一個傍晚,母親忽然告訴我,如果到夏天時父親還不讓她出門,她將在房中生
下一個嬰兒。她說著靠近窗子。這個季節頗為悶熱,家中其他房屋俱已除下木窗,
代以柔軟的青紗,唯獨母親所居的屋子除外。母親微伏下身示意我把手伸進木窗的
空格,就這樣我初次感覺到了弟弟的心跳。母親與我都確信那是一個男孩。父親回
來了,經過此處,在遠遠的地方站了一會兒。我和母親默不作聲地看著他。他終於
沒有過來。
自那晚之後,我曾多次觸及弟弟的心跳,直至初夏的一個深夜。大雨如注,父
親在書房沉醉不醒,僕人在廚房聚賭。我聽見母親的慘叫,看見血從門縫下流出來,
我從窗口爬進去。母親生下一死嬰。我和母親都曾確信弟弟的出生並不需要他人相
助,只有我們仨人才是血脈相連的骨肉。天明時我和母親收拾好一切,擦乾血跡抹
去所有線索。母親把弟弟抱在懷裡,我在她腳邊,十分安靜。天色漸明,母親把弟
弟埋在她房中地板下的泥土裡。如此,我們仨人仍是朝暮相隨。這是一個我們仨人
才知的秘密,父親自始至終並不知曉此事。如此天上地下,我和弟弟照看著母親。
父親如何變成一個陌生人,我始終不曾明白。這一年他47歲,我7歲。只是此後
他曾言非常憎恨我,惡言說我奪走了母親,讓他和母親終生如仇人。初回洛陽時,
他曾打算博取功名,可是很快打消了這個念頭。我們所處的時代是上天寫成的最華
美的詩篇,大唐被稱為「天朝」,才人代出,士林競爭十分激烈。他很快發現,此
時的大唐,已與曾祖父的朝代大相徑庭,一切都飛速地發展,服飾用具日趨精美,
士人的觸覺日趨細緻,節奏日趨快疾。風景依舊,可是洛陽于父親日見生疏。不久,
父親酗酒不能自控。那段時間裡,我曾偷偷自他房裡拿酒給關在房中的母親。酒至
半酣,我仍會夢見自己身為白蝴蝶,飛在不為人知的世界。
父親終於放母親出來。其實房門的那把鎖早已不知去向,只是母親堅持不踏出
房門一步。已是秋季。洛陽坊間種植的槐樹黃葉掉落一地,我們猶自記得初到洛陽
的春天美景。
父親終於放棄了仕途的打算,他用母親僅剩的幾件首飾做本,又借了高利貸,
做起了南北往來的生意,經營絲綢、茶葉、藥材、瓷器、毛皮等等。他雇用了三個
夥計,一出去就半載,或是一年,或是更長。有時他甚至把兩個下人和廚子一塊帶
走,於是家中只剩下我和母親兩人。我在廚房中燒菜,在走廊上煮茶,一隻寬口長
耳的陶罐裡浮著幾朵銀耳,潔白如睡蓮,這是我和母親鍾愛的甜品。母親漸漸習慣
了我煮的飯菜。
遇到大雨的初夏夜晚,我走近母親房中,仍可清晰地聽見在泥土中的弟弟的心
跳。
我從不覺得這樣的日子有何缺憾,可是不久我覺察到母親日漸憂鬱,經常在院
裡搬一隻藤制的搖椅坐著,漸漸神不守舍。夏天的太陽一會兒就升到中天,直直地
暴曬下來,灼熱得像火,太陽移過來,她很快就在大太陽底下了,可是她不覺著,
獨自坐著,她也一樣睡過去。中午的院子裡,只有蟬在叫,一聲高,一聲低。一個
人坐著,坐累了,有時我也會慢慢地盹著。我覺得我和母親仍在海島,我們在沙灘
上睡一個午覺,而洛陽坊間的這個院子,只是我們在夢中曾停留的地方。
我和母親偶爾出去散步,經過一個叫壽和堂的藥鋪,偶然識得一個青年男子張
生,他是祖傳三代的醫師,可是對自己的病卻無能為力。母親把他帶回家來,給他
細細診治。
其間父親回來過一次,帶回來大批蘇杭的絲綢。他品味不俗,我一生對服裝的
鍾愛便是由此而來。父親是個天生的商人,只是在為夫為父方面一無是處。此次回
來,他與母親商議把我送往坊間的一個私塾。他似乎是在經商途中臨時想起此事,
趕回來,又急急趕去南方。
我不喜歡私塾,時常逃學,幾次中途回家卻不見母親,等候良久才見母親回來。
她告訴我說她去郊外摘草藥,為張生熬藥。我凝視母親,終於沒說什麼。
我不再逃學,枕在書桌上沉沉睡去。在夢裡我極度困頓,我夢見我在一間巨大
的藥材庫裡尋找什麼東西,那藥材庫或許是父親的,或許是壽和堂的,各種藥材的
氣息混合成釅釅的一團,使我不能呼吸,可我從來也不曾停止尋找。在我快找到時
我被私塾老師的竹杖敲醒。我細細尋思夢中情形,忽然出了一身冷汗。回到家中,
我日漸察覺點滴變化。母親甚為焦躁,且不再要我為她煮飯。她夜不歸的時候,我
從窗口爬進她的屋子,坐在床上,與冥冥之中的弟弟說話直至天明,醒來時見她若
無其事在廚房備飯。
睡在她床上的時候,我還時常夢見父親,夢裡的父親不置一辭,而容顏甚為模
糊。有時我偶爾夢見我的喉嚨非常痛,如被利刃割開。回味這些夢境我極為茫然。
歲末,父親押著商隊回家。得知信息,我曾希望母親有所反應,然而我非常失望。
母親一如往昔,坐在廊簷下熬藥。
獲利頗豐的興奮使父親一反常態,十分健談。而他亦訝然於我對他的親熱。末
了,他要我進書房去為他背誦我在私塾中學會的功課。臨出門時我轉身看見母親的
眼神,我向她笑了笑。她一刹間臉色慘白,使我有些許快意。
第二天,母親便割腕自殺。記得早上去私塾之前,我曾在她門前略站一站,現
在想起,她的房門好像是虛掩的,似乎,她還曾叫我一聲。春風,母親叫我。那一
日我枕著書桌沉沉入睡,夢見我鍾愛的木質走廊上的陶罐忽然破裂,水中銀耳盛放
似睡蓮,色如胭脂。
綠翹在咸宣觀紫雲丹房為玄機道士設宴洗塵時,恰逢月圓,清輝滿地,道觀遍
灑銀光。咸宣觀地處偏僻,四下裡一片寂靜,須臾,雲板三下,兩人不覺覺出一絲
寒意——房中特意生了火爐,可是仍擋不住四面八方聚攏來的涼氣。綠翹笑道:
「怪冷的罷?」一手取過玄機搭在椅背上的袍子,捏了捏,道:「咦,你這個人,
這麼冷的天,知道一坐就坐到深夜的,還穿這件衣服……」又摸一摸,訝然道:
「這不是去年我給你絮的那件絲袍罷?這麼薄。」又湊在燈下細看一看——果然不
是,式樣相仿,顏色也略為不同,這件是極深的紫色,原來那件應該是玄色的,且
這件袍子極為寬大。
她也不作聲,依舊走過來,替玄機搭在肩上,回身卻不落座,走到鄰屋,向老
道婆吩咐了幾句,那婆子正在打盹,睡眼惺忪,忙不迭地去了。
綠翹回來,見玄機已有幾分醉意,舉著杯向她遞過來,她推開道:「我喝不得
冷酒。」一手在碟子裡頭夾了幾樣乾果吃了,方才坐下來。玄機不作聲,又喝一杯,
向她看了一眼,笑道:「你做的我好好收著,捨不得穿,這是今年在青城山別人送
的。」
綠翹十指交叉,雙肘支在桌上——桌面是玉石的,鋪著秋春色的繡氈,還是能
感覺到底下是冷的——她笑一笑道:「我管得著麼,送給你就是你的了,你自己的
東西愛給誰就給誰。」說著,唇邊已有微微的笑意,給自己斟了一杯酒喝了。玄機
道:「怎麼又喝了,叫人拿去燙燙罷?」綠翹搖手道:「不要不要。隔壁也沒人,
剛才我讓她去你房裡取你的大毛衣服,走的時候穿,臨時措手不及倒在其次,天這
麼冷可別凍著了。」又道,「已經在隔壁的爐子煨了白粥,又預先備著幾樣精細小
菜,待會兒餓了,端過來就行。」玄機微笑道:「你一向這麼細心,下次再出門真
該帶上你,那些人真不中用,一路上淨給我添亂。」綠翹瞅她一眼,不忙回答,正
好那取衣服的老道婆回來了,在門口探了探,綠翹忙起身接過,擱在一邊,順手拿
了一碟果子打發婆子依舊回去守著爐子,重來這邊坐了,方慢條斯理道:「那哪成
啊,我要去了,要添亂,一樣還是不中用,只怕被你罵得還厲害些。再說我知道,
你哪有這個心,忙你自己的事還忙不過來呢?」又瞅她一眼,「看你,又瘦成這個
樣子。——你不過是誑我罷了。我呀,這一輩子做了你的丫頭,就給你好好守著鹹
宣觀,讓你出門在外時,想著這兒好歹有個家,在外面倦了、累了、傷了、跟人生
氣了,想著回來時,一看什麼都是好好的。這就是我的本份。別的,什麼都不求了。」
末了一句不覺放低了聲音。
玄機道士默然半晌,道:「這咸宣觀有你守著,有你這句話,我就放心,在外
頭再怎麼著也能忍下去——這麼多年都過來了。」
綠翹聽了此話,不覺一震,抬頭向她看了半晌。玄機卻不看她,只顧呆呆地出
神,好一會兒看見綠翹向她望著,不覺一笑,伸手在她眼前晃了晃。綠翹伸手一推,
就勢握住她的手,不發一言。兩個人維持著這個姿勢一動不動。隔壁房間忽然咚地
一聲,又聽見老道婆嘰咕了幾句——聽聲音像是老道婆盹著,頭在木板壁上撞了一
下。玄機道士側耳聽了聽,向綠翹笑一笑,抽回手去。
綠翹道:「我見你這一趟出門回來,老是悶悶不樂,像是添了老大一件心事,
事情辦得不順?」玄機道士道:「這種事有什麼順不順的。左右不過是願打願挨,
他出得起什麼價,咱們給他什麼樣的官。不過今年不比往昔,這一行越來越難做,
一路上我碰上好幾撥,長公主,長樂公主,宰相府今年都派人出去了。哪一撥人都
比咸宣觀勢大,我們不過是吃些殘羹冷炙,再過幾年——」她看看綠翹,歎一口氣,
不再說了——再過幾年,她人老珠黃,加之朝中人事更迭,她總有再也撐不起場面
的時候,到那時候就只有看現如今觀中幾個小丫頭的能耐了。幾個侍婢中間,靠得
住的或許只有綠翹能繼承她的衣缽——她不是最拔尖的,相貌不夠好,但有一樣頂
合她心意,簡直是她一手造就的——善解人意,不僅能夠摸透男人的心,也能摸透
女人的心思,更難得是她跟了她幾年,從來沒有二心——不過也難說得很。玄機道
士半閉著眼,不禁微笑起來,別人她說不準,可是綠翹她卻是看准了:她不會跟她
作對。
綠翹見她微笑,不覺詫異,道:「瞧瞧你這個人,喝這麼幾杯,也不至於醉了
呀,醉了也不用作出這副怪樣,怪嚇人的。」說著過來扶她。玄機道士仍半閉著眼。
一手擋著她:「我好著呢,你別理我。我告訴你,你只管找出帳本來,一筆筆好好
記著:山西靈谷的錢茂元,出一萬兩,平谷的李琳出八千兩,蜀中的吳大誠出一萬
二千兩,蘇州的孫小三出五千兩……」她屈指數著,綠翹一筆筆記著。末了,她張
開眼睛,側過頭去略看了一看帳本,皺眉道:「這麼簡單,記得清楚嗎?可別弄糊
塗了。」綠翹笑著拍拍帳本道:「忘不了,哪一筆哪一個人,都在我心裡記著呢,
您放心——錯不了。左右不過是些小錢,隨便派他們一個小官就行。」玄機道士聽
了,瞅她一眼,歎口氣道:「數目是小了點。錢再少,可好歹是生意,不能大意,
弄錯了,壞了規矩。」綠翹也低沉了聲音:「誰說不是呢。」側頭想了想,又道:
「這幾天,趕春闈的各地才子已陸續啟程,早的,已經到了長安城,我們總該還有
幾筆大生意,只要你在李宰相跟前說句話,什麼都成。」她悄悄看一眼玄機道士,
見她微皺雙眉,便忙道:「你要是有什麼心思,可得趕緊說出來,你不出面,我去
求求他也行。他哪能不瞧著你的面子。」話未說完,被玄機道士中間截住:「我理
會得。」便不再吱聲了。
綠翹見玄機道士頗有倦意,起身走到窗前雙手一推,冰涼的空氣湧進來,不覺
打了個寒噤,叫聲,「好冷。」又關上,打了個轉身,徑直到隔壁去喚醒婆子,用
個紫檀託盤裝了粥菜,一併端上來。
綠翹陪玄機道士嘗了幾口,一邊向她一一稟報觀裡的幾筆收支。玄機道七不置
可否,只問道:「她們幾個人的琴技學得怎樣了?」她是指最近新買的幾個侍婢。
綠翹少不得一一向她稟報,這幾個侍婢是去年春上她親自去江南挑選的,花了不小
的一筆銀子——她不要那些逃荒的,這是她的忌諱,綠翹曾隱隱聽說玄機道士幼年
時逃過荒。綠翹皺著眉頭道:「都是些不上進的,不趕緊趁著年紀小,用點心學點
技藝,笨點的也學點應酬工夫——光顧著玩,什麼都不上心。前天那個山西客還來
過這裡,支了好大一筆胭脂花粉錢。我們買這些女孩進來,倒作成了他的生意。這
麼沒出息——你還淨寵著她們。」玄機道士放下筷子,懶懶地伸了個腰,道:「是
不成話,你就往死裡打罷——看教訓出哪種粗使丫頭來。咸宣觀以後就指望著她們
了——不過也不能由著她們的性子,慢慢調教,咸宣觀要的是哪一類人才,你又不
是不知道,跟朝中那些大老爺們周旋,可不是鬧著玩的;得跟那班清高的讀書人往
來,還得籠絡著那些個無恥之徒——他們出得起錢;要能高能低,能貴能賤,這其
中的利害也不是三天兩頭裡教得會的,只能預先每日裡耳提面命地叮著幾句,過些
日子,慢慢帶她們出去見見世面,揀幾個老成的放她們出去交情,讓她們自己慢慢
琢磨,那時方知咱們今日所言是些真知灼見——她們自己得來的教訓,記得牢著呐。
那時候,優勝劣汰誰高誰下一眼便知。成的,便留下,支撐咸宣觀這塊招牌,給你
養老;不成的,只能慢慢熬著留著使喚,怎麼也比外頭買來的粗使丫頭強,不知你
覺得這樣成不成?」
綠翹笑道:「成,成,怎麼就不成,你怎麼說都成,這裡的道理我也明白,還
用得著你教嗎,跟你那麼多年,你的心思我哪能不明白。你放心,這幫小妮子我留
意著,誰該松,誰該緊,我心裡都有一本帳,哪個不聽話,我就往死裡打——哪能
就打死了呢。咸宣觀這幾年買進賣出的人多了,看哪一回教訓丫頭能訓出人命!」
玄機道士笑笑,冷眼看她:可不是,她越來越像她了,說話、舉上、心思都像她。
早些年跟綠翹同一批買來的小丫頭如今都散了。當時她可沒少親自動手,不打不成
才。這幾年這些事她不親自出面了,不打不成才。當年她可從不手軟,想來綠翹也
一樣。只是對於綠翹,她從來都沒動她一根手指頭。
綠翹說笑了幾句,忽覺一陣寒意,不覺雙手交叉,緊了緊搭在肩上的披風,仔
細一看,原來取暖的火爐已不知什麼時候熄了,便問玄機道士:「你也困了,不如
咱們就散了,我叫她們來收拾了去,你早點歇著。往後這幾個月你想閑也閑不了,
收了人家的銀子,總得給人家跑腿。咱們觀裡的事由我擋著,你只管放心在外頭,
聽說你回來了,少不得又是一大堆應酬。個個都是貴人,還不算那些職位低,有能
耐的,哪個都得罪不起,哪個你都不好意思不去敷衍幾句,——生生把人累死。」
玄機聽她這一大堆抱怨,便道:「我累我的,倒聽你這一大堆話。」一邊轉身。
綠翹趕過來把大毛衣服給她穿上,又取了一個燈點上,笑道:「可不是嗎,在
你身邊這麼多年,別的沒學會,倒連話也不會說了。」玄機道士停了動作,想了想
道:「——你在這兒快有十年了罷?」綠翹撫一撫髮髻,道:「那時還是個小丫頭
呢。」玄機道士看著她,也輕聲道:「可不是。」一語末了,兩人都有點愣愣的,
一時想不起說什麼話。一會兒,玄機道士道:「這幾年難為你一直跟著我,沒有你,
就不會有今天的咸宣觀。」這是肺腑之言,還有一句話她沒有說出來:沒有綠翹,
也沒有今天的玄機道士,她們是天生的搭擋,誰缺了誰都不成。十年來,諾大的世
界,只有她們倆才是骨邊的肉,肉中的骨,一旦分離,是撕心裂肺的痛楚。玄機道
士輕聲道:「世人只知道唐朝有長安,長安有咸宣觀,咸宣觀有玄機道士。卻不知
道有綠翹。」
綠翹呆呆地看了她半晌,忽然流下淚來。玄機道士不看她,向著門外道:「你
也該為自己的今後打算了,這些年你做得很好,咸宣觀交給你,我很放心。」綠翹
強笑道:「這些年來,我已把咸宣觀當作一生一世的家了,我能有什麼打算,這一
輩子我只求能替你守著這個家就成了。」玄機道士不覺看她,見她兩行熱淚滾滾而
下,苦笑道:「就是這句蠢話,真是個傻孩子。家?這哪是什麼家,你比我更清楚
這兒是什麼。是咱們在這世上暫時的一塊棲身之地,算不得什麼。過得幾年,住這
裡的人都散了,只剩下幾尊泥菩薩,你就知道我今日的話。」綠翹低聲道:「只要
你在,我在,這咸宣觀就是家,就是哪一天你不在了,我也守著它。」玄機道士道:
「要是我死了,要是我不回來了呢——別這麼死心眼,咸宣觀算什麼,你可以成全
它,也可以毀了它,可以一輩子住著,也可以哪一天走了,但它什麼都算不上——
你怎麼就不明白?」綠翹頓足:「我就是不明白——」回過神來,盯住玄機:「你
說你不回來,你要到哪裡去?」
玄機淡淡一笑,道:「我有什麼地方可去,我不過是那麼一說,提醒你,趁早
為自己打算,別像我……世事難料,別等到有變故的時候措手不及?」綠翹道:
「像你怎麼了——」玄機搖搖手,阻止她說下去,伸手過去撫了撫她的臉頰——淚
痕已經幹了,到底是年輕,淚水也來得快去得快,十年前的自己可不是這個樣子。
她記得自己走出李府的時候……她在心裡暗暗歎了口氣:怕有十年,沒流過一滴眼
淚了吧。她向綠翹笑一笑,轉身走了。從紫雲丹房到她獨居的小院要穿過放生池和
兩重大殿,她一邊走一邊仰首看著那些黑黝黝的巨像,那些在黑暗中仍睜著凸出的
泥金的大眼睛,有著靛藍的眼珠子,驚詫的然而漠然的——是假的,她早就知道。
可十年前初來此地,頭一晚她還是被嚇得險些跌倒。而今什麼都慣了,眼熟了,也
沒什麼可怕。心驚的事情不是沒有——像那件事情……可是一直存著僥倖,如今,
真的來了,她還是有著似真似假的感覺——十年來,她一直只把這當作暫居之地,
只是沒想到一住就是這麼久。然而,十年,還是太短了,太快了,在她剛心定的時
候,有迅雷不及掩耳之感。其實她早該想到,在蜀山初見戴春風的那一刻。可只是
剛才與綠翹談論咸宣觀的種種打算時,她才猛然悟到:是時候了,她和咸宣觀的緣
份盡了,是應該離開此地的時候了。只是綠翹還不知情,她已經把話給她了——知
情又怎樣,她幫不了她的。再說,不知情也好,這些年綠翹跟著她,她的那點糊塗
心思,……醒醒也好,任由她誤會好了,哪一天綠翹發現她忽然不辭而別,她或者
會怪她,但顧不得了。——她是打定主意此生再不回到這個地方來了。
她把手探進大毛衣服裡去抓住那件深紫色的袍子,——是他的衣服,她想起戴
春風。按照約定,他此刻應在青城山等她,不,應該在杭州,他說他要去一趟杭州。
等她回來的時候,春闈應該結束了,曲江大會也應該結束了。她的嘴角浮起一絲笑:
不結束也沒關係。真的,只要他不來長安。而三個月後,她應該如約前往找他……
她忽然站住了,前面即是咸宣觀的後園。春天夜裡的霧濃得化不開,像有腳似
地,緩緩地移動著,裹住什麼都不肯再鬆手,死死纏住,緊得透不過氣,像條大白
蟒……原來她不知不覺走岔了道,她猛然間打了個寒顫。這時她好似聽見「錚琮」
一下琴聲,凝神聽,又沒有了,疑心是幻覺,又是一下,還是渺渺茫茫地不真切。
她一下子全身冰涼,閉一閉眼,又使勁瞪大眼,可她前面全是白茫茫的厚重的霧,
卷過來了,像沉甸甸的冷澀的手和腳,她什麼都看不見。
霧散了,後園裡空無一人。
玄機道士在李宰相府邊門下車。她戴著一頂玄色面紗,飄飄灑灑地走過去。守
門的家人是新來的,手一攔,另一邊的李勇忙不迭地一手推開他,趕前趕後地道:
「道長,你別生氣,他是新來的,不認識您,您好久沒來了。」玄機道上微微掀開
面紗一角,向他笑一笑,腳不停步地進去了。李勇躬著身在原地站了一會兒,才回
身瞪了一眼:「沒半點眼色。告訴你,還好今天人家脾氣好,沒跟咱們計較,要不
然可有你好瞧的。」那家人被說愣了,半晌才回了一句:「我又不知道她是誰……」
李勇在他腦袋上啪地一聲,數落道:「要不怎麼說你是榆木腦袋呢,不知道,不知
道也不會在心裡尋思尋思,這宰相府是不相干的人能隨隨便便進來的嗎,人家要沒
跟府上有交情……得,不說這個,反正別人能攔,她你可惹不起,今天還好我在。
做奴才的也是一樣本事,瞧你——不學看個眼色,不會半點機靈勁兒,沒半年我看
你就得捲舖蓋滾出這宰相府。」
玄機道士順風聽到幾句,不覺一笑。這李勇是老家人了,不說前些年,這十年
來她在這兒出出進進,他都趕前趕後地侍候著,當然她也沒少虧待過他。她出手一
向大方,在府裡時也好,出府了也好。有幾個勢利下人,當年跟著人往下踩她,她
都忍了。如今見了,一樣不跟他們計較,一樣的銀子賞賜,難怪他們——當年出府
的時候,可沒誰想到會有今天,連她自己也相信不會再踏進這裡一步。可如今……
他們如今照樣和她當年最得寵時一樣殷勤侍候她,只是稱呼變了:如今他們叫她
「道長」,當年可不是這樣。……她尋思著,不覺胸中一陣翻滾,隱隱有點心酸,
趕緊走快了幾步。
這裡她可算是熟門熟路了,閉著眼睛也能走到任何一個當年她最熟悉、最常去
的地方。她愛的花、池塘、小樓,無一不是按她心意購置設計的,他也由著她。那
時候她驚魂初定,看見了這裡,覺得就可躲在這裡一生一世,生老病死,一生一世
的家,天長地久。那時候可真是沒經過世面,心無城府,抱著一點點小小的快樂就
緊抓不放,心滿意足——怪只怪那個半夜裡常把她驚醒的惡夢,實在嚇得她太厲害。
只想躲著、藏著、掖著,以為不見人,不出這府門便可沒事。如果時間能倒過去,
她當時就能預知後來發生的事,她可能會放鬆一點,放肆一點,享受一點。因為明
知一切都躲不過——不過誰知道,就像她現在,知道又怎樣,還不是一樣不甘心,
一樣地不肯服輸。知道了結果,只怕掙扎得還厲害些——按照她的脾性。冥冥之中
知道什麼是因,什麼是果?如今她回首往事,只剩感慨。
她看見一頂寬大的轎子停著,是他的,他應該已經下朝了。此刻他或許就在書
房,他也許不知道她來,但他應該知道她這幾天會來找他的。二十年如一日,他的
轎子的顏色仍是當年她在他身邊時替他選的,她選的也是他鍾愛的……他的脾性蠻
橫,不講理,有時陰沉得可怕,外人是不知道的,但是——總有好的地方,令當年
的她心折——現在也一樣。她打量了一下轎簾上金繡的花紋:他又多一樣官職,嫁
他時,他還是個職微言低、不起眼的侍郎。近年來,皇上慢慢器重他,朝中權貴更
迭,可他還不是穩穩當當的,她冷眼旁觀,不能不佩服他的心計和手腕。他始終是
謹慎的,權力越來越大,但府裡並沒有擴大多少,只新建了一幢樓:她看見上面的
木匾《春暉堂》——這一點也是他的心計與為人,他從不弄那些浮誇的東西。要是
換了別人,一定取作什麼「天恩堂,」把掛念皇上的恩德赤裸裸地給世人看。他就
是他,他的功夫在內裡。樹大招風,可是他按他的處世原則,雖也驚濤駭浪,但曆
來都是有驚無險。皇上眼中的他,只是一個隱忍的孝子和不貳的忠臣。這是他保身
的高明。
她看見書房門口有一個人影。他果然在等她,她不由加快幾步。他穿著一身便
服,微微的顯出老相來——他一直保養得很好——或許是衣服的關係:脫下一身官
袍,他只是個普通的老人,倦了,在夕陽裡微眯著眼,向越來越近的她殷殷地張望,
細細地打量。
她在他面前幾步遠的地方站住了,在玄色面紗底下微笑著,他向她伸了伸手。
她忽然想起,當年他沒有向她伸手,丟下她一個人站在冰涼的石階上。站了半天,
等了半天,聽了半天,或許是等他出來說句話,或許是只為了聽聽他在屋裡做什麼,
又或許什麼也沒聽,什麼也沒等,只是無意識地站著,站得全身冰涼,冰涼。然而
他始終在書房裡沒有出來——屋裡靜靜的,記不清是什麼季節了,或許有太陽光,
或許只是冬日蒼茫天色下的灰色塵埃。天也是靜靜的,整個宅子全是靜靜的,死過
去了,昏睡過去了。然而她知道在這個靜靜的硬殼下,有些人影在它的芯子裡走動
——是行屍走肉,卻有著幽怨而張狂的活人氣……端坐其中的貴婦——他的原配,
似笑非笑地端著一張大白臉,微張著嘴,方而小的牙齒粒粒可見——對於這世界她
是不貪心的,守著她的這個家,守著她的丈夫就行,因不貪心,所以更固執,更不
讓人,更不容人,偏執得像個小孩。她蠢氣的嘴角有著難得的聰明而得意的笑,她
不能容下那個年輕女人,她知道,只要她堅持,他准會讓步——她的娘家沒什麼了
不起,有些可有可無的貴親戚,可也讓他投鼠忌器……果真,讓她猜著了。可她仍
覺得不痛快。或許只是因為她從窗縫裡看見的那個年輕女人站在書房外石階上的姿
勢——什麼都不顧不管,只是站著,癡癡的,似乎就此站到地老天荒,一往情深地,
只等著書房裡的一聲響動,一聲呼喚。那一刻她真怕她的丈夫受不住忽然從書房裡
出來——那時候她什麼也擋不了他們——她甚至想到,其實當初只要這女人上前叩
一聲門,只要一聲,他肯定會出來……那半天裡,那個年輕女人站在書房外,他在
書房裡,她在遠遠的窗子後邊,等待一樣地長,焦慮一樣地長,甚至她平漠的心裡
覺到的微微的絲絲縷縷的鈍痛也一樣地磨人,以為就此凝成死結,以為就此風雲突
變,可她終於看見那個年輕女人——她也曾叫她二妹,她丈夫的第二個妻子抬腿了……
然而,什麼也沒有發生,她看見她抬起腿轉身,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地走遠了。那
個季節的天色,灰黯得很,她以為天夜得早,其實才是上午,她知道他一定也在窗
子後面注視著那個遠去的女人,雖然他沒開窗。遠遠的這扇窗子的後面,沒來由地,
她流了幾滴眼淚,不知道為誰。她再笨也知道:那個男人,她的丈夫依從了她,把
那個女人趕走了。但從此以後,她再也挽不了他的心。他會始終在她身邊,但他從
來都不是她的。這一點,走了的那個女子同樣也知道,因此她忽然想通了,從石階
上轉身,走得那樣決絕。心裡有著尖銳痛楚的快意。
李宰相走前一步,一手輕輕撩起她的玄色面紗,看定了,微笑道:「你瘦多了。
臉色也不好。」她眼睛發酸,趁勢把臉頰依在他的手上:當年她走的時候,他沒有
向她伸出手,沒有說一句話,更沒有留她,她以為她此生此世再也不會見他,直到
她成為咸宣觀玄機道士,重新走進李府。她求他做事,他無一不允,她也幫了他一
個大忙……她一直不明白自己究竟為了什麼。
他似乎是看透了她此刻的心思,歎道:「其實,當初如果你不走,忍一忍,留
在府裡……」他沒有再說下去。他一直都把她看了個透。她笑一笑,也沒有接下去,
只顧把臉頰偎在他的手掌上,他有些臂酸了,但沒有動。她閉著眼,一副心滿意足
的樣子。她想如果當年她沒有走,結局也會一樣,不管延長多少歡樂,時到今日,
她一定亦像現在一樣,作為一個女道士,玄機道士出現在他面前——一定會有別的
機會,殊途同歸。這些年只有一宗事她是想明白了,如果能重回往日,仍舊在他身
邊,她一定會盡情享受與他的歡樂時光,不管多麼短暫。
他覺得站得太久了,也不想讓下人看見這個情形。她的突如其來的溫和讓他吃
驚,也讓他些許感動,他一直以為,她在心裡恨他至深。他拍拍她的臉頰道:「你
不是有事要找我麼?」玄機抬起頭,笑道:「哪裡是我的事,我不過是替你跑腿……」
玄機道士邊說,邊扶著李宰相進了書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