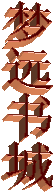
第一章
我四歲時已學會飲酒,沉沉大睡。我做夢,夢見蝴蝶在昏昏的陽光裡翩然飛舞。
光太強烈,使我暈眩。我在夢裡暈眩,與蝴蝶一同飛舞,恍若孿生兄弟。
夢醒時我便見村落起火。是在一場大雷雨之後,雷電擊中村子邊緣的森林。那
一刻我以為是夢中蝴蝶飛來塵世,細看才知是煙灰,他們在諸物焚燒對從火中爭相
逃逸。
我和村人們一起觀看火勢至三天之後,我們在河邊席地而坐。衣食如常,只是
無人耕種捕獵撒網。我們守至村落化為一片灰燼,移地他去。遺落的滿坡農作物無
人收割,任他自生自滅,化為塵土。
這裡所有人都熟知潮汐漲落,卻從不關心自己內心,甚至忘卻了來自何方。沒
有前世,沒有人猜忌這裡的世界。少數孩子或許曾夢想出海,然而稍長年歲便全然
忘記,或許是存心。
村中有夫婦爭執,妻子負氣出走,其他人都不著急。數天后必歸,恍若無事人
一般。在椰林裡織布,唱歌,踩著乾淨的沙子。因為沒有根,無處可去。也有人墮
崖而死,如我舅母,揮力一躍,屍骨全無。舅舅是族長,三日後便娶另一女子回家,
新婦戴著舅母的銀首飾出來見客。
我母親坐在屋外,沒有人留意到她。此時突然沖進來打了新舅母,扯掉她的首
飾,引起一場大亂。我母親是舅舅的姐姐,與死去的舅母是好友。
是她教我飲酒。好的天氣裡,她攜我去海灘,兩人一左一右向海端坐,條狀白
雲酷似沙丘上烈日暴曬下多年的枯骨。長長的時間裡寂寂無聲,海鳥的飛行不可捉
摸,翩然而來,倏然而逝,如同陽光下的鬼魂。我和母親一左一右相鄰而坐,像兩
個前生的好友,前情盡在前塵訴,乍然相逢,唯有默然。
我不知母親何以打發寂寞。童年所見,她唯有空坐而已。有一段時間,我以為
她會就此在海邊空坐一生,望盡天邊過往白帆、夕陽餘暉。有無數這樣的時刻,我
看見她的臉,那是我不能進入的世界。她的臉是安靜的。
有一次她帶我進入海邊一個岩洞裡,我們攀著山藤從懸崖下去約一丈便已到內,
探頭出去下面便是海。母親說潮汐來時海濤距洞口僅一臂之遙。她說這洞此後便是
我們兩個人的秘密。
我們經常在海濤聲中睡著。有一次我在母親懷裡醒來,發現四周漆黑一團,唯
有洞口有淡淡的銀光,原來我和母親酒後不知不覺酣睡至午夜。我爬到洞口,看見
滿天星斗,大海無聲無息在底下奔流。我在洞口坐至天明,看見星辰一顆顆熄滅、
退隱,遙不可及。母親酣睡如同嬰兒。醒來後,我們一齊坐在洞口看了一會兒海,
聽見懸頂上有村人採摘漿果的聲音,啁啾如雛鳥。母親轉臉與我相視一笑。母親伸
手出去,一會兒果然接著一顆滾落下來的漿果,色如胭脂。我想我便是在此時懂得
女子的美麗與婉約。過了一會兒爬出洞去,已是暮色沉沉、我們在海灘上走了一會
兒便回家。此後另有多次,母親在岩洞中酒後沉睡,我在一旁守護。有時我會生堆
火。天邊若有帆船經過,便可看見火光燦若雲霞,但沒人知道那是母親與我。沒人
知道此中快樂與奧秘。
一次父親與島上另一女子睡覺,母親知道後便說要搬去洞中住,永遠不再見父
親。母親把一些零星物件逐漸搬去洞中,我在一邊幫忙,其他人對此事毫無察覺。
一晚半夜醒來,我忽然覺察到母親離去。時已深秋,從我睡覺的木樓望出去唯見深
藍色的夜空,天涼如崖下海水,我聽見自己的心跳和隔壁父親的咳嗽聲,我翻身便
又睡去。次日我果然在洞中找到母親,母親不以為意。我沒有說什麼,枯坐一會兒,
便上崖回去。次日再去,母親砍斷了山藤不肯再見我。
我隔兩日便自家中拿來食物和酒,用山藤吊著竹籃送下去,再扯上來時,竹籃
便空了,有時還是原封不動。隔兩日再來。有時我在崖邊坐一會兒,或在樹上采漿
果。那種色如胭脂的漿果已很稀少了,豐盛時連飛鳥蹲在樹枝上,它們都會僻裡啪
啦往下掉,陽光酷烈時還能聽到果實爆烈的清脆的聲音。在深秋的山崖上,我坐在
樹枝上,想像漿果豐盛美好時的情景。我想像我的腳便是飛鳥之足,那些漿果總有
一顆會墮入母親掌中。
所有人都猜想母親像舅母那樣跳崖而死。我守口如瓶,看守著世人不知曉的秘
密。父親在木樓的窗口讀書,偶爾向我投來懷疑的一瞥,可是部分的時間他都在靜
靜地觀察我。那個與他有過一夕之歡的女子已不知去向。
我坐在樓梯口仰看父親在油燈下吟誦史書,心裡有著與坐在母親的山崖邊一樣
深刻的悲傷,那悲傷突然而至猶如潮汐。如果在三十年後的星空下我回首前塵,我
會看見一個坐在深夜的木樓梯下自言自語的男孩。
如此,我每隔兩日便去山崖邊給母親送酒,攀援于崖邊危樹,風巨時幾欲墮崖,
而身輕似鳥。偶爾上山的村人見我安睡於風中之崖。
又一日我醒來時看見母親,她端坐在我身邊,我默默地跟著她回家,就像很久
以前,兩個人只是在海島逛了半天,逛累了回家。母親若無其事,我也是。或許真
的是什麼事也沒發生,母親只是一個任性的孩子,在外面逛了一圈回家。
走在半路上,我忽然蹲在地下半天不能動彈。母親問我怎麼了,我告訴母親是
睡在山崖,經常肚子痛。母親久久地看著我,後來她告訴我說,春風,其實在哪裡
都一樣,山崖,岩洞。
巴蜀士人戴春風後來又在青城山白雲觀重見長安城咸宣觀玄機道士。
春濃的山裡,遊人懷著獵奇的驚喜,越往前走越是興趣盎然。明知春色在深山,
只是沒料想到會那麼濃,幾乎每步都有驚喜。懷了這樣的心情,眼中所見,耳中所
聞,不是春光也勝似春光,自覺做了最識趣的人。
臨進山的前一晚,月亮明晃晃地照著,襯著墨得發藍的天。因著那藍光,整個
天空都像是晶瑩的,虛虛的,托著一個月亮,月亮邊上一層光暈,是喜極而泣的人
的淚光,清冷的,但不是冷的,有心底的溫暖洇上來,一層一層,絲絲縷縷,幾乎
忘卻了的,然而那麼細微地妥帖著,不由人不感動著那點好——相形之下,那些孤
寒的歲月立時就遠了,遠到與現實不相於的地步,起碼也是那些不見天日的懨懨的
鬼魅,雞啼一聲,便作煙霧散去。清天白日,朗朗乾坤,容不得半點虛假——他和
她的相逢是真的,她的猶抱琵琶半遮面的心事也是真的。他在內心不無佻地把她的
回避看作了矯情。這也得怪她自己,誰叫她在三天前的那個下午,那個酒肆,她扮
演得出神入化絲絲入扣,明知是假的,也不由人不心動,何況真假難分,更增刺激。
他不是個愛冒險的男人,可是這個夜晚他在月光裡仰頭看著,自得其樂地微笑著:
他覺得什麼都可以試一試——既然三天之內,她令他躊躕到如此地步。
他沒想到她在白雲觀看見他時毫不吃驚。其實她的從容更令他心安。他在她跟
前站定,他們站在道觀的院子裡。他注意到院中有一株老梅,一個道婆蓬著頭在廊
下掃落葉,堆成一堆,再燒。應該是早晨太陽剛出來沒多久,因為知道是剛開始,
知道還有大把的時間,所以天地間有一種迷離的、從容的氣氛,太陽就是那夢初醒
時一抹游離的、篤定的笑。棕黑的廟宇的飛簷隔著乳白色的霧,古銅的鐘,泥金的
神像,都像是一幅年代已遠的壁畫——久遠到未曾發現褚色和靛藍的年代;沉重的
靈與肉,被層層疊疊厚重厚重的雲霜壓著,掙扎著喘息。他在這裡覺得沉悶。可是
玄機道士一出現就不一樣了:整個世界原來是不相干的,樹是樹,山是山,可這地
兒一聲令下,忽然一齊緊縮到這一方道觀中來,緊湊的,可還是條理分明,像緊鑼
密鼓在蟄伏,一切都是啞然的,太陽是一束光,照定她全身——只等她開口,然後
可以按部就班地演下去——等待太久,誰都心神不寧。她就有這個魅力。
他一手拿著扇子,一邊走過去心裡在盤算怎樣對她開口,其實是不必要的,那
些話於她。只是她把氣氛造得那麼足,由不得他也興致盎然。直到這時他才覺出自
己有點慌張。
他笑道:「我早該預料到你會在這裡的。」她把眉毛挑了挑,做了一個驚異的
表情。他又道:「你適合於咸宣觀,但我卻不知道你適合於天下所有的道觀。」她
盯著他,慢慢地笑了。他又笑了一笑,補充道:「你好像生來就做女道士的,我聽
說皇家公主,貴妃都喜穿道袍。只是我從來不知道,女子穿上道袍可以美成這個樣
子」。她又在笑。他不知道她在笑什麼,可是信心像受了鼓勵一般。他歷來不喜歡
多話的女人,可此時他希望她開口說點什麼,她這樣安靜地看著他笑——或許是天
熱,他覺得有些口渴。這時他才發現太陽已高高地懸在空中了,明晃晃地,可是半
天不動,像凝固了一般。
她看著他:「或許你說得對,可是你卻生來不適合在道觀出入,」她覺得好玩。
「拍」一聲,他打開了扇子,白底灑金的杭扇在陽光中翻飛得像一隻碩大蝴蝶——
只是逃離不出他的掌心。他笑道:「不適合到怎樣的程度?」她忽地收斂了笑容,
細細地看著他的眼神,似在揣摩什麼,末了,輕輕地吐出兩個字:「會死。」
他怔一怔,驀地大笑起來。她也像上一次那樣慢慢地笑了起來。他覺得她雖是
笑著,眼睛卻仍是審視著他——不獨是她的眼睛,她的周身,甚而她身邊棕黑的樹,
蓬發的老道婆,地上的白冷的石子路,都籠罩在一種窺視的氣氛裡。他心下驚喜而
詫異,然而不自覺地怪自己多心。他定定神,告訴自己這不過是一次豔遇的開始,
在她是如此,在己也是如此。
她伸手取過他的扇子,在手裡把玩著,扇面上乾乾淨淨,沒有一筆劃,一個字,
這未免使她詫異,或許這就像他的人——他這種身分的人,習慣於舉重若輕,不著
一絲痕跡,恩也好,怨也好。她不由得猜想他從前的或者曾經有過的那些女人,時
過境遷之後,至多不過成了這把扇面上的小金點——虛浮在上面,本身一無是處,
只是一種可有可無的點綴。可是他現在就這樣拿著白底灑金的扇子站在她身邊,眼
裡沒有半點往事。只有信心,十拿九穩的信心,對塵世的滿心歡喜與對享受的熱切
的期待,他根本不需要考慮未來——她想如果她告訴他真相,不知會怎樣,當她一
個瘋子?或是一句玩笑?她對自己笑了起來。
戴春風注意到她的笑,便道:「你若喜歡,我可以送給你,不過你若肯在上面
畫一株碧桃,我倒情願自己留著。」她看一看扇子,笑道:「你怎麼知道我喜不喜
歡?」他道:「你若喜歡,不過是一把扇子而已,你若不喜歡,也不過是把扇子而
已,只不過我有點私心,誠心誠意盼著它能代我時常陪著你,盼著你能時不時想起
我這個人」。她輕笑一聲道:「這個並沒有什麼好處,即使我想要你陪,你也不見
得肯呢。」他笑道:「說得也是。」
她把扇子打開,半遮住臉,露出一雙眼睛看著地下,不知在想些什麼,驀地裡
把扇子一收。「嘶」一聲輕響,倒使他微微一驚。她把扇子的頂端支著下頦,慢慢
地左右移動著,道:「那麼你到處找是為什麼呢?」她的口氣冷冷的,眼睛卻是笑
的。他從她手裡取過扇子,慢條斯理地搖著,並不說話,踱了幾步。
老道婆進去又出來了,此時坐在廊簷下,前面是一隻紅泥小火爐,她坐在那裡
打瞌睡,爐子上的壺裡不知在熬什麼東西,可半天也不見有熱氣冒上來。戴春風就
這樣來來回回走了兩步,院子裡分外地靜,玄機道士心中不覺有些發急,答案其實
她早就知道,可是還得做戲做下去——兩人都在演一齣熟透了的老戲。這時他突然
轉過來,他似乎想了想,笑道:「我是在找你嗎?我倒覺得我們不過是處處相逢。」
一刹那他神色茫然,似乎自己也吃不准是怎麼回事。他看見她面無表情,自己也覺
得自己說了一句最落俗套的話,不過也難說得很,最俗套的往往最得人心,不出人
意料的情話平乏是平乏了點,不過有一種最安穩的妥帖。像一味叫「療妒湯」的藥,
雪梨冰糖水,於事無補,可往往有意想不到的奇效:無過便是功德圓滿。他想起他
曾在洛陽坊間認識的一名紅歌伎百合——他們的相逢也是最落俗套的:他慕名去尋
歡,她待他如尋常恩客,稱不上有半分特殊甚至有點壞脾氣,可是有一點,他說什
麼她都信,開始他認為她作假,後來發現這是她的脾性,像一個小孩子,他心下詫
異:竟有這樣的人……不免有一絲感動,有關她的其他好處他都沒有什麼印象。可
是為著這一點她對他結結實實到蠢的信賴,他直到現在還時不時地想起她來。現在
想來,當初自己對她說的,也不過是些平常到極點。被世人用濫的假話。
他後來想起,或許就是他說的這句話觸動了玄機道士。她說的那幾句話,當時
情景下,未免殺風景。她笑道:「我早就知道你是戴春風。」他心下不免詫異。可
她接下去細細詢問他的年齡、籍貫、業師,認真到今他忍不住失笑的程度。他看見
她在屈指推算,便笑道:「人算不如天算,你算歸算,我可是不認帳的。」她睜開
眼,淡淡地道:「不用你認帳,自有人替你認帳的。」他覺得她這話糊塗,便趁勢
道:「只要你肯替我認帳就行。」她不再言語。
他等了半晌,看見她還在閉目推算,可是手指不動了,不知道在想什麼心思。
他不耐煩起來,轉過去向著廊簷踱了幾步,冷不防那小火爐的壺咕嘟響了一聲,像
睡夢中的人打了個哈欠,又歸沉靜,把他嚇了一跳。轉臉看見玄機道士的眼光停留
在他臉上,不由一笑道:「說一個來聽聽,好也罷,歹也罷。」玄機道士把眼光移
開,道:「沒什麼,一件小事而已,你的書房會毀於一場大火,」他做了一個驚訝
的表情,太明顯了,連自己也能想像其中的揶揄:「哦,是麼,什麼時候?」她知
道他不信,下置一辭,本來,也是她胡編的,純屬心念一動。誰叫他這麼忽視她的
警告,嚇唬嚇唬他也好,當下再不理會他,轉身走了。
她發現不論她去哪裡,他總能找到她。她不躲他,由著他來去。她懷著一種複
雜的心態細細探究他的一切。其實也沒什麼:他寄居在城中香火極盛的般若寺中—
—不是道觀,她想起他取笑的那些話,不覺自己一笑——他單身在此,連書童也沒
有——似乎真合了一句「來去無牽掛」。他于她是一個全然陌生的人——只除了一
點……可是這陌生仿佛是長在他身上,已成為他這個人的一部分:除了他告訴她的,
她再也找不到一點蛛絲馬跡——可能她自己也不明白自己在找什麼疑點——疑點是
有比較的,可是她對他一無所知。但是——他的一切又似乎太明白了,明白到了令
人生疑的程度:大太陽底下不是沒有鬼影,是人眼看不見。
她對他——有時不免懷疑自己心裡鬼影憧憧,可是一看到他,她不由得悚然警
覺——不會錯的,再也不會錯的,她告訴自己。
他們後來又去了青城山,故地重遊,不清楚是誰先提議的,或者雙方都無所謂,
七天過去了,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雙方都有些懈怠。她不知道在他心裡是否還有
暗暗的失望,一切都無從預料。她沒有急著回長安,或許下意識裡早已知道這一點,
可更多的是她的不甘心,她的好奇——二十年過去了,好容易有這麼一個真相大自
的機會。「殺了我的頭也不後悔,」她想。她這樣想的時候,她還不知道一句無心
之語亦可成讖語——待得領悟,一切都已無可追悔,為時已晚。
第二次去青城山的當晚,他們在白雲觀附近的一間木屋住下。是月半時候,可
是出奇地亮,不容人,她向他笑道:「我這才知道原來古來多少寫月亮的文字都是
逛人。月亮就是月亮,其他什麼都不是。」他輕笑了聲道:「不知道是月亮逛人呢,
還是人逛人自己。」聽得她不由得一怔,自認得他以來,一直都見到他那點什麼都
不以為然而又什麼都不是的浮浮的笑——看輕了天下人,只是沒料到他會說出這樣
的言語。她側臉向他細瞧了半晌,確信了他只是無心之語。木屋外是一叢細竹,在
夜風中龍嘯鳳吟,可是——竹影斜映紙窗,她只是心生不快——細竹雜陳如一蓬亂
發,山風由東而西地來了,遇到山竹便滯住了,在其中狼奔豕突,試圖找到生路,
可是糾結太多,只是徒然地在其中嘶叫不停,不依不饒,如同細獸。好容易待勢大,
一陣陣把細竹壓彎了,蓬發只向一邊傾飛,世界漸有條序,不提防蓬一下,又一下
子反彈過來,又亂如蓬發,起起伏伏,如難以下定的決心。她吃驚地看著,不禁泄
氣。月亮太亮,亮到慘然的程度,也讓她滿心不快——四處是鬼影憧憧。她轉到屋
後,見堆著一堆山石,可能是山民用來建屋、壘灶的,她猜不出,可是那山石,凹
凹凸凸,在月影中明暗有致,個個分明,猶如壘壘白骨,她不由退後一步,握緊了
自己的手。她的眼光驚訝地停住了,她看見自己伸出的手,不知不覺虛握成形,手
空握住一把無形短劍,蓄勢待發,她打了一個寒顫——那是一把二十二年之前的舊
劍。
忽然有只手在她肩上輕輕一拍,悄沒聲息,她於頃刻間一個轉身,戴春風猝不
及防,險些摔倒。他這才發覺玄機道士的姿勢:兩指並著,指尖離他的喉頭只有兩
寸之距,他不由得怔住了,玄機道士也怔住了,兩人面面相覷。玄機道士呆呆地看
著自己的手——她沒想到這一刺如此快捷,如此純熟,就像已練過千百遍——可不
是,二十二年來,她夢見它恐怕也有一千夜了罷,她沮喪地想。她維持著這個姿勢,
是不敢動,也不敢眨眼,怕一眨眼間,一切頃刻就倒坍。明知一切都未發生,可她
仍然不敢動。她已經心飛天外。
他為她的神色所嚇住,一會兒才緩過神來,可是「一會兒」亦是「一刹間」,
在快如雷電的一刹間,他什麼也沒意識到。他乾咳了一聲,想起剛才的驚慌,略微
有些尷尬。可他自以為是那種最善隨機應變的男人。他微笑著,似有意無意間擋下
玄機道士的手,伸出手去虛虛地攬著玄機道士的肩,道:「我不知道你原來也會舞
劍的。」玄機道士向後退了兩步,靠著石子堆站著,一言不發。戴春風看不清她的
表情,對她的反應頗為不快,可心下詫異,他覺得他的手剛才碰到她的肩時的感覺,
玄機道士似乎全身發抖……他不禁微笑了起來,天下人都知咸宣觀玄機是唐朝最豪
放不羈的風流女道士,可她此刻在他面前是這樣恐懼,與一個尋常女人無異。明知
這恐懼的心情與他無關,可他還是忍不住暗暗欣喜。他側耳聽了聽,想,此刻青城
山上,此時此地,只有一個尋常的女人和尋常的男人……他不知為什麼忽然想到:
他與她的這段相逢,他要的,可能不是他心裡以為的,是一段豔遇。或許他和她都
錯了……他這樣想的時候不知不覺地向她伸過手去,聲音也柔和了:「過來。」可
是她仍然站在那裡,這次他看清她了,她的眼裡是深深的恐懼。他越加糊塗了,因
為糊塗,更加小心翼翼,凝神屏氣,放低了聲音,卻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他的模
糊的喉音在四周空曠的山野裡引起了略微的回音,森森鬼氣,連他自己也心下一凜,
不覺住了口。
他們倆都沒料到山石堆後便是懸崖。她的黑白條紋道袍忽然從他視線裡消失的
時候,他還沒來得及反應,接著便聽到了她的驚叫和石子、樹根等雜物滾落到崖下
的聲音。她掛在崖邊,等他把她拉上之後才發現她死死扳住的只是一塊極其圓滑的
大石,沒有半點棱角,他不覺蹲下身去伸出手臂,試了試,搖搖頭,又側頭看看玄
機道士,想不明白她何以藉此逃生。
他不明白她是嚇糊塗了,還是生性冷淡。他見她只是直直地站著,不言不語,
也沒向他看一眼,便向木屋走去,被掛破的衣袖一飄一飄的,只是若無其事。他不
由得出了半天神。
回去,他在門口的大月亮地站了半晌,遠處白雲觀青黑的屋頂和粉白磚牆,是
他在白天時看慣和熟悉的顏色和質地。只是一刹間,他覺出這遠山,這屋子都是有
生命的,無聲地呼吸著——只待一聲異響,一聲慘叫,一聲哭泣,便撲上來,不問
情由地把利爪碰到的第一棵樹,第一個人撕成碎片。他無緣無故地覺著茫然和恐怖。
然而,他深深地吸了口氣,清新而冰冷,是理智的人世,他又覺得自己內心的不可
理喻和荒唐——他決定了。
他隔著窗子看她,她半蹲著,好像在找什麼——看不見,也無心去看。他眼裡
只閃著她的衣角,黑白條紋交叉,在她身上憑空成了一層網,或者是柵欄,關住所
有的不可能性。他不由得揣測,她年輕時,或者再往前一點,她還是個初諳世事的
小女孩時——那時候生命裡只有好,生命裡所有的好才開始:像祖父年青時候的大
唐王朝,什麼都是好的,什麼都是開始,什麼都來得及,四海靖平,歲月祥和,腐
朽皆可化為神奇;都以為一日如十年,十年如百年,百年如千年,千年亦如萬年,
愛與痛皆是天長地久的事,是鐵打的江山,是萬世的基業,一切恩怨都可由著人的
性子,慢慢來——連傷痛也是鮮辣辣的,有著火的的新鮮,痛得真切,也癒合得快……
可不過是百十年的功夫,或許只是一眨眼那麼短,那麼短……輪到他眼中所見,只
是一個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王朝,或許腐爛早就在它的全盛時期就開始了,只是
一切太絢爛,一切太好,令人無暇他顧。見她的身上就是一層網,她有她的世界,
由她來決定生、決定死,決定種種的可能與不可能——二十餘年的放縱,淫逸與驕
橫,到如今已是覆水難收,他料想連她自己也做不了自己的主。他又想起她的那首
詩:
紅桃處處春色,碧柳家家月明,
柳上新妝待夜,閨中偶坐含情。
芙蓉月下魚戲,(蟲+帶)(蟲+東)天邊雀聲。
人間悲歡一夢,如何得做成雙?
這一刻他覺得他似乎了然她的心事,他已經覺察到了她的危險性,可是他不由
自主,對這個相識七天的女人心生親近。
他在那裡兀自出神,柴門「呀」的一聲輕響,見她托著一隻竹託盤出來了,她
微笑著把兩隻粗瓷碗放在石桌上,他跟過來看一看,雙手舉碗,淺嘗一口,不禁一
笑。她輕笑道:「一碗白水而已。」他又笑一笑,道:「好水。」他說的是真的。
她聽了不由得默然,頓一頓,又道:「你若喜歡,一碗白水而已,你不喜歡,也是
一碗白水而已。」他一怔,卻說不出話來,她用了他的句子來還他,語氣卻是苦澀
——如果他沒聽錯她的弦外之音的話。她聽他半晌不語,拿眼看他,他只看著月色,
默然半晌,忽道:「我在想你的那首詩,紅桃處處春色,碧柳家家月明。」她不語。
他又道:「我在洛陽,有一日學中紛紛傳抄此詩,聞說咸宣觀玄機道士此詩一出,
士林皆狂。」他並不喜歡這首詩,可是看了這樣的詩,就不免要想到寫詩的人。她
確信他並不是在調侃她,還從來沒有人當著面說這些,尤其是那些懷著各種各樣目
的來到她面前的男人——她大膽放肆,反而使他們私心裡有顧忌。她低了頭,輕輕
道:「溫飛卿、李子安、李近仁等都與我有詩文往來。」——她不需要避諱,有詩
文往來,或有過一夕之歡,只是說法不同而已。他「哦」了聲,便不作一言。可是
她忽然有了興致,笑道:「你若有興,我可以一首首念給你聽。」他不置可否,她
便一句句念給他聽。他閉著眼,似聽非聽,不知道她什麼時候念完的,可他的心還
有所待,還在懸疑——或許他只是為了感受她的聲音:這一刻隻為他所有,縱使她
講的,不過是她與別人的故事。他真正覺得自己是糊塗了,可是同時又心如明鏡。
他在等著,她卻站了起來,收拾東西進屋,他眼睜睜地看著她,忽然一把拉住
她,她並不意外,然而他只是搖搖她的破袖:「破了。」她低頭看一看,道:「剛
才被樹枝掛破的。」一來一往,都是可有可無的廢話,可是心思在問答之間漸漸轉
換了,她的聲音也不知不覺柔和下來。令她詫異的卻是他身上帶著針線,拉她坐下
來,一針一線地縫。她起先是百感交集,然而漸生寒意:他與她漸接近——一切太
順利,太像一個陰謀,或者根本就是一個陷阱,每一步,縝密到天衣無縫的程度……
不知他是否生疑。驀然間,她對著冥冥之中的天意冷笑了一聲:她偏不信,她要改
變整個事件的發展。此刻她感受得到他的心跳,他的體溫,他的衣服殘留的熏衣香……,
只是,那個結局,他與她之間的最終結局,令她不寒而慄。他與她,只有她熟知一
切往來事。只是、沒有證人。但是,如果她告訴他呢,或許,有一條生路。
她看他站起身來,他不由得問:「怎麼了?」她定一定神,向四周看一眼道:
「我想,我們不如就此下山。」他不禁一愕。她淡淡地道:「興盡便是索然寡味,
此時下山,是功德圓滿。」他瞠目結舌,不禁對她刮目相看:知他心的,是她。剛
才自屋後回來,他便決意下山,只是山路崎嶇,更兼黑夜行路,他不禁心下躊躇,
更有一層理由,他不知她的心思,怕無端尷尬。
他道了一聲「好」,兩人便相偕下山。一路上只是默然,他舉著在山屋裡找到
的松明子,火光搖晃只覺身前身後皆是她的影子,連真人也是似真似假了——只聞
腳步聲,腳步聲也是他一個人的,她穿著絲履,落地無聲。可是一切的一切,都讓
他放心,她在此時並不比在陽光裡更為虛幻。
她笑道:「我說下山,你便下山,可有比我們倆更瘋狂的?」他在黑暗裡笑了,
道:「不要緊。」她不明白,問道:「什麼不要緊?」他停了一停道:「不為什麼。」
他想此夜應該任意妄為,只怕一生也只一次像今夜的放縱,今夜發生的無論什麼事
都應該有理由,都應該被原諒。可是,什麼事也不會發生,他隱隱覺得遺憾。這只
是一個平常的夜。他忽然衝口而出:「我有一種奇怪的感覺,為什麼我們會重遊青
城山,因為我早就知道會有今夜,今夜我門夜下青城山像這樣,我舉著火,而你這
樣和我走著。」——真的,就連此刻她的頭髮被山風吹起,無意間拂在他的臉頰上
的感覺也是熟識的,像在夢裡走了千百回。他不由得變了臉色,伸手出去,他要觸
摸到她,感覺她的存在,以證明他不是身在夢境。
她感覺到他的手隔著絲袍用力地握著她的手臂,她一動不動,被一種恐怖懾住
了,臉色蒼白,她的高髻被吹散了,散著長髮,千絲萬縷猶如心事——她不知千言
萬語如何講起,講起來自己也覺得荒唐。她只是怔怔地看著他,作不得聲,他在頃
刻間頓悟,發急道:「會有什麼事發生?」她眼睜睜看著他,從牙齒間擠出微弱的
聲音:「你會死。」說罷,淚流了下來——連她自己也料想不到。他愣了愣,她緊
張地注視著他的反應,他一下鬆開了她,似乎不知所措,卻舉著火向前走著。她跟
在後面,不時偷看他的臉色。走了一會兒,他停下了,玄機道士轉到他眼前,她看
見他的臉是平靜的——他側過臉去,似乎忍受不了她的目光,他道:「我不需要知
道未來。」她有點急:「你不相信?」他不置可否,他走得太快,她迫了幾步,黑
黑地看不清楚,一不留神便絆倒在地。
他轉過來看她,蹲在她前面,拉她起來,她不動,忽然一伸手死死拉住他的手
臂,拉得他生疼。她清清楚楚地低聲道:「今年的新科狀元姓戴,名春風,可他會
死在曲江大會當晚。」
他凝視著她,原想說句玩笑話,可是此時忽然傳來一聲嘯聲,他們同時向山上
望去。可是他們什麼也沒看見。倒是看見了對方的臉,恍忽猶如幽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