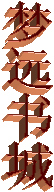
03
留園這天與往日有點不一樣,遠遠地邯鄲便聽見京韻十足的梅花大鼓的聲調,
倒是字正腔圓,只是聲音還不夠透亮。這梅花大鼓在上海的茶館歷來是不多的,邯
鄲一時有些好奇,穿過茶館時便向臺上望去。只見一個白衣黑裙的女孩子手裡拿著
兩塊朱紅板敲著唱著,唱的卻是隋唐開業的大事,與他平日所聽的曲子不相干,不
免向她多看了一眼。也就是那一眼間,臺上的女孩子白衣黑裙地唱著做著,邯鄲在
她的生命之外靜悄悄地穿過人群飄飄地進去了。
進去了,裡面正有人在唱著:
恰正好嘔嘔啞啞《霓裳》歌舞,不提防撲撲突突漁陽戰鼓。劃地裡出出律律紛
紛攘攘奏邊事,急得個上上下下都無措。早則是喧喧嗾嗾、驚驚遽遽、倉倉卒卒、
挨挨拶拶出延秋西路,鑾輿後攜著個嬌嬌滴滴貴妃同去。又只見密密匝匝的兵,惡
惡狠狠的語,鬧鬧炒炒,轟轟騞騞四下喳呼,生逼散恩恩愛愛、疼疼熱熱帝王夫婦。
霎時間畫就這一幅慘慘淒淒絕代佳人絕命圖……。
是《長生殿》裡彈詞一折李龜年細訴當年往事的一段。人人都有當年往事,說
起初怎麼驚豔了,怎麼沉落了,又怎麼雲淡風清了的故事,獨他沒有。他坐在一個
僻靜的角落裡,很孤寂地聽了半晌。回頭卻見一個女孩子正倚著門聽曲,聽得很專
注,白衣黑裙的便是臺上那女孩子。這種地方女子很少來的。邯鄲也不便多看,便
把目光移了過去,一時似乎觸動什麼,想起一些若有若無的舊事,譬如,像小時候
住在蘇州鄉下跟了奶媽的孩子在外面玩,天是高的,地是平的,山清水秀,他不知
怎麼會想起這個來。
想遠了,後面的一段便沒聽見。再注目時卻是那個女孩子在唱,正好斜對了他。
他沒想到一個女孩子竟會唱這樣的曲子,是《山門》一折裡魯智深「漫揾英雄淚,
相離處士家。謝慈悲剃度在蓮台下,沒緣法轉眼分離乍。赤條條來去無牽掛。那裡
討煙蓑雨笠卷單行?一任俺芒鞋破缽隨緣化」一段。因是京戲,唱得慷慨激昂。再
看她的臉,果然是有主見的模樣。尤其注目的是黑黑的兩道長眉。他不由地對她另
眼相看,因是剛才唱了梅花大鼓,感覺上她便不是此地人。別的也沒多想,他們到
底是兩路人,他一看便知。他從心底裡對唱戲的有些厭惡。他跟俞翠亭學笛子是不
得已,好歹是一種寄託,他不能沒有寄託。這個寄託縱然不頂合他意,多少也解了
他的悶。他對她並無好感,只覺得她有點特別,所以當別人一起擁出去聽那女孩子
唱梅花大鼓時,他是安之若素,獨自在裡邊喝茶,他什麼都覺沒意思。
也不知過了多久。那個女孩子就進來了,白衣黑裙地走到邯鄲桌邊坐下。他不
提防她真的是單刀直入的一種談話方式。陳先生,我聽說你的笛子吹得極好的。他
有點答非所問:我剛才聽說了,李小姐是李老闆的侄女。李紫蕭挑起了兩道黑眉,
詫異地說,哦?聲音是拉長了的。他忽然省過來,他說他知道她的名字,她不免誤
以為他對她注意,專程了去打聽她的底細,如此一想,不由地心中有些懊侮。李紫
蕭一笑,自己說,陳先生,你不妨叫我紫蕭好了。我從小跟著姑媽在北平,在天橋
唱大鼓。上個月我姑媽沒了,就投奔伯父來了。邯鄲說,上海聽梅花大鼓的人是不
多的。紫蕭驚喜地笑著說,陳先生果然是個內行,能聽出我這是梅花大鼓的人這兒
還真不多呢。邯鄲微笑著不作一語,她話裡不免含了有誇張奉承的意思,他豈有聽
不明白的。只是聽了這樣一個女孩子的稱讚,心裡畢竟有幾分驚喜和得意,又想,
這果真不是個簡單的女孩子,才二十不到吧,可處事待人老練處比繡襦有過之而無
不及,到底是從小在天橋混飯吃的。人精得很。
邯鄲說,李小姐,到上海覺得習慣嗎,幾處地方都兜遍了罷,上海沒有你們北
平熱鬧。紫蕭含了笑說,剛來沒幾天,前幾天忙著安頓,還沒來得及看,不過上海
大概也有上海的好處吧。邯鄲說這話是打好了腹稿的,準備她說出譬如「沒兜兒處
呀,陳先生你給我介紹介紹」或者「陳先生有空做我的嚮導」之類的話,他就把早
準備好的一些話搪塞了過去——她想打他主意,他就先提出來,然後不慌不忙地斷
了她的想頭。她這樣輕描淡寫,倒令他出乎意料。一時忘了下文,靈機一動說,李
小姐剛才怎麼想到唱《寄生草》那支曲子呢。說了出來,倒覺得真不是白問,或許
這個疑問早在心裡存著。紫蕭卻不忙回答,把兩手支在桌子上,下巴頰擱在上面,
想了一想才說,不是嗎,沒緣法轉眼分離乍。不就是這麼回事。打從小兒我就聽我
姑媽唱這支曲子。咱們唱大鼓的能有什麼能耐,要真像了魯智深就好了,來去無牽
掛。可是像不了他,只好白唱唱,騙自己罷了。他覺得她說的話沒到點子上,聽不
大懂,可是其中一種身世飄零的蒼涼味卻使他起了惺惺相惜之感,他這一生沒經過
大的生離死別。可那種身不由己孤家寡人的滋味他卻不是不知道。
後來談話又很自然地繞到邯鄲的笛子上來。活一開頭,邯鄲自己也不知道自己
隨著敘述竟然有了一種如釋重負的感覺,他在她面前一定程度上太急於傾訴,一講
就講到了自己小時候怎麼在奶媽家過,後來又怎麼回了家在閣摟上偶然間找到了這
支笛子,其餘的他沒說,他知道她肯定知道他家的底細,像她這樣的女孩子不會缺
個心眼似的跟一個陌生男子一見如故。她是有備而來。他知道她要聽的也不是這個,
也不是他小時候的傻事,她用意不在此,可他還是說了。邯鄲想了一想,又說,這
支笛子還是我三叔給我的,給我的那天他就死了;後來有人說不吉利。紫蕭不自覺
地放下手裡的笛子,臉色都變了。邯鄲把笛子拿起來,放在嘴邊輕輕地吹了一聲,
對紫蕭笑道,他們說要扔了,我不肯。紫蕭明白地說的家裡人便是他母親,因而抿
了嘴笑道,看來你小時候肯定不是個乖孩子,這麼不聽話。她不知這話卻正好犯了
邯鄲的忌。邯鄲把笛子往桌子上一放,懶懶地說,誰知道呢,李小姐肯定很聽你母
親的話樓。紫蕭靜了一靜說,我從小就沒了爹媽的。邯鄲心中略略一動,有些後悔,
可臉上一時下不來,辭色間依舊是冷冷的,正想著怎麼想個法子混過去。紫蕭卻已
識相地轉移了話題。邯鄲便說,李小姐,我剛才見你在敲兩塊朱紅板,是什麼呀。
這個他倒真是不知道。李紫蕭拿出那兩塊板來,一手持一塊說,這個呀,叫做紅檀
板,我們唱大鼓用的,我們李家傳了好幾代呢。她說著用兩塊板敲擊一下,笑著對
他說,是我的吃飯傢伙呢,逃荒啦,兵荒馬亂啦,我帶了它就跑,一路唱過去,好
掙口飯吃呀。他知道她是在說笑,一時也來了興致,便說,那好呀,我也有笛子呢。
她笑著包他一眼,道,你又在說笑了,你哪能跟我們比,你是天生好命的,怎麼能
拿了根笛子做江湖中人。我們是混一口飯吃,你不同,怎麼行呢。她一陣「你們」
的平白地兩人之間的距離遠了許多,使人不能不感到寂寞。他忽然泄了氣般垂下頭
來,半晌,微弱地說,有一天我也會跑了。紫蕭沒聽清,再追問,邯鄲只是沉默。
紫蕭突然有一種把握不住的感覺,這是以前從來沒有過的,她放了魚餌,他知道這
是魚餌,想吃不想吃卻還沒表露出來,雙方都在暗暗地盤算,相互打量了再決定走
下一步。他是小心的,可她也不粗心。
晚上繡襦過來到書房找鞋樣子,卻意外地見邯鄲沒有出去,伏在桌子上睡著了。
繡糯記得鞋樣子是順手夾在一本書裡的,只管在桌上亂翻,她一眼瞥見邯鄲臂下露
一角書來,輕輕一扯,那只耳墜子便從書下滾落出來。繡襦拿起來看一看仍照原樣
放好,找了鞋樣就出去了。
邯鄲睡著覺得冷,清醒過來,一探手,摸到了耳墜子,閃著桃紅光澤和些許溫
柔。他不禁把耳墜子握緊在手心裡面。一刹那間心裡有溫柔的牽動。他仰面躺在床
上,月光通明地把他渾身浸了個透,他覺得自己是遍體透明的,只有手心裡握住一
點桃紅,那點桃紅是活的,是火在跳。他覺得這是他死灰的生命裡唯一的一點燙手
燙心的火星。
第二天再見紫蕭。這一回他沒有徑直穿過茶館,而是站在一個僻靜的角落裡看
臺上白衣黑裙慷慨激昂地唱著一句句燕趙悲歌。他把頭倚在門柱上,心裡只跟了一
句句音律飛。他頭一次發覺梅花大鼓的韻味竟這樣的決然和不容置疑,於果斷處卻
又山溫水軟、柳暗花明。聽到結束,他便踱進留園的老位子坐下。這天人稀少得很,
只一個瘦老頭在伊伊啞啞地拉著二胡,另一個在吊嗓子。紫蕭跟過來,笑著在他面
前坐下,他也笑。她忽然說,咦,你手裡是什麼呀,握得這麼緊。邯鄲一低頭,不
由得臉發燒,定一定神,微笑了攤開手心。紫蕭看他一眼,卻不伸手接,忽然紅了
臉,笑著道,陳先生。卻又不說下去。邯鄲忽然明白過來,自己手心裡托了一隻耳
墜子給紫蕭看,她自然是以為自己有心買了送給她,又是初次見她後的第二天。他
想她大概是在笑他迫不及待地買了東西在她面前討好。可是自己是不是想送給她呢,
下意識裡未必有這個概念,只是不知怎麼一拿就拿出來了,即使是送她,也未免著
痕跡。這不是他的方式。
他急中生智,說,李小姐你戴上這只耳墜子一定好看。送她就送她,他索性豁
出去了。李紫蕭卻懷疑起來,只有一隻呀,李先生怕是把另一隻送給別人了吧。邯
鄲不知怎的心裡發急,想想這也確實令人難以置信。誰像他這麼傻,在珠寶行買了
一隻耳墜子回來,換作別人,他也不會相信的。沒奈何,只好再扯一個謊,道:是
祖傳之物,一隻老太太給了早先謝世的姑媽陪葬了,這一隻就給了我爹爹。聽說是
印度寶石,不多見的,他自己也沒料到扯謊竟這般順當,毫不費勁就脫口而出。在
紫蕭面前他人也聰明多了,她是有點特別,但到底是小女孩。他自然覺得對她扯謊
輕輕易易。
紫蕭忽又飛紅了臉,睃了他一眼,那給我幹什麼,我哪配呢,這樣的貴重東西。
他繞過去,站在她身後俯身笑著說,我說過給你嗎,也不害臊。紫蕭笑著起來打他,
打了兩下,忽然扭過頭跑了。邯鄲笑著拿了耳墜子追上去。
自那以後,邯鄲十分愛上留園去。常常是下了班在藥房坐一會兒便關上門,慢
慢走到留園去。經過那條走廊走下樓梯時,空洞的空氣裡腳步聲依舊錯錯落落,空
空曠曠。邯鄲的心也是起起落落,起起落落得非常有目的,像他假日偶爾與同事出
去玩經過龍華機場時看見的那一架架飛機。工作多年,他第一次發現樓梯拐彎處堆
積的那些木箱子原來都寫著一些「盤尼西林」之類的字樣。木箱上積著厚厚的灰塵,
人走過,呼吸裡就感到那種陳舊的氣息。木質粗糙的原木箱上用紅筆描的字,極龍
飛鳳舞,有一種沉甸甸的溫暖的質感。走在路上,正好是初春,兩邊匆匆路過的行
人都有一種按捺不住的春意在臉上,一臉的惟恐春歸無處尋。一個拉洋車的車把上
掛了一對鈴鐺,叮叮噹當地跑著,那一霎間天地都仿佛生氣了許多。他走在這一種
明亮背景裡,無論怎麼看都是一副安寧的圖畫。
走過那家珠寶行時,他照例進去彎一彎。原來放耳墜子那個櫃檯裡已換上了一
套新首飾。那只耳墜子像從來不曾在過。桃紅的色澤裡一絲冰涼滑爽似乎還留在他
的掌心裡,可一切都恍然如夢,它在他手心裡停留的時間是那樣短。他忍不住猜想
這只耳墜的歷代主人和他們的故事。一對耳墜是理所當然和平淡無奇的。然而單單
獨獨一隻耳墜則有著不可思議的魅力。因為不成雙,更有著傳奇色彩,使人無法不
聯想到一些有著濃重浪漫意味和悲劇色彩的悲歡離合上去。邯鄲忽覺他與紫蕭的相
遇是天意。
邯鄲聽紫蕭在臺上明眸皓齒地唱。不知為何,她唱的總是那種躍馬橫刀戎馬生
涯。譬如唐太宗怎樣開天闢地,宋太祖怎樣打下江山,說不盡的風華絕代,道不完
的智謀詭計。他不由地想,在這種氣氛下生長起來韻女孩子怎會流於一般的鶯鶯燕
燕呢。她無疑是聰明的,栽了在她手裡似乎也情有可原。紫蕭常常在臺上唱著唱著
就瞥見了他,黑白分明的眼波閃電般過來,邯鄲常有迅雷不及掩耳之感。紫蕭常常
戴著那只耳墜子,鬢如黑鴉耳垂如玉下一點桃紅的炫目光澤,十分新奇,令邯鄲不
勝欣喜。
李鶴田出面了。邯鄲料想到紫蕭叔侄倆必定有所動,只是沒料到有這麼快的。
他的本意是和紫蕭鞏固一下感情,結不結婚他拿不定主意,他母親的意思,還有紫
蕭的性情他也拿不大准,誰能保證她將來不會恃寵而嬌。她從小在梨園中打混,難
保沒有一些上不得檯面的脾性。邯鄲在猶豫不定之際正好碰上李鶴田出面,打亂了
他的全盤計劃。
李鶴田的打算卻讓他出乎意料。李鶴田打開天窗說亮話,開口便道,你打算怎
麼安置紫蕭。邯鄲心下暗暗有氣,只是不作聲。李鶴田緊逼著說,我知道你們公子
哥兒的脾性,要說結婚呢,一來您未必有家底,紫蕭肯定是沒有這個福氣。邯鄲不
禁失笑,李老闆你們都替我打算好了,我還說什麼呢。他在「你們」二字上加重語
氣,心下怨恨紫蕭,什麼話她不能對他說,他未必就不答應,倒和她叔叔細細盤算
了來和他談判,這一下陣壘分明,兩軍對峙,他陳邯鄲在她心中不過如此。她不出
面她聰明,其實是失策,擺明瞭想避嫌,卻是欲蓋彌彰,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說
不定她還是主謀呢。
李鶴田揭開茶蓋,吹了吹浮在上面的茶葉,他還在沉吟。邯鄲故意不作理睬,
李鶴田終於沉不住氣。原來他所要求的不過是一大筆錢和每月付給紫蕭一筆安家費,
比邯鄲設想的要少。邯鄲心裡透出一陣悲涼,原先他以為他是可悲的,他在她心目
中的位置不過如此,現在他才知道不是,她更可悲,她低估了自己在他心中的位置,
她叔叔沒把她當成一回事,她更沒把她自己當成一回事。她把她自己賣了這麼個低
賤的價錢,她要求的不過如此,倒是他看走眼了。寧願她脅迫了和他結婚或要求一
大筆他付不出的錢來,那樣至少使他覺得與她之間的交易不那麼肮髒和卑賤。邯鄲
抑制不住地笑起來,笑得眼淚都出辛,她賣,他就買,錢物兩訖,有何不可,他想
若是紫蕭知道他原來對她的安排,不知會怎樣。
李鶴田叔侄倆原來只是敲一筆竹杠的意思,見邯鄲答應得爽快,生怕夜長夢多,
次日便約邯鄲商談幾件附帶的條件。這回紫蕭是出了面的,泰然自若地坐著,雙方
都有大局已定的感覺。邯鄲見到晃悠在她耳邊的耳墜子,桃紅的一亮一閃仿佛是紫
蕭細碎的貝齒間閃亮的笑,真有恍如隔世的感覺。他買了她,一個願打一個願挨,
但他覺得不公,她一點餘地都不留給他,他註定了是只能買她而不能愛她。居然是
這樣。他唯一的一次感情。
邯鄲在這事件的過程中唯一沒料到的是他的母親。各種事項商定妥當之後,邯
鄲把錢交予紫蕭治家。邯鄲的意思是自然不能住在留園。一日兩人便乘了車去看房
子,是在一個叫平康裡的弄堂裡,平康裡、平康裡,給邯鄲一種治家安住的新奇感
覺,加上他一路和紫蕭在綢布店、首飾店、家具店置辦各種用品,那種氣氛和感覺
幾回使邯鄲真有了一種幻覺,仿佛和自己心愛的人一起置辦一個新家。紫蕭低著頭
在看一隻細瓷花瓶。她穿著淡黃的旗袍,一頭黑髮挽了一個橫愛司髻,眉眼冷冷透
幾分清雅,額際的幾絲頭髮束不進去垂在臉頰邊,又有種不修邊幅的童稚。邯鄲忽
然心念一動:說不定紫蕭並不是和她叔父合計好了來盤算他的呢,說不定真是他想
錯了呢,說不定李鶴田貪財,而紫蕭全被蒙在鼓裡了呢……難道紫蕭真的對他沒有
一點真感情?幾個說不定堵在他胸口,幾次想開口問她。他患得患失得不行,萬一
她是真的有點對他好,他豈不是誤會她。萬一不是,他自討沒趣不說,在她面前更
失優勢。幾回彷徨,下了狠心問個明白,衝口叫了聲,紫蕭。紫蕭笑微微地睨他一
眼,你看這個花瓶好不好,放在客廳裡很好。邯鄲聽她一副廝守永遠的口氣,忽然
泄了氣。他不能問她,他無論如何不能問她。就算她愛他或者不愛他,她怎肯實資
告訴他?即使告訴他又能怎樣,他能就此撒手而去?邯鄲下意識地閉閉眼,他為什
麼不可以糊塗一點?權當它是一回春夢。
和紫蕭商定了是今天搬進去住的。早上邯鄲起了個大早,踱踱就到了那間小閣
樓。天還沒有透亮,是一種清朗的灰色,星子已經很淡了,樹的枝枝丫丫看來比平
日都低,交錯縱橫。天空是一張泥金紙箋,樹的枝丫是上面淡青色的紋理,只是太
陽沒出來,看不清在這張紙箋上書寫的是離愁還是別緒。邯鄲面對窗口坐了半晌,
他拿出那支笛子。
少芳在客廳裡也聽見了他的笛聲,靜靜地過了一會兒,不知為什麼心裡有點酸
楚,她還有點可憐她的兒子。
邯鄲出門上班時,少芳叫住了他,邯鄲,頓了頓又說,今年我們家那間紡織廠
生意不錯。你今天不用上班,跟我到廠子裡去看看。將來這些都是你們兄妹倆的,
你現在不學怎麼行,我總會老的。邯鄲轉眼看她,果然是老了很多,這些年的辛苦
都寫在眉梢眼角了。他很是詫異,今天她為什麼忽然服起老了。從前她總是對他不
放心,嫌他不能幹,不會治理家業,他也落得輕鬆。倒是繡襦,十幾年來跟著母親
進進出出,精明強幹,分明又是一個少芳。邯鄲輕笑一聲,媽,不是有繡襦幫你嗎,
她比我能幹,你們倆去就行了。少芳不吱聲,過一會兒,和顏悅色地對邯鄲說,今
天你下了班早點回來,家裡有事呢。邯鄲淡淡地說,我有事。繡襦在一旁說,哥,
今天是媽過生日,你可得早點回來敬媽一杯壽酒。邯鄲應了,走到路上才想起,他
母親一向不過生日的,二十年母子他竟不知她的生日。
邯鄲下班前繡襦來拖了他一起給少芳買壽禮。兄妹倆一起給少芳選定了一件狐
皮大衣和一對金鐲子。他這個能幹的妹妹一下子對他親熱異常,他簡直有點受寵若
驚,後來想想小時候他們倆脾氣合不來也是有的,雙胞胎嘛,大多數是死對頭,無
形中是競爭對手,很難和睦得起來,大了,懂得到底是親兄妹,自然而然地前嫌盡
釋,沒什麼奇怪的。再說,他是男孩,繡襦是女孩,終歸要嫁出去的,將來難保沒
有要有仰仗他做哥哥的時候。繡襦是聰明人,自然懂得尋機來與他修好。他自以為
分析得十分透徹,心下安然,便把先回平康裡給紫蕭說一聲的念頭忘了——有繡襦
在旁,他到底也有些不便。也許潛意識裡還有點怕,怕與紫蕭真實相對的一刻的到
來,拖一刻是一刻,下意識裡他未必不是存心拖延。
在少芳過生日的家宴上,他多喝了幾杯,有點微醺,擦了把臉,一迭聲地叫僕
人備車去平康裡。繡襦忍不住上前要勸阻他,被少芳暗暗止住了。
邯鄲從平康裡回到家裡時,少芳正坐在燈下等他。不知道為什麼桌上的酒菜沒
有讓傭人收拾下去,杯盤狼藉。點點金紅的蠟燭燒殘了大半支,擁著如雲如霧的燭
淚。客廳裡灑金紅紙剪成的壽字在橘紅的燭光裡一跳一跳,長長向下一拖的筆劃像
一隻長腳在一蹺一蹺,燭光跳躍中,屋頂有濃重的黑影,那個壽字像要活了一般隨
時都會鋪天蓋地地掩蓋過來。遠遠的窗外有長長的風悄悄地偷襲過來。風過處奪城
掠地,毫不留情地把春光付水流,少芳舉起盛在高腳杯裡的紅葡萄酒——多年來,
她也逐漸在不愉快的時候喝這種洋玩意,不知過了多久……二十年前她也是如此等
過一個人,那是另外一個男人,她的丈夫。也是這般枯寂的夜,這次她要等她的兒
子回頭,縱使他怪她,她也顧不得了,她不能由著他上人家的當。
邯鄲回來時怒不可遏。他搶過桌上的一隻酒杯狠命往地上一摔。「嘩」的一聲
輕響,少芳看見玻璃酒杯在地上濺起一朵寒光閃爍的花。一個小丫頭聽到響聲跑過
來探探頭,被守在門外的秋兒一把揪回去。屋子裡的母子倆在相互掂量著,二十年
的生疏一下子濃到了極點。
邯鄲喘了口粗氣說,是你,是你幹的。少芳不回答。他把手裡捏的紅檀板嘩地
一下拍到桌上,恨得不能呼吸。你逼得紫蕭連這個沒帶就走了,是你幹的。我現在
到哪裡去找她,我到哪裡去找她。少芳又痛又氣,厲聲道,邯鄲,你有點男人氣好
不好,為一個賣唱的就做出這副樣子給誰看,邯鄲恍若未聞,聲嘶力竭,你說,你
逼走了她有什麼好。我是不是你兒子,為什麼你老是不肯放過我,老是跟我作對。
繡襦正好一頭撞進來,邯鄲劈面揪住她,還有你,你和她串通好了來算計我,騙我
一同訂壽禮,哄了我回家來,卻是駕空了我,騰出時間來趕走紫蕭。你說,是不是
你把我騙來家裡好借機攆走李家叔侄。繡襦冷不防被他勒得喘不過氣來,伸了手像
游水的人亂扒亂劃,臉憋得通紅,乾咳著說不出話來。邯鄲一愣,略微松了鬆手,
繡襦乘機解脫,在一旁撫了喉嚨喘氣,氣喘吁吁地罵她哥哥,神經病。廳裡亂成一
團。
少芳氣得嘴唇直哆嗦,摹地一拍桌子,銳聲道,邯鄲,你聽著,別說我還站在
這,就算我死了,陳家的大門也不許那種賣唱的賤貨踏進一步,更別說做明媒正娶
的陳家少奶了。人是我趕走的,不錯。這種女人,她也配!別怪我說你腦子糊塗,
她哪兒是看上你了,你有哪點像個大家公子,跟你老子、叔叔一樣,都是沒出息的
貨。她怎會看上你。你以為這是唱戲哪,哪個姐兒不愛鈔,她看中了你的錢哪。今
天索性實話告訴你,省得你老以為我做娘的虧待了你。姓李的叔侄是我讓他們走了
的,我給他們整整五百大洋呵,他們是收了我的錢,才捲舖蓋走人。姓李的老頭說
了,少一個大子也不行。有了這筆錢他們早上天津衛花天酒地去了,你不知道吧,
姓李的是個賭鬼。不定哪個傻瓜又要上當了。我叫人打聽了,李家叔侄是專門做這
種生意的,專騙你這種傻瓜,偏你還蒙在鼓裡,什麼都信他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