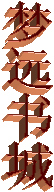
04
邯鄲聽了宛如五雷轟頂,不用多想便知道他母親說的未必不是實話,至少八成
是真的。他想,他還以為他買了她呢,其實是她把他賣了,兩下裡得錢,一絲情分
都不講,可是他母親……他驀地對她咬牙切齒地大叫,你胡說,你不要以為你這樣
就拉住了我,我不受你的恩。我上人家的當是我的事,我願意的,你以為你籠絡了
我就可以乖乖地聽你的話,你這算盤打也不要打,他喘口氣,冷笑地對著他母親,
說什麼唱戲的不准進家門,哼,這幾年唱戲的進咱們家還少嗎。少芳變了臉,跳過
去刷地給他一個耳光,沉聲道,你瘋了,這話是你對你母親說的嗎。說完頭也不回
地出去了。
邯鄲清醒過來,看著少芳的身影疾速地向外走,心中說不清是什麼情緒,恨不
得有支筆,輕輕一抹就把當日發生的事件統統抹去,就當這天沒活過,是他生命中
的空白。他拾了那兩塊紅檀板在手裡,看見燭光裡有一雙素淨的手兔起鶻落地敲擊
著晶瑩美麗的紅檀板,又像是浸在月光裡,雲裡霧裡分明是幻覺。他曾設想了他以
後的生命將是一段珠圓玉潤、吐詞婉轉的梅花大鼓唱出的故事,給紫蕭的手輕輕一
敲紅檀板,那些故事的引子和旋律便張嘴即來,唱著做著演出許多意義深遠的細節。
他曾幻想了他的此生便是如此,人海茫茫,譬如他真是她心中唯一的唱詞。
兩個月後,少芳為著徹底收攏邯鄲的心,給他物色定了一位中等工廠主家的小
姐,小名四兒的,雙方都見了面,邯鄲無甚異議,少芳便一手包辦,趁熱打鐵,不
久就把四兒娶進了門。
翌年,四兒生了一個女兒,喚作紅檀。
紅檀出生時是一九三七年,日本人已打進了上海。紅檀也算是在多事之秋的戰
亂時期降生,陳家在浙江鄉下的地因為佃戶都跑光了,收成十分不好。幸好還有上
海的幾家工廠和蘇州的生絲廠維持生計。
眼看著時局愈亂,邯鄲周圍的親戚同事紛紛各找門路。邯鄲本無所謂,被那股
大難來時各自飛的惶惶然氣氛感染,漸漸有些坐不住,他擔心四兒母女倆,便和少
芳商量了搬進租界住。少芳痛駡了邯鄲一頓。邯鄲也不與她計較,自顧自在租界托
人找了住所,把四兒母女和繡襦送過去,自己回來陪少芳住在老房子裡,他想,大
不了等死罷了。
說是陪,其實是兩個不相干的人住在同一幢房子裡。吃飯時他在書房他母親在
自己臥房,兩不相擾,等於是獨居,只是彼此都知道這幢房子裡還有另外一個與自
己有血緣關係的人,這種不痛不癢的關係。這些年他們幾乎都忘記了這一層母子關
系。他們的母子情譬如是翻開書,發現裡面夾了一根頭髮,不知是什麼時候是誰無
意間落在書上了,不料自己翻翻無意間又翻到了,因為不知道是誰的,落在肌膚上
幾天都癢的那種瑣碎的感覺一直在心裡。
邯鄲一日走出房門來,發現家裡的下人房裡、門廊裡擠滿了不知哪兒逃來的難
民,橫七豎八地坐在地上。邯鄲在各色縱橫交叉的褲管間尋縫走,看看是有腳可下
的,走下去仍然冷不防踩了別人的腳或手,那種感覺極不舒服。
走到了少芳門前,只見布簾半卷著,少芳一個人背著房門腰半弓著坐在桌子跟
前,一動不動的。沒有電,點了一盞小小油燈,燈罩上一縷拉長了的青煙筆直地上
升,到上面卻撐不住了,有點松,一彎曲就四散不見了,沒來由的鬼氣森森。邯鄲
移了兩步才看見他母親原來是在吃飯,兩碟小菜微微冒著熱氣,一屋子的死靜把她
給吞噬了。這畢竟是他的母親,她再不好,也是為了他,是她給了他生命。亂世之
中,人人自顧不暇,許多平常生活裡厚厚的面具及一切牽牽絆絆的東西都風化了迅
速剝落下來,這種人際關係的蒼白無情他想想都不寒而慄。人與人之間剩下的只是
那點不加掩飾的、真正唯一有點依靠的親情。就這一點,也是那樣的靠不住,因而
更加可貴。這是他以前沒發現的。同時因了這一點親情,更使他倍覺世間冷酷。
少芳遲緩地抬起手來撫他的頭髮,他這才發覺自己不知何時已伏在少芳的膝上。
他覺得有點羞愧,這是他記憶中從來沒有過的,然而雙手卻不由自主抱緊他母親的
膝蓋,少芳遲疑地把手擦過他的頭發落在她自己的膝上,雙手軟弱無力。邯鄲仰起
臉看她,她失神地說,怎—麼—辦—呢—今—後—我—們—怎—麼—辦—呢—日—
本—人—打—過—來—了—還—有—那—個—一—夫。聲音斷斷續續的,沉重而木
訥。邯鄲的心一牽一牽地痛起來,像有根線扯住他的心尖一上一下地抽。他用他母
親的手遮住自己的臉,叫他母親,媽,媽。
少芳一下子蒼老了許多,她定定地看她的兒子,邯鄲,我是老了,什麼樣都不
要緊了,可是你呢;你還有許多日子要過,還有四兒、紅檀、繡襦,還有陳家的一
大堆產業呢,你可不能垮了。你以前沒出息,我不怪你,現在亂世呀,你不知道人
心多壞,要提防著人家害你。邯鄲的臉緊緊貼在他母親的手上,他覺得他母親的手
抖得厲害,抖得他幾乎捉不住。少芳過了一會兒,輕聲說,邯鄲,你要記著還有一
夫呢,他比你大,是那個日本賤女人生的,按說是陳家的長子,可我怎能讓你吃虧,
這幾年我苦心經營,都是為了給你們兄妹倆守住這片家業呀。可我一刻也沒放鬆要
防了一夫來奪你的錢。你要記著,這世上誰都會騙你,只有錢才不會騙你,先前咱
們不怕,可是現在日本人得了勢,他豈有不回來的。邯鄲神不守舍,她的話只聽了
個三四成,忽覺手上幾點涼涼的,不覺一驚,他知道他母親在哭,肩膀一聳一聳的,
他這才明白他母親這二十年來原來都一直籠罩在一種大的恐懼裡。少芳驀地大哭起
來,哭得不可抑制。邯鄲一動不動的,不知從何說起安慰他的母親,半晌才出了聲,
不會的,不會的。究竟什麼不會的,他心底也沒有底,到後來聲音不覺哽咽,心下
卻只覺茫然,他有什麼本事來保他母親餘生平安呢。自欺欺人罷了。少芳哭得悲喜
交加,這會兒她才感到兒子是自己的。
繡襦每日坐了車子去幾家工廠。由於戰事影響,外面的原料進不來,這裡的東
西也運不出去,解散了大半工人。說是去處理一下事務,實際上是個空名——一些
具體事她也幫不上忙。只是每日一次巡視好歹是樁事,好比是茫茫大海裡抓住一根
救命稻草,亂世中好歹抓住了一樣實在的東西才心安,才不致無頭蒼蠅似的沒個著
落,這一日她看見辦公室外進來兩個穿軍裝戴手套的日本人,再一會兒是個頭戴禮
帽穿中國長衫商人打扮的年輕人。也沒看清他的臉,繡襦驀地心下冰涼,她不用看
就知道是一夫。看清了他的臉還是吃驚。一夫的臉酷似照片上的望庭。
當天晚上少芳母子仁商議了一夜。看這情形是鬥不過一夫的,一夫這次回國不
是單槍匹馬,聽說在日軍駐滬司令部掛個文職,他現在叫小山一夫,和子後來還是
嫁給了那個日本銀行家小山。少芳母子要跟他鬥,明擺了是作死,跑吧——天地之
大,又跑到哪兒去?家業都在上海,外面亂亂的,他們出了上海就好比沒腳蟹一般。
不跑吧,又摸不准一夫究竟會對他們怎麼樣。兩下裡沒個計較。眼見是無路可走,
邯鄲反而定下心來。他們揣摩一夫無非是要回他的家產。可吃不准他這般見過大世
面的人怎麼還計較這些。少芳心神不定地說,人心不足蛇吞象呀。奇怪的是她怎麼
也記不起一夫小時候的模樣,太專心把他當作一個敵手了,就忽略了其他的。繡襦
說,他是報仇來了,秋兒不是說媽在他小時候到他們家去揍了那個日本女人嗎。少
芳冷笑了說,我還嫌揍得不夠呢。他真是替她報仇,大不了我賠了一條老命給他,
話是這麼說,三人心下還是忐忑,想想住在這大房子裡終究不是辦法,便決定第二
天一早就送少芳到租界去,繡襦也不用上班了——橫豎肉在砧板上,一夫要拿什麼,
也擋不了他的,只留下邯鄲一人單刀赴會。邯鄲心想,這個虧是吃定了,不如變被
動為主動,索性大方地約了一夫談談,他要什麼不妨開明價碼,作最壞打算,他不
念一父所生之情,有得寸進尺之意,他也好在旁察言觀色,隨機而變——大不了把
家產大半讓了他,保了全家的性命要緊。這番話他並不敢對他母親說,只和繡襦說
了。她也說,只好如此。
一夫很快給了回音,約在四季茶樓見面。邯鄲抱了大不了一死的決心。原想不
至於那麼嚴重,可是到底他沒有把握。前天藥房裡還有人扶了來配藥,說是給日本
人打傷的難民。一夫一半是日本人,又是個日本司令部的軍官,難保他不是嗜血成
性的。
邯鄲比預定時間去得早了點。四季茶樓是相當有古中國情調的,一間間小小的
單間由高高大大的屏風隔開來。屏風上繡著牡丹鳳凰,濃豔祥瑞。說是茶館,其實
又有點中西結合,還供應咖啡西點,往來的客人都不是平常市民,與留園兩種情調。
當初邯鄲愛上留園,還因了它的名字。留園,不知為何使他想起「不醉無歸」來。
單憑這一點便使他無限心儀。後來碰上紫蕭,留園便成了另一種代名詞。想想紫蕭
走後,從此他絕足不再去留園,不過是兩年的時間,前塵往事便已如春夢一般。這
樣胡亂想著他便看見了一夫。他原來猜想他一定會帶了衛兵來壯聲勢,給自己來個
威懾。四下裡一探頭,卻見只有一夫一人。他不禁心下嘲弄自己,你算什麼人,人
家還需要帶衛兵來壯聲勢,你也配。人家才不把你放在眼裡呢,現在是兵臨城下,
你是窮寇他是贏家,自然是有恃無恐的。見了一夫的臉,心下更覺出乎意料。雖然
聽繡孺說過一夫的相貌穿著,但沒想到他是這麼中國化的。灰色長衫在一夫高瘦的
身上異常挺拔妥帖,不大像日本人。他想像中的一夫應該是略有點矮胖,戴金絲邊
眼鏡,腮上有點肉,一笑起來至少表面一團和氣,其實笑裡藏刀的那一種類型。他
沒想到他是這麼異常整潔而又修邊幅的,越發顯出自己的灰黯來。
一夫伸手叫他坐,邯鄲看見他熟練地向夥計吩咐,對各種茶點如數家珍,心下
訝然,轉而想起,一夫小時候畢竟是在上海長大的,自己又不是不知道,總是自己
一心把他視作日本人的緣故。他不禁想,不知他這一次跟著母親國家的軍隊來殺他
父親國家的人,他心裡會怎麼想,再想下去,當然一夫也可以來殺與他有著一半相
同血統的異母兄弟。邯鄲被自己的想法嚇得毛骨悚然。
一夫卻不談正事,話題無非是繞著中國、上海的名山大川、勝地景致、各色名
菜、各樣風俗來講。也談到了留園。不知怎麼邯鄲就說,四季茶樓不算是真正有中
國風味的茶樓,該是留園,那才是真的。說到留園,他總有點恍恍惚惚,他猛然醒
覺,這兩年多來他幾乎沒吹過一次笛子,是不是為了紫蕭?他自己也不明白。他想
起來,他們相識的頭一句談話即是有關他的笛子的。他愛而不得是他自己傻,她是
在她那種環境下長大的女孩子,絕對不是那種賢妻良母,嫁了圈內人是不可靠,圈
外人又不屑娶她,如此想來,她也有著許多委屈和不平。女孩子的心事,像一枝未
成熟的蓮,包了許多青澀在心裡。邯鄲這麼想著多少能夠心平氣和一點。他也只敢
想到這兒,再想下去他就不能原諒她。
邯鄲一轉眼間,看見臨街的一徘玻璃窗被陽光一打,活靈活現地勾勒出自己與
一夫據桌而談的身影。不像是親兄弟間近似於殘殺的談判,倒像是好友在談心。一
夫大概有三十歲了吧,因為軒昂看不出年紀,反而自己是一臉老相,兩兄弟差別這
麼大。他的生死還系於一夫的手中,一夫的意思是要了陳家所有工廠改而生產日本
軍中急需的藥品、軍需被服。還有那間大宅院。明擺了是掠奪。邯鄲原來還指望他
多少會手下留情。他於一瞬間明白自己決不可能有別的選擇:一夫是存心的,他哪
會在意這幾間小工廠,不過是報當日之仇,奪回自己長子的地位。他入主陳宅,這
個企圖便十分明白。
邯鄲臨走時對一夫笑笑說,殺兄弟比殺一般中國人有趣吧?說著揚長而去。他
是一時洩憤,同時現在反而於性命一樁無考慮了,他對一夫的心理自以為看了個透
徹,他不會殺他,一夫不過是要陳家吃不飽餓不死地活著。殺了他?豈不是少了一
個慢慢折磨的趣味和對象?
出得門來,只覺陽光耀眼,照得他抬不起頭來。他用手半掩著額,一腳高一腳
低地走,周圍的一切都沒了聲音沒了色彩,他的心突突地在荒山野嶺間遊著,撞得
他胸口都疼了,一腔煩悶無處發洩。但是他想他又能怎麼樣。
他後來終於又見到了紫蕭。一夫似乎是為了表明他不忘兄弟情,時時叫邯鄲陪
了他去各處戲園茶樓。他偏好這個。邯鄲簡直有些弄不懂,一夫的三弦琴彈得極出
色,這一點喜好他們兄弟倆是最相近的,邯鄲對一夫貓戲老鼠的惡意不是不知道,
但他又覺得無法反抗,只好走一步算一步。
那一天他和一夫到城隍廟。遠遠的便見湖心亭上,幾個老頭四散坐著,中間一
人一句句唱出來:相離處士家……沒緣法轉眼分離乍……。聲音被風吹散了,不十
分聽得清,那個曲調卻是他到死也忘不了的。
一夫看見一個白衣黑裙的女子側身向著他們。湖心亭是暗朱紅的,天是灰色的,
湖水是綠的,柳是黃的,有風吹得人衣衫飄飄若仙,一點點不知名的花香若有若無
地自哪裡跟了來,揮之不去,招之即來,總在眉間唇邊縈繞。一夫覺得這一幅圖景
便是他所嚮往的中國江南水鄉的情調,目中所見圖畫中的女子無端便有一陣煙濕霧
氣,同樣帶了溫婉的氣氛。
邯鄲先前聽了那支寄生草,又見了那白衣黑裙的身影,心裡總覺得熟悉得很,
以為不會是紫蕭,待得她回過頭來,這一下確定了,真是她。那一刻說不清是震驚
還是什麼,第一個念頭是,她竟然還敢回來。她沒看見他們,想必是一曲唱罷,掌
聲寥寥無幾,彎了腰在收拾東西。看樣子她的情形不是太好。白衣依舊是白衣,黑
裙依舊是黑裙,只是不知怎的,少了那種山明水淨的氣質,無緣無故地令人覺得寒
酸。
他聽見她又在唱了,這一次卻是《長生殿》裡那一折,李龜年道盡人世滄桑,
恩怨離合。她唱的每一折戲都是裝了底氣十足的男聲,不是老生便是武生,非常的
老氣橫秋,唱的人不覺著什麼,聽的人總覺得有絲絲悲涼自心底來。一曲是《寄生
草》,一曲是《長生殿》,唱來唱去都是兩年前的舊調,他記得那時她就是只會唱
這兩段。可見她做人做戲都不十分地用心。邯鄲又想,她到底還是改唱京劇了,大
概聽梅花大鼓的人更少。她的聲音倒還是唱大鼓的好,一板一眼中又有著無限的花
腔動作,十分像她的人。他總覺得唱大鼓的是以局外人的身份唱了做了,完全不必
拖泥帶水,只是張口便來敷衍一段故事。唱戲就不一樣,需要你化身為劇中人,是
完完全全的感情介入。前一種就合她的脾性和身份。邯鄲想她還是聰明的,不知是
先天還是後天生涯造就了她一副決然心腸。一曲唱畢,邯鄲忽然明白,紫蕭原來是
在賣唱,而不是原先的唱著玩了。這時紫蕭收拾完東西,起身向另一邊走了,大概
看客不多,另找地方去了。到底沒有看見邯鄲他們。
一夫說,唱得不錯,可不夠字正腔圓,你認識她嗎。邯鄲不由地歎了口氣,是
以前留園唱梅花大鼓的。一夫哦了一聲,倒稱讚起來,怪不得,不是科班出身,能
唱成這樣倒也難得。
正是四月時節,沒料到這裡一塊極僻靜地方突地燒出一大片杏花來,深處是一
個小小草亭,一夫進去觀看,邯鄲推說頭疼,在外面無聊地走走停停。不知不覺已
走出老遠,一條細細的石子路青苔點點傍著假山過去就不見了。他繞過假山,便和
紫蕭打了個照面。她雙手濕淋淋的,正面對著他用一條帕子絞了洗臉,眉毛上都是
濕濕的。邯鄲看見她身旁一支竹筒從石頭縫裡出來,汨汨地冒著水,大概是她走累
了,停下來掬一把水喝,洗洗臉。一下子兩人都有點驚慌失措。
紫蕭住在平康裡。不過不是他過去曾租過的那幢。他想像得出,憑她的生活窘
迫只能是那種連腰都伸不直的小閣樓,從天窗射進來一方慘淡的白光,走上去時樓
梯會咯吱咯吱地響,兩邊是濕淋淋地掛滿了房東家小孩子的花布衣服和尿布,因為
曬不到日光,始終是濕乎乎的,不小心搭在手臂上,便忙不迭地甩掉,說不出的別
扭和難受。也真虧了她也曾過過好日子,也曾錦衣玉食,如今這般落魄也忍得下來。
他在她的樓底下徘徊了許久,始終沒有上去找她。未見面時還有著一些對她的怨恨
和留戀,他生怕此次重逢之後什麼也沒有了。
他快快地走出巷子,遠遠地便見紫蕭拿著一隻手提袋匆匆而來,包裡鼓鼓的一
塊,反正不會是紅檀板,她現在只唱京昆了,他閃在黑影裡,她沒看見他。
離他十幾步遠有一家小小的小吃店,賣餛飩、麵條、豆腐花。紫蕭走過去看了
看,走了,不一會兒又折回來,這次走得爽快,叫了一碗最便宜的豆腐花,也不怕
燙,端了就喝。大概餓得太久了,露出一副饞相,一小碗豆腐花吃得無比香甜。邯
鄲看得心酸。吃完了,分明是沒飽的樣子,終於下了決心還是走了。李鶴田也不知
是怎麼死的,她雖有主見,畢竟是個女孩子,沒了依靠,又沒錢,一路漂泊重回上
海,定有她的不得已。她此番吃了苦頭,也不知這兩年多她是怎麼過來的。
邯鄲腳下加快,一路追上前去。紫蕭聽見背後的腳步聲,一回頭看見是他,忽
然奔跑起來,一溜小跑逃命一般。邯鄲咬了牙追趕。紫蕭慌不擇路,不提防黑燈瞎
火地扭傷了腳踝。邯鄲趕到,卻見她痛得坐在地上直揉。一見他來,她狠狠推開他
的手咬了牙就想站起來,不料噯喲一聲,又跌坐下去,痛得倒抽一口冷氣,刹那間
種種不快和苦楚像決了口的堤壩洶湧而出,她覺得滿心委屈,再也顧不得什麼,一
扭身趁勢坐在地上驚心動魄地大哭起來。邯鄲僵著身子一動不動。
紫蕭哭累了,隨手抓過邯鄲的長衫下擺擦了擦眼淚。她絕望地說,我不想就這
麼活下去,你知道嗎,我會死,我會死,邯鄲的心一下子暴怒起來,到現在她也只
關心自己的生死。他輕聲笑了笑道,誰沒有生死呀。說得太輕,紫蕭也不知道有沒
有聽見,只是一個勁兒地說,你可以幫我的你幫我呀。邯鄲苦澀地說,我有什麼辦
法,我這樣一個沒用的人。紫蕭看著他,眼裡有許多意思。邯鄲看她分明有了計劃,
卻又不啟口,一副欲言又止的樣子,心念一動,冷笑了說,你怕是又把什麼主意都
打定好了,還用得著我幫你?紫蕭蒙住了臉,看不見她的表情,哭聲卻止住了。邯
鄲心下更是透亮,盛怒之下,拔腳就走,一走走到巷子口,看見月光透亮,明明白
白地照在巷口上方石刻的「平康裡」三字,心中不知怎的一震,頭幾乎暈了。他到
現在也想不通為什麼紫蕭仍擇了平康裡居住,是對他的一種紀念嗎?顯然不是……
可是萬一是呢,她什麼地方不能去,偏偏還是到了上海來。邯鄲覺得真是想不通。
夜色漸深,偶然有個行人做賊一般在黑暗裡飛快地溜走了。那間小吃店的老闆封了
爐子,收拾碗筷。邯鄲聽見他打了一聲呵欠,砰啪一下上了門板就進去了。邯鄲背
靠著牆角蹲了下來,他覺得脫了力的疲憊。他不想生,不想死,在這一時刻他清醒
得不可理喻,清醒得要生不能,要死不得。
這一會兒他又聽見吱呀一聲,那個店老闆趿著鞋披著衣服摸黑出來,一路踢踢
踏踏地腳步聲響到弄堂口,嘩啦一聲,倒了什麼東西,又一路打著哈欠走回來,依
舊是那樣沉重的腳步,絲毫沒有減輕,關了門又進去了。這一次是熄了燈再沒有出
來。
街上空無一人,也沒有任何一種生命經過。天地真是冷清呵,仿佛世界上就只
剩了他們倆。他知道她還沒有走。可是跟走了又有什麼分別。其實他們根本就從來
沒有走近過,他唯一可以明確的是她在他的生命裡曾經來了又去了,他家裡的紅檀
板是唯一的見證。她是絕情的。她幾乎根本沒想到他的感受,這是她的處世方式。
經過今晚之後,連這一點明確的東西也將消失得乾乾淨淨。
邯鄲待了一會兒,走回去,他好像看見紫蕭在笑,他閉閉眼,什麼都過去了。
沒幾天,邯鄲探了一夫的口風,安排他與紫蕭會面。他對紫蕭說,留不留得住
一夫,就看你自己了。沒說之前他就覺得這句話多餘,不說又覺得沒囑咐她不踏實。
他自己也知道紫蕭比他精明百倍,可他忍不住,說了之後還是覺得多餘,這句話多
餘,自己也多餘。天地間就多餘了他一人。
轉眼紅檀已經七歲了。
一九四四年的上海,日本人的日子並不好過。這天邯鄲從藥房回來,教紅檀認
字。她趴在門口的一張方凳上,臉扣在上面,抬起頭來問邯鄲:tan,怎麼寫。邯鄲
明白過來,寫給她看「陳紅檀」。她寫了半晌,忽然問,紅檀是什麼意思。邯鄲沉
吟了半晌,就是一種紅色的木塊,人家唱戲時用來敲的。紅檀忽然不高興了,我不
做什麼紅色的木頭也不唱戲。邯鄲呆了半晌,看一看她說,紅檀,等你長大你就知
道有些事自己是作不了主的。
這幾年,陳家算是捱過來了。仍住在租界,房間換小了,傭人也只剩了秋兒。
少芳十分地不慣,但也無可奈何。繡襦一直沒嫁。一夫施的壓力邯鄲是打死他也不
往外說的。可不是古人說的,甯為太平犬,莫為亂世人。他逢了這個時機,又沒有
能力反抗。開頭總還有些憋悶,自己的苦楚別人是體會不到的,冷暖自知罷了,許
多話說了也沒人幫你,他寧願憋在心裡。久而久之,反而覺得對萬事無話可說。就
像那次對於紫蕭的死也是這樣。
紫蕭那天不知為什麼逃到他家來。他下班時正好碰上七八個日本憲兵拽著紫蕭
的頭髮一路拖著出來,長長的一溜血跡觸目驚心,紫蕭那時已死了。那天四兒陪了
少芳出去看病,家裡只剩了紅檀和秋兒。他沖進去時只看見臥房裡一片狼藉,紅檀
頭抵著牆一聲不吭地朝裡坐在小板凳上。他先放了一大半心。小孩子禁不得問,三
言兩語地便大哭起來。好容易才弄清點眉目,原來秋兒陪紅檀吃了飯便牽了她一同
在後門口與隔壁的李太太閒聊。紅檀坐了半晌不耐煩,便奔進臥房,也不知找什麼
一開衣櫥門,便見櫥裡一個滿面血痕的女人把她一推就在外跑,沒跑出大門就被一
夫派來的憲兵給揪住了,一頓好打。也不知道她什麼時候來的,總歸是他早上出門
之後的事。
邯鄲安頓好了紅檀,便進來收拾東西。大櫥裡的衣服東一件西一件地扔了一地。
他過去收拾才發現他合家歡的照片被紫蕭拿出了放在衣櫥裡。照片上有他、四兒和
紅檀。他記得原來是放在床頭櫃上的。他看見照片夾的玻璃上有一個血紅的拇指印,
正好在他的頭像上,一抹就拭去了。是紫蕭的血。也不知她拿了來看還是順手做防
身武器。想想好像都不大可能。她已經死了,究竟怎麼想的都無關緊要了。
四五年,一夫在日軍投降前夕的一晚剖腹自殺。過了好幾個月,邯鄲一家重新
搬回陳宅居住。幾天前邯鄲去看了看房子,偶然發現了紫蕭的紅檀板。他記得他搬
到租界前曾把它和許多雜物一起搬到閣樓去的。沒想到紫蕭到底找到它擱在梳粧檯
最末一隻抽屜裡。
邯鄲拿起來,在手裡輕輕掂了掂。許多歲月輕輕一掂間就過去了,桃紅的光澤
無比溫柔,明明是木質的紅檀板,可遙遠的年代裡那個他以後再不曾見到的耳墜予
似乎還清清楚楚地捏在手心底,他不由得打了個寒顫。開了窗,一揚手,便想扔了
出去。停了一停,終於沒扔。
許多往事都沒法扔。
199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