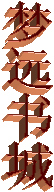
01
邯鄲第一次回家過年是在七歲時。以前也回來過幾次,先是老太太,後來是望
庭,年紀大小,邯鄲只記得家中遍地縞素,別的什麼印象也沒有了。
有一回他正好四歲,似懂非懂的。秋兒牽了繡襦叫她喊哥哥。繡襦已有了一些
大小姐脾氣,很不屑地看他,很有點敵視,冷不防就推了她哥哥一把,邯鄲不防備
坐了一屁股的爛泥,又羞又急竟哭起來。秋兒笑著過來拉他起來,一邊笑一邊哄道,
真是個鄉下傻小子,小笨蛋,真是不害臊,被妹妹推倒了還好意思哭,你還不如你
妹妹呢,你有什麼用,長大了不過是個笨頭笨腦的小笨瓜,你有什麼用啊,繡襦在
一旁瞎起勁,跳著腳喊小笨蛋、小笨蛋。秋兒正嘻嘻笑著,沒瞧見少芳正好路過,
站住了看已有好一會兒了。少芳不言不語地就給了秋兒、繡襦每人一巴掌,打得秋
兒眼淚都出來了,捂著嘴不敢作聲。少芳冷笑地說,你是什麼東西,你敢罵他鄉巴
佬、小笨蛋,你敢罵他,除非你不要命了。他是我兒子,你就得管他叫少爺。下次
我再有一回聽到你嘴裡不乾不淨的,我用針戳爛了你的嘴。秋兒掙紅了臉又不敢分
辨。少芳刀子似的目光停留在繡襦臉上,還有你,繡襦,你也給我記著,他是你的
哥哥,你再聽下人們挑唆,再那麼霸道,我一樣扒了你的皮。
邯鄲在一旁看著,忽然掉頭就走。他娘攔住他,命令他,邯鄲,你去打秋兒和
繡糯。邯鄲一在他母親面前便呆頭呆腦。他遲緩地抬了眼睛向她看,也不知有沒有
聽懂。少芳蹲下來,熱氣哈在他臉上,說,邯鄲,你去打她們,像我剛才做的,狠
狠抽她們的耳光,用腳踢也可以。她們剛才罵你,你沒聽見嗎。她們是什麼東西,
你是我們陳家的大少爺,你愛打便打,愛罵便罵。一夫他算什麼,他們都是你的。
陳家將來都是你的。你以後要記著,不管誰罵你、打你,你一定要打還他,罵還他,
不要讓。讓了你就什麼也沒有了,都讓人分光了。少芳著了魔般正對著邯鄲,也不
管他有沒有聽進去。
邯鄲始終垂了頭,不肯動手。少芳的眉毛漸漸豎起來。這時張媽喊邯鄲回去洗
澡,邯鄲一溜煙地跑了。
剛才的情景張媽也看見了的,問秋兒,不過隔了三四年的工夫,二少奶奶怎麼
像變了個人似的,脾氣老大,說話也這般不顧情面,你還是從小侍候她的呢。秋兒
說,其實,她也就是這個脾性……剛到這家來時你們不知道……,說著秋兒又不言
語了。張媽壓低了聲音問,聽說原先老太太房裡的簪子不知犯了什麼,被拖進柴房
打了半夜,路都走不動了,可是有的?秋兒不言語,頓一頓才說,其實這幾年也真
是難為她了,別看她人前威風,前兩年老太太過世,接著又是我們二爺。剛忙完,
大房又出了事,不明不白的大少爺就癱在了床上,一日三餐要人伺候,算是完了。
三房那位少奶奶又是不管事的。各房親戚都是大難來時各自飛的,又沒有幾個至親
好友在旁撐著,眼看著忽喇喇如大廈傾了,虧了她作了陳家的棟樑柱,重新支撐下
來,一個女人家夠難為她了。張媽說,真是看不出,嫁到我們家時那樣一個嬌怯怯
的少奶奶,現如今跟個男人似的能幹。秋兒歎了一口氣,能幹有什麼用。你看見她
對我們的這副樣子嗎,我在她身邊幾十年了,她有什麼心病我還不清楚?張媽說,
二少奶奶還會有什麼心病,怕是……。秋兒白她一眼,你老別轉那些肮髒念頭。我
說她的心病是少爺邯鄲。張媽說,邯鄲以後還不是陳家三房挑一子的寶貝,陳家還
不都是他的,秋兒說,說你糊塗你真是糊塗了,還有個一夫嗎,雖說是現在還住在
日本,又斷了往來,但人家畢竟也是陳家的骨血,難保人家有一天不回來要回他的
東西,陳家家大業大,誰不眼紅呢。張媽若有所思地說,少奶奶想得可真夠遠,可
話又說回來,那個一夫回來不回來還不知道呢,現在白耽著心幹嗎。秋兒說,張媽,
你也是老家人了,不瞞你說,二少奶奶就是不放心這一點,她怕邯鄲性子弱,將來
鬥不過一夫吃了虧。可是俗話說的「江山易改本性難移」,不管她怎麼想法於,邯
鄲還是個蔫不拉幾的性
邯鄲自那以後總躲著少芳,輕易更不肯回陳家去。少芳見疏遠了兒子,一面有
些懊悔自己對邯鄲的種種教育操之過急,一面又暗暗地覺得失望。也試著把韁繩略
松一松,使出了許多手段來籠絡兒子,但邯鄲與母親疏遠的根子就此種下了。他們
倆始終是不親不疏的,像有時天青的夜空裡一彎珠灰的月亮,若即若離地在人的心
上,一點點光可有可無,大多數時候不過應個景兒。母子之情不過如此。
少芳漸漸地在牌桌上對人說,我就不懂,我生了他,他是我兒子,我們好歹是
母子倆,怎麼他見了我就跟個冤家似的,跟奶媽都比跟我親,這個兒子是白養了。
親戚說,才四歲呀,他懂什麼,小孩麼。也怪你從小兒就送他出去,時間一長跟奶
媽熟了就跟奶媽親嘍,這都得怨你。趁早接回來收收心。少芳一邊打出一張牌一邊
笑著說,我還沒這個閒工夫管他呢,你瞧這家裡家外的一大堆事還不都得我管。我
管得了他麼。再說他畢竟是我們陳家的,等他大了,自然明白非靠我不行。離了我,
他還不得上街要飯去。奶媽養他,哪能有什麼真情分,別看現在都慣著他,他一個
小孩子人緣是娘肚子裡帶出來的?她還不是看在我每月給她的一份銀錢上?兒子,
誰不會生,我的兒子倒要她來稀罕。說著用力摜出一張牌。同桌打牌的親戚裡有一
個是舅太太家的遠房侄女,人稱李小姐的,這幾年少芳打麻將漸漸上癮,牌桌上便
少不了李小姐。她看一眼少芳說,二少奶奶,說能生,還是你福氣大,一胎就得了
邯鄲和繡襦。繡襦從小跟你長,伶俐得很,長大准像你。少芳冷笑道,像我有什麼
好。女人天生的命賤。我不指望她什麼,我供她吃喝,過兩年她要上洋學堂,也由
得她上,這一點我倒是看開了,現今交際場合,女孩子會幾句英文,會唱個歌彈個
琴不吃虧,就怕她將來越長越醜,女孩子一醜可就什麼都完了。讓她念幾年書,挑
個好一點的人家嫁出去就算了。女大不中留,在家裡鬧出些什麼事來就難說了。她
忘了李小姐也是個未嫁的老姑娘。李小姐聽慣了她這些言論,笑笑只作聽不懂。打
了一會兒,李小姐又說,大少奶奶這一向很少打牌了。少芳懶懶地說,怎麼打?整
天伺候個病人。李小姐說,大少爺這一向怎樣了,少芳嘩啦嘩啦地洗牌,有什麼怎
麼樣的,一個癱子,吃喝拉撒全在床上,跟個死人差不多,你沒到那個房裡去過,
那股味兒,嘖嘖,大少奶奶是賢慧人,她受得了,別人受不了。李小姐,你也不是
外人。有些事奇怪著呢。這大少爺吧,病也來得奇,說癱就癱了。開頭半邊身子還
能動。大夫說調理調理說不定還有指望,誰知我們大少奶奶調理來調理去倒成全癱
了!
李小姐當下不吱聲,少芳點起一支煙,蹺起腳來碰碰李小姐,又說,我也奇怪,
難不成我們大少奶奶起壞心害自己男人不成。照說麼,大少爺的請醫煎藥都是大少
奶奶一手包攬的,別人想害他也不成啊。李小姐說,就是,不過親戚們都覺得奇怪。
害了他有什麼好,我是從不信那些閒言碎語的,我就對她們說,二少奶奶怎麼可能
虧待了人呢。少芳聽見此話,略微變了臉,停了手,吸了口煙,慢悠悠地吐了口長
氣,也不看李小姐,淡淡地說,害了大少爺怎麼沒有好處,好處多著呢。我就巴不
得他早點死,拿毒藥毒死了他,陳家的財產不就讓我一個人給占了,百萬家產呀,
我眼紅著呢!
李小姐笑著說,瞧瞧你又說笑了,誰不知你是個豆腐心腸刀子嘴。少芳呸了一
聲,那些亂嚼舌頭的閒言碎語我還不知道?說我克扣大房的銀錢,去他娘的。一個
癱子我還怕他作反不成,還能活幾年,我倒克扣他們的銀錢,下毒藥把他們害死?
我用得著操這份心嗎。我說這話並不怕誰來,說給誰聽也不怕。現在陳家還不都握
在我的手心裡,我怕過誰?李小姐點頭笑道,你呀,就壞在這張嘴上,這話能說嗎。
知道你的人還真以為你是個多張狂的人,少芳冷笑道,怎麼不能說,誰能管得了我?
說這些話的人讓她們爛了舌頭,她們也不拿鏡子自己照照,自己是什麼東西?窮光
蛋,仗著八竿子打不著的沾親帶故甜言蜜語地靠上我們家來,說得好聽,來給我請
安,千方百計地哄著我,打量著我被他們給哄了,就好算計我的錢!我可不糊塗,
這世上有什麼是真的?只有錢!你告訴那些亂嚼舌頭的賤貨,趁早給我放規矩點,
別豬油蒙了心。沒我,他們早喝西北風了。我誰都不怕,別看我們陳家淨孤兒寡母
的就好欺侮。
少芳一頓連珠炮,說得李小姐臉上發燒,訕訕地說,人說你的嘴是不饒人的,
果真是。我不過是好意提醒你,倒招出一大堆是非來。少芳瞅她一眼,歎一口氣,
李小姐,我跟你是什麼人哪,我不把那些混蛋放在眼裡,還能不把你放在眼裡麼?
你還不知道,我這心裡堵得慌,不找個人說說不行,別看我表面好好的,我這是虛
的,渾身都是病。在陳家苦捱了這麼多年,沒有功勞也有苦勞哇。你瞧這上上下下
一大攤子,又沒個頂用的男人。若有,我們孤兒寡母的也不願出頭露面的。我這是
給逼的。我不為陳家幾十口人想,也要為我們邯鄲想呀,終不成大家坐吃山空都上
街要飯去。
李小姐說,終究你還是個能幹人,換了我,下輩子也不行。
少芳說,說什麼能幹不能幹的。我說,還是你好。瞧,多清閒,自自在在一個
人。
李小姐正在喝茶,猛地咳嗽了一下,臉都紅了。
少芳說,秋兒,快給李小姐捶捶背。真的,李小姐你不知道,坐吃山空哪,我
們家也窮嘍,哪禁得起人家三天兩頭地打秋風。偏有那麼多人不知事的,以為萬貫
家財是花也花不完。李小姐你來當當家就知道了,這不,昨兒帳房的顧老大來說,
城南的那間廠今年不好,虧空了好多,我跟秋兒說笑,今年怕是要賣房子賣地過年
了呢。
李小姐說,哪能呢。說著有點神不守舍。少芳不答話,揚臉叫秋兒把去年中秋
節她娘家送的兩段衣料拿出來送給李小姐,說,也不是什麼貴重的東西,因是湖南
老劉家湘繡的手藝,現今上海不易得到,所以有些稀罕,一直沒捨得穿,壓在箱底。
你拿去做件過年的衣服吧。李小姐紅了臉推辭,少芳端正了臉說,你還跟我客氣。
唉,陳家也是一年不如一年。要在往年,這些東西哪拿得出手呀。我剛嫁過來那年,
也是這時節,老太太面上的天津的外甥女來拜年,正碰上老太太高興,一出手就給
了個一兩多重的金鐲子,這些東西,少芳拍拍衣料,就是在我娘家,也只是逢年過
節賞了給丫頭老媽子的。李小姐還待推辭,少芳把手一推說,拿著,不拿,不定還
被哪個打秋風的刮了去。你知道我這人,心軟,擱不住人家兩句好話。說著就拍一
拍大腿,嗟歎,人呀,真是賤骨頭。不知觸動什麼心事,她眼淚汪汪起來。
正在這時,小丫頭上來說,蘭馨戲院那個吹笛子的高師父來了,等在後花園的
亭子裡,說是今天要教一出新戲呢。
少芳拭了拭眼睛,吩咐說,給高先生泡一壺好茶,我馬上就來。她轉頭對李小
姐說,這些年我也想開了,望庭他扔下我走了,我哭得不行,可哭有什麼用呀?隔
壁王太太常過來勸我,別累壞了身子,身子是你自己的,有個三長兩短誰來疼你。
世上的這人心啊,不提也罷——王太太人頂好的,頂會說笑話的,有一段傷心故事
呢,下次我說給你聽。我一想,對呀!這家缺了我不行,可我也不能累死了呀,不
能委屈了自己是頂緊要的,錢多,有什麼用,人死了,兩眼一閉就什麼都完了。後
來就跟這個高師父唱倆嗓子,不圖別的,散散心,圖個舒暢。她忘了剛才還說要賣
房子賣地過年。李小姐不知為什麼神情有點忸怩。少芳瞥她一眼,一笑道:高師父
一表人材,李小姐一起過去見見吧。李小姐索性大方了說,早就聽說江南一支笛高
逸梅高師父的笛子是最清絕脫俗、最有名的。說了,臉上到底有些緋紅,像在她青
白白的臉上淡淡地打了層胭脂,不夠均勻,因而那喜悅也是遲暮的,猶抱琵琶半遮
面的,又怕又留,多了怕放縱少了怕呆板,自己都作不得自己主,合符她那種身份
的喜悅。
走出少芳房門,遠遠近近的,便有一支笛如明月清輝天外仙音般來,在眼裡,
在夢裡,在心裡若有若無地繞,在李小姐聽來分明是敘述古代女子的一段與書生偶
然相戀的故事,所有的細節在眉間心上繞,不知何以訴說,斜風細雨落紅點點,燕
子雙飛去,小園香徑獨立。漸漸地那故事是相思入骨,譬如為人為鬼,天涯海角總
要陪了那樣一個眼角眉梢都落寞的人,成就一段情緣。笛聲忽高忽低,逐漸轉緩,
那個結尾終是難測,猶疑不定反復的曲調,遲遲的像疑問——李小姐正聽得入神,
不料笛子忽然停了,使她沒來由地悵然起來。
遙遙的,李小姐看見從亭子裡石桌旁站起一個穿灰綢長衫的人,持著笛子,微
微向她們頷首。李小姐卻不過去,隔了十幾步看見少芳指著這邊捂著嘴笑著向高逸
梅說些什麼。風大,送過來的一二個詞在耳邊也連貫不起來。像一種散落的佛珠串,
在漆成薑黃的地板上滾,在李小姐的心裡滾,滾過去了仍餘音嫋嫋,她躊躇了一下,
俯首看身旁一棵開花的不知名的樹。那花有著陳舊的粉紅色,是春天過後洗退了的
顏色,李小姐的眼睛被火燙了似地轉過身去,正好看見少芳在向她招手。
少芳向高逸梅介紹,李小姐對高師父的笛子佩服得不得了呢,常說要尋機會向
您請教。高逸梅笑著看一眼李小姐說,哦,難得李小姐喜歡,不知李小姐平時最愛
聽哪一支曲子。李小姐十分尷尬,不好說是又不好說不是,說曲子她其實是不懂的,
哪知少芳竟半真半假地替他們撮合起來。
高逸梅是個機靈人,當即說,這笛子呢,最難得是心靜。凡帶些酒肉氣,這氣
不清,吹出的曲子就俗了。還講究個環境,李小姐你肯定曉得,聽笛子呢最好是在
晚上,秋天,有落葉,孤星幾點,明月半殘,最有情致。吹笛子的也是這樣。春天、
夏天、冬天都不如秋天好。春天景致大過完美,夏天是太過張狂,冬天呢太過蕭瑟,
就秋天最好。我就跟二少奶奶說,咱們吹笛子教戲呢,就在這亭子裡邊最好。
少芳忸怩地說,喲,我可不懂這個。咱們是俗人,風花雪月的事跟咱們不沾邊,
高師父不嫌我笨,肯教我幾段戲,玩玩則罷。高師父,李小姐平時倒有空——就陪
我打幾圈麻將,還待字閨中呢,早先可是個美人——高先生你說是不是,
李小姐臉上紅一陣白一陣,不自覺地用手撫臉頰。經少芳有意無意地一說,仿
佛自己真是不禁老,三十年過去了,人生還有幾個三十年呢,她越發地不敢看高逸
梅,真像自己已老得十分不堪——其實李小姐保養得不錯,一向也是最自負的,忽
然今天在高逸梅前就沒了信心。她沒看見少芳向高逸梅飛了一眼,眼裡盡是譏諷,
高逸梅惜著喝茶的時機垂下頭,把笑容向著茶杯,長衫底下的白襪黑鞋輕輕踢了少
芳一腳。少芳的臉色慢慢變了,猶作鎮靜地端了茶杯喝,碧綠的茶葉魚一般遊進了
她的喉嚨,咕嘟一聲就進去了,有一股腥氣。高逸梅沒事人一般,掏出一塊白綢軟
帕輕輕拭著笛子。高逸梅和李小姐的談話忽然熱心起來,你願不願意學,我教你。
像你這麼聰明,學會吹笛子不難。李小姐頭一次聽到別人如此稱讚,帶了幾分驚喜
交加和半信半疑,她很實在,不相信這姓高的真的會僅此一面就對她鍾情,不禁心
下疑惑:這姓高的憑什麼就這麼熱心,難道他不知道少芳近來的脾氣越來越大,人
人眼裡有了她便不能有第二人的?他不過是一個吹笛子教戲的,雖說是清高倨傲,
可也是多少仰仗著少芳吃一口飯,不然不會……,他此番這般冷落少芳,定有什麼
緣故,李小姐留意觀察,心下便有幾分明白。高逸梅只顧遠遠地扯著話題,李小姐
偷眼看少芳,見她神情有幾分急躁地喊秋兒兌點冷茶來,嫌茶太燙了,一會兒又嫌
毛巾太冷。談了幾句,更兼此情此景,李小姐打散了初見面時對高逸梅的一點幻想,
含笑對少芳說,二少奶奶,您不是跟高師父學戲嗎?我得先走了。少芳也不挽留,
喊秋兒,去叫廚房裡準備幾隻肥雞肥鴨魚肉讓李小姐帶了回去。倒是高逸梅說,李
小姐,你沒聽見二少奶奶唱過戲吧,那嗓子呀你不聽真是可惜了。李小姐看看少芳
說,下次來,下次來,二少奶奶你一定不許賴掉。
李小姐走了之後,亭子裡的兩個人都不作聲。少芳喝口茶,忽然笑著說,李小
姐長李小姐短,李小姐走了你怎麼不趕上去送她。高逸梅不答話,拿起笛子輕輕吹
了幾下,仍是剛才的曲調,只是亭子裡的人此時聽來,分明換了另一個故事,李小
姐剛跟著提了東西的秋兒走到大門口,聽到背後傳來遙遙的笛聲,停了一停,卻沒
回頭。仍是剛才的曲調,仍然沒有聽完那個結局就停住了,可她不聽也知道——到
最後不外是一場空,秋天空白的天空上一隻孤雁也沒有的就到了盡頭。都是這樣。
她的故事沒開始就結束了——亭子裡的故事沒完,可是已不關她的事。坐上洋車,
都離開陳家十幾步遠了她才忽然想起來般「呸」的一聲狠狠吐了口唾沫在地上,她
急著要把這新發現告訴舅母去。這好歹是她心理上的小小勝利。
少芳在高逸梅的笛聲裡忽然可憐起自己來了:漫漫長夜裡靜等著成為骷髏,孤
身一人來到上海終究還是受了丈夫的騙,明媒正娶居然還鬥不過一個日本下女,與
自己貌合神離的兒子邯鄲……往事在她的心裡漸漸翻騰,像冷風吹動了清明節墳墓
前的紙灰,翩翩地,像一隻只灰色的大蝴蝶遮住了她的視線,她覺著累。
高逸梅在她耳邊吹了口熱氣。少芳說,你好大膽,你不怕我叫傭人們來捆了你
打個半死。高逸梅輕描淡寫地說,你不會,我剛才就算准了你不會在那個李小姐面
前發作,這種事你是不敢讓人抓住把柄的。少芳冷笑道,你怎麼知道我不敢,我現
在一樣可以叫人把你趕出去,你以為那個姓李的真是木頭?她看破了,為了堵她的
閒言碎語,我也要給你點顏色看看。高逸梅說,堵不堵,是你的事。再說你剛才送
了她那麼多東西,她以後還有仰仗你的地方,她才不會亂說呢。少芳咬牙切齒道,
你知道什麼,那都是一班狼心狗肺,翻臉就不認人的東西,送給她的東西還不如給
狗吃了!都想騙我的錢。若不是我籠絡著她們,不定她們背後怎麼勾結起來給我搗
鬼呢,饒是我三天兩頭地應付著她們,這幫東西還是捕風捉影、不依不饒地編排我。
高逸梅嘻嘻地笑了說,可不,我也想騙你的錢呢,少芳變了臉,上下打量著他,銳
聲冷笑道,你也配,你有這個能耐就不會在這兒混飯吃。她說話這麼不留情面,她
不怕他翻臉——他的人跟他的笛子是那樣的不配,她不懂笛子,可她的眼睛不會錯。
她瞭解他那點底細:他愛錢,又怕花錢,所以一生也賺不了大錢;他唯一叫人瞧得
起的就是那支笛子了,憑了這,他才得在上海各個官宦人家混下去。他這樣千方百
計地接近她,自有他的打算。她也不趕他,可她得讓他明白:她並不糊塗,她花錢
甚至養他都是她自願的。可她不能對他太狠了,得慢慢給他一些好處——那也得讓
他明白為什麼給他。
少芳的一張一弛果然有效。跟著高逸梅學戲居然也成績斐然,兩年後便邀了十
幾個票友在蘭馨戲院披掛登臺,一切事宜自然大半托給了高逸梅。十幾個票友中倒
有大半少芳是不相熟的,但人人都有一台拿手戲,如扮青衣的程家大小姐程慧儀,
扮老旦的李家三姨太小金枝,還有就是桂香園的老闆李正、連慶紡織廠的老闆娘和
青蓮閣茶館二老闆張東清等。少芳潛心學了兩年,有心要出一出風頭,在票友中間
一鳴驚人,因此托人疏通,請到這些還算是有點身份的名票友。這些人原來都不認
識少芳,後來聽說是高逸梅在教她,倒有大半人相視而笑,都說,怪不得高逸梅好
一陣子沒露面了,原來找上新買主了。說得十分不堪。大家都想瞧瞧讓高逸梅整整
教了兩年戲的——可不是,以前從沒這麼長的——陳家二少奶奶是怎樣一個三頭六
臂的人物,有心來瞧瞧熱鬧,因此少芳登臺那天,十幾位票友都到了,戲院裡擠得
滿滿的,很像個樣子。
蘭馨戲院裡有人托了零食,小吃在座位間穿梭往來。夥計給前幾排的看客依次
送上茶水,碗蓋輕輕一掀,天青色細瓷的茶杯裡一縷綠煙冒上來,睫毛都濕濕重重
的,沾了露水——容易使人想起人生譬如朝露的話,可戲園子裡的人生又如此真實、
喧鬧,一介平民的生活。只有戲臺子上的故事是假的,大家不都花了錢來看一個假
麼——今天不一樣,少芳是花了錢請人來捧場,請人來看她扮演一齣假戲。少芳把
臉對著鏡子,那是過分鮮豔美得誇張的五官。小小的房間裡掛著一排排蟒衣錦袍,
鳳冠霞帔,不容置疑的恩恩怨怨隨了這些衣服帶來的故事情節,仿佛有了生命一般
表情豐富地互相推推搡搡,爭著要上臺。少芳不良覺地把臉偎過去,貼在一件石青
繡金色蟠龍的錦袍上去,閉上眼,覺得神思恍惚起來,好像自己並不是章少芳,不
曾千里迢迢從湖南嫁到陳家當二少奶奶,而是一個從小在戲班子裡長大的藝名叫做
月月紅或者七齡童的孩子,在這戲臺子上進進出出,演出一折折忠孝義烈、貞女節
婦的故事。
邯鄲這幾天由張媽帶了回來過節,少芳自己忙得雞飛狗跳的根本無暇管他。她
不是嫌這件錦袍的料子不好,便是嫌那只鳳冠的珠子顏色不對勁,索性叫了裁縫在
家現說現做。少芳的房間裡到處堆滿了各色料子,張媽跟了傭人們忙活,邯鄲自己
在綢緞料子裡一混就混到天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