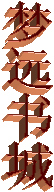
04
秋兒陪了少芳回到店鋪是一會兒的事。綢緞鋪門面不大,可也是老字號了。陳
家一年四季的衣服都作成他們的生意。因此老闆與陳家的少爺奶奶大多相熟。臨進
門前,少芳悄悄地囑咐秋兒,待會兒進去先不要和老闆說什麼,悄悄兒地看了,有
那段緞子就說,沒有就算了。咱們再扯一段。都是老情面了,說清了倒顯得咱們小
氣。
店老闆賠了笑過來,少奶奶還要點什麼,缺什麼打發秋兒來一趟,我叫夥計送
去就是,不勞您駕趕來。秋兒白他一眼,秋兒秋兒,看來我是一輩子丫環的命啦。
打發秋兒來一趟,你倒會使喚,要拍馬屁你幹嗎不早點差人送進來。我們少奶奶來
了,你倒說得好聽。店老闆打個哈哈,哪能呢,哪能呢。秋兒一面說一面東張西望,
卻不見那卷水紅緞子。正說著,她聽見小夥計在對一位女客說,正是不巧,李太太,
你要的那種水紅緞子咱們兩天前就賣完了,老闆已叫人趕了去蘇州,明天您再來准
有。秋兒看一看少芳,少芳正背對著他們看一匹新到的緞子。秋兒對老闆說,少奶
奶要件小孩披風的料子,你揀合適的讓少奶奶挑吧。
少芳慢慢地踱到臨街的木窗前,站定了向外看,沒有什麼表情,窗子是舊式的
木頭窗,一格格細密的窗棱裡面看出去,外面的世界也是分了格的,不完整。外面
的人看不見少芳,少芳的臉半掩在光線中,白皙的臉上發亮的眸子,身體也隱在黑
暗裡,那些無盡的灰色裡不知藏著怎樣的夢魔與悲哀。半露在光亮裡的她有著幾分
脫俗,仿佛在光與影的交接處冷然地觀望人間。總是這樣,總是措手不及地離開她。
她對望庭真的是不無恨意。
後來秋兒過來叫少芳時,便看見瞭望庭。原來綢緞鋪子正好是在後門出去拐彎
的那條巷子裡,他到那邊去必經的路。望庭從前門出去反而讓少芳趕在了前面。望
庭就是這樣一種人,出去嫖妓也是光明正大的——何必偷偷摸摸走後門。何況是名
正言順和太太說了去那邊,沒有理由不心安理得。
秋兒抱著一卷用紙包著看不見顏色的料子在後。少芳不言不語遙遙地跟瞭望庭,
秋兒心裡實在是有些恐慌:准得有一場大鬧。一刹那間她心裡絕望得不行。少芳是
陳家唯一與她相關的人,儘管她是主,她是僕。她是從不敢有何非分逾規之想,不
管打也好,罵也好,總比無從牽掛無所依附的好。主尊婢貴,在她心裡自有一本算
冊。如果少芳果真遭了遺棄,她做奴才的這一輩子當真是不用想有出頭的一天了。
她知道少芳這一回真的是鐵了心的,只是贏不贏還不知道。
裡面真正廝打起來只是一歇歇的事,回憶起來卻像是一場夢,亂而短促。望庭
的這個日本姨太太據說是思鄉得很,不但經常下廚做日本菜,連住房也是望庭由著
她的心意,依照東洋的家造了紙糊的拉門,在1919年的上海交際界很有點名氣。當
時和望庭一起出去留洋的人也有混得比他得意的,但是總覺得不如望庭會享福,都
覺得自己的青春是磋跎了的,又說早年也曾有過豔遇,只是沒有望庭這麼決斷。望
庭益發覺得自己的遠見,真是個聰明的男人。和子雖說早年是做下女的,但自小在
歌舞場裡廝混,原是與望庭的日本夫人一樣,遲早要做歌伎的,現在正經到中國做
了姨太太,撫養舊主人的孩子,可原先的手腕和本領一點沒丟。上海稍微上檔次的
交際場所的日本人本來就不多,何況她這樣的佼佼者。因而無意間望庭的小公館也
漸漸有了一些常客,都是一些留在中國的銀行家、商人、醫生,還有一兩個白俄音
樂家,甚至還有英國人和猶大人,雖算不上是頂上流的交際場合,總算得是很有人
緣的。
少芳沖進去一把揪住和子的頭髮時,正好只有一個銀行家叫小山的在那裡。雪
白底上繪粉紅櫻花的細瓷茶杯被少芳一路橫掃過去,成了碎片,茶水流了一地,屋
裡益發像遭了劫。少芳起先沒言語,狠命地操著一根木棍朝著和子亂打。雖說是亂
打,其實是有目的有步驟,專揀幾個地方下手,打得和子震天價慘叫。小山先是發
了呆,在一旁作聲不得。後來一個箭步沖過去想把少芳手裡的木棍奪下,哪知曉少
芳使出了蠻勁,散了頭髮像一隻目光炯炯的小獸般左沖右突,異常敏捷,棍子依舊
不依不饒地打在和子身上,連小山也猝不及防地吃了幾下,再看和子,這會兒叫倒
是不叫了,死了一般一動不動地臉朝下伏在地上。小山不覺著慌:不知哪裡跑來個
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劈面亂打的女人,門口還有個丫頭模樣的女孩子睜了眼望著她們
發愣。他猛然醒悟:只怕是望庭的太太到了。這時才發覺望庭不在,早上聽和子說
已打發人送了口信去,不知為何等到現在人影未見。他是個精明的商人,不免又想
到,少芳的這一番突如其來的大鬧,是不是有望庭的因素在內。說他給她撐腰倒還
不至於,他知道望庭新婚才三個月,聽和子說已有大半個月不曾到這兒來了。怕是
望庭但聞新人笑,不聞舊人哭,一時受了少芳的迷惑,有意無意間把這裡的地址漏
了給少芳,否則她主僕二人不過從湖南來上海三個月,人生地不熟,這地方又是極
難找的,怎的一下子就摸到這裡,二話不說就打。他揣摩少芳此舉大半是望庭借了
太太之手來煞一煞和子的威風——和子這一廂也太囂張了,拿腔作勢,裝癡做嬌,
拈酸吃醋,無論大小事大多數倒由她說了算,又有個舊日的老毛病,喜招蜂惹蝶的。
望庭礙於她的交際面,被壓制多時敢怒而不敢言。此番他絕跡半個多月不來此地,
大半原因也是和子為了一件區區家務事和他慪氣,不依不饒當眾給他難堪,掃了他
的面子。小山這麼一細細推斷,他把其中的關竅細節都推想了,益發覺得自己推想
的正確。另外他也有一層不可說的隱秘在心頭,覺得心虛,他出手阻擋時便謹慎得
多,男女有別,又礙著秋兒在旁虎視眈眈,他去奪少芳手裡的木棍不免束手束腳,
到後來索性紮煞著兩手在旁邊喊:太太,太太,有話慢慢說。他不喊別打,明知和
子這一場揍是挨定了。少芳這時才含糊不清地罵起來。和子和小山雖是中國通,可
對著湖南話也摸不著頭腦。和子受了羞辱,索性閉了眼由她打罵。少芳打得累,一
轉眼看見一個穿著洋服的男人在一旁跳來跳去,她認定是和子一幫的,不假思索,
瞅准他的小腹狠狠踢了一腳。小山不防她有這一手,痛得半蹲下去,情急之下不及
細想,狠命搡了她一把。少芳噯喲一聲,不偏不倚正好跌坐在和子腿上。秋兒見勢
不好,丟了東西撲過去就向小山懷裡撞去,小山驚魂未定,又聽得和子驀地木叫。
這次卻是少芳吃了虧。日本是忍耐的民族,和子在此時也不曾忘了她們這一族的古
訓,尋機突然發難,一口咬住少芳的手背。這一招其實中國古兵書上早已有之,其
名叫「出其不意,攻其不備」。日本女子和子用起來一樣得心應手。
正自鬧得一團糟間,早有小公館的廚子奔了出去找望庭回來。原來望庭剛巧在
門口碰上幾個生意上的朋友,拉了一起去喝酒。不想一會兒工夫家裡就鬧得翻了天。
小公館的幾個下人看見望庭一路氣急敗壞地沖進來,他們本來迫于和子平時的積威
只敢在院子裡探頭探腦,這會兒便趁勢跟著望庭一窩蜂地進來。
少芳一眼看見望庭倒呆了呆,她是一鼓作氣拿定了主意要拼個魚死網破的,此
時猛然一見望庭,原先未考慮到的事驀然兜上心頭,身子不禁冷了半截。和子騰地
一聲翻身坐起,刷地一下就抽了少芳一個嘴巴,也不看旁人。一件鵝黃底繡藍仙鶴
的和服早就被扯碎了,她就這樣半裸著進房去了。少芳卻不還手。她的臉此時正好
背了眾人,起先一動不動的,慢慢地肩膀一上一下地抽動。都以為她哭了,後來才
知道她在笑。那笑仿佛被她狠命壓在胸口了,卻又抑制不住地要出來,一進一退,
沖得身體都在抖。少芳滿懷淒情,卻又抑制不住地要狂笑起來。
房間的氣氛有點不知所措。望庭看見少芳的臉慢慢地轉過來。他準備了看一張
狂怒的臉,至少是扭曲變形的——因妒忌也好因怨恨也好。然而他看見少芳的臉是
平靜的。她的身體不抖了,嘴角兀自含了未去的笑意痙孿,而眼睛是冰冷的。這平
靜是望庭沒有料到的,因為沒有料到,心中不禁隱隱失望。他們夫婦兩個對峙著,
一股怒氣在望庭心中漸生。他想,原來夫妻間就是最大的敵人,這一層是他以前未
曾想到的。他們相互廝咬爭個頭破血流,只為了一點點難辨真偽的情分和似真還假
的名份,說得絕對一點,還不如兩個路人。他不過是個平凡的男人——還不是頂壞
的,她不過是個平凡的女人。今生今世他們註定要在這齧咬中耗盡生命。他恨她為
什麼不可以像個最平凡的太太那樣容忍丈夫最平凡的風流。
秋兒就是在這種場合下一眼發現一夫的。一夫跟一般的孩子沒什麼兩樣,有點
瘦但很結實,臉是帶點圓潤的瓜子臉,幾分清秀像他故去的母親。秋兒只看見他的
側面,他正專注地往屋裡看,腮上的一根青筋鼓動了爬到細細的脖頸上,也許是太
專注了,幼稚的臉上竟帶了兇殘的殺氣。他這時覺察到了秋兒的目光,霍地轉過身
來。秋兒不知怎的,想對他笑一笑,他也出人意料地笑了。然而接下來的一個動作
卻使秋兒嚇了一跳。一夫收起了笑容,輕蔑地看看秋兒,然後狠狠罵了一句髒話,
說得很響。秋兒的臉一下子漲紅了。
這時節的一夫也就是六七歲的樣子,他是躲在院子的一個角落裡,秋兒聽見有
笨重的東西被撕扯的聲音和發洩般的悶哼聲才走過來查看。就這樣她看見了一夫一
邊從樹枝縫裡盯著房內的廝打,一邊用一把切菜刀狠命地砍,砍秋兒忙亂中扔掉的
那卷料子。刀是鏽壞了的,用起來不利索,但是一夫砍下去提起來牽牽扯扯連撕帶
剮的一股狠勁更叫人膽戰心驚。紙包破了,才看清裡面原來是一段紫紅緞織金雲朵
的花樣。織金的雲朵太暗看不清楚,攤在地上只是憤懣的、無處發洩的一種暗紅色
的象徵。
秋兒扶了少芳回來,陳家上下早就風聞了此事。幾個得信快的親戚已經跑了來,
當然不好說是打聽二少奶奶的行蹤,只說是探望老太太,湊個牌局子,老太太房裡
因而擠滿了此等熱心牌友。張媽在廚房裡得意的大嗓門連少芳臥房裡都聽得見,我
說吧,被我說准了不是?好歹我在陳家也做了幾十年了,什麼樣的人也別想逃過我
的眼睛去。
少芳遮面朝裡躺在躺椅上。她知道她不會瘋——哪裡這麼容易就瘋了呢。她恨
望庭可她一樣對付不了他,她豁出去,瘋了一樣打了那個和於,可也只是到此為止,
她依舊對付不了他。許久秋兒才聽見她忽然冷笑了一聲。
再是冬天的時候,少芳生了一對雙胞胎,一男一女。
望庭自從經了那場大鬧之後,忽然之間有些心灰意冷起來,輕易不往家來,日
本姨太太那兒也少去,只是一味弄了錢在外花天酒地地玩。老太太先是暗暗高興:
望庭不聽她的話,就讓他吃虧了試試,看他以後還敢。後來望庭的開銷越來越大,
她才著慌起來,少不得拍桌子板凳罵媳婦不中用,連男人都拴不住。少芳聽而不聞,
望庭照樣往外跑。和子一氣之下,就帶了一夫回了日本,住一陣又回來,望庭還是
老樣子。於是和子便和一夫東京、上海兩頭住,據說也在小山的指點下做一點瓷器
生意。望庭只作不知道。
望庭得知自己添了一兒一女的時候正躲在書房裡。書房裡沒生火,他父親給他
留下的那一排排從地板到天花板的線裝書大多是發了黃的,一撚書頁就脆得直碎,
因為冷,又像是給凍得四分五裂的。望庭冷得直跺腳,覺得那一排排書也和他作對,
仿佛是一排管子和幾千隻薄薄的嘴,都在張大了,咻咻地呼吸,把他身上的一點熱
氣都吸盡了,還不止,還要吸他的血。秋兒叫他替孩子取名,望庭從書架上隨手抽
了本書出來,卻是本折子戲唱本。他無聲息地翻了半晌,對秋兒說,男的叫邯鄲,
女的叫繡襦吧。他不喜歡看戲,《繡襦記》他是一點印象也沒有,但也懶得知道。
《邯鄲記》他卻是多少知道一點。也不知道是不是對,許多古老的故事都有著驚人
的相似,聽過了,看過了,往往在印象中纏繞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好像
是說一個書生忽然睡去——不知道是不是酒醉之後,夢裡落魄,夢裡高升,夢裡文
才風流意氣風發子孫滿堂——後來才知道是一場夢。不過是一場夢而已。望庭沒有
酒醉,也沒有落魄,也沒有高升,更沒有文才風流意氣風發子孫滿堂,但是近三十
年的時間,此刻想來,恍恍惚惚,可不正有一種夢的感覺。後來他瞥見《繡襦記》
裡的幾句唱詞:
喜書生弱冠,喜書生弱冠,赴試長安,車馬金裝,盛其服玩。紫府佳娃罕見,
遽爾墜鞭屬意。買笑揮金,暮樂朝歡,早不覺囊空長歎。娃留意,阿母嫌,看撚出
機關悄然拋閃。
遙遠的故事,卻與現實不相干。與他也不相干。
邯鄲與繡襦滿月的那天,陳家三少爺韶庭出了事。他這一段時間一直住在外面,
與家裡人很少碰面。見了面也是匆匆就走,為此老太太恨道:一個個都往外溜,像
見了鬼似的。這天他忽然回來,事後人們回憶他給望庭道賀時,神情也與往日無甚
分別。奶媽抱了邯鄲、繡襦出來見客,韶庭笑嘻嘻地接了邯鄲過去,逗了一陣,抬
頭對望庭說,一時倉促,來不及給侄兒侄女買什麼。望庭記得他從腰間抽出一支竹
笛說,這個權且給他們,以後補買。看以後誰喜歡就教誰。望庭心下躊躇,不知為
何他覺得這種東西有些不吉利,其實是無根據的,不接又不好,後來喚了秋兒收進
去。誰也不知道韶庭那日是什麼時候回房的。
後來趙敏因覺得悶熱,酒席未完就叫了環兒趕回來換衣服。一進門就看見韶庭
伏在桌子上,一隻手臂筆直地墜了下去,地上的血已經靜靜地汪了一大攤,趙敏接
著就看見了他手腕上血肉外翻的傷口。環兒慘叫了一聲就往外跑,被趙敏眼疾手快
地一把拖住,跑什麼?她用奇怪的語調對環兒說,又像是對自己說,他完了,你懂
不懂,救不活他了。她就這樣張了雙臂攔在門口,像是盡了力氣要攔住從前院傳來
的陣陣喧鬧,她拼了命要攔住什麼。然而夜色還是濃濃地來了,來得很快,幾乎是
一瞬間的事,屋子裡面就黑了,她的後半生也就黑了。有什麼東西在看不見的黑暗
裡迅速地塌陷破裂,她坐在黑暗裡真願意就這樣捧了韶庭的頭坐在一塊四周虛空的
沙地上無盡地向地底深處塌陷——有風卷了細微的沙石伴了他們無聲無息地墜落。
韶庭有一歇歇清醒過,靜靜地看她,她心裡痛得不行,掙扎了對他說,你放心。他
那樣的平靜,她那樣苦痛地掙扎,倒像是她而不是他在生與死的邊緣徘徊。沒點燈,
也沒關門窗,此時沒有誰經過,經過了也看不清。門慢慢地開啟了,又慢慢地關上
了,鬼氣森森,原來只是風。她叫他放心,她不會讓他的家人們及所有相干不相干
的人來看他流血,她不用閉眼就能看見那些冰冷的、興奮的、茫然的、無限期待的
眼睛。他們畢竟是夫妻,一夜夫妻百日恩,她無論如何要成全了他。可是誰成全了
他們?他們是青梅竹馬,郎騎竹馬來,繞床弄青梅,春天的郊外,有著小小的藍色
的野花,一路星星點點到天涯……滿是童年的回憶。成婚時,她並不曉得他那不正
常的心理,曉得也已經晚了。她已沒有了退路了,她恨他,她愛他,幾十年來這種
感情捆綁了她。況且,即使再嫁,她父母不答應,她自己又怎敢確定那個男人會怎
樣待她——帶了曖昧的語氣細細盤問她與韶庭之間的一切?不是沒有這種男人。她
想起來就要發瘋。
她居然叫他放心。她幾乎想笑。他居然自殺,她一直以為最終被拖垮的是自己,
他有什麼權利自殺,該發瘋該自殺的是她。她聽教會裡的嬤嬤講過上帝造人的故事,
上帝用男人的一根肋骨造了女人。她和韶庭不是。她幾乎是許了願要和他過一輩子
的。他做了她的男人,卻是別人的肋骨。
秋兒後來隨了傭人們擠去看三少爺,卻被環兒攔在外面。回來時便對少芳說,
三少爺也不知為了什麼,有錢有勢的卻短命,我們做丫頭的只好還在娘肚子裡就把
自己掐死了。她輕蔑地嘴一撇,做一個狠命一掐的動作。一語牽動少芳的心事,她
問秋兒,三少奶奶呢,她怎麼說。三少奶奶在老太太房裡哭呢,說是和三少爺住在
一起的那個男人謀財害命,砍了三少爺一刀;大少爺和二少爺已經去找了當局管事
的,趕緊追拿逃犯呢,秋兒說。秋兒過了一會兒又悄悄地說,二小姐,這事可透著
點蹊蹺呢,我聽張媽說,三少奶奶一口咬定了看見那個男人的背影在牆頭一晃就不
見了,趕過來就看見三少爺倒在地上,氣息也沒有了。打雜的老劉說了句這麼高的
牆頭可沒人跳得過,就被三少奶一陣臭駡:你怎麼知道跳不過,你跳過?我這正找
凶主兒哪,你倒找上門來了,好哇,你說跳不過就跳不過,反正兇手不是外人就是
家裡的人,敢情是你,你拿刀砍了三爺了,你把刀藏在哪兒了,拿出來,嚇得老劉
當場就跪下了。秋兒說著看一看外面,說,幾個下流的男傭人都在議論,怕是三少
奶奶勾結了野男人殺了親夫哪。少芳聽了,心裡一盤算,早就明白了幾分,暗暗地
點頭,趙敏這潑辣貨,也難為她一番做作了,死的是不得已,活的也是不得已。說
出去陳家三少爺是自殺的,非但陳家的聲名受影響,她也落個不賢的壞名聲。其實,
瞞得了初一瞞不了十五,就說這老太太,這老大房裡的,還有望庭,誰不是心知肚
明呢——說出來有什麼好。
當晚少芳就下了決心,把邯鄲送出去讓奶媽帶。她思量了一夜,好的壞的都比
較了。自己帶邯鄲吧,陳家是一口井,直筆弄通的井壁,生著滑膩陰冷古老的青苔,
一些潮濕的呼吸像蛇一樣蜷曲在磚縫裡。另有些鬼氣森森若有若無作了井水表面的
霧,夢魘一般纏繞著。有些人聲音都沒有就掉下去了,進陳家大門的人都得掉下去。
有一會她迷迷糊糊地盹著了,忽然奇怪地夢見瞭望庭那個日本的歌伎。她連她的名
字都不知道,但她知道是她。她夢見她拼命拉一夫出了陳家的大門。她在夢中渾身
一激靈,電光火石間猛然什麼都明白了。那個日本女人比她聰明,拼了命不讓一夫
回陳家來自有她的道理。旁觀者清,少芳斷定那個歌伎正是從望庭身上看到了陳家
特有的腐朽氣息。她不要邯鄲有一天也人不人鬼不鬼的,那樣他真的會不是一夫的
對手。
事情比她想像的要順利。望庭不置可否,他現在是三天兩頭不在家。老太太因
韶庭的事含了滿肚子的怨氣和灰心,竟沒有大吵大鬧,說她的孩子她要怎樣就怎樣
由了她去鬧吧,我們陳家的子孫都往外跑,留不住。少芳怕夜長夢多——不是怕老
太太反悔,是怕自己變主意,邯鄲滿月沒幾天就讓張媽帶出去了,張媽說自己老了,
正好帶邯鄲去鄉下散散心。奶媽是蘇州鄉下張媽的遠房侄媳婦。一切安排妥當之後,
少芳才定了心:只要邯鄲是個正常的孩子,她先讓他在外頭長大,只要她有錢,將
來照樣供了他上學做事,她怕什麼。
邯鄲被送走的一個星期後,梨庭從外頭打探了消息說,那個和韶庭住在一起的
男人昨天被人在護城河邊發現了,當局斷定是畏罪自殺,趙敏哭了幾場,但也無可
奈何,其實她倒真是驚異,她原想把他牽扯進來,不死也讓他吃點苦頭,哪料到是
這個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