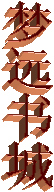
01
那時陳家還沒有敗,迤迤邐邐枝葉森森的深宅大院,好大一片占了一條狹長弄
堂的大半。因為兩邊皆是灰磚砌的圍牆,又固執又硬,平白地使人覺得弄堂的長,
走走,走走怎麼也走不到陳家的大門。正好是冬天,無限蕭瑟,陽光似乎也被嚇住
了,縮成細長的一條,小心翼翼地在弄堂的石子路上探一探頭,樹影一晃,又心虛
地縮了回去。終是寒冷。
邯鄲被傭人張媽一路牽著手小跑。不過是五、六歲的小孩子,被張媽一急,未
免弄出點驚慌失措,卻一聲不吭悶了頭由張媽連拖帶拉地跑。弄堂口有一個老頭兒
生起小火爐賣糖人。一色紅豔豔的鳳凰、飛龍等鳥獸花蟲顫巍巍地沾在細細的竹簽
上,仿佛怕冷似地縮著腳,一律是透明的、不能活動的,險險地不勝脆弱仿佛隨時
要掉下來的樣子,令人時時防備著「啪」的一聲碎裂,等了半天沒動靜,倒叫人疑
疑惑惑地懸著心。放了心擎著走,卻又忽然一下掉在地上。一種好叫人患得患失的
吃食。邯鄲路過糖人攤便有些疑疑惑惑,略略一停腳步,卻被張媽腳不沾地的一把
抓過去。邯鄲一驚,便有些垂頭喪氣。張媽百忙中騰出來瞅他一眼:邯鄲,還不識
相點,撥倷姆媽看見依隔副樣子,又要惹氣。張媽老家是蘇州鄉下,一口蘇州話。
人都說蘇州話糯糯軟軟的,可張媽不一樣,說起來總是硬硬的,倒像是糯米團裡不
小心混進了玻璃碴子,冷不防一下咬著,再找又好像沒有了,吐又不是咽又不是地
難受。連邯鄲的母親陳家二少奶都有點忌憚她,可又得罪不得,她是陳家老太大的
陪房,侍候過陳家好幾代人的老傭人了。
陳家二少奶奶少芳的娘家曾顯赫過一陣子,結婚時她哥哥騎著馬一路送她從湖
南到上海完婚,送親隊伍吹吹打打,披紅掛彩的嫁妝拉開來足有半裡路。少芳坐在
轎裡悠悠忽忽地覺得一切都不像是真的,紅繡鞋露出衣裙,鞋尖上一隻翠綠的蝴蝶
忽忽地撲打著翅膀,幾欲振翅而飛。忽然蝴蝶停住,轎停了。少芳不知發生了什麼
事,在轎裡等,不知為什麼有點茫然。
她哥哥章少華微掀起轎簾,探頭進來,皺著眉說:得耽擱一會兒了。少芳耳尖,
聽見轎外正有一支細細的嗩呐迎面而來,吹的是熱鬧的曲子《鵲登梅》。想必也是
一支迎親的隊伍。這一段正好是窄窄的山路,兩支隊伍迎面碰上了,雙方都有點笑
笑的影子在臉上,《鵲登梅》吹得更鬧了。少芳她們這一支隊伍正好有回旋餘地,
便停下來等對方走過,轎夫們也趁機歇一歇。此時離上海還遠,送親的轎夫和擔箱
籠的都穿著自己的破布襖,應景的紅襖壓在包袱底背在身上,被風吹開了,一點紅
色在灰布中活活地生氣,為這灰色天地增了喜氣,《鵲登梅》的歡樂曲子一和,紅
色更是舞得熱鬧。
是冬天。喜日子定在大年初二,算算日子,緊趕慢趕還來得及。少芳靜坐在轎
子裡,不知為什麼心裡總是栗栗的。她忍不住,終於掀開一條縫。她不清楚她想看
什麼。冬天的山腰,風緊一陣慢一陣地吹著,《鵲登梅》喜慶的曲子孤獨地高一陣
低一陣,她覺得歡喜又淒涼。她看見一頂小小的花轎已在吹吹打打中走遠,人數不
多,大約是平常人家的婚嫁。那為數不多的幾點紅色一顛一顛地在冬季長長的風裡
細細地唱著歌,喉嚨細細的,眉眼細細的,灰色再濃一點就侵蝕了它。那樣的脆弱。
章少華皺著眉叫轎夫們起程。他總是皺著眉,人生總有太多的不如意令他皺眉。
父親放了一任道台,為人拘謹得很,不會花錢,但章家的錢也從來不見多,章家好
歹是個大家族,他父母又都愛面子,儘管撐不起的時候不少。就像冬天發脆泛黃的
窗縫紙裡溜溜地吹進來的北風,許多銀子就這樣溜溜地走了。章少華總覺得溜溜地
走了的還有他的運氣。沒有天光的帳房裡,四周是黑沉沉的大家具,桌上是零亂的
帳冊,他皺著眉怔怔地想:他章家的錢到哪裡去了。他覺得他被章家騙了一場:他
是有才幹的,卻不得不被縛在章家這艘破船上共存亡,他竭盡思慮東挪西騰來的錢
卻不得不投在井裡——總是虧空,連聽個響聲都不能夠。可他又跑不了。他覺得冤
枉。他這樣皺著眉過了許多年,到了四十五歲時,他小妹少芳出嫁,他仍然覺得冤
枉,可他想他大概也跑不動了。
少芳出嫁,因是父親在任時定下的親,因而對方陳家也很有點財勢,差不多是
門當戶對了。可是他母親聽說陳家的老太太是寧波人,寧波人規矩大,他母親覺得
不放心,又沒辦法——總不能不嫁,只好一遍遍叮囑少芳。少芳有了這樣一個脫離
章家的機會,本來是有一點興沖沖的,給她母親幾次三番一來,想想往後離家的苦
楚,淚汪汪起來。她娘牽動心懷,又不好太傷感,只拍著女兒的手:少芳,少芳。
翻來覆去叮囑那幾句話。少芳不聽則已,驀地悲從心來、摟住她娘大哭起來。她自
己也不明確為什麼傷心。她娘一手撫著少芳的頭髮,一手抖抖地抹淚——少芳,少
芳,凡事多忍讓,心字頭上一把刀,忍為貴啊。她益發覺得她女兒是去受罪的,忙
忙地囑咐。少華在一旁看著不像話,皺著眉說他母親:媽,你這是幹嗎。他母親豎
起眉,狠狠地說,幹嗎,幹嗎,怪我這一生沒養個好兒子,跟你老子一樣的窩囊廢。
她也覺著冤。人人都覺得自己有一大堆理由可以抱怨,偏偏那些話像冬天河裡凍住
的魚,飛不動挪不動左奔右突的難受,眼見是沒指望了,好容易有條縫隙,便忙不
迭地發洩出來。
少華皺著眉不作聲,木木地把臉轉向另一邊。他也慣了。他還有什麼話好話呢
——再凶點,也是對著自家人,多年來他倒是看透了這一點。他一直不曾凶過,以
前倒是曾有過機會,他有個同學約了他一起出洋,那時還是大清朝,可是他家裡人……
他不是沒有鬧過。他不願意再想一記憶都是鈍鈍的,幾十年來,許多年輕時看來甚
為要緊的事現在想來都不甚要緊了。人生一世,草生一秋,不就是那麼回事。
章家老太太翻箱倒櫃把章家的一點家底統統收羅出來給少芳武裝起來。他們章
家雖說光景冷落了,也有好幾進房子,一色的青灰結實,少芳的母親住在靠東首的
臥房裡,穿著舊的銀灰緞湘繡的大襖和深紫色的紮腳褲,小腳顛顛地在房裡亂轉。
四面沒有窗,屋頂有一扇天窗,頭仰直了才看見上方一小塊天空,春天稍帶點藍色,
摸不到夠不著的那種明朗;夏天是紋絲不動的燥熱;秋天是乾乾淨淨的,空白得讓
人發急;冬天裡望出去則是一片鐵灰色,重得人透不過氣來。也許是天窗太高,從
來沒有人把它打開來。房間裡滿是笨重的家具,都像人一樣木著面孔,沒有生氣。
瘦小的少芳母親在裡面轉呀轉,像一個木偶——牽線木偶。這天有太陽,天窗裡斜
斜地投下一方變形的陽光,更顯出四周的黑。少芳正坐在中間,光亮裡看出去看不
清她母親的眉目,只知道她在找什麼,身影瘦瘦小小的,在灰塵的黑暗裡沒有眉目
地走來走去。她不由覺得心酸,另有幾分愧疚:以後待她好的機會都沒有了。她不
由走上前去,卻站在母親身後呆愣愣地礙了路。她母親揮揮手,發煩地數落:別站
得不是地方。大姑娘家,什麼都不懂。少芳停一停,慢慢地走開了去。
她也卸道她母親並不是特別寵愛她這個小女兒,這般翻箱倒櫃的,一半是為了
維持章家的臉面,另一小半也許是為了和那個寧波老太太她的婆婆明裡暗裡的較量,
她母親就是這種人。剩下的多多少少是母女情了。多多少少是一點。
登轎上路的那一天,她和母親坐在房裡等少華在外打點完畢。因為是該說的活
都說了,該哭的都哭過了,就等著上路了,她和母親都有點心不在焉的,一時不知
從何說起。
後來她對她母親說,我那塊水綠的帕子還晾在天井裡,怕是一時半會兒幹不了。
不要緊,叫秋兒帶上,路上就幹了,絲帕子幹起來快。她母親說,那帕子還是
正宗老劉家的湘繡呢,你有沒有多帶上幾塊?她母親又說,到上海怕是沒這麼好的
東西了。
少芳淡漠地說,忙忙亂亂,哪兒還顧得上這個。她的心裡翻騰得厲害,也空得
厲害,眼神兒發虛,許多歲歲月月像霧一樣,飄移著飄移著來了,遠遠的老大一片,
近了,原來什麼也沒有。
少華這時候來了。都民國了,穿長袍馬褂並不十分時興了,穿了多少看上去有
點懷舊的味道,少華這天穿著一身西服,神情卻還是古老的。少華起初並不肯穿他
剛自東洋回來的朋友送給他的這套禮服,雖然少年事俱忘卻,但少華偶爾聯想起往
事仍不免有受挫的感覺。後來穿上了,仍然有受挫的感覺,因而眉目裡多了點委屈,
穿著洋服的少華有點拘謹,看上去是新瓶裝舊酒的尷尬。
親戚朋友裡的一大幫女眷簇擁著少芳上轎,反而是她母親無意間被擠在一旁。
少芳昏昏沉沉的,只管手伸出去摸。有人說,少芳,你找什麼。少芳猛然一驚,閃
電一般頓悟:這兒將不再是她的家了。不再是了。從今後她只是一片孤獨的葉子。
從乾枯的枝丫上縱身一躍,下面是崖後的茫茫雲海,雲海下面是陸地是深淵還不知
道。她放聲大哭起來,眾人忙忙地打發他們起程。先是《鵲登梅》,後來是什麼曲
子聽不出來,一支迤邐的隊伍慢慢走遠了。
少芳止了淚,忽然想起忘了交待她母親收好她的水綠帕子,很是懊悔了一陣。
少華皺著眉對他妹妹說,你哭什麼呀。陳家也是個世家,好歹不會虧了你。他
不明白,他覺得少芳不必為錢奔命,又不用養家,舒舒服服地嫁了過去做少奶奶,
有什麼委屈的,要哭也輪不到她哭。他暗歎:女人呀,怎麼樣都是忘恩負義。
少芳見到陳家人是在婚禮完畢以後。陳家的幾個子弟都曾出過洋,因而多少帶
了點洋派回來,吃的用的都有點洋化,連老太太也喜歡用西洋的琺瑯表,因此陳家
更沒有理由不成為新派的摩登家庭了。少芳和二少爺望庭的婚禮在幾個新派子弟的
主張下一致決定採用新式結婚。少芳有一張照片是梳著齊眉的劉海,戴著金絲邊平
光眼鏡,神情稚稚地仿佛一個女學生,望庭西服筆挺地站在她身後。少芳以為這是
她所有結婚照中最時髦的一張。只是少芳對這場婚禮一直不滿意,沒有鳳冠霞帔就
不像是正式結婚。她想不出她母親知道後會怎麼說。不過現在也顧不得了。少華也
不滿意,他穿那套西服更覺得彆扭。陳家的大少爺梨庭、三少爺韶庭過來招呼他,
一口的京片子,少華的湖南話更覺得難以見人。雙方語言都不甚通,交流上不免大
打折扣,好在陳家兄弟都是伶俐人,一句接一句寒暄,各說各的也就混過去了。
韶庭到底年輕,看著這古不古新不新的少華納悶,暗地裡向他大哥嘀咕:二哥
這位大舅子怎麼這樣兒。旁邊的丫頭咭地一聲笑出來,梨庭瞪他倆一眼,自顧自和
少華有一句無一句地閒聊。少華土是土,可不笨,心裡惱怒得不行,又不好發作。
正好韶庭養的一隻波斯貓跳過來,偎在少華身邊。少華平時最恨這種粘不拉幾的依
附,袖子一抖:去、去、去,哪來的野貓招人嫌。韶庭一愣,臉上頓時有些不好看。
梨庭一扯他的袖子,若無其事地叫丫頭給舅老爺換壺熱茶來,少華也覺自己有些太
冒失,臉上一時下不來,只好一口氣地喝茶。喝下來才覺得燙,一股火氣在心裡折
騰,找不到出路。
當晚新舅老爺的故事便在陳家的傭人間傳開了。晚上大房的墜子和三房的環兒
兩個丫頭便急不可耐地催自家的主子去看新少奶奶。兩個丫環在前麵點一支小小的
燈籠引路。花園裡漆黑一片,只有眼前一團雪亮,主僕四人追逐著這點亮光,真有
點荒山探險的刺激。
進了房間,便見陳家的一大家子人早等在那兒了。陳家雖是世家,可子弟都是
新派,對這湖南鄉下來的新少奶奶都有點好奇,韶庭捅捅望庭,望庭一笑置之,說
不清表情是悲是喜。
少芳是這時候由秋兒引進來的,揣著一顆跳得不知所以的心。她把手放在胸口
使勁壓著,外面是那麼的吵,燈光是那麼的亮,許多人都眼睜睜地看著她,看著她
的婚姻故事——漠不關心地看,仿佛是看酒酣處的一齣戲。陳家有一條長長的走廊。
少芳走著,忽然想起在湖南時看的那些戲,什麼名字什麼情節都憶不起來了,此時
仿佛只看見那一片紅,紅得幽幽怨怨的,鳳冠霞帔的新娘在燭光中鬼影也似地舞;
新郎醉了,伏在桌上,都是遮了臉的、看不清表情的花燭良宵,戲班子的樂師一下
又一下地吹出假的喜氣來。她猛然記起,怪不得那支《鵲登梅》的曲子那麼熟悉—
—原來都是被人用濫了的。今夜她也在出演,看客如雲。少芳打了個寒顫。
少芳沒想到自己後來竟意外地鎮定起來。觸目花團錦簇的一大家子人,她挨個
行禮。
大少奶奶沐慧有些近視眼,又不肯戴眼鏡,說是不慣那個新鮮勁兒,可是她又
愛把它帶在身邊,沒事拿出來瞧瞧:戴上去世事就清晰了一分,褪下來世事又一下
子遠了、模糊了,頗有點收放自如的快意。看見沐慧的人都說陳家就數大少奶奶是
過得頂適意的人了,怎麼看都是賢良的,只是不明白竟不會生養。沐慧也不知道有
沒有聽見,或者根本是聽了一半丟了一半;看了一半掩了一半。她就是這麼個醒了
一半睡了一半的賢妻——由得梨庭在外胡鬧!麻將桌上李太太似笑非笑地說。
沐慧光著雙眼迷迷瞪瞪地看見穿軟紅緞旗袍的少芳向她來行禮,近了,抬起頭,
看見一張尖尖的瓜子臉。沐慧沒戴眼鏡,虛著眼神兒微笑著,自己也覺得有幾分睡
眼惺松的霧美人的情調。少芳看她笑得似乎和氣,心裡也生了幾分好感。
秋兒在相熟了之後問墜子,你們少奶奶的眼睛怎麼啦。墜子撇撇嘴,輕輕罵了
句老妖精。
陳家的大少爺梨庭,三少爺韶庭都早早地把新娘娶進了門。只有二少爺望庭一
度在日本留學,耽擱了幾年。三少奶趙敏的出場頗像《紅樓夢》裡的鳳姐,頂摩登
與時髦的,一雙雪白的手上只有拇指與小指的指甲是突兀地塗了兩點寇丹,尖尖的
仿佛是兩滴欲滴的血,少芳不知道這是不是時下最流行的塗法,趙敏矜持得很,看
著少芳只是抿著嘴笑,那笑意也有些突兀地帶著尖利。趙敏回過頭去,壓低了聲音
向韶庭笑道:二少奶奶可美得很呐,人想必也老實。二哥,你可不能欺負她。未一
句話是對望庭說的,說得響了點,眾人聽見了,都笑起來。少芳瞟一眼望庭,望庭
好像沒聽見一般,不知在想些什麼。
張媽就是在這時瞥見了少芳的眼風,夜裡服侍老太太睡覺時嘀咕:到底是湖南
鄉下小地方來的,不大方。有句話藏著沒說出來:眼睛花花的,不是旺夫相,倒像
個小家碧玉出身的姨太太。老太太不說話,過了一會兒,上床時停了停又說,也好,
興許能收瞭望庭的心。這沒出息的東西就喜歡那個東洋婆,整天价掉了魂似的。
少芳是在新婚第三天知道望庭的日本姨太大的。
陳家有前前後後好幾進房子,人多,也不覺得空。少芳的房間是在西邊,窗戶
底下長著一大叢月季,再過去就是圍牆了,站在樓上能看見牆外的小巷,陰陰涼涼,
細長綿延,圍牆裡伸出樹枝把一條小巷遮了大半陽光,一會兒看得見人,一會兒看
不見人,任何走進這小巷的人,在上面看來,都出現得突兀,消失得也突兀,斷斷
續續的,老也連不起來。少芳被巷子外的一陣隱隱的叫賣聲驚醒,一個蒼老的聲音
拉長了尾音喊:酒—釀—湯—團—。她聽不懂上海話。從窗子裡望出去,天空還沉
沉的黑,但過一會兒就有點淡了,隱隱帶著金紅的樣子,像是誰在天空後面隔著簾
子放了一把火,燒的是什麼就不知道了,只是隱隱地燃燒,叫人捉摸不透,恨不得
一把掀起來看個究兄。
秋兒來服侍少芳梳洗。暗紅的梳粧檯旁放一個紫銅臉盆,熱水放進去,一會兒
就溫溫吞吞的了。少芳把一隻髮夾咬在嘴裡,兩手上舉,一下一下地梳頭,擰著眉
頗有點怒目橫眉的味道。屋裡還點著燈,鏡子裡反映出來的房間與人也是沉沉的影
象。秋兒放好毛巾來幫少芳梳頭,少芳煩道:什麼臭規矩,大清早的叫人睡不得好
覺,她自己睡得舒服,倒叫人等在外面。那個「她」自然是老太太了。望庭在床上
翻了個身,笑著說,我們家就這點子規矩,你順著她好了。他的話聽上去隱隱有一
絲不滿,一種不知道針對誰的懶惰無聊的不滿。少芳湊近鏡子去看自己的眉目。她
們湖南人的胭脂花粉都是塗得極濃的,陳家雖說是北方人,可也在上海多年,又是
極新式的家庭,趙敏的打扮就與別人不同,也是一般的濃豔,臉頰上兩片紅紅的胭
脂夾一支長長的瓊鼻,最是醒目,都說趙敏是一個標準美人,少芳暗暗不服氣,用
手帕把臉上的胭脂輕輕抹掉又抹掉一點。她對望庭說,我先到老太太那兒去,你一
會兒就過來吃飯。望庭正穿鞋子,停一停說,你不用等我,我有事得出去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