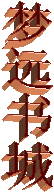
第十八章 俄羅斯粉條
我清楚地記得,當時,我的心情就和一個當真裡通外國的奸細被人抓住了證據
一樣。我甚至於張不開口說明那天是怎麼回事,而按小皮球的說法,卡佳「沒有穿
衣服」,這太駭人聽聞。我的經驗是,在這種情況下我已必敗,用後來學到的臺灣
國語說已經「死定了」,如果我強調她並非裸體而是穿著完整的泳裝,除了證明我
態度不好和狡辯,還能有什麼用處嗎?
另一條船上的專家組長給我與卡佳照了一張照片。這張照片給我找了太多的麻
煩,我的生活從此走向了蹉跎直至危難——這樣的故事了無新意,容略。
使我難忘的是那個包裹。我當著領導與皮球的面打開了它,裡面竟是——對不
起,喀秋莎和俄羅斯,相當劣質的黑乎乎的粗粉條和一廣口瓶鹹菜。
這就是蘇聯的副食?這就是蘇聯的禮物?這就是喀秋莎的饋贈?我們在莫斯科
餐廳吃過很好的俄式大菜呀。
這裡還有一個最最不可思議的謎:我雖然俄文並不過關,字母還是會認會讀會
拼的。我翻遍了那個倒黴的包裹,沒有王也沒有萬或者哪怕是吳或者翁,我沒有從
包裹的收件人欄那裡找到自己的名字哪怕是類似自己的名字,也沒有從寄件人那裡
找到或卡傑琳娜,或斯密爾諾娃,或二者皆備,或卡佳,或喀秋莎的名字。俄國人
的名字再複雜,包裹表面再磨損,我的俄語再差,我相信我是能夠分辨我們兩個人
的姓名的。恰恰相反,我從包裹收件人欄讀到的模糊不清的字母更像是皮球的名字。
在我拿起包裹看個不停的時候,皮球大喝一聲:「看什麼?還想念你那個蘇聯女特
務嗎?」
論級別皮球連科級都算不上,而我當時已經是正處級了。她怎麼敢對我這樣吆
喝訓斥?問題是我與穿泳裝(進行日光浴)的斯密爾諾娃划船事發,該死的專家組
長那天確是高舉著卓爾基相機對著我們的船照過相。我是肚裡有鬼(毛主席說愈怕
愈有鬼),根本不敢分辯。我已經頭昏腦漲,我想到的比已經發生的竟然還糟,我
想如果領導讓我交待粗粉條加鹹菜是什麼密電碼,那可怎麼好?在階級鬥爭民族鬥
爭國家鬥爭你死我活的時刻,有這種問題的人先槍斃再定案也不是不可能的。我想
著唯一的活路是過兩年發生與蘇聯現代修正主義的戰爭,給我一個炸藥包吧,我准
備連炸20輛蘇聯坦克。還不行嗎?
條條大路通向失事和墜毀。條條道路都可以叫你完蛋。反胡風和肅反中我基本
無事,反右中我僥倖過關,反右傾中我也只是自我緊張了一下而已,這回,我可是
跳到黃河裡也洗不清了。這以後的故事乏善可陳。有一點變化,從此我喜愛起吃粉
條來了,沒有「思想動機」,只是口味上愛吃。我一直納悶,俄羅斯的粉條到底是
什麼味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