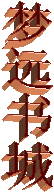
第十二章 情到深處
400塊錢拿回我的桌子,妻用惡狠狠的眼睛望了我一下,提前退場以示抗議。
音樂響起來了,雖然仍然是電聲樂器與架子鼓,曲調並沒有現代化或搖滾化,一切
仍然是那麼安詳。
在那矮小屋~裡,
燈火閃~著光,
年輕的紡織姑娘,
坐在窗~旁。
年輕的紡織姑娘,
坐在窗~旁。
我用我的歌詞來附和她的俄文歌詞。別來無恙的紡織姑娘啊,你的聲音經過了
山山水水,風風浪浪,險險惡惡,死死生生。你的溫柔,你的純真,你的思念和你
的稚氣和傻氣的嗓音竟然比USSR或CCCP,比「俄羅斯聯合各自由盟員共和
國,結成永遠不可摧毀的聯盟」這氣魄宏大的蘇聯國歌,比「烏拉斯大林」的冒死
衝鋒,比中蘇牢不可破的友誼和磐石般的團結,比「伏爾加河畔聽到長江流水聲」
(《莫斯科——北京》歌詞)更久長更有力。
我實在不好意思,在聽到了她的《紡織姑娘》以後,我幾乎痛哭失聲。所以我
只能低下頭。
歌聲向我走來,一種我早年間熟悉的香水——更正確地說應該是「花露水」或
者更更正確地說應該是一種古老和美好的香皂——氣味在向我走來,我感到了一陣
清風,我感到了一陣暖意,然後是涼意,我抬起了頭,我已經成功地控制住了自己
的眼淚。我畢竟是一個年老的男人。德國人就告訴過我,他們的男子脫離開兒童時
代以後,再不會哭泣。
歌手走到了我的桌旁,向我單獨地唱歌,向我微笑,在她唱歌和微笑的時候,
我覺得她正隨風飄了起來,我也開始隨風飄了起來,我們都離開了地面……她太像
40年前的卡佳了,只是頭髮比喀秋莎長些,臉也比當年的喀秋莎略長一些。甚至
她的聲音,也是卡傑琳娜·斯密爾諾娃那種沙啞的熾熱型的。當然,她的聲音拿得
準確,不像卡佳那樣五音不全。那次團幹部會上,我是怎樣地為她的不會唱歌而心
痛呀。
我的嘴動了動,我的嘴的動作像是在試探地說「卡佳,喀秋莎,卡傑琳娜·斯
密爾諾娃」。在我的想像中,她應該是卡佳的女兒,雖然一直到40歲了,她從中
國離去的時候,她還沒有結過婚。莫非是那一個?我想起了皮球的長舌。那麼現在
唱歌的姑娘懂了我的意思嗎?她為什麼點了點頭?她為什麼笑了笑,笑得那麼苦?
她後退了一步,她要離去了嗎?她回過身去了,她突然又回過了頭,正是曲子過門
的地方,她分明在說:「陶瓦裡稀赤萬?」就是說,她在問我是不是萬或王同志。
俄語裡沒有ng的音,它的n「萬」就是「王」?
這天晚上,我在喀秋莎餐廳裡一直呆到11點45分打烊,年輕的歌手沒有再
唱第二次《紡織姑娘》,她表現了剩餘的卻是堅定的矜持,她退回了400塊錢,
而且不因為你多給錢而連唱數遍,畢竟是前蘇聯或原蘇聯的,其實更正確地說就是
蘇聯的俄羅斯的姑娘呀。原啊前啊,我們為什麼這麼多的廢話!我尊敬她們,並為
自己的近乎失態而慚愧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