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達書庫 > 賈平凹 > 秦腔 > |
| 八十四 |
|
|
|
回到家,瞎瞎一夥還在搓麻將,媳婦卻想不出把錢放在哪兒安全,先放在櫃中的麥子裡,又取出來,就從穀糠甕背後翻出一個破紙盒,放在盒子裡了,再想想,怕錢潮了,用一片塑料紙包了,還在紙盒上放了些麥草,重新藏在甕背後,謀算著明日下午就可以重到南溝廟裡去了。瞎瞎在堂屋喊:「喂,喂!」媳婦知道在喊她,偏不作理,瞎瞎就罵:「你耳朵塞了驢毛了嗎?」媳婦說:「你吱哇啥的?」瞎瞎說:「你攤些煎餅,去大哥院裡摘些花椒葉墊上,椒葉煎餅好吃!」媳婦說:「我不去,上次摘花椒葉,大嫂蠻不高興哩。」瞎瞎說:「摘她個片花椒葉都不行?你去,你偏去摘!」媳婦說:「你能行,你去摘!」瞎瞎逗火了,當下放下牌,就去了慶金家院子摘花椒葉。一會兒回來進門竟吼道:「是你把大嫂領到南溝廟裡去了?」媳婦說:「她說要給光利抽籤的,她要我帶路,我能不去?」瞎瞎扇了媳婦一掌。瞎瞎的個頭低,他是跳了一下扇的媳婦的臉,說:「你抽的屁簽哩!光利已經坐車去新疆了,如果大嫂在,光利還不敢走的,你把大嫂卻偏偏帶到廟裡去了,現在大嫂尋死覓活的,你負責去!」媳婦一聽,說:「爺!」轉身就走。瞎瞎又跳著一個巴掌扇過去,說:「你往哪裡去,你惹下事了,你不乖乖在屋裡還往外跑?!」媳婦挨了打,並沒有哭,在院中的捶布石上坐了一會兒,進廚房攤煎餅。這媳婦做針線活不行,攤餅在五個妯娌中卻是最好的。她娘死得早,四歲上她就在案板上支了小凳站著學攤餅。嫁過來後,瞎瞎不務正事,又惹是生非,她已經習慣了,知道這是她的命,也就不哭,也不在人前唉聲歎氣,但該怎麼辦就怎麼辦。餅煎了一案,她的奶驚了,孩子還放在婆婆那裡。就在灶火口將衣服撩起,將憋得生疼的奶水擠著灑在柴火上。然後把餅盛在盤子裡,又在四個小碗裡調了辣子醋汁,一切都收拾停當,拉閉了廚房門,在院子喊:「餅子好了!」自顧出門去接兒子。 麻巧的臉青蘿蔔似的,從巷子裡小步跑,一對大奶撲撲閃閃像兩袋子水,咕湧得身子跑不快,瞎瞎的媳婦就忍不住笑了。瞎瞎媳婦說:「嫂子,嫂子,狼攆你哩?!」麻巧沒吭聲,但跑過三步了,卻說:「你有事沒事?」捏了一下鼻子,把一把鼻涕抹在巷牆上。瞎瞎媳婦說:「我去接娃呀,娃在他婆那兒。」麻巧說:「那你跟我走!」瞎瞎媳婦糊糊塗塗就跟了走。走出了巷到了街上,她不知道往哪兒去,說:「嫂子,你知道不知道光利到新疆去了?」麻巧說:「去了好,都窩在咱這兒幹啥呀!」瞎瞎媳婦說:「他一走,他娘尋死覓活的!」麻巧說:「誰的日子都比我好!」瞎瞎媳婦覺得不對,也不敢多說,跟著只管走,瞧見麻巧頭上似乎長了個大紅雞冠。瞎瞎媳婦說:「嫂子你頭上有個雞冠?」麻巧說:「我成了人的雞啦?!」瞎瞎媳婦再看時,那不是雞冠,是一團火焰。揉揉眼睛,火焰又不見了。 這兩個婆娘到了萬寶酒樓前,腳底下騰著一團塵土。丁霸槽在樓前的碌碡上吃撈面,辣子很汪,滿嘴都是紅,剛一筷子挑了一撮,歪了頭用嘴去接,驀地看見麻巧過來,忙咽了面,跳下碌碡把路擋住了。麻巧說:「矬子,君亭在沒在樓上?」丁霸槽說:「啥事?」麻巧說:「他幾天不沾家了,是不是在樓上嫖妓哩?」丁霸槽說:「啥?你是糟賤君亭呢還是糟賤我酒樓呢,我這兒哪有妓?」麻巧說:「誰不知道你那些服務員是妓,三踅帶著到處跑哩!他幾天不回去了,家還是不是家?!」丁霸槽說:「君亭哥是村幹部,你見過哪個大幹部能顧上家?」麻巧說:「他算什麼大幹部,看有沒有指甲蓋大?」丁霸槽說:「你權當他就是大幹部麼!你不認他,我看他就是清風街上的毛主席!」麻巧說:「他人肯定就在樓上,你為啥不讓我上樓去?」丁霸槽突然大聲說:「我君亭哥肯定沒在樓上,你是警察呀,要檢查我呀!」麻巧說:「你喊那麼高你別報信!」就對瞎瞎媳婦說:「你就在樓口守著,我上去尋!」瞎瞎媳婦到這時才明白是來要捉姦的,她才不想沾惹是非,轉身就走。這時刻,酒樓上有聲音在說:「胡鬧啥的,在這兒喊叫啥的?!」君亭披著褂子從樓梯上下來。麻巧說:「矬子說你不在樓上,你在樓上幹啥哩?」君亭說:「我的工作得給你彙報呀?往回走,清風街上哪個女人這樣過?你在這兒信口亂說,我還工作不工作?!」一腳朝麻巧屁股上踢,沒踢著,麻巧卻貓腰就上了樓,砰地將一間房門踹開,床上睡著一個女的,拉起來就打。樓上一響動,丁霸槽先跑上來,君亭也上來了,兩個女人已糾纏在一塊,你撕我的頭髮,我抓你的臉皮,丁霸槽忙拉開,各自手裡都攥了一撮頭髮。丁霸槽說:「人家是我這兒的服務員,你不問青紅皂白憑啥打人家?」麻巧說:「大白天的她睡啥?」丁霸槽說:「大白天就不能休息啦?」麻巧說:「她休息就脫得那麼光?」指了那女子罵:「你要清白你把你那×掰開,看有沒有男人的?在裡邊?」君亭壓住麻巧就打。麻巧叫:「你打死我讓我給她鋪床暖被呀?!」君亭吼道:「你給我叫,你再叫一聲?!」麻巧不叫了。瞎瞎媳婦趕忙拉了麻巧就走,君亭就勢站起來,理他的頭髮,臨下樓了蹬了那女的一腳。 麻巧鬧了萬寶酒樓,消息不免在清風街傳出,可是第二天,麻巧卻再次來到萬寶酒樓,當著眾人的面,說她錯怪了君亭,也錯怪了萬寶酒樓上那個服務員,而且道歉。這絕對是君亭導演的。如果君亭壓根不理會,別人倒認作是麻巧生事,而麻巧不是順毛能撲索的人,她這麼表演,就欲蓋彌彰了。但是,這種表演不管多麼拙劣,你得佩服君亭畢竟是制服了麻巧,清風街又有幾個男人是制服住老婆的主兒呢?我好事,曾經去君亭家和夏天智家的周圍偷偷觀察。我發現了君亭從那以後是每天都按時回家吃飯和夜裡回去睡覺的,而夏天智也在他家院子裡大罵過夏雨,不久,萬寶酒樓上的那個女服務員就再不見了。那個女服務員一走,三踅好久一段不去萬寶酒樓了,丁霸槽從北原上採購了五條幹驢鞭,用燒開的淘米水泡了,對三踅說:「你不來吃錢錢肉呀,厲害得很,才泡了半個小時,就在盆子裡栽起來了!」三踅說:「我已經上火了,還讓再流鼻血呀?!」倒是坐在萬寶酒樓前讓剃頭匠剃光頭,拿了炭塊在牆上寫:「你可以喝醉,你可以泡妹,但你必須每天回家陪我睡,如果你不陪我睡,哼,老娘就打斷你的第三條腿,讓它永遠萎靡不振!」夏雨知道三踅這話指的誰,用瓦片把字刮了。 清風街好長好長的時間裡再沒有新聞了,這讓我覺得日子過得沒意思。每日從七裡溝回來,在街上走過,王嬸還是坐在門道裡的織布機上織布,鐵匠鋪已經關門,染坊裡的叫驢叫喚上幾聲再不叫喚,供銷社的張順竟趴在櫃檯上打起盹兒了。我一拍櫃檯,他醒了,說:「啊,買啥呀?」我說:「沒啥事吧?」張順說:「進了一罐酒精,陳亮來吸過導管了。」我罵了一句:「誰稀罕喝你酒精呀?!」回去睡覺。枕著的那塊磚,把頭都枕扁了,就是睡不著,便坐起來想白雪。我很想白雪。想得在街巷裡轉,就看見了陳星挑著一擔蘋果從果園裡回來,擔子頭上別著一束月季。我抓起一個蘋果要吃,他說:「你給一角錢吧。」我沒錢,理他的,我把蘋果狠狠地扔回筐裡,卻把那一束月季拿走了,說:「這月季該不會要錢吧?!」拿著月季,我突然想,也許是那個人的心意呢,就覺得自己像月季一樣盛開了。 那個傍晚,我的心情陡然轉好,而且緊接著又來了好事。我拿了月季唱「清早間直跪到日落西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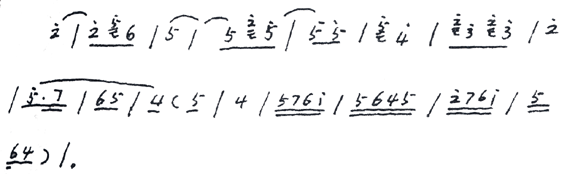 |
|
|
| 學達書庫(xuoda.com) |
| 上一頁 回目錄 回首頁 下一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