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達書庫 > 賈平凹 > 秦腔 > |
| 四十八 |
|
|
|
我才要轉唱到《水龍吟》,屹甲嶺上過來了一片雲,我還以為又來了地虱婆,仔細看了看,不是地虱婆,是真雲像一個白蒲團,浮在中街的上空。我說:「雲,雲,你下來!」雲就下來了,落在土地廟的臺階上。土地公和土地婆是現在的清風街最大的神,清風街所有的故事它們知道,就該曉得我的心事,我就不唱了,雙手合掌在廟前作揖。君亭嘟嘟嘟騎著摩托過來,輪子碾著一攤髒水濺了我一身,我沒有惱,還給他笑,他竟然也笑,說:「你笑啥的?」我說:「你笑啥的?」他把摩托靠在了廟前,雲繞了他,他以為是煙,揮了揮,說:「引生,笑!高興了就笑!」然後披著褂子,他穿的是府綢褂子,無風而扶了風,從街上往過走。 市場建成後,為了爭攤位和繳攤位費,發生過許多爭執和吵鬧,甚至王嬸和狗剩家的寡婦還廝打在一起抓破了臉,但清風街開始繁榮,村裡所收的租金和管理費也多起來卻是事實,君亭就得意了。他從街上走,開小飯館的就說:「支書支書,你吃了沒有?」君亭說:「有沒有紅燒肉?給我留一碗!」書正的媳婦將淘米水往街上潑,猛地看見了君亭,一時收不住,自己先在門檻上跌倒了,水濕了一懷。君亭說:「街面就你這門前壞了,你要再潑,這段路你家得鋪了!」書正媳婦說:「我哪兒要潑!你吃啦?」君亭說:「沒吃哩,有啥好吃的?」書正媳婦說:「現在了你還沒吃?當幹部的就是辛苦!君亭,我沒叫你支書你不會不高興吧?嫂子給你說,身子骨是本錢哩,你的身子骨可不是你君亭的!」君亭說:「你也會說了這種話!書正呢,廁所還沒修好?」書正媳婦說:「開始用啦,你去啊,給咱多拉些!」但君亭已經走過去了,和染坊裡的年輕女人開玩笑。染坊不再是誰把土布送進來,染了色澤花紋再交給誰,只收個染錢,而是從方圓村鎮收土布,染過了在市場上擺攤子賣。312國道上每天有車停下來購買了回去做床單和桌布,賣得最好的一次竟然出手了四十八件。君亭就說每件布為什麼不做個塑料袋呢,塑料袋上還可以寫上染坊的歷史和各種產品的介紹呀。白恩傑的媳婦噢噢地叫:「你把我點醒了,你把我點醒了!」君亭就說:「那怎麼個謝我?」女人說:「謝麼,你說咋謝?」君亭說:「今黑兒把門留上。」女人笑喘著,攆出來拿著挑布竿兒打君亭。君亭一跳,雙腳跳到南邊的臺階上,卻見一家門過道裡是四個人在玩麻將,見了君亭也不避。坐在桌東邊的是三踅的老婆,穿著裙子,黑瘦腿上爬著一條蚯蚓。君亭說:「瞧你那腿!」三踅老婆看了,呀的一聲,掏了紙就擦,原來是來了例假,說:「你眼睛往哪兒看哩?!」君亭說:「整天都見你玩麻將哩,人都成幹螞蜢了,還只是玩哩!」三踅老婆說:「我沒事麼,地裡就那麼點活,做生意不會,人又這麼大歲數了,沒人親,沒人愛,沒人弄了,不打個麻將幹啥呀!支書,我們玩的可是甜麻將,沒賭的!」君亭臉燒了一下,去供銷社買了一條紙煙,往大清堂去了。 大清堂裡坐著趙宏聲和中星他爹,兩人趕緊起身。君亭說:「宏聲,你沒去市場?」趙宏聲說:「我咋沒去?你這一回為清風街幹了好事了,現在沒人說你的不是了。」君亭說:「是嗎?那你怎麼不給牌樓上寫個聯呢?」趙宏聲說:「我早就寫了,不知你願意不願意?」當下拿出兩副,一副是:「我若賣奸腦塗地;爾敢欺心頭有天。」君亭說:「這不行,黑貓白貓逮住老鼠就是好貓,你管人家怎麼賣的?!」看第二副,是:「少管窩裡閒事;多賺外人銀錢。」君亭說:「還行。市場上攤位多人多,就像天天在開老碗會似的,我最煩有些人說是非!這聯如果能加些政治話就更好了。」趙宏聲說:「我沒當過幹部,我不會說政治話。」君亭想了想,說:「『要開放就得少管窩子裡閒事;奔小康看誰能多賺外來的銀錢』,怎麼樣?」趙宏聲說:「好!」君亭說:「我路過丁霸槽家,門上貼了聯,一邊是『交通基本靠走,治安基本靠狗』,一邊是『通訊基本靠吼,娛樂基本靠手』,這是你給他寫的吧?」趙宏聲說:「他的意思我編的句,調子有點灰,是不是損害了咱清風街的形象?」君亭說:「他這是有野心了麼!」趙宏聲說:「你知道不,他現在正鬧騰著要蓋酒樓呀!」君亭說:「好麼,村兩委會支持哩,這個小矬子還真沒看出!」趙宏聲說:「人不可貌相,海不可鬥量。三踅是歪人吧,昨日他就和三踅打了一架,敢給三踅頭上撂磚!」君亭就急了:「打架了,為了啥?」趙宏聲說:「三踅瞧不起丁霸槽,他在街上看見了丁霸槽,故意攆上去蜷了腿和丁霸槽並排走,街上人一笑,丁霸槽就生氣了,兩人一吵就打起來。我看是三踅尋事的,他其實心裡怕丁霸槽起身哩。」君亭「嗯嗯」了幾句,就不問趙宏聲了,卻對中星他爹說:「榮叔,我還要求你個事的。」中星他爹立即挺了身子:「是托中星在縣上找什麼領導?」君亭說:「你就得意你家出了個中星!」中星他爹有些不好意思了,說:「那我給你算一卦?」君亭說:「那就不必了。算什麼卦呀,不想幹事了總能有藉口,但要想幹事了就一定會想出辦法!」說完,拍拍手出門而去。 如果佩服君亭,我就佩服君亭自以為是的氣質。我多次站在遠處看他,他頭頂上的火苗子躥得高。他騎摩托的速度越來越快,前後輪扇起的塵土像一朵雲,我甚至想過,憑他現在的運勢,披上一件麻片都能浮上天的。收麥天揚場,講究有風了就多揚幾鍁,君亭在市場建成後剛剛取得成效,就謀劃起了又一個決策。他的謀劃,一般人是看不懂的,但他瞞不了我,當我看見他見了三踅是那樣的熱乎,說說笑笑,拍拍打打,轉過了身臉立即恢復了平靜,我就知道他三踅沒好果子吃了。我說這話是有原因的。二十年前水庫建成後,水庫上除了澆溉就又飼養了魚,但水庫離清風街太遠,養下的魚難以賣出,後來便在清風街的灘地上修了四個魚塘,這些魚塘平日供縣上的幹部星期天來垂釣,逢年過節了,捕魚又作為年節貨給各級領導上禮。魚塘先由鄉政府代管,同時代管的還有磚場,鄉政府代管是今日換人明日換人,經營不上心,結果是獲不了利反倒虧損了還得補貼,鄉政府就把磚場交給了清風街而只管了魚塘。三踅當了磚場負責人後,鄉政府不知怎麼將魚塘也讓三踅替管。三踅是堅硬人,他手裡有磚場和魚塘,在清風街就更橫了,硋三喝四,可以和兩委會抗衡,以至於誰家娃娃夜裡哭,哄不住,當娘的就說:「再哭,三踅來了!」三踅簡直和舊社會的土匪一樣,嚇得娃娃都不敢哭了。君亭當了村幹部,為了打開工作局面,常常是依靠三踅,而局面剛一穩住,他就曾提出過收回磚場,或者讓三踅乾脆承包磚場。他的提議大家一哇聲地支持,可三踅就是不交讓也不承包,一面向鄉政府送東西賣好,一面向鄉政府告狀兩委會中的經濟腐敗。結果,三踅的問題不但按下未動,反倒查起我爹在河堤賣樹和修街道工程中的賬。當然這查不出個什麼來,但尿泡打人,不疼,卻臊哩,壞了我爹名聲。待到君亭當了支書,再次提出讓三踅承包磚場的事,兩委會裡卻有人說:「不惹他了,村裡還需要一個惡人,有許多事情咱們辦不了,利用他倒能辦的,鬼是越打越有,打鬼不如敬鬼!」君亭覺得一時難以扳倒三踅,就琢磨著慢慢削弱三踅的勢力。君亭要扳倒三踅,我是支持的,但他幹著幹著,我就看不慣了。他是第一步想收回魚塘,考慮到水庫管理站肯定不同意,就以對換七裡溝作為條件和水庫管理站溝通。水庫管理站是同意了,他們想將七裡溝統歸於水庫周圍的綠化帶中,將來創辦水庫綠化風景區,發展旅遊事業。君亭把協商的結果提交了兩委會討論,一半人竟然反對,說用七裡溝換四個魚塘不划算,把七裡溝賣了自己就能修十個魚塘的。君亭當然在會上不能說出他最根本的心思,只強調七裡溝是個荒溝,除了水庫外誰還肯要?反對派說不過君亭,卻堅持七裡溝就是沒用,也不能和魚塘交換,因為清風街人在那裡投過錢,出過力,說不定以後,還可以再次淤地。一提到淤地,君亭就火了,發了一通脾氣,會議再沒開下去。君亭權衡了幾天,拿不定主意,見了中星爹原本想讓老漢給這事算一卦,預測一下得失利害,可中星爹的神氣讓他不舒服,也就不肯再說一個字來。又是過了數日,秋收全面鋪開,此事暫放下,而丁霸槽的舊院牆就推倒了,開始挖坑夯基,夏雨也雇車從縣上運回了鋼材和水泥,在戲樓前的場子上做水泥預製板。君亭去看了,問:「你有多少錢就辦酒樓呀?」丁霸槽說:「辦酒樓才掙錢呀!」他把丁霸槽抱起來,打了一拳,說:「你矬子是濃縮的精華啊!」心裡卻堅定了七裡溝換魚塘的決心:碕,換了就換了!有啥反對的?過沼澤地能沒蛤蟆叫?!這如同幹部任用一樣,任用前意見大得很,一旦任用了,所有的人還不都是狗,尾巴給你往歡著搖哩!當天就帶了上善和金蓮去了水庫,和站長簽了合約。 一天下午,劉新生請了夏天義到他的果園裡察看樹木病情,因為許多樹葉子莫名其妙地都枯黃了。夏天義去了,發現是一種蟲子隱身在樹根的土裡,白天你看不見,晚上順著樹根上來咬噬樹皮,就建議用石灰漿塗抹樹身。新生和陳星是互不往來的,夏天義又怕新生不會將治蟲的辦法傳授給陳星,就離開了新生的果園又到了陳星那兒。果然陳星的果園裡也枯死了好些樹,正愁得撓頭,見夏天義這麼關心他,又感激夏天義從未干涉過他和翠翠的事,便一定要留夏天義喝酒。夏天義喝酒喝到了八成,吼著秦腔往家走:「將八台平落在背街哎上,包文公下轎來細觀端詳」。沒想用力過猛,一吼門牙就掉了一顆,拾起來包著,詞兒是不唱了哼哼曲調:  才走到鐵匠鋪門口,卻見土地廟那兒擁了一些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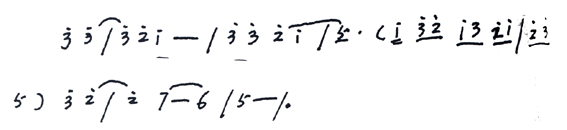 |
|
|
| 學達書庫(xuoda.com) |
| 上一頁 回目錄 回首頁 下一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