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達書庫 > 賈平凹 > 秦腔 > |
| 四十七 |
|
|
|
夏雨把英民叫到了雞圈旁邊,夏雨說:「你把這些家具賣給了三踅?」英民說:「我急著用錢呀。」夏雨說:「你這是不是要給人看的?」英民說:「給人看能把三萬元的東西一萬二賣出?」夏雨說:「人都說你有錢,那你這些年掙的錢呢?」英民說:「不就是蓋了一院子房,又添了這幾件家具麼。外頭倒是還欠著幾萬元施工款,可已經兩年了要不回來。」夏雨說:「我剛從白家過來,那邊天都坍了,你能給人家拿多少?」英民說:「五千。」夏雨說:「五千元太少。出了這等事,誰也不願意,既然出了,趕快讓人入土為安,五千元是少了,你給上一萬,我代表我爹平這場事。」英民說:「你和白家是親戚,四叔讓你能來給我說這話,我感激四叔和你哩!可我確實再拿不出來,如果給白路一萬,那兩家肯定也要一萬,那我也就只有死了!」英民扭過頭對老婆說:「你倒還哭個啥麼,,把紙煙拿來,夏雨代表四叔來的,把紙煙給夏雨!」夏雨說:「我不吸。」英民拿了凳子讓夏雨坐下。 英民的女兒從院門外跑進來,連聲著喊爹,說:「來啦!來啦!」英民說:「誰來啦?」女兒說:「西山灣人來啦!」英民說:「來了就把人家請進來,誰也不能惡聲惡氣。」女兒說:「來了兩撥人,十幾個哩,在街口就罵,說要賠兩萬,一個子兒都不能少!」英民臉當下煞白,就對三踅說:「兄弟,你幫幫哥,你快去巷口把人擋住!」三踅說:「要鬧事呀?我去看看!」三踅就出去了。英民說:「你看,你看,他們倒要兩萬!」遠處已傳來了吵鬧聲。英民突然說:「夏雨,不怕你笑話,我現在得了稀屎癆了,一急就夾不住屎啦。你坐,我上個廁所。」 英民去了山牆後的廁所再沒出來,一夥人就進了院,粗聲喊:「李英民。」夏雨跑到廁所,英民沒在廁所,廁所牆上搭著一架木梯,木梯下掉著英民的一隻布鞋。進來的人全都戴著孝,見英民逃跑了,就跳著蹦著罵,越罵氣越大,有人把小板凳踢飛了,小板凳偏巧砸在中堂桌上的插屏上。插屏的玻璃就裂成條,插屏裡裝著英民爹的照片,老漢的臉成了麻臉。英民說:「土匪打砸呀!」他們說:「誰是土匪,你家才是土匪!當老子的害了一輩子人,到兒子手裡了,還是害人?!」竟真的砸起來,把條櫃上的一個鹽罐抱起來摔了,鹽白花花灑了一地,把銅臉盆用腳踩,踩出一個坑。又要抱電視機,英民的娘身子撲在電視機上。夏雨喊了一聲,說:「誰也不能亂來!一亂來你們什麼也得不到了。咱都是來解決問題的,他李英民跑了,跑了和尚跑不了廟,還有清風街村委會哩,村委會解決不了還有鄉政府,咱找政府麼!」他們說:「你是誰?」夏雨說:「我是夏天智的兒子夏雨,白路是我的親戚!」他們就不鬧了。 夏雨鎮住了西山灣的來人,等到他們一窩蜂又去大清寺找君亭了,夏雨也出了門,碰著三踅。三踅說:「夏雨夏雨,你有四叔的派頭哩,哥佩服你!」夏雨走得很急,眼淚卻下來了。 整個下午,夏雨沒有說話,他收割完了白雪二哥家的豆稈,背回去攤晾在院裡,他也沒再問李英民到底是賠償了五千元還是一萬元,他一概不問。從白家出來,也是悶著,也是累著,他的腳步沉重,世上最沉的是什麼,他知道了,不是金子,也不是石頭,是腿。書正擔著兩桶泔水從鄉政府回來,老遠就說:「夏雨夏雨,給我發什麼紙煙呀?」夏雨說:「啥紙煙都沒有,你要是癮犯了,我給你卷個樹葉子!」書正說:「你咋和你三伯一樣了?來,哥給你發一根。」從耳朵後取下一根紙煙給夏雨。夏雨看了看,是「紅中華」,說:「你不是向我要紙煙,你是要成心給我顯派麼!」書正說:「這一根紙煙抵一袋子麥價哩,我能吸得起?今日縣上來了領導,領導說我做的飯香,給了我一根。兄弟,哥是夥?,沒啥光彩的,要說這工作好,好在離國家政策近,能常見到領導,你瞧,領導吃什麼,我就能吃什麼,我家的豬也能吃什麼,這泔水裡一半是剩飯剩菜!」夏雨說:「家裡現在還有幾頭豬?」書正說:「一頭母豬,十二個豬娃。你去看不看?」夏雨竟然就跟著書正走。 書正家和武林家原是五間老瓦房,一個大院子。十年前,書正掏了錢分住了一半,堂屋和院子就一分為二,中間磚蓋壘了界牆。書正家沒有什麼像樣的家具,什麼東西都就地擺,裝菜的竹筐子、爛網套,和麵鋁盆,臭鞋破襪子,亂七八糟攪在一起。那只母豬並沒有關在圈裡,領著十二個小豬,哼哼唧唧在院子裡用黃瓜嘴拱地,然後一個進屋去,都進了屋去,擠到炕洞前的麥草窩裡。夏雨才站了一會兒,覺得褲子裡有什麼東西在跑,把褲管綰了綰,蹦出兩隻虼蚤。書正說:「虼蚤咬你啦?你到底肉細,一來虼蚤就咬上了!」取了一包「六六六」藥粉要給夏雨的褲子裡撒。夏雨不要,他解開懷給自己灑了些,說:「你看這些豬娃咋樣?」夏雨說:「肥麼。」書正說:「你看它們是啥?」夏雨說:「豬娃麼。」書正說:「我看是一疙瘩一疙瘩的錢在跑哩!」抓住了一隻,提著後腿,要夏雨掂分量,夏雨不掂,隔壁屋裡有了什麼動靜。書正喊:「武林,武林!」不見有回應。書正說:「明明聽著有響動,咋沒人呢?」又喊,「武林,武林,你耳朵塞狗毛啦?」夏雨說:「人沒在你喊啥呀。武林日子惶,今夏看上去老多了。」書正說:「人有可憐處又有可恨處,瓷腳笨手麼,這幾天我讓他幫我在312國道邊挖個廁所坑,說好坑挖好給他二十元,你猜他挖了幾天?三天了還沒挖好!昨日我給黑娥說了,黑娥罵了他半夜。」書正在一隻大柳條筐裡撮糠,撮出一大盆,將桶裡的泔水倒進去,果然泔水裡米呀面呀菜頭肉片的都有,老母豬就先過來吧唧吧唧了一陣。書正也從櫃上拿了一塊饃,還拿了根青辣子,一邊往青辣子上撒鹽末,一邊說:「豬一動嘴,我就口也寡了!你吃不?」夏雨搖搖手,書正就一口辣子一口饃,嘴咂吧得比豬還響。又說:「你聽戲呀不?」從堂屋取了收音機,一擰開關,正好裡面播了秦腔,唱了大花臉。夏雨一時感覺那唱者在滿臉漲紅,脖子上的青筋暴起,而大嘴叫喊出的聲音和唾沫星子似乎都要從收音機裡潑出來了。夏雨說:「你快把它關了,你要人命呀?!」書正說:「你不愛聽?我跟著四叔學哩,你不愛聽?」夏雨一時無聊,起身要走,書正突然說:「你聽見什麼了?」夏雨說:「唱得像吵架!」書正說:「你坐坐。」自己進了屋,一會兒又出來,給夏雨招手。夏雨莫名其妙,走過去後,書正又讓他爬上靠在隔牆上的梯子,夏雨是看見了隔牆那邊的炕上,黑娥光著身子趴著,慶玉像個狗在後邊做動作,兩人都像從水中撈出來一樣,但勁頭不減,黑娥還時不時回過頭來,嘴裡咬著枕巾。夏雨趕忙從梯子上下來,小聲罵道:「啥事麼叫我看哩?!」書正說:「我只說你沒見過……」夏雨噓了一聲:「小聲點。」書正說:「我讓他們喊起來你聽!」就把收音機聲放大,滿屋子都是嗡嗡聲,約摸兩分鐘,猛地一關,秦腔沒有了,隔壁屋裡傳來噢噢的淫聲,叫過三下也停止了。 清風街的人偷什麼的都有,有偷別人家的莊稼,偷蘿蔔,偷雞,偷拿了大清寺院牆頭上的長瓦,但偷人家女人的事,夏雨第一回看到了,從此反感了慶玉,更可憐了武林。那是個黃昏,我和武林正站在大清寺院子裡,看君亭處理李英民賠償的糾紛。大清寺的人很多,一是來看咋處理,二是防備著西山灣的人若要再撒野,我們好給君亭壯勢。武林呆了一會兒,說他頭暈要回去,我不讓他走,我就看見他臉上發綠,頭髮突然地全了起來,像個栗子色,也像個刺蝟。他那樣子非常可怕,西山灣的來人也看見了,互相示眼色,他們的口氣就軟了,終於同意給賠償費再加一千,五千加一千,六千。 解決了糾紛,白雪的二哥就連夜派人去伏牛梁上掘墓,這勞力活自然還是少不了武林。上善讓我也去,我說:「人家讓不讓我去?」因為白雪的二哥恨過我,也踢過我一腳。上善說:「你該去,給你個立功贖罪的機會。」我們整整忙了一夜,天亮時把墓全部拱好。但是就在這一天,清風街氾濫了地虱婆。地虱婆你肯定知道,小小的蟲子,有翅膀能飛,卻飛不遠,以前在夏季裡能見到。而這天早晨不知怎麼就滿空中飛,像下雨一樣,從樹上,房頂上叭叭地往下掉。到了飯辰,地虱婆更多,家家屋裡屋外,地裡,打麥場,牆根,灶台,甚至水裡都能看到一堆堆地在蠕動,到處一股腥味。人都說這是咋啦,是白路那三個死鬼作祟?你三個死鬼算什麼呀,償命錢已經給了你爹你娘,還陰魂不散嗎?!供銷社的張順把所有的農藥粉都賣光了,地虱婆還殺不死,全部的雞放出來吃,吃撐了臥在地上,雞身上的地虱婆爬的還是一層。我原本要回家美美睡一覺的,但家裡的地虱婆太多,睡不成,只好到地裡去幹活。地裡全是人,收割豆稈和穀子。白家就把白路埋了,去送葬的人不多,放了一串鞭炮,隆了個不大的土堆。說來也怪,白路的娘在墓堆上哭得人拉不起來,就刮了一陣風,地虱婆竟然全隨著風起飛,遮天蔽日的一片黑雲在清風街上空兜了三個來回,就朝西消逝了。 白路畢竟是白路,他如果不牽涉賠償的糾紛,死了也就死了,村人會說「白路死了」,或者再說,「娃可惜,花骨朵沒開哩」。有了賠償的糾紛,清風街折騰了一下,他一入土為安,清風街也安靜了。太陽還是那麼紅,繼續曬得包穀黃,稻子也黃。白雪的二哥買了一把大錘,和三個人去了州城為人家拆一座舊樓打工走了,只有白雪的娘還在病著,白雪就從巡迴演出的鄉鎮回了清風街,而且帶回了夏天智的那些臉譜馬勺。 馬勺缺了七個,不知道夏天智是如何接受了的,反正他沒有尋過我的事。而白雪在西街陪伴她娘,每天我總能見到她的身影,我高興地笑,看見誰就給誰笑。陳亮瞧著我給他笑,忙著擦自己的臉,這快結巴以為他臉上有了鍋灰,說:「你你笑你娘娘的×,×哩!」我還是笑,又唱唱歌歌著往市場上去。我唱的是秦腔的《十三鉸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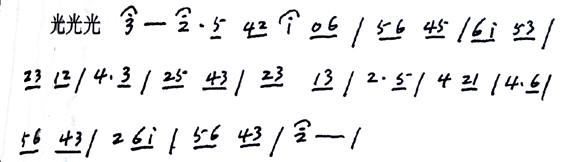 |
|
|
| 學達書庫(xuoda.com) |
| 上一頁 回目錄 回首頁 下一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