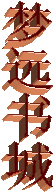
高曉聲文集 老清阿叔
一
老天爺的面孔還極模糊,長伯伯就起來了。起來了不幹事,開了大門坐在門檻上,撫著膝頭吸旱煙。片刻吸完,邊站起來邊把煙杯插在褲腰頭,然後跨下階沿石,就近站定,仰起頭呆呆看著遠方,好像在想什麼。其實什麼也不想,他那眼光是散神的,一看便知道他沒有心事。不過這時候他的樣子顯得特別高,村子上的人不知為什麼把高說成長,都叫他長伯伯。只有我不。他是我爸爸的親弟弟,應該叫他叔叔,叫伯伯就叫亂了。但是叫叔叔他往往不答應,以為是叫的別人,所以我只好連著他的名字叫,叫他老清阿叔。那時候我年紀小,以為老清就是他的名字。其實錯了,他的大名是清泉,因為排行最小,才照「老來子」的慣例,在名字上冠個老字,叫他老清。這「老」其實就是「更小」的意思,常州人把孩子稱「老小」,很有小看對方的味道。所以,老清這名字,只該讓他父輩或同輩叫,不該讓我小輩叫,然而我卻一直如此叫他。我們都不懂這規矩,不以為悖。奇怪的是旁人也從不曾糾正我,連做老師的爸爸也如此。這大概是因為我的老清阿叔,眾人都沒把他當大人看,雖然他的女兒還比我大一歲。
總之,老清阿叔是村子上起身最早的一個,可是他並不多做事,一定要等到別人做了他才做,別人叫他做他才做。否則他一向不知道該做什麼,也想不到該做什麼。這還是生活在舊社會,並非是吃了生產隊的大鍋飯才養成的惰性。從小他有一對能幹的父母和兩個能幹的哥哥,四根柱子頂天立地,別說小小一個家,就是一個村,一個鄉,他們的肩膀也都扛得起。帝王將相,寧有種乎?中國歷史上,從農家走出來的顯赫人物就有的是。老清的兩個哥哥,一個從種田開始逐步開糧行、油坊發了財。一個先當老師、後來在縣裡邊做了科長,都能幹得很嘛!所以,老清或老清之流就命裡註定了只能當小夥計,絕輪不到他當家,當家人叫他做什麼就做什麼,不叫他做什麼就不知道做什麼,即使想到要做什麼也不知道該不該去做——還是不做也罷。反正鍋裡有,碗裡也會有,吃現成飯省得多操心。如此看來,吃大鍋飯思想也不是農業學大寨學出來的,倒是大寨的大鍋飯思想是從老清阿叔那兒學得去的。不過老清阿叔當然不知道後來的事。他在大家庭裡當小夥計,家事不作主,可也有無需當家人作主的事可以做,比如捕魚、捉蟹、釣黃鱔、摸鳥窩、追兔子、鬥蟋蟀、做弓鍘黃鼠狼、架鋼絲圈扣野雞……他就把過剩的精力,消耗在這些上面。捉著了大家吃,提不著也不計較合算不合算。有時玩出了神,丟了應該幹的正經活,給罵一頓甚至打幾拳,也不在乎。不過這都是小孩子幹的事,小孩子當正經事幹都不要緊,可老清阿叔長大了還這麼幹。兄弟們分立了門戶,他當了家,娶了老婆,生了孩子,孩子長成十多歲了還這麼幹,當正經事兒幹,就脫髒了。弄得田都種不熟,年年欠收。所以村上人都說他還是個孩子。背後有人譏笑他是暗敗子。而他始終不覺悟。也許就靠了這些,他倒保住了一顆童心。大人不喜歡,孩子可喜歡。他在幹那些玩意兒的時候,總有一群孩子跟在他屁股後頭。他同孩子相處極自然,不擺架子也不厭煩,充分自由平等。他並不靈活,而且捕、捉、釣、套、追、鍘……總難免有失誤,因此有的孩子竟怪他手腳不快,這時候他也會提高喉嚨反駁一聲:「你的本事(領)大?你倒來試試!」可也只是說說而已,並不真的罷了工要孩子的好看!我是最佩服他的,有一次親眼看到捉在簍子裡的一條大鯽魚跳落水裡去了,老清阿叔急忙縱身躍進水裡,居然手到擒拿,又捉了上來。簡直像關雲長斬顏良誅文醜,酒尚未冷,便提了人頭去也。
我父親跟他很不一樣,架子大,愛教訓人,把我教訓得離他遠遠的,更加覺得阿叔的好處。只要他有空,我就像尾巴一樣跟著他。他玩什麼我也玩什麼。玩得忘了吃飯,父親也不便說什麼,因為是他弟弟帶著我呀,他能說弟弟帶壞了我嗎!況且他也難得在家,對我知之甚少。凡涉及我和老清阿叔的事,我母親也不向他告狀,因為家中有許多事情,都還得靠老清阿叔幫忙呢。我母親是從鎮上嫁過來的,不大懂農活,連裝一把鐮刀或鋤頭柄,菜畦整好了下種籽,她都要對我說:「去叫阿叔來幫忙。」可見阿叔對我家是不可或缺的。況且真正到了關鍵時刻,他也會背叛我而維護我父母的利益。例如有一年春節以後,快開學了,我父親在晚餐時丟給我五角錢說:「把賭帳還掉,明天不許出門了,在家溫課!」這話並沒說錯,他知道我春節裡賭博(那時候是極普遍的現象,因為是舊社會嘛),怕我輸了錢拖了債讀書不安心,願意替我還,用心良苦。可是他那種施捨的態度卻傷害了我;再說我也沒有輸錢,無債一身輕。心氣完全硬得起來。當下便把錢一推,說:「不要,我不欠別人的。」這一來。我也把父親激怒了,他伸手就狠狠打了我一耳光。待第二記打上來,我已像兔子般溜了。溜了自然就要堅持不回去,嚇一嚇父親,讓他以後收斂點,莫隨便打人。父親果然急了,又不好意思來找,於是又用上了老清阿叔。老清阿叔當然很容易找到我,叫我跟他回去。我不依。他居然企圖強迫。我一看不妙,拔腳就逃。他就追,我們在昏暗的麥苗地裡賽跑,大約跑了二千米,還是我得了金牌,他空手回去了。我卻不敢再上村去,無可奈何,就在墳圈裡躺下來睡覺。一睡就熟了。也不知過了多久,忽然電光閃閃,雷聲隆隆,快要下雨了。這下子我再無辦法,只得往村上跑,想找哪家屋簷下躲一躲。誰知剛到村頭,猛不防上牆邊頭竄出一個人來,一言不發,把我攔腰一抱就走。嚇得我大叫一聲,隨即馬上知道了,這是老清阿叔;因為他身上的氣息塞進我的鼻孔來了。
他把我挾持回去後,當夜我被父親撳在床上狠狠打了一頓屁股。恨得我長久不理老清阿叔。但從此以後,我的長跑倒出了名。人家取笑老清阿叔說:「長伯伯,你的腳生得那麼長,連個小孩子都追不著,算什麼?」老清阿叔就提高喉嚨反駁道:
「你也去追追試試看!腳長有什麼用!他溜得比兔子還快,像野雞一樣埋著頭朝前直攻……你倒說得容易呢!」
老清阿叔可以算做我童年時代最有影響的伴侶之一。我有許多愛好,就是受了他的薰陶。比如捕魚吧,後來簡直成了我的癖好。五十歲離開農村以前,凡碰到有捕魚的機會,不管寒冬臘月,我都甘願赤腳上河去捉,不是為了嘴饞,主要是想過一過捕魚的清頭。很小的時侯,我就背著魚簍跟著老清阿叔轉,不久就玩起力所能及的各種漁具來,終至於十八般武藝件件精通。有一次幾十個人在一條長河裡捕魚,老清阿叔用網趕,我用漁罩。老清阿叔眼尖,看見長河另一頭有條大魚尾巴出水扇了一下,便招呼我跟他跑過去。到了那裡,我第二次下罩,便激動地大喊:「老清阿叔,在裡面了!」我的意思當然是「魚被我罩在裡面了」。當時卻有人描了一句:
「老清阿叔在裡面了」,弄得許多人笑話我。這樣興奮的事情,不知有過多少次。然而捉到了魚也並不都有好結果,就拿那一次說吧,我記得回家以後,失業在家(當時已淪陷了)的父親毫無興趣地說:「捉什麼魚呢,沒有一滴油,怎麼燒?白起勁!」母親心軟,見我氣得要哭,連忙說:「送到外公家去吧,外公愛吃。」我就拎著魚跑到鎮上外公家。外公看了很高興,但是搖搖頭說:「今天六月十九,觀音菩薩生日,不吃葷腥的。天氣這麼熱,這魚又留不到明天吃,怎麼辦呢?」大家眼睜睜看著這條魚,倒像平添了許多愁。我真的流出了眼淚,一串串的,這才使大舅舅的腦袋瓜像上了點油一般活絡起來,他說:「去送給街北的楊先生吧!」楊先生是外公的老朋友,外公馬上說:「對,楊先生是基督教,不信觀音菩薩的。」於是大舅舅便送去。回來說:「楊先生收了,還說謝謝你家大外甥。」就這樣,一條大魚被基督教吃去了。
我十歲那年冬天,為了捉魚的事,還同老清阿叔大鬧了一場。有天晚上,我找他不見,聽嬸嬸說:「他會(同)了幾個人,到河對岸蒲溝裡扉水捉魚去了。」我聽了就動氣,他提魚為什麼不喊我同去呢?回去告訴母親,母親說:「回水要有一夜才能提魚呢,你明天早晨去看看吧。」我想這是個好主意h全沒想到人家辛辛苦苦商幹了水,我是不該去捉魚的。大概以為有老清阿叔在那裡,我就去得。第二天一大早我趕到那兒,隔著一條河看見他們還在回水,魚還沒有捉,來得正是時候。便喊阿叔擺渡。誰知喊來喊去,他全不理睬,只管庫水。我就哭,一面哭一面喊,一面喊一面吵,一直吵到我明白他不會來擺我了。於是氣極而罵。罵得心頭火起,全不顧天寒地凍,穿著棉襖棉褲就往河面一跳,狗爬式遊過去。遊到一半,褲襖裡全吃進了水,遊不動了。這時才見老清阿叔的船劃到河心,他大概是嚇壞了,臉白得脫色,一伸手便把我拎上了船。我仍罵不絕口,可是在水裡還好,一上船,西北風像尖刀,刺骨地冷,冷得馬上要凍住了。牙齒得得地打架,罵人的話也不連貫了。老清阿叔很快把我送到岸上臨時搭的草棚裡,剝了我的衣服把我獄在被窩裡,氣急地啞聲說了句:「不講理,沒見過你這種老小!」便出去回水了。我冷得沒收羅,一路抖下去收不住,用控制不住的嘴巴大罵了老清阿叔半天,究竟罵了什麼卻一點也記不得了。只是從此以後,老清阿叔捉魚再也不會忘了叫我。我的名氣也鬧大了(那時候還沒有冬泳這個運動項目,我是創世紀的),都知道我脾氣醜,不好惹。儘量同我拉開距離,敬鬼神而遠之。
二
孩子們跟在長伯伯的屁股後頭轉了幾年,隨著年齡逐漸增大,長伯伯在他們心中所占的地位就越來越微不足道。一旦成年,便覺得長伯伯忠厚,無用,可憐,可笑,反過來認為長伯伯是個小孩子,自己倒比他成熟得多了。好在孩子們長大了一批,又有一批小的來接班;所以長伯伯的日子過得依舊還熱鬧。不過這一批批來了又去的孩子全都一個樣,到頭來很少不叛離長伯伯的。長伯伯全然沒有覺察這一點,不是氣度大,不是有修養,而是他從來沒有想到一個人活在世上還要同別人去比什麼長短。儘管村上的人無不有意無意同他比長短,他卻連「這究竟是為什麼」也從不曾想一想。
我也從沒有想到要拿老清阿叔去同別人比,荒唐的是,突然之間跳出來一個不相干的人,竟拿我和老清阿叔比上了。
那時我還只十一歲,是日本鬼子侵入家鄉的第三年。大概是秋季吧,有一天下午,老清阿叔要我幫他划船一起把肉豬運到鎮上去賣。那時候都是私商開的肉鋪子,老清阿叔的肉豬就賣給他認識的一位肉鋪老闆。老闆買下了,付錢給老清阿叔,叫他當面點清,免得差錯。那也不過很薄一疊鈔票,多少我也記不得了,按照當時斗米三斤(肉)的例價,就算一百五十斤豬,殺得九十來斤肉,最多也不過三石米的價錢。可是老清阿叔接過了那筆錢,錢就在他的手上活起來,要翻翻不動,不翻它亂動。老清阿叔的手很大,繭很厚,勁很足,幾百斤重的石碌碡,他翻得輕飄飄;七斤重的大鐵囗,一天鋤到夜;握刀殺得雞羊,提叉叉得魚鼇,空手捉得雉雞,兩指撚得蛇尾……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手這樣窩囊,拿了票子就發抖了,抖得那麼厲害,再也數不清究竟是多少錢。我本來不想驚動他,讓他心定下來慢慢數就是了,總能數清的嘛!可是,我看見那老闆翻著白眼,一臉瞧不起人的樣子,實在忍不住了。於是我就說:「老清阿叔,讓我來幫你數。」老清阿叔把錢給了我,我很快就數清了。「不錯。」我對他說,「我們走吧!」
我們已經轉身前鋪子外面走去,想不到就在這時候那老闆取笑老清阿叔說: 「你還不如你侄兒!」
這句話使我終生難忘,它把我們叔侄兩顆心全都刺傷。從此以後,我們彼此的看法都和以前不一樣了,或無心,或有意,身不由己。
不久以後,老清阿叔夫妻又吵架了。這種吵架是常常發生的,吵架的理由也極其簡單,或是因為沒有錢買油鹽肥皂了,或是水缸幹了沒有及時挑,或是孩子被人欺了不曾幫,或者是燒好了飯等他回來吃他卻在外玩得忘記了,或者是被三朋四友拉去賭博,或者上街多用了幾個錢,或者什麼都不為,光想著他不及別的男人精明能幹就有氣,就忍不住埋怨,嘮叨……從這些可以看出我那嬸嬸是個極平庸的人,沒有知識,心胸狹窄,卻又總不知足。這種女人原沒有自立的能耐,出嫁了就要靠丈夫過日子,只要丈夫當得有校有角,她就服服帖帖,夫唱婦隨,做個奴隸。她嫁過來頭兩年,原也不識得老清阿叔的脾性,看他人高高的,力氣大大的,脾氣好好的,同孩子們玩得歡歡喜喜的,跟他過日子倒也滿滿意意的。後來出於一些好心人的告誡,大概也包括我母親在內,私下裡要她多看著點兒丈夫,因為他是個沒有心計的人。總說「吃勿窮,著勿窮,沒有計算一世窮。」「不識字還有飯吃,不識人就要餓肚皮了。」所以,做了他的妻子,如果不多幫他盤一點心思,就會出大大小小的糸漏,不得太平。除此以外,嬸嬸自然也聽到一些風風雨雨的背後談論,也嘗到了丈夫對於家庭漫不經心的味道,特別是頭胎女兒生下來,老清阿叔趁她坐月子,被三朋四友拉去賭輸了兩百米錢,傷透了她的心,確認這家庭的重擔不能讓他挑下去。看他種地不像種地,玩耍不像玩耍,成人不像成人,孩子不像孩子,過日子隨隨便便,衣服髒了不曉得脫下來洗,破了不補也無所謂,沒有葷菜吃素菜,沒有素菜醬油湯,沒有醬油鹽花湯……捉了魚蝦野味回來,大人小孩子一大群呼嘯而來,你一筷他一筷,嘻嘻哈哈一掃光……她如果不挺身出來當家,如何得了。這莊嚴的使命,便歷史地落在了她的肩上。然而她既非能征慣戰的將軍,也不是運籌帷幄的謀臣,所以,她那莊嚴的歷史任務也是命定不能完成的。她的唯一基本家策,就是管住丈夫。要管住丈夫,第一就要抓財政大權。這也罷了,反正老清阿叔全不在乎。比如賣了肉豬,絕對百分之百內交。如果肉鋪老闆不叫他數一數,他絕對不數。他輸掉過兩擔米錢,那是賭場裡的朋友借給他的,然而當時每擔米價多少?他不知道,朋友給了他多少錢,他也沒有數,所以老婆願意管財政,他還求之不得呢。可是我嬸嬸管的是死錢,她決無辦法把一個錢變成一個半或者兩個,她絕無開源的能耐,只有節約的美德。說穿了也無非是讓全家過得更苦一點就是了。即使這樣,她還怕丈夫不甘心,會陰謀篡奪她的領導權。比如錢由她管轄以後,丈夫要用自然得朝她伸手,她就看作是危險的信號,圖謀復辟的新動向,絕不願滿足他的要求,總是千方百計把他擋回去。實在擋不回去的時候,起碼也要打個七折八扣才給……她出於婦女具有的那種傳統自卑心理,不自覺地去打擊丈夫的尊嚴來提高和維持她的地位。因此她常常為一些很小的事情同丈夫吵架,儘管老清阿叔不會鬥嘴,難得同她糾纏,她卻總要大吵大鬧,以為不同她拌嘴也是看不起她,而老清阿叔有什麼本事敢看不起她呢?神氣些什麼呢?不就是個成不了大人的孩子嗎!不就是個種不熟田禾的懶漢嗎!不就是個家都當不了的暗敗子嗎!……這些話,別人只是背後暗底裡說說,到了她嘴裡就像戲一樣唱出來了。老清阿叔在眾人眼裡本來位置不高,但總還是個堂堂男子漢,如今被老婆說得一無是處。過去背後的議論都被經驗過的老婆證實,當然是毫無疑問的了,於是刻薄的人便又用他老婆說出的話當面取笑老清阿叔,沒有什麼顧忌了。尤其難堪的是,老清阿叔賣了肉豬,或者新穀登場糶了些穀(儘管不夠吃,總得某一點,才有得零用),捉了魚蝦賣出了……別人知道他有了錢,手頭緊的人往往來開口借幾個,這也是人情之常,總有往來的,老清阿叔當然答應。但這時候錢已經到了我嬸嬸袋裡,老清阿叔得向她討出來。她的逆反心理作怪,十九不肯,硬叫老清阿叔丟失信用。而借錢的人,看出老清阿叔無能,乾脆跳過他,直接找我嬸嬸商量。她偏又慷慨得很,總肯借給。她信得過別人,獨獨信不過自己的丈夫。真算是把老清阿叔的臉皮都剝了。於是他有時突然也狂怒起來,便砸鍋摔碗,卻從不打人,這樣可以嚇得嬸嬸暫時閉上嘴。到了明天,老清阿叔便仟悔地悄悄從鎮上把鍋碗再買回來。這更給人家瞧不起,說現成話諷刺他道:「準備買,還砸什麼呢?不是白砸了嗎?何必把鈔票丟到江水裡去呢!」
那時候我還是孩子,全不曾想到這些,有許多情形也不知道(比如借錢的事)。我只是出於本能,總是站在老清阿叔的一邊。我從不曾覺得他窩囊,倒反像英雄一樣崇拜他。他有那麼多能耐,我全學會了就好了。我從不聽人們的那些誣衊之詞,他們憑什麼呢?誰能夠像他那樣幹出許多使孩子們神魂顛倒的業績來?我也極欣賞他對嬸嬸的寬容態度。他肚量大,好男不與女鬥,要不然,只一拳頭不就把嬸嬸的嘴巴打癟了嗎!可是從那次賣豬以後,我的看法就變了,覺得老清阿叔老實得可憐。這一次,同樣是看到嬸嬸罵他,全不以為他大度,確認被可憐地欺負了。
就在下一年冬天,嬸嬸又生下了第五個孩子,坐月子的時候,老清阿叔竟被人勾搭去賭場,一夜天輸掉了一畝田。
那是落下了紙筆的。
嬸嬸曉得後,吵得烏天黑地,鬼哭神號。但木已成舟,無可挽回了。
老清阿叔一聲不吭,變傻了。有一次我背著草籃別草,經過他輸掉的那塊土地,看見他佝僂著背,低頭坐在麥田一角,一動不動。我有點害怕,悄悄地走近去看,才知道他在哭,一點聲音都沒有,那眼淚卻像潮水般湧出來,把一片麥苗都濕潤了。我年經雖小,也有過幾年農事的經歷,也曾幫著老清阿叔在這塊地裡勞動過多次,這裡的每一粒泥土我都撥弄、撫摸過,每一寸土地都有我的手印足跡,都浸潤過我的汗珠。它是我的寶貝,也是我的命根啊!我的心頭湧起一股酸楚,跟著老清阿叔大哭起來。
我和老清阿叔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場。我的情緒越哭越複雜,想起了許多大人們的事情,那麼窩囊,那麼尷尬,那麼殘忍。說有理人人有理,說無情個個無情。善善惡惡,不可開交;模模糊糊,難辨形影。我還來不及去想我自己,我只為他們傷心。我是為前輩而哭。而在這裡面,我當已感到了人世的悲涼。
三
淪陷區混亂、緊張、痛苦的生活促使孩子們普遍早熟,走馬燈似的一批批漸漸同老清阿叔疏遠淡漠。我十一歲那年,夏天和老清阿叔一起在村外靜靜的蘆塘邊頭布網攔魚,偶然踩到了一個軟綿綿的泛起血色污水的麻袋。這就像火山口突然冒出了滾滾的濃煙,把我純淨如春天的心地抹黑了一大片。從那以後,稚嫩的軀殼裡跳著的已經不是潔淨的童心了。十三歲,我母親不幸死去,父親又在後方抗日,家中丟下我們四個孩子在一起過日子,既忙於爭吵,又忙於照顧。我再讀一年初中就畢業了,千方百計也得想辦法借錢去把它讀完。我肩挑的擔子、思考的內容把我一下子送進了青年時代。我已經不能再像過去那樣同老清阿叔親密相處。紛繁複雜的世事向我的腦袋瓜子衝擊過來,得寸進尺,蠶食和侵佔地盤,一步步企圖把老清阿叔排除出去……我再不能像過去那樣常常想到他了。虧得我的學校是在農村裡,在學校周圍,還常常能夠碰到提問、垂釣、把叉、架弓、設圈套之輩,便能聯想到老清阿叔,聯想到自己童年生活的情趣,心裡便覺著溫暖香甜的滋味。我知道老清阿叔很苦。我又何嘗好呢,母親死下來,也是賣脫一畝水田才買得棺材人殮的。升人初三讀書,我走親訪友跑酸了腿也沒借到錢(誰有錢存著呢,都窮啊),結果只得強行入學,學費掛欠。我不知道自己的出路在哪裡,也不知道因何而苦,甚至不知道究竟什麼才算真真的苦。也根本沒有見過奢華的生活。周圍雖然有比我好過的,但又何嘗沒有比我更苦的呢。比上不足,比下有餘,能忍自安,知足常樂,好像人生無非就這樣自然而然地過下去而已。祖祖輩輩不就這樣過來的嗎。我實在還不懂什麼,能想的東西太少而且想得很幼稚。我天賦平庸,所以想到老清阿叔,也只是浮光掠影,一晃而過,並沒有多少感情的波動。
從初中到高中,一直到進入大學,我離開農村去到小城又進入大都市,雖然各方面同老清阿叔的距離越來越大,但是回想起童年的生活,老清阿叔的形象是那麼突出,明顯地超過了我的父親。
我已經只有暑、寒假才能夠回到家鄉去了,後來父親和後母搬到小城裡住,有時我暑、寒假也不一定全在鄉下過。有時在回去之前,先寫了信給姐姐;告訴了行期,到那一天乘船到了鎮上上岸,到碼頭來接我的總是老清阿叔。他穿得很破舊,冬天也裸著頭,臉總是習慣地朝天仰著,手裡提著一根扁擔,過分正經地大聲喊著我的名字。等我聽見了,看到了,跟他打了招呼,他才高興地嘻開嘴笑。然後不管我帶了多少行李,都上了他的扁擔,少了不說,若是多了,他就料事如神般說:
「我說要來接哪,你姐姐還說不要呢。你看,這麼多東西,怎麼叫你拿得動!」他顯然平時不大上街,偶爾碰到熟人,人家就問:「老清呀,怎麼上街來啦?」他就神氣地回答說:「喏,來接我家侄子的,他學堂裡回來!」那樣子,好像很光榮很滿足。
他的生活越來越艱難,蒼老得也快。整個農村已經破產了,不是他一家困難,有些原來笑他種不熟田禾的人,比他更糟,竟有許多人吸毒上了癮。不買肥料不買農藥,蟲害蔓延,大面積欠收。有一年老清阿叔一畝田只收了十二斤稻子,其餘盡是白莠。通常年景,老清阿叔的米回到麥收時就空了,奸商趁機放米賬,講定一石米換三石麥,到冬天討賬時,一石麥價已等於一石米,轉眼三四個月就被剝削了二倍去。老清阿叔年紀一年大一年,又身虧,做事不能像小夥子那樣有使不盡的力氣了。他原有個大兒子全生,只比我小一歲,原可以是他的好幫手,可是國民黨抽壯丁,地方上的鄉長、保長,固然看我父親的面子,不會抽他去,他的壯丁捐是照例要繳的,一年沒有二石米過不去。他哪裡交得起?只得央我父親介紹全生去城裡學生意,省得在家得眼。這樣,壯了捐不交了,家裡也損失了一個勞動力。學徒沒有薪水,除吃飯外,老闆只給些零用錢剃頭洗澡,家裡得不到一點補貼。
儘管這樣,我每次回家,老清阿叔總還要請我吃一頓飯。有時候沒有米了(比如暑假),燒不出飯來,捉到了魚、「蝦、黃鱔。青蛙就送到我家讓姐姐燒給我吃。不讓親侄兒吃一點他的東西,就會內疚得不能自安。
我記不起是否曾經有過一次(哪管一次吧)對老清阿叔的款待做過回報。我仔細搜索過我心臟的每一隻角落,每一條縫隙,沒有任何「受之有愧」的記憶儲存,我居然認為理所當然,因為我當時還是一個沒有收入的消費者,我可以視而不見地在窮得沒有衣服穿的親人身上剝下一層皮來。生活中許多先例早就向我做了示範,只不過我自己沒有意識到這種影響並且自己也跟著幹出來罷了。
悠久的歷史形成的心態和習慣,使自私的人能夠在社會上不知羞恥地活得坦坦蕩蕩。等到覺悟,人已物化,我也老了,悔之晚矣。
大學沒有讀畢業,我隨大流參加了革命。革命到了勝利的時候參加進去,也像我對老清阿叔的態度,那樣覺悟得過遲了。況且我又有一個國民黨員和科級幹部的父親,我的行動從壞處想,輕則是投機,重則是混進來別有陰謀。當時革命形勢發展如萬馬奔騰,一下子需要千千萬萬個工作人員,不可靠的人利用一陣也無不可,縱有陰謀也盡可讓它暴露出來了再說。要證實自己的忠誠自然並不靠語言,我參加了工作之後再也沒有回過家鄉,每次填寫表格,填到社會關係一欄,我便想到了老清阿叔,我就感到輕鬆,因為他在政治上是一清二白的。正為了這個緣故,我從來沒有把他填上表格。然而每一次填表,我總算又想念了一次我的老清阿敘了。有一次機關裡需要增加一名炊事員,找不到人,我還曾想把他介紹來。竟不曾成功。原來他已五十出頭,哪裡還肯背井離鄉啊!金窩銀窩,不及家裡草窩,外邊千好萬好,不及全家團在一起好。他不但自己不肯出來,就連解放前在城裡當學徒的兒子全生,在土改中也回到農村分了土地。五二年春天,全生還趕到省城來找過我,已經完全是個壯實的小夥子了,性格同老清河叔一樣憨厚。他來找我的原因,只是為了要買一本農村劇團的演唱材料,這種材料各地新華書店都有供應,全不用找我。可是全生有全生的理由,他像天真的孩子一樣對我說:「我要你幫我揀一本最好的。」可見他對我何等的信任。誰知到了五三年春天,我剛從農村蹲點回來不久,有一天傳達室傳呼有人找我,我走去一看,竟是老清阿叔。他一身舊黑布裝,面目黧黑,不僅過分地蒼老,而且像經受過一場大災難弄得枯敗了。他見了我,只說了一個「全……」
字,眼淚便籟籟落下來,泣不成聲。
原來這一年中,家裡起了大變故。春天裡我嬸嬸患了重病,看病吃藥,拖了一屁股債,當時雖然參加了互助組,也並不像宣傳的那樣就搭上了社會主義的大船,經得起風浪顛簸。他們少做了工分,全年收支差了一大截,再無來處。他們不曾抱慣債,又沒有把公家的東畫當成自己的那種主人翁氣魄,心理上受不住債務的壓力,急著要賺錢來還。那時候村上還有一爿私人開的小車油坊,兩爿豆腐店。依靠政府定量供應的一點大豆,開工不足。他們貪心重,嫌供應太少,站在資產階級的立場上,進行反限制的鬥爭。當地產豆量有限,農民私下裡拿出來做交易的不多。於是油坊、豆腐坊老闆就唆使一些缺錢用的農民做私販子。全生中了糖衣炮彈,也去幹那勾當,憑一副肩膀,兩隻腳板,花整夜工夫,來回走五十幾裡地販一挑大豆,賺得三、二塊錢。出了絕力,還擔心驚。倘在路上被檢查的幹部捉住,就會連本搭利一起充公。所以大路不走走田埂,田埂不走踩查壟,不知要多花幾倍力氣。全生就因為有一夜挑著一百五十斤的擔子逃檢查,逃脫了力,回來就病倒了。偏偏請來了一個中醫學不好,趕時髦改學了幾天西醫的全能大夫,誇口西法治病好得快。三言兩語,便拿出家什來替全生掛鹽水。掛到一半,全生就發抖了。全能大夫說:「不要緊,有點反應是正常的。」後來抖得手臂都快把針頭摔出去了,全能大夫還硬捺住了他把鹽水掛完。等到針頭拔出,全生竟從床上竄起來,跳了幾跳,幾分鐘就死了。是什麼原因,也查不出來。許多人慫恿他去控告醫生,他想想,他雖然不敢高攀把醫生當朋友,總也是見了面就打招呼的熟人。他們之間,無冤無仇,更無財產糾葛。他老清有幾畝薄田已進了互助組,幾間破屋全不起眼,整個家產抵不上醫生一個腳趾頭,誰都不相信這是謀財害命,那還費神去追究什麼呢?誰能沒有失誤?木匠會截短一根料,瓦匠會砌斜一堵牆,農民會插歪一席秧,誰叫醫生面對的是人的性命呢?我老清阿叔歎了一口氣,認了命。他想死的已經死了,再無辦法叫他活轉來,而活著的還在要死,還有什麼閒工夫去計較沒有意思的事情呢!我嬸嬸的病剛有點好轉,哪裡再經受得住這麼大的打擊,病情複又加劇,不幾天便又歸天了。老清阿叔連續死了兩個親人,一句話沒有,只是哭。後來不哭了,一天到夜發傻,給他吃就吃,不給就忘記了。他那比我大一歲的女兒已經出嫁,回來陪了他一陣,也沒法解他的悶。剛巧婆家村上有人到省城來走親戚,便勸老清阿叔跟著來找我散散心,老清阿叔倒肯,所以就來了。
聽了老清阿叔斷斷續續的訴說,除了微微點頭表示我在認真聽著之外,我竟找不到一句合適的話來表達我的情緒。在老清阿叔談到全生挑著重擔拚命逃避檢查的時候,我非常激動,因為就在那個階段,我剛巧在農村裡工作,也常常帶著幾個鄉里的工作人員在離家千裡外的一處村道口巡夜,查偵私販糧食的「宵小之徒」。
這種莫名其妙的巧合,把原不相干、毫無牽連的兩件事聯在一起,像口同一樣罩住了我的思緒,留下了永生難忘的記憶。
四
一晃又過了幾年。我再次同老清阿叔見面時,已到了一九五八年的冬天。那時候,反右派運動已經取得了偉大的勝利,猖狂地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都早已有了應得的下場。我在這場鬥爭中雖然不能算是積極分子,但也是堅決跟著黨走的,我的言論和行動無可指責。就是交心也交不出什麼東西來,我是表裡一致的人。沒有見不得陽光的東西。我堅信只要跟著黨走,聽黨的話,照黨的意見辦事,就不會犯錯誤。這是五十年代革命青年最基本的政治品質,它絕對是正確的。過了三十年,到了現在的八十年代,我也相信這種觀點是完全正確的。在八十年代裡,我常常碰到一批年紀比我略大或相差無幾的領導幹部,他們就這樣教育他們的子女和接班人。他們以現身說法,指出他們幾十年來所以一直工作順利不犯錯誤,始終正確,唯一的原因就是堅決照黨的意見辦事。其實他們是過分謙虛了,如果說得到家一些,還應該補上一句「即使黨犯了一些錯誤他都也還是正確的」。共產黨並沒有說自己永遠正確,以為永遠正確自信的倒是這些人。反右鬥爭擴大化了,而他則聲稱「我並沒有搞擴大化」……唉,不多說了,家醜不可外揚,留點餘地吧。其實我說這些,完全不是譴責別人,而是檢討自己。因為按照我的設想,原也應該成為他們那種人的,問題在於我的設想沒有實現。在社會主義這個重要關口前面,右派被擋住了,反右鬥爭中表現不壞的我也被擋住了。我被擋住的原因經說明是「不適宜在上層建築工作」,但究竟為什麼不適宜卻並未進一步指出來。這也可以算作朦朧派的傑作,可以使當事人更加耐想一些,不至於像主題鮮明的小說那樣淺薄也。上層建築既然不讓我待,我自然聽黨的話到基層裡去。基層很好,勞動光榮嘛!工資沒有就沒有吧,好在年紀還輕,身體也還硬朗,總還可以為黨和人民做些事情的。
決定了榮歸的日期,我不得不先寫封信回去,因為這不是回鄉作客,而是遷去落戶,雖然作為無產階級,並沒有多少行李,但兩箱書的份量卻是沉甸甸的。
到鎮上碼頭來迎接我的,仍舊是老清阿叔。
班船還沒有靠岸,我就看見他站在碼頭高處了,他還像從前一樣,提根扁擔,仰著頭筆直地站在那兒,也許瘦了,更顯出挺拔的髂骨。我們這一族人,都是老年也不傴僂的。他看見了我,像過去一樣,正經地大聲喊我的名字說:「回來啦,我在這裡呐!」於是便來幫我搬書箱。這時我才看清他滿臉皺紋,一頭花白。我心中一熱,兩眼竟濕了。側過身去咬了咬嘴唇,才忍住了沒有掉下眼淚來。
我嬸嬸和全生死後,老清阿叔就只有一個七歲的小兒子興生和他在一起生活了(養了不少,成活率不到一半)。合作化以後,雖然種田已用不到老清阿叔動腦筋,只須聽領導安排就行,自己不必再被釘在暗敗子的十字架上;但開門七件事,少了個內當家,穿戴吃喝,燒補曬藏,亂不成套,套套都亂,日子過得還是很糟。倒是前幾個月動了秋忙以後,生產隊辦了食堂,管了他父子的吃喝,不但無需再忙著燒那一天三餐,而且豬羊雞鴨全不用私人飼養,他一老一少簡直變成大爺小爺,舒服得很了。老清阿叔年近六十,不用再幹重活,隊裡給了一條牛讓他飼養,極其輕鬆。興生還只十四歲,原來為了賺工分,已經在隊裡掛了個號,經常參加勞動了。現在生活有了保障,讀書又不要錢,而且省力氣,他為什麼不乘機學點文化!便進了小學一年級,同七、八歲的孩子坐在一個教室裡,起坐之間,顯得出奇地魁偉。所以,老清阿叔是熱忱擁護大躍進的,精神比以前好多了,甚至懂得了一點世道。他猜想我這次丟掉飯碗回來,大概是為了我父親(他已經死了)的緣故,十分感歎,卻不直說,反埋怨外頭的飯難吃,蹲在那兒受氣,倒不如回家來安穩。「回家來,苦是苦點,飯總有得吃的。」他自信我比他懂得多,原不該他來開導我,就裝著自言自語地說。然後起勁地一揮手,略略提高了喉嚨道:「我還巴不得你回來呐!回——
來——好!骨肉在一起,暖暖熱熱!」
他說得那樣真摯動情,好像真有一股暖暖熱熱的氣流飄過來裹住了我。
然而,我心頭的優問、疑懼、冤怨,不是老清阿叔能夠排除得了的。生活的驟變雖然沒有擊垮我,使我失去信心,失去希望,但是我也知道始於足下的道路將是艱難而漫長的。我回鄉以後便迅速追上大躍進的步伐,盡自己的力量投入到勞動中去,求得脫胎換骨,徹底改造自己。所以,我仍舊很少想到要關心老清阿叔。我能給予他的只能是他付我的十一,我也萬萬沒有料到,這已經使他感到滿意了的生活,他都無福同別人一樣過下去。我回鄉不到半年,江南的風還沒有把麥穗吹黃,他忽然就病倒了。
大家都忙著積肥下秧、準備夏忙,對於不參加主要勞動的老清阿叔生病,全沒注意。連我也是他病倒三天以後,早上偶而發現小弟興生在代他放牛,問了興生才知道的。興生也和老清阿叔一樣憨厚,從不知道央求別人什麼,難得沒法也只會發呆。我中午端了飯碗邊吃邊跑去問候,見老清阿叔用被角蓋著腹部躺在床上,兩眼失神,一臉灰暗。問他有什麼不舒服,他搖搖頭。摸摸他的額角頭,似乎並不發燒。我還是不放心,把了他的脈,發覺太粗太快,我懷疑說:「老清阿叔,出什麼事了?」
他定神看看我,仍搖頭不答。我估計沒有什麼大不了,便安慰了他幾句。回去放了飯碗幹別的去了。到了晚上,我再去看他,他正在吃興生去食堂領回的薄粥。見我在床沿邊坐了下來,默默喝了幾口,忽然哽咽地說:「侄呀,我只怕要死了。」
「怎麼呐?」我吃了一驚。
「我倒黴,碰到鬼了!」他絕望地說。
「努!」我立刻放心地說,「別瞎說,鬼是沒有的!」
「哼!」老清阿叔第一次這樣不屑地對待我。然後想了一想,極嚴重地悄悄說道:「你不要說出去。我告訴你,鬼是有,我看見的!」
我雖然還是不信,但看他那麼緊張,也有點發怔。
「倉庫後面的河潭邊頭。」老清阿叔確鑿地說,「我碰到的。是初四夜裡,我晏睡,架了口網想弄點魚吃。走近河潭那邊,就聽見有響聲。」
「什麼響聲?」
「啜啜啜啜啜啜啜……好像喝水,聲音很大,又不像喝水。」老清阿叔出神地說,「我心裡就發毛,便撳亮了手電筒,想看看是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呢?」
「老鼠,都是老鼠,數千數萬,大得像小豬。河潭邊頭上上下下蹲滿了,擁過去搶水喝。」老清阿叔緊張地說,「電筒光一射,馬上大亂。它們不逃走,反而對著我沖過來。我逃都來不及,有幾隻追到我身邊,爬上我的身,咬了我的腿,又一陣風朝倉庫那邊跑,一眨眼就沒有了。」
「啊,」我想了想便安慰他說,「那不就是老鼠嗎,怎麼是鬼呢?」
「有那麼大那麼多的老鼠嗎?」
「最多些最大些還不總是老鼠嗎?」我說,「吃了食堂,家家沒有糧食儲存了,老鼠沒有了吃的,大概都搬到倉庫裡去了,吃住方便些。」
「別騙我了,那是鬼!」
「你不明明看到的是老鼠嗎?」
「你傻了。」老清阿叔胸有成竹地說,「你當鬼就不能像老鼠一樣嗎?你說,鬼究竟是什麼樣子?」
「哎呀,你……」我覺得老清阿叔想得太可笑。可是又找不到話說服他。
「你還說老鼠都去了倉庫呢。你來看。」老清阿叔倒說得精神起來,他把右腳露出來,抬高了腿指指腳跟讓我看。那腳跟後頭半塊老繭,像個冷團子的皮子,被啃掉了厚厚一層,齒痕細碎,分明是老鼠咬的。
「要不是碰到了鬼,老鼠它敢咬我嗎?」老清阿叔證明自己有理卻又悲涼地說, 「我晦氣透頂。被老鼠咬過了,活不長久的。」
五
不管我怎樣勸說,勸說了多少次,我沒有勸醒老清阿叔。他顯得異常地固執,認為一切早註定了,他的期限已到,老鼠咬他腳跟上的老皮等於是閻王在他身上做了記號,不久就會差小鬼來帶他走。他不必要指望什麼了,等著鬼來就是。
他的精神再也振作不起來,他等待著,越等越萎懨,而克卻沒有來。他原本是害怕它到來的,因為等不到,反而倒在盼望了。於是便常常有夢,常常跟我說他夢見了我的祖父、祖母,夢見了我的妹嬸、爹爹和大伯,嘮叨著要祭奠他們。我們家有個慣例,每逢過年、清明和七月十五,都要用兩張八仙桌並起來祭祖先。祭祖也有一套程式,這程式我大伯和父親都沒學會,獨獨老清阿叔內行,這都是祖父教會他的,也算是派他分管的一項家務。那兩張並起祭祖的八仙桌擺著十六副盅筷,表明祭十六位祖先。每人一個座位,最老的祖宗坐在首位,但是如果陽間又有子孫跟到陰間來了,那坐首位的祖宗就該撤走,讓次座升上首座,用不到選舉,其餘跟著提升一座,空出末位讓新鬼去坐。長江後浪推前浪,這倒不是流水無情,只有這樣才有出路,才能運轉。新陳代謝的道理,大概陰間也是通行的。為了完成交接班,新鬼來後的第一次祭奠,首座還是不換祖宗的,只是在末位以後加上第十七副盅筷,表示新客來了。那盅子倒蓋著,表示新客還沒有座位,站在那兒恭候老祖宗引退。到第二次祭奠時,就恢復原狀,表示該退的已退,該升的已升,該就坐的已就坐了。當然這純粹是一種形式,內容是空的,當真還有什麼一個不退一個要搶的戲做,活人也看不見。可是老清阿叔卻說得出每個座上祖先的名字、輩份。如今祖父母、父母、伯父母以及嬸嬸都已坐在席上了,所以老清阿叔的腦子裡是有鮮明的形象的。只要他一講,那些人我也很熟悉,也會在我的腦子裡活起來。於是便升騰起一團鬼氣,老清阿叔魂縈夢回,經常睡不好覺,身體一天虛弱一天,放牛的時候會坐在田埂上打瞌睡,那牛便乘機偷吃田裡的莊稼,亂了套了。
生產隊的日子也越來越難過,放開肚皮吃飽飯是二十四小時實現共產主義的產物,已經變成歷史的陳跡,接下來便是定量供應,又經過了供應不足,粗糧細糧並舉等階段,逐漸進入瓜菜代的新時期。過去總說稻場底下六十日飽,五九年秋收就像沒有收到糧食一樣,很快就餓肚皮吃健康粉。一天只有半斤定量,燒三碗粥照得出人影子來。老清阿叔和興生領了兩份,興生年幼不懂,老人又顧惜孩子,常常自己只吃四分之一,將四分之三給了孩子。孩子也不曾覺得受了恩惠,因為反正還沒有吃飽。
老清阿叔的活動量已經很少了,然而他還是很早就起身,開了門坐在門檻上吸旱煙,然後呆呆地站著昂頭看天。這樣的時間越來越多,常常是靠在山牆上這麼發呆,似乎站著也力乏了。
秋冬之際,涼氣已經很重了。有一天午後,公社漁業隊的網船,開到村外河浜裡來捕魚,老清阿叔遠遠看到了,又勾出癮頭來,便拖了兩條疲倦的腿走過去,坐在河岸上看,當時大家都忙,只他有空。看捉魚的除他而外,幾個小孩而已。那網船上的人,也認識老清阿叔,知道他有捉魚的癮頭,少不得在這漁業隊管轄(占山為王)的河浜裡偷過魚吃,雖然不同他認真計較,卻也不尊敬他。老清阿叔看那同下了又收,收了又下,倒也捉到了上百斤魚。後來一網下去,收著收著,下面像被什麼東西死死咬住了,再也收不上來。船上人用鉤篙橫撥豎卸,累出一身汗,一無用處。
老清阿叔一看就明白了,這兒河底裡有幾根木樁,本樁上釘著爬頭釘,原是防偷魚賊的,漁業社的人笨,把網掛牢在爬頭釘上了。他很有點瞧不起他們。看他們白費了半天力氣,便衝動起來,突然說:「下河吧!」
捕魚的也知道非下河不可,但是天氣冷,身體是自己的,網是公家的。
「我替你們下去卸!」老清阿叔英勇地說。
「冷!」有人提醒。
「不礙,他骨頭老,經凍。」有人促成。
「什麼條件?」船老大問。
「讓我揀一條魚。」
「可以,再貼你半斤燒酒。」船老大加碼。
「不要你的酒。」老清阿叔說。他當時大概燒得厲害,脫光了就下河,潛水下去只分把鐘,就把網卸下來了。
他拎了一條四五斤重的魚回來,沒有油,沒有酒,光放了些鹽把它煮熟了,一頓把魚肉全吃光,只剩了個魚頭蓋在鍋裡。興生回來時他已睡著了,沒有告訴興生。興生不知道,才沒吃掉。
這完全是反常的行為,完全不似他平時的為人了。若在平時,他先想到的是興生和我。決不會獨吞。
第二天早晨,老清阿叔依舊是起得很早的,不過他坐在門檻上吸了幾筒旱煙之後,卻不想站起來了,他把興生喊醒,叫他到牛圈頭去燒水,刈草喂牛。
整個上午,他都躺在門前稻草堆上享太陽,那大太陽持別好,似乎是特意讓他享用的,他就在太陽底下吃了一碗稀湯當午飯,始終沒有離開那溫暖的草堆。後來看見隊裡派工挑了山芋上窖去儲藏,他似乎受了引誘,站起來拖拖遝遝,三步一停兩步一歇跟到了窖上。坐在挑來遮蓋山芋窖的乾柴堆旁,吸著旱煙,看別人藏山芋種。那種子裡夾有帶傷殘的山芋,藏種人便剔出來丟在旁邊,老清阿叔便隨手拿一個大的來,拉把草殼擦擦,就著他們拿來挖土的鐵鍁口削了皮,生咬著吃。藏種的人肚子都餓,剔出來的傷殘山芋原就是打算充饑的,見老清阿叔先吃了,有人只說了聲:「你倒比我們還老誠呢。」便由他去吃,全不阻止,大家知道他餓,猜他可能就是為此而來的。
也不知過了多久,他吃了幾個山芋?猛不防那堆乾草竟燒起來了,等到發現,火勢已旺,難以撲滅了。幾個藏種的人搶上去,把還沒有燒著的柴捆搬開,著了的只好由它燒去。這時才注意到老清阿叔手裡捏著一根煙杆,還一動不動僵立在火邊。這下把大家惹惱了,七嘴八舌,把他罵了一頓:「吃昏了頭,定是把煙灰撞在柴草上了,才會燒起來!燒了自己不救,也不喊救。怎麼著,死人嗎?真該死了!等歇回去告訴隊長,跟你算帳!鬥。你!」
老清阿叔聽了,也不曾說話,仍舊像段木頭,呆在那裡。大家也是氣頭上嚇嚇他的,等到火熄滅了,便又窖藏山芋去,不再理他。也沒有注意他是怎麼回去的。
我一整天都不在隊裡,隊長派我用條小船運五百斤稻草到鎮上飼料加工廠去軋成粉做豬飼料用。這本來不是我幹的事,應當由飼養員去,但這是件很苦的差使,又累又髒,那軋出來的粉又不能揩油來填肚子,回來的時候說不定會餓癱在半路上,所以才讓我去。食堂裡給了我兩個用健康粉做的團子,我靠它一直熬到晚上才回來。小船靠了碼頭我幾乎站不起來了。隊長派人來幫我卸粉的時候,他們才跟我談起老清阿叔下午火燒山芋窖的事。我正在餓得發昏,立即聯想到老清阿叔當時一定也餓糊塗了。於是走過他家的門口,順便就去看看他。推門進去,只見興生一個人靜靜的在幽暗的煤油燈底下吃一個魚頭。興生說老清阿叔從容上回來就睡了,這魚頭是他看見野貓老是悄悄偷跑來爬鍋蓋,起了疑心,才在鍋裡發現的。興生講的時候很有情緒,因為他爹吃得只剩一個魚頭了。他也有氣量,把個魚尾巴從脊骨上折下來給了我,那上面還有一些些肉。我也極饞,拿過就吃。果然是仙丹,原來乾渴的嘴巴,一抿那魚尾巴就生津。舌頭也活絡了。我喊了幾聲老清阿叔,他沒有答應,提了煤油燈進屋看了一眼,他確是躺在床上,於是我安心離開,不會出什麼事情的,他吃了一條魚呢。
那一晚我睡得很沉,早上還睡過了頭,起身後匆匆忙忙拿了只大陶碗上食堂打糊糊吃,卻碰到了興生。這時別人早打過了,我便問興生,怎麼會這麼遲。興生說他早晨代爹去燒水鍘草喂牛,回來爹還躺在床上,連早飯也不來打。
「你喊他了嗎?」我忙問。
「我喊他做什麼,他要困就困好了。」興生隨便地說。
我忽然覺得異樣,因為老清阿極從來不睡懶覺的。便一路喝著糊糊跟興生去看他。沒到他家糊糊就喝光了。
我走進屋裡,老清阿叔朝天靜靜躺在床上,閉著眼睛,我喊了幾聲他不響,才發覺臉色變了,走近去用手一摸額角,冰冷。
我不知道他是什麼時候死的。也許昨晚來看他的時候就已經——煤油燈暗得實在也看不清。興生同爹困在一張床上都沒曉得,孩子畢竟還小。
按照生產隊的老規矩,老掉了人應該吃一頓喪飯。這喪飯原該家族去辦了請社員吃,既然口糧不分到戶,自然由食堂去辦。現在是冬天,新一年的口糧剛剛開始吃,老清阿叔的全年口糧還剩得多呢。這些口糧雖然因為「天災」的緣故沒有落實,但計劃還是有的。生產隊裡多少總還有點伸騰的辦法,於是大家靠著老清阿叔的過世吃了一頓很飽的喪飯。
「唉,又老掉了一個人。」年紀大的人歎息了。
「還是他福氣!」這話的內涵就豐富了。
興生也沒有哭,他還不懂。奇怪的是我也並不怎麼傷心,反想著他死前吃了一條大魚,倒很得到些安慰。
雖然總說「隔夜飽,只是飽」,但再隔一夜也就徹底消化掉了。所以過了幾天,人們只能夠想著那一頓飽食了。於是青年人在田裡勞動的時候,便嘻嘻哈哈拿隊裡的老人排隊,看下一次會吃哪一個的喪飯。
我也奇怪地常常想起,下次祭祖的時候,應該替老清阿叔添上一副蓋著的盅筷了。老清阿叔一時還不能接受小輩的孝敬,不過他肚裡有一條魚,當不致餓壞的。
1987.8.19——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