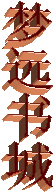
高曉聲文集 送田
在南周村上,最不會算帳的人,也明白現在種田是出大力氣賺小錢的職業。同住一個村上,多年來都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可是,在廠的人過什麼日子?在採石場的人過什麼日子?做小生意的人過什麼日子?搞運輸的過什麼日子?憑技術做包工的過什麼日子?幹部過什麼日子?種田人過什麼日子?全都清清楚楚。瞎子看不見,啞子不會說,心裡都明白。
南周村是個富村,從外表上一眼就看得出。只要看那房屋,新房子把舊房子擠進地下了,擠在縫裡了。可憐它們從前也住過人,如今能倖存下來,卻是甘心受委屈做豬舍柴屋。它們原來的主人都住到新房子裡去了。難得還有幾家住老房子,那也並非特別念舊,不過是沒有造出新的來罷了。而這樣的人,自然越來越少,所以形勢越來越好。更加難得的是,有一批造了新房的人,竟像造出了痛頭來,每過三年四年,就要大動土木。比如周錫林,就最有代表性。南周村上是他第一個造新屋,十步兩開間,足有七十五平方公尺。過了三年,看見造的人多了,竟趕上他了,這就顯不出他獨闊。好,乾脆拆了重造樓房。造樓房先造二層,可是他有預見性,估計過幾年村上二層樓又會普及,所以造二層樓的時候,牆腳裡就下了大本錢,打的五層樓基礎。果然,再兩年,許多人造二層樓了。他便在二層上面輕輕巧巧加一層,變三層。到去年,村子上好些三層樓出現了。他又不慌不忙在三層上面加一層,變四層。造來造去,房子越造越高,越造越好,形勢可真不是小好,是大好。而且最好最高的,還是周錫林那一幢。真了得!時代不會埋沒英雄。
南周村上的人靠什麼賺到錢造房子?說起來簡單,最初無非是靠幾塊石頭。石頭是天天看見的,可是想到它能讓許多人過好日子卻不容易。蘇南這塊地方,工廠也多,土地也肥,賺錢的門道多得很,誰的眼睛也不輕易會去瞧上那些又硬又冷又重又呆的石頭。南周村所在的豐裕鄉,有幾座光禿禿的小荒山,上肉瘦薄,山坡上的青草像唐痢頭上的毛,沒一點神氣;種了樹都不長,沒一點出息。不知被大家咒駡了多少年。五八年大躍進,雖然我們沒有提出以石為綱,但到處造橋、築路、蓋廠房,還要修補被英雄們踢破的地球和戳破的天,石頭一下子也便像糧食一樣,變成了基礎的基礎,寶貝中的寶貝。
好傢伙,這兒可不是四川峨眉山,整個地區都缺大量的石頭。這兒的石頭卻在腳底下睡大覺,實在太冤了!於是,一點兒沒有出息的荒山一下子就變成了使不完。用不盡的金山銀山。鄉里辦了個採石廠,各村各隊都調人上山採石。採石工全年的工資,比在生產隊種田的社員高三倍、四倍。可惜不能讓大家都去,農業是基礎,糧食是個綱,田地要人種哪!咱們不能光算經濟帳,要算政治帳哪!
那麼,該誰去,該誰不去呢?極複雜,說不清楚。
這不奇怪,世界上說不清楚的事情比說得清楚的事情多得多。在說得清楚的事情裡面還有許多不該說清楚、不便說清楚的,連不該和不便說清楚的原因也有許多不清不楚的地方呢。所以乾脆莫說它了。反正去的、不去的,吃虧的、沾光的,都是我們自己的事情,和外國人沒有關係。
且舉兩個代表人物做例子吧。比如周錫林,那自然是要去的。不但去,而且負點責任,因為他覺悟高,有經驗,到任何什麼地方去都能負點責任,到任何什麼地方都能表示還可以多負點責任。在村裡是這樣,上採石廠是這樣,後來又調去其他單位,也全是這樣。而且虎父不生大子,精明人家的門閂都是能夠容出白米來的榔頭,挺出息。兩兒兩女兩媳婦,沒有一雙手捏鋤頭柄的。領導、供銷、會計、技術員、工人,這一家門都占全了。所以不管有沒有政策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事實上他早就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占了先。他那幢房子不就說明問題了嗎?!他一家倘若在田裡苦,到哪一年才能闖出這個場面來!真是賺錢不吃力,吃力不賺錢呀!誰說文化知識沒有用呢,這要有階級分析。要看文化知識掌握在誰手裡,資產階級把字典背熟在肚裡也沒屁用,他周錫林能識得《人民日報》上一半鉛字,在鄉里擺擂臺也沒人敢上去打了。趙匡胤做皇帝,靠半部《論語》治天下[注],那麼,憑周錫林肚裡那點墨水,還有什麼塗不黑的呢?!總說「文官動動筆,武官幹一日」,真是不錯。那生活悠閒的情趣,冬天龜縮在屋子裡不容易讓外人看到,夏天就表現得非常清楚。天還不曾夜,一家子已經洗頭洗腳洗身子,弄得乾乾淨淨香噴噴,坐在屋頂上吃晚飯。屋頂是鋼筋水泥澆的,四周圍著欄杆,還點綴有花卉盆景,真可算得是個屋頂花園了。吃過晚飯納涼,周錫林就坐上一張特製的椅子,這椅子的四隻腳裝在兩根抛物線型的木棍上,人坐在上面,只要重心略略變動,那椅子便一前一後擺動,俯仰之間,天上的星星和地上的燈火,全過了目。像看一朵朵放光的花一樣,舒舒服服,安穩得叫人不想動腦子。
真開心。簡直是神仙過的日子。房子高了不光威風;風還大,蚊蟲也少(下面有血吸,它花力氣高飛幹什麼),再一個好處呢,就是看得遠。「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嘛!
一說那麼多,真弄糊塗了。我是在舉兩個代表人物,說到這裡還只說了一個。另一個是誰呢——就說周炳南吧。周炳南就是該不去的,就是該讓別人去的。有許多人爭不著幹採石廠的長工,農閒時還可以去做一陣臨時工,一年也能收入三四百,周炳南連這也不能夠,幹臨時工也該讓別人去。總而言之一句話,周炳南該的只有一樣,就是侍候土地公公,土地婆婆。別的都該讓別人去幹。若問為什麼,不必寫出來,一則被人寫爛了,二則事情過去了,三則說出來反而挂一漏萬。要知道南周村上像周炳南那樣一貫忠誠於種田事業的還有好幾家,各有不同情況,寫了周炳南一個,別人就會罵不公平,為什麼不寫他們呢?
還是直截了當說結果吧!結果是什麼?就是周炳南一家五口子造不起新房子,還住在同別人家做了豬圈一樣的老屋裡。
寫到這裡,應該特別聲明的是,這種情況是正常的。周炳南本人沒有一絲一毫抱怨情緒,你叫他是阿Q也好,你鼓勵他從阿Q的翅膀(不知道阿Q什麼時候長出翅膀來了?原來不是只有一條辮子嗎?)下飛出來也好,甚至你鄙棄他、認為不能寫人小說也好,都沒有關係。但千萬不要替他打抱不平,你打不了,他也不需要。他也跟著大家,在新社會裡活到現在了,一點不比你差。他風格高,見好處就讓,見困難就上。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他知道水漲船高,他橫豎也在船上呢。這看法完全沒有錯,現在就輪到他有錢造房子了。
周炳南有錢造房子,也是到採石廠去做工賺來的。「文化大革命」一完蛋,周炳南「該不去」的理由忽然沒有人再說得出口(可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不過沒有了該他不去的理由並不等於該他去。該他去還有別的原因,那是因為鄉里辦了些比採石廠還要好的工廠,那兒安全、乾淨、輕快,賺的錢更多,原來在採石廠工作的人,有辦法的都鑽到新工廠去了,比如周錫林一家,原來有三個在採石廠,現在剩了零。採石廠缺人,抬高工資公開招工,還招不足。許多人嫌吃苦,費力氣,髒,不小心還會傷筋動骨,打炮的時候萬一砸死了更是倒楣。這時候周炳南去幹,自然開著大門表示歡迎。
也不過是四年不到,三年多點時間吧,周炳南父子倆在山上幹著幹著,一天天把錢積聚起來,就足夠造兩間二層樓房了。他們究竟積了多少錢,一角一分都有數。可是他們究竟流了多少汗呢?
誰量過!誰稱過!
周炳南父子在採石廠幹了這幾年,最重要的結果,其實並不在掙到了一筆造房子的錢,而是把兩個農民變成了工人。他們一家的主要收入,不靠包種生產隊那幾畝田裡的出產,而是採石廠的工資。所以他們的精神氣質變了,有氣魄辦事情了。要是在過去,周炳南積了這麼些錢,還不敢造房子。他會想著萬一碰上天災怎麼辦?母親萬一倒下來怎麼辦?兒子良良找到了對象怎麼辦?造房子造虧了要借債怎麼辦?現在就不在乎這些了,他有了靠得住的來源,用不到留後步,敢於放開膽子豁出去了。
「不管他,愜愜意意先把房子造了再說。倘若又碰著要用錢的事情,先借了,以後還。」周炳南有了這樣的自信心。
「快造吧!」村子上的人都支持他說,「你看,全村還有幾戶不造房子的?也該輪到你了。」
「哈哈,太陽光也有照到我家門前的一天。」周炳南心裡很樂。
他原不是沒有計算的人。前幾年分田包產的時候,他就想到了造新房的地皮。離他家老屋不滿五十公尺,有塊大約一分半的空地,其中六厘是他的老自留地,另外九厘是周錫林的老自留地。當時周炳南要求生產隊把周錫林的九厘也劃給他做屋基,生產隊沒法同意,因為有個公約,劃給屋基之後,一年之內要把房子造出來,周炳南沒那個財力,只好作罷。有人還笑周炳南說:「你能在原來的六厘地上把房子造滿了就不差了,那也靠近四十個平方呀!」周炳南又要求劃給他做自留地,周錫林當然不肯,他說:「你老弟若是造房子呢,我不能不成全你,只好讓。倘若拿去做自留地,那我種著不是一樣嗎?況且是我種慣了的,為什麼讓給你!」周炳南沒有理由,輸了。
等到現在,村子上的地皮都造得差不多了。還是那塊地,因為自己占了六厘,剩下的九厘別人不夠造,總算還空著。也只有這塊地,出路寬敞,走水快,同前後左右的鄰居不會有「你遮了我的陽光,我被你擋了風」的矛盾。所以周炳南舊話重提,向村民委員會提出了要求。
沒有疑問,土地的所有權屬于集體,村民委員會有義務滿足周炳南的合法要求。可是世界上每一件事都牽涉到許多方面。不錯,土地的所有權是集體的,但使用權卻在社員手裡。村主任感國平年紀輕,上臺不久,論資格別說同周錫林比,連周錫林的兒子都不如。於是個人和集體、使用權和所有權的關係都得換一個位置。他很客氣,開口就稱「炳南叔」,說:「你要那塊地,村委會沒有什麼意見,但是要和錫林伯商量,要他答應才行。」
「那就請你同錫林去講講吧!」炳南說。
「你去,你們直接商量好了就行。」
「你去!」
「你去!」
推來推去,非常客氣。炳南不是笨人,越見主任客氣就越覺得裡面有難處,就更加不敢直接找周錫林,怕當面弄僵了沒有轉彎的餘地,便央求說:「主任,你幫幫忙,無論如何你去同錫林說一說。說得通也好,說不通也好,哪管探一探他的口風也好,我都感謝你,你就把他的意見告訴我,讓我心裡有個底,然後再商量。能讓這塊地給我,我不會白沾光,有什麼條件,只要我辦得到,我都辦。總不讓別人吃虧。」
話說到這個地步,村主任周國平點點頭,答應了。
三個月沒有回音。同在一個村上,見面不難,周炳南白天上山,沒有空,只好晚上做工作,上門找主任。他深知「皇帝都不差遣餓兵」的道理,先行起「東風」
來,巴望有「夏雨」。主任也為難,情面難卻,無法沽名釣譽,只得順水推舟。不過「雖然在一個村上,大家都很忙,」他這樣說:「我有空的時候,他沒有空;他有空的時候,我又沒有空。我找過他幾次,都不曾碰著。有兩次我約了他來,他倒真來了,我又不在家。在路上還碰到過兩次,他去上班,又沒時間細談……你別心急,我上個勁……」
到了第四個月快過完的時候,周主任主動跑來找炳南說:「我同錫林伯談過了,沒有問題,他絕對不要你什麼,不讓你受一點損失,你當面去同他商量就行。」
周炳南心上一塊石頭落了地。事情能夠這樣容易地解決,畢竟是新社會。
「不錯。是新社會。」周錫林在自家的四層樓房裡接待周炳南,三言兩語就提了這個綱:「要是在舊社會,老弟,別說你我同姓一個周,就是同一個娘肚裡出來的,我也不答應。」
「那自然。」周炳南感恩戴德地說。雖然同在一個村上,雖然同姓一個周,周炳南從來沒有到這兒來坐過,如今是第一趟,算初見世面,開了眼界:「好!」他暗叫一聲,肚裡尋思,「總說『人要衣裝,佛要金裝』。話還不曾說到家。金裝的佛還要住在大雄寶殿裡才相稱,這多舒服!房子就要造得這樣氣派,長人的威風。」
跟周錫林比一比,他的根基實在差。
「造房子的地基是寸金地呢。」周錫林輕輕鬆松地說,「買的話,比普通水稻田貴三倍價,還是客氣的。」
「那是舊社會,我也造不起。」
「我是講舊社會。」周錫林聲明,然後內行地說,一碰到這種事,難得講客氣的。村東洪富家那六間老屋,現在不像什麼樣子了,以前他祖父造這六間房,有八厘地基是水田填出來的,光做牆基就多花了幾倍錢。可是那水田在人家手裡,你謀他們的寶,他們不肯。你買,他不說價。你知道洪富的祖父怎麼做的?他在一棵稻根樁上放一塊銀洋錢才買下來。好大的氣派!」
「是氣派。」周炳南點點頭。這是老故事。
「這種尷尬事情多呢。當年劉根大房子造好了,大門外面是別人的地,要買一條出路,硬硬頭皮任別人敲竹槓。吳志洪呢,他父親造那兩間房,只為了後包簷簷頭水滴下來滴在別人家地方,花了十擔米,辦了兩桌酒,才真真叫做寸金地呢。」
一講好多,周炳南只能唯唯,插不上嘴,談不上正經事。好不容易讓周錫林說完了這些,夜都深了,周炳南起早要上工,趕忙告辭,說:「老哥,謝謝你了。」
「為啥謝我。」
「謝謝你答應把地基讓給我。」
「這個不用謝,你去同國平主任具體商量好了。」
「國平說他沒意見,你答應就行了。」
「他沒有具體同你談嗎?」
「談什麼?」
周錫林笑笑說:「你去找他談。我的意見都告訴他了。他怎麼沒有同你講呢?總是年輕,做事不到家。你問他吧。」
送客,關門。周炳南的心掉在門裡了。他曉得不順遂。
究竟有什麼話要,轉個彎才能說呢?不弄清,周炳南睡不著,白躺。他當天夜裡就去敲國平主任的大門。
「他並不想你什麼。」周國平披了衣服開了門,對著炳南尷尬地斟字酌句地說,
「灘南有他包產的兩畝三分田。他沒人種。你要他九厘地皮造房子,他答應。條件是連那兩畝三分田都讓給你。」
周炳南聽說,就「哎」了一聲,呆住了。
半晌,周國平輕輕歎了口氣說:「你看呢?」
周炳南兩手是汗,在布衫上抹著說:「我能受嗎?」
周國平輕輕地說:「我也曉得你的難處。所以他要我告訴你,我都不曾肯;勸他當面同你說。你看,他還是推我開口。」
一時間,兩個人都不知說什麼好。
世道變得多快,五年十年就連底翻了個身。大家都是世世代代的種田人,田地歷來當做命根子。遠的不說說近的:十年以前,誰把田地包產到戶是反革命;四年以前,田地分戶包產還怕分不公平打破頭。可現在呢,田地成了許多人的累贅,送都送不掉。周錫林的做法,是學的官商做生意,把滯銷商品搭在緊俏商品一起強迫顧客買。雖然這裡是奉送,但畢竟搭得太多,多得連他自己都內愧。內愧也還要這麼辦,可見機會太難得。
周國平還是要幫周錫林說話:「他也實在難,你看他家六大一小,哪一個還會下田去做!」
周炳南苦著臉說:「他要把尾巴裝到我身上來,我也吃不消。自家已經有五畝,加上這兩畝三,我父子兩個就得從廠裡抽一個人回來種田了,這一年要虧多少?!」
周國平沒話。聽他說。
「算粗一點吧。」周炳南說,「一畝田統算全年做三十天工,兩畝三分田就要做六十九天。我上山推石子每天七元錢不用開口,在田裡做一天呢,能保住二元五角就差不多了。做一天我要損失四元五角,六十九天一共要三百一十多元。這又不是一年兩年的事,長久下去得了嗎?」
「話是不錯。」
「況且灘南那地方離村又那麼遠,施肥的話,一天能挑幾擔呢!」
「那倒不要緊,一路都是大道,可以開拖拉機運。」
「為那兩畝地,我還搞機械化嗎?我沒那個本錢,安安穩穩上山做工不好嗎?」
「那怎麼辦?」
是呀,那怎麼辦?
周炳南沒有能耐回答。
沒有辦法就拖著再說吧。歷史不就是「拖著」才那麼長的嗎?厭煩死了!
周炳南原也沒有同周錫林硬到底的骨頭。儘管他有理,但是周錫林有權,誰勝誰負明擺著,怨命吧!此處不能造,總有造屋處。另找一塊地方怎麼樣?當然可以,向村主任周國平申請就是了。
誰知道這也行不通,周國平嘴裡一口答應,卻今天推明天,這月推下月……橫豎不落實。一拖又是幾個月。周炳南這才嘗出味道來了,原來情況又翻了個兒了,現在不是他要不要那塊地皮的問題,是周錫林看中了他,粘著他不放了。這麼一來,周國平他聽誰的話,聽周錫林還是聽周炳南,不是明擺著的嗎?嘿!
誰說「拖」不是辦法呢?
糊塗!「拖」不正是辦法嗎!
周炳南牙齒一咬,低頭認輸。
「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用現代的語言說,就是「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的意思。
經過了一番微妙的較量,不但沒有死人,沒有傷筋動骨,沒有擦破皮膚,就連臉蛋兒都沒有紅過,雙方便都得到了各自需要的東西。這好比是少林寺的武術大師同三歲小孩兒比武,高低、勝負最容易顯出來,倒反一點不會驚動社會輿論,影響社會治安。
不過,前前後後,時間幾乎拖了一年。是上年秋後鬧出的矛盾,到下一年大暑,周炳南才答應接受對方「割地求和」。他選擇這個時間也有原因,那時候青苗都抽三眼了,周錫林總得收了這一熟才麻煩他去種麥子,也算討得半年的便宜。
有了地基,說造就造。稻子還沒有成熟,周炳南兩間新屋就落成了。錢是用了不少,可不曾用虧,好像還挺能再花費點,意外地顯示出底子挺厚呢。
過了霜降,大秋全收完了。周錫林把灘南那塊田空在那兒,由周國平出面通知周炳南去種麥。這自然用不到舉行什麼儀式,就算把使用權無償奉送給他了。
究竟是新社會啊!從前誰肯!?
周炳南說話算數,接受了。可是,過了小雪也不曾去種麥。
讓它荒掉嗎?不,大家都知道周炳南不是這種人。周國平走來勸他不要賭氣,周炳南笑笑說:「我賭什麼氣?還早呢!」
「還早?」
「對,我要種的東西還早。」
「你種什麼?」
「我種什麼?我可不能同錫林哥比。你記得灘南那塊田,原來就是旱田改成的水田、能改嗎?改了這些年,年年收不著幾斤稻。它盛不了水,通底都漏!集體嘛,橫豎不在乎,周錫林嘛,橫豎也不在乎,都虧得起。我可虧不起,我要改過來。」
「種旱田更費工,一夏一秋澆不及!」
「我不澆。」
「不饒就幹死!」
「有幹不死的。我種樹。」
「種——樹——嗎?」周國平大出意外,覺得挺彆扭。怎麼種樹呢,不是已經習慣了種稻子嗎,管它收成多少呢!
可是他沒有反對。不好反對,時代不同了,反對也沒有用。周炳南肚裡也裝著對付他的話。他不反,也就不說出來了。
說幹就幹,只要一有空,只要忙裡能抽得出空,必要的時候哪管向廠裡請了假,周炳南帶著一家人冒著尖利利的鑽骨寒風,在凍土上挖出一個個穴,點人基肥,栽上樹苗。整整辛苦了一整個冬天,在二畝三分地裡栽了三千棵樹苗。密是密了一點,但也不會棵棵成活的,有一部分是後備軍。
對一個家庭來說,完成這樣一個工程並不容易。現在看上去還都是光禿禿的枝條,很不起眼。但只要到了春天,氣候暖起來,下幾場春雨,樹苗苗的枝條便轉青、發芽、放開嫩葉,那麼,這田裡就會像聚了許多孩子的幼兒園一樣活潑、歡騰。這該多美!
一家人忙忙碌碌,沒有想到歷史的車輪還在轉,不知不覺「又一村」。真沒完。
樹苗栽好不久,臨近春節以前,有一天傍晚,周炳南父子倆下了班,從採石廠走出來。剛上了回家的大路,便聽到前面有人在喊炳南老弟。周炳南抬頭一看,不覺驚疑。那不是周錫林嗎!要說是周錫林,他叫人的聲音怎麼這樣順耳好聽?要說不是周錫林,豈不是自己眼睛出了毛病。就在這判斷不定的刹那間,周錫林已經撲面到了身邊。沒有錯,是他,無可懷疑。他原來就有這種好聽的聲音和好看的面孔的,只是以前周炳南沒有看見聽過罷了。
「炳南老弟。」周錫林親熱地眯著眼睛說,「我找你,找了好半天,人家告訴我,你在這裡,我卻不相信。都快過年了,你還天天上班。真虧你!」
「沒有辦法呀!」周炳南從沒戴過高帽子,這會兒手腳無措,應付不過來, 「你……
「有辦法,有辦法。」周錫林搶著話頭說,「有共產黨領導,都有辦法。你老弟造兩間樓房,還不是說造就造了,乾乾淨淨,屁股後頭沒有一分錢債。」
「錫林老哥,你找我有什麼事?」周炳南要不來嘴唇皮,不會繞彎子,想快點問清楚了好回家。不是年底了嗎,忙著呢,況且肚皮還餓在背上。
「沒事,我們一同走。」周錫林說。他回身就和他們一起走,一面說,「真沒事,回家去,同到我家去,你老哥請你吃頓年夜飯。大侄子也一道去。」
這不是顛倒了嗎?周炳南答應也不好,不答應也不好。半晌才說:「不能呀,老哥,該我請你才是。怎麼你請我呢?」
「一樣。」周錫林馬上截住說,「同宗兄弟,一筆寫不出兩個周字,你來、我往,完全應該。今天你來了,明天我也上你家嘗嘗弟媳燒的菜味道。客氣什麼,總不成你怕我上門吃你的!」
周炳南是個忠厚老實人。儘管厚實到了他那把年紀,也能懂得點世故,聞出點氣味,但卻如身人囹圄的囚徒,無法擺脫鐐銬的束縛,一面唯唯諾諾跟著別人走,一面咒駡自己連推脫的話語都找不到。他原想最低限度應該讓兒子逃出這口羅網的,結果連這一點也不曾辦到,竟被錫林老哥揪住了不放。
「什麼話!你是嫌伯伯家燒得不好吃?不行,嘗也得嘗一嘗,不肯嘗也得進去坐一坐!你放心,伯伯家的凳子咬痛了你的屁股,都不用你出一分錢醫藥費,放心好了!」
父子倆像一對呆瓜,一個都沒走脫。其實一切顧慮都不必。幸虧被拉進去了,一進去,他們就肅然。客堂裡坐著六個人,除了周錫林的大兒子大媳婦以外,其餘四位都是父母官。官銜最小的就算周國平了。另外三位,因為平時在路上碰到了都膽怯,不敢招呼,他們見了周家父子進來,居然也含笑點頭打招呼,使周炳南父子的骨頭也加重了四兩,一抬腿,一舉手,只怕鬧笑話,都呆板了。心裡只是想著莫讓人家看不起。別的念頭都丟了。
這是一套絕妙的催眠術。華麗的堂屋,高貴的客人,精緻的餐具,豐盛的酒菜,使周炳南父子像兩個木偶一樣,被釘在桌子邊頭。周錫林非常熟悉這種精神狀態,他非常喜歡他們,他對於自己習慣了的虛偽早就找到了充足的辯護理由,想當然地把裝腔作勢當作真誠的感情。
「老弟我敬你一杯酒。」周錫林鄭重地站起來,舉杯向周炳南說,「來,來,你別客氣。今天我請的就是你,書記,主任,都是陪客。你一定要先飲一杯。老哥我這是向你做檢討,你飲下了,就算是肯原諒我。」
「老哥你……」
「憑道理講呢,我是欠缺了些。考慮不周全,沒想到你也不願意要田。早知道呢,也就算了,你又不肯說明。田拿過去了,種麥呢,不顯眼;一種樹哪,就起輿論了。不錯,是要有輿論,是你老哥虧待了你。」
「老哥,我可不是……」木偶被牽著說。
「我曉得,你不是有心要拆臺。是別人利用了這件事大做文章。我們兄弟倆不能讓別人鑽空子,我向你認個錯,那塊田你讓我收回,莫讓旁人說我欺了你。」
「老哥你……」
「老弟你只管相信,我都是說的真心話。書記、主任都在這裡,我是誠心誠意要挽回這影響。我原本沒有想在這裡邊圖謀什麼個人利益,何必讓別人說得那麼難聽,我吃點虧就是了,你讓我收回來。就是我沒空去種,荒掉一年賠幾十塊錢公糧,算不了什麼,兩個朋友上趟飯店就吃掉了。」
周錫林越說越有感情,越表現出無可懷疑的誠意,使周炳南忽然內愧起來,覺得自己也許從前真的把他看錯了,也許他真的不是想沾什麼光(實在無光可沾哪,又不曾拿他的錢),不過是省一點麻煩罷了,看來倒是自己用小人之心,度了君子之腹。想著這些,便期期艾艾地說:「老哥呀,你怎麼不早些說呢?我把樹都種上了哪!」
「沒有關係,我早替你想過了,決不讓你吃一點虧。你買樹苗花了多少錢?肥料花了多少錢?人工一共花了多少?你只管告訴我,我付給你。」
這真是考慮周到,公平交易,仁至義盡。兄弟之間,還能不答應嗎!
這時候,一直不敢開口的周炳南的兒子為難地說了一句話:「老伯伯,別的倒有帳,只是人工花了多少,誰還記得。」
「這個沒關係,大行大情,估得出來的。你請人估,估出來了我再加你一成。工錢呢,照採石廠的標準算給你。」
天,有這麼好的事情嗎?!都叫人不敢相信。
「唉,我是做了不妥當的事。」周錫林非常瞭解對方的心理,故意沉重地努了努書記、主任低聲說,「是我們內部不允許,有文件的,能不執行嗎?」
周炳南父子都哦了一聲,這才恍然。
「這件事辦好了,我也不會忘記你們的。大侄子,採石廠是件苦差事,你青年人在那兒,前途不大。我以後有機會,讓你轉到好一點的工廠去。」周錫林關心地說。又看看周炳南,「還有個女兒在家裡吧?幾歲了?一有機會我來安排她進廠。」
……
成功了。地球是照著周錫林的意志旋轉的。
周炳南植樹是挺認真的。春暖花開的時候,那三千棵樹苗幾乎都長出了綠葉。之後不久,灘南那一片土地,一共三十八畝四分,包括周錫林種了樹的二畝三分在內,都被國家一個大工廠徵用了。徵用單位付了村委會一筆徵用土地的款子,答應安排三十九名社員進廠做工。那些土地的包產戶得到了一年產值的賠償費,大家都覺得很滿意。周錫林言而有信,把應該歸他的兩個進廠當工人的名額讓給了周炳南的兒子和女兒。一度有過的誤解消除得乾乾淨淨,相互之間的感情十分親昵。
又過了幾個月,傳出了一些謠言,說周錫林那二畝三分田地裡的三千棵樹,是論棵讓徵用單位賠錢的,有說一棵賠五元,有說一棵賠十元,有說是二十、三十……
甚至五十的。議論紛紛,又掀起了如浪般洶湧的輿論。為此周錫林不得不闢謠,村主任周國平也說是謠言,不要相信。但對知己人則私底下說道:其實也只拿到十元一棵,也不是錫林一個人裝進去的。
這話很難說是真是假。
周炳南當然也聽到了,不免也起了疑心。怪不得這位老哥要把尾巴拿回去,大概當時已經知道有了出路。自己種的樹,倒他得了很大的好處,很覺得不平。轉念又想,這也是周錫林的能耐,倘若這田在自己手裡,也不會想到去敲國家的竹杠,這財不是他發得的。周錫林畢竟也做了好事,兒女兩個都得益。他周炳南不能貪得無厭,也該心滿意足了。
於是他心裡也坦然。不管怎樣,大家都是在好起來啊!好不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