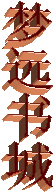
高曉聲文集
我的兩位鄰居
落筆寫我的兩個鄰居,很覺為難;總說遠親不如近鄰,一個人和鄰居的關係,實在忽視不得。相處得好,是很舒服的,倘若見面就礙眼,那就尷尬了。比如,清早起來,都是差不多時候去上班,往往你剛走出大門,他也正跨過門檻,如果相好,便會微微一笑,一個說「你早」,一個說「你好」,大家快樂,帶來整天高興,工作累些也不覺得,那效果賽過一碗參湯;如果相惡,就糟了,本來是吃完早點,和親愛的孩子媽貼了貼臉,鼻子上沾滿了香味兒,被柔情蜜意陶醉著,滿面春風跨出門來的,撲面碰著鄰居,驀地便如在冰天裡宿了一夜,一臉霜花,一個向東別頭顱,一個朝西扭脖頸,一件件陳賬宿怨湧上心頭,十億八千萬個細胞都像生錯了位置,渾身沒一塊地方舒服,精神受挫,身體受損,一年三百六十天,難得一天不是如此,誰能受得了?何況過了今年還有明年呢。
所以,我歷來主張,同鄰居應該和睦友好。我像汽車駕駛員一樣,堅決遵守
「寧等三分,不搶一秒」的交通規則,至今從未發生過「撞車」事件。有朝一天,居民委員會想到要評選睦鄰模範,我是大有希望的。但是,這次寫小說,我異想天開,要把倆個鄰居寫出來,真擔心會出點紕漏。從來寫小說,總要有褒貶;一褒一貶,會引出一喜一怒,一愛一恨,三家人家,鬧出兩派;儘管我篤定是在多數派一邊,心裡也不受用,萬一以後吵出事來,我就有「拉一家,打一家」的嫌疑。倒不如各各表揚一番,落個皆大歡喜。可是這也很難,古來論功行賞,也不曾有幾回做得公平,哪能就沒有意見了!說了東鄰十分好,西鄰好到九分半,那半分也能掀起風波。自然,全批滿分也可以,不過小說寫成那樣,便如一九七八年的獎金了。世界上的事情,難煞過多少皇帝,我一個握筆桿的,焉能做到八面玲瓏!拍馬嗎,也不容易,一拍沾上一身屁臭,自己因可以假裝聞不見,或者聞慣了不在乎,但在人群裡就難混了。有風的時候還好,只有下風頭的人聞著了罵,一旦風停,四面八方就都會罵過來,豈不成了過街老鼠!所以此路也是不通的。怎麼辦呢?我不禁又想起從前的皇帝來,他們到了沒有辦法的時候,索性面孔一板,各打五百個屁股,不怕你不伏地謝恩,三呼萬歲。這是我能做得的嗎?
千難萬難,真是寫鄰居最難,左思右想,還是三十六著,不寫為上著。因此,兩年多來,一直未敢動筆。
最近,我的東鄰方鐵正同志不幸病故,哀傷之餘,我的心又萌動起來,為了紀念他,忍不住不寫了。但這種情緒,必然會使我過譽老方而疏慢西鄰的劉長春同志。老劉呀,這可要請你原諒了。人類的感情總傾向于懷念死者的好處,一個人的缺點隨著死的到來會被寬恕,一個追悼會上總免不了看到同死者生前相惡的人,由此可知死對人們感情的變化起著多麼偉大的作用!而你和我,確實是老方的好朋友,我們同過患難,經常互相幫助,都為友誼建樹過功勳。為了他的過世,我們至今還沉浸在悲痛之中,即使我們發生了不愉快,我們也有充分諒解的基礎。這次老方同我們永別,我們已清楚地看到了死神把手伸進我們裡邊來了,我們不能不想到自己也總有那麼一天。如果我今天對你的稱讚j比老方遜色,便覺得不樂;那麼,我鄭重保證,只要我能死在你後頭。我一定有機會像稱讚老方一樣稱讚你的。如果倒過來,要勞駕你參加追悼我的會,那也幸甚,像我上面說的那樣,你也只會叨念我的好處了。我充分理解我們都能夠顧全大局,所以我毫無後顧之憂。
一
我和我的鄰人——東鄰的方鐵正和西鄰的劉長春,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身體都搞垮了。那原因無非是挨了些無情棍,受了些窩囊氣。現在也不必再多說。一四人幫」粉碎以後,各種冤案、假案、錯案,逐步清理,平反昭雪,活著的恢復名譽,重新走上工作崗位;死了的也不虧待,都開追悼會。報紙上不斷登載這一類消息,在社會上的反響非常熱烈。老百姓受「惟送死,可以當大事」的影響極深,對忠臣的被害,雖然忿忿不平,但現在看到了大出殯,滿足於死後的榮耀,心中也就釋然了。對於追悼會上,偶然夾雜個對死者實有罪責的人,有時也會引起一番議論,但都寬宏大量,並不學「四人幫」的樣子,把他拎出來;認為他既然能在死者靈前同大家一起默哀,也是一種追悔的,表現。當然,有人也談到這可能是裝腔,而裝腔是牽涉到究竟算「光明正大」還是「陰謀詭計」這個原則的,未免放不下心,或有餘氣,或有餘悸;既而想到一個人終於不得不煞住氣焰,裝出「腔」來,又何妨看他今後如何把戲演下去,暫不計較也罷。人民總是樂觀的,對前途充滿信心,自古以來,壞人從來就有,一旦絕種,生活就顯得單調了;鱷魚、老虎,現在都要重點保護;最傑出的醫生,在癌細胞面前束手無策;最平庸的生物學家,卻高喊禁止破壞生態自然,你看這世界有多矛盾!壞人能夠存在,是因為有好人可以欺侮;好人能夠存在,是因為終於能不讓壞人得勢。你看,生活不就是這樣嗎。
我們三個人,都關心這種帶有運動勢頭的追悼會。有時一起閒聊,痛駡一頓
「四人幫」之後,便往往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要講一點心酸的話,開幾句苦楚的玩笑。有一次,劉長春長歎一聲說:「唉,十年『文化大革命』,想做的事情不曾能做,現在老羅,好時光錯過羅,身體垮成這個樣子,你們要替我開追悼會羅!」
我看著他紅潤的臉色,已經發胖的身體,比三年前年輕了十歲,正在返老還童,心裡十分羡慕,嘴裡卻說:「老劉,我們三人中,論年紀是你最大,按理你應該先死。你的兒女都成人了,自己也當過幾年(區房管所)主任,雖然『文化大革命』
中丟了官,例證明你同林彪、『四人幫』沒瓜葛,落得一身清白。無論從哪方面說,都不算虛度一生,人困難免一死,你我誰能破例,細想起來,的確還是你先死為順。」
我說罷,自己先笑。方鐵正睜大著近視眼,在鏡片後盯著我,那蒼白清瘦的臉,正兒八經,先張開嘴巴「哧」的一笑,然後又罵我說:「扯淡。」便抿緊了尖瘦的嘴,不再理睬。老劉聽罷,皺起眉頭,半閉著眼睛瞅住我,半惱半笑地說:「你看你,我一說死,你就巴我第一個,盡念咒語,再沒一句好話。」說罷,撫了撫臉,挺了挺胸,還做了個擴胸的動作,好像聽到了晦氣話,要為自己壯膽似的。
我笑得更甜了,連忙分辯說:「哪裡哪裡,原是你自己不好,要我們參加你的追悼會,你不先死,這會我能有價嗎?我倒希望走在你們兩位前頭,免得為老朋友傷心掉淚。」
於是,老劉也跟著我笑了。但這笑,就像敲錯了琴鍵一樣,隨即戛然止住。因為我們都看到老方沒有笑,他啄著嘴,一臉不屑的神氣,分明在罵我們言不由衷。因為他明明知道我們最擔心的是他的身體,他是最可能走在我們前頭的。他看出我們故意回避不說,就生氣了。好像我們要瞞著他把狀元搶走似的。
這無聲的責備,逼得我和老劉互相使了個眼色,一時沉默了,後悔不該開這種黴氣的玩笑。起初,我們到並非有意,後來確實是存心不說他的。現在被他看穿,真覺得虧待了他,有點過意不去;好像只有贊成他第一個升天,才對得起他似的。
要在這種窘境中解脫出來,我是個低能兒,我竟說:「好,好,不說了,不說了。」這分明是廢話,本來就已經不再說了嘛!這更是蠢話,難道「不說」還要發表聲明嗎!
老劉畢竟當過主任,會做思想工作,他倒似乎認為我的話揭開了蓋子,便抓住戰機,直截了當攤牌了。他板著臉,又正經。又嚴肅地說:「老方。你確實應該當心,你看你的身體,一天天壞下去,叫你吃藥不吃,叫你休息不休息,叫你鍛煉不鍛煉,一天到夜還在狗一樣叫,貓一樣跳,你究竟還想不想活下去?這話我跟你說過多少遍了,你不聽,你要做頑固派;再不改,你的命就要頑固掉了,有好處嗎,唔?」
這些話,聽來狠得過分了,但卻明顯地是為了一個同志的生命擔憂,狠得越過分,就是越關心的表示。我自愧不如,我不能這樣做;我也很感動,我承認老劉對老方的感情確實勝我一籌。於是我連忙說:「是啊,老方,大家都很關心你啊(我不敢說『我很關心你』,真慚愧),你的身體,是要趕快修理修理,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只要活著,還怕沒有事情幹嗎!何必急得那樣子,像來不及了似的,白天忙了不算,還磨夜呢。」說到這裡,老方好像不耐煩了,簡單明白地插話道:
「我睡不著。」
我不甘心地說:「睡不著,就吃點安眠藥,總不能任它去,一個人有多少精神呢……」我還想說下去,忽然被老方睜大的眼睛盯得有點吃不消,好像他在責問我:
「你剛才聲明『不說了』,還嚕嗦什麼?」我連忙閉上了嘴。
這時候,老方才把眼睛望著別處,毫無表情地說:「我只想再活五年。」
「五年?」老劉大聲說,甚至站了起來:「你這個聰明人,給什麼迷住了心竅?你今年幾歲了?四十六,比我小八歲,難道連我這點年紀都不想活?孩子還小,老婆還年輕,你能死了嗎?」老劉說著,忽然憤怒起來:「『四人幫』要整死我們,我們都挺過來了,那時候,我們就是不死,要活著看到他們垮臺,這不是,他們垮了。告訴你一件真人真事,省委書記老周被關起來的時候,『四人幫』想害死他,又不敢下手,他們一面裝腔作勢,告誡他不許自殺,一面卻在關押他的房裡放了繩子、小刀、安眠藥、敵敵畏……誘他上鉤。可老周哪,就不上當。你想想,你還能……」
說到這裡,老劉忽然像想起一件大事似的,連忙看了看表,說:「總是為了你,又過了五分鐘了。」說罷轉身就走,還連連回頭說:「你想想,你捨得,我還捨不得你呢。」
我也看了看表,二十一點過五分,唔,不錯,老劉上床的時間是二十一點,真超過五分了,這是難得的、三四年來,老劉定了個作息時間表,執行得極嚴格,他的身體明顯地健康起來。唉,假使老方也能像他那樣,何至於叫人擔優呢!
老劉走了,我又不敢再講話,沉默了片刻,老方站了起來,一面走,一面咕嚕道:「我只想活五年。」
他一點也沒有聽我們的勸告。
二
我想著這兩位鄰居,當天夜裡竟失眠了。
這兩個人,都是強脾氣,從來不聽勸。各人還自以為是,要求對方聽話,真是怪極了。更奇怪的是,他們不但不抱成見,反而很合得來似的,一向互相關心,互相照顧。為了老方的健康,老劉一再勸他像自己一樣,有計劃地進行持久的體育鍛煉,要他早晨起來跑步,下午打太極拳,晚上做氣功,並且把買來的有關資料送給老方。老方不聽。老劉不灰心,有一次便請人從吉林買到一斤人參,他按原價讓半斤給老方,老方不要,他就送了兩支。到下一年過了梅雨天,竟發現都黴爛掉了。他把老方狠狠地罵了一頓,聲明從此不管他了。可是,有一次老方病重,一時住不進醫院,他卻千方百計走後門讓他住進去,而老方卻待不住,治療得稍有好轉就出院。老方呢,一貫主張老劉在落實了政策以後應該去上班,老劉至今不去,他說:
「這算落實的什麼政策,我本來是第一把手,被『四人幫』坑害了這些年,反倒叫我去當第二把手,我咽不下這口氣。」老方就說:「第一也好,第二也好,不都是為人民服務嗎?」老劉大笑道:「你們知識分子就是呆,也難怪,沒有當過頭頭,不懂。第一和第二,相差十萬八千里呢。」老方不贊成說:「你是受過『四人幫』
害的人,竟也會沾上『權迷』的習氣。」老劉不滿道:「不是我去奪人家的權,是我的權被別人奪了,不還給我,我就不上班,我是受害者。現在降職使用,倒像是犯了錯誤,這不是顛倒了嗎!」老方也不滿說:「就算你有理,人民總沒有虧待你,不做事,白吃人民的,總說不過去。」老劉一揮手說:「算了,你是個迂夫子,同人民的賬,也不是一天兩天結算的,死下來總算吧。我身體不好,現在就鍛煉鍛煉,這不是為了將來更好地為人民服務嗎。」講來講去,就是這樣。老劉不但不去上班,反過來倒要老方代他起草遞給組織上的報告,老方也居然會答應,兩個人常在一起,細談情況,斟字酌句,花掉不少時間。這種報告前後打過幾次,老方白天沒有空,都是熬夜寫出來的。更動人的是老劉的兒子,功課本來極差,七七年高考低於分數線很多,後來跟著老方補習,七八年竟考取了大學。現在,老劉的女兒,又幾乎每天晚上都拿了課本上老方家去,老方也從不厭煩。我在旁邊看了,著實感動,又覺得老方耗費的精力太多,實在有點替老劉說不過去;也難怪老劉會對老方如此情重。說到根上,總是既然住在一起,不會沒有這些往來,也說不上誰沾了光,誰吃了虧,反正是為大家好。都值得稱讚。
但是,老劉畢竟是很會照顧自己的人,不僅用不著我擔心,倒是更值得我羡慕。我的身體,本來比他強,由於他堅持體育鍛煉,我竟不如他了。確實,我們是很聰明的,終於找到了延年益壽的最好辦法。參加體育鍛煉的人越來越多了,在我家門前的廣場上,每天從清晨三四點鐘開始,就開始有各種各樣的跑步聲。青年人最有雄心壯志,他們豈止為了健康,還力爭當出色的運動員;中年人就不同了,無非是為了加強抵抗力,保住朝氣而已;至於老年人,生活在這樣美好的時代,實在不忍離去,也參加了這個行列,因為即使做不動什麼,活動活動筋骨也是好的。我深深被這種精神所吸引,所感動,覺得個人的身體也是革命的本錢,實在無權玩忽,也常想參加到鍛煉的隊伍裡去;有時候真的做了,但總是一天捉魚,十天曬網,堅持不下去,而且起得過早,鍛煉得過分一點,反而早飯以後想睡覺,上班也差勁,人家笑我煉的不得法,而我則模模糊糊地想到鍛煉也要具備條件,我一天到夜很忙,體力消耗得多,本來就累了,再鍛煉豈不更累。但又怕別人誤會這理由是為自己意志薄弱辯護,自然不說出來。
可是,老方是腦力勞動者,意志又堅強,身體這樣差,為什麼不肯聽老劉的話呢,鍛煉鍛煉,對健康應該有好處啊!他是我們之中最年輕最有作為的一個,如果這樣下去,豈不糟糕!想起來,老方的經歷,也真叫人感歎,他四九年就參加黨的地下組織,解放後就在黨委部門工作;五七年反右後,就調到中學裡去教語文。他是個腳踏實地、埋頭苦幹的人,工作幹得很出色,但從未受過表揚,他也從不計較。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紅衛兵翻他的檔案材料,才查出五七年調來中學的原因在於思想嚴重右傾,有同情右派的言論。這樣重大的政治結論,他竟像被蒙在鼓裡。這時候別有用心的人,就抓住這一點,說他是內定右派。他當然不承認。他性格本來就強,竟硬頂起來,於是從靈魂到肉體,被鬥得七葷八素。從此竟一蹶不振。起初還堅持勞改,在學校裡打雜,從掃廁所到拉板車都幹;後來躺倒了,又被認為是裝死,罰他站在冰天雪地裡請罪,一直到失去知覺。之後便常發氣喘病,不久又查出心臟不大好,自然是肺心病了。他又不懂得肺心病的厲害,平生也不曾學會照顧自己,一旦讓他工作,他又拼命地幹,發病的時候,喘得躺不下去,就乾脆備課或批作業,往往幾乎整夜不睡,看了真叫人心痛。近兩年來,精神上愉快了,更是不要命地幹。我有時半夜起來解手,總見他房裡的燈還亮著,湊進玻璃窗一看,他還在埋頭批作業,喉管裡「嘰兒嘰兒」的喘聲,竟響出窗外來。我憐惜地說:「老方呀,你不要命啦,還不休息!」他便說:「快好了,就睡就睡。」卻不動身。我看不過,有時推門進去(他從不閂門,愛人在鄰縣做婦女工作,難得回家),合掉作文本不讓批。他忙揪住,笑著說:「你看你看,這個學生想得有趣,但不會寫。」
我當然不肯上當,乾脆滅了檯燈。他拗不過我,歎一口氣,坐到床上去說:「睡,睡。」然後又咳嗽,喘著說:「這些學生,都快高中畢業了,作文還寫不順,錯別字好多,他們同我們一樣錯過了光陰,再不抓緊些,將來怎麼辦?」我非常感動,功道:「你也要替自己想想,身體再垮下去,怎麼辦?」
我的話完全沒有用。他不但沒有改,從去年十二月,他那「內定右派」錯案得到改正以後,整個寒假,他幾乎門檻不出,成日成夜伏在桌子上寫著寫著。問他在幹什麼,他起初靦腆著不肯說,後來才告訴我,他在寫一本反映學校生活的小說,他要用自己的體驗去感動學生,他要讓學生充分認識到自己的責任,他要推動學校的工作更好地為四化服務。我又高興又憂慮,說:「好雖好,你吃得消嗎,該量力而行啊!」他笑著說:「勁道上來了,倒放不下手;這小說一動手寫,就像發了神經病,旁的事都想不進去,腦子裡想的盡是這事兒,夢也做著它。」我說:「這可糟了,你還是不要寫吧。」他搖搖頭說:「已經上了馬,總要跑到頭才能歇了,否則,就是手停了,心也停不住。」
寒假過去,他顯然又瘦了不少,但那時候穿了棉衣,還沒有徹底暴露出來,只是更像老頭子了,佝僂著背,腳步拖遝,右手時時按在下肋骨處,好象那裡生疼。天一熱,脫棉換單,使人大吃一驚,他真是皮包骨頭了。他卻開玩笑說:「這裡邊也有學問,課文裡有『精瘦』這個詞;什麼叫『精瘦』,以前我只會解釋成『瘦極了』;可是,『瘦』到什麼程度才算『極了』呢?總還不懂,現在可明白了:只要用手指按住肋骨推皮膚,若推得動,那還不算『精瘦』,要真正推不動,皮貼牢在骨頭上,夾層裡不再有一點肉,才叫『瘦極了』。」說罷,竟開朗地哈哈大笑。我也算是個樂天派,也想說幾句俏皮話,竟幹了嗓子,講不出聲音來。……
想到這些,我怎能入睡。睜眼看看,他的房裡仍亮著電燈。我躺不住了,穿衣下床,悄悄走近他的窗口。我看見他伏在桌上,正在全神貫注地用筆指點著一篇作文,向站在桌邊的老劉的小女兒講解。不知為什麼,我竟留淚不住,心裡又酸又甜,又愛又怨,又苦又痛,不辨所以了……
三
一個人,像老方那樣夜以繼日地勞累,即使有強健的身體也是不能持久的。我和老劉都十分後悔沒有能及時把他阻止住。
實在說來,我們還不夠關心,也不完全懂,存在著盲目的僥倖心理。一天過去了,老方好像和昨天差不多;十天過去了,老方好像還是那個樣子;一個月過去了,老方也並沒有躺下來。於是就認為大概還不要緊吧,有意無意之間就讓他一天又一天地拖下去,姑且看看再說。我們好像在做著一種試驗,試試一個人的生命力能頑強到什麼程度,究竟具有多大的戰勝疾病的能力,究竟死亡怎樣才能夠靠近這個堅強人物的身體。……我現在不得不承認我是這樣的殘酷!我枉為老方的老鄰居,幾十年親密的接近竟不曾使我認清他的品格;我竟沒有想到這個人從來沒有叫過苦,從來沒有在困難面前低過頭。他從來就是甘願燒盡自己的油脂、照亮別人的火燭,從來就是慷慨剖開自己胸膛,提供甘泉的甜瓜。我早就不應該指望他會向病魔屈服,早就不應該認為他有一天會喊吃不消而躺倒。……我們總是容易關心那些有一點病痛就大喊大叫的怕死鬼,而忽略了甘為人民赴湯蹈火的英雄好漢的生命。我們為什麼這樣愚蠢!
老方在寒假裡寫的小說,三月裡在全國性的文學刊物上發表了,評論家還寫文章,稱讚他寫得好。我們這個小縣城,立刻轟動起來。大家議論紛紛,猜測小說裡的那些人物,是指實際上生活裡的哪個、哪個,甚至還來向老方討謎底。學校裡更加熱鬧。那些被猜成正面人物原型的,心情舒暢,十分有勁,拼命要做出更大貢獻,好讓老方再寫一篇。少數幾個被懷疑是犯有官僚主義或對教學工作不負責任的模特兒的,不免暗暗鬧了一陣情緒,深怪老方出他們的洋相,過後想想,大都能夠覺悟,有所悔改。只有極個別的人,竟懷恨在心,盼望第二次反右,好把老方打下去。還有一些人,雖然自己身上明明也有小說裡指出的那些毛病,卻連聲稱讚老方寫得好,說那種人確實應該批評,否則就妨礙四化,自己卻偏偏不改。這種人大概也是受了
「文化大革命」的影響,早就練老了臉皮,或者是長期被觸靈魂把靈魂觸僵了。這些都瞞不過學生的眼睛,都是他們告訴老方的,後來老方又把這話告訴我和老劉,並且謙遜地說:「總還是我技巧不夠,熱情不熾,不曾能夠感動這些上帝。」
總之,老方成了人所共知的作家。內容儘管有爭論,文字功夫卻無人不說好。學生像一群蜜蜂似的繞著他,他教的又是畢業班,誰都知道現在考大學有多緊張,認准了好老師,個個都希望多受點指導。所以,每到晚上,穿梭似的上他家來,拿出作文請他面批。他們總是把他團團圍住,就像是繭皮困住了蠶蛹,顧不上這蠶蛹快要把絲吐盡了。他強喘著氣,耐心地講解,有時還發出帶喘的「呼哧,呼哧」的笑聲。……就這樣一天一天忙碌著,一直到把這批學生送去考完大學。他看來一直很興奮,臉色常常發紅,眼光很亮,好像腰板也挺直了一點。我和老劉都暗暗驚奇,覺得生命實在偉大,實在神秘,以為奇妙的精神力量會使他在千錘百煉中健康起來,我們忘記了他的軀殼也是物質,忘記了任何物質承擔壓力都不能超過限度。誰都體會不到那個時期疾病究竟怎樣在折磨著他,他又用怎樣巨大的毅力同病魔抗爭。
高考揭曉,他教過的兩班學生,語文成績沒有一個不及格,平均分數是全專區最高的。老劉的小女兒,也考取了大學。這些消息,就像是一支支強心針注射進老方的身體裡,使他有可能作最後的一躍,暑假以後,他毫不猶豫地又登上了講壇。
終於有一天,他像一張硬弓的弦,鏗鏘一聲繃斷了。
那天早晨,我去上班,像往常一樣,他也走出門來。打過招呼,我就見他身子微微一顫,咳了幾聲。我以為是今早上比昨天稍稍冷了一點,並未引起特別注意。我們還同走了一小段路。街邊的梧桐,落葉增多了,但街心花園的菊花,卻正盛開。我們就在那裡分別,這時一天晴朗,陽光已經照到樹頭,高空裡飛過幾隻鴿子,響起一派輕淡縹緲的哨聲,老方抬頭看看,還微微笑了一笑,好像非常欣賞這美妙的天曲。這一天我非常愉快,因為工廠要新建一個車間,決定派我到外地去參觀同類工廠,收集參考資料。這是一次很好的學習機會,也可以見識見識外地的風光。下班後,我一路輕快走回來,一進院門,就覺得有些異樣,三家人家,寂靜無聲,不見一個人影、喊了幾聲,無人答應。突然,老劉流著眼淚出現在我的面前,嗚咽著說:「老方死了。」
我頓時如遭天打雷劈般呆住,似乎大叫了一聲「怎麼會呢?」其實這句話並沒有說出來。
「已經送殯儀館了。」老劉接著說:「我們兩家的人,都在幫忙。」
我一頭沖進老方的房間,好像偏要在這兒再找到他似的。……我像撲進了大海,被波濤顛簸得搖晃起來。我支撐在一張椅背上,眼淚無聲地嘩嘩直淌。
我立刻想起了老方一年前說過的那句話:「我只想再活五年。」我覺得我們真傻,當時竟一個人也沒有聽懂,他這不是明明白白告訴我們,他已經活不到五年了嗎!可我們……我們真傻呀!
我抬起淚眼,看看老劉。老劉站在台前,正聚精會神地看著臺上的幾張紙,臉色非常難看。我不禁也伸頭去看,很快就弄明白,那是老劉請老方代筆卻還沒有寫完的一份申訴書(據我曉得,這已經是第六次申訴了)。我不禁想起昨天晚上的燈光,這應該是老方最後的筆跡。
當時我確實沒去想別的。但是,老劉忽然像女人一樣大聲地哭起來,我驚異地呆望著他,因為從未見過他這種樣子。我這種態度不知道觸動了他哪一根心弦,他竟哭哭啼啼朝著我喊道:「我要把兒子、女兒都叫回來參加追悼會!我要把兒子、女兒都叫回來!……」
…………
為了替老方治喪,我請了三天假,開過追悼會以後,領導上就催我趕快出差。
我隔天買好了早晨六點鐘的火車票,打算五點起身,吃點東西動身。這樣時間也很充裕。
這天清晨,我按時起身了。孩子媽也被吵醒過來,她睜眼看了看表,就說: 「還早呢,才四點鐘。」
我連忙再看看,果然只四點。不禁苦笑一聲,覺得自己這幾天真有點昏頭昏腦。但既然已經穿好衣服,也就不想再睡。嗽洗完後,打開爐子燒早飯。坐著無事,就走出門來呼吸點新鮮空氣。深秋的早晨,氣候已經涼了,穿著絨線衣,仍覺單薄。這時天色濃黑,門前廣場四周有幾盞路燈,透過梧桐枝葉,一線線射到廣場上,明暗相間,有一二十個人,已經在那裡鍛煉身體,有的跑步,有的打拳。我真自愧不如,又一次想起了老方,便更羡慕這些強健的人了。
我一面深呼吸,一面信步走去。我看到近處梧桐樹下,有一個人在原地跑步,上身一件汗背心,下面一條短褲頭,氣喘吁吁,一線燈光照在他的臉頰上,看出那晶亮的汗珠,如雨點般滾落下來。我欽佩得五體投地,不由得再靠近去細細欣賞這位傑出的鍛煉者的神態,我很快就發覺他竟是老劉。
這時候,我心頭驀地湧起一股非常厭惡的情緒,幾十年來我第一次失禮了,竟不曾招呼他就迅速回身走開。我憤怒,我憎惡,我頓時背叛了我一貫稱羨的東西,我詛咒這種鍛煉!當時我的神經顯然出了毛病,我竟辨不清什麼叫生,什麼叫死,不知道我的兩位鄰居,活在世上的究竟是老劉還是老方。我強制自己不再想下去,以免真的發起瘋來。
1979.11.8——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