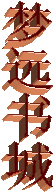
高曉聲文集 陳奐生包產
一
採購員陳奐生,首次出馬,便大獲全勝,班師還朝,也不虧是一員福將了。人貴有自知之明,他在回來的火車上,就已經曉得採購員這飯碗不是他端得長久的,應該適可而止,功成身退,仍舊去幹那種田、賣油繩的老本行。這主意原是打定了的,但回來之後,出乎意外,一次竟拿到了六百元的獎金。他高興之餘,總感到不自在。覺得這麼容易得來的錢,多少有點不正路。現在沒有人說什麼,將來政策一變,說聲「退賠」,你陳奐生就逃不脫。「文化大革命」的樣子還沒看見過嗎!弄不好還要害吳書記呢。將來打倒吳書記,就會從你這條藤藤摸上去。還是趕快洗手不幹妥當。但是鈔票的誘惑,也不是輕易能夠擺脫的。窮了大半輩子的陳奐生,難得碰上一個發財的機會,如果打錯了主意,放了過去,以後懊悔都來不及。這樣的大事,是不能隨便甩手的。加上老婆也像扭股糖似的纏著他,一個勁兒慫恿他幹下去,活著也好享點福。所以,陳奐生便像蚊子粘在蛛網上,掙扎著想飛,可飛來飛去飛不脫。廠長、書記又不斷鼓動他。因為吳書記那裡,原來是兩扇鐵門關得嚴嚴的,如今好容易靠陳奐生去擠開一條縫,正要靠他繼續努力把門打開(最好是把門都掮下來,做到夜不閉戶),工廠才能大發展。所以,對陳奐生十分照顧,說他立了大功,辛苦了,叫他回家休息休息,橫豎目前沒有任務。又教育他不要以為拿了六百元錢就發了大財,可以用一生了。愜意日子還在後頭呢!六百元算得什麼,夠造房子還是夠買彩色電視機!你兒子也十五六歲了,眼睛一霎就要娶媳婦了,你能拿得出什麼來?想做公公,還要出把力呢!現在這好機會,赤了腳也找不到。奐生呀奐生,你是個四十九歲頂在頭上的人了,為什麼一直生活不及別人好過?你懶嗎?浪吃浪用嗎?還不是因為你太笨,腦子不靈巧,不會打算盤!?現在總算走上正路了,你倒還想打退堂鼓!
陳奐生被訓了一頓,回頭想想,人家也是一番好意。看來,這件事只好拖一拖再說了。陳奐生做夢也沒有想到,自己竟被一些人當成了香狸貓的卵子,被一個勁兒吹捧起來。不但在本大隊被說得神乎其神,公社的主交辦公室也大會小會表揚他,那主管工業的李書記還特地接見他,談了幾個小時的話,央他細細地把吳楚書記如何招待他,吳書記家中的情形等等講來聽。連公社的頭把手趙書記,見了他都笑呵呵地主動打招呼。陳奐生上一趟街,來回路上同他搭腔的人就數不清。陳奐生上街回到村裡,別人也不再問他「今天街上怎麼樣?」他也不再說「人擠,豬行裡有豬,青菜賣不掉。」等一類的話。卻一問一答講些:「去工交辦公室沒有?」「去的。」
「見到趙書記沒有?」「趙書記不在。」「下次碰著了,那件事請你同他講講。」
「好的。」……等等。有人還惋惜陳奐生出山遲了一年,否則穩選上鄉人民代表。有一次,趙書記要廣播員王小蓉在廣播裡通知在鄉下蹲點的副書記張和生回公杜開緊急會議。當時她正在聽人家講陳奐生的業績,回身進去,對著話筒反復講了三次要陳奐生迅速來公社開緊急會議,而竟沒有發覺錯誤。一直到陳奐生暈頭轉向趕來,她還莫名其妙。幸而張和生恰巧回來,才沒有耽誤工作。可見在王小蓉的腦子裡,陳奐生竟把張和生趕跑了。廣播的時候,群眾正捧著飯碗在填肚子,大家聽得清清楚楚,簡直就轟動了。全公社果真形成了「陳奐生熱」。陳奐生的腦殼子並未經過冷處理,於是也就有點發熱了,有點飄飄然了。在家裡不大肯做事,一天三餐,要老婆端到桌上來吃。擺起家主公的架子來。隊長王生髮,是個見錢眼紅的人,尤其看不得社員發財。他不管陳奐生有多紅,橫豎還是他手下的社員,強不到哪裡去。一再放出話來,要陳奐生表示表示。陳奐生心裡雖然不滿,也只得請了他一次客,才算安穩。盯著陳奐生錢包的人,也不止一個,試探著想開口借錢的人,不斷放出風來。陳奐生幾乎失了主意,倒還是老婆厲害,常常在大庭廣眾之間,罵丈夫沒有算計,手裡有幾個臭錢,就東借西借,躉檔打成零碎,要買磚頭修房子都湊不全,才把別人的口塞住。但是,到了年底,陳奐生的堂兄,小學教師陳正清,還是跑來開口。因為他家缺乏勞動力,負擔又重,掙幾個工資,生活已夠清苦了。沒想到今年縣裡規定口糧提價,要照國家收購的糧價付。他原來準備的錢就不夠了,還缺六十元,口糧還押在生產隊的倉庫裡,不得不借。陳奐生一直同他要好,念著兄弟之情,不顧老婆嘰咕,滿足了他。就在這個時候,公社裡又掀起一個浪潮,要搞生產責任制,陳奐生知道了,不免又擔心起來。
陳奐生早就聽說過農村裡要起大變化,怎麼變法搞不清。幹部也不宣傳,問問他們,他們眼一瞪說:「把田分給你自己種,你要不要?」那神態和口氣,就像他們的腰包被動了一動,正要查扒手呢!陳奐生看著聽著就難受。他雖然笨,也曉得共產黨歷來主張集體化。土地、土地,種了幾十年田的莊稼人充分懂得它的好處;為它喜,為它愁,為它笑來為它哭,它是社員心頭一塊肉。哪個不想把它抱在懷裡困覺。好容易經過二十幾個年頭,才勉強斷了私情。雖然有時候看著它受糟蹋,弄得肚子吃不飽,心裡又會枯並重波。但單幹就是反對共產黨,陳奐生餓死也不會唱這對臺戲。他已經考驗過來了,何必吹鬍子瞪眼睛!這樣大的事情,能開玩笑嗎?聽到謠言,問個清楚不應該嗎?不該問,不問就是了。分也罷,不分也罷,橫豎他又不作主。真要分的話,他也不會第一個伸手接,也不怕少了他一份。他要想那麼遠做什麼。狗捉老鼠,多管閒事!這兩年吃飽了肚皮,穿暖了衣,安穩日腳不過,找什麼麻煩!分了就鑿定好到哪裡去嗎?!弄不好會煩死,壽也要矮幾年!陳奐生從此把它丟在腦後。一動不如一靜,捏牢鋤頭柄就算。過一陣又聽說真要分田。而且是中央的政策,要社員包種生產隊的土地,讓社員有更多的自主權,有更大的積極性。陳奐生倒犯愁了。他想,這田叫我如何包法?記得二十歲前,那時單幹,倒也獨當過一面。後來集體化了,自己一直吃的蔭下飯;隊長指東就東,隊長叫西就西,跟著他的屁股轉了二十八年了。自己只管做就是。至於各種稻、麥品種的特性,栽培技術,不同性能的化肥、農藥的使用方法,要說心裡有譜,也都搞亂了弄不清。一年兩熟,弄錯了收不著,又不能重來,吃西北風!還有那種田家什,在隊裡勞動呢,十樣缺八樣也不礙。隊長把工種派給你,你沒有家什,就改派別樣,工分照樣賺。如今夫妻兩個,家裡只有鐮刀兩把,鋤頭一把,鐵囗一把,罱網一口,鐵鍁一把,扁擔一條,土筐一副。碰到下雨,只有笠帽,沒有蓑衣,也照樣一年一年混過去。若要一變,還得了!光是禾場上用的,就有翻耙、掃帚、丫槍、搔耙、大小備箕、籮筐、小扁,……買一半也要幾十塊,哪裡來的錢!還是大呼隆隆,混混算了,橫豎大家的事,我又不想過好日腳。何必另起爐灶,既沒有本錢,也煩不來那種心思。他把這想法,說給老婆聽,這位賢德的夫人,一口贊成。還說她上次回娘家,娘家村上東邊的生產隊,就在鬧分田。出頭的人盡是些「尖鑽貨」,只想自己發財。最後還撂上一句:「你看好了!他們『想發財,必倒黴!』」她真是陳奐生貼心的好同志,無愧是困在一頭十多年的人。
陳奐生擔心了一陣,後來只聽雷聲響,不見雨下來;一忽兒又說要收了,接著又有叫做「不要一刀切」的話。陳奐生雖笨,也琢磨出幹部不贊成,頂住了。陳奐生這才放心。他覺得好,中央在北京,天高皇帝遠,管不著。只要幹部不動,蔭下飯照吃。
這已是將近一年前的話了。後來陳奐生忙著賣油繩,早就丟光忘記。誰知如今當了採購員凱旋榮歸不久,「陳奐生熱」還未過去,忽然異軍突起,全公社熱火朝天地宣傳起包產責任制來。原來他老婆娘家村上的東頭生產隊,包產一年大增產,不僅是幾個「尖鑽貨」突破了歷史上最高產量,百分之九十三的人都大幅度增加了收入。全公社的幹部群眾都轟動起來,原來反對的人也只得服貼。可是陳奐生一打聽,那百分之三減產和百分之四平產的戶頭,竟有兩家和自己的人品、條件差不多,於是他的心頭頓時沉重起來,好像擱上了一塊磨盤大的疙瘩。
那就難啦!要是不當採購員,到明年年底,不就歸進那百分之七裡頭去了嗎!
二
公社裡雖然出了一個包產責任制的好榜樣,但等到大家曉得,秋種早已過去,麥田都加工了兩遍。這時再分田包產,本無不可。但陳奐生生產隊的那個工隊長,主張要包就該在下種之前,如今種上了,麥苗出得好壞不等,分著好的沒話說,至於壞的,哪個肯舔屁股?再說已經花的工,下的肥料,沒法算帳,還是拖到麥收以後包產為宜。陳奐生聽了,十分贊成。可是急著要分的人不同意,不管陳奐生紅到什麼程度,人家搶白他說:「你倒靠著吳楚,撈得到外快;我們呢,就別想過好日子了!」陳奐生馬上吃癟,無話可答。他們又同王隊長吵起來。王隊長罵他們是
「尖鑽貨」,想發財想得等不及了,不死有得發呢。別人也罵王隊長「尖鑽貸」,多吃多占慣了,捨不得變。鬧來鬧去,沒有結果,便告到大隊裡去。陳奐生很放心,他知道大隊周書記也是反對包產的。記得兩個月前,周書記動員他出山當採購員,就曾在他思想上打過防疫針。周書記說:「你別賴在家裡等分田,那是劉少奇路線(天曉得,那時少奇同志已經平反過了),要弄得富的愈富,窮的愈窮,兩極分化。像你這種胚子,弄得過那班『尖鑽貨』嗎?」
想不到過了一天,周書記就到隊裡來開會,一出口就表示贊成包產責任制,而且支持大家積極去搞。這可叫陳奐生大吃一驚。接下去周書記才談到這個工作不容易做,要充分醞釀,做好準備工作,確實需有一段時間。只希望在麥收以前,把包產任務落實到戶,就可以了。這和王隊長的意見相同。陳奐生這才覺得周書記仍是周書記,又放下心來。
誰知會議結束之後,周書記便拉了工隊長到陳奐生家來交換意見。這就是有心同陳奐生表示親昵了。因為通常應該是到工隊長家去坐的,現在移到陳家來,說明在周書記眼裡,把陳奐生看得比王隊長還重。這種榮耀,就連奐生的志同道合的老婆都感覺到了,高興得連忙抹桌子、掃地、燒開水。
兩個幹部交換意見,想不到竟也頂起牛來。陳奐生這時才明白周書記確實變了。他很嚴肅地指出,。包產責任制是中央的政策,一定要搞。麥收以前一定要做好這個工作,不能藉口麥收以後再包產就把準備工作拖下去,弄得夏種又包不成。王隊長反問他:「什麼叫『不要一刀切』?」周書記說:「要看社員願意不願意,社員要搞,就該搞。」王隊長吵嚷道:「周書記,這『一把刀』究竟捏在誰手裡?捏著刀把子去切什麼人?以前你不贊成包產,就說『不耍一刀切』,頂住上面,這刀把子是你捏的。現在你頂不住了,就把刀把子交給社員來切我,我是刀砧板上的肉嗎?那就切吧!」
王隊長一吵,周書記倒笑了,說:「意氣用事。我幾時頂上面的?啥叫『頂不住』?人總是跟形勢走的嘛!不信你就一直這樣啦?」
工隊長氣咕咕地坐著不響。片刻,站起來說:「好了,不說了。你想得通的原由我也曉得,我想不通的原由你也曉得,還不就是那麼回事。」說罷,把頭一搖晃,走了。
陳奐生不曉得他們彼此互相曉得的是什麼,也不便問。王隊長走後,周書記也沒多坐,他關照陳奐生:「你看看你們生產隊,就是搞了包產,要上軌道還有幾年呢!橫豎現在不關你的事,你替我安穩點跑跑供銷吧!」說完,也就走了。
這兩個人,從前都罵過陳奐生「漏斗戶」,陳奐生也都憤慨過,現在都同他平起平坐了。「君子不念舊惡」,總還要念新惡的。陳奐生比君子更勝一籌,他連新惡也不大念,打了他之後馬上替他拍拍背,他立刻就不怨;罵他的時候只要態度好一點,他就認為你是好心,而不抱怨。所以他是個超級的君子。一個使勁拉他在工廠裡,心腸好得讓陳奐生有苦難言。假使真有能力把供銷幹下去的話,他肝膽塗地也要報知遇之恩。另一個雖然最近還敲過他的竹杠,但頂住不包產,使陳奐生真要不幹供銷時照樣有大鍋飯吃,這交情也就不淺了。
果然,書記、隊長沒講妥,王隊長屁股一拍,甩手不管。雖然有人著急,但如礱糠搓繩,起不出頭來。加上年關腳下,許多人都想收拾點農副產品,上自由市場去賣,撈點過年盤費,東竄西竄很忙;至於娶親嫁女的人家,置備喜事用品,早就前門後門,搞得七葷八素,包產的準備工作,眼看也只好擱一陣再說。
陳奐生雖然心裡有個疙瘩,但他從來就不是擔得起憂愁的人,他若要擔憂愁,過去早就愁死了。他這個人碰到憂愁,擔著擔著就丟光了。「管它呢,船到橋下自然直!」「愁什麼,活著就快活點,誰曉得幾時死!」家裡沒得米下鍋,只要眼看田地還能種出糧食來,為什麼要發神經尋死!所以,陳奐生很快就把「疙瘩」挖出來當(米困)子給狗吃了。哈,你們看,八○年江南農村年底年初是什麼情景呀,豬滿圈,魚滿糖,咕咕呷呷是雞鴨,白白胖胖有兔羊,到時候都成了砧上肉。缸裡米酒沉清了,東鄰西合,三朋四友,碰在一塊,高興就吃,隨便那家都一樣。等到大年夜,還要紀念紀念祖宗,然後拆豬頭;小孩子東家西家亂竄,進廚房揀豬骨頭啃,到一家吃一家。家家燉酒,吃年夜飯,愛熱鬧的成年人又串門,一家家把酒吃過去。最後吃到蘿蔔湯,老年人輕鬆地舒口氣,總算無災無病,一年又活到了頭;做父母的輕輕敲著孩子的後腦勺,過門交代清楚:馬上又長一歲啦,乖點!等到炮仗一響,新年來到,一律穿新衣,戴新帽,著新鞋。路上的行人,來來往往如龍燈,東邊西邊團團轉,然後在親戚朋友家團團坐下吃年夜飯,講山海經……來回往復,日復一日,直到吃光了準備好的年菜。這時如果還有客來,那麼,有句老話,叫「新鮮(米困)子醃鹹肉」,只得從簡了。
這種熱烈豐盛的境況,雖然每年都有(只是程度不同),但陳奐生的家境能和大家融和一致的,還只是第三年。今年是在上乘了,有米、有肉、有酒、有新衣不算,枕頭邊還有一厚疊花花綠綠的鈔票,五百多塊。確實從未有過。陳奐生哪裡還愁得起來!他樂,還不止是這樣的樂,更有勁的是人家把他看成檯面上的人物了,請客的時候都要拉他去坐坐。陳奐生從不拿架子,一拉就去,這實實在在不是貪嘴(以前他就不肯去),倒是想到別人看得起他,不能不識抬舉。他從不曾因為別人捧他就真的以為自己了不起,倒是覺得人家把他捧錯了,有點誠惶誠恐。所以,別人拉了不去,就更對不起人家了。況且他也有力量回請,並不白吃。這樣一來,整個年底年初,陳奐生幾乎天天有肴饌吃,光自己家裡,就請了三次客,有一次書記、廠長都來了。有個老吃客,當面稱讚陳奐生的菜肴豐盛,肉有簸箕大,一塊就把人打倒了。周書記大笑說:「今年能這樣不錯了,明年就有細貨吃。」陳奐生沒聽懂,光知道是說的好話,開心得很。
這樣吃了一陣,陳奐生覺得很精神,睡覺脫衣服,撫撫身上的皮膚,比以前光滑。有一次在東屋山頭曬陽光,他堂兄陳正清坐在旁邊看他,看著看著就笑起來。陳奐生問他笑什麼,陳正清說:「從前有個張良,騎著紙鳶飄到女兒國。女兒國裡的人看他白白胖胖的,想殺來吃。張良說,我不胖,應該養胖了再吃我。人家問他養到什麼程度才算胖,張良說,要等肚臍眼凸出來。」說罷,戳戳陳奐生的肚子,問道:「凸出來沒有?」陳奐生這才覺得自己真的胖了。
真的胖了。陳奐生想起這一陣的生活,也頗得意。特別是小除夕那頓夜飯,是廠裡聚餐。乖乖,那個吃法:整雞、整鴨、整蹄、整魚,八大盤炒頭都是細貨,不識得名堂。陳奐生一面吃,一面想到過去社員請幹部吃東西,幹部去了,說起來就是歪風邪氣。其實社員哪裡辦得起這樣的肴撰!現在辦了工廠,才吃得更好呢。
說來也巧,酒酣耳熱之後,周書記講話也特別提到這一點。他說:「今年馬馬虎虎聚一聚算了。明年大家出點力,把廠辦好,有得吃呢。現在農業上包產了,我可以少管些,集中力量來辦廠。」接著重點突出,竟點了奐生的名:「奐生呀,現在就要看你的啦!」
陳奐生聽了,肩胛上頓時像被千斤重擔壓了一壓,幾乎叫出來……
等到吃完,陳奐生已經八分醉,腦子裡已經不能連續想什麼了。哪裡還把書記的話放在心上。
回到家裡,燈還點著,老婆已經睡在床上,見他歪歪斜斜走到床邊,乜眼瞪著他罵道:「醉了。少灌點!」陳奐生眯眼望望老婆,沒搭理她,順手一拉燈線,上床就睡了。
三
一九八○年雖然受自然災害的影響減了產,但是蘇南農村的氣氛卻新鮮而活躍。盲目的開河、築路、移山填海、平整土地,把房屋搬到一塊去建設「新農村」等等,都停下來了。社員們得到了休養生息的機會。同時,對黨的政策已有所瞭解,有了信任,對今後該怎麼辦已經明白了。這就使社員們膽大放心地各自根據自己的條件去種植,去飼養。去編織、去引進新的技術、去創造更多的財富。
精明的社員,在年底年初的走親訪友活動中,已經為全年的家庭副業畫好了藍圖,然後便忙碌地、很有信心地埋頭於去了。
陳奐生卻還不知道該怎麼辦。生產隊裡的農活不多,無非是鋤一次草,修理排水溝,輪班罱河泥,為秋種積肥,做不著工分,春天變得很空閒了。陳奐生沒有別的手藝,只能養些家畜家禽,也上城賣過幾次油繩,生意卻大不如前。車站上的小吃品種多了,挑擔賣小餛飩的、賣豆腐腦的、賣煮熟了的雞蛋的……比比皆是,很少人再買那吃了口於的油繩。這背時的活兒就不能於了。原來他不想再到廠裡去。年底裡廠長叫他休息,開了年他也沒有去。自己既然幹不了,就不要掛名揩油拿工資。後來看看不行,這樣下去沒出息。況且生產隊的包產責任制勢在必行,自己還拿不定主意,還是先在廠裡呆下去再說,橫豎眼下廠裡還有原料,暫時還不用出門採購。況且採購員也不光他一個,並不全靠他,可以拖一段時間。去了之後,其實也沒有事情做,他倒閉不住,儘量插手進去,什麼都幹,例如搬運、掃地、上街買零碎。心裡還老是忐忐忑忑,生怕有一天打發他去找吳書記。
開頭幾天,並不曾引起別人注意,後來廠長就找他談話了,說:「奐生,你來上什麼班!你是採購員,應該出去跑,跑著了貨,廠裡付獎金;跑不著,你的工資和出差費廠裡付。其他事情,有別人做。你做了,工資也不好開支的。」
陳奐生聽了,例說不出話來。廠長又說:「家裡安排安排好,還是去看看吳書記吧,要帶些什麼禮物去,只要你認定吳書記肯收,只管告訴我,給你帶去就是了。」
陳奐生也沒有回答,從此只好呆在家裡,想拖一拖再說。世界上的事情實在太複雜,陳奐生真是弄不懂。
儘管陳奐生不夠關心國家大事,但時代的新風依然不斷地吹進他的胸膛。自從
「文革」以來,大約有十年的光景。每到春天,總有一群群外省的農民流到這裡來,要求幫助他們一點糧食。那時候陳奐生自己肚餒,無法解囊,但同病相憐,總是打了稻草地鋪,留他們住,照顧是很周到的。七九、八○年,就不再有人來。陳奐生先例想著他們,後來也忘記了。現在他們又來了,不是因為饑餓,倒反帶了各種各樣的土產來這裡兜售。他們三三兩兩在村頭上轉遊,既賣這裡缺少的土產,又講他們近兩年來的變化。其中居然有過去住在奐生家裡的人,念著舊情,找上門來,送了奐生五斤花生。奐生留了他一宿兩餐,當天晚上談了半夜。原來他們那裡早已包產。那人興高彩烈,反反復複地說:「各人包種一份田,收多收少自己負責,你別想沾別人的光,別人也沾不著你的,哪個還能不起勁!這才真是多勞多得呢。不光多勞,還要多動腦筋。農民有了自主權,哪個不會種田!哪個不曉得學好經驗!哪個不想往好路上走!眼睛一眨,我們不就好起來了嗎!要在過去,就不行,光聽幹部指揮,明知不對也不能強,餓肚皮自己倒黴。有難同當倒也罷了,偏偏有些幹部靠手裡有權,手臂直伸,多吃多占,撈得結結實實,叫社員還有勁嗎?!現在他們撈不著了!」又說:「你們這裡怎麼還不包?幹部不肯嗎?社員倒甘心把虧吃下去?」
陳奐生聽了,不覺心動。疑疑惑惑問道:「這算不算資本主義道路呢?」
「當然不算。土地還是集體的,你又不去剝削別人,倒還把有些幹部的剝削行為堵塞了,才真是社會主義道路呢。」
從那以後,陳奐生心裡就常常盤算這件事。深更半夜,困不著覺,和老婆嘀嘀咕咕商量。老婆說:「分了田,你在廠裡,哪個來種?收不著要賠呢。」奐生說:
「這廠裡的飯,我看也吃不長。」「為什麼?」「吳書記……」「吳書記什麼?」
「你莫跟別人講。上次吳書記就說了,這碗飯不是我吃的。」「只要他肯開條子,你就只管定心。」「唉,吳書記說那話,意思就是叫我下次不要開口了。」
老婆聽了,也發慌起來說:「這頭剛開,倒又斬斷了。」接著嘴一噘,嘟囔道: 「吳書記也真是,他曉得你忠厚,就不肯再幫幫忙!」
陳奐生歎氣道:「現在都反走後門,他是個正派人,倒去開?」
「哼!」老婆癡不癡,呆不果,忽然說了句絕話:「關了後門,前門為啥不拿貨色出來賣?」
陳奐生不理她,自顧自說:「再去,我也說不出口。」
「我曉得你是知趣人。」老婆奚落他道,「肚子餓到不得過的時候,你也照樣開口借米的。現在臉皮倒嫩了。你跟他單個單說一說,就是求求他,也不礙。」嘿,別看這女人平時不響,枕頭邊有了錢,人就變得精明了。
「上次我也不曾在喇叭裡喊。」
「不喊?一個天下都曉得了。」
「說了他不答應呢?」
「也不算坍台!」
「白跑一趟,空著手回來,就坍台了。」
「坍什麼台?買不到也作興的。」
「人家會說我和吳書記的交情也不過如此。笑我!」
「由他去笑好了。又不是沒被人家笑過。」
「路一斷,廠裡還要我做啥?只好回來了。」
「做啥,你又不曾犯錯誤。」
「人家不要你,你老著臉皮挨在那裡。男子漢大丈夫,做得出嗎!」
「廠裡人也不都是採購員,你不能做別的事情嗎?」
「自說自話。」陳奐生被纏得懊惱起來:「你去做,你能幹。」
「我去好了。掃掃地總會的。」
爭來爭去,哪裡有結果。陳奐生只得獨自盤算。
就在這當口,陳奐生看見王隊長家裡常常請客。廠長來過,書記來過,就連廠裡幾個數得著的頭面人物,也都分別在隊長桌子上紅過面孔。真叫人猜不透是什麼原因。請客就該集中一次頭,分散了豈不多花錢,這就不像精明人幹出來的事。看來分明是有事情同他們個別商量。
想不到過了幾天,王生髮竟一臉掛笑來拉奐生吃酒。陳奐生吃過虧,料想黃鼠狼拜年,沒有好事,推託不去。誰知隊長拉住不放,說什麼「吃了你的,還要還還禮。」不由他不去,拉到家裡就倒酒。一頓吃下來,嘻嘻哈哈也不曾說什麼正經話。直到黃昏深了,送他出門時,王隊長才正經地說:「奐生,你幫幫我的忙!」
「幫啥忙?」
「我要到廠裡來。跟書記、廠長講過多次了,不答應。今天總算口氣裡有點鬆勁,趁熱打鐵,你也從旁幫我說幾句。」
陳奐生詫異道:「你不當隊長了?」
「再下去隊長還有啥當頭!」王隊長說。他自己一怔,知道失口了,想了想接下去道。「哪個社員還會聽隊長的話,生產不好管,將來減產了,倒要剋我。還是進廠安穩。」
這些話,往常陳奐生是聽不懂的,這一次心裡倒也有些明白。便說:「我說話有什麼用,又沒得權。」
「嗨,你現在是紅人,有用。反正你也別管,有用沒用不關你事,只要說了就算幫忙。剛才我也同書記把話說到底了。只要答應我進廠,我馬上積極把隊裡的包產工作搞完。否則我就拖,大不了辭職。就是辭職了,照往常的規矩,大隊裡也要安排我!」
說罷,王隊長做了一個手勢,表示務請關照的意思,這才送他出門。
陳奐生心裡著實震動了一下:「哎呀,這『尖鑽貨』連隊長都不要當,一定要鑽到廠裡來,他是看准了這是塊肥肉呢。」
四
春風馬蹄,又快又香;吃過了甜蜜的春酒,照例就應該各奔前程了。大隊工廠裡的另外兩名採購員,已經上了征途。陳奐生上班不能去,找吳書記又怕去;包產吧,一則吃著了甜食,捨不得丟脫那好差事;二則左思右想,拿生產隊社員的情況,挨家排戶,同自己比較,總覺得別人都比自己精明、能幹、條件好,會發上去,自己只會落在後頭。心中悶悶不樂,不想做事,躺著困大覺。
生產隊裡倒熱鬧起來,王隊長的勁頭忽然很高,成天嚷嚷,找大家討論包產的事。陳奐生心裡明白,一定是書記、廠長已經答應他進廠了。不由得更升起一股煩惱。幹部究竟是幹部,有辦法。要是自己買不到貨,不當採購員,想在廠裡做別的,恐怕就辦不到。這王生髮也做得絕,自己反包產,倒又起勁地叫別人包,真是屙了屎不打算擦屁股的人。不過他離開了生產隊,又是一樁好事。自己在廠裡,要和他共事,只怕還要當心呢。
這些思想,在陳奐生腦子裡兜來兜去直轉,轉不出名堂來。書記、隊長倒一趟趟又上門來了。
「奐生呀,悶在家裡做啥呀!」
「沒得事。」
「沒得事,那就收拾收拾出去吧!」
「哪裡去?」
「去看看吳書記呀!」
「看他又沒得事。」
「怎麼沒得事?要他批材料呀!」
陳奐生沉默了。半晌才說:「廠裡不是還有得做嗎。」
廠長連忙開導說:「你莫看現在廠裡有材料,工作是要趕在前頭的。否則,一脫空,生產停下來,大家要吃西北風。你的收入,也全靠搞到材料呀!快點,趁早動身。」
書記說:「你想,吳書記待你這麼好,你就要多跑跑。去了,幫他菜畦上做做,也是好的,莫顯得有事有人,無事無人。有了關係,也要靠自己去搞熱絡。」
勸了幾次,陳奐生還是不去,倒反說:「沒得事去做啥,我的嘴笨,又不會同人家熱絡。」
廠長勸道:「沒得關係,我曉得吳書記也不歡喜花言巧語的人。他歡喜勤快的人,你幫他種菜,這個主意很好,真是開了一個好頭。他歡喜你,你只要常去跑就是了。慣了,就會像自家人一樣。」
橫說,堅說,陳奐生還是不動身,但也被弄得愁死了。白天書記、廠長來說,晚上老婆還嘮叨,日夜不得安穩。幾天下來,頭裡昏沉沉,渾身沒得勁,真的病了。
他一病,廠長就軋出苗頭來了。一面關照赤腳醫生天天來看病,自己就對症下藥做思想工作。他打開天窗說亮話,說:「奐生呀,我也曉得你的難處。吳書記雖然對你好,但畢竟不是你的爹,不是你的舅,去一趟就求他一趟,你也開不出口,對嗎!」
「就是。」陳奐生感激地說。
廠長點點頭說:「我知道,你是個老實人,老實得沒法跟你說。你就不曉得,做採購員的工作,就靠一股韌勁。看准了,就要螞蝗叮螺螄;就是石頭,也要鑽它一條縫。你同吳書記的關係,若換了別人,早就搞得要啥有啥了。吳書記很明白,社、隊辦工廠,材料須有計劃供應,弄來弄去,總還是到公家的倉庫裡去挖出來;他若不批,我們工廠還是要尋別的路走。那麼,他又何必難為你,只要方便,還會不照顧你嗎!所以,你不要愁。我也不逼你,你病好了就去。到了那裡,你也不要就開口。吳書記問你來做啥?你就說:『沒有事情,來看看你的。』他心裡自然就有數,你不說,如果吳書記也不說,你也不要急,就在那裡住幾天,幫他做做家務,再回來。回來以後,過幾天再去。幾趟一跑,吳書記保險會幫你解決。因為他就是有心也急不來,要有了貨才能給你批呀!你看,這有什麼難!做事情就是要開竅,包你不會坍台。」
廠長這番話,真把傳統的世道人情,放在太君爐裡,煉得鏗鏘作響了。將來寫
「關係學」教科書,是要放在總綱裡面的。陳奐生聽了,一肚子疙瘩統統從肚門裡屙出來,果然藥到病除,十分輕快。
過了三天,陳奐生打扮就緒,決定去找吳書記。這三天中,真也花了一番心計。為了要帶點禮物去,夫妻兩個拿不定主意,連書記、廠長也都跑來精心策劃。他們都曉得,對吳書記,不能送洋,不能送好,不能進多。想來想去,還是只有送土產。土產送什麼?這裡是稻麥產區,春天裡青黃不接,自留地上也沒得東西。後來還是奐生想起吳書記下酒愛吃花生米,便把外省人送給他的那五斤花生拿出來剝光了殼,用塑料袋裝了帶走,既不顯眼,也討得吳書記喜歡。
出得門來,總覺得有點心虛,不免放慢腳步,停住而行。這也是他本性老實,不會改變的了。他包裡的那袋花生米,好像在作怪,沉重得就像壓在他的心上,氣也難透。只想著這番送禮,別有用心,已不光明磊落。少雖少,拎在手裡,卻像偷來的一樣,生怕人看見,左右不是味道。正在這時候,只聽那邊有人喊道:「奐生,你到哪裡去?」奐生竟一嚇,連包也落在地上。抬頭去看,原來走過小學校,是他堂兄陳正清在招呼他。
陳正清走近來,注視著他說:「怎麼這樣瘦,一場病生到這樣嗎!我聽說了,今天原打算來看你呢。你這樣子還出門嗎?」
「我去找吳書記。」陳奐生老實地說。
「吳書記。」陳正清盯著他說:「你還去開口?」
陳奐生忽然覺得委屈,心中有淚。忍一忍,摸出香煙來,兩人都點著了,便在路邊坐了下來。
陳正清看奐生像有話說,便等他開口。吸了半支香煙,奐生卻一言不發。陳正清就問了:「奐生呀,你見了吳書記,那六百塊錢的事,告不告訴他。」
陳奐生腦子裡表的一聲:「哎呀,倒沒有想著!」他答不出。
「說不說?」陳正清又問。
「該說不該說呢?」陳奐生反而討教起來。
「你不說,就是欺騙他。橫豎他也會曉得,瞞不過的。」
陳奐生點點頭說:「要跟他說。」
「好。」陳正清說:「你講了,他就要問你:『奐生呀,這趟你來,打算回去再拿多少獎金呀?』你怎樣回答?」
陳奐生的臉紅了。
陳正清毫不放鬆地說:「你想發財叫別人犯錯誤,這不是缺德?!」
陳奐生把頭低下去,雙手捧著,耳朵像被熱水燙著了。
陳正清見他那樣子,也就不說了。一支煙抽光,摸摸自己袋裡,竟沒有帶,便向奐生再討一支。奐生伸手到袋裡去摸香煙,陳正清才看到他哭了。
「說重了嗎?」陳正清問他。
「我呀……想不到是這樣的。」
陳正清歎了一口氣,抽著煙緩緩地說:「本來呢,我也早該勸勸你了。倒不是怕你不聽,就相人家以為我存心拆臺。上次我問你,肚臍眼凸出來沒有?我倒不是看你胖了不歡喜,我是說你是被別人吹胖了。要當心被吃掉!人家捧你,是要利用你,你當你真的本事就大了?你不還是原來那個樣子嗎!嘿,還好,幸虧只當了採購員,「文化大革命」裡,還有被捧上天的,就真當自己是神仙了。結果呢,梯子一抽,跌個半死。想不到你也給捧得自己下不了臺!我看你趁早醒醒吧!」
陳奐生一面掉淚,一面捧著頭嗚咽著說:「我不去了。」
陳正清笑了,更加緩和地說:「你真糊塗,還跟著王生髮反對包產。我曉得,你是怕包不過別人,這有什麼關係?跟著大家學就是了,還怕學不會嗎!一包產,王生髮卻站不住腳了,你還愁什麼。長手臂截短了,大家高興。」
……
陳奐生醒過來了,他果然沒有再去找吳書記。想著包產以後,只要勤快、肯學,總能趕上大家的。他記得,從前的油繩,自己也不會做,也不會賣,都是向人家學來的,難道以後倒反不能學了嗎?!
於是,陳奐生又信心十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