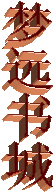
高曉聲文集 陳奐生轉業
一
哈哈,這世界真是個萬花筒,千變萬化,好看煞人。(「漏斗戶」主)陳奐生,人人都認定他要在農業上幹一輩子,他自己也從未打過別的算盤。想不到忽然被大隊領導看中了,要把他調到隊辦工廠去。
這種好事情,有些人求之不得。可陳奐生腦筋忒死,看那廠裡的工作,輕輕巧巧,細吹細打,自己一身力氣,到那裡去也使不出來,肌肉要發脹,骨頭要生疼;工資倒可以多賺些,但風雨落雪,天天要上班,身子就賣在那裡了;想上市場去賣油繩,就沒得自由。若叫老婆去賣,她腦子不靈,連本錢也會錯脫。自己一進廠,這副業就只好收攤。「嘖!吼!」他實在有點捨不得。
還有那孩子媽,別看她傻乎乎的,聽了這個消息,也緊張了。近兩年來,她吃飽了肚子,穿暖了衫,別的不懂,也懂得了丈夫本事不小。她是又敬又愛,生怕被旁的女人勾引了去,兩隻眼睛,就把他盯緊了。陳奐生到別人家去坐黃昏,講空話,稍遲一點。她就要喊回去。那五元錢住一夜棧房的事,她總懷疑是有人陪丈夫困的。要不是隊長罵她污蔑新社會,要不是陳奐生摸出吃剩的藥片給她看(後來那藥片又吃好了她的感冒),她不知要吵幾次才完呢。現在領導要丈夫進工廠,可見是吃香了;料想他去了之後,自然更加風光。自己看不住他,怎麼得了!外面花花世界,女人雪白粉嫩,這「投煞青魚」直來直去,一投投進人家的網兜去,豈不就會把老婆拋棄掉!「喔唷,還是不讓他去好!」
這對夫妻,二心一意,都捨不得鋤頭柄。他們哪裡曉得,這是大隊的既定方針;這方針又是以陳奐生的光輝歷史為根據的。陳奐生已經註定要為大隊的工業化作出貢獻。他怎麼可以不去呢。怎麼還可以拖遝呢?於是幹部們。特別是大隊書記就來勸導他,一趟、兩趟、三趟,三請諸葛亮。幹部們對他真心實意,說的話叫他稱心滿意:「奐生、奐生,你應該出來幫幫忙哪!」「奐生、奐生,大家都看中了你呀!」
「奐生、奐生,大隊待你不差呀!別人要進廠我們也不要呢!」「奐生、奐生。不要疑三惑四啦,我們還會讓你吃虧嗎?」「奐生、奐生,你不出來幹,叫誰出來?喔唷唷,架子搭得這麼大,虧你好意思啊!大家誠心誠意,為你跑酸了腿呢!」……
哎呀,這叫陳奐生怎麼擔當得起!他也四十八歲了,年紀並不活在狗身上;別的不懂,難道連「幹部比爹娘還大」這個道理還不懂嗎!爹娘打罵兒女,歷來理所當然;這比爹娘還大的幹部,倒反為請他出山跑酸了腿,豈不要折了他的陽壽!況且,他能搭什麼架子呢?他為什麼要搭架子呢?他和老婆都是鴨,有架子也不會爬呀!
陳奐生心裡暖烘烘,臉上紅彤彤,頭上像蒸熟了饅頭的蒸籠一樣騰騰冒氣,戴那二塊五角的帽子,從來也不曾有這樣熱。
他還有什麼話說?他老婆還有什麼話說?
得!得!得!陳奐生走馬上任了。
陳奐生上任去幹啥?他去做採購員。咦呀,他怎麼能做採購員呢?第一,他不會講話,第二,他不會交際,第三,他外面沒有「關係」,無「路」可走。
但是,陳奐生是個直來直去的人,他的思想是容易打通的。
「採購員是個重要人,不是隨便哪個能夠做得的。」廠長抬他的轎子說,「所以我們才看中你。」
「倒是。」陳奐生點點頭。有人看重他,他倒也並不心虛,他至少是個老實人,從來沒有做過虧心事,為什麼不該被人看重呢。「吃虧我沒有做過。」他猶豫地說。
「不關事。」廠長壯他的膽說,「哪個採購員是天生的?你看,農機廠的王樣大,膠術廠的劉玉林,我們廠的施龍大……哪個不是種田的,現在照樣打出天下來。」
「這班人,」陳奐生動心而又羡慕地說,「倒真有本事!」
「你本事不比他們小!」
「我?」
「當然。」廠長十分正經,那口氣的嚴肅性把聲音都壓低了,「你的路子比他們大得多。」
「哎!」陳奐生愕然。
「唔。」廠長點點頭,微微一笑,伸出一個指頭點了點奐生說,「你有一條大路。」
「大路?」
「你去找吳書記——吳楚。」
「吳楚?」
「他現在到地委去當書記了,主管工業。」廠長說,「我們要的東西,只要他一點頭,就有。」
「他肯點頭嗎?」
「你去找他,就肯。」
「真的嗎?」
「我敢包,他很看得起你。」
「真的嗎?」
「他不是到你家來吃過飯嗎?他不是送你一斤塊塊糖嗎?他不是坐汽車陪你去看病,還送你住招待所嗎?你看這交情……」
「真的!」
「還有好的呐!」廠長興奮得輕輕一拍陳奐生的肩胛說,「你們的交情不是寫在小說裡了嗎,外面議論得熱鬧透了。吳書記升官,還沾著點光呢,他會虧待你嗎!」
「真的?真的?」
「真的,真的。」
「咦……」
「哎……」
「呀哈哈……」
一個人的腦殼子,都是電燈泡,誰摸著了開關,一撳就亮。陳奐生現在的腦門頂。毫光萬道,簡直是一盞探照燈;住在幾百裡外地委幹部宿舍裡的吳書記,說不定會有感應,弄得心血來潮呢。「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果然是親得很的。陳奐生好像重新找到了一個外公了。
二
定下來要做的事情,陳奐生是從來不疑三惑四的。
例如:吃不飽肚子要不要勞動?要。定下來了,他一干就是十多年。難,也難慣了。所以覺得難也容易。沒有做過,是因為不曾去做;只要做,就「過」了。一年前頭,油繩也不曾賣過,現在也「過」了。哎哈,世界上的事,簡單極了,筆直一條路。有飯吃,就吃。沒有飯吃,就吃粥。沒有粥吃,就瓜菜代。沒有瓜菜,就吃榆葉、馬蘭。陳奐生不都「過」了嗎!種田,就種田。種了田還可以賣油繩,就賣。賣過油繩又要他當採購員,就當。咦,這有啥了不起。船到橋下自然直,就像人死了進火葬場,都會歸口過去。萬一歪了,把船碰翻,也無非是落水。困在蘆扉上,還怕滾到地下去嗎!青魚產卵,尾巴一扇,一直線竄出去幾十裡,順利的也有,撞死的也有;橫豎要如此做,管他!何況當採購員,也不至於拼性命,做得成就做,做不成就算,又不礙。吳書記自然是好人,會不講交情嗎!這交情又是天下人都曉得的。不瞞天,不瞞地,沒有一點要忌諱;把心碾成粉,也找不出一粒黑星星。此番去找他,純是為公事;是請他關心關心我們集體的利益。他當然要照顧。他的頭一點,事情就成了。有什麼難呢!容易容易。否則廠長還會看准他這把鑰匙嗎!萬
—……萬一吳書記不點頭,又怎麼辦呢?唉、唉,假使他不點頭,也只好拉倒,總不能像造反派那樣把他撳得低下頭來。吳書記是大官,他陳奐生是社員,大官對社員不講交情,陳奐生也不算丟臉;他的臉丟了也無人會拾得去。吳書記就是不講交情,總也會講道理。那麼,陳奐生回廠就有了交代,就沒得干係了。
「唉!」陳奐生想到這裡,不禁歎息了:「總不至於吧!吳書記啊,吳書記,天下的大官多得很,認識我陳奐生並且有點交往的只你一個。我可只有你這一條路,倘若你打官腔,關門,那麼,我跟你們這班大官的一切關係就算全部一刀斷。」……
陳奐生想了一通,曉得自己去倒去得,包票是打不得的。倘若辦不成功,這工分和費用,怎麼個說法,自然先要講妥。否則,用虧了,賣老婆沒人要,拿什麼去抵?他直截了當,就向廠長說了。廠長說:「這個是有定規的,採購員搞回來這種材料,每噸獎金一百五十元,例如你奐生這趟出去,替廠裡搞到一噸,你就得一百五十元。搞到二噸,就是三百。你出外一天,搞到了,也給這許多,十天半月,也是這些。工分、花費都在這裡邊,廠裡不另貼。」
陳奐生搖搖頭說:「我不去。」
廠長忙笑道:「不要急,你剛開頭,我們不用這個辦法。可以照老規定:工分照最強的勞動力靠,車旅費實報實銷;在外一天,再補貼八角伙食。你就是搞不到,這筆錢一個也不少你的「。搞到了,就照新規定獎你。總之只讓你沾光,不讓你吃虧!」
廠長的話,說得溜滾圓綻,陳奐生像吃了掛粉湯糰,喉嚨裡再也不打嗝頓。接著,廠長便把這次出去要辦哪些事,如何辦,一切細關末節,統統關照清楚。陳奐生著實得益非淺。最後講到交際費用,卻發生了一點小小爭執:廠長說此番出去,全靠陳奐生和吳書記的老交情,除了帶兩包香煙在身邊方便方便以外,不必再花費什麼。陳奐生聽了,一口咬定要給吳書記送一份厚禮。廠長連忙搖頭說:「送禮要看對象,給吳書記送禮,是用黑漆棺材抬新娘子,錯透又錯透。」陳奐生不但不聽,反而擺出窮大爺的架子說:「我陳奐生窮雖窮,面子是從來不失的,兩手空空跑上別人家大門,我寧可敲斷腳脛坐在家裡。何況這次又是公事,又要去求人,空口說白話,我不幹。」廠長咂咂嘴,撫了撫面孔,無可奈何說:「老實告訴你吧,他在這裡蹲點的時候,我們送了點東西給他,吃了個大批評,弄得現在不敢去見他,才請你出面的,再帶禮去,不是討苦頭吃嗎!」陳奐生反駁說:「這個我不管,吳書記這個人,我曉得;他到我家來吃頓便飯,都帶來一斤塊塊糖。他都講究禮貌,我倒能不講嗎?」廠長還是搖頭說:「算了吧,送也沒用,不罵你,就算交情,受是決不會受的!」陳奐生又頂住道:「人情大於債,受不受由他,造是不能不送的。」
爭了半天,沒有結果。廠長見他固執,沉吟了半晌,試探道:「那你說要送些什麼貴重東西呢?」陳奐生胸裡似乎早有成竹,不加思索說道:「三斤豆油,一隻雞婆。」
之後兩三天,陳奐生忙著打介紹信,到公社工交辦公室及縣工業局轉介紹信(這裡面又出了一些事情,以後會看到),領路費,打聽乘哪一班汽車接哪一班火車,到了哪個站頭下火車乘什麼車子到地委。禮物也硬是準備了,不過聽了廠長的勸告,把三斤豆油改成三十斤山芋,因為吳書記曉得鄉下吃油比城裡緊張;又決定這禮物是陳奐生私人送的,和工廠無關。
一切打點就緒。誰知出門隔夜,陳奐生的愛人忽然發起嗲來。不許陳奐生在外邊住夜,事情辦不完,也要天天趕回來。陳奐生罵她癡婆,這又不是上城,只要跑三十裡。幾百里呢!能天天回來嗎?他愛人見行不通,就吵著要和他一同出去。陳奐生罵她發瘋:豬呢,羊呢,兔子呢,孩子呢,哪個弄給他們吃?愛人不聽,還是嗲來嗲去。陳奐生這才弄懂了她的用意,他火冒三丈,破口罵道:「昏了你的頭,我這人參果,豬都不吃。天底下只有你一個人當寶貝,只管放心!」
三
公路上駛的是汽車,鐵路上跑的是火車,上上下下,轉轉盤盤,陳奐生竟一點沒有摸錯,順順當當,到了目的地。他在地委機關的傳達室裡,先自報家門,然後指名要找吳楚書記。
地委機關的大門有它的嚴肅性,傳達室具有傳遞信息和保衛安全兩重任務,工作人員當然小心謹慎、一絲不苟地值勤,他們在門口豎著一塊牌子,上寫「主動下車,出示證件」八個大字,但是對轎車和吉普則尊敬而多禮,即使那上面藏有機關槍甚至大炮,也可以直馳而過。步行而派頭奇大的人物,眼裡根本沒有傳達室,傳達室也等於自動讓步。只有那些看去不大上眼的來訪者,才受到嚴格的盤問;有的受到阻撓不得進去,或先坐一陣冷板凳再說。陳奐生當然是很不起眼的,而傳達員因為從不看小說,又不知道他是個大名鼎鼎的人物,按理不會順利通過,但是,這傳達員偏偏獨具慧眼,他從頭到腳細細打量了一番之後,便斷定陳奐生有些來頭,因為他穿戴得過分隨便,送的禮物又輕又土,這說明他和吳書記的關係既親密又古老,不是姑表,總是姨表;不管哪一表,都怠慢不得。所以連忙拎起話筒,就往裡面掛。哎哈,他想得一點不錯,接電話的辦公室劉主任,竟像聽到第一顆衛星上天的消息,興奮得大聲喊道:「快叫他進來,快叫他進來!」
陳奐生按照傳達員的指示,走到地委辦公室,劉主任早已滿臉笑容,在門口等他。見他來了,一把緊握他的手,連連搖著說:「不錯,不錯,你果然是這個樣子!」
一面說,兩隻眼睛盯緊了奐生的鼻子,好像要認出吳楚的指紋印來。陳奐生只覺得鼻子都被看酸了。辦公室裡另外幾個同志,也都十分親昵,接過他的山芋,接過他的雞婆,請他在沙發上坐下,請他吃茶。陳奐生已見過世面,不再怕沙發坐壞,倒也安然。只有那雞婆似乎煩躁,拍拍翅膀,咕咕叫著,好像不舒服。因此引起大家注意,問起鄉下雞婆的價格。陳奐生見大家對他帶來的東西有興趣,覺得雞婆只有一隻,無法分贈各位,便撐開袋口、拿出幾個光溜溜的大山芋來,請大家嘗嘗。大家都說不要,陳奐生哪裡肯聽,便說這山芋錛出土來已經兩個月了,吃來雪嫩筍甜,賽過鴨梨,城裡人是難得吃到的。不由人不依,硬是每人送了兩個。還說:「天冷了,這東西容易凍壞,我都是揀好的拿來。再冷下去,就不會有了。」
可也奇怪,這些話,陳奐生在農村裡從來想不到說,因為這是小孩子都知道的事情。現在倒細細地說給幹部聽,好像他們連小孩子也不如。而幹部們聽了,都認真地點點頭,一點不笑。於是陳奐生就覺得尋得著話說了。
只停了片刻,吳楚就來了。陳奐生連忙站起,喊了一聲:「吳書記」
吳楚呵呵笑著說:「奐生,你這傢伙,怎麼跑這麼遠的路來?帶油繩來賣嗎?唔!」
陳奐生只是笑笑,說不出話。
劉主任說:「他是看你來了,還帶了禮物呢。」
吳楚連忙說:「唔,什麼禮物?山芋!好好。還有老母雞?它生不生蛋?自家養的嗎?拿來送給我?你老婆曉不曉得?她捨得嗎?不跟你吵嗎?」
陳奐生申辯說:「我老婆呆是呆,總不癡,好醜也曉得。那趟你來我家後,一直念你呢!」
「哈哈,說得好聽,還念我!罵我吧?」
陳奐生急道:「我家小丫頭,看見別人家吃糖,就要問她娘:『吳書記怎麼不來?』」
「真的嗎?」吳楚連連搖頭說:「我不相信。一夜天花了你五元錢,你老婆總要罵我一世了。你這傢伙,碰上你,我就倒黴。招待所問你要錢,就說我吳楚去付嘛!你付了,又肉痛,回去又吹牛皮,被人家寫到小說裡去,通天下都笑話。你這傢伙,你還來看我,還送禮來,又要弄得議論紛紛了!這山芋、這雞,要多少錢?我算給你。還有那五元房錢,也算我的。」
陳奐生急巴巴說不出話來,他拎起雞和山芋,沒輕沒重地說:「喔唷,吳書記,你官做大了,老百姓巴結你也巴結不上了。真是……」他強著勁說:「你到我家來,也帶東西的;准你送,我就送不得?只許州官放火,勿許百姓點燈,虧你說的!走!」
「哪裡去?」
「送到你家去。我還拿回去嗎!」
吳楚哈哈大笑,看了看表說:「好好好,客人我總要招待。你不要急,看你額角上汗都出來了。那帽子還是去年住招待所買的吧?都舊了!我有一隻呢帽子,尺寸買大了,送給你吧。」說著,要去拎山芋袋。陳奐生不讓,他只得空著手,陪他同走。
兩人出了地委大門,往西走過兩百來米,落北進了弄堂;再走二、三分鐘,跑出弄端,便是一片空地。空地北端,有五、六丈圍牆,正中有個門堂,吳楚帶著陳奐生走了進去。奐生一看,裡邊只有兩間老式樓房;樓房東、南兩邊,好一大片空地啊!足有一分多面積,兩個人的自留地也沒有這麼多,卻是一片荒蕪。陳奐生不覺發出一聲輕輕的歎息。吳楚猜准他的心理,便指著說:「你看,這裡種熟了,一年四季的菜就吃不完。我一直想把地翻一翻,就是沒有空,來了半年了,只翻了那邊一隻角。」奐生看去,果然那邊翻了一小塊,卻拾出了許多磚角瓦片,可見這地,收拾起來也不容易。
兩個人進了屋,吳楚就喊阿姨,樓上答應著,走下來一個六十多歲的老太婆。吳楚說:「阿姨,鄉下有朋友來了,夜飯夠嗎?不夠就再燒點。那邊房裡空鋪收拾收拾。」又對奐生說:「這個阿姨,不是請的,是我的真阿姨,就是我娘的小妹子。一直在幫我做家務。」
陳奐生見吃住都安排了,一片放心,說:「家裡人呢?」
吳楚說:「老婆還不曾調來,孩子都跟著她;我老爹、老娘在這裡,一個八十一,一個七十八,天氣冷躲在房裡不大能出來,全靠阿姨。」
閒話了一陣,吃晚飯時,吳楚邀奐生喝了點酒,聽奐生談了些農村裡的情況,便問起奐生來的目的;因為他估計到沒有正經大事,奐生不會跑那麼遠的路來看他的。
奐生見問,就把書記、廠長找他,他如何進了工廠、如何被派當採購員,想買什麼,老老實實,告訴吳楚。
吳楚哼了一聲,說:「他們也認識我,為什麼要叫你來?你面子大嗎?」不等回答,又笑了笑說:「嘿,鬼主意還真不少呢!」
陳奐生沒法開口,吳楚頓了片刻,又問:「他們不曾叫你送禮吧?」
「沒有,沒有,不好冤枉他們的。」奐生忙說。
吳楚說:「不冤枉,他們送過的。否則,你那山芋袋裡會塞手錶進去的。」
陳奐生嚇得不敢響。
又飲了杯酒,吳楚忽然笑著說:「你這個『漏斗戶」,有吃有穿了,還想發洋財嗎?」
「發什麼洋財!」陳奐生申辯。
吳楚搖搖頭,說:「我也不來查。你嘛,是老實人,叫你空手回去吧,說不定別人要唱你的空曲。不過這東西緊張,我還要瞭解了情況才能答覆你。你住下來再說吧。」
睡覺的時候,陳奐生正在解衣扣,吳楚拿了一隻嶄新的呢帽走進來,笑著說:
「你看,我嫌大。」他往頭上一套,果然遮到眼睛上。脫下來戴到奐生頭上去,恰是正好。便說:「給你吧。」陳奐生心頭的暖氣,一直流到腳趾上。吳楚走後,陳奐生把那帽子放在手上,足足撫了兩個鐘頭。
明早起來,吃了早飯,吳楚匆匆上班去了。陳奐生閑來無事,便出去逛大街。一路上車水馬龍,花花綠綠。想到要回去吃飯,已經走出好遠,來不及了。只得買了一斤羌餅,到老虎灶討一碗開水,填飽了肚皮。索性不再回去,去那百貨公司、食品公司細細看了一遍;只見吃的、穿的、用的,五花八門,種類繁多,眼也看花了,心也看野了。想著這世界上竟有這麼多好東西,可歎自己辛辛苦苦做了一生,也不曾能買得幾樣,真是苦哇!
等到看完,天將黑了,陳奐生有點詫異,怎麼城裡時間這樣容易過去?便匆匆忙忙,奔回吳楚家去。
吳楚不在家。老阿姨見他回來了,舒出一口氣,說以為他摸不著家門了。趕快盛出飯來,還叫他到這裡來了就別客氣,以後不要到外面去買了吃,橫豎家裡是準備了的,不回來吃反而剩了,吃隔夜食。
奐生連連應著,問道:「吳書記吃了嗎?」
「他上半天接到電話,回來吃飯收拾收拾,又到省裡去開會了。」
「哎呀,」陳奐生叫出聲來,「幾時回來呢?」
「他也說不定。」
「他說什麼沒有?」
「吃飯時查你的,你又不在。」
陳奐生一口飯含在嘴裡,目瞪口呆。
四
這天晚上,陳奐生平生第一次失眠了。那軟軟的被子,軟軟的枕頭,比家裡的好得多,偏偏竟覺得手腳無處安放;橫翻一個身,豎翻一個身,橫豎總是不舒服。想自己從不貪玩,難得放任一次,卻誤了大事。吳書記是個忙人,此番出去,幾時才能回來。他對自己這件小事,會放在心上嗎?說不定過幾天就忘記了。豈不糟糕!
清早起身後,陳奐生心緒不甯,左思右想,不知如何是好。也沒有心思出門去玩,想找個人商量商量,卻一無親戚,二無朋友。問得發慌,便幫著阿姨淘米洗菜,把地面掃得乾乾淨淨。吃過飯,困了一個午覺,起身後找不著事情做,一個人坐在門檻上吹涼風,消散那胸中的悶氣。坐了一陣,又不舒服,渾身肌肉緊繃繃,催他出力。他看看空地,忽然想起上午掃地時東屋裡有一把釘耙,立刻高興起來,便拿了去鋤地。這地裡碎瓦斷磚極多,鋤了兩耙就得彎下腰去拾了丟在旁邊;也不敢用力,怕碰壞了釘耙;所以幹了一陣,使不出力,出不得汗,照樣不痛快。第二天不想鋤了,但沒有事,想想吃了吳楚的飯,不幫他做點什麼,總過意不去,還是翻地吧。翻著翻著,想起事情不曾辦好,書記。廠長還在等回音,在外耽擱久了,空手回去不好交代;又想起老婆、孩子、豬、羊,不禁歸心如箭。這陳奐生除了小時候舅舅娶舅母在外公家住過一夜,再就是在招待所耽擱半夜之外,從不在外住宿,自然不習慣了。
第三天一早,儘管阿姨殷勤挽留,陳奐生千恩萬謝,說要回去看看再來。然後上樓別了吳楚的爹媽,把吳楚送給他的呢帽和裝山芋來的布袋,塞進從前賣油繩的旅行包,走出堂屋。在天井裡,又看到那只雞婆悠閒地在他翻過的土地上覓食。不禁深情地戀戀留眼,唉,他不是捨不得送給吳書記,而是習慣了和它在一起呀!
出了小弄,他摘下棉帽塞進包裡,把新呢帽戴在頭上。跑過百貨公司,他記得那裡有一面大鏡子,特地彎進去端詳了一下自己的「尊容」,果然神氣了不少。陳奐生笑了一笑,然後揚長而去。……
回到大隊,陳奐生滿懷未能完成任務的歉意,唯恐受責;他家都未到,就先找書記、廠長彙報。誰知書記、廠長聽了,把手一拍,勁道十足地說:「哎呀,奐生你呆,回來做啥呢!吳書記待你這麼好,還怕他不替你想辦法嗎!快點再去,快點再去!今天來不及就明天一早動身,你給我坐在那裡,十天八天,半月一月,也要等得吳書記回來。」
「去了沒事做,等他回來了再去不好嗎?」陳奐生不願意。
「你知道他幾時回來?你不去等他,他還會等你嗎?他東一天,西一天,錯過了機會你就尋不著。快去快去!」
陳奐生聽著也對,只得答應。回去住了一夜,不顧老婆嘀咕,帶了幾斤上白米,一捆大青菜,又匆匆就道。
此番已是熟門熟路,原不必再有周折了;但陳奐生下了火車,經過一家旅館門口,卻觸動了心機:人貴有自知之明,吳書記家雖然有吃有住,也該知趣;況且不是一天兩天,不如住在旅館裡妥善。橫豎費用廠裡可以報銷,何必去揩吳書記的油呢。躊躇半晌,便走進旅館,在服務台旁看了片刻,學會了辦理手續;便拿出介紹信來登了記,說明要一個最便宜的鋪位;付一元錢鉀金,拿了鑰匙,住進了214號房間。那房間放了六張單人鋪,擠得很;陳奐生不打算在那里拉場賣拳頭,自然不嫌。躺了一會,想起那一捆鮮嫩的青菜,應該當天送到吳家,吃個新鮮。便提著走到吳家。書記還不曾回來,阿姨拿了菜,聽他說住了旅館,想他是個老實勤快的人,有心幫忙,勸他還是住到這裡來,因為吳楚萬一夜裡回來,早上又跑了,住在旅館就碰不著,白等。奐生覺得有理,連忙答應。吃過夜飯,就到旅館去取東西。拿了東西,到服務台去還鑰匙,服務員告訴他,鋪位每天一元二角,鑰匙押金一元,還應再付二角。奐生不懂,服務員才告訴他,這鋪位不管他住不住,都應付一天的錢。陳奐生心裡叫聲:「苦呀,又碰到鬼了!」他不肯吃虧,賭氣不還鑰匙,決定住一夜再走。又怕阿姨等他,只得再跑一趟,順便把米也帶了去。
等到回來,房間已經有兩位旅客在那裡交談,一個年輕的,呢制服筆挺,皮鞋賊亮,長頭髮在電燈底下油光閃閃,派頭十足。一個中年人,打扮得平平常常,面容卻和善,見奐生進來,還微微點了點頭。奐生不會交際,無話可說,便往床上一坐,看著電燈發呆。聽了一陣,聽出那兩人也在談生意經,不禁問道:「你們也是採購員嗎?」
那兩人見問,回頭細細看了他一眼。年輕的便說:「你也是?」陳奐生點點頭。年輕的又問:「幹了多久了?」奐生回答:「剛剛頭一趟。」年輕人便看不起,再瞧他那寒酸相,更不入眼,頭就別過去又和中年人談話了。那中年人雖不說什麼,眼裡卻漾著關切的笑意,好像要同他攀談。只是在聽那年輕的講,不便張開嘴來。
後來,年輕的有事出去了,中年人便坐到陳奐生的床沿來,先自報家門,姓林名真和,是×縣×公社×大隊×廠的採購員,然後請教了奐生的姓名、單位,笑道:
「我們是同行嘛,要搞的都是那種原料,現在很緊張。剛才那年輕人,也和我們一樣。不過他們廠大,手段大、路子大,搞起來是有把握的。陳老兄,你搞到沒有?」
「沒有。」陳奐生高興地說。他覺得林真和很看得起自己。
「局裡邊、廠裡邊有熟人嗎?」
「沒有。」
「你沒有路,又不曾搞過,廠裡為啥叫你出來?」
「不瞞你說。」陳奐生輕鬆地舒了口氣,「我有個朋友在地委裡。」
「做啥?」
「書記,管工業的。」
「喔!」林真和恍然說,「怪不得,怪不得。」便從袋裡摸出一包大鳳凰,抽出一支敬奐生。奐生推不過,只得接了。林真和便喀峻打亮火機,幫他點著,自己也燃了抽起來。然後又問:「老朋友嗎?」
「他以前一直在我們那裡工作。」
「你跟他交情怎麼樣?」
陳奐生見人家這樣看重自己,就像殺豬的給豬吹了氣,自覺脹得大了。忍不住要擺一擺海,便把自己同吳楚的關係,吹了一遍;末了,又把帽子摘下來指指說:
「這就是他送給我的。」
林真和聽了,著實羡慕,對陳奐生十分看重,一連請他吸了幾支香煙,說碰巧認識他,也是緣分。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以後大家要互相幫助,奐生有什麼為難,只管找他。又聲明,他曉得奐生是初次出馬,他不指望靠奐生搞什麼,倒願意幫奐生出出主意;因為他多少有點經驗,山是高的)江是長的,吃虧沾光,不在一朝一夕,能夠真心實意交上一個長遠的朋友,大家都有好處。
陳奐生見他說得動聽,倒反有點疑心,因為他也常常聽說外面有騙子。但看看林真和,額頭寬闊、臉色正派,特別是那雙善良的眼睛,好像流露出一種委曲求全、叫人憐憫的光彩,想來不是壞人。也就欣然贊成了。
臨睡之前,林真和端來一盆水,問奐生洗過腳沒有?勻了半盆給他。等到奐生洗好,林真和已穿了鞋,隨手就把兩盆水並在一盆裡拿出去倒了,做得非常自然。陳奐生十分過意不去。便也拿出自己帶來從未抽過的「牡丹」,抽出一支硬要他吸,這才安心睡覺。
早晨起來,見那年輕人還在打呼,也不知是什麼時候回來的。林真和早已起身,兩人又熱絡了一番。」奐生說了吳楚的地址,叫林真和有空就去找他,然後走了。
從此,陳奐生住在吳楚家裡,等書記回來。他是個閒不住的人,清早起來,就代阿姨上街買菜,家裡事見什麼就做什麼。阿姨非常高興,幾天下來就覺得臉上胖些。每天下午,奐生就鋤那空地,揀出的碎瓦斷磚,一齊搬到南牆下,堆得整整齊齊。地翻過來,曬了幾天太陽,便做了壟,上街買菜時,買了些高在秧和三月白,種了幾壟。林真和來看過他兩次,還幫他拾磚瓦。他晚上也去看林真和。最後一次,林真和著急地悄悄告訴他,那年輕人厲害,幾爿大廠都答應給他貨色,如果吳書記再不回來,到時候貨色給別人弄走了,面子再大,也只能以後有了再說,那要等到幾時?林真和又說那年輕人習,看不起人,請他幫點忙,硬是不肯。林真和只搞到半噸,再無辦法,自己都不夠,所以也不能幫奐生的忙。
陳奐生聽了,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早盼夜盼,望穿了眼睛,吳書記卻影蹤全無。那省裡的會,一正不知要開到幾時。
五
吳楚回來了。
他九點多鐘到了地委,連忙就通知開會。十點一刻會議就開始,一直到下午五點結束,飯也沒有回家吃。
回家的時候,他把旅行包放在辦公室裡,不曾帶走;因為明天一早,他就要帶幾個人下去檢查工作。在外面換下來的髒衣服,在賓館裡請人洗過了。老阿姨年紀一大把,行動已不大方便,燒點吃的已經夠累了,再要從外面帶髒衣服回來給她洗,也作孽。
吳楚兩手空空,悠悠然踱著慢步走進院門,眼前忽然一亮,他吃了一驚:原來院子裡完全改了一個樣子,已經變成極好的菜畦了。泥塊敲得極細,壟溝做得筆直,一棵棵菜秧,種得疏密勻稱,一片片嫩葉,已經豎了起來(活棵了),顯然是內行人幹的活。
「這是誰幹的?」吳楚一時想不起來了,但馬上猜到,「哎呀,一定是陳奐生!」
他很高興,心裡暖暖的,甚至感激了。接著就內疚起來,罵自己道:「該死,我把他的事忘記了!」
吳楚快步走進堂屋,想看奐生在不在。卻碰到老阿姨從廚房裡出來,她打開電燈,見進來了吳楚,喜得兩手一拍圍腰布,說:「嗨呀,楚楚,你到今天才回來,奐生在這裡等你,人都等瘦了,真要急出毛病來呢。」
吳楚說:「他人呢?」
「他今朝只吃了半碗飯,就困了,還沒起來呢。」
吳楚連忙打開房門。奐生床上空了,人不在,原來他借了附近菜農的糞桶,給萵苣澆了一次肥,還糞桶去了。
「哪裡去了?」吳楚問。
「不會到哪裡去,總在近旁。」阿姨說,「這個人真是老實勤快,樣樣都做,不肯歇。他在這裡,我動也不要動,享福了。你看看,我自己都覺得胖了呢!」
吳楚看看,老阿姨真的胖了。
老阿姨說了奐生一番好話。又說:「他在這裡橫等豎等,做完了事,就呆鈍鈍坐在門檻上望著院門口,好像你同他約好了馬上就回來的;那可憐相,我看得也心酸了。我就想,不曉得楚楚可曾幫他辦哪?楚楚,你辦了沒有?你可要幫他辦。他是個好人,又難得求你,你不能推哪!」
吳楚連忙應著,因為老阿姨是個知趣人,從不輕易代人求情的,如今說了這樣動情的話,吳楚自然感動了。他心裡很高興,不禁好玩地想:「嗨,這陳奐生,還真厲害呢。」
說話間,陳奐生還掉糞桶,像青魚一樣投進屋來;一見吳楚,喊了一聲書記,就說不出話來。頓了頓,才自顧自說:「還好,幸虧今天不曾回去,回去了就白等了。」
吳楚看看奐生,覺得他的眼睛變大了,吃驚地想:「哎呀,真瘦了一圈啦!」
「真的,我原打算今天回去的;幸虧不曾回去。我又拖了一天,明天是鑿定要回去了。幸虧你今天回來了。要是你明天回來,我鑿定已回去了。……」陳奐生反反復複嘮叨這幾句話,除此以外,他好像沒有說的了。
這單純的、真摯的、深沉的情感,強烈地震撼了吳楚。這個做報告從不帶稿子的地委書記,忽然也訥訥起來,連聲說著:「我回來了,我回來了,我回來了。」……
好像也找不到別的詞兒。
等到坐下來吃夜飯,喝了一點酒,空氣才活躍起來。吃過夜飯,吳楚想了一陣,便問奐生可曾帶介紹信來。
陳奐生高興了,他想也沒想,直通通說:「有,有兩封呢。」
「怎麼有兩封?」
陳奐生這才知道說錯了話。又一想,反而理直氣壯,覺得不錯:應該老老實實告訴書記嘛!他伸手到胸口內衣袋裡,掏出來兩張紙,攤開來認了一認,說:「這一張是廠裡開的,說好只要買兩噸。」他遞給吳楚。
「那一張呢?」吳楚問,覺得奐生還有別的話。
「這一張是公社工交辦公室開的。」奐生遲疑了一下說,「我拿廠裡的介紹信去轉關係,工交辦公室的老陸說他們也要,替我另外開一張,要五噸。」
「牛吃蟹!」[注]吳楚罵了一句,「這又不是河泥、豬灰,能隨便要嗎!」
「我也不肯。」陳奐生申辯說,「可是老陸開了,不肯在我們廠裡的介紹信上蓋印,叫我拿了他開的介紹信到縣裡去轉。我到縣裡,縣裡也不肯在我們廠裡的介紹信上蓋印,倒說是老陸那一張合法。我就只好拿它來。老陸說,買了五噸,我們廠裡的兩噸就在裡邊了,不必另外再買。」
「你上他的當!」」
「我沒辦法。他說:『你難得去找吳書記,兩噸是一趟,五噸也是一趟。吳書記有的是辦法,他若肯答應你,二噸、五噸還不是一樣!」陳奐生原原本本轉告說。
吳楚看奐生傻乎乎的樣子,赫赫笑了幾聲,說:「奐生呀,你總是牛皮吹在外邊,大概人家以為我吳楚有半個家是你當的了。不行,你別理他們。」吳楚把工交的介紹信丟給奐生:「這種原料現在很緊張,二噸也不見得有;一噸也還要看人家有沒有辦法節約下來支援你。」他說著,拔出鋼筆,在工廠介紹信上寫了幾個字,遞給奐生,交代道:「明天上午,你乘九路公共汽車(到百貨公司門口去乘),一直到底,下車順馬路往南跑半裡多路,就是××廠,你去找朱明源朱書記,拿這介紹信給他看。這東西已經分配給他們廠裡了,他如有得多,能給你一噸就一噸,二噸就二噸,我也不能勉強他。」
吳楚說罷,又沉吟半晌,交代說:「如果一點也沒有呢——你就到辦公室去找劉主任,我明天一早就要下去,又不知幾時回來。走之前,我再和劉主任講一講吧!」
「你莫忘記了!」阿姨說。
「不忘記,不忘記。」吳楚連忙說。
陳奐生自然也不好再說什麼。到了明天,就照著吳楚說的路線,到了××廠。經過幾道關口,才在一個辦公室裡找到了朱明源朱書記。朱書記看上去年紀很大,鬚髮都白了;待陳奐生倒很親切。他把那介紹信反復看了幾遍,又眯著眼睛看看奐生說:「吳楚怎麼肯給你寫這條子的?」那口氣,好像他很瞭解吳楚,又好像吳楚是他的下級。
奐生雖笨,也曉得這句話有分量,連忙申辯說:「完全不為別的,吳書記曉得我們困難。」
朱明源就不再問,說:「材料的事,不是我管的。也不曉得有沒有,我來問問看。」說著,正要打電話,就進來了一個人。朱明源不打了,對那個人說:「老王,我正打電話找你。」又對陳奐生說:「王廠長。」
「什麼事?」王廠長問。
「吳書記介紹來的。要支援他們一點材料。廠裡能不能解決?」朱明源一面說,一面遞過介紹信。
王廠長看了介紹信,又看了看陳奐生說:「就是他嗎?」
「唔。」朱明源點點頭。
「沒得辦法。」王廠長毫不猶豫地說,「我們自己都不大夠。」
陳奐生緊張了。
「一噸半噸都抽不出來嗎?多少支援他們一點也好。」朱明源說。
「唉,朱書記。如果有一點辦法,吳書記的批示我會不執行嗎!」王廠長委婉地說,「前幾天也有一個單位來求援,還是老關係,我同供銷科商量了半天;他們不答應,一點拿不出。」回過身來,王廠長對奐生說:「我們不是不肯支援,吳書記是難得開口的,只要有一點鬆動,我都會想辦法批給你;現在是一點辦法也沒有,請你回去向吳書記打個招呼。過兩個月,等下季度的材料分配下來,我想天法也給你們一點。」
話說得這樣圓轉,朱明源也不好開口了。他心裡明白這不一定是真話,這樣大一爿廠,多少是能夠拿出一點來的。但自己並不徹底瞭解情況,吳楚也知道不能勉強,信上是介紹陳奐生來求援,是請廠裡酌情支持。現在主管人不答應,自己就不好做主了。只得也跟著姓王的勸奐生說:「以後再說,以後再說。過兩個月你再來看看吧。」
王廠長那番話,有真有假。他前幾天為了一個老關係,確同供銷科糾纏了半天,要五噸材料。他知道廠裡二噸、三噸能抽得出,緊一點抽五噸也行。但是供銷科長不答應,回說即使多下那麼一點,已和××單位講妥,要交換另外一些材料。其實供銷科長已看出蛛絲馬跡,曉得王廠長供應別人材料,是拿回扣的。那個老關係,本來和供銷科長先搞上,說實在話,供銷科長也得過一些好處,後來看到那老關係忒豁,報紙上又常揭發貪污這一類事,自己怕出紕漏,就收斂了。誰知那老關係倒搭上了王廠長,那暗底裡的交易,供銷科長自然一眼就看穿了。所以就不肯鬆口。但材料多在廠裡,王廠長曉得,也不肯就此罷休。供銷科長正在設法同其他廠協作換材料,把它處理掉。這個鬥爭,暗地裡著實激烈。
只是難為了陳奐生。吳書記的大面孔都派不上用場,他灰心喪氣,沒精打采告別了兩位領導,走出辦公室。王廠長隨後也出來了,他看看陳奐生的背影,心裡罵道:「窮煞胚!鄉下人!衣裳沒一身好的,還出來跑供銷。呆頭木雕,好話不會說一句,香煙不會遞一根……你就是吳書記的小舅子,我也不睬你!」
六
陳奐生搭上九路車,到百貨公司門口下來,再無閒情逸致去大鏡子前照自己的
「尊容」,急急忙忙,就往地委機關裡跑。走過一段路,忽然被人一把拉住,那人叫道:「奐生兄,投什麼!」
奐生一看,原來是新交的朋友林真和。奐生忙停住說:「哎呀,我都沒有看見你。」
林真和說:「你倒快,去了回來了嗎?」
「你怎麼曉得的。」
「我剛才到吳書記家去找你,碰著老阿姨,說你到××廠去聯繫了。怎麼樣,答應多少?」
陳奐生把頭一強說:「屁!」
「怎麼?」林真和不信,「書記批了,會打回票?」
陳奐生直爽地把介紹信摸出來給他說:「我還騙你嗎!」便把在廠裡碰到的情形,一一二二,統統告訴林真和。林真和把腳一跺說:「老陳,碰著姓王的那只猢猻,你算倒了黴。那個人你同他空口說白話,不給他好處,你就是他爹娘,他也不會認。我是吃過他的虧的。唉,你也不曉得,難怪你。若早上同我商量了再去,我事前會提醒你避開他。候他出門了,你再去找朱書記;朱書記就會直接問供銷科。只要供銷科說聲有,就好辦了。現在弄僵了,怎麼辦呢!」
奐生見林真和一片誠心,比自己還著急,十分感動,說:「吳書記說過,打回票就找地委劉主任的。」
林真和忙說:「那好,只要有這句話,劉主任辦起來比書記著力。書記是領導,有些話不好說,轉一個彎,讓劉主任出面,當任務壓下去也沒關係。走,我跟你同去,怎麼樣?我在門口等你,聽你的回音,再有什麼周折,也好給你出點主意。」
說著,也不等奐生同意,跟著就走,一面悄悄地說:「要快。這裡只有幾爿廠有這材料。那個年輕的採購員,和××廠的王廠長恐怕有關係,前幾天他露了點風,說有一爿廠答應給五噸,正在談判。說不定就是××廠的。等他們談妥了,你就完了。」
然後又坦率地說:「我這個人沒有歪心思。你只管放心。我看你也是老實人,誠心交一個朋友。採購員這碗飯,真不好吃,我們廠小,手段小,人家看不起。我又沒有什麼門路。我開始出來跑,這裡有一個遠親,是靠他幫忙。後來調走了,我就瞎了,要想搞點東西,一直是磕頭跪拜求人的。哪個有辦法,要我服侍也肯,跑腿也肯,化小錢也肯,用得著我只管喊我,我做小媳婦做慣了。只要別人搞到材料以後能回給我一點,我就把他當老子待。那個年輕人忒狂,我同他認識兩年了,只要碰在一起,香煙總是吃我的……衣服髒了我都替他洗。他一直答應給我點材料,到現在不曾給一斤。這一趟他已經搞到了三噸,還在搞五噸,我開口要回半噸,他說自己還不夠,一推精光。還說他黑龍江有個朋友手裡有點貨,他沒空去取。如果我等著要,他寫封信去商量,給我半噸,自己去拿。嘿,趕幾千里路去拿半噸材料,光路費都算不來,他真把我當小孩子,弄我的白相了。」
陳奐生聽他這麼說,知道是和自己一樣的可憐人。自然信得過了,到了地委,林真和果然在傳達室等他,讓他一個人進去。
陳奐生跑進辦公室,劉主任正在寫東西。奐生在背後叫了一聲,劉主任回頭見他來了,放下筆,說:「怎麼樣,他們給不給?」另外幾個同志,也都回頭來看。
陳奐生一聽,知道吳書記交代過了,心就放寬了一點,把到××廠的情況,詳詳細細向劉主任又說了一遍。
劉主任聽了,好像很生氣,重重地說了一聲。「好!」便問著長久不開口。
劉主任把手裡半支煙吸完了,才抬頭朝奐生笑了笑說:「不要急,介紹信呢?」
陳奐生連忙遞給他。劉主任看了看,便拿起電話筒,撥了號,開始講話。「物資局嗎?我找唐科長……啊,你就是老唐,好,吳書記有點事,要拜託你呢。……
不是客氣,難哪……事情很小,就是吳書記不會燒香……你來?不要不要,我來吧,我來吧。」
電話掛斷,劉主任對奐生說:「你坐在這裡等一等,我去了就來,很近。」他出去了。不到一分鐘,又跑進來對奐生說:「你還有介紹信在身上嗎?隨便什麼介紹信都行。萬一仍舊到××廠去拿材料,他們看見這是打過回票的,會改不過口來,最好換一封。」
陳奐生說:「有倒有一張,就是上面開了五噸。」
「五噸就五噸,管它!」劉主任說。拿了一看,又說,「這一張好,是經過縣裡轉的,合法。」拿了就走。
不到一個鐘頭,劉主任興沖沖回來了,大聲說:「奐生,挑挑你[注],給你五噸。你拿這介紹信,上面有物資局的印,仍舊到××廠去拿,直接找他們供銷科的高科長,已經聯繫好了。不要去找那姓王的。」劉主任見大家在聽,就告訴大家說:
「還是那姓王的鬼,連供銷科對他都一肚皮意見,那傢伙邪得厲害,家裡二十寸彩色電視機,冰箱,空調都全了,手還伸得老長,人家說他還缺一口水晶棺材!」……
陳奐生喜出望外,走出來,在門口碰著了林真和。林真和看了介紹信,聽陳奐生一說,就和奐生商量道:「這件事,我來幫你辦,那姓王的認識你,別碰著了,你別進去,我去。你在門口等我,我辦起來比你有經驗,包你不出紕漏。」
陳奐生原怕再碰壁,樂得聽他。兩人一同到了××廠,林真和進去,陳奐生就在門口等。他提心吊膽,生怕再生枝節;等了幾分鐘,就像等了幾十年。但急也無用,只得耐著性子,蹲在那裡拾一塊磚角在地上劃痕痕,劃了一陣,再一條一條地數清它,等到林真和出來,他已經等得心都爛了。其實還不到半個鐘頭。
林真和一見奐生,連連說:「成了,成了,只要回去把錢匯來,就好開票提貨。」
兩個人都高興得不得了。乘車到百貨公司下來後,林真和一把拉住奐生,進了一家不大不小的飯館,硬要請客。把陳奐生按在朝南坐位上,要來了兩斤黃酒,一個拼盤,三個炒頭,一隻砂鍋。兩人邊吃邊談。足足坐了三個鐘點,那林真和當了七年採購員,經驗豐富,講了許多苦處;也講了一個採購員應該懂得的各種事情,諸項關節;描繪出社會上各種人的嘴臉,把那表面一套,背後一套;搽了紅粉,藏著黑心;開口為人民服務,伸手撈黃金鈔票;婊子裝正經的偽君子,罵了個狗血噴頭。
末了,林真和以商量的口吻,問陳奐生能不能看朋友交情,回一噸材料給他救急。陳奐生從未受人如此尊敬,想著他許多好處,覺得小隊裡本來只要二噸,公社給二噸也說得過去了;反正有得多,自然一口答應了。林真和又勸他不必回去取款,只要打電報把匯款賬號,匯多少款子,告訴家裡,就可以了。如果奐生不會打電報,他包辦就是。這樣,還可以在這裡玩玩名勝古跡,開開眼界,他也沒有事了,打算陪奐生到處走走。
出了飯店,林真和又拉著奐生到旅館裡吃茶,揩面,洗腳。然後告訴他,這五噸材料,將來的發票,自然只能開奐生廠裡的抬頭,所以要拿出一噸,還要奐生廠裡的領導點頭,這就要看奐生回去能不能說服領導了。其實這也不難,只要說是吳書記和劉主任的意見,廠裡就沒得話說。
陳奐生聽他說得在理;其實是被他教會了,否則,回去就想不到要這樣說。現在有了主意,曉得不會有困難,連連點頭稱是。
「至於鈔票,」林真和說,「我馬上打電報回廠,叫他們匯到你們廠裡,以後再來提貨。」
兩人剛剛說完,房門打開,那個年輕的採購員也吃得面孔紅彤彤的闖了進來,他眼裡像沒有看見奐生,朝林真和瞪了瞪眼,狠狠地罵道:「×他娘,老子倒黴!」
「什麼事?」林真和忙問。
「唉,別說它了。那五噸東西,明明要到手了,不知給哪個狗×的搶了去!」
「哪個廠的?」
「××廠,他們廠長和我老交情,一口答應的。供銷科橫撐船,作梗。拖來拖去,拖到今天,被物資局一口吃去了。不知他們私底下塞了多少錢!娘的,挑人家吃飽了。」
陳奐生一聽,分明是說的自己,正想說話,被林真和輕輕踢了一腳。
林真和不動聲色地說:「唉,你也會被人家吃癟,我們這些人,還有什麼辦法!難啊!」
七
陳奐生回來了。
火車到達縣城的時候,已經萬家燈火了。陳奐生一點也不著急,他悠閒得很,好像已經到了家裡。不,不是到了家,而是陳奐生心裡太舒服,因此覺得這世界上的一切都很親切,到東到西,都像在自己家裡一樣。他一路上碰到所有的人,都覺得很親愛;那些老人,那些孩子,那些老漢,那些婦女,都像是自己人。在火車上,坐在陳奐生對面的一個中年女人,漂亮極了,使陳奐生想起了自己的老婆;不錯,老婆是很醜的,但總覺得那個漂亮女人有些地方很像自己的老婆。是眼睛嗎?鼻子嗎?還是嘴巴呢?好像是,又好像都不是;總之吃准了有些相像的地方,不過是吃不准什麼地方像罷了。陳奐生因此就開心,想像著自己的老婆如果也和那漂亮女人一樣細細地打扮起來的話,一定也會把男人的烏珠兒吊出眼窩來的。
走出車站,陳奐生知道已經沒有汽車下鄉了。他橫豎不想乘汽車,也不要住旅館,早早晚晚只要兩隻長腳晃蕩晃蕩,到家極容易。所以他一點不急,像了結了人生的一切大事,可以隨便遊轉了。他走過一向擺攤賣油繩的地方,依戀地逗留了一會,好像在尋找那少掉的三角錢;他又去看了看那次病倒、落難困著的長椅,想起和吳楚的邂逅,誰知道這竟是他命運的轉機。咦呀,一個人活在世上,原不必窮凶極惡,苦也罷,樂也罷。總要憑良心過日腳,要吃、要穿、要錢用,就老老實實出力氣去賺,不要挖空心思去轉歪念頭。自己想發財去害別人,到頭來總沒路好走。吳書記這條路,大隊書記、廠長自己不能走,卻叫他陳奐生走,也就能看出「天意」
了。
想到這裡,陳奐生心裡坦蕩蕩,無憂無慮;天氣雖冷,胸中滾熱。他劃著兩隻長腳,提著賣過油繩的旅行包,輕悠悠地摸黑走回去,看那夜空裡的寒星,也覺得明亮清爽。他確實很滿意,回顧自己的生平,也找不出一件快事能和今天比較。他不禁想起大隊裡那個說書的陸龍飛,講過薛仁貴征東,岳武穆抗金;大將軍旗開得勝,班師還朝,也不過像今天我陳奐生這樣吧!當然,那些人是騎了高頭大馬回來的,不像自己靠「11」號;威風雖然威風,其實大官也不容易做,從來伴君如伴虎,皇帝一變臉,午朝門外就殺頭,真不及自己安穩呢。
陳奐生手裡拎的旅行包,裝得滿鼓鼓的,不是金,不是銀,也不是油繩;而是老阿姨送給陳奐生老婆穿的幾件舊衣裳。陳奐生把它看成了寶貝,不是值錢,而是情重如山哪!這是他用勤儉老實換得的關切和尊重,憑這就證明了吳書記一家對自己的情意。他回來的時候,吳書記還在外面檢查工作;假使吳書記在家,也許會有更多關心的表示。因此,陳奐生竟然想到了買上一斤塊塊糖,他要告訴老婆和他的孩子,這糖是吳書記給孩子們的禮物。這不是騙人,因為吳書記定會這樣做,這叫知情著意,方稱得上知己呀!
勝利是勝利了,但是陳奐生覺得自己實在幹不了這個行當。外面的世界這樣複雜,如果碰到壞人,把自己賣掉了,也會不自知。他決不想吹牛皮,他在外面一共十六天,除了整理好一塊菜畦之外,什麼事情都不是他幹出來的。沒有吳書記、劉主任、老阿姨以及新交的朋友林真和的幫忙,他會連屬屎都摸不著茅坑的,還能幹什麼。所以,林真和那一噸材料,不給他還有良心嗎!
……
果然,回來以後,書記、廠長都把他捧得幾乎上天,工交辦公室原來也並不真指望他能辦成功,不想居然也拿到了兩噸,也喜出望外;拿他做例子,在全公社的採購員面前吹噓。陳奐生成了香狸貓的卵子。
但是,陳奐生在外面出了大力氣幹的一件事情,回來卻碰了壁。那是開了提貨單以後,要把材料運到火車站去托運。叫一輛汽車,要六十元錢,叫板車拉,算算也要五六十。按林真和的意思,根本不在乎,橫豎回去報銷。但陳奐生捨不得,他想想,這六十元錢,一個農民要辛辛苦苦做上二三個月才賺得到。這五噸材料,自己借一部板車來拖,頂多兩天也拖完了,與其讓別人把錢賺去,自己不好賺嗎!所以他主張和林真和兩人動手拖。板車他早已看在眼裡,地委大院裡有幾部停在那兒,問劉主任借一借,不會不肯。林真和不同意,說是多花掉的力氣;自己拖了,沒有發票,回去報銷會說不清。會計根本不會肯報。陳奐生哪裡肯聽,沒有發票有啥關係,難道材料沒人拖,它自己能跑到火車站去嗎。會計又不是呆大,連這點道理都不懂。即使有意見,他陳奐生也可以便宜些,不要六十,算個三十、四十,也好嘛!這樣廠裡、個人都沾光,為什麼不幹。說來說去,林真和見他不肯聽,也只好隨他。但朋友交情,又不能不幫忙,只得跟在板車後面幫他推一把。聲明自己不想要這腳錢。兩個人整整拖了兩天,汗水流了幾碗。可是陳奐生向會計報帳,會計竟然一文不付。氣得奐生罵山門,問會計可是吃飯長大的?會計也不示弱,聲明制度如此,誰也不能破壞。還笑奐生小算,貪小利,誰叫你出那麼大力氣去運呢,都像你這樣,運輸公司不要關門嗎!你只想獨吃飯,飯也應該留點別人吃吃嘛!公說公理,婆說婆理,鈔票還在會計抽斗裡。陳奐生火也沒用,只好破口罵娘,說什麼「早曉得行了好心沒有好報,倒不如省點力氣同老婆困覺」。唉!真不相干。
哪知過了三天,會計竟把他叫了去,拉開抽斗,數出一大疊鈔票,一共五百八十三元二角,叫奐生當面點清,說這是按廠裡規定,付給他的獎金:一噸獎一百五,連工交辦公室的一共四噸,就是六百元,扣除了陳奐生十六元八角預支的路費。
陳奐生驚呆了,不相信這是真的;但事實攤在他的面前,不由他不信。他數著那票子,兩隻手瑟瑟地發抖。他活了四十八歲,從來不曾數過這麼多的鈔票。更別說佔有了。假使在農業上,就算現在工分單價提高了,至少也要起早磨夜做一年。陳奐生把錢拿回去,好一陣心裡不落實,他反反復複在想:「難道這是應該的?」
村子上的人都羡慕他,誰也沒有說他不該拿。陳奐生卻比以前更沉默了,他認定這一筆飛來橫財不是他的勞動所得。他拿了,卻想不出究竟有哪些人受了損失。
為什麼出力流汗拖板車卻沒有報酬?為什麼不出力氣卻賺大錢?為什麼吳書記寫條子求援兩噸搞不到?為什麼劉主任跑一趟就答應了五噸?這些問題在陳奐生腦子裡轉來轉去,像擺了迷魂陣。沒有人向他解釋,他也不好意思請教,怕別人說他笨。常常半夜裡醒過來,推推老婆嘮叨這些話,也不過是想讓心頭輕鬆些。但是老婆看見家裡有了錢,心寬了,夜裡困得特別沉;好不容易被推醒了,聽奐生一嘮叨,就罵他十敗命,只配做一「漏斗戶」!然後翻一個身,又睡著了。
1981.1於常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