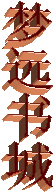
高曉聲文集 「漏斗戶」主
欠債總是要還的。現在又該考慮還債了。有得還,倒也罷了,沒有呢?
陳奐生背了一身債,不是錢債,是糧債。近十年來,他年年虧糧,而且越虧越多。他約摸估計,等今年口糧分下來後,還清債,連做年夜飯的米都不會有。但是,寧可沒有吃,還是一定要還的。他總是這樣對老婆說:「我們已經是『漏斗戶』了,還能再失掉信用嗎?」
他說這些話的時候,臉色很平板,但心裡卻禁不住要顫抖,他真愧對老婆孩子,自己沒有養家活口的本事。他力氣不比人家小,勞動不比別人差,可他竟落到了這個地步,在人面前連頭也抬不起。
同他相好的一些人,都替他著急,常常忍不住要替他歎息說:「奐生呀,到哪一年你才夠吃呢?」
陳奐生聽了,總是默不作聲,別人也就不說了。因為這個問題,沒有人能夠回答。
年輕的時候,陳奐生有個綽號,叫「青魚」。這是讚美他骨骼高大,身胚結實;但也有惋惜他直頭直腦,只會勞動,沒有打算的含義在裡面。他往往像青魚一樣,尾巴一扇,向前直穿,連碰破頭都不管。性格未免有點危險。這幾年來,在「青魚」
上面,又被加上了「投煞」兩個字,成了「投煞青魚」。這就不僅突出了他的性格,而且表明了他的處境;他確實像圍在阿裡的青魚,心慌亂投了。常有這樣的情形:他和社員們一起從田裡勞動歸來,別人到家就端到飯碗了;而他呢,揭開鍋一看,空空如也,老婆不聲不響在納鞋底,兩個孩子睜大眼睛盯住看他,原來飯米還不知在哪家米圍裡、他能不心慌亂投嗎!
「漏斗戶」主是不好當的,哪個「漏斗戶」主不是「投煞青魚」呢?虧了糧,要能借得著吃也真不容易。每年分配,各人都有自己的一份糧,誰也不特殊;若要借,不肯的人會說:「你不夠吃,我就夠吃嗎?」這句話,陳奐生不知聽過多少遍了。集體的儲備糧,年年有得借一些,但是有時間性,總要到快要農忙的時候才借。其他時候想借就難了,有的幹部會說:「別人夠吃,為什麼獨你不夠?」這句話,陳奐生也不知聽過多少遍了。這些人似乎都認為陳奐生是傻瓜,連這樣簡單的道理都不懂。而陳奐生卻奇怪他們為什麼老愛念這種「緊箍咒」,卻不肯看一看簡單的事實。世界上每一個人的情況本來不是一樣的,為什麼竟說成是應該一樣的呢?
但是,他總是體諒他們,他們是有他們的難處。大多數幹部通常是為他盡力的,曾經替他豁免過一百五十斤借糧,年底裡也往往有一點經濟照顧;不過他們只能做職權範圍內能做的事。他們有時候對他態度不好,其實也有替他煩惱的情緒在裡邊。現在糧食沒有過關,無法滿足他的要求啊。有的人這樣對他說:「虧糧不是你一個人的問題,有一大批人呢。如果光是你一個人,倒又容易解決了。」這種話雖然並不實惠,他聽了卻也有些心安,不但不埋怨「也有這個問題」的那一批人連累了自己,倒反欣慰有許多同伴。此外,心底裡也有一個模糊的疑問,卻又塞在胸口說不清楚而不愜意。那疑問大概是說:「為什麼牽涉到了一批人的問題倒反不去努力解決?」
一九七一年本來大有希望,因為這一年又重新搞「三定」了。當時陳奐生還只是個「新生」的缺糧戶,僅僅是因為老婆過門時娘家「忘記」把她的口糧帶過來造成的。那時候,關心他的人勸他說:「奐生,你應該去把口糧要過來,不好客氣哪!」
他卻極動感情地回答說:「他們連人都肯給我,這點糧叫我怎好開口呢?」這句話把勸說的人也打動了。他們都清楚,奐生確實是一無所有,他父母生下四男四女,女的嫁了不說,三個男的都和女的一樣嫁了,單留他一個養老。而他盡了一切責任以後,父母卻只遺留給他一間破屋,拖到三十四歲才算找到了這個對象,他對岳家感激不盡,還提什麼糧不糧呢?況且岳家並非故意為難新女婿,也是實在拿不出來啊!可是想不到,老婆生過腦炎,有後遺症,不大靈活,不大能勞動,這就成了大問題。但事已如此,奐生卻能想得通,他覺得這個女人如果十全十美,他也沒有條件同她配對了。因此,有些關心的人勸他應該鉗制老婆下田勞動時,他為難地說:
「她是個沒用的人,嫁了個我這樣的男人,也算得可憐了,我怎能再去勉強她呢。」
如此,別人除了感動以外,就只有歎息了。女人呢,也曉得體貼奐生,雖然不大會做,但據岳母來後的觀察,則說:「比做姑娘的時候會多了。」這已足夠他高興。以後就是生孩子,三年兩個,不巧又都生在正月裡,按當地的規定當年的口糧沒有供應,於是糧食又虧了一層。七一年是增產的,按年初的「三定」分配,生產隊除了公糧、餘糧、平均口糧、飼料糧和種籽以外,還多四萬六千斤超產糧。照「四六」
開的辦法,國家購去四成,計一萬八千四百斤,其餘的二萬七千六百斤,應該留隊作為社員的勞動獎糧。陳奐生的工分是五百四十七工,占總工分的百分之二點三,得到的獎糧數是六百三十四斤八兩,已經足夠使他踢開「缺糧戶」的帽子了。想不到這竟是騙騙人的,結果仍舊照「有一斤餘糧就得賣一斤」的公式處理了。真是吊足了胃口,騙飽了肚皮。
「為什麼說話不算數呢?」陳奐生心裡有疑問,但是不肯說出來,怕人家笑他餓昏了,連這樣簡單的道理都不懂。
可是畢竟也還有不買帳的人提出來了。得到的答覆卻更不買帳:你們要這麼多糧食做什麼?吃不掉還賣黑市嗎?還是貢獻給國家好!
陳奐生聽到了,心裡並沒有服,他明明是不夠吃,為什麼偏要冤枉他吃不掉呢?
這也罷了。偏還有雪上加霜的事情來。公社派到生產隊裡來的那位「包隊幹部」
(好大的口氣,驚人的名稱,眼裡還有群眾嗎?)為了爭取產量達到一千斤,稻子軋下後不曬太陽就分給了社員,等到曬乾可以上機加工的時候,一百斤只剩下八十九斤。面對這個事實,陳奐生毛骨悚然,他不愁自己少分了糧食,而是擔心這樣一來,大家的口糧更加緊張,他就更難借到了。
於是,他禁不住要歎口氣:「唉——!」
這一聲長歎,偏偏被他的堂兄、小學教師陳正清聽見了。
「還歎什麼氣?」陳正清似惱非惱地說,「現在,『革命』已進入改造我們肚皮的階段,你怎麼還不懂?連報紙也不看,一點不自覺。」
「改造肚皮?」陳奐生驚異了。
「當然。」陳正清泰然道,「現在的『革命』是純精神的,非物質的,是同肚皮絕對矛盾而和肺部絕對統一的,所以必須把肚皮改造成肺,雙管齊下去呼吸新鮮空氣!」
「能改造嗎?」陳奐生搖搖頭。
「不能改造就吃藥。」
「什麼藥?」
「蠱藥,是用毒蟲的口水煉成的,此藥更能解除人體的病痛,你吃下去就發瘋,一瘋,就萬事大吉!」
「唉,老哥,你真是……還有興趣尋我的開心!」
「是正經話。」正清大聲說,「就是我們辦不到!」
是的,辦不到。那就做「漏斗戶」吧。
可是,使陳奐生耿耿在心的,偏偏就是某幹部在拒絕借糧後罵了他一句:「你這個『漏斗戶』!」
「這個帽子是哪裡來的?」他常常忿忿地想,「這是富人嘲笑窮人,地主嘲笑農民。共產黨的幹部,能這樣看待困難戶嗎?我種了一世田,你倒替我定了個『漏斗戶』的罪名。你就只曉得我糧食不夠吃,卻不曉得我一生出了多少力!」然而,時間一長,這種忿忿也沒有了,陳奐生徹底認輸,當上了「漏斗戶」主。
陳奐生越來越沉默了,表情也越來越木然了。他總是低著頭,默默地勞動,默默地走路。他從不叫苦,也從不透露心思,但看著他的樣子,沒有一個人不清楚,他想的只有一件東西,就是糧食。有些黃昏,他也到相好的人家去閒逛,兩手插在褲袋裡,低著頭默默坐著,整整坐半夜,不說一句話,把主人的心都坐酸了,叫人由不得產生「他吃過晚飯沒有?」的猜測,由衷地發出一聲輕微的歎息。而他則猛醒過來,拔腳就走,讓主人關門睡覺。這樣的時候,總給別人帶來一種深沉的憂鬱,好象隔著關了的大門,還聽得到夜空中傳來他的饑腸轆轆聲。
陳奐生的思想雖然並不細密,但也能感受到這種無言的同情,他和相好的人一同默默坐著的時候,他總覺得別人也在想著他心裡想的事情。如果這時候他說一句
「再借幾斤米給我」的話,他總是發覺對方早就準備好了儘量使他滿意的答覆。他又是感動,又是慚愧。他和他們都是從舊社會過來的,他們的經歷(包括他們自己和祖輩)使他們的感情都早同舊社會決裂了。現在,在新社會裡,許多人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而他卻愚蠢地沒有找到。儘管這樣,他還是一點沒有辦法懷念過去,能夠寄託希望的只有現在。所以他一刻也沒有失去信心,即使是餓得頭昏目眩,他還是同社員們一起下田勞動,既不鬆勁,也不抱怨。他仍舊是響噹噹的勞動力,仍舊是像青魚一樣,尾巴一扇,往前直穿的積極分子,這使同情他的人十分心痛。但是,也並非所有的人都能理解這種美德,刻薄的人卻說:「他還能不做嗎,不做就更沒有吃了。」
而且還不止此!陳奐生本來是勤快而樂於助人的,別人央求他幫忙做一點事情,他幾乎從未推倭過,歷來如此。誰也不否認這一點。可是他也有一點嗜好——吸煙。在他有錢買煙的時候,別人請他做事,請他吸支煙,誰也不以為奇,決沒有人認為他幫助別人做事是為了一兩支香煙;因為他勞動的代價決不是那幾支煙能夠抵消的。但是,到他當了「漏斗戶」主,無錢買煙的時候,刻薄的人卻竟會這樣說:「只要給他一支煙,他能跟你轉半天。」甚至一個星期只燒一頓米飯,背後也有人指責他
「有了就死吃」,「餓煞鬼一樣,吃相真難看」。因而就說這種人不值得同情,是
「提不起來了」的。為了使這個結論有絕對的權威,就牽牽拉拉地說到「豬也養不壯」,「雞鴨養不大」,「新衣裳穿上了身也不曉得換,一直到穿破了才歇」等等。真同一個笑話裡責怪窮人「沒有米吃為什麼不吃肉」的那種混蛋邏輯一樣。
看來,當了「漏斗戶」主。名譽也能輕易毀掉的。
陳奐生能說什麼呢,自己吃苦果,自己最曉得滋味。他的思想本來是簡單的,當了「漏斗戶」主之後,這簡單的思想又高度集中在一個最簡單的事情——糧食上,以至於許多人都似乎看透了他的腦筋。可是,誰也沒有意識到,正因為他想糧食的事情想得比別人多,他的見解也就很豐富,只不過是沒有能力把那些萌動的思想表達清楚罷了。他不相信「糧食分多了黑市就猖撅」的說法,認為像自己這樣的人家也有了餘糧的話,就不會再有黑市了。在口糧緊張的情況下,他不相信用糧食獎勵養豬是積極的辦法,因為大部分社員想方設法養豬的目的已是為了取得獎糧來彌補口糧,小耳朵盼大耳朵的糧食吃,養豬事業是不會有多大發展的。他不相信「有一斤餘糧就得賣一斤」的辦法是正確的,因為它使農民對糧食的需要,同收成的好壞幾乎不發生關係,生產的勁頭低落了。他不瞭解國家究竟困難到了什麼程度,為什麼到了已經有許多人家寅吃卯糧的情況下還不放寬尺度?這樣下去,農業生產不會上,只會落。最後,他還不相信分配口糧的辦法是完全合理的,因為它只考慮了一般情況而不考慮特殊情況。他自己就是一個明顯的例證。假使他能無糧食之憂——
哪怕稍微緊一點也無妨——那麼,他就會有成倍成倍的力氣去進行勞動。他做夢也指望自己能像英雄那樣去大幹一場,爹娘生就他一副好身材就是為了和大地搏鬥的;當然也希望雞鴨成群,豬羊滿圈。卻想不到竟被「漏斗」箍住了手腳,窩囊得血液都發黴了。用不到別人說閒話,他自己都覺得不爭氣,自己都覺得窮困在拖著他墮落。他向來心地光明,從不偷偷摸摸;可是,這幾年來,忙於奔走借糧,工分比別人少做了一些,負擔又重,分配時不大有現金收入了;因此不得不從不夠吃的糧食裡面再拿出一點來,賣了黑市價,換幾斤鹽回來煮菜吃。他做這種事,真覺得比做偷兒還心虛,萬一被人發覺,他就再也借不到糧食了。就會被許多人更看成是「提不起來」的戶頭了。但不幹又不行,糧不夠,瓜菜代,瓜菜裡總得放點鹽啊!所以,為了穩當起見,僅僅賣五斤米,他得天不亮就動身,趕到遠離家鄉的市場上去出售,以免碰到熟人。他做這種事情的時候,總覺得像有人拿著保險刀片在一小塊一小塊地割他的心,但又有什麼辦法呢,否則鹽錢哪裡來?搞副業嗎,已被判為資本主義道路了,他還有點自尊心,不肯犯這個「錯誤」呢。
「漏斗戶」主真難啊!特別是那些還有自尊心的「漏斗戶」主。
有一天晚上,陳奐生終於忍不住了,他跑到小學裡去找堂兄陳正清老師,想請他寫封信給報社,反映反映他的情況。
陳正清一本正經地搖搖頭說:「不能寫。」
「為什麼?」
「在社會主義社會裡,根本就沒有你說的這種事實。」
「這是我自己的事情,還會騙你嗎?」
「我知道你不騙我,」陳正清忽然生氣道,「可是你不懂,事實是為需要服務的,凡是事實,都要能夠證明社會主義是天堂,所以你說的都不是事實,我若替你寫這種信,那就是毒草,飯碗敲碎不算,還會把我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叫我永世不得翻身的!」
陳奐生嚇了一跳,忙說:「不寫就不寫吧,你別惱,我不害你,」說著,拔腳要走。
陳正清一把拉住了他,原想笑著向他道歉,卻忽然濕了眼,悲愴地說:「熬不下去啊,特別是我也懂一點……」
艱難的歲月啊,只有那些不僅關注上層的鬥爭,而且也完全看清陳奐生他們生活實情的人們,才會真正認識到林彪、「四人幫」把國家害到了什麼程度。
陳奐生沒有這種覺悟,他也沒有心思去考慮這樣大的大事,但陳正清也終於努力使他懂得一點,他比以往更明白,他是不該吃這樣的苦頭的。他弄不清也沒有能力追究責任,但聽了那麼多謊言以後,語言終究也對他失去了魅力。他相信的只有一樣東西,就是事實。
「四人幫」粉碎了,他的平板的臉上也出現過短暫的笑容,但跟著肚子裡一陣嘰咕就消失了。他還是當他的「漏斗戶」主,最相信的還是事實。
儘管陳正清的情緒變好了,同他講了好幾次充滿希望的話;也儘管陳奐生信任他,但卻實篤篤地問道:「現在你能替我寫信了嗎?」
這就把陳正清難倒了,即使形勢變得如此之好,他也還沒有膽量把陳奐生的情形在社會上攤出來。因為有許多的人還不肯承認這種現實,而且似乎也和當前的大好形勢不相稱了。儘管中央領導同志已經明白地指出我們的國民經濟已瀕於垮臺,但一個小人物也說這樣的話卻照樣會被某些人指責是對社會主義的攻擊。這就是當代的玄學。
看到正清如此為難,陳奐生平板的臉上自信地笑了,他說:「還是再看看吧。」
這句話,使他有足夠的資格當「漏斗戶」的代表。
一九七六年冬季分配過去了,一九七七年又過去了,一九七八年夏季分配又過去了,雙季稻的前季稻又分配了,一切如舊,政策不動。陳奐生的「漏斗」裡又增虧了一個數字。唉,有什麼仙法能改變他的情況呢,從前不是有人已經對他講過嗎,這不是他一個人的問題,而是一大批人的問題啊。
陳奐生認為這是可以原諒的,因為他自己也想不出解決的辦法。可是有一點,只是一點點,陳奐生卻又著實不滿,大家明明知道,雙季稻的出米率比粳稻低百分之五到十,為什麼從來沒有一個人替農民算算這筆賬。他陳奐生虧糧十年,至今細算算也只虧了一千三百五十九斤。如果加上由於挨餓節省的糧食也算這個數字,一共虧二千七百十八斤。以三七折計算,折成成品糧一千九百○二斤六兩。可是十年中稱四雙季稻六千斤,按出米率低百分之七點五計算,就少吃了四百五十斤大米。占了總虧糧數的百分之二十三。難道連這一點都還不能改變嗎?
陳奐生卻不想說出來,因為這太小算了,真是只有他這樣餓慌了的人才會這樣小算。而且這又不是欺他一個人。按照他歷來的看法,只要不是欺他一個人的事,也就不算是欺他。就算是真正的不公平,也會有比他強得多的人出來鳴冤,他有什麼本事做出頭椽子呢。
「還是再看看吧。」他肚裡尋思,不敢再想下去,也看不到希望。
他看不到希望是對的。原來希望竟在他身後追趕著他,不在他的前面要他去追趕。
有一次,陳正清告訴他說:「要搞三定了。」他馬上想起了七一年,堅決地搖搖頭說:「空心瀝團。」
「你不相信嗎?」
「還是再看看吧。」他說,心裡想:餓倒也罷,別再引誘我去想肉的味道了。
「你看好了,這次是一定的。」陳正清努力要說服他。
奐生悶悶地回答說:「再餓了一年看。」這意思是說,「三定」作為計劃,也只有到七九年春才會制訂,制訂後會不會兌現,要到七九年冬才見分曉。遠著呢,豬還沒有生下來,倒想吃肉了!
秋忙過去了,分明是繼夏熟大豐收以後的又一個大豐收,一大堆一大堆的糧食耀花了大家的眼睛,可是,陳奐生卻在想著今年的年夜飯米去向哪家借。
一個星期六的傍晚,陳正清從學校回家,興奮地大聲對奐生說:「看你再不相信吧,今年就要照七一年的三定辦法分配!」
這個聲響是巨大的,即使不能把奐生心頭的冰塊融掉,也該把它震碎了。但震碎的冰塊仍舊是堅硬的,他不願意上當,也高聲回答說:「說得太好聽了!」
陳正清笑了:「我不來和你爭,橫豎是眼前的事情了。」
「看看再說吧。」他還是那句話。
可是,晚上他睡不著覺了。「要是真的呢?」這個念頭纏住了他。但在別人面前卻不肯問起,怕給人家笑。
謠傳卻愈來愈多,終於很快就證實了,隊長傳達三級幹部會議公佈的分配辦法,同陳正清說的一模一樣。陳奐生的心激動了,甚至一想到這件事就顫抖,他的希望熾烈地猛燒起來,又怕萬一再被冷水潑滅。十年來額三倒四,倏忽萬變的政策在他心上的投影還那麼清晰而亂七八糟,使他迷信地感到「七一年」這三個字不像好兆。生怕再被一場惡夢繚繞。他強忍住心底的健羨,告誡自己說:「還是再看看吧。」
幾天之內,生產隊的方案造好了。在造方案的那幾天,會計家裡出出進進的人流整日不斷,有的人一天去了七八次,最後會計只得把自己鎖在房間裡工作。但是一個總的數字大家都知道了,照七一年「三定」算,今年生產隊超產了六萬七千一百斤糧食。
「六——萬——七——千—————百斤」,這個龐大的數字立即成為統治全體社員思想的權威,成為田間、場頭、飯桌上。枕頭邊的唯一話題。每一個當家人都在燈光下撥著算盤珠子約摸估道計算著自家將會分到多少糧食,算完一遍又一遍,一遍一次驚怪地詫異是不是算錯了,似乎不是他們自己在撥動算珠,而是有一個童話裡那樣可愛的神仙在暗中幫他們加到了一個巨額的數字。就這樣他們反反復複地做著這個遊戲直到深夜,在普遍的喜悅中共同憂愁著沒有足夠的容器盛放那麼多的糧食。
酷熱的炎夏被人們認為將有一個嚴寒的隆冬,但是到現在為止卻一直很溫暖,天氣的變化當然也難預料,說不定也會出現凍結大地的酷冷;可是不管它冷到什麼程度,也不能影響人們心中早開的鮮花了。大家感到現在已是春天,大自然只得無可奈何。
就在這樣的暖冬裡,一天上午,在背風向陽的地方,社員們被召集來聽取會計造好的分配方案。這是一個難得見到的社員會議,不管是男的女的、老的小的,都沒有一點聲音,都沒有一點動作,他們都聚精會神地伸長脖頸、睜大眼睛靜靜地聽講,有些則張大嘴巴似乎想把會計的聲音吃進肚裡。會計的平靜的語調像一支魔笛吹響的神曲,攫住了全體聽眾的靈魂。他們在享受如此美妙的音樂的同時,直感到一個新的時期已經具體地來到了自己的面前,不僅看得見而且摸得著了。
他們心底的激動和歡樂,用文字來描摹是徒勞的,可是在幾億社員隨著這支樂曲的節奏邁開舞步時,大家會驚異地看到我們的遠景忽然一下子推近到身邊,將馬上發現我們偉大的農民無一不是耍弄糧食的超級雜技演員,能夠用他們各自特有的方式將它變出千百萬種無窮無盡的奇珍異寶。
現在,樂曲還在演奏著,陳奐生的那個音鍵捺響了。在陳奐生名下,一共分配到三千六百零五斤糧食,比去年的二千二百五十九斤多了一千三百四十六斤,這個標準同大多數社員比較起來還顯得低了一點,因為他缺乏飼料,全年只養了二百九十斤豬,僅僅超額完成任務九十八斤而沒有得到更多的超產獎,即使如此,光是這二百九十斤豬,也比去年多分到三百六十五斤糧食。
會計把方案讀完了。停了三分鐘以後,大家才知道他真的讀完了。這才嘩啦啦地吵鬧起來,就像早晨打開了鴨棚,嘈嘈雜雜,已經無法聽清哪一個在說哪一些話了。但也有天生喉嚨大的,在喊著:
「大解決了。年年巴望糧食寬一點,寬一點,一直巴不到,現在一下子寬得叫我們想也想不著!」
「養豬養雞盡養吧。」
「拔光了毛的翅膀這一回又會長出毛來高飛了!」……
陳奐生什麼也沒有說,他靜靜地坐在那兒不動,像是傻了。一會兒,他決然站起來,朝主持會議的隊長走近去,閃雷似地問道:「鑿定了嗎?」
「當然。
「不變了嗎?」
「還變到哪裡去!」
「那麼,」陳奐生挑戰地說,「現在就分給我。」
生產隊長驚訝地看了他一眼,明白了。「好。」他爽快地說,「大家回去拿籮擔,馬上就分。」
禾場上,曬乾揚淨的金黃稻穀堆成山。大家聚攏了,隊長說:「開秤吧!」他向人叢裡看了看,瞧見了奐生,喊道:「奐生,第一個稱給你!」
這時候,人群忽然靜下來,幾百隻眼睛靜靜地看著陳奐生,讓路給他走上來,好像承認只有他有權第一個稱糧。
陳奐生走到過秤處,司秤員開始工作起來,一籮籮過了秤的糧食堆放到陳奐生指定的另一塊乾淨的空地上,堆得越來越高,越來越大。陳奐生默默看著,看著……
他心頭的冰塊一下子完全消融了;冰水注滿了眼眶,溢了出來,像甘露一樣,滋潤了那副長久乾枯的臉容,放射出光澤來。當他找著淚水難為情地朝大家微笑時,他看到許多人的眼睛都潤濕了,於是他不再克制,縱情任眼淚像瀑布般直瀉而出。
1978.12.7——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