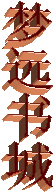
高曉聲文集 系心帶
鄉村汽車站的下午是寧靜的。小小的候車室裡,散散落落放著幾張靠背長椅,只有五六個旅客寂寞地在那裡等車。他們的車票都已經買好了,但是還不知道什麼時候能搭上車子;如果汽車在前一個站頭已經滿載了,到了這裡又無人下車,它就直駛而過,不再停頓。這樣的事情是常常發生的,今天下午就出現過兩次。眼睜睜望著別人在前進,自己卻停留在原地不動,總覺得有點悵惘。但焦急毫無用處,有了車票並不等於就有了位置,位置是需要正有得空,或者別人讓給你,才能獲得的。經常在鄉村車站上下的旅客,大都有這種經驗。然而他們並不失望,因為他們知道時間越晚車越空,歸根到底總有位置給他們。因此他們乾脆不去盤算,有的看書,有的躺下假寐,有的就細細地欣賞貼在牆上的宣傳畫;實在無事可做的人,則充當臨時的數學家,先數清房頂有幾根椽子,再算算有多少塊鋪地磚……儘量對時間的逝去表示毫不介意。
因為誤點,李稼夫同志把來送行的人都推回去了。在家都忙著工作,沒有必要為他耽誤生產。他要對他們講的話都已經講過了,要講的話終究也不能都想到並且都講過。一切都應該有一個自然而然的結束,然後也會有一個自然而然的開始。他在這裡的時候大家都認為非有他不可,他一旦走了,或許別人會發現:不依賴他倒反容易進步。歷來如此。
汽車終於又來了,他走出車站,車卻又開過去了。他不想再回到那個寂寞的候車室裡去,就在公路邊樹底下一塊石頭上坐了下來。他呼吸著鮮潔清香的空氣,讓和煦明麗的陽光透過枝葉扶疏的楓楊,一線線射在身上。他撫摸著花白的頭髮,抬起瘦削而顯得蒼老的臉龐,眯縫著眼睛看了看晴朗而高遠的天空,眼光隨著一隻盤旋的蒼鷹落到附近的幾座小山上。他第一次驚異地想到:在那寬闊的平原上面,怎麼會有這幾座孤零零的隆起的山頭。它們似乎不是地上長出來的,倒像是童話裡的神仙,帶了禮物出門作客,偶爾經過這裡,一時疏忽掉落下來的幾塊點心。山頭被平原上快要成熟的金黃色的稻海包圍著,一座座村莊,一叢叢樹木,也像騰空漂浮在海面上。李稼夫望著這熟悉的一切,忽然升起了一種無法克制的眷戀之情。
李稼夫在這塊地方整整生活了十個年頭。他不是抱著希望,而是希望被毀滅了之後來到這裡的。他是一個知識分子,出身也不大光彩,自從搭上社會主義這條船之後,倒是努力要做一個好的水手的。他的努力受到過稱讚,於是有一天就跟著稱讚他的人倒黴了。他既被當作「走資派」用人不當的證據,又被當作凡重用了他這樣的人就是「走資派」的證據。被這樣用過之後,他就失去了價值,被從船上拎出來,拋進了「大海」。在這一刹那之間,他忽然明白:有人駕船載著他迎著礁石開去,因為自己不願意毀滅,於是就先毀滅他。而他也明白,即使自己還待在船上,也沒有力量扭轉方向,好像他的毀滅已經註定了。
他記得,那時候他木然地被推上火車,然後又被汽車載到這裡扔下來。一路上他看到無數匆忙來往的旅客,似乎他們都堅定地朝著一個目標前進,知道去哪兒和去做什麼,知道有什麼樣的人在等待他們。只有他什麼也不知道,空空漠漠,似乎走出了這個世界。他從汽車上下來,望著這個陌生的小車站,陌生的走路人,以及那裡的情況一無所知的村莊和茫茫的田野,感到寒冷,感到顫抖。他不知道這裡的人會怎樣對付他這個「反動學術權威」,不知道將把他遣送到哪一個村莊,在哪一個屋頂下生活和怎樣生活,真像被拋進了大海般苦寒和窒息。
很久以來,他已經忘記了這種情景,就是在最後要離開的時候也沒有想起。因為現在的情形已經完全不同了,他在臨上車站之前,還緊張地想著一切必須交代清楚的工作,接著又是歡送他的人群在車站上伴了他許久……可是,汽車卻似乎故意不肯帶走他,要他在這個地方單獨地多留一點時間,強迫他去想一想來時怎樣?去時怎樣?
「總以為被丟進大海裡淹死了,結果雙腳卻站在堅實的大地上。觸礁毀滅的不是任何一個無辜的人,而只是那些大大小小罪惡的艦隊。」他微笑地看著被陽光照亮的山頭,想道,「生活好像要結束了,其實它永遠不會結束。不過是推移到了一個新的站頭,向你展示出另一個方面而已。一切企圖毀滅生活的人都是徒勞的。這個運動把我們許多同志推到生活的反面去了,粗淺地看去該是多麼不正常。獰笑著做這件事情的人,現在哀泣已為時太晚,因為這無非使我們的人多認識了生活的一個方面,從而變得更加聰明和更加有力量了。我們再也不會停滯在過去的生活裡。」
他望著那藍湛湛的天空,望著那只還在盤旋的老鷹,不禁想起了那一架著名的三叉戟飛機和那只天馬。他總覺得從那次事件以後,我們就有了測定「天才」的經驗了。那是並不費事的,以後凡遇自稱「天才」者,只要請他坐飛機升到高空,然後俯衝下來同大地相撞,苟能腦袋完整,自當刮目相看;如果天靈蓋也成齏粉了,那也只好表示惋惜而已。後來的那四個,本來是早該請他們去試一試。無奈死皮賴臉不肯去,一屁股坐在地上打滾,滿以為撞不著頭了,卻讓地火燒爛了屁股。李稼夫有趣地想著這些,獨個兒悠悠地笑了起來。
是的,混亂的時期已經結束了,他早就該離開這裡。調令已經下達了近一個月,他原來的機關裡還派了同志來找過他,催他盡可能快一點回去。他也已經允諾了。但是一直拖到今天,他才下決心離開這裡,因為他在這裡已經很習慣了。十年來,他在這個小汽車站上上下下乘過多少次車,總是來了又去,去了又來,都是為了這個地方和這個地方的人。民在忙碌。這裡的人民已經把他像紙鳶營一樣放到一個位置上了,而他也習慣於讓人民用一條線牽住他,使他能夠固定在那個位置上;以至於他想像不出萬一這條放紙鳶的線一斷,他會飛到什麼地方去。一直到他終於想明白,無論他在什麼地方,這條線再也不可能斷掉,即使他這次走了再沒有機會回來,他也不會忘記這個地方永遠是他的起點。他和人民的關係將始終千里姻緣一線牽,這一條紅綢絲帶將隨時傳遞雙方脈搏的跳動。於是他才決定離開。
這時,他注意到山頂上騰地飛起了幾隻小鳥,隨即傳來了「轟隆隆」的炮聲,他馬上猜想到崖壁上的岩石又剝落了一層,仿佛看見大塊大塊的岩石怎樣被震裂,慢慢地傾斜,然後迅速地倒坍下來;小石塊又怎樣飛濺到半空,雨點般落下來,同地上的岩石鏗鏗相撞。採石廠的生活真像一鍋開水般沸騰翻滾。李稼夫記得、他來到這裡的時候,古老的荒山還沉睡未醒,人們還習慣於派出船隊到一百多裡外的地方去運回石塊,來適應建築的需要;使他這個陌生人一開始就覺得奇怪。在一個偶然的場合裡,他向公社黨委書記講到了開發當地山石的可能性,講到公社與其千方百計、煞費苦心去籌辦其它工廠,倒不如辦一個採石廠來得容易,而且穩當可靠。想不到這個建議同書記的意見不謀而合,很快就動用了全公社的勞動力,開闢了一條三裡路長的河道,溝通了山腳同外界的運輸。一個小型採石廠建立起來了,發展到現在已經成為年收入二百萬以上的工廠。那開闢的三裡路河道,不僅僅是溝通了運輸,最終還證明它使他同公社領導人之間的心胸也溝通了。他們雖然無權把他解放出來,但是他們卻有權表示出對他有所諒解的態度。他愉快地回憶起自己如何參與了那個開發的計劃,以及怎樣教會那些剛剛丟掉鋤頭柄的新工人科學地使用炸藥。他也就看到了那個古老的山頭怎樣第一次開花。
現在,這老山上的石頭已經被當地人方便而廉價地廣泛運用,並且還供應了鄰近兩個城市的用材。平原上星羅棋佈的村莊,越來越多地建造起一幢幢下半截用石頭砌成的、堅實的新房子,被綠色的樹叢襯映得更加鮮黃醒目。在這個小小的汽車站上,也不知是在什麼時候搬來了一塊平整得可以當凳子坐的黃石。有無數個旅客曾坐在它上面等待過出發,從來不曾有誰感覺到自己的褲子受到過黃石的磨損;但黃石的粗糙的表面確實已經被這些旅客的褲子磨擦得平滑了。持久的生活以這樣巨大的力量影響著一切,李稼夫顯然也不是原來的那個人了。他臉上添加的皺紋並不是樹木的單純的年輪,新增的白髮更不是為了顯示他的蒼老,風霜和勞動給了他智慧,也給了他力量,這裡的人民終於教會了他,使他懂得並且堅定地相信,他這個人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對人民有用處。往後他不會害怕什麼了,儘管到現在為止,他仍舊設有學會保衛自己的那一套「本領」,但勇敢的人根本就無需那一套。今後的鬥爭還是不可避免的,即使他再被拋出來,他也能夠馬上找到自己的位置。就像他坐下的這一塊黃石,它誠然是孤零零地放置在這個小小的汽車站上,但是它每天讓旅客得到休息,每天都感覺到坐在它上面的人的心跳和呼吸,它終於也看盡了人世的悲歡離合,洞悉了過往的一切。它是有足夠的理由為自己緊靠著人民而感到滿意的。
人的尊嚴為什麼要受到那麼殘酷的侮辱?假使事前想到可能遭受的侮辱儘管比後來實際碰到的還輕十倍,也會覺得無法忍受。但是,李稼夫實際受到的侮辱比他事前能夠想像到的要惡毒百倍。為什麼倒又能夠對付過來?這是因為他遭受的一切太野蠻了,太獸性了,已經無可懷疑地證明不是社會主義的行為了,不是毛主席、不是共產黨、不是社會主義的人民在制裁他了。摧殘他的不過是一批野獸、一批法西斯惡棍、一批窮凶極惡的封建惡霸。因此他再也不肯輕率地自殺,他要活著,憤怒地去消滅他們呢。他永遠記得一九六七年秋天的那個晴朗的早晨,他胸口掛著用鐵絲吊在頸上的一塊二十七斤重的牌牌,站在市場上示眾的時候,來來往往有許多人停下來看著他;可是只要他也抬起頭來望望他們,他們就都低下頭去匆匆走開,連眼光都不敢同他相碰。他馬上就知道他們不是來嘲笑他的,他們是在同情他,甚至因為看到這種情形而羞恥,為了無法制止這種暴行而慚愧。他們是完全站在他一邊的。他意想不到自己是在這種情況下才第一次這樣深刻地理解了人民。他也就是依靠了這個認識,度過了當時精神的危機。
人生竟有這樣的經歷:有一次他被拖到社會上去參加批鬥大會,路上被踩脫了一隻鞋子,他不曾有抬回的自由,只好赤著一隻腳走去。會前他被單獨臨時禁閉在靠近會場的一間小屋裡。他緊張地等待著即將施加到他身上的狂暴。這時候他發現外面有人透過玻璃窗在窺視他。他立刻敏感到這是把他當作籠子裡的困獸在欣賞;他忍受不住這種動物園的遊戲,猛地。站到了窗口。他看到那個人的臉刷地漲得通紅,羞澀而痛苦地低垂著眼睛,惶遽地閃走了,而窗臺上卻放著他被踩落的那只鞋。這件事給李稼夫留下了不能磨滅的印象,因為他看到了那個人的臉上流露出來的感情比他自己還要難受。他同他素不相識,不知道他叫什麼名字,多大年紀,做什麼工作;他長得同大多數人一樣的身材,一樣的臉型,穿著大多數人一樣的衣服,毫無特色。但是他卻在李稼夫的腦海裡佔據了那麼特殊的地位,十年來無數次清晰地而且是越來越清晰地顯現出來。雖然後來一直沒有再看到這個人,但是李稼夫總覺得這個人在每一個群眾場合裡面,似乎一直伴隨著他,而使他終身難忘。
山頭那邊的遠空裡緩慢地飄過來一縷輕紗似的白雲,它無聲無息,高高在上;但寬闊的天空卻似乎只有作為它的背景才能證明自己確實存在。李稼夫不禁發出了一聲輕微的歎息。他想到自己過去的研究工作正像這一縷白雲,它和人民不發生任何直接聯繫,以至於許多人不知道他搞的是什麼名堂。太專門了,太尖端了。然而也只有同他相類似的那些專門的、尖端的科學研究,才能夠最終地對人民的生活發生巨大的影響。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其實也首先體現在這個方面,它保證了在比較窮困、比較落後的現實條件下進行最先進的科學研究,從而保證了它的前景會變成現實。它就是作為這樣的「白雲」的背景而存在,一旦「白雲」沒有了,人們也就失去了對它的實感。認識到這一點的日子終於來到了,一陣勁風吹散了迷霧,走破了腳底才發現自己仍站在原地,不得不忍著苦楚,咬緊牙關向前追趕。這一切該是多麼令人遺憾呀!
白雲漸漸地飄過來,自然地散成一條條越來越細的雲絲,最後在天空中消失了。李稼夫確實還感覺到它的存在,就像他自己在那個研究工作中消失而仍舊確實存在一樣。假如不消失,它也許會發展起來下一場好雨,潤濕乾燥的土地,旺發遍野的翠綠。但是它的消失終於還是作為物質存在,它的水分至少也增加了空氣的一點濕度,空氣也總會到達溫度的飽和點下起雨來的。十年來,李稼夫雖然一點也沒有能夠發揮自己的專長,但總也像消失了的白雲一樣,給這裡的空氣留下了一點濕度。人民在生活中對現代知識的需要迫切到了如此程度,使李稼夫使用他的一般常識就能夠替他們做很多事情。他無法想像僅僅是一點最普通的技藝,竟拆除了他這個
「勞改」的「反動權威」和當地人民之間的那堵厚牆。他曾經為了使長期生病的愛人(她已經長眠了)治療方便,學會了打針(注射),而他到這裡來了之後,卻發現人們一旦生病需要打針時,必須跑五裡路趕到公社醫院。於是他就非常輕易地得到了一個為他們服務的機會;一直到幾年以後,赤腳醫生這個新生事物出現為止。人們也就一下子認識到他是一個善良的、有用的人了。原來像站在高處用懷疑的眼光把他當怪物透視的群眾,就忽然變得親近了。一個老媽媽愛護地強迫他必須戴了涼帽下田,說他的皮膚太嫩,當心被太陽曬得額角頭上起泡。小夥子們也熱情地把著他的手教他勞動,似乎都要儘快地讓他變成他們中間的一個。在他們的幫助下,他花了不多的時間就學會了生活和勞動。他的知識馬上促使他開始改進這種生活和勞動。他利用煤油燈罩的形式,改進了煤球爐膛,達到了使煤近乎完全燃燒的程度;他發現了刈麥的速度決定于勞動者如何以自己為軸心,拉大扇形面積;他總結了提高蒔秧的速度在於盡可能地縮短兩手之間和手與泥面之間的距離的經驗……一切細微的但是顯然經過精心思考的在原有基礎上的提高,獲得了大家由衷的讚揚。接著而來就出現了一個反復多次的奇特的情況,一家家社員分別地、默默地但是十分執拗地把他拉回家去,關起門來陪著他吃一點專門為他準備的飲食。他們秘密地做著這一件事情,似乎有所顧忌,但又堅決要這樣去做。李稼夫很快就明白了,這就是人民用他們自己特有的方式在對他表達感情,表達他們對迫害他的人的抗議。這種抗議的形式又表明人民也是被迫害者,而他則毫無疑義被他們看成自己人了。他不禁感動得熱淚盈眶,覺得人民實在是太好了。他深深譴責自己曾經犯過的錯誤,譴責自己的工作至少做得太少、大不好了。特別是他自認為還不曾有足夠的行動,證明自己可以得到他們的信任,而信任已經給予了他;他就更加相信他們的正直。正是這種正直使他們非常實際和非常聰明,所以也就有非凡的判斷能力。從那時候起,他就對他們不再有任何保留,願意讓自己成為一面紙鴦,而把線的一端交在他們手裡,讓他們來處理自己的位置。並且認為只有這樣,他的位置才能適當而且得到固定。從這一點來說,他倒是希望自己是一朵已經消散的白雲,毫無影蹤地融合在他們中間。
十年的往事像洶湧的波濤,一霎時撲滿他的胸膛,思緒像一條條澗水,清晰地淌流出來。他帶著人民的恩情走上新的征途,心底裡會永遠蘊蓄著故地的懷念。一雙雙佈滿老繭的大手伸出來向他道別,叮囑一句山重海厚的話:「今後若再有三長兩短,你就到這裡來!」
啊,我的親人啊!……
公路遠處飛揚起一陣灰沙,一輛客車疾馳而來,這已經是今天的末班車了。他一定能夠乘上去。這時候他騰地升起一股怒火:十年了,按照原來的計劃,已經會有幾十個、成百個新人可以站上他的位置,可以把他的工作推到一個新的境地。可是,時代的列車縱然隆隆地開著,卻駭人地只見一個個老的旅客下車,稀疏地缺少新上的乘客,他那個位置始終還是空著,有誰能容忍這滔天大罪!
汽車停下來,打開門讓李稼夫拎著行李登了上去,於是又關門開動了。這時他忽然覺得掉了東西,伸出頭來瞧了瞧車站,他不禁笑了,原來他有意要把那塊石頭帶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