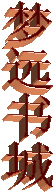
苓植文集 茶樓軼事
大褲襠胡同好就好在它的古色古香。
雖四周高樓乍起,大廈林立,它卻仍然是這邊塞古城特有的鬧市區。遊人扣織,川流不息。人稱口外王府井,又名漠北小天橋,足見其影響之深遠。
但最重要的去處卻當推古泉居茶樓!
地處要衝,引兩條褲腿兒裡的各路諸侯竟相到此一露尊容。諸如驢肉陳、雞眼侯、肉串楊、膏藥張等等,來一位就是一串兒故事。就連上茶樓湊熱鬧的老外聽後,也准得伸出大拇哥連聲用中國話喊:蒿!蒿!
可老茶客們卻在搖頭……
好什麼呀?就剩下了擀麵杖、大炒勺、鹵肉鍋、修腳刀這類玩藝兒,古泉居茶樓上還有什麼說得出口的絕活兒?大高樓的黑影兒拔盡了風水,真人就不來大褲襠胡同露相了!
您若不信,老茶客們還准能給您回憶一連串的奇人奇事兒!
茶樓作證!下面就是兩則……
其一鼻涕蟲
那還是在老年間……
也不知從哪兒鑽出這麼一位傻小子,大大咧咧地賴在大褲襠胡同愣不走了。
這愣頭青二十郎當歲。倒也生得膀大腰圓,但卻在長了一身好膘。鬆鬆垮垮,恰似堆憨乎乎會走的肥肉。再往上瞅,青皮腦瓜兒剃得鋥光瓦亮。天生娃娃臉一張,傻不溜秋,就會咧開那棉褲腰似的大嘴沖著人笑。
且瞧瞧他怎麼在這兒混飯吃!
大褲襠胡同就像條粘蒼蠅紙。黑乎油膩的,卻透著寬宏大量。只要您有一技之長,准保粘住您不放!您瞧瞧!就連打著蓮花落討吃叫街的瘸腿劉也算得一路諸侯,這足以證明兩條褲腿兒裡有多皇恩浩蕩了。
可這小子……
沒仨月,大夥兒就瞧出他是給大褲襠胡同抹黑來了。替瓦匠當小工子,他愣把苫泥扔不准地兒。瓦匠孫說他兩句,啪!這一鍬泥水竟應聲拍在瓦匠孫的腦門子上。替雜碎楊去燒火,得!就更出大漏子了。就在雜碎楊外出解大手這功夫,他愣把鍋給燒炸了。夠火爆熾烈的,就不該羊雜碎全變成了黑炭沫子,沒轍了!杠房仇又咬牙收留了他。誰料想,這位抬棺材也踩不住點兒。攪得眾人腳步一亂,又差點兒把死人給倒扣出來。他還笑,咧開大嘴傻笑。
您哪!整個兒的廢物點心一個!
這不是讓口外小天橋跟著掉價嗎?為此,諸如驢肉陳、肉串楊、燒餅王、修腳李等等各路好漢就難免憤憤不平。但細一打聽,卻原來和古泉居茶樓的老掌櫃有著某種干係。
但絕非桃色新聞……
據說,在一個月黑風高之夜,伸手不見五指的茶樓上驟然閃現出一位不速之客。身輕如燕,落地無聲。著夜行衣,見老掌櫃倒頭便拜。後來情況如何,不得而知。只曉得這位神秘客飄然消失之後,大褲襠胡同裡便多了一個窩囊種兒。
對!得摸摸底兒去……
要知道,古泉居茶樓正居兩條褲腿兒交接處要害部位。廣交胡同裡的各路諸侯,早成了大夥兒公認的「忠義堂」。而只要說到這兒,老掌櫃在眾人心目中的地位也就可想而知了。但誰料想到,這位平時以維護胡同榮譽為己任的老爺子,竟對此事來了個一問三不知。
「您說,這傻二姓什麼?」
「不知道。」
「總該有個名兒吧?」
地處要衝,引兩條褲腿兒裡的各路諸侯竟相到此一露尊容。諸如驢肉陳、雞眼侯,肉串楊、膏藥張等等,來一位就是一串兒故事。就連上茶樓湊熱鬧的老外聽後,也准得伸出大拇哥連聲用中國話喊:蒿!蒿!
可老茶客們卻在搖頭……
好什麼呀?就剩下了褂面杖。大炒勺、鹵肉鍋、修腳刀這類玩藝兒,古泉居茶樓上還有什麼說得出口的絕活兒?大高樓的黑影兒拔盡了風水,真人就不來大褲襠胡同露相了!
您若不信,老茶客們還准能給您回憶一連串的奇人奇事兒!
茶樓作證!下面就是兩則……
其一鼻涕蟲
那還是在老年間……
也不知從哪兒鑽出這麼一位傻小子,大大咧咧地賴在大褲襠胡同愣不走了。
這愣頭青二十郎當歲,倒也生得膀大腰圓,但卻在長了一身好膘。鬆鬆垮垮,恰似堆憨乎乎會走的肥肉。再往上瞅,青皮腦瓜兒剃得錫光瓦亮。天生娃娃臉一張,傻不溜秋,就會咧開那棉褲腰似的大嘴沖著人笑。
且瞧瞧他怎麼在這兒混飯吃!
大褲襠胡同就像條粘蒼蠅紙,黑乎油膩的,卻透著寬宏大量。只要您有一技之長,准保粘住您不放!您瞧瞧:就連打著蓮花落討吃叫街的瘸腿劉也算得一路諸侯,這足以證明兩條褲腿兒裡有多皇恩浩蕩了。
可這小子……
沒仁月,大夥兒就瞧出他是給大褲襠胡同抹黑來了。替瓦匠當小工子,他愣把苫泥
扔不准地兒。瓦匠孫說他兩句,啪:這一鍬泥水竟應聲拍在瓦匠孫的腦門子上。替雜碎楊去燒火,得!就更出大漏子了,就在雜碎楊外出解大手這功夫,他愣把鍋給燒炸了。夠火爆熾烈的,就不該羊雜碎全變成了黑炭沫子,沒轍了!杠房仇又咬牙收留了他。誰料想,這位抬棺材也踩不住點兒。攪得眾人腳步一亂,又差點兒把死人給倒扣出來。他還笑,咧開大嘴傻笑。
您哪!整個兒的廢物點心一個!
這不是讓口外小天橋跟著掉價嗎?為此,諸如驢肉陳、肉串楊、燒餅王、修腳李等等各路好漢就難免憤憤不平。但細一打聽,卻原來和古泉居茶樓的老掌櫃有著某種干係。
但絕非桃色新聞……
據說,在一個月黑風高之夜,伸手不見五指的茶樓上驟然閃現出一位不速之客。身輕如燕,落地無聲。著夜行衣,見老掌櫃倒頭便拜。後來情況如何,不得而知。只曉得這位神秘客飄然消失之後,大褲襠胡同裡便多了一個窩囊種兒。
對!得摸摸底兒去……
要知道,古泉居茶樓正居兩條褲腿兒交接處要害部位。廣交胡同裡的各路諸侯,早成了大夥兒公認的「忠義堂」。而只要說到這兒,老掌櫃在眾人心目中的地位也就可想而知了。但誰料想到,這位平時以維護胡同榮譽為己任的老爺子,竟對此事來了個一間三不知。
「您說,這傻二姓什麼?」
「不知道。」
「總該有個名兒吧?」
「不知道。」
「打哪兒來的呢?」
「不知道。」
「您、您這是?」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誰冤諸位,誰是孫子!」
「那、那您也得給大夥露點底兒吧?」
「瞎!」
只有一聲長歎,再無其它解釋。老少爺們兒進一步緊逼,這才逼得老掌櫃頹然崩出這麼幾個字兒來:
「不能說!不能說……」
爺們兒!這就夠了!該猜就自個兒猜去吧,大褲襠胡同有大褲襠胡同的規矩。再要問什麼,就透著不知深淺、不講義氣了!
得!傻小子就這麼留下了。
但老掌櫃也真夠意思。再不麻煩大夥兒,把這憨大個兒留下給茶樓挑水了。
水井就在茶樓下面。
井水清冽,也算得塞外一景。尤其是井旁那兩根攀龍石柱,更是別具一番風姿。傳說當年拴過禦馬,故俗稱禦拴馬樁。高出地面七尺,埋在地下的也絕不少於此數。多少年來拴過無數烈馬,竟未能撼動過其分毫。少說也有個千二八百斤,早被老少爺們奉為大褲襠胡同的鎮街之寶!
就不該偏偏配上這麼一位傻爺來挑水!
先拿那副水桶來說,夠大的了,別人挑著怎麼瞅怎麼順眼。可讓這位五大三粗的一挑,就透著有點滑稽。簡直就像大狗熊挑著一副玩具桶,不倫不類。每挑一擔還准灑半擔,一道兒演不完的水漫金山。老掌櫃跟著他說不完的好話,賠不完的情。
但好就好在他的窩囊。
絕沒脾氣,大人小孩都可以拿他窮開心。而且膽子特小,傻頭巴腦兒的見了誰都害怕。頑童們常跟在他屁股後頭朝水桶裡扔石子,他竟只懂得挑著水逃跑。得!連人帶桶一個大馬趴。沒轍了!渾身泥水,愣咧開了大嘴就會個哭。樂子大了去了!為此,很快他就成了老少爺們喜見的「西洋景兒」和孩子們少不了的「玩物」。並且跟各路好漢一樣,不久也得了個響噹噹的綽號:鼻涕蟲兒。
絕了!
「鼻涕蟲兒!笑一個!」孩子們追在他身後起哄。
「嘿嘿!」他竟馬上咧嘴一樂。
「鼻涕蟲兒!扭一個!」頑童們還是對他不依不饒。
「嘿嘿!」他愣馬上扭動著一身憨肉。
「鼻涕蟲兒!放個屁!」渾小子們更加得寸進尺了。
「嘿嘿!」他似為難了,但仍不忘撅起了屁股。
哈哈!眾好漢也跟著開懷大笑了。
也難怪!大褲襠胡同什麼都不缺:好吃的、好喝的、好玩的、好看的,如今又添了這麼一位供大夥兒打哈哈的。不算多餘,也算得一路諸侯。
可就愁壞了老掌櫃了……
鼻涕蟲兒窩囊是窩囊,卻份外能吃。肚子大得像個無底洞,一頓飯十個大窩頭都填不飽。逼得沒法子,老掌櫃只好提著個泔水桶向各路美食高手求援。什麼殘羹剩湯,什麼餿飯舊饃,總之賣不出去的他全往回收。為這事。大夥兒真懷疑老掌櫃是不是有點摳,於是便決定試試鼻涕蟲兒肚子皮到底有多大。
這一天……
背著老掌櫃終於把這小子弄來了。各路美食高手踴躍得實
在可以,眨眼間便湊足了四隻臭燒雞,大半鍋變了味兒的羊雜碎,十幾個硬成鐵餅的芝麻火燒,半籠屜餿了的狗不理包子,還有其它一些隻配倒進泔水桶的小玩藝兒。沒想到鼻涕蟲兒竟毫不發怵,就像一頭紮進了瓊林禦宴一般。就著大半桶冷水,剛半個時辰便風捲殘雲一掃而空。等老掌櫃得知了消息,他早已躺倒在禦拴馬樁旁不見動彈了。
這還了得?!
要知道,這些玩藝兒就是喂豬也夠喂好幾口的!莫非讓大夥兒愣把這傻二給撐死了?老掌櫃叫苦不迭,眾好漢也一時傻了眼。但誰能料想到,正當大夥兒又驚又悔之際,鼻涕蟲兒竟一伸懶腰意外地坐了起來。睡眼朦朧,一瞧見老掌櫃便嘟囔著伸出了手兒:
「今兒午飯,俺那十個窩頭……」
笑!笑!瞧大夥兒這個前仰後合地笑!鼻涕蟲當即受到一片誇讚,老掌櫃也立刻恢
複了仗義疏財的好名聲。樂子大了去了,足夠大褲襠胡同的老少爺們兒樂幾天。
但樂極往往生悲……
就在大夥兒耍狗熊似地玩過這窩囊廢不久,這一天從口裡來了一位不同凡響的「混混兒」。單人隻身,竟敢到這塞外小天橋,『闖字號」「搶盤子」來了。一瞧就不是善茬兒,冷如冰,寒似鐵。上得古泉居茶樓用食指往茶桌上一擰,桌面兒上頓時便留下個窟窿。老掌櫃一瞧,不敢怠慢,馬上以柔克剛地奉上一盞好茶。點頭哈腰,隨之便是一套江湖暗語來套輩數。誰知這位冷爺就是不買帳,喝過了茶還真給錢兒。只聽嗖的一聲拔出了一把柳葉刀,再聽嚓啦一聲已經在大腿上旋下一片肉。血糊淋拉,足有半斤多重,啪的一下甩在了老掌櫃面前。冷眼一斜,還要「找頭」!
要什麼「找頭」?這不是明擺著嗎!
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拿老掌櫃開涮,說白了看,就是要大褲襠胡同的各路諸侯俯首稱臣,這位冷爺要在這漠北小夭橋專吃「獨一份」!誰來救駕?文的當數算卦的
「鐵口黃」,嘴皮子行,能把死人給說活了。武的當數賣大力丸的「黑三泰」,功夫不錯,能腰崩鋼絲,頭斷頑石,武藝高強,威鎮關外。多少年來,就憑著這一文一武,愣沒有一個人敢來大褲襠胡同撒野!而現在?文的不知到哪兒去溜彎兒了,武的竟聲稱來者是其「師叔」,按武林家規他只好躲了。得!剩下些褂面杖、鐵鍋鏟、泥瓦刀、大茶壺能頂什麼事兒?就等著跟老掌櫃倒黴去吧!
來者不善,善者不來!
說話間,老掌櫃已被逼下了茶樓,跪倒在古泉井旁那根禦拴馬石間。光天化日之下,要的就是這股勁兒!禦拴馬石,鎮街之寶。挑這個地兒,為的就是要把整個大褲襠胡同都給鎮了!果然,各路諸侯心裡滴著血,就是沒有哪位敢吭聲兒。
等著瞧吧……
尚有一絲希望!只要老掌櫃不簽這個字,不劃這個押,不低這個頭,就是受點屈辱也還不算輸!但這位「闖字號」的冷爺更叫絕,也不要筆墨伺候,要的卻是一種令大夥兒終身難忘的狠招兒。只見他還是一聲不吭,猛「叭」地一聲吐出一口濃痰,鐵著臉示意非讓老掌櫃舔了:這就是那「找頭」!
面如死灰,老掌櫃抖抖瑟瑟地跪著。
什麼哥們兒?什麼義氣?面對著這可怕的「押」,一時間各路好漢都給忘光了。諸位!先夾緊了自己的屁股,免得夾不緊崩出聲來招禍!誰要不服氣,小心先把自個兒祖宗留下的招牌砸了!老掌櫃好是好,可誰叫他偏偏遇上這麼個冷面混混兒呢?
戰戰兢兢,四周一片鴉雀無聲……
但就在這時,卻猛聽得一聲號啕。只見兩隻水桶一撂,一堆憨肉竟熱切切地撲倒在老掌櫃身旁。啊!鼻涕蟲兒!老爺子沒白收留了他,沒想到傻裡巴嘰竟有這份兒孝心!出現得意外,真讓人害臊!在這節骨眼上,大褲襠胡同能挺身而出的,竟只有這位窩囊主兒!
「二大爺哎!」但就懂得哭。
「傻二!你、你靠邊兒去!」老掌櫃雖很感動,卻在顫巍巍地喊著。
「俺不!」他卻像小孩兒撒嬌一般。
「走!」老掌櫃猛地一推。
「不!」他哭的聲兒更大了。
這不是擋橫兒嗎?也不看看自己的本事,活該這鼻涕蟲兒自找倒黴!只見那位冷爺輕輕用腳向他一撥,那傻小子嗖一下便被踢出了老遠。肥豬打滾一般,抱著腦袋更哭得滿臉鼻涕眼淚了。但還憨頭巴腦兒地嚷嚷著:
「你敢踹俺!你敢踹俺……」
那位冷爺顯然不屑一顧這窩囊廢,只顧著斜靠在鎮街之寶的禦馬石上。用腳尖點著那口濃痰,似在威逼著對老掌櫃喊:
「舔!」
老掌櫃老淚縱橫,就是咬牙不彎腰兒。他知道後果:砸了牌子,丟了地盤,愧對鄰里,何顏再見祖宗?!
又是一點:「舔!」
老掌櫃猛地一閉雙眼,似決心以身相殉了。
可成嗎?
只見那位爺的面孔驟然變得更冷了,驀地一伸鐵掌向老掌櫃的脖梗按去。任老爺子再想當「強項令」,爺們兒!鼻尖還是一點一點向那粘乎乎的濃痰貼近了。
完了……
但就在這時,又聽得鼻涕蟲兒的一聲號陶。隨之,這小子又不識眼色心事地爬了過來。要知道,這位冷爺若不儘快制服了老掌櫃,時間一久,老爺子倒會顯得大義凜然,他卻反而會落得個難對老朽之輩。掉價兒!而現在偏偏又遇上這麼個不知深淺的窩囊廢,擋在中間,護住老掌櫃竟向他嚷嚷起來:
「俺來舔!俺來舔!」
「靠邊去!傻二!」又是淒慘的一聲。
「俺來舔!俺來舔!」
「傻二!」近於絕叫了。
怪不得老掌櫃捨命阻攔。你來舔,這不等於變成了窩囊廢對窩囊廢了嗎?真不知深淺,玩玄!果然,只見那位冷爺兩眼驟閃凶光,猛起腳便惡狠狠向鼻涕蟲兒踢去。別忘了!指尖一擰,桌面兒上便留下個窟窿。腳尖一撥,傻小子便是幾個翻滾。這一腳下去,那不傷筋斷骨才算怪了!
嘣的一聲悶響,驚天動地的號陶!
但令人驚詫的卻是,沒見到血光飛濺,更沒見到肢斷骨裂,那鼻涕蟲競在號陶聲中傻乎乎地站了起來。
那位冷爺顯然一愣……
「俺、俺!」鼻涕蟲兒卻越哭越傷心,愣潑口大罵起來,「你、你、敢尥蹶子!俺、俺操你八輩兒大祖宗!」
要壞事!
是這樣!沒事還在找茬兒,何況又操了人家的八輩兒大祖宗。江湖上最忌諱的就是
這個。您哪!要玩命了!說話間,只見那位冷爺嗖的一下便又抽出了那把柳葉刀。長不盈尺,寒光四射。就不知為什麼偏偏拋下了鼻涕蟲兒,徑直向老掌櫃逼來,似求速戰速決,刀尖上又驟然閃出那個字兒來:
「舔!」
「俺操你八輩兒大祖宗!」鼻涕蟲兒還在一旁傻裡巴嘰地火上加油。
不好!要出人命了!
沒戲了!老掌櫃要想不見血,那只有甘當三孫子去舔痰!看得出,傻小子也明白,要想救他的二大爺,單憑一身憨肉絕對不行了。刀尖從來就不是吃素的!但就不該三著急兩著急,愣猛然間憨頭巴腦兒地撲向了鎮街之寶——禦拴馬石旁。
蠢貨一個!想幹什麼?!
就在各路諸侯哀歎之際,只見鼻涕蟲兒雙手一摟,一聲大叫,竟把那紮地生根的禦拴馬石驟然拔起來。再順手一掄。便只聽嗡的一聲,那千二八百斤重的鎮街之寶,楞被他玩兒似地高高舉過頭頂!
神了!神了!
大褲襠胡同似頓時陷入夢境一般。人人目瞪口呆,個個恍若隔世。再聽不到一絲聲息,這漠北小天橋一時間就像死絕了人似的。好片刻,才聽得噹啷一聲,那是冷面客認輸時扔下柳葉刀的聲音。
可那傻二還把那擎天石柱高高舉著……
「放下!」老掌櫃終於發話了。
傻勁頭兒上,不放!
「放下!放下!」近似於哄著。
怪委屈的,還是不放!
「小心我告你師傅!」語帶威嚇。
似被逼無奈,驟然又放聲大哭。您哪!好不甘心!只見他把禦拴馬石掄來掄去,一咬牙這才撒開了手。但這一撒手不要緊,卻更驚天動地。只聽嗡的一聲,那鎮街之寶便被賭氣拋向半空。驚心動魄,目不暇接。等人們還未能從頭暈目旋中緩過神兒來,便聽得又是一聲巨響,那禦拴馬石早又從雲中紮下,頭沖下直插進原來的土窟窿裡。紋絲不動,只是稍稍斜了點兒。
誰還敢喘大氣兒……
「俺讓你欺侮俺二大爺!俺讓你欺侮俺二大爺!」只有那位傻爺還不甘心地坐在地上號啕著。
第二天,大褲襠胡同便又恢復了往日的升平。
冷面混混兒灰溜溜地不見了,但鼻涕蟲兒也隨之消失得無影無蹤。據說,就在出事的當天晚上,那位神秘的不速之客就聞訊又殺了。怎麼回事兒?不知道。只聽說後半夜便帶著那傻二樹葉般飄下了古泉居茶樓。刹那間便隱沒在漆黑的胡同深處,只留下了一串又一串難破的謎:
他到底是誰人的後代?
他到底是哪家的門徒?
他到底為什麼偏苦苦隱匿於此?
心癢難熬,令人浮想聯翩。但當各路諸侯會聚古泉居茶樓想掏騰點底兒時,老掌櫃卻只顧搖著頭竟還是那兩句話:
「不能說!不能說……」
多少年過去了,就連老掌櫃的小孫子也又變成了名符其實的老掌櫃,但有關鼻涕蟲兒的奇事兒還在傳說著。誰敢懷疑,大褲襠胡同的老少爺們准會和他翻了臉。小瞧人啦!不信?您就到古泉井旁親自見識見識!
果然,那禦拴馬石還在那兒頭朝下斜插著。
您哪……
其二引魂樊
隨後,就是小日本長驅直入……
但大褲襠胡同還是大褲襠胡同。該怎麼著呢?上頭的只顧自個兒撒丫子往後跑,逼得小老百姓只好當順民。財大氣粗的爺們仍不忘尋歡作樂,於是這漠北小天橋又恢復了昔日的亂亂哄哄。
只有這麼一個人兒似超然物外……
這可不是乍猛冒出來的。有名有姓,大褲襠胡同沒有一個人不認識這位爺的,只是對他恭敬得有點出格兒。
不信?你瞧——
每天大早,古泉居茶樓一開門兒,您准能瞧見這位隨腳就跨進了門檻兒。身穿一領洗得褪了色的長衫,手拿一把古色古香的摺扇,頭梳老式中分頭,腳蹬千層底兒舊布鞋。三十五六歲。雖略顯寒酸,但舉手投足間仍不乏斯文。
塞外王府井少見的人兒!
進得茶樓,方寸不亂。左手提起衣襟,右手捏著摺扇。有板有眼,一級一級拾階而上。目若無人,頗具名士風度。而且上得樓來,徑直就在那臨窗口的茶桌坐穩。專用一般,永不更改。隨之,便頗為瀟灑地翹起二郎腿,用摺扇在桌面兒上輕輕敲擊三下。雖再不多言,但隨著小夥計的一溜小跑,那上等的龍井扣碗茶總是應聲而來。
窮譜兒大了去了!
更奇怪的卻是,這古泉居茶樓地處鬧市中心,居高臨下,茶
客熙攘,本是處難得一張茶座的地兒。但任憑來人再多,卻似乎沒人敢來打攪這位寒酸爺們兒的清靜。獨霸一桌,閑雲野鶴一般,而且一坐就是一天。雖不知這位爺是幹什麼的,似乎這輩子專門和這張茶桌棵上勁兒了。
可茶樓每天總有個關門的時候!
您再瞧:這位爺還是那麼瀟灑。八字步一邁,似踏人無人之境。睥睨一切,行走于夜色初罩的鬧市之間。兩旁的鋪面裡都難免伸出了店掌櫃的腦袋,但又好像誰也怕擾了這位爺的悠閒。似乎天越黑就越對他肅然起敬,直到他消失在拐彎兒處的一片陰影裡,大夥兒才放心地收回了自個的眼神兒。
到了!這裡顯然就是他的府邸。
但令人納悶兒!大褲襠胡同別的鋪面兒都是掌燈上火的,一片通明。唯獨這三間鋪面兒黑燈瞎火的,死氣沉沉。相比之下,竟透著一股陰森森的氣息。
「樊爺!」有人還在黑影中迎接他。
「嗯!」他竟受之無愧。
「討帳的今兒個多老去了!」似在提醒。
「信不過爺們兒?」他冷冷一問。
「不!不」這位趕緊解釋,「那是他瞎了眼睛!就憑您那一手絕活兒……」
「知道就好!」更冷了。
「對!對!」這位進而婉轉提示,「我這可是為您好!三年沒開張了不是?如果您能屈尊點兒、隨和點兒、馬馬虎虎點兒,也省得成天清茶灌大肚不是?」
「你這是嫌我!」沒想到他竟來火了。
「哪敢!哪敢!」這位立馬掏心剖肺地喊,「我是那種人嗎?再說,誰不知您是咱這一行的幌子!」
「這不結了!」他傲然地甩手而進了。
暗影裡只留下了那恭候他的人兒。呆久了,這才朦朦朧朧看清了,原來這位竟是個祖傳專吃死人飯的主兒,九世「杠房仇」。
兼做棺材鋪的掌櫃子!
借著其它店鋪射過來的燈光,這位身後那一溜三間門臉兒也隱約看清了。只見一間鋪面兒內屹立著一對對紙糊的金童玉女,一間鋪面兒內橫著一口口貴賤的棺材,一間鋪面兒內杵著一頂頂大小的欞轎和長短抬杠。冷氣嗖嗖,陰氣慘慘,要多慘人有多慘人!說白了看,這就是杠房仇的聯合體。一家是紙紮鋪,一家是棺材鋪,一家是杠房鋪。三者合一,再無分號,可奇怪就奇怪在於,竟把這麼個窮酸斯文人兒,畢恭畢敬地當成自己這一行的幌子?
蹊蹺!夠蹊蹺的……
且不說偏偏住在這專門和鬼打交道的鋪面裡,就是怎麼當這個幌子也頗讓人猜疑,棺材匠?抬杠夫?紙扎手?全不像。店東?老闆?掌櫃子?又搭不上邊兒。幌子?他到底憑那一份兒當這個幌子?
邪門兒!
猜他是落難公子,他又敢整日裡逍遙於茶樓之上,說他是有錢的少爺,他又得每天都落腳於棺材堆裡。肩不能挑擔,手不能提籃,卻能在能人薈萃的大褲襠胡同裡獨得一份尊敬。天哪!瞧他那落魄文人的樣兒,莫非他是閻王殿裡不中的舉子?鬼門關裡溜出的秀才?要不,他怎麼會被樹為這冥司行的幌子?
可怕……
這一天,他難得地沒在古泉居茶樓上露面兒。但也就在這一天,茶樓上的氣氛也顯得有點兒個別。往日間扯著嗓子的鬧鬧嚷嚷,今兒個竟變成了捏著嗓子的嘰嘰喳喳,別瞅聲兒不大,卻透出了少見的興奮和騷動。
只有他那張茶桌旁冷冷清清……似和他無關。老少爺們兒顧不上往那兒瞅,只顧得頂著頭兒、咬著耳朵、使著眼色、壓低聲兒議論著一件大事情。諸位!諸位!聽說了沒有?古城維持會長的老子玩兒完了!老天有眼!脖子後長了個斷頭瘡,愣嚎叫了七天七夜給疼死了!
得!就等著大出殯瞧熱鬧吧!似馬上又和他有了關係!不知為什麼,只要一提大出殯這茬兒,茶客們的眼神兒就由不得往那張茶桌兒瞟。雖然空著,卻似更具吸力。好像今兒個那位孤芳自賞的爺們兒沒來,這份樂子中就仿佛少了什麼調料似的。
您哪!更透出他在這份熱鬧中的重要性!
「老掌櫃!人呢?」有人忙問。
「人?」九世老掌櫃只好苦笑著回答,「您還不知道樊爺那脾性?最後一個大子兒也沒了,怕當著諸位摘面兒!」
「誰和誰呀?窮犯倔!」另一位馬上惋借道。
「就是!就是!」附和者頗多。
「要不這樣兒,」有人卻有不同看法,「樊爺也稱不上樊爺了!」
「唉!唉!」又是一片惋借聲。
「也難怪!」還是老掌櫃說得精闢,「三年不開張了!」
「唉!唉!」惋借變成了歎息。
「唉什麼?」又一位猛一擊桌,聲兒驟然一轉,「這不來了嗎?三年不開張,開張頂三年!財神爺正向樊爺招手兒。諸位!就等著瞧絕活兒吧!」
絕活兒?……
古泉居茶樓竟為了這一聲,頓時顯得無精打采起來。老少爺們兒一時啞了口,只留下一片掏心堵肺的難受模樣兒。你瞅著我,我瞅著你,就是沒人再願瞅那張空蕩蕩的茶桌兒了。
這茶還喝什麼勁兒?堵得慌!
「絕活兒……絕活兒……」有一位老者竟為此搖頭晃腦地哀歎起來。
「絕活兒……」隨之又是一片惋借之聲。
「就是!」終於有一位年輕的主兒爆發了,「眼看就要白糟踏了!給老狗日的開道兒,太便宜他了!憑老王八旦造下的孽,早該打進十八層地獄!」
「諸位!諸位!」老掌櫃有點兒緊張。
「就是!」但還有一位膽大的,「仗著小子當了兒皇上,楞專摘棒小夥子的雞巴蛋配藥吃!七老八十的了,還成夭一個勁兒地的糟踐大姑娘小媳婦兒!」
「閻王爺饒不過他!」咬牙切齒的聲兒。
「小聲兒!小聲兒!」老掌櫃慌不迭地按捺著諸位,臨了還不忘補充了一句,「可別忘了:有錢能使鬼推磨!」
有錢能使鬼推磨?茶客們又啞了口。
唉!可惜的絕活兒……
又過了兩天,那張靠窗口的茶桌還冷清清地空著,始終未見那位寒酸而又斯文的身影。這簡直成了茶客們的一塊心病,這天下午有人竟建議老掌櫃把它砸了:
鬼氣兒太重……
但就在這群情激憤的功夫,就見得杠房仇興沖沖地跑上了茶樓。大白亮天看得清楚,原來這位專吃死人飯的主兒可真夠胖的。滿面紅光,就像塗了一層死人油兒。一上得樓來,對著大夥兒就是一陣討好的嚷嚷:
「諸位!諸位!我給老少爺們兒送財來了!」
什麼?什麼?眾人由不得對這位渾身晦氣的人物刮目相看了。
原來,這古城維持會長是想借老爺子之死,大出殯,大發喪,大擺排場,以在其主子面前顯示自己確實「維持」下一片「王道樂土」。不但要有那絕活兒引路,三班鼓手開道,六十四抬大杠舉欞、一百單八個大姑娘和小媳婦兒嚎喪,還要動員全城人皆披麻帶孝加人送葬隊伍,傾巢出動相隨墓地直至入土為安。夠辛苦的了,但不白去!您就聽杠房仇這份兒嚷嚷:
「每人三塊現大洋,丈二白布也歸自個兒呀!」
頗具誘惑力……
「還有披掛的麻,拿回家納鞋底兒呀!」
是不能白扔……
「玩兒似地走一趟,掙下半月的錢呀!」
確實如此……
「省下冒臭汗,還得瞧西洋景兒呀!」
夠引人的……
「再說絕活兒,不瞅就後悔死呀!」
且聽下文……
「聽聽價兒吧,一千塊現大洋才肯露一手呀!」
舉座驚絕……
頓時,古泉居茶樓上便只剩下了一片開了鍋似的喳喳聲。剛才人們還覺著那張空桌兒是塊心病,恨不得立刻把它砸了。現在卻又由不得眼神往那兒溜,似這才看出了它的莊嚴和偉大。一千塊現大洋!叮叮噹當,足夠一家小民百姓三年吃香的喝辣的了!怪不得老掌櫃半晌才緩過氣兒來,說:
「一招鮮!吃遍天!……」
說到這兒,是該掰開瞧瞧了!要不顯不出這位爺的特殊身價來。
原來,這位貌似斯文的主兒,竟也是一位專吃死人飯的好漢。祖傳的行當,特准專門來往於陰陽兩界之間。據說沒他在前引道,新死的亡靈絕難安然度過鬼門關。其間種種慘人的傳說雖只是耳聞,但大多數古城的老年人確實見過他那一手驚天地位鬼神的絕活兒。為此,他世襲了老祖宗留下的那陰陰森森淒淒慘慘的綽號:引魂樊!
怪不得杠房仇把他奉為幌子……
但這幌子卻常閑著。一般貧民百姓問心無愧也用不起,而達官貴人問心有愧又難得天天都死人。非極大排場的大出殯用不上他這手絕活兒,故三年不開張竟是常有的事兒。而這位爺又極願依附風雅,開一次張就大把往外撒錢兒。三撒兩撒只剩下餓肚子了,但再被冷落也絕對架子不倒。
也難怪!天下無雙,南北一絕!
到時候您就瞧著吧!不管死主的官再高、勢再大、錢再多、送葬的隊伍再氣魄,這位也得被恭恭敬敬地請在最前頭。還得屈尊地看他的臉色,那譜兒大了去了!
您哪!完全為了他那手絕活兒!
只見他昂著頭兒,挺著脯兒,任身後哭著、嚎著、吹著、打著,他卻只管著在前頭引魂撒紙錢兒。要多傲氣有多傲氣,要多瀟灑有多瀟灑。瞧!絕活兒也就跟著來了!一撒,漫天飛銀。再撒,遍地鋪白。揚揚灑灑,飄飄忽忽,由不得老少爺們兒開始喊好兒。但這還不叫絕,最令人喝彩不止的是第三撒!只見隨著他漫不經心地那麼一揚,欞柩過後,那兩旁的樹葉上便馬上掛滿了紙錢兒。株株披白,棵棵掛雪,街道兩旁頓時變得銀裝素裹!俗稱「滿街孝」,又名「傾城喪」!據說,他曾做然宣
稱:只要樹上還露一片綠樹葉,他就少收一塊現大洋!
不接著再為他爆個滿堂好兒成嗎?
真不愧為祖傳的陰司使者!不但知道怎麼為死者引道兒,而且知道餓鬼冤魂要的價碼兒。果然有錢能使鬼推磨,只要財大氣粗就不怕造孽多。不過要讓全城披麻掛孝還得有權有勢,故爾難得見著引魂樊一露這手絕活兒。
而現在……
齊了!這不全齊了!別的且不說,就拿這白花花的一千塊現大洋來講,誰能夠不動心思?更何況那位爺早窮得連最後一個大子兒也花光了,再撐著非餓死不可。得!天無絕人之路!這麼大的數目,又夠那位陰司秀才擺幾年譜兒了!討債的肯定換成了笑臉兒,哪個茶樓酒肆不得把他重新當成祖宗?雖然身上鬼氣重了點兒,但現如今這世道有錢就是爺!大夥兒也跟著披麻掛孝去吧,三塊現大洋還是三塊現大洋呢!
良心值多少錢一斤?
不對!正當大夥兒向杠房仇報名準備去湊熱鬧時,就聽得樓梯上又響起了那有板有眼的上樓聲。再一瞧,那領洗得褪了色的舊長衫又閃現了。只不過多了幾塊補釘。中分頭梳得照樣地道,但就不該千層底兒鞋咧開了嘴兒。一臉傲氣,卻又透出了菜青色。身子板兒瘦了許多,大概是餓的。和平時有所不同的是,摺扇沒拿,倒提著個沉甸甸的包袱。正當大夥兒不知怎麼來招呼這位乍窮乍富的爺們兒時,杠房仇卻似見了活祖宗一般迎了上來:
「樊爺!大夥兒正念叨您呢!」
「等等!」氣喘噓噓,卻猛地把包袱向自己那張茶桌兒上啪地一扔!攤開了,錢!錢!全是白花花的現大洋!
「您、您這是幹什麼?」杠房仇目瞪口呆。
「先給我數數!」冷冷地作答。
「五百!」杠房仇忙不迭地解釋,「數過了!數過了!沒錯兒,五百整呀!」
「這就夠賣祖宗的了嗎?」聲兒更冷了。
「樊爺!樊爺!」杠房仇又慌著說明,「不是全講好了嗎?發殯過後見了好兒,剩下的那五百再送上嗎?」
「拿回去!」又是一推。
「怎麼?」望著菜青色的臉,杠房仇實在大感意外。
「不怎麼!」頭兒昂得瀟灑,「昨夜裡我到閻王殿裡遛了一趟彎兒,見陰曹地府還 沒讓小日本兒占了!」
「您?」杠房仇更瞠目結舌了。
「我?沒轍!」一斜白眼,再不多言。目中無人一般。轉身便向茶樓下走去。似仍力圖有板有眼,但幾經掙扎竟難瀟灑起來。
搖搖晃晃,像踩在棉花堆上。
「爺們兒!別、別餓死呀!」有誰帶頭失聲痛哭了。
沒應聲兒……
消失了,像鬼影兒似地飄飄忽忽消失了。茶桌兒上丟下了一堆白花花的現大洋,從此茶樓上再沒見到他的蹤影。
頗費猜疑……
但一千比三,大夥兒還是能掂出其間的份量來!致使維持會長白布蒙樹,長麻披街,那「王道樂土」裡送葬的隊伍還是蕭瑟得很。據說,從此便夜夜驚醒,一閉上眼睛就瞧見老爺子不是上刀山,就是下油鍋,再不就是讓血淋淋往下摘卵子!後來,多虧了大白亮天有皇軍壯膽兒,這才發現了原來是那位陰司使者通「匪」。一聲令下,大肆搜捕。幾次把大褲襠胡同翻了個底兒朝天,但均無所獲。就差懇請皇軍出兵閻王殿,儘快把
陰曹地府也納入「王道樂土」了!
又是一年多過去了……
奇怪!生不見人,死不見屍,竟連個鬼影兒也沒抓著。
漸漸地,古泉居茶樓又恢復了往日的熙熙攘攘。難得一個茶桌兒,但那張靠窗口的茶桌卻始終空著。牆上是貼著醒目的「莫談國事」,可管得著老掌櫃就偏愛擦這張桌子嗎?沒人坐是沒人坐,可礙得著總有人願掏錢兒往上頭送茶嗎?龍井。還是上等的。
您哪!禁不住個人想人……
是「生不見人,死不見屍」,可離了那手絕活兒他還能活著嗎?肩不能挑擔,手不能提籃,又抹不下臉兒討吃叫街,大概早已不在人世了!
唉!引魂人的魂兒卻沒有人來引!
完了!完了!……
可誰料想到,就在這歎息過後不久,古泉居茶樓上竟出了一件怪事。神神道道,頓時又使大夥的眼前變得撲朔迷離了!
但這是「據說」……
這一天晚上,茶樓早早就關了門兒,只留下一溜兒小陰風在窗外溜彎兒。茶桌兒間還剩下幾位老哥們兒,正頂著一盞燈在聊大天兒。聊什麼?還不是謀劃著暗下裡燒點紙錢兒。總不能讓人家一輩子撒金撒銀,臨完了倒讓自己落個兩手空空吧?
啊!不對勁兒!
四周朦朦朧朧,卻聽見靠窗口那兒似乎有什麼動靜。老哥兒幾個剛來得及一怔,便猛聽得那張空桌兒擊響了三聲。似摺扇敲的,好熟悉的叫茶聲音!當即,老掌櫃便舉燈驚呼了:
「樊爺?……」
「是我!」回答得相當清晰。
「您?!」仍存疑懼。
「我?」回答得更加斯文,「說我死了,也算得活著。說我活著,也不妨當著死了!」
「您、您這一向還好?」還想刨根兒。
「好!」回答得越發瀟灑,「陽世不好陰司好,陰司不好陽世好!東邊兒不好西邊兒好,西邊兒不好東邊兒好!」
「樊爺!」再不想打聽,只剩下激動了。
「老掌櫃!」回答得也很熱切,「我這不是來瞧您了嗎?」
「您哪!」熱淚盈眶了。
後面的事兒就說不清楚了,像僅僅是個傳說。但第二天發生的事情卻是千真萬確的,大夥兒都親眼瞧見了維持會長親自帶人沖上了茶樓。聞訊而來。殺氣騰騰,似非抓住這位不給他老子引魂的「匪」不可。但更令人驚詫的卻是老掌櫃!一不否認,二不發怵。有問必答,承認得倒也乾脆:
「沒錯兒!來過。」
「哪人呢?!」
「喝過茶,給了錢兒,就沒影兒了!」
「哼!沒影兒了?!」
「是啊!我也覺得邪門兒。丟下了白花花的現大洋,怎麼會一轉身兒就不見了?別是有什麼說道吧?我就把現大洋往水盆兒裡一丟!」
「別他媽的胡扯!」
「胡扯?我老頭子敢嗎?不信,您就親眼瞧瞧——」
順手望去,果然茶桌上放著一盆清水。水面兒是漂著幾塊白花花的現大洋兒。圓的。就是不沉底兒。
天哪!竟是幾片鬼才使用的紙錢兒!
他是活著?還是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