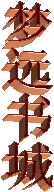
第十二章
「沒有一個好人!」
唐啟昆一想到十爺就生氣。他自己一天比一天窘迫,仿佛就是十爺害的。他記
起從前過的那些好日子,象在心頭長了個癤子那麼難受。
誰都知道他叔侄倆特別要好。早先大太太跟二少爺簡直是替十爺當家,什麼事
都替他把主意打得停停當當。
「十爺你真要小心哩,」唐啟昆伸出個食指,壓著嗓子告訴他。「你做人太老
實,家裡人又這麼多。現在分了家——我只怕你上人家的當。」
做叔叔的擔起心來:
「怎麼辦呢?」
大太太也插了嘴:小聲兒把二少爺那些話說了一遍。她認為頂靠不住是五房裡
——偷呀搶的什麼都來。
「如今不過才分家,就是這些鬼鬼祟祟的事。將來五爺敗光了——嗯,他這個
樣子抽大煙還抽不窮啊?你望著罷,到那個時候他們一定欺侮你。」
於是二少爺出了個主意,他拍拍自己胸脯。
「有我!——我代你想法子!」
他叫十爺把分得的那些字畫——藏到他們大房手裡。大太太跟他都比他精明,
誰也騙不去。十爺越想越可怕,再遲點兒就怕給搶了去似的,就在當天晚上,這兩
叔侄把三口大箱子搬到這邊來了。
那時候十娘過門來還不到半年。身材比哪位太太奶奶都要高一點。走起路來挺
胸突肚地跨得很快。她不大開口——也許是因是新婚之後有點害臊。一雙眼睛可顯
得很懂事,瞅人一眼就仿佛要看穿別人的心事。
大太太很不喜歡她。
「十娘才好玩哩——長得這樣高法子,高得蹺蹊,鄉下女人倒有長得高的。一
個太太長得象個金剛樣子,我還沒有看見過哩。」
她兒倆都想不透——怎麼十爺會跟新娘子這樣要好。他差不多每天呆在屋子裡,
兩口兒廝守一個整上午。他們扔骰子,搶開,吊天九。有時候還哄出了十爺的傻笑。
二少爺總是踮著腳走到過道裡,反著兩隻手,側著腦袋聽著。他母親偷偷地拐
過,揚揚眉毛張張嘴,表示問他什麼的時候,他只抽出手來搖幾搖。
「呃不行!」——他們聽見十爺在嚷。「這一副是我的!」
跟手板壁那邊就透出一絲輕笑聲。
「你賴痞嘛。」
「十娘說十爺『賴痞』」二少爺貼著大太太的耳朵告訴她。
大太太一想到這些就發悶:
「怎幹十爺不發脾氣的嘎,她罵他『賴痞』?」
大房裡這兩母子靜靜地等著:他們巴望著那對新夫婦吵嘴打架。大太太挺有把
握地說:
「新造茅廁三日香。過一向你看罷:有得吵哩。」
那兩口子那種親密勁兒逗得大太太跟二少爺都不大舒服,十爺一有個新人上了
門——就連嫂子侄子都丟開了。十娘這個人是——哼,靠怕是靠不住的。將來她一
替十爺當家,十爺就會跟他們疏遠,就再也不會象現在那麼相信他們了。
大太太一瞧見十太太,就總得把下唇一撇。
「看看瞧!——這副粗腳粗手的樣子。」
她這就動手跟十爺談到一個人的貌。她用著老嫂嫂那種關切的樣子——告訴他
一些千真萬確的道理。她眼皮下面打著皺,沒辦法地動著手指,擔心到十爺將來的
命運。太太們長得太高總不是福相:她或者克夫,或者犯夫星,這種女人總是不會
生兒女的。
「這一著倒著實要防哩。不孝有三,無後為大。」
她到他們屋子裡去坐了一會。她驕傲地告訴十娘——二少奶奶已經懷了六個月
的喜。她用種真心照應人的神氣勸著她:頂好是快點生個兒子,她叫升了天的老太
爺歡喜。
等到聽說十太太有了孕,她老人家就跟那些姑太太們小聲兒說著:
「十嫂也真是!她親家母①有三個月沒有來了哩:說是有喜了。你相信啊?看
她那個樣子就不象。五嫂說:十嫂啊——哼,她有暗病!」
①原住:H·斯立斯說:以尾骶骨為圓心,N寸為半徑,畫一個圓圈,這圓圈裡
面的東西,人們都諱言。唐家的太太們尤甚,說時則用許多代用語,如月經,則曰
「親家母」。
第二年十娘生了一個男的,那個啟良,誰都料不到那個女人那麼會生:差不多
兩年一個。並且個個都很結實,一直到現在——只死了一個小科子。
「真奇怪!」大太太越想越不服氣。她這就把怒氣泄到二少奶奶身上:二少爺
一連讓她養了三個小孩——都壞掉了。「這賤貨!——帶孩子這個樣帶法子!她就
看不得我有孫子!」
二少奶奶氣忿忿地回嘴:
「嗯,你不怪你兒子——倒來怪我!你兒子生了一身不要臉的病,你不曉得啊?
連我都過上了身,我一肚子怨氣正要找你們算帳哩!」
全家人都知道了這回事,這裡那裡時時有些很難聽的話。就是以後二少奶奶丟
下了兩個孩子死了,他們還認為就是那個毛病送的命。
「怪不得老二的孩子老長不大,如今這兩個孩子往後還不曉得怎麼樣哩。」
這兩母子瞧著十娘那一窩蹦蹦跳跳的孩子大聲吵著,好象故意來挖苦他們似的,
他們就更加恨那位十太太。他們看著自己帶病的孩子,就似乎覺得他們這種抱兒抱
孫的運,是十房裡硬搶了去的:那邊生一個,這邊就死一個。
大太太說:
「一個人要是在相上不招子息,偏偏有許多孩子的——那一定就是報應。不是
壞東西投了胎,就是前世欠了債。」
那時候她老人家老是跟十爺談起十娘的相貌:
「你看她的眉毛。」
說了輕輕噓一口氣,舌尖頂出嘴唇,好象叫自己別洩漏什麼似的。
十爺搔頭皮;
「怎麼呢?眉毛?」
「我本來不該派說的,」她躊躇了一會之後,自言自語地說。「不過我想想真
不放心。唉,眉毛粗——脾氣就有點那個。你望望五嫂子瞧,那雙眉毛。」
不錯。的確是的。十爺一下子沒了辦法:他想像到他家會出些什麼可怕的事。
那麼又高又大,象五嫂子那麼潑辣起來——那簡直!這些他怎麼沒早點注意到呢?
啟昆二少爺也結結實實跟他討論了一次。
「十爺,並不是我在你跟前說十娘什麼。我是一片好心,我。」
這麼一開了頭,就長篇大段地說了開來。他叫十爺別多心:他們有天生的血統
關係,他們天性就規定了他們要彼此關切,彼此幫忙的。十爺怎麼能夠信不過親人,
倒去相信一個新進門來的人呢?——況且這個人個兒長得那麼高。
「我看——錢上面的事萬不能給十娘管。」
十爺的錢比別房裡多些。他分得他那份家產之外,還有老太爺的一些金條,一
些玉器——都私下給了這個小兒子。這也是十爺自己對大嫂跟二侄兒說出來的:他
把什麼秘密都放心地告訴他們,雖然老太爺還對他囑咐過這些話:
「你對什麼人都不要說。你太忠厚,容易上當。我要給你這些個東西——也為
的你太忠厚。這些個你要好好藏起來,頂好是存到二姑媽那塊。」
可是二少爺斬釘截鐵地告訴十爺:
「不行!」
老太爺的遺教他們當然得依著去做,不過一個人總要有變通辦法。這裡他打打
手勢來了一句「此一時也彼一時也。」現在二姑老太太家裡窮了下來,這就難保她
老人家不挪用一下。
「還有——」二少爺很為難地在嘴裡「嘖」了一聲。「十娘——十娘曉不曉得
這一筆貨?」
「我還沒告訴她哩。怎麼?」
做侄兒的透了一口氣:
「還好。」
那年唐季樵要到城裡去,他們叔侄倆就又商量了一回。二少爺出了一個很好的
主意,叫十爺一天到晚提得高高的心放下來。這個辦法的確千穩萬妥。不過一想到
要自己怎樣來動手,十爺又躊躇起來了。
「埋到花園裡——倒是保險的。不過叫哪個去埋呢?」
「怎麼,叫哪個去埋!」二少爺瞪著眼,壓著嗓子叫。兩個眼珠子分得很開,
看來象個斜視眼。「當然自己來呀——你跟我。要給第三個曉得就糟了。」
他們約好了時間,十爺就一直心跳著。他從小長到這麼二十幾歲——從沒有冒
過這樣的險。等全家哪一房都睡覺了,他摸手摸腳走出自己的房門的時候,他膝踝
子顫得發了軟。牙齒沒命地敲著,連話都說不上。
「慢慢……等下子……」
二少爺可很沉著,警告地觸一下他的胳膊。兩個人手裡拿著那五六包東西溜到
了花園裡,二少爺這才有機會埋怨他。
「你怎麼這個樣子不小心,嚷呀嚷的。」
顫巍巍的十爺一個音都吐不出來。那幾包重甸甸的東西把他累壞了。
天上一些星星——象遠處的燈火似的閃爍著,象一些鬼頭鬼惱的眼睛——偷偷
張望著他們幹什麼勾當。園子裡黑得巴了起來,叫人再也想像不起白天是個什麼樣
子,簡直不相信這天地間丕有個太陽。只要偶然低下身子去,一些樹就高起來——
給濃膩膩的天色襯出一個模糊的黑影。
他們身上一陣陣的冷,感得到露水浸到了他們臉上,他們手上。
十爺害怕地拖著二少爺的袖子,他那顆心簡直會跳出嘴裡來,他不順氣地說。
「我一定會生病,我一定會生病。……」
四面靜得不像是人的世界。聽著自己的腳步子——十爺老覺得後面有誰跟著他。
一回頭——一片沒邊沒際的黑。他打了個冷噤。可是前面那個金魚池發著亮,顏色
是慘白的,逗得他聯想到死人的眼睛。忽然好象什麼人扔了石子進去——咚!十爺
全身一震,腿子軟得溜了幾步,幾乎跌了一跤。
只有二少爺那堅定的聲音叫他得了救:
「來!」
他領他穿過彎彎曲曲的路,繞過那座堆起來的石山。二少爺什麼都有個計算,
正象他自己拍拍胸脯講過的——
「莫慌!我有成竹在胸,我!」
於是他加緊了步子,毅然決然往前走著,只不過把腳踞起點兒就是了。
然後他兩手做了一種動作,「擦」的一聲——四面陡地發出紅黯黯的光來。
嗯,他倒帶來了洋火,還有一支短短的洋蠟。總而言之他一切都安排得周周到
到,不用做叔叔的操一點點兒心。
那位長輩膽大了些:對著亮光,對著這麼一位靠得住的侄少爺,他覺得世界上
的事都有辦法了,這就帶著商量的口氣問:
「埋在哪塊呢?——這是,怎樣?」
他們快走到牆邊了。可是二少爺忽然頓了頓步子,靜聽了一會。外面有人在走,
響著沉重的梆子聲。那帶嘎的叫聲似乎飄到了天上——才又悠悠地蕩過了牆來的:
「小心——火燭!」
「這倒頭的更夫!」十爺嘟噥著,把冰冷的手指貼到了胸脯上。
唉,這些個事情真麻煩。要是老太爺不給他這些金條,這些玉器,他也就用不
著這麼提心吊膽。現在他們可還有一部大手腳沒做完:一想到那上面——他腦子裡
就一陣昏。再也想不上怎麼掘土,怎麼把那些玩意放下去。不錯,他們還得再把土
蓋上去。
一陣冷氣打脊背上流了下去,那燭光沒命地晃著,閃動著燭心上的青色的火焰。
他們的影子竟變成了活人,很不安地在那裡搖動,仿佛拚命要打他們腳底下脫開。
叔侄倆的臉上給映得一會兒清,一會兒紅。
唐季樵使勁咬著牙。他恨不得一腳就逃到屋子裡去,一面叫著——
「我不管了,我不管了!」
然而不行。啟昆連鋤頭都預備好了——在白天就擱在那個亭子裡的。這位侄少
爺替他的財寶照顧得這麼周到,簡直叫他自己有點慚愧。一個人怎麼竟想要丟掉這
些麻布包不管呢——光只這五條黃閃閃的東西就有五十幾兩。誰都在嫉妒他,誰都
想要從他身上打主意。
他打了個糊裡糊塗的手勢,連他自己也不知道這是什麼意思。肚子裡忽然閃了
一下很隱秘的抱歉心情:覺得先前他那種念頭——有點對不起去世的老太爺,也對
不起眼前這位侄少爺。
「這件事總會要做完的,」他橫了橫心對自己說。
什麼天大的難事都會過去的。他小時候一提到背書就怕,擔心第二天一早會挨
打,可是這個難關到底也自然而然過去了。他怕五嫂跟老太太瞎鬧,怕不知什麼角
落裡流來的難民搶到這鎮上,怕發大水,怕鬼,怕吃藥:這些你索性死閉住眼睛,
咬緊著牙,等過了這個時辰,於是什麼又照平常一樣。並且——
「今晚算不得什麼難事……包給他做就是了。……」
那個可指揮他起來:
「十爺,你快把那個鋤頭拿給我!」
十爺不敢正眼看亭子那邊,只很快地瞟了一眼。他打了個寒噤。他小聲試探著
說:
「就不要用鋤頭罷。」
茫然地看著侄兒的臉,一會兒他又加了一句:
「用手——可行啊?」
「你真是!」二少爺一轉身就往亭子那邊走,洋燭火焰一晃——拖成了平的,
火尖子掃到了二少爺胸襟上。
後面——緊緊地跟著十爺。他不敢一個人站在那黑地裡。
十幾秒鐘之後,他們動手掘起土來了。
地點是打那棵老槐樹往東北跨三步——那塊太湖石的旁邊。這個原來也有個講
究。
「我算好了的,」正經事一做完了,二少爺就搓搓手解釋給他聽。「今兒個是
個好日子,又可以動土。我呢——不代人幫忙則已,代人幫忙總是處處都顧到。我
生來的脾氣,就這個樣子。這個方向,也是個好方向,這塊財旺,我研究過的。…
…唉,我真累死了。要不是為的你——唉,真累!……你可不能跟旁的人說我,留
神點個!」
唐季樵感動地透了一口長氣,走開花園的時候他緊緊抓住二少爺的膀子,喃喃
地說著:
「唉,只有你待我這樣子好……你待我真好……」
假如沒有啟昆——他這位十老爺就會不知道要怎樣過活,怎樣做人。他跟這個
侄兒怎麼也分不開:他們可以共患難,共富貴。這麼一個大家裡,除開了去世的老
太太老太爺,另外還有個這麼體貼他,幫助他的人,這是誰也想不到的。
「我可以分一半家私給他,」他打著主意,一面擔心著啟昆怕會拒絕,瞅一眼
那個的臉色。「金條一人一半,還有玉器骨董……」
等到二少爺一吹滅了燭火,他又覺得身子掉到了冷水裡。眼面前老有個五顏六
色的東西在晃著,就連星星也看不見,只是感到前面有什麼鬼怪在等著他似的。一
直回到屋子裡,睡上了床,他還全身發軟,仿佛一絲絲的肌肉都分散了,拆開了。
「嗨,我再也不來了!」
花園裡那些景象跟夢一樣叫他糊塗:他簡直不相信他自己也在場。他對二少爺
那種膽量,那種能幹法子——竟起了一種敬意,仿佛他在一個神道跟前似的。他閉
了會兒眼又張開,忽然又想起一件叫他擔心的事。
「將來怎麼掘出來法呢?」他對自己念著。「會不會再要來這一套呢」……噴,
唉,怎麼掘出來法呢?」
可是在他出門到城裡去的第三天——也是這麼一個滿天星的半夜裡,他二少爺
把他擔心著的事辦妥了。
進行得很快當。二少爺輕輕巧巧走出房門,二少奶奶坐在床上等他。那時候二
少奶奶還沒有死,雖然正在坐月子,這件事可叫她興奮得撐起了勁來。她照著做婆
婆的做丈夫的教給她的那些方法,把小孩子推醒——讓他哭著叫人聽不見二少爺的
腳步響。
從這天起,大房裡的箱子裡多了五六個麻布袋。
這些現在想起來,差不多是前一輩子的事了。不過二少爺指頭上還感得到那些
東西的冷氣,仿佛它們還留在他手上。心裡可空蕩蕩的,象早年記起他的孩子一樣
——好容易生一個,又壞一個。
「要是留到現在——」他怨聲怨氣地說,「唉,如今也不會這樣窘法子。」
他不大記得起那些玩意是怎麼花掉的。大概他到北京進法政講習所的時候,在
前門外花得有個樣子。嗨,真是誰叫自己那樣呆的嘎!——跟同學們聽戲,吃正陽
樓,花的全是他的。連逛班子也是他掏的腰包。
「算我的!」他動不動就拍拍胸脯這麼叫,接著用長官對屬員的派頭看看他的
同學們。「看今兒個晚上怎麼個玩法,你們說!」
大家謹謹慎慎對他提供一些意見,帶著挺認真的臉色跟他談著,仿佛他們都在
實習——預備畢了業好去到什麼顧問機關裡服務似的。末了總是那個矮子——他們
把他看做唐啟昆的國務總理的那個,站起來晃著手,斬斷了那些亂糟糟的話聲:
「我們還是讓老唐來帶領罷:唯老唐的馬首是瞻。我們都聽從,不管他怎麼辦。
我們絕對的捧場!」
有些人拍起手來。其餘的喝著采,這裡還響起了那個老卞的嗓子:
「咦,好!……好哇!……咦!」
唐啟昆還記得老卞脖子上突出的青筋,臉發了紫,一本正經地叫著,似乎在苦
心學習什麼。據老卞說起來——要想在北京謀活動的,總得會這一手。他還莊嚴著
臉色告訴過別人:
「國會裡有誰演說,那些議員贊成的——只喝采,不怕手。叫得挺熱鬧。」
「那時候真有點個意思,」唐啟昆想著,閃了一下微笑,接著深深呼吸了一次。
他要記一記那些班子裡的熱鬧勁兒,那些姑娘的名字,可是糊成了一片。只是花出
去的錢他還有點數目。
「真傻!」——因為想到了在北京的事,就連對自己說話也不知不覺調上了京
腔。「一年要花四五千!——嗨,四五千!」
可是他又對自己辯解著:一個人在青年時候總該有點豪興。他也並不是不懂事,
那時候。他每天回到公寓裡總是有點懊悔的
「又是兩百多!——我怎麼要到班子裡打牌呢!」
他抽著老炮臺,對燈光發著愣。隨後他細細地記上這筆帳。臉上總是有點發熱,
覺得自己做過了什麼虧心事。上了床之後他對自己下了個結論:他這些同學全靠不
住。他們揩他的油,帶他去幹那些荒唐勾當。
真可惡!一個個都是小人樣子!還有那個老卞——簡直俗不可耐。
於是他打了個阿欠,打定主意——從明天起就不跟他們來往。真是的,他自己
也得想一想。這幾年不比從前:現在分了家,花的並不是公上的。這怎麼行呢,一
出手就是幾百。
第二天他什麼事都精明起來。嗯,這個夥計靠不住:六個銅子花生米只這麼一
點兒!
「夥計你不要走!」他叫。「呃,你買了六銅子花生米麼,的確是六個銅子兒
麼?……哼,你當我不知道……」
出門叫洋車的時候他總得冒火:
「什麼,要四十枚!——放你娘的狗屁!」
他很快地往前面走,連頭也不回。洋車夫可老跟著他,開玩笑似的——三十五
枚吧,三十枚吧。他們只要逗他多花幾個冤錢。他們老卡著價,叫他老這麼走著。
「混蛋!」他咬著牙罵。
這時候大概是九月裡,他記得。那件大衣壓在身上重甸甸的。太陽有氣沒力地
透著黃色,把這個京城照得非常慘淡。時不時有陣風卷過來,路上的灰土就沾了起
來,陀螺似的直打旋。
他拿手絹堵住鼻子嘴。可是呼吸不靈便,更加吃力得喘不過氣。可是他一直沒
理會那些車夫:他怕自己管不住自己的性子——一個不留神會跟那些粗人打架。牙
齒老是咬著,眼睛瞪得大大的四面瞧瞧——實在想要找巡警來替他出氣。也許是因
為他太憤怒,腿子竟有點發軟。
那些車夫可還滿不在乎地在那裡嚷哩——
「二十八枚吧!」
該死的傢伙!——多賺了這幾個兒就發了財麼!
一個勁兒走了小半裡,到底作成了這筆買賣,二十六枚。車夫一拔腿跑了起來
——唐啟昆又覺得自己做了冤大頭。真是該死!——走了這麼一大截了還是二十六!
為著要報復一下,他不住地在車上頓著腳,催別人快點兒跑。他老是罵著,還
干涉車子走的路線。
「你這個混蛋!——怎麼不一直走!」
他老實想要叫那個車夫多繞些遠路。
「唉,到底省了幾個錢,」他安慰著自己。「真的,不省點個用真不行。」
可是到了四五點鐘光景,他一個人在公寓裡孤寂起來。他拿起晚報來又丟掉,
走到房門口又打回頭。他碰到了一個頂難解決的麻煩問題:
「今天到哪塊去吃晚飯呢?」
他想到了那些小飯館——老是白菜!老是炒肉絲兒加榨菜!一個人可也得吃上
什麼毛半錢,每個月的伙食就是九隻洋!只有吃面上算些,可是他把下唇一撇:該
死,怎麼好好的一個人要吃面當飯的嘎!
「面不過是點心,」他對別人說過。「只有誇子才不吃飯:中飯也是面,晚飯
也是面,所以就變得這樣蠻法子。」
胸脯一挺,他又毅然地加一句:
「我呢——我是一定要吃飯的!」
現在他可感到十二分為難,他埋怨北京的飯食太貴。
照例在這個當口——他的幾個同學轟進門來了:
「今天怎樣?去溜達溜達吧?」
唐啟昆沒聲沒息地透了一口氣:他這個難關倒給他們沖過了。不過他臉色仍舊
很難看,身子也躺在椅子上沒有動,自暴自棄地答:
「我不去!」
「怎麼呢?」
那位老卞總是在這時候插嘴,認認真真說起大道理來,並且總是預先乾咳一聲。
「我們學法政的——咳哼,將來當然是在政界活動。所以應酬的學問倒是挺要
緊的:我們這麼著——倒是學了真正的學問。」
大家都看著唐啟昆懶洋洋地站起身,懶洋洋地打箱子裡掏出一疊鈔票,他們臉
上的肌肉就一絲絲放鬆,眉毛眼睛也飛了起來。於是他們由唐啟昆帶領著——到班
子裡喝著酒,打著牌。
第二天上午唐啟昆打前門外回來,跟洋車夫吵了嘴之後,他覺得他面前開了一
條路——一條熟路,他常常走的。他記起了他的十爺。
「一個人怎麼能夠不用錢呢?」他想。「就是只要會想法子。」
這只有十爺那裡打得通。
十爺總是相信他的。那年年假他回到柳鎮,他叔侄倆就在十爺屋子裡小聲兒談
著。棉門簾放了下來,窗幔子也封得嚴嚴的。他們把十娘支開,還不住地四面瞧瞧
——怕有什麼歹人聽了去。
「真的呀?」十爺叫。「怎麼會有這樣大的利息呢?」
「小聲點個!小聲點個!」
做侄兒的側著腦袋靜聽了一會,這才松了一口氣:
「怎麼不會有這樣大的利息呢。北邊的皮貨才便宜哩,只要我們有本錢販了來,
一轉手——就是個對開。」
那位長輩站起來,踱了幾步,歎著氣,仿佛嫌利息太大的樣子。他想到了做生
意的麻煩,又想到怕會貼本。一面又莫名其妙地有點著急,似乎有什麼鬼神在催逼
著他,叫他趕快動手——遲一點兒就會給別人賺去了。
老半天他才迸出了一句話:
「好是好。不過這個生意——這個生意——做起來才煩神哩。」
「嘖,噯!」
這裡唐啟昆挺到了他跟前,兩片嘴唇很有把握地緊閉著,叫人看一眼就什麼也
不用擔心。隨後他伸出五個指頭來計算著,視線老盯著十爺的眼睛,聲音可放得很
低的。他主張湊四萬塊錢先下手做它一筆。
「連你一共五個人,一個人八千。本來有個山東人要跟我們合股,我們不要他
來。我早就想到你,不過信上不好寫——要是給人家曉得了不是玩意賬。」
於是這回——十爺帶著萬分感激的臉色交給二少爺四千。這位侄少爺永遠是照
應他的:
「你千萬不要說給人家聽,人家一曉得了就要搶著來做這筆生意,那——才糟
哩。」
「唔,唔,」十爺機警地點著頭。「等你到了北京我再寄四千給你。要添本錢
的話——再加。」
當年十爺就有這麼大方。後來二少爺寫信告訴他生意貼了本,欠了債,他又還
寄了三千多塊錢去。
有時候唐啟昆忽然有種怪念頭一閃,似乎有點不安的樣子——覺得自己對十爺
做得太那個了些。可是一會他就想開了:
「十爺是——反正不在乎。」
然而近來——
「哼!」二少爺恨恨地在鼻孔裡響了一聲,把骨牌一推,捧著腦袋沉思了起來。
整個屋子靜悄悄的,叫他有種淒涼的感覺。外面似乎有沙沙的雨聲,抬起頭來
一仔細聽——可仍舊是一片寂靜。這世界上的一切都丟開了他,誰也不理他。於是
那種從來摸都不敢去摸到的念頭——在他心裡長了出來,象一根釘那麼塞在裡面。
他預感到自己會要遭到什麼不幸。
瞧瞧自己的影子,連自己也有點害怕。他總覺得這裡不是他的家。他只有在對
江省城裡——他能夠找到一點兒安慰。那塊有個人真心愛著他,等著他去。
「唉,我真要待她好點個,」他想。「她如今恐怕正在泡京江擠給小龍子吃哩。」
什麼地方響起了幽幽的腳步子:聽來仿佛是在老遠的什麼高處,又仿佛就是他
身邊。接著還聽見輕輕咳了一下,像是打一個罎子裡發出來的。
「哪個呢?」他模糊地想著。「靠哪個——替我——替我——我該相信哪個呢?」
這簡直是一個好兆頭——丁壽松在門口探頭探腦地要鑽進來。
二少爺眯著眼瞧著他,腔調再柔和沒有:
「你還沒有睡?」
那個吃了一驚。他本來打算挨駡的,二少爺這麼一客氣,他反而把身子縮了攏
去。舌子也變得結裡結巴——不知道要怎麼回話才好了。
「我……我……二少爺在這塊養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