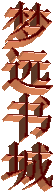
秋天的憤怒
九
小織的手指也不知是怎麼長成的,又細又圓,那麼光潤,那麼軟!用它拿蘋果、搬凳子、捏鋼筆……它觸摸過的東西都變得比原來美好了。李芒曾經不眨眼地看它彈撥過一次琴:
它按在絲弦上,黃色的絲弦彎下來,它也彎下來;絲弦顫動著,它也顫動著。當它在絲弦上揉動時,指尖就微微發紅了,像害羞似的;它用力彈了一下弦,弦要激動地跳起來,它卻異常機敏地、有幾分頑皮地先一步從弦上跳開了。指甲又硬又亮,閃著瑩光,像十枚小小的銅片。小鋼片打在弦上,當然是金屬的聲音。幾道絲弦,有粗有細,它不冷淡任何一根弦,去撫摸、去揉動。它的溫柔全在弦的身上了,絲弦敘述著各種感觸。委婉的語氣也像是模仿著它。有時它全從弦上移開,與弦相距一寸,像是默默地對視,又像是在輕輕地喘息。這安靜的幾秒鐘裡,空氣凝住了。它重新按在弦上時,是幾根手指輪換地觸摸,顯得小心翼翼,像是怕驚醒了對方的熟睡,又像是躡手躡腳的行走。絲弦終於沒有被驚醒,熟睡過去,發出輕微而均勻的鼾聲。於是它離去了,指尖勾起,戀戀不捨地從弦上移開……一個男子這樣細緻地研究一個姑娘的手,他自己也感到有些難為情。可是沒有辦法,這雙眼睛特別執拗。李芒有時故意把臉轉向一邊,但眼睛卻仍要去尋找那雙手。
那雙手曾捏緊了一個做標記用的小鐵旗子,插在一個鉛球砸出的印痕上。那個鉛球就是李芒擲出去的,她驚羨地看了他一眼。他也同時看清了她是肖萬昌的女兒,於是深深地吃了一驚。
他當時看到的是一個嫺靜的姑娘。她穿了洗得發白的黃軍衣,一條學生藍制服褲。與上衣不同,這是筆挺的、使下肢顯得特別修長的新褲子。衣服特別合身,恰好襯托出她的豐滿與嬌小。她的臉色很紅,猛然一看還以為她正害羞呢。像一株秀美的香椿樹,挺拔地長在屋前的空地上,並沒有因為水肥充足就癡憨地瘋長起來。它矜持得很呢,將雨露閃爍在葉子上;葉梗兒發紅,像永遠披了霞光。她的確使人想起這樣的一株香椿樹。
畢業了,她和他都回村了。她依然常常穿著那身泛白的軍衣。那個年代軍衣時髦得很,她開始是趕這個時髦的;後來誰都發現軍衣使她更加漂亮了,她實在需要這樣的一件衣服。……肖萬昌安排女兒做了大隊廣播員。她可以不下田,這就招來了村裡人暗暗的怨恨。可是她的甜潤的聲音慢慢使人喜歡起來,人們都在心裡問:有這樣一個廣播員有什麼不好?
年輕人很寂寞,從學校回到田野很寂寞。李芒和小織每天要參加夜校,他們就在這時組織了一個文藝宣傳隊。
排練節目時,李芒常常著小織彈琴。
宣傳隊要到造田工地上演出,工地上的先進人物,無一例外地都要編進節目裡。只有李芒和小織兩個人是高中生,節目也就靠他們編了。他們常常編到深夜,一點也不累。他們編了快板、數來寶,自己先要說一遍。李芒能將數來寶最末一段的最末一句羅列上七八個形容詞而後押韻,這使小織覺得新奇而痛快。她靦腆,內向,極度興奮時往往垂下眼瞼,擺弄她那支鋁杆兒鍍金鋼筆。她那兩隻柔軟的、可愛的、未被粗重的東西磨損過的手掌不時去翻動一下紙頁,李芒把她弄亂的紙頁再理整齊。他總是微微含笑,表現了一個男子的沉著和自信。他和她很少說話,因為有些更細微的東西,有些還嫌模糊的感覺,語言反而說不清。他們兩人都自覺地在一種氛圍裡大致沉默著。夜色真美好,月亮姍姍來遲了。窗外不安分的鳥兒叫一聲,風懶懶地搖動著樹梢。他們疲倦時走出屋來,伸一伸腰,踩一踩濕漉漉的青草。小織腦後那兩個彎彎的毛刷刷在月色裡顯得特別可笑,揪一下多好,可是沒人敢揪。它就那麼驕傲地搖擺、顫動吧!它就那麼高高地翹著吧!暫時沒有人理睬,沒有人去過問……這裡是一所學校,就處在村子的西北角上,離村子有半裡之遙。校舍在一片稀疏的樹林裡,夜晚有一個老人在睡覺。此刻老人早就睡著了。
他們走出屋子時,聽到的是校舍四周各種奇奇怪怪的夜之聲息。蟲鳴、蛇走、刺蝟咳嗽,一個大烏鴉在遠處落下。村子裡狗吠了,小孩子在哭泣,有位老人悲傷地號啕,這聲音真正打破了一片寂靜,使月色也變得淒涼了……他們這時候就默默地望向那黑赳赳的村子,猜測著,憂慮著,用目光尋問:又是誰家的老人遭到了不幸?在這樣的夜晚裡,在這樣的月色裡,什麼事情都會發生啊……
老人的哭聲越來越大了,狗吠得更急了。他們終於聽出是那個老寡婦在哭。兩個人都長歎起來。……老寡婦只守著一個傻女過活。傻女瘋起來的時候就滿街亂跑,老寡婦就不吃不喝地跟上她。有一回老寡婦追傻女追到一片蓖麻林裡,出來的時候也變傻了:抓扯著自己的頭髮嚷叫著,說治保主任在蓖麻林裡糟蹋傻女了,不一會兒又說是民兵連長。她說的那個治保主任死了快兩年了,這顯然是瘋話。大家尋到蓖麻林裡,什麼也沒有看到,都說老寡婦是瘋了……
她從那開始就常常抓著自己的頭髮哭喊了。
兩個年輕人站在慘白的月色裡,覺得一陣陣發冷……
李芒說:「我記得傻女上小學時一點也不傻。她是後來才傻的……」小織回憶著,點點頭,「大概是十四五歲時……」
兩個人再不說話,往前走著。李芒走著走著突然站住了,眼望著遠處的樹影說:「有一回傻女在巷子口遇到我,笑著,一點也看不出傻來。這樣站了一會兒,她突然尖聲大叫起來,用手去扯自己的頭髮,轉身就跑了。我正發怔,覺得後面有什麼人,回頭一看,見民兵連長在我身後站著!原來傻女是看見他了……」
小織驚訝地望著李芒。
「你看,傻女見了民兵連長就瘋!……」
宣傳隊排練時,村裡的好多人都要迎著琴聲趕來觀望。民兵連長也背著槍趕來了,他還兼任著治保主任。他笑眯眯地看著好多人伏在明亮的窗前住裡張望,第二天就禁止了「隨隨便便看排練」。他一個人來,有時也陪伴支書肖萬昌。當肖萬昌不來的時候,他就找一個角落坐下,長久地盯著小織。肖萬昌如果來到這裡,總是顯得十分莊重。他不聲不響地坐下,先點燃一支煙。有一個漂亮的女兒活動在這裡,他顯得十分得意。在這裡,他的臉上流露得最多的神情,就是一個支書的威嚴和一個父親的慈愛。偶爾他也站起來,問一下文藝節目中的某個問題,那時人們就會知道,支書關心的主要是政治,他要在政治上把關的。這時候民兵連長坐在他的背後,微笑著,不時地遞給支書一支煙或是小聲地解釋幾句什麼。支書點著頭,顯出十分滿意的樣子。民兵連長跟支書說完話,就專心地研究幾個女演員了。他看得最多的是小織,但偶爾也警覺地掃一眼李芒。
有一次民兵連長一個人來了。他站到小織的身後看她彈琴,突然臉上消失了微笑。小織只顧彈著,當她黑亮的、柔軟的頭發落到琴上時,她就甩一甩頭。她想不到他站那麼近,有幾根髮絲碰了他的臉。他的臉有些灰黃,有著三十多歲的人不該有的深皺。他有些驚訝地張開了嘴巴,露出了被煙草染黑的牙齒,發出一聲很難聽到的呵氣聲。他伸手搓了一下臉,嫌熱似的退開一步說:「小織會彈!」……臨走時他對小織說:「明天,不一定排練了,李芒要去隊部開個會。」
「開什麼會?」小織冷冷地問。
「他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不開會還行?這是治保會的制度。」
從此,李芒就常常被叫到民兵連部開會了。這裡集中了二三十個年輕人,民兵連長和他們對坐著,一個人吸煙微笑。
他說:「先學習『老三篇』吧,待會兒再談。」他有時也請肖萬昌來講講話。肖萬昌常講的就是:「重在政治表現。到底是不是可以教育好,就看你們自己了。?」他走後民兵連長就發揮起來,有時扳著手指告訴他們哪個國才是「第三世界」。
他講累了就直眼瞅著一個女青年,嘴裡又發出不易聽見的呵氣聲。李芒在一邊暗暗想:民兵連長的腮幫上,就短那麼狠狠的一拳頭!
他從民兵連部出來,再晚也要到學校那兒看一看。這種帶有侮辱意味的會,使他沮喪極了。好比一個急需新鮮空氣的人被強迫關進一間發黴的屋子裡一樣,一經解放,就馬上奔到曠敞的原野了。他急於聽一聽那兒的歌聲,那兒的歡笑。
那兒有歌聲嗎?
太晚了,沒有歌聲了。只有一個人在樹下等他歸來,這就是小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