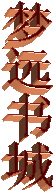
混沌加哩咯楞 第二章
「你的出身?」他又問。
「革幹!」我抬起頭。
「革軍!」小汀聲兒更大。
「嗯。」男孩兒把踏在椅子上的一隻腳拿下來,仔細地看了我們幾眼。他的眼
睛真是不小。
「會說' 他媽的' 嗎?」他走到講臺桌前去拿表格。
「······」我倆沒說話。在家白練了。
「啪!」男孩兒又用皮帶抽了一下椅子。「敢打人嗎?」
「······」我倆被他嚇了一跳。
「敢用鮮血捍衛紅色政權嗎?」他的眼睛又放大了一倍。
「······」我想起刮舌苔的老頭來。
「怎麼不說話?啞巴啦?!」他突然發怒,狠狠地用皮帶抽起桌子來。
「還不快回家去?你們太小了,什麼都不會,帶你們只能是累贅。」一個五年
級女生說。
「嗨,哥們兒何必認真?她們還是小孩兒。」另一個五年級男生沖大眼睛男孩
兒說。說話的人比我個子還矮。
「回家過了生日再來!」大眼睛男孩兒還是瞪著眼睛,好像他在忍著不笑。
玩兒蛋去。我突然想起哥哥說我的話。
我和小汀逃出教室,半天誰都想不出話來說。
「為什麼?」到了操場上我才問。
「(口)害,你還看不出來?因為咱們不會罵人唄。」
「那怎麼辦?」
「那還不好辦?練呀。」
「怎麼練?」
「來。」她拉我到牆角,「我先說一句,你跟我學,咱們倆比賽看誰說得好。」
「行。」
「他媽的。」她說。
「他媽的。」這句我會。
「你媽的。」
「你媽的。」
「你他媽的。」
「你他媽的。」
「你他媽的蛋。」
「你他媽的蛋。」
「你他媽的混蛋。」
「你他媽的混蛋。」
「滾你媽了個蛋。」
「滾你媽了個蛋。」
「你他媽的王八蛋。」
「你他媽的王八蛋。」
「你媽--- 」她突然停住不說了。
「你媽--- 」她笑起來。
「說呀!」我也笑。
「你媽---bi---!」她突然小聲說出來。
「你媽--- 」說不出來。「我不行。」
「你看我敢大聲沖著操場喊。」她兩腿叉開,大笑著沖操場運氣,像是準備跳
水。
我捂著嘴聽。
「你媽--- 你媽--- 你媽---bi---<---i---< 」最後一個字像炸彈一樣,使
「八·一八」司令部裡的全體人都把腦袋探出窗外看。
當紅衛兵的基本條件是--- 要當著所有人的面說出只有在公共廁所牆上才有的
話。媽媽說那種話只有最沒家教臉皮最厚的流氓才說得出來。關於厚臉皮,哥哥倒
有故事為楷模:說的是有個人死後到地域裡面去問閻王,為什麼我不長鬍子?閻王
說你本來應該長一寸長的鬍子,但你的臉皮是兩寸,所以鬍子拱不出來了。哥哥講
這個故事時一定自信他將來會長鬍子,再多罵幾句「他媽的」也沒關係。要光榮還
是要臉皮?大表姑說:「別當是孩子生下來就完了,往後的事愈來愈多。」事已經
不少了,誰都搶著向我證明活著不容易。人工體操之後就是走路、跑步、說話、爬
杆兒、雙杠、倒立、游泳、跳舞、寫字、算術······只為了在成績單上證明
你不是傻瓜。
「練死你!」男生舉著杠鈴沖自己說。
「練!」少先隊長說。
「出去練練!」打架的孩子們說。
人生就一個字:練。
「他媽的。」插上衛生間的門,在裡面對著鏡子練口型。慢慢張開嘴,鏡子裡
的眼睛是圓的。
「他媽的!」鏡子裡的眼睛又變成長的了。
「你他媽的!」從「你」字就開始使勁兒,牙咬緊,嘴唇往薄裡咧,眼睛更使
勁兒瞪,得讓這句話一出來所有人都怕你。「媽」字一出來,我發現我還長著酒窩。
嘿!我好像長得像哪個電影演員。「當電影演員還不容易?全一個模子。」哥
哥一說這個就撇嘴。「你得有那股勁兒,你看你就缺那股勁兒,哈哈就有。」大表
姑說,「哈哈,再扮一次女英雄。」我就使勁一瞪眼一梗脖子一抿嘴,大表姑又笑
又拍手。
「Cao !」罵出這個字算頂頭了。鏡子裡的臉通紅,看看四周,當然沒人,連
那個老趴在牆上的土鼈都沒有出來聽聽。
那只土鼈又大又黑,一堆長毛爪子伸開扒住衛生間的白牆。它常扒在澡盆上方
的那面牆上,如果你坐在馬桶上一抬眼睛就正好看見它。它從來不躲人,只有人躲
它,它要是在這兒我連屎都拉不出來。
這房子太老太大了,我是在這兒出生的第一代我們家的人,而土鼈、老鼠、蠍
子、蜈蚣、螞蟻可能已經是這兒的第好幾百代了。大表姑說每次「改朝換代」這院
子的主人都換:前一個房主在這兒殺了一個人跑臺灣去了;再前一個房主當了一回
漢奸就被殺了;再前一個跟著袁大總統鬧;再前一個給慈禧當太監;再前一個··
····爸爸說,說不定從前這是個屠宰場,也沒準兒是墳地。大表姑說爸爸淨揀
不吉利的話說。我說老鼠和土鼈的祖宗肯定沒有搬過家,哥哥就馬上想像古代的衛
生間是不是有臭味兒?
「那時候哪有這麼講究?」大表姑說。「得了吧,古代人絕對不會在一個房子
里拉屎和洗澡,想想楊貴妃出浴。」哥哥說。「媽呀,你還懂得楊貴妃出浴呢?」
大表姑吃了一驚。「那時剝削階級的生活方式。」媽媽馬上說。「我們不是也有工
人叔叔給燒鍋爐嗎?」我問。「爸爸對革命有貢獻。」媽媽說。可是爸爸並不愛洗
澡,寧可在門框上蹭他的背;我寧可帶著毛巾肥皂和街上小孩兒約了去公共澡堂湊
熱鬧。媽媽說:「這家人怎麼祖祖輩輩農民作風?」
我不喜歡這兒,屋子又大又暗,綠色的漆牆剝落後好像到處都是人嘴。除了大
還是大。大瓦房、大院子、大紅門、大影壁、大月亮門、大紅漆柱子、大搞臺階、
大蠍子、大土鼈、大毛毛蟲、大老鼠、大蜈蚣、大黑樹影子······「大表姑,
咱們家怎麼這麼不舒服呀?鄰居王大媽家一進門就是床,屋子裡香噴噴暖和和的。」
「你這孩子天生命賤不是?趕明送你上農村去算了。」「是不是吃貼餅子、燒柴火?」
「你先學學幹活吧,連手絹都不會洗還上農村呢。」大表姑教我擀麵條:先和麵、
後用擀麵杖擀,哽哽哽、哽哽哽,再擀得更薄更大,哽哽哽哽哽--- 哽哽哽哽哽---
手心兒又紅又癢。把大圓面片兒疊起來用刀切成條兒,這是麵條。大表姑說得擀一
個星期麵條才合格,然後擀餃子皮,然後學蒸饅頭,然後拿著大掃帚去大老鼠!
那是貓幹的活,老鼠跑得比我快多了,我和大表姑一人拿一把大竹掃帚滿院子
跑著追一隻小老鼠,直到它昏了頭。大表姑「噗」地一下拿竹掃帚把它按住,然後
揉巴揉巴,小老鼠就被揉巴死了。掀開竹掃帚一看,老鼠身上全是竹子戳的傷。大
表姑還不罷休,用火筷子又把它戳了兩個洞。我說它可憐,大表姑說它還沒長骨頭。
然後大表姑把貓放進地洞,讓它爬到地板下面去捉老鼠。可貓不願意,站在地洞口
叫了一夜,把老鼠全通知遍了。大表姑就罰貓三天不許吃飯,然後又放它進了地洞。
「不能嬌慣它,貓就得捉老鼠。」可它生了小貓、小貓又生小貓,一代一代愈來愈
不愛捉老鼠。我們同學家的貓每天喝牛奶吃魚,見了老鼠就藏起來,它怕老鼠。大
表姑一聽說這個,就「嘖嘖嘖」地撇撇嘴:「怪不得報上整天說要變修了呢!」她
更加把貓往地洞裡關。「造反」一開始,「革命反修隊」乾脆來個徹底「返修」,
把貓全抓起來殺了。大表姑一聽說又叫起來:「唉呦這趕明兒又耗子了可怎麼辦?」
然後她又心疼貓:「招誰惹誰啦?至於做的那麼絕?」貓們有的被屁股裡塞上「二
踢腳」崩得滿天飛;有的被從高樓上扔下去摔成了泥。大表姑把我們的貓放進一菜
籃子裡蓋上手巾送出了城。到了沒人的地方,放它出來,它又伸懶腰又打哈欠,跟
著大表姑就往回走。大表姑說:「哎喲我的媽呀。」把它裝進菜籃子裡又帶回來了。
第二天送它到更遠的地方,它一鑽出籃子就看著大表姑,大表姑又把它帶回來了。
第三天再送得更更遠,送到了山裡,放在大樹下,大表姑沒敢多看,撇腿就往回走,
它沒叫也沒跟著回來。最近老有只特大的野貓站在我們家房頂上,誰都覺得它長的
像送走的「花兒」,叫它它也不下來,只是沖著我們笑。大表姑說它當野貓當壯實
了,比原來大了好幾倍,一千那張臉也不大愛笑。我說當野貓比當家貓好,家貓得
成天給人拍屁拍,還被迫著抓老鼠,最後還被判死刑。
「Cao !」這句話還是說這費勁兒,而且不知道什麼時候罵。
「砰砰砰」,有人敲衛生間的門。
我打開。
「拉金子呢?這麼長時間?」大表姑問我,「快來安慰安慰你哥哥,他們組織
讓他帶頭' 破四舊' ,他燒他的集郵冊呢!」
那可是哥哥的命根兒;那些郵票呀,他仍了不要的都夠我在小學裡辦展覽的!
我跑出去。
活已經著起來了。那些成套成套的郵票,那些方塊兒、三角、菱形和彩色紙片,
那些可人疼的全世界各國童話故事、偉大人物和花鳥蟲草名勝古跡,那些誰都懶得
記必須用郵票提醒的歷史大事件及其他,全跟著火光消失啦。它們變成小紙灰飛到
空中又落在哥哥的白回力鞋和紅袖章上。哥哥哭,大表姑因為心疼哥哥也哭,我卻
找不出合適的詞安慰他們。
「操!」我突然說。聲音不大,但我說出來了。大表姑的小眼睛突然瞪圓,眼
淚也突然停了。可哥哥沒理我。
一提起往事哈哈就像吃了興奮劑一樣無論沖誰都想嘮叨個不停。她也奇怪怎麼
過去的屁大的事也是事,而現在仿佛生活裡不放炸彈她就不知道是不是還活著?每
一分鐘她生活中的「現在進行時」都被她硬拉出來的「過去完成時」給比的黯然失
色。哪怕是她和麥克去吃飯,看著飯桌上的蠟燭她也不會停止回憶:「你要是拿了
燈一照才發現到處都是蛆,地上都鋪滿了,沒有下腳的地方。過了春天蛆長成蛹,
睬在腳下吱吱響,糞坑裡泡著死豬死雞,不小心掉下去,跟跳進游泳池裡一樣!」
她笑麥克也笑。大餅、炒飯、印度菜就跟著中國農村大糞坑的想像力全進了肚子,
「怎麼不影響你的胃口?」哈哈故意問。「吃的更多。」麥克也要顯示他的瀟灑,
「這像大糞一樣。」他指著咖哩做的菜,說得哈哈反倒吃不下去了。
「你不知道只有我對大糞有真實的感覺?」她委屈地說。
「噢!對不起,我以為你已經麻木了,再說誰對大糞沒有真實的感覺呢?」麥
克邊道歉邊笑。
「不一樣!」她堅持她的權利。
「對不起!」麥克再次道歉。
那時候麥克也中了邪,她說什麼他都愛聽。
「要是那時候我嫁給了農民呢?」她捏著他的鬍子說。
他用嘴堵住了她的嘴。
「要是那時候我得了麻風病呢?」她剛一有工夫喘氣就說。
他幫她解扣子。
「胖子才值錢。我們那個村子娶媳婦論斤秤……」她看著自己的肋骨。
他迫不及待地要把愛奉獻給這個「歷盡滄桑」的「異國情調」,含著眼淚摟住
她,她只是在他的身子底下問:
「你知道什麼叫血吸蟲病嗎?」
麥克是哈哈在大學裡的老師,兩人一見鍾情。麥克說哈哈是非同尋常、神奇不
可知;哈哈說麥克成熟的恰到好處,哥哥爸爸情人弟弟全能當了。麥克愛聽、哈哈
愛說、麥克用愛的氣氛給哈哈製造了一個由她暢開說的舞臺,哪怕哈哈自己也懷疑
麥克是否真聽得懂,但她一見麥克,要說的話就跟洪水氾濫似的擋不住。回想起來,
似乎純屬是她用「過去」引出她兩人的「現在」,而真實的生活其實是麥克離不開
她的未婚妻。
麥克的未婚妻,誰都沒見過誰都知道,但一點兒不耽誤麥克有無數女朋友。和
哈哈在一起時,麥克和所有的女朋友斷了關係,但只有未婚妻仍在那個牢固的座位
上暗暗坐著。麥克和哈哈在一起時打電話給未婚妻、和未婚妻在一起時打電話給哈
哈。對麥克來說,這正常得跟麵包上要抹黃油一樣;對哈哈來說,這無疑是枕頭底
下勞放把手槍。
「不行,我這叫小偷。」她說。
「我們倆是天生的一對兒,天生的東西還用偷嗎?」麥克說。
「不行不行,算了算了。」
「不行不行,堅決不算。」
「這事情太複雜。」
「這事情很簡單。」
「怎麼辦?」
「我愛你。」
「你跟麥克的事真是亂七八糟!」東霞說。她也從北京來,自稱北京人都有共
同語言。
「簡單極了,他愛我我也愛他。」黃哈哈一口氣說出這句話,做出一副瀟灑狀,
其實心裡「對、錯、對、錯」已經走了好幾遍了。
「他有個未婚妻是不是?聽說比他小十歲,還特別有錢?」東霞邊說邊大口嚼
果子。她是理工碩士生,丈夫還在北京,她等了四年才等到丈夫有了助學金,最近
也快來倫敦了。為此她老自稱「王寶釧」,頭一回給自己買了新衣裳,以前她老給
人一種身上有味兒的印象。
「······」
「要不就拆了他們,要不就跟他吹!」沒等哈哈答話,東霞就邊往裡面咽邊往
外噴果子邊說:「別把事情弄得這麼不明不白的,讓別人說起來也不光采。」她果
斷地把一個果殼吐在地上。
「生活本來就不明不白,活著也不是為了讓別人說。」哈哈邊說邊想:我要是
真信這個就好了。
「挑明瞭算了,好就好,不好就拉倒,別白耽誤工夫。」東霞又吐了一個果殼。
什麼叫不耽誤工夫呢?
「要不要性交?」一個倫敦年輕人迎面走過來突然沖東霞說,但並沒看她。
哈哈也愛找老古聊天兒。他們在北京是「一個圈兒裡的人」。
「人哪,得節制。」老古斜著眼睛瞧她。他自稱是「俗緣已畢」。
「俗緣已畢你上倫敦來幹嘛?」哈哈也自以為很知道他,有時甚至想像要是和
老古在一起會免了一切誤會麻煩和神秘感,可是沒了神秘感就沒了激情;沒了激情
就沒了麻煩;沒了麻煩就什麼都沒了。
也許這世界對老古來說已是「什麼都沒了」,連他談「性」的時候臉上都帶著
一副超凡入聖、刀槍不入的表情,嘴皮子不大動,可說出來的又都是「性」的絕密
震驚,面對一屋子聽眾,他能越說越「邪乎」可愈說愈嚴肅,最後使聽的人只覺得
自己豬狗不如。
「外國人……當然你要想活得熱鬧點兒……」他的話總是一半兒一半兒地說:
「別染上艾滋病就行。」他用細長的手指為毛筆摘毛,不動聲色地盯著筆尖兒。
哈哈知道跟老古談什麼「愛情」簡直是找罵。在他那兒,西洋人是艾滋病的象
征,東洋人是小家雀。這世上沒人值得為他/ 她著急上火,你要是說:「我愛他/
她……等等等,他會笑著說:」這麼大把年紀怎麼甩起小孩子脾氣來了。「
他表面瀟灑實際「克制」,怕坦白怕得邪乎,用「幽默」把人都降到蠢驢的地
位。以前他也曾為女孩子甩過菜刀,後來歲數漸長,在他的字典裡「愛情」就和
「愚昧」成了同義詞。
「行了行了,你老大不小的,找個歸宿吧。」老古說。
「什麼他媽的歸宿,我還什麼都沒說呢,你怎麼就說起歸宿來了?怎麼什麼事
都得有結果呀?」哈哈知道老古已經把她的問題「簡化」了。
「那你想說什麼呀?愛情?那你就愛唄,還說什麼?要不就結婚,這不是歸宿
嗎?」
「我他媽現在是第三者。」
「我說你是想活得更熱鬧不是?」老古笑。
哈哈也氣得直笑。
「鬧,三者、四者、五者、六者,能鬧就鬧,反正比不鬧強。」他站起來去沏
茶。
「我想結束了。」哈哈認真地看著老古的後背。
「那就結束,吃點兒好的,比什麼都強。」他沏好茶,吹吹浮在茶缸上面的茶
葉。
「告訴我該怎麼辦。」哈哈站起來,還指望談話可以稍微認真點兒。
「我替你?」他故意一本正經地看著她。
哈哈過去狠踹了他一腳,轉身走了。
「女人哪。」背後是老古的最後一句話。
女人哪。男人呢?「一聲巨雷震天響,孟薑女哭倒鐵長城,」「回想起十八年
春秋度寒窯,老爹爹比我改嫁也徒勞,平郎他飛黃騰達多榮耀,寶釧我砂明水淨也
清高。」除此之外似乎沒有別的活法,老公終於「飛黃騰達」,老婆必得「砂明水
淨」。包公加陳世美、武松加潘金蓮。俗話說:「生米煮成熟飯」,什麼叫生米,
什麼叫熟飯?熟飯就非吃不可了?你要是胃口不好呢?「要節約鬧革命」。
什麼是對?什麼是錯?
哈哈從椅子上站起來,乾脆坐在桌子上,覺得位置高點兒可能有利於思考,最
後看著大街上的垃圾桶出神,還是想不明白。
當然,在老古的字典裡面,女人幾乎沒有智商。有那麼一點兒還被逛商店給消
耗了。遠古的時候,也沒那麼多商店,女人就用那點兒智商來算計家用,全用光了,
只剩下力氣對付菜刀和丈夫。後來呢?「後來呀,這不愈活還愈熱鬧了不是?」老
古對女人的故事就講到這兒,哈哈知道老古又在挖苦她,也知道如果少問問題多裝
糊塗,生活會更顯得美好。男人愛聽女人說:「不知道。」
她盤腿坐在桌子上盯著樓下的垃圾桶。麥克和她現在是真吹了,他那股「不行
不行堅決不算」的熱情也消失了,哈哈不用再內疚,小偷的義務讓給另外一個女人
了,而那個未婚妻仍是在家裡穩穩地坐著,等著麥克從那個女人家掛來的電話。第
三者的責任卸了,哈哈還死纏在「是非感」中想不清。過去猶豫得認真、愛得也認
真,剛以為找到了「歸宿」,又咕咚一下坐回自己的破船上。「愛情」是什麼?垃
圾桶?破玩具?手絹?錄音機?麥克風?報紙?煙缸?圖書展覽會?冬天儲存的大
白菜?
他發現智商還是不夠使,連腳趾頭都用上,也算不清人生有多少道理。麥克突
然告別的理由是她「太深刻」,這評語她這輩子倒頭一回聽說。
哈,倫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