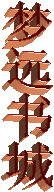
立體交叉橋 第五章
十五
侯勇打完電話,掀簾進屋一看,使不禁心裡發堵。
屋裡滿滿騰騰全是人,方桌上擺了兒樣酒菜,父親侯勤豐已經下班回來,正與侯銳分坐在方桌兩邊對酌。侄女小琳琅趴在床邊,一邊玩一個已經跌破了頭的舊塑料娃娃,一邊吃著一個棒棒糖;母親和嫂子白樹芬一個坐在籐椅上,一個站在洗臉盆架子前頭,興致勃勃他講著什麼。整個屋子裡彌漫著一股糖醋帶魚的味道,這味道使侯勇深入骨髓地意識到這間屋裡的低級與鄙俗,加以剛才的電話弄得他心煩意亂,他恨不得立即發作一番,泄一泄心中的鬱悶。
「老二呀,你也來喝兩盅吧!」父親見侯勇進了屋,如獲至寶,居然欠起身,象讓客人似地來了那麼個動作,這使得侯勇把一腔邪火壓了下去。在他看來,父親的姿勢、表情,集中體現出了父親的慈祥、善良、庸俗、淺薄、懦弱、誠實……侯勇勉強做出一個笑臉,說了聲:「爸,您先喝著吧,我有點累,先去裡屋靠靠。」便理也不理正對他點頭的嫂子,幾步邁進了裡屋。
侯勤豐與老伴的不同之處,在於他對三個子女都充滿了自豪感與信心。侯銳曾在《北京日報》上發表過詩作一事,至今他仍念念不忘;而且,每當他在郵電所發信載有蔡伯都的劇本的刊物時,他便不由得油然聯想起自己的老大侯銳,他總覺得憑老大的才學,早晚有一天,他也會在發售刊有侯銳大作的雜誌。對於侯勇,他的滿意自不必說了,只不過他比老伴自尊,他去親家的次數,一年控制在「十·一」和春節這麼兩次,而且從不在那裡留宿,甚至也不在那裡洗浴,他總覺得當親家母才有資格享受的事情,他作親家翁的不必去沾光,對於侯瑩,他仍然堅信是可以找到一個相當不錯的丈夫的,剛才聽說蔡伯都正給侯瑩介紹一位當編輯的對象,他不由得心花怒放,借著酒興,他笑吟吟地說:「好呀,趕明兒老大寫詩,女婿編詩,我來賣詩,咱們家都在一行上了!」
侯勇進了裡屋,靠在侯瑩睡過的床鋪上,本沒有注意聽屋外幾個人的談話,忽然,嫂子的亮嗓門把這樣的話語甩進了他的耳中:「……咱們東單十字路口的立體交叉橋,聽說可能明年春天開工!咱們這兒今年秋、冬還不得拆遷完畢?……」
啊,立體交叉橋!
侯勇的腦海中立刻浮現出電影上見過的鳥瞰鏡頭:立體交叉橋在大土上劃出優美的直線與弧線,穿梭的車輛自由自在地奔馳著……
是啊,有了立體交叉橋,不,甚至還不需要建成立體交叉橋,僅僅是開始拆遷這周圍古老的胡同,包括侯家在內的許許多多家庭的命運,將會發生多麼大的變化啊!
在拆遷的過程中,侯家起碼能夠分到一個三間的單元,那就夠了。侯銳夫婦和小琳琅盡可以佔據一間,父親母親平時佔據一間,侯勇回家時,侯瑩暫去同母親同住,父親同侯勇合住一間,豈不天下太平?侯銳夫婦和侯勇都不在家時,家裡會多麼寬敞,侯瑩的神經質,在那寬鬆的空間中定會得到慰息,因而她也就可以更順利地嫁出去……侯勇和愛人倘若調回來,怎麼住呢?也住得下,侯瑩嫁出去空出來的那一間,不就正好留給了他們嗎?侯銳一家的戶口,一旦拆遷完畢以後,也便可以暫時遷出一段,以利侯勇夫婦調回,那麼他們有了漂漂亮亮的房子,那戶口幹嘛非死留在父母的房口本上呢?……
唉,立體交叉橋!
快建成立體交叉橋吧!不,就算一時半會兒建不成,也快點拆遷吧!這對於政府來說,對於那些已經住上了寬敞的房屋,享有著充分的空間的人來說,該並不是一樁十分困難的事!
有了立體交叉橋,侯勇也就不用找葛佑漢,去進行那莫名其妙的三角交換的把戲了;也就不必為自己家與岳父家的強烈對比而痛苦了,也就不會對哥哥和妹妹那般粗暴了。甚至對二壯,也就不會有一種天然的隔閡與仇恨了;侯勇的靈魂便可以不再那麼蜷曲,那麼萎縮,那麼壓抑,那麼憤懣,那麼煩躁
侯勇就那麼靠著,嚮往著,什麼理論,什麼宣傳,什麼道德說教,什麼文藝感化,什麼會議,什麼口號,什麼文件,什麼精神,什麼民主,什麼獎勵……他認為尋他都不管用,啊,我只要一座立體交叉橋,給我一座立體交叉橋!
立體交叉橋,這意味著將有限空間向寬闊處開拓,意味著將擁擠的人流向開闊處疏導,意味著給人們提供更多的空間,在人與人的關係上提供更多必要的回避機會,因而也就意味著撫慰、平息大量因空間壅塞而感到壓抑與痛苦的靈魂!
這個晚上,侯家的人又說起了立體交叉橋。他們沒有意識到,每當他們聚到一起時,這個話題便會自然而然地排擠掉別的話題,而成為他們談話的一個長時間的中心。
這回,又是白樹芬頭一個提起立體交叉橋的,白樹芬的一個大學同學,後來調到了市政建築公司工作,她的消息是從她那兒來的,似乎格外具有權威性;其實,那仍不過是一種傳聞而已。
十六
侯家以及他們那一片的居民,與其說是嚮往著立體交叉橋,不如說是嚮往著拆遷。
拆遷!對於北京市成千上萬仍舊住在古老的、不方便的、往往是擁擠的平房中的家庭來說,不啻是福音,是通向光明與幸福的階梯。拆遷總是伴隨著這幾種情況發生的:要建龐大的公用建築;某系統某單位要徵用地皮進行擴建;要為首長建築用房;房屋危險需拆除重建。解放後的頭十多年裡,政府對拆遷戶充滿了歉意與關懷,所以,幾乎所有的拆遷戶所提出的要求都得到了滿足,凡拆遷到新住宅的,不但肯定可以改變幾代同室的擁擠狀況,而且往往大大地擴大了居住面積,改善了居住條件。那時候,拆遷戶本身很少提出非分要求,未輪到拆遷的家庭對他們也不嫉恨,因為總覺得市政建設發展得很快,不久也便會輪到自己。主辦拆遷的工作人員們那時也比較廉潔公道,很少有因受禮受賄或因「背景」、「面子」而徇私的事情發生,直到今天,人們還津津樂道一九五九年因修建人民大會堂而拆遷的那些住戶的可羨命運,他們不但一律遷到了比原有條件好的新住宅樓中,而且,人民大會堂建成後,他們又一律受到了市長的親自邀請,成為了那富麗堂皇宮殿的首批參觀者,並在金碧輝煌的宴會廳中受到了一次終生難忘的款待……
然而,北京市政建設的發展遠非一帆風順。
看看散佈在北京城內外的近三十年所建的居民樓吧,五十年代初第一代居民樓的典型,如景山後街兩旁的那一組高樓,高大的琉璃頂,寬闊的玻璃鋼窗,平均二十多平方米的大開間……絕不實用,但體現著當時人們的心境:社會主義就是如此氣派,共產主義指日可待!第二代居民樓所建不多,其典型如西城福綏境大樓和廣渠門內大街的「安化樓」,沒有大屋頂了,但追求層多體大。那是一九五八年「城市人民公社居民住宅」的活樣板,當時的時代氣氛,是「共產主義就在眼前」,而「共產主義」的象徵之一,便是「樓上樓下,電燈電話」;許多居民在自豪的鑼鼓聲中搬進去了。開頭,他們也曾被人羡慕,但很快地,隨著「大躍進」理論上的絕對「成功」和實踐上的徹底失敗,待建的這類樓房停建了,住進去的人們一天比一天更煩惱與苦悶;電力缺乏,無法安裝與使用電梯,住在八層上也只好爬上爬下;以煤氣為燃料始終只是一種設想,因此還得從樓下往上搬蜂窩煤;有幾年冬天,甚至無法供應暖氣,因此家家只好升火爐取暖,於是大樓很快便被熏黑了,加以保養工作很差,現在看去,這樣的大樓便有如擱淺在沙灘上的生銹的巨輪。從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新的居民樓蓋得很少。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六年春天,是第三代居民樓大規模崛起的黃金時代,在和平里,在三裡屯,在西郊的許多地區,設計得比較合理的、外觀看上去也算順眼,然而無可避免地互相雷同、顯得單調的大片不算太高(以五至六層為多)的居民樓雨後春筍般地出現了。住在這些樓裡的居民,至今仍被樓外的大多數北京人視為天之驕子,人們在拆遷時所最嚮往的,就是這類居民樓裡的單元。然而好景不長,一九六六年夏天的急風暴雨一來,這樣的已蓋好而未及住上人的空樓,便首先成了到北京進行「革命大串連」的紅衛兵小將:的臨時招待所,他們毫不愛惜這些新樓,所造成的破壞,使後來遷進去的居民們費了很大力氣,才一一彌補上。到了一九六九年左右,「隨時準備打仗」的氣氛甚囂塵上,大量的資金和人力都投入到「深挖洞」的偉大工程中去了,於是在北京各處都出現了一些名副其實的「簡易樓」,又名「戰備樓」,這算是北京市的第四代居民樓吧,它們的特點是低矮、狹小、單薄、醜陋;這類樓房在修建時還往往把一些磚頭突出,以形成「敬祝偉大領袖毛主席萬壽無疆」之類的標語,後來人們意識到這是無謂的與不必要的,又搭起沙篙架將它們一一鑿掉,結果本來就很醜陋的樓牆就更顯得不堪入目。「簡易樓」幾年後便聲名狼籍,於是,從一九七五年鄧小平同志第一次複出主持國務院工作起,又開始興建聞名於世的三門工程,即在崇文門——前門——宣武門一線的原順城街(內城與外城的分界線)南側,蓋起了一排有如灰色高牆般的多層居民樓。這些居民樓的特點是只求總體高聳集中的「唬人」效果,而設計上很不實用,施工也相當粗糙;這類大片居民樓的修建從那時一直持續到今天,隨著近幾年人們思想的變化,每一座新建成的樓總比前一座建成的樓要多少改進一點,不但更注意內部的實用,也更注意外觀的美觀協調,這,大致就構成了北京的第五代居民樓。
雖然以上面的眼光計算,三十年來北京市蓋起的居民樓已有五代之多,而且近兩年來建成的數量與以往相比大有增加,但是能分到新樓單元的,主要還是大機關的幹部以及各種需落實政策的高級知識分子、民主人士,一般的市民仍舊排不上號,他們只好照舊擁擠地居住在古舊低矮的平房之中。不用往偏僻的地方去,即以從西單商場向北直抵新街口商業區之間的十裡長街兩側而論吧,有多少居住在狹小黑暗的小鋪面房中的家庭啊!他們開了家門就是人行道,沒有廚房,只好把爐子擱在門外,用漆成灰色的鐵皮做個小罩子,罩住那爐子。有時早晨現升火,從拔火筒中冒出滾滾的濃煙,與馬路上汽車排出的廢氣在空中匯合在一起,形成一張罩住北京城的污濁的氣網。象侯家這樣的住在胡同小院裡的家庭,跟他們一比,還算幸運的呢!
這些住在古舊擁擠的平房中的普通市民,既然不可能象大機關的幹部那樣,有機會分到新樓單元,他們便只得寄希望於拆遷,故而他們經常把拆遷作為一個話題,隨時展開著牽心掛肺的議論。有的企望著在自己那一帶蓋劇場,有的企望著有自己那一帶蓋旅館……侯家那一片的居民,則企望著在東單十字路口早日修建立體交叉橋。
隨著人們見識的增長,拆遷中的戲劇性因素,特別是鬧劇和悲劇因素也不斷地增長著。
常有這樣的事發生:住著較好平房的人,自願與住著較差平房的人換房。為什麼呢?就因為他打探到了這樣的消息:後者所住的那一帶將要開始拆遷!
也常可以看到這樣的景象:一大片房屋已經拆掉,出現了一片頗大的空地,但獨有一所搖搖欲墜的住房仍兀立在那空地之中,裡面依舊住著人,屋外的幾株蒙滿塵土的向日葵也便依舊聳立著,而小廚房裡也照例往外飄著油煙……凡懂得拆遷一事的北京人都知道這是為什麼:房裡的主人向拆遷的部門提出了很高的條件,對方如不應允便堅決不搬!這種拆遷中的「硬骨頭」,雖不一定能夠如願以償,總也會比那些「聽話」的拆遷戶多得些好處。
還有許多不能直接看到的情況,一些如葛佑漢似的人物,他們本來與一場拆遷並無關係,但他們就象蒼蠅撲向變質的鮮肉似的,聞味而至,與拆遷部門的人打得火熱,從中得到好處;當然,更有一些為官的、有錢的、近水樓臺的人在幕後進行著微妙的,或公然違章的,或表面上符章而實際充滿「貓匿①」的勾當,結果是一些與拆遷無直接關係的人從拆遷中大獲利益,而一些與拆遷有直接關係的老實人、懦弱者,卻被剝奪了某些連他們自己也不清楚的應得的好處……
①貓匿:北京方言,指搞小動作、耍花招等不正當手段。
如今,人們對拆遷,已不是二十多年前的那種純樸的心情了。人們知道拆遷的機會並非易得,所以應當充分珍惜,錯過了這一次,那下一次不知多少年方能到來。人們懂得拆遷中會遇到「貓匿」,因而必須分外精明。總之,對於人們來說,拆遷乃是一生中只能遇到一次的大事,是難得的開拓居住空間的機會。的確,拆遷的給房標準儘管在一再地壓低,但大體上總還體現著不硬行拆遷、給予改善居住條件的原則,至今仍為狹小的空間壓抑著的千千萬萬的北京市民,對於拆遷,他們真是望眼欲穿啊!
十七
外屋關於拆遷和修建立體交叉橋的議論,把侯勇從裡屋吸引了出來。侯勇的重返外屋,使父親非常高興,他甚而產生了一種感激兒子「賞臉」的心情。
白樹芬一見小叔子出來,也便招呼說;「你們仨先喝酒吃飯吧,我跟媽、小琳琅等你們吃完了再吃。」
侯勇淡淡地「嗯」了一聲。他心裡想:你這當嫂子的,說這話就算賢惠了嗎?其實主要還不是因為屋子小,沒地方,倘若這屋子寬,八仙桌往外一抬,你保管得同時上桌子吃。
侯勇一邊這麼想著一邊過去面牆坐下,同父親、哥哥一起喝酒。
本來,立體交叉橋這個題目,是最能使他們一家人息掉宿怨的;但是侯勇一摸酒杯,就不禁想起了剛才接到的電話,葛佑漢還等著他去呢!去幹什麼?去走路子調回北京!欲成此事先需如何?先得讓哥嫂侄女把戶口遷出去!先得讓侯瑩嫁出去!什麼立體交叉橋,什麼拆遷,沒影的事兒!有影的事兒便在今晚!想到這裡,他便繃著一張臉,對於父親的問話,只是「嗯」、「哼」地敷衍著。
「老二,吃菜呀!」父親象對待貴客似地,滿臉笑容地招呼他說:「吃塊帶魚吧,你媽的手藝,退休以後提高了不老少……」說著,便往侯勇的碗裡挾紅燒帶魚,侯勇端起碗,使勁地一躲,父親吃了一驚,筷子一抖,一大塊紅燒帶魚中段掉到了地下。
這情景使侯銳萬分憤慨,他不禁紅漲著臉,喝斥侯勇說:「你怎麼回事兒?給你臉你不要!」
母親發現了這一鏡頭,忙走過來勸解,先對老伴說:「人家老二如今不吃這無鱗魚!」又勸侯銳:「成啦成啦,好不容易全家團團圓圓的,你就少說兩句吧!」
父親滿臉尷尬,確確實實下不來台。他驀地回憶起當年被單位裡「專政」時的情景。他被關在地下室中交待歷史上的罪行,每天認認真真工楷書寫好幾張信紙的交待材料,寫完以後,就不免要想點別的,他常常想到的,便是老伴作的紅燒帶魚,尤其是當看守人員給他端來窩頭和白菜湯時,他就極其生動地回憶起那紅燒帶魚的色、香、味,乃至於剛出鍋時,帶魚段表面上那閃閃發響的小油泡。後來「落實政策」,放他回家了,邁進家門,他對老伴提出的頭一條要求,便是「買點帶魚燒給我吃吧!」老伴提著菜籃,從東單一直尋覓到哈德門外,才終於買到了二斤帶魚,回家來沒歇著,立即拾掇、烹燒……唉,記得那一天侯銳不在家,侯瑩也在兵團沒回來,就侯勇從插隊地點回來探家,侯勇簡直是撲上去搶著吃,一大盤紅燒帶魚,侯勇倒吃去了三分之二,那情景真是歷歷在目啊;可今天,侯勇成為「將門貴婿」了,人家不屑再吃這種無鱗魚!……想到這兒,父親有點撐不住,眼圈兒頓時紅了,鼻子一陣陣發酸,他歎了口氣,仰脖喝幹了大半杯二曲酒。
父親的神情,使侯勇多多少少有點良心發現,他便掩飾說:「在飛機上我就有點反胃,這會兒好象更厲害了。我今天不想吃葷腥……」說著他挾了一筷子涼拌黃瓜,吃完又喝了一口酒。
侯銳見侯勇自動下了臺階,也便光是瞪了他一眼,不再說什麼,悶頭只管喝酒。
一時間屋子裡變得異常肅靜。
又喝了幾口酒,侯勇就起身宣佈說:「我還有事兒,得出去。不在家吃飯了,你們吃吧!」
父親和母親望著他,光知道用眼神問:「你去哪兒?」卻都說不出口。侯銳自然不會沉默,他梗著脖子問:「你怎麼這時候還出去?」
侯勇一看腕上的手錶,已是八點五分,他沒有工夫吵架,他怕去晚了見不著葛佑漢,那傢伙經常是神出鬼沒的;因此,他便和和氣氣地對侯銳說:「去趟北新橋,業務上的事,晚上人家在家,晚上去家裡找比白天去單位找好說話。」說著他拔腿便要出去。
誰知,臨出門他被嫂子白樹芬給叫住了。
十八
在侯家這小小的空間裡,真正對侯勇無所懼讓的,只有白樹芬一人。
白樹芬會置身在這麼個空間裡,說起來真是一件她自己當年萬萬想不到的事。
退回十六年去,白樹芬正在家鄉南昌上高中,是班上的團支部宣傳委員。如今她還保留著大量當年的照片,那些照片上的白樹芬,是一個身材苗條、隨時隨處把兩隻眼睛彎成兩個月牙兒使勁歡笑的姑娘。那時候她最愛唱的歌,是《地質隊員之歌》,那歌曲的頭一句:是那山谷的風吹動我們的旗……多少次惹出了她滿眶的眼淚!聽了一次地質局幹部的報告,看了一場描寫地質隊員生活的影片《沙漠裡的戰鬥》,她便認認真真地在日記本上一遍又一遍地書寫著「立志作一個地質尖兵」的誓言。那時候的青年多麼單純!党的號召,祖國的需要,人民的期望,這些話一灌進耳朵,心頭上立即燃起熊熊火苗。一九六五年報考大學時,白樹芬在志願表中填滿了地質學院的各種專業,當她得到一紙北京地質學院的入學通知書時,她覺得自己成為了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她簡直是唱著、舞著來到北京,來到北京地質學院的……
然而,接踵而來的世態,將白樹芬的天真狀態擊得粉碎,他們進校便被派到農村去參加「四清」,據說不管學哪種專業,頂要緊是必須學習階級鬥爭這門主課;從「四清工作隊」回到學校,剛開始學了一點基礎課,忽然爆發了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白樹芬猶如一個掉到海中的軟木塞,她沉不下去,卻浮得分外痛苦,隨時被翻騰呼嘯的惡浪拋擲著、沖蕩著……
白樹芬目睹身歷了許許多多讓以後的歷史家們研究不盡的事,她的思想在震驚和煎熬曾經極度混亂,然而即便是那種情況下,為自己的祖國和人民開採寶藏的意願,仍象古蓮種深埋在煤層一樣,存于白樹芬心中。多少次,她以為「這下總該讓我們學地質了吧」,然而「是那山谷的風吹動我們的旗」的理想,一再如同風撲肥皂泡般地被破滅著。
當地質學院裡的兩派武鬥最激烈時,白樹芬雖然也附驥於最強大的一派「地院東方紅」,但她只是一個掛名的成員,因此她逃到了住在城裡一條小胡同的姑姑家中。姑姑家「文革」中也飽受衝擊,那裡的生存空間也非常狹窄,除了晚上勉強可以臨時搭一塊鋪板給她一個床位,白天簡直沒有多少轉身的地方,於是她和同院的比她小兩歲的葉玉秋交上了朋友。葉玉秋因病沒有下鄉插隊,在家裡待分配,她家雖然也並不寬敞,但總算有一個角落可供讀書、談話,於是她們兩個就常常坐在那個角落裡,讀一點劫後餘存的外國小說,絮絮地談一點只有她們兩個之間才能談的私房話……
後來白樹芬聽說工宣隊已經進校,武鬥業已結束,她心底裡又浮出了「是那山谷的風吹動我們的旗」的歌聲,於是便回校去探察究竟,誰知一去,便被工宣隊扣下了,說是地質學院已決定外遷,根據「農業大學辦在城裡不是見鬼了嗎?」的邏輯,地質學院辦在城裡當然也是見鬼,必得搬遷到山溝裡去……白樹芬被編入了打整搬遷物資的連隊。那時的地質學院已經慘不忍睹了,教學樓的樓牆上有彈痕和被火燒過的焦跡,窗玻璃很難找到一塊完整的,昔日整齊漂亮的操場這裡一堆穢物,那裡一個大坑,更不用說到處都有破敗的大字報和新塗寫的惡俗不堪的標語口號……啊,這裡己是文化沙漠,「沙漠裡的戰鬥」終於兌現了!
後來突然又來了一道什麼戰備命令,工宣隊要求大大加快設備拆裝外運的速度。當時白樹芬他們那個小組負責裝運的全是些玻璃器皿之類的儀器,她找到工宣隊的一位負責人,試圖告訴他:這些東西必須極為耐心地收放包裝,否則會造成重大損失,因而可否不必硬性限期完成任務?那工宣隊負責人氣乎乎地把白樹芬訓了一頓,咚咚咚地大步來到實驗室現場,把兩個正小心翼翼因而顯得慢慢騰騰地裝箱的同學拉拽開,示範性地把剩餘的幾件玻璃儀器往箱裡一扔,「咣啷」蓋上了箱蓋,拿起草繩就捆綁,為拉緊草繩打結,他一隻大皮靴毫不留情地踩了上去,只聽木箱裡一陣玻璃破裂的聲響……
這響聲埋葬了白樹芬心中對從事地質事業的最後憧憬,也送走了白樹芬心中最後的一絲溫情,一絲嚮往,一絲對自身以外的責任感。
白樹芬意識到,一俟搬遷的苦力活結束,她也便會象已經分配走的同學一樣,面臨著極為可怖的命運,她接到了先期分配走的同學的來信,那些在運動初期被江青親昵地摟著肩膀誇獎過的「小太陽」也好,那些在運動當中被當作「修正主義苗子」、「現行反革命」、「五·一六陰謀集團分子」而被整得脫了一層皮的「小爬蟲」也好,那些以為當個逍遙派便可僥倖逃脫厄運的「膽小鬼」也好,除了極個別有背景、有門路的而外,幾乎全都被當成廢物,處理到了與他們所學專業、所抱理想全然不沾邊的工礦、農村,據說因為他們是大學生,因而就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因而也就是最危險最討厭最無用的東西,所以必須讓他們幹最髒最苦的體力活,以利他們脫胎換骨,在接受「再教育」中重新作人……
正是在這種形勢下,白樹芬在姑姑所住的院中,在葉玉秋家裡,遇上了蔡伯都;正是出於蔡伯都的樂善好義,才介紹她同侯銳見了面;她通過與侯銳確立了夫妻關係,這才爭取到了分配時照顧她留在北京郊區,並且爭取到了去公社中學教物理課的工作。
白樹芬幸福嗎?她對幸福的渴求;早已枯竭到麻木狀態,所以她現在很少去思考這類重大嚴肅的問題。她有了丈夫,在結婚之後,她發現這丈夫還算不錯,使她避免了吞食後悔這劑最苦的藥。後來她又有了小琳琅,小琳琅每日隨她在她那個學校生活,這使得她的生活更易於脫離冥想而更接近於實際,因而使得她的心境更易於趨向平衡。開頭,她和侯銳一樣,為沒有自己的家而深深地煩惱,後來,她被這曠日持久的事態也弄得麻木了。她曾勸說過侯銳,就在公社安個家算了,但是不用侯銳跟她講,她自己也漸漸看出這樣的人情世故:她所在的公社裡的那些人,即使不說是全部吧,也有百分之八十以上,在他們眼中,侯銳夫婦沒有很快地把自己的工作調回城裡,是一件很古怪的事,「你那小叔子他岳父不是什麼什麼嗎?他給你們說句話還不結了?」似乎這應該是一條顛撲不破的真理!到了這二年,縣教育局乾脆確定了這樣的精神:夫婦均在本縣教學的,可以優先照顧其中一名調往城內,門路可以自找。既然如此,白樹芬也就不再跟侯銳提在農村安家的事,並且,也就更積極地參加到嚮往立體交叉橋的行列中來。只要一開始為立體交叉橋拆遷,他們夫妻孩子就可以在城裡有一個窩了,那時她盡可以讓侯銳先調回城來,家中有了足夠的空間,小琳琅也便可以留給奶奶看管,到了上學年齡也能在城裡入學,受到較好的教育。
白樹芬雖然準備著離開那個半山區的農村中學,卻認認真真地努力上好每一堂物理課。她還擔任著班主任,這是一項開掘學生心底寶藏的工作。學生們從她口中很少聽到那種枯燥的大道理,但她那種和善的態度,親切的眼光,特別是從微小處作起,給人以關懷、幫助的行動,使她贏得了學生們的愛戴。一個雪花飄飛的冬日,她發現孫鎖柱放學後還蜷縮在教室的火牆邊,便問他為什麼不回家,孩子抬起一雙哀傷的眼睛,沒有吭聲。白樹芬想起他爹剛娶了後娘,把他打發到土坯房去睡了涼炕。白樹芬心裡一酸,跑回宿舍,從自己床上抽下一床舊褥子,給了孫鎖柱,孫鎖柱用一雙破裂的手接了過去。白樹芬背過臉去,不知為什麼,心頭上浮現出了立體交叉橋的圖像,久久沒有消失……
都說當嫂子的容易同小叔子處好關係,而最難同小姑子相處;白樹芬恰恰相反,她同侯瑩的關係是非常融洽的。回到家中,她常攬著侯瑩的肩膀,而侯瑩也常挽著她的胳臂,說許多知心的話……她同侯勇的關係卻相當緊張,她驚異于侯勇的心如同花崗岩般緊硬冷酷,而侯勇也打心眼裡看不慣白樹芬那種清高的氣派。不過,由於侯勇畢竟不在北京工作,白樹芬在他出差來京時又儘量避免回城,他們碰上的時候不多,因而也還未曾衝突過。
誰想到,在這天晚上,叔嫂之間終於衝突起來了。
十九
「小勇,你什麼時候回來?」
當侯勇抬腳就要出門時,白樹芬叫住了他,問出這麼句話來。
白樹芬這話問得有理,事關這晚上一家人的睡法,這晚上還不算人丁最盛的,因為侯瑩要去上夜班,只有三男二女,但這三男三女之間存在著兩層理應互相回避的關係:公媳之間,叔嫂之間;而兩層關係中的核心人物正是白樹芬。白樹芬帶著小琳琅一到家,聽到了侯勇也已回來的消息,心理就開始盤算當晚的睡法了。當然只好採取「合併同類項」的方法。因為裡屋床位比較充裕,所以男性成員自然應佔有裡屋,而她和婆婆、小琳琅則合睡在外屋的大床之上;他們進了裡屋以後,把中間的門反扣上,外屋的三位婦女才好脫衣入睡,這方案本是切實可行的。但現在侯勇宣佈他要出去,現在已八點多鐘,按他外出的慣例,在外頭總要耗兩三個小時以上,因此,他很可能要十一點左右才回來,這樣,三位婦女要麼得等他回來才好入睡;要麼就得作出這樣的決定:三位婦女睡裡屋,三位男子睡外屋。外屋只有一張大床,父子三人得橫著睡,把腳搭到拼過去的椅子上,那當然是很不舒服的。白樹芬叫住侯勇,就是希望他表個態,或表示不會太晚回來,或表示「你們女的睡裡頭吧!」
誰知白樹芬的這話一出口,猶如將一個火星濺到了侯勇心中的乾柴垛上,他正極端煩躁而無法排遣,經這句一激,頓時火冒三丈。
侯勇並沒有意識到嫂子這話的潛臺詞是「今晚怎麼個睡法」,他只覺得自己的尊嚴遭到了挑釁。在這個家裡,父親母親對他都是理順毛的態度,哥哥侯銳雖然敢於對他發怒,但發怒本身其實也是一種對他無可奈何的表現,至於侯瑩,那在他面前就連大氣也不敢出一口;只有這位嫂子,也不跟他頂,也不跟他吵,甚至說話口氣還滿客氣,但從她的眼神裡,從她嘴角淡淡的微笑(侯勇總覺得那是冷笑)上,侯勇深刻地感受到了嫂子對他的輕蔑,這個上過大學的嫂子知道他的不學無術,懂得象他這樣的「將門貴婿」實際上處境十分尷尬,也絲毫不懼怕他的驕橫無理。
侯勇把臉轉向白樹芬,惡狠狠地回答她:「你管得著我什麼時候回來嗎?」
白樹芬並不退讓,面上和顏悅色,語調也並不提高,但兩句話把他噎了回去:「你要是回你岳父那兒,我當然用不著管;你要是回這兒,咱們就得商量商量,晚上怎麼個睡法。」
白樹芬把問題挑明瞭,更惹得侯勇滿腔邪火。侯勇的自尊心受不了這個話。這話,意味著他雖攀上了住大屋子的高幹,但並不能在那家人佔據的空間中獲得一個心安理得的位置;這話,也意味著在這個小小的空間裡,他畢竟不是一個可以隨心所欲的霸主,他還得接受別人同他商量!
「你愛睡哪兒睡哪兒,我管不著!我愛什麼時候回來什麼時候回來,愛在哪兒睡在哪兒睡,你也管不著!」侯勇氣得渾身哆嗦,嚷了起來。
屋子裡其餘的四個人頓時亂了起來。小琳琅被嚇得「哇」的一聲哭了;侯銳簡直是從椅子上跳了起來,瞪著弟弟,張嘴想喝斥他,一時又不知該喝斥什麼;侯勤豐心驚肉跳地望著劍拔弩張的叔嫂二位,沒了主意;當母親的急得連連自語:「這是怎麼說的,這是怎麼說的……」
白樹芬卻一點也不慌張,她甚至也並不生氣,依舊語氣和藹地說:「既然咱們是一家人,同在一個屋頂底下生活,那就不能誰也不管誰,遇上事兒就得一塊兒商量。」
白樹芬越冷靜,侯勇便越蠻橫,他滿臉肌肉亂抖,不管不顧地說;「什麼一家人!這兒不是你的家,你給我走!」
侯勇話音沒落,侯銳已經沖到了他面前,借著酒勁就扇了他一記耳光,侯勇豈能甘休,當即就揪住了侯銳的脖頸;父親趕忙過去攔在兄弟之間,急出了一身汗來;母親心內只埋怨媳婦不該惹是生非,她不由得跺著腳,白了白樹芬一眼,朝那擁成一團的父子三人歎一口氣;小琳琅嚇得撲到白樹芬身上,摟著她的腰,哭得更加響亮;白樹芬見事已至此,越發感到沒必要懼讓,她略微抬高嗓門,但語調並不潑辣地一字一板地反駁說:「我走不著!告訴你,我是明媒正娶來的,我戶口在這兒,這兒就是我的家,我在這個家裡呆著名正言順,誰也別想排擠我!」
一家人正鬧著,錢大爺掀簾進了屋,一進屋便揚著嗓門勸解:「嘿,這是怎麼了?一家人什麼話不能好好說?快別動火,快別動火!」他進屋前已經聽出了屋裡在爭吵,聽見別人家鬧糾紛,他就勃發出一種管閒事的熱情,此刻他目睹著憤怒、惶急、尷尬、羞慚、冷峻和幾張面孔,這種熱情達於極點,他先把侯勤豐連扶帶拉地歸到座位上,又把侯銳連拉帶拽地推到床邊坐下,又請當母親的坐到籐椅上消氣,嘴裡還一邊叨念著許多誰也聽不清也用不著聽清的話語;但是,當他想繼續安頓侯勇和白樹芬時,侯勇已經恨恨地說了句;「哼,咱們回來再說!」一跺腳,掀門簾走了,而白樹芬的反應也極為靈敏,她揚起嗓門,故意用一種客氣到極點的語調,把話送到門簾之外:「對蠻不講理的人,我一句話也不再說!」
侯勇以這種姿態出了門,弄得侯勤豐心裡好不是滋味,酒和帶魚都從胃裡翻到了嗓子眼。他又急又氣又羞又怕,他的生活準則就是維繫小康之樂,他願意一家人團團圓圓、和和美美,他最怕家醜外揚,尤其不願將家醜顯露在錢大爺這種他認為比自己低下的人面前;他怕侯勇一腔邪火跑出去鬧亂子,更怕侯勇很晚回來還要在這個家裡繼續爭吵;但一時之間他又判斷不出是非。媳婦似乎也沒有什麼錯處,她為一家人能睡好,問一聲小叔子本無可厚非;侯勇忙著出去,被叫住自然不痛快,說幾句氣話也算不了什麼大事;侯銳見弟弟這麼不尊重嫂子,兼以又喝了酒,借著酒勁打了弟弟一下,打得並不重,好象也可原諒……一家人都是好人,都無大惡,但竟鬧成了這個樣兒,究竟是怎麼搞的啊?他那麼愣了幾秒鐘,突然,一種本能促使他站了起來,錢大爺不及勸阻,他已快步出得門去,他是去追侯勇。他急中生智,想追上侯勇,告訴他:「我一會兒就回郵電所睡去,我替老張去值夜班,讓他回家去;我不算跟他換班,下次輪著我,我還值班,他准樂意……家裡讓老大三口和你媽都睡裡屋,外屋給你一個人留著,你可千萬別再生氣,別再吵鬧!……」
以自身的忍讓,換取全家的和睦,這便是侯勤豐的治家之道,這一回他又打算這麼辦。
但是,他一直追到胡同口,也沒見著侯勇的影子,一陣晚風吹來,他的醉眼模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