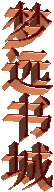
生命通道 第四章
事實上並沒等到半個月,蘇原便離開了萊陽城。不是逃走,而是跟隨北野的部隊向昆崳山區掃蕩。北野將與山本在海陽城北一個叫現石的地方會師,然後東犯。這是日軍繼秋季清鄉又一次重大軍事行動。同時也是一次強弩之末的軍事行動。
時令已入初冬,中國黃河以北大半個版圖已開始降雪。寒流漸次南侵,整個中原地區朔風凜冽,枯草瑟瑟。然而戰爭並未因季節之冷而冷,反而因臨近終了而變得如火如荼。中國軍隊與日軍在湘、桂、黔、豫、鄂諸區域的所謂「大陸決戰」正激烈地進行。日軍為扭轉必敗之局做殊死的「最後攻擊」,以進為退,爭取主動。十月下旬,幾路敵軍合圍桂林、柳州,十一月初兩城相繼攻陷。此後,日軍繼續冒險西進,占取桂林外圍龍勝、融縣、南寧,又攻陷金城江、河池、南丹、六寨,直取貴州大門。其時,敵輕裝部隊一直向北追擊,再占三合城、川寨、獨山。至此中國軍隊開始反擊,湯恩伯兵團從河南一路步行入黔,到達黔南前線,另一有力部隊由美國航空隊趕運抵黔增援,在八寨與敵軍交火。一夜之間戰局驟變,敵人迅速向南退卻,中國軍隊尾後追擊,先後克復三合、獨山、荔波、六寨、南丹。迄月底,黔桂線戰局送穩定。黔桂戰事之轉折趨向可視為當時整個中日戰局之縮影。
出城後蘇原不由回首一瞥。那瞬間他有一種預感:今生今世不會再回到這座小城了。他的回首自不是出於對小城的留戀,那裡沒有值得他留戀的東西。恰恰相反,往日的一切都不堪回首,那是他的牢獄,那裡斷送了他的一切。那最後的一瞥只是他無言的詛咒。
天空陰晦。寒風掃掠著空曠荒蕪的原野。樹木的葉子已經落光,站在那裡如同一些赤裸的漢子,在冷風裡簌簌發抖。途經的河流大都乾枯,映入眼簾的是狀如絲帶的白亮河沙,風吹塵起,逶迤奔騰,流水一般。蘇原油然記起老馬所說他去的那個河裡流淌白沙的「怪地場」,他的心不由一沉,他覺得此刻的。自己正在步老馬的後塵踏進那個「怪地場」,只是老馬已原路折回,自己卻怕要一直往前走下去。如果無法脫身,也許會一直走到「死地」。
十天以前,他已將敵人這次行動的情報放在那個秘密樹洞裡,他相信抗日隊伍會接到並已採取了相對措施。北野要他隨部隊行動,其目的已不同往前,這次是把他當作弈棋的對手,以便在戰事的間隙隨時對弈一局。自從與蘇原對弈過,北野便對原來的對手龜田失去了興趣。但因北野未占蘇原的上風,因此耿耿於懷。
因為老馬的緣故,高田藉故留在城裡。臨走前高田關照他可利用這次機會脫離日軍,如果逃脫不成也無妨,待回城後再從長計較。儘管高田沒有明說,可他看出高田捨不得自己離去,希望能為「生命通道」計劃再度合作。蘇原心裡也很矛盾。
北野的部隊疾速東進。中午時分經過一個小村,村人已望風而逃,村裡村外空空蕩蕩。北野下令在這裡埋鍋造飯。飯後又繼續東進。道路漸漸向上傾斜,進入兩縣交界的丘陵地帶。為防備抗日隊伍的伏擊,隊伍的行進速度減緩。當再次途經一個村莊,天色向晚,部隊不敢貿然前進,決定在村子宿營。是夜,無戰事。如果說有,那便是北野和蘇原的方格之戰。第二天天亮部隊繼續行進。這時已踏進海陽地界,地形漸現陡峭。中午,部隊經過一個狀若蚌殼的谷地,四周是一圈山丘。騎在馬上的北野神情惶惶,有一種不詳的預感。果然當他的軍隊完全進入谷地,四面山頭便驟然響起槍聲。
這場後來被載入縣誌的谷地伏擊戰由此拉開序幕。
幾乎與此同時,另一支抗日隊伍對山本部隊的伏擊亦在十裡之外的楊莊展開。
戰鬥打響之後,驚慌失措的日本兵和偽軍各自尋找隱蔽物臥倒。蘇原卻出奇地冷靜。他仍然站在原地,像個局外人,眼睛顧視著前面不斷閃著亮火的山地,直到有一個上歲數的偽軍向他大喝一聲「臥倒!」他才下意識地蹲下身子。這時他感到有一股強烈而灼熱的氣流從頭上呼嘯而過,緊接身後不遠的泥地飛起一串土花。
他仍然沒有驚慌,只是向那個吆他的上歲數偽軍靠過去,臥倒在他的身旁。前面的隱蔽物只是一塊隆起的山岩,不時會聽到子彈擊中的砰砰聲。
這是一塊十分狹窄的谷地,長不過二裡,寬不過一裡,儼然是一個「口袋」。抗日隊伍選中的是一塊極佳的伏擊地,居高臨下的射擊使未及散開的敵軍傷亡慘重。北野的坐騎被槍彈擊中斃命,他被龜田少尉和其他幾名軍曹掩護到谷地中間的一處凹地裡,趴在地上用望遠鏡向周圍的高地觀察。對於一個征戰已久的高級軍官,他清楚自己已陷入在劫難逃之境地。
日偽軍開始還擊,這是條件反射般的盲目射擊,造不成任何殺傷力。但無意中卻產生出另一種效果,射擊的煙塵彌漫,谷地地勢低窪,又沒有風,煙塵無法消散,便形成一種天然屏障。抗日隊伍從山上看不清具體目標,殺傷力大大減弱。而谷地裡的日、偽軍在煙塵的掩護下,很快恢復起建制,各中隊長指揮各自所屬部隊投入戰鬥,重機槍和擲彈筒猛烈向山上射擊。
這裡不是戀戰之地,必須儘早突圍出去。戰鬥僵持了一段時間,北野已選中了一個突圍口,在谷地東南,兩座山丘之間有一個百余米寬的豁口,由強大火力掩護從這裡突圍會有成功的可能。北野做了突圍的部署,但沒等下令,抗日隊伍便發起對谷地的合圍進攻,數不清的抗日戰士從四面的山頭上向下衝鋒,槍聲和喊聲連成一片。
谷地裡的日、偽軍拼命抵抗,各種火力一齊向沖過來的抗日戰士掃射。暴露在開闊地上的抗日戰士不斷有人倒地。日本兵的擲彈筒也發揮了威力,炮彈在抗日戰士頭上炸開,造成很大傷亡。這對抗日隊伍離谷地邊沿大約有二百米距離,合圍基本完成,為避免過重傷亡,暫時停止衝鋒,利用谷地四周的有利地形,對谷地形成了鉗制之勢。
蘇原仍然臥在那個上歲數的偽軍身旁。整個戰鬥過程都收入他的眼底。儘管他不具有軍事眼光,但也看出北野的部隊已陷入了「死地」。他想這是自己脫離敵營最後的時刻了。當敵人被殲滅之後,他會在抗日隊伍中間找到老胡。老胡會將自己帶到他的上級面前,向上級報告他就是送出情報的蘇原醫生。上級會握著他的手再三對他道謝。那時他會如釋重負地長噓一口氣。他知道只要找到了老胡,後面的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
隨著抗日隊伍射向谷地的火力不斷加強,谷地上的情勢愈來愈混亂嚴峻,偽軍們並不積極參戰,只是應付,舉槍朝半空胡亂射擊,隨時做好或逃或降的準備。日本人見狀惡語咒駡,甚至以槍口相對。他們也知道關鍵時刻指望不上偽軍,只得靠自己作戰。他們一邊射擊,一邊修築臨時掩體。軍醫隊的軍醫和衛生兵在谷地中央設置了臨時救護所,將受傷的日本兵抬過去包紮,敷藥。重傷號疼得哭天號地,軍醫便往他們嘴裡塞滿紗布。一戰地執行軍官,陰沉著臉走來走去,對那些奄奄一息的傷兵補槍殺死。忽然一匹中彈的白馬在谷地裡瘋狂奔騰,嘶叫不已,見人便踏便踢便咬,幾次沖到北野面前。龜田少尉端衝鋒槍向馬頭一陣猛射,直到那馬倒地斃命為止。
為儘早實施突圍,北野重新部署了據守谷地的兵力,並變換戰術。他命令森日中隊長帶領一支衝鋒隊搶佔谷地北面的山匠。這座山丘只有一百多米高,樹木茂盛,這將給攻擊帶來便利。如果能搶佔成功,陷入谷地的日軍便可以此為依託向北突圍出去。
森日中隊長帶領他的衝鋒隊躍出谷地,貓著腰邊射擊邊穿越谷地與山丘間的開闊地帶。這是一個死亡地帶,然而卻並未遭到抗日隊伍的抗擊,似乎抗日戰士突然從陣地上消失。森日有些意外,腳步下意識地一停,突然迎面飛來一顆槍彈射中他的胸膛。森日倒下的瞬間一排手榴彈落在衝鋒隊中間,爆炸開來,衝鋒隊頓時死傷過半,搶佔計劃告吹。剩下的日軍趕緊拖起同伴的屍體縮回谷地裡。
當北野正欲再次組織衝鋒時,一陣激烈槍聲從谷地東南方向傳來,谷地裡的日軍頓時慌張起來,一齊向槍響方向張望,終於看清,是一夥被追擊的日軍倉倉皇皇從豁口處向谷地擁來。槍聲是豁口兩邊山頭上抗日隊伍的密集射擊。谷地裡的日軍見是「自己人」連忙接應,將火力掉向東南,總算使那夥逃竄過來的日軍進入了谷地。
豁口處的空地上留下一具具麥個子似的屍體。
這是山本部隊在楊莊被抗日隊伍打散的一支殘部,不到三十個人。他們沒想到費九牛二虎之力突圍出去卻又鑽進新的包圍圈,可謂在劫難逃。他們個個垂頭喪氣,一臉的晦氣。
蘇原仍臥在原處,聽見那邊的動靜回頭不經意地一瞥。他沒看清什麼,卻聞到從那邊飄過來的一股腥臭氣味兒,就是當地雞蛋黃花發出的那種惡劣的氣味兒。他打了一個寒戰,再次轉回臉時,看見了八木那張又白又胖的臉,還有八木手下另外幾個軍醫。白衣殺手。蘇原只覺得一股血沖上頭頂,耳朵嗡嗡叫,爾後,那股股臭味兒愈來愈濃烈地挾裹著他。他出現了噁心嘔吐的症狀,神智也變得迷離。這時他的思維十分簡單,心中唯一所想便是實現一個誓願:不能讓這夥白衣殺手活著出去。他知道這個誓願不是出自眼前,他和高田埋葬那個青年農民時這誓願已萌生於心。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不到,眼下就到了他們遭受報應的時候。他這麼執著而迷離地想著,可對自己當前究竟該做些什麼卻模糊不清,只隱隱約約覺得手裡該有一支槍。
雙方的對射沒有一刻間歇,煙塵從谷地緩緩向四外彌漫過去。當煙塵淹沒了抗日隊伍的陣地時,抗日隊伍便開始又一輪衝鋒。匍匐於谷地邊沿的日、偽軍只能朝煙塵裡盲目射擊,直到抗日戰士沖到離谷地不遠顯露出身影來,日、偽軍的射擊才恢復了殺傷力。戰鬥就變得異常激烈,攻與守都同樣殊死不怠。只是愈接近谷地,地面愈平坦,抗日隊伍暴露得愈嚴重。每前進一步都要付出高昂代價。
蘇原在身後揀到一支槍,是一個被打死的偽軍丟棄的,那偽軍很年輕,仰面躺在地上,他的頭部被擊中,血染紅了他那張娃娃臉。蘇原只看了一眼便趕緊將槍撿到手。他這是頭一次觸摸槍支,間一個感覺是槍的分量很重。
他回到那個上歲數偽軍的身旁重新臥下,觀察那偽軍怎樣射擊。看了一會兒覺得很簡單,他沒想到可以將人致於死地的可怕事情做起來竟如此簡單。
那上歲數偽軍停止射擊,側頭向他看看,臉上露出詫異神色。
「小老弟,臨秋末晚了還撈家什幹啥呢?」上歲數偽軍說。
蘇原不吭聲。
「傻瓜,快把槍扔了!」上歲數偽軍說。
蘇原仍然不吭聲。
上歲數偽軍歎息一聲,然後又開始射擊。
蘇原這時才發現他射擊時將槍口仰得很高很高。
天漸漸黑下去了,射擊的火花劃破昏暗的天幕顯得怪異而猙獰。
這是北野等候已久的時刻。
谷地裡的局勢已愈來愈嚴重,抗日戰士已可以將手榴彈投進谷地。日、偽軍傷亡慘重,不得不向中間收縮。擲彈筒已失去了效力,幾挺重機槍成十字狀擺在新挖掘的掩體內,不斷向四下吐著火舌。
北野開始佈置新的突圍。這是一個新的突圍計劃,利用夜幕的掩護,從東北方向的豁口處向外突。北野將全部偽軍和部分日軍組成掩護隊,他自己和其他軍官們由余部日軍保衛組成突圍隊。
北野竟然沒有忘記蘇原,他找人尋到他,將他叫到跟前。暮色中,蘇原眼裡的北野像一隻蒼老的狼。
北野見蘇原手中提著一支槍,先怔了一下,卻也沒說什麼。他看了一眼站在身旁替補蔔乃堂的黃翻譯官,便開始對蘇原說話。黃曾擔任山古隊長的翻譯,蘇原和他稍有接觸,知他的日語水平很一般。
北野說:「蘇原君,現在不是敘談的時候,這你知道的,可我得告訴你,又到了該你做出選擇的時候了。」
這話由黃翻譯官多餘地翻譯出來。
如果在以前,北野這句話又會嚇得蘇原心驚膽顫了,可這遭他十分的平靜。只是定定地盯著北野。
「你說吧。」他說。
「跟我突圍?還是將你留下來?這由你來決定。」北野說。
蘇原的眼前出現了八木女人模樣的臉。
「軍醫隊的人一起突圍嗎?」蘇原問。
「留幾個衛生兵,其餘的一塊走。」北野說。
「山本部隊的……八木隊長?」蘇原似不放心,又問。
「他是佐官,當然走。」
「那我也走。」
「這是好主意,留下落到抗日隊伍手裡可是要倒楣的。」北野說。
蘇原在心裡罵了北野一句。
「要是能活著出去,我非和你好好棄一局不可,死了,咱們就在陰間裡從從容容地奔,爭個高低輸贏……」事到這般天地,北野竟還想來點小幽默。
只是蘇原沒響應。
天已完全黑下來,西天最後一抹晚霞早褪盡顏色,鉛色的天幕不時被戰火耀亮。夜風已起,從山口向谷地刮來,陰森森的。
戰鬥仍在僵持,這時蘇原突然明白:日軍所以能支撐下去,主要靠那幾挺重機槍的火力。他有些擔心,如果再拖下去,北野和八木他們很可能會逃之夭夭。
突圍隊已集中起來,聚攏在北野身邊。雖然看不清這些人的面孔,可蘇原憑那股腥臭氣味兒知道八木和他的手下軍醫俱在。由於離得很近,這氣味更為濃烈,蘇原有一種要被窒息的感覺。他心裡一直都疑惑不解,八木身上的氣味究竟是真實存在還僅是自己的一種感覺?反正二者必居其一。但此刻他的思維已難於進行更深入的分析,他覺得頭很脹疼,有一種昏昏欲睡的感覺,他唯一清晰的一點是,哪怕天再黑,憑自己的嗅覺會像獵犬那般跟緊八木的……
突圍隊無聲無息轉移到谷地東南與豁口相對的陣地前。
北野的突圍計劃簡單而狡詐:他要率部像蛇樣偷偷摸摸從豁口開闊地上「滑」過去。
這是一個醞釀陰謀的時刻。
突圍隊開始行動,幾十個人匍匐著爬出谷地,那情景確像一條蛇小心翼翼地向前滑行。且很快便脫離了谷地。開闊地生長著茂盛的麥苗,像一條軟氈鋪向前方,隊伍在上面爬行省力而無聲。這是一個陰晦之夜,天上無星無月,天地間混沌一團,前面兩座山丘的半腰不時有火光閃爍,那是射向谷地的火力,短促的光亮時時將山丘的輪廓顯示,同時也威脅著向前運動的突圍隊,只要稍稍出現意外,後果將不可想像,可謂是千鈞一髮。蘇原亦爬行在這支隊伍中間,他警惕地嗅著那股惡劣的氣味兒,以便弄清八木他們在隊伍中所處的位置。他暗暗地「咬」緊。但那氣味給他的頭腦帶來很大的損傷,他只能進行一種單向思維,那就是跟緊八木,不能讓他逃走。而對於自己究竟將有怎樣一番作為,仍然模糊一團。這時突圍隊已離開谷地很遠,漸漸靠近抗日隊伍佔據的兩座山丘。蘇原兩眼向前尋覓,他想看清到山丘還有多少距離。他忽然覺得面前的空間一下子變了模樣,十分怪異,作為一個外科醫生,他不難認出這是一個寬闊巨大的胸腔,他似乎覺得自己曾到過這裡,但又記不清晰。他感到驚異,感到迷離。這瞬間他好像又記起了高田,記起了老馬,還有他的妻子單青,但一切又是那麼遙遠,如同隔世。就像那些人和自己只有一面之識。胸腔裡漸漸明亮起來,又像上次那樣出現雷電天氣,一道道耀眼的弧光照亮前面的景象,那巨如山峰的心、肺清晰地矗立,他看得見巨心在有節律地搏動,看得見巨肺在不停地收縮擴張。這是一幅生命蓬勃壯闊的景象。他難以抑制心中的激動,慢慢將視線壓低,眼前又出現另一種景象,他看見一條寬闊平坦的道路從這些巨心巨肺中間穿越過去,一直通向那迷茫的遠方。他冷丁覺悟:這就是他和高田軍醫尋找到的那條生命通道,人只要從這裡走出去便會得以複生。這是一條神奇之路,是一條鋪滿光明的路。他突發奇想:假若在這條道路設下關卡,在這裡將行人盤查,讓好人通過,將壞人阻攔,善善惡惡都各得其所。這時他的眼光有些癡迷,他好像看見有一個人站在那座心山下面,向他張望,那人高高瘦瘦,脖子很長,啊,是老胡!他疑惑無比,老胡怎麼會在這兒呢?莫非老胡已在這設下了關卡,一定是這樣的,謝天謝地,老胡竟與自己不謀而合,他興奮異常,失聲高呼一聲:老胡——
應著他的呼叫,是一陣炒豆般的強烈槍聲……
第二天天亮,抗日隊伍打掃戰場。漸升的太陽驅散了彌漫於谷地上空的霧氣,顯現出這塊彈丸之地經歷過戰事之後的悲涼。屍陳遍野,草木焦枯,幾叢燒著的灌木還在冒著餘煙,空氣中飄散著一股令人窒息的怪異味兒。
抗日戰士有條不紊地在清查並掩埋日、偽軍屍體。一個抗日戰士在兩座山丘間的開闊地上發現了仍還活著的蘇原。他的前胸和後背都有槍傷,全身的血幾乎流盡,臉色蒼白如紙。于彌留之際,他的神智尚清醒。他央那個發現他的抗日戰士幫他找一個人。抗日戰士問找誰,他說我老胡。抗日戰士問老胡是誰,他說老胡是抗日隊伍的敵工。抗日戰士想了半天,最後告訴他這支隊伍裡沒人姓胡,自然就不會有個姓胡的敵工。蘇原不信,說老胡是他的聯絡人,怎會沒有?他說他要見見部隊上的長官。那個抗日戰士儘管心裡很不情願,但還是找來了他們的連長。那位連長聽完蘇原的要求再次向他證實:這支隊伍裡確實沒有一位姓胡的敵工。他說假如那人真是敵工的話,那他對外使用的便不會是真名真姓,是化名。化名便無定規,今天姓李,明天也可以姓王。蘇原聽了張嘴說不出話來。不過那位連長還是個很厚道的人,不想撒手不管。他問蘇原那位自稱姓胡的敵工長一副什麼模樣,蘇原就一五一十地向他做了描述。這時站在連長身旁的一位抗日戰士插言道:聽他說的這情況倒與情報處的黃科長很相似。連長聽了亦表示贊許,遂讓那個戰士立即去連部打電話與情報處的黃科長聯繫。那抗日戰士飛奔而去。連長又喊來了連裡的衛生員為蘇原包紮。不久,去打電話的抗日戰士又跑步回來,說那位姓黃的科長接了電話。連長問黃科長可有話說?抗日戰士說那部從日本人手裡繳獲的電話噪音很大,耳機裡像在刮十級大風。可黃科長最後那句話還是聽清了。他說他聯繫的人中沒有一個姓蘇的醫生……此時蘇原已氣力不支,張口無聲,只對著那位連長久久瞪著眼。
太陽從兩座山丘間升高時,蘇原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