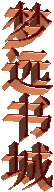
生命通道 生命通道
——抗日戰爭勝利半世紀祭
第一章
戰爭至一九四二年下半年始見到曙光。日軍在中途島、瓜島和所羅門群島連連失利;中國戰場,中國軍隊繼浙贛戰役大捷,緊接又取得第三次長沙會戰的勝利,斃敵五萬六千餘。這次大戰是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首次大慘敗,致使日軍自開戰起一直保持的海陸空優勢宣告消失,從而轉入防禦。第二年年初,日軍又有數個師團在華南戰場被殲。日本內閣首相東條英機在國會驚呼:「局勢嚴重,需要吾人做最大之努力,本年可謂決戰之年。」然而語出不久,日軍又在鄂西、常德二戰場失敗,八萬餘兵員戰死。是年,美軍在新幾內亞、所羅門群島等地轉入反攻,步步逼近日本本土,海上交通被切斷,使南洋一帶近五十萬「南方軍」陷入孤立無援之境。為此,日軍大本營意識到在中國大陸打開一條與南方軍的通道刻不容緩,於是要求中國派遣軍抽調五個師團轉用於太平洋方面,支援南方軍;另以五個師團就地集結,作為日軍大本營總預備兵力。然而由於戰爭形勢的不斷變化,至年底,日軍扼守連接千島群島、小笠原、巽地和緬甸這一環形所謂「絕對國防圈」未取得成功,防線出現嚴重薄弱,於是又下令中國派遣軍自一九四四年春從華北、武漢、廣東分別開始進攻作戰,擊破國民黨中央軍,先行佔領黃河以南、京漢鐵路南段以及湘桂、粵漢兩鐵路沿線重要地區。這便是有名的被秘密稱為「一號作戰」的軍事方案。為確保其「一號作戰」的有效實施,日軍大本營決定,給中國派遣軍增加兵力,除可以重新使用預定調出的那五個師團外,又於一月至三月間下令新編十一個獨立步兵旅團。其中兩個旅團在日本本上編成,八個旅團在中國關內的滋陽、正定、汾陽、濟南、宜昌、南京、安慶、陽泉編成,另一個則在關外鐵嶺編成。日軍大本營命令。在日本本土編成的第八、第九旅團以及在鐵嶺編成的第十一旅團必須於四月底五月初抵達指定地點,並立即投入作戰行動。
四月中旬某天,由北野俊太郎率領的第十一旅團先遣隊從遼寧半島橫渡渤海。由於船隻原因,大部隊在海邊紮營候渡。按通常的原則,旅團司令應與大部隊一起行動,但北野少將行前對彼岸戰場形勢做了深入研究,認為先遣隊登岸後凶吉叵測,便執意隨先遣隊一起行動,以應付事變。
那是一個晴朗的白天,蔚藍的天空與蔚藍的海面在前方連成一片。季節已是春日,海風尚透著寒冷。被臨時徵用的「九州九」貨船在海面平穩航行,高懸桅端的太陽旗在風中呼啦啦飄揚。這是一個愜意的時刻,兵士們在甲板上各行其事,盡情歡娛,時而響起悠揚的歌調,時而又響起為比賽摔跤助威的呐喊;北野旅團長則與幾名軍官站在船舷射擊繞船飛翔的海鳥,迎著槍響,一隻只海鳥墜於波浪之間,然後衣物狀向船尾漂浮,直至消失於視線之外,而另一批饑餓的海鳥則不知死活地前撲後繼,於是又贏來新一輪槍響。這次軍事調動以一種海上旅遊的方式進行,無論對於最高長官還是普通士兵懼感到十分振奮,如同進入忘我境界。直至望見前方一抹黑色的地線,方意識到又逼近廝殺不已的戰場,心情頓時黯然。
先遣隊在一個叫龍口的碼頭登上陸地。曾考慮「九州九」是一條非武裝貨船,在有一個大隊日軍駐守的煙臺上岸比較安全。但北野研究過的情報中特別強調煙臺至鐵路線間的萊陽、海陽一帶有民兵遊擊隊佈設的範圍遼闊的地雷區,不易通過,於是不得已改在龍口。按照預定計劃,先遣隊登陸後不在此等候,獨自向半島腹地深入,線路是經招遠、平度、昌邑直達濰縣,在濰縣等候大部隊的到來,然後乘上火車西行南下。從總體上說,這道寬闊的走廊屬日軍控制範圍,尚為安全。
部隊在龍口宿營,稍事休整,第二天一早出發西行。
渤海連接著兩塊地面,同時又連接著兩個季節:那邊冬的寒氣尚未褪盡,這邊田地裡的麥子已接近黃熟,熱浪陣陣,老百姓光著膀子在地裡幹活;北野的部下還穿著厚重的棉衣,撲身而來的燥熱與潮濕使人人感到不適,得病般頭暈、噁心、渾身乏力,步履艱難。如此捱過一日,第二天卻又是另一副光景:陰雲密布,不久大雨滂淪,兵士們棉衣濕透,負重如裹鐵甲,在雨水中蹣跚行走,狀如蒙人之舞蹈。爾後又雷電交加,聲色俱厲於天地之間,忽而如當頂降落,忽而又如從一方橫掃而過,驚人心魄。又捱過一日。再一天又換個晴日。雨後之日格外紅豔,懸在頭頂一個勁兒向下烤曬,地面蒸騰起一片黃濁霧氣,霧氣中散出一股熏人的惡臭,令人窒息,如同置身於一片無邊無際的墳場,北野的兵士倍受煎熬。偏偏禍不單行,許多人又染上了一種莫名其妙的足疾,如同被哪樣毒蟲叮咬般紅腫,疼癢交加、行軍時苦不堪言。軍醫們加緊診治,卻因不明病因難以下藥,一籌莫展。北野本人倒平安無事,但作為肩負使命的最高長官,騎在馬上望著如螻蟻之動的隊伍,一腔怒火無從發洩,只將眉頭鎖緊。
這天天黑,隊伍在一座村子宿營。北野的司令部占了村中的一座祠堂。祠堂有一個很大的院落,一株古柏挺立在院子正中,鬱鬱蔥蔥。這時晚霞已快褪盡,天空一片灰暗,成群的烏鴉在這灰暗中穿梭飛翔,發出「哇哇」的淒厲鳴叫。
開過晚飯,北野叫人傳來軍醫隊長高田中尉,又叫來翻譯官卜乃堂。這二人一起站在燈光下,反差甚大。高田軍醫三十四五模樣,身材適中,面皮白淨,蔔乃堂卻生得高高大大、濃眉大眼。一個似書生,一個似武夫。其實蔔乃堂也念過大書,雖也是三十幾歲,經歷卻甚為複雜。
北野先問高田軍醫足疾是否還在繼續蔓延。
高田軍醫答說是。北野面呈怒色,叱斥說:「帝國軍人自應各盡本分,兵士打仗殺人,軍醫治病救人,天經地義,可你們對區區小疾卻束手無策,成何道理?」
高田軍醫無言以對。
北野又轉向蔔乃堂說:「卜,你是中國人,難道就沒見識過這般害人疾病?」
蔔乃堂搖搖頭,說:「中國有句話叫解鈴還須系鈴人,在這方水土上患病,怕只有這方水土上的醫生才能醫治。」
北野似有領悟,說:「你的意思是找本地醫生給大日本軍人診治?」
蔔乃堂點點頭說:「是。」
北野想了想,說:「蔔你去找一個中國良民來。」
蔔乃堂應聲走出祠堂,不一會兒帶著一個五十幾歲的村人進來。北野便開始盤問,蔔乃堂在中間翻譯。」
北野問:「這村裡有醫生沒有?」
村人說:「沒有。」
北野又問:「四下的村莊裡有醫生沒有?」
村人仍說:「沒有。」
北野勃然大怒,臉色極難看。站在他身旁的一個少尉軍官拔槍抵住村人的腦殼,一陣嘰裡哇啦。
卜乃堂翻譯說:「皇軍不相信你的話,沒醫生難道你們得了病就等死不成?皇軍說你不是良民,故意與皇軍作對。他說你今天不講出個醫生的下落,就斃了你!」
那村人嚇得渾身顫抖,說:「離這兒八裡的蘇家泊有一位老中醫,只是年歲大了,早就不出來看病了。」
北野問:「這是不是說謊?」
村人說:「全是實話。」
少尉這才收起槍,北野轉向高田軍醫和卜翻譯官下達命令:「立刻讓這人帶路趕往蘇家泊,將老中醫找到帶回。」
二人不敢怠慢,趕忙從軍中挑出一撥兒健壯兵士,匆匆鑽進黑沉沉的原野之中……
大約就在北野少將帶領部下登上「九州丸」那一時刻,蘇家泊老中醫蘇子熙咽下了最後一口氣,歸於黃泉。那個被北野審訊的村人並沒有說謊,蘇老中醫確已染恙多年,連本村人都極少見他那身著藍布長衫的瘦長身影。
大約也就在北野的軍隊在龍口登上了陸地的那刻,蘇老中醫的兒子蘇原帶著年輕的妻子回到蘇家泊。他回得遲了一步,探病變成了奔喪。蘇原是蘇老中醫唯一的兒子,在青島一所醫科大學的附屬醫院做外科主治醫。
在蘇原回到家之前,他的幾個姐姐姐夫已先他從各處趕來。另外還有一些本家親朋幫忙張羅,喪事正有條不紊地進行著。蘇老中醫七十而終,也算是壽終正寢,是喜喪,因此整個殯喪過程沒有過濃的悲哀氣氛,如同大家齊心合力安排老人做一次離家遠行。蘇老中醫躺在靈床上,十分安詳,只等著兒子回來為他入殮。只因未看老父生時一眼,蘇原內心很是悲痛。蘇原的妻子牟青是城裡女子,不諳鄉俗,蘇原只能一樣樣教她,比如怎樣叩頭,怎樣啼哭,以及如何與各等輩份的親朋敘禮。牟青是聰慧女子,凡事一點即明,無庸贅述。只一天過去,一切均做得恰如其分,贏得婆婆和眾多親朋的滿意。按照蘇老中醫生前的囑咐:戰亂年月,喪事一切從簡,不請吹鼓手吹打,不請僧人做功德,靈柩在家不可超過三日。蘇老中醫在世時,家人未曾違背過他的意願,臨終之言更是遵照不悻。於是便在蘇原回家的第二日將老中醫安葬于蘇家塋地。也就是在這一晚,日軍軍醫高田和翻譯官卜乃堂來到蘇家泊。
他們將蘇原和他的妻子從家裡帶走。
離開蘇家泊大約是晚上十點鐘光景,天上懸掛著半輪月亮,照得遠遠近近的山巒朦朦朧朧。夜風太冷,抑或還有驚嚇,蘇原的妻子牟青渾身簌簌發抖,蘇原脫下自己的外衣給妻子披上。在離家之前,蘇原曾強烈要求留下他的妻子,讓他一人跟他們去。但沒被容許。日本兵按慣常戰術兵分兩隊,蘇原和牟青被夾在兩隊中間,還有高田軍醫和卜翻譯官。一路上所有人都緘口不語,默默行走,只有腳步聲向四方傳遞。這條路蘇原從小到大走過無數次,可在這樣的深夜走還是頭一次,他感到心裡有一種隱隱的恐懼,為自己,更為妻子。
在遠遠望見日軍宿營的那個村子黑黝黝的輪廓時,忽然聽到了槍聲,開始很稀疏,轉瞬便密集起來,槍聲在靜夜裡顯得很尖厲、很刺耳。槍聲來自村裡,同時又看見爆炸的火光。這突如其來的情況使所有人都惶惶不安,隊伍停止了前進,在原地等待事態的明朗。大約過了一個時辰,槍聲停息下來,爆炸聲也不再有,唯見一兩處房屋在燃燒,火舌舔著陰冷的夜空。隊伍又開始前進,速度增加了許多,快到村子時,幾乎變成了跑步。
進了村,只見街上呈一派戰鬥過後的景象,被打死的日本兵橫七豎八地躺在地上還沒來得及收屍。受傷的在呻吟叫駡,醫務人員一邊包紮一邊指揮兵士抬往臨時救護所。著火的房子天燈般照耀著街上的情景,沒有人救火,也見不到一個老百姓的蹤影。
高田軍醫和卜翻譯官沒在街上耽擱,帶著蘇原夫妻急匆匆地趕到北野所在的祠堂,北野正在大發雷霆,斥駡幾名站得筆直的軍官,軍官們一面「哈依哈依」地接受訓斥,一面不失時機地推卸著自己的責任。蘇原讀大學時修過日語,他聽出的事體是:剛才的戰事是遭受從澤山上下來的一股抗日隊伍的夜襲。遊擊隊神不知鬼不覺地靠近了村子,先摸了村西的崗哨,然後沖進村,對正在睡覺的日本兵開火,亂打一通,等日軍清醒過來,遊擊隊已經撤走。日軍只在村口抓到兩名傷了下肢的遊擊戰士。日軍傷亡慘重。
北野揮手退下軍官,余怒未息。高日軍醫正在要向他報告蘇家泊之行,這時從外面急匆匆進來一名少尉軍官,向北野報告說抓到的兩名遊擊隊員已自殺身亡。北野愣了一下,說捆綁了怎能自殺?少尉說他們互相咬斷了手腕上的血管,崗哨在月光下發現從屋裡流出一道紅亮的溪流很是詫異,開門查看,這時倆人已死,少尉報告完,在場的人都不再說話,包括憤怒不已的北野。蘇原盡力保持平靜,做出什麼也沒聽懂的模樣,而心裡卻是十分驚駭。作為一個醫生,他清楚這種自殺方式是多麼驚心動魄而又不可思議,只有充滿視死如歸勇氣的人才能實施並達到目的。蘇原嗟歎不已。過了一會兒,高田軍醫開始報告蘇家泊之行,請示北野如何處置。北野目光不善地打量了這對中國夫妻一眼,說先關起來,天亮再說。
天亮後蘇原和牟青再次被帶到祠堂院裡,高田軍醫、卜翻譯官已在。北野的情緒仍很嚴峻,但打量他們的眼光已不像昨夜那麼兇狠了。他好像明白過來這一男一女不是他的俘虜,相反倒有求於他們。他問他們可用過早餐,卜乃堂翻譯給他們聽,蘇原回答他們夫妻沒有吃早餐的習慣。北野停了停隨之說昨晚的事你們都親眼目睹了,遊擊隊不宣而戰,向進入睡眠的皇軍進行襲擊,造成慘重傷亡,中國人不講戰爭規則,是有失文明的行為。蘇原聽著心裡憤然不已:真正不講規則有失文明的是你們這夥侵略軍,在中國,在朝鮮,在珍珠港,你們發動戰爭哪回是有宣而戰?看來北野很善談,還在滔滔不絕,說蘇原君你是中國人,中國醫生,你必須好好給皇軍將士治病,將功補過。蘇原這才明白北野大說中國人搞突然襲擊不講戰爭文明的目的,是要說服做為中國醫生的他只有乖乖地給日本軍人治療才是替中國人將功補過之舉,才符合他的所謂戰爭文明,真是沿天下之大稽的強盜邏輯。蘇原早已成竹在胸,決不給這夥強盜醫治。他說治病救人是醫生的職責,問題只在醫術是否高明。我雖然讀過醫科,可在戰爭年月,兵荒馬亂,並沒學成什麼,所以十分慚愧。希望你們趕緊另請高明,否則耽誤了治療我擔待不起。北野聽了蔔乃堂的翻譯,臉色變得陰沉,說蘇原君無須客氣,你出身醫學世家,又讀過專科,怎會是庸醫之輩?快快隨高田少尉去給將士們治療,要真耽誤了治療,卻是罪責非淺。蘇原已覺無話,心想不妨敷衍一下,再相機脫身。
蘇原和牟青隨高四軍醫、卜翻譯官以及肩負看守職責的少尉走出祠堂,向日軍病員宿地走去。行走中牟青陡然察覺側方有一雙眼直勾勾地盯著她,那是卜翻譯官。狗漢奸!她在心裡罵了一句,低下頭去。
村街很靜,空蕩蕩的街面上殘存著斑斑血跡,散發著腥氣。著火的幾幢房屋還在冒煙,風將煙柱歪向一邊,如同巨人頭上豎起的粗黑髮辮。
為便於診治看護,這些病員被集中起,分住兩處,一處為軍官病員,另處為兵士病員。他們先往軍官宿地。這是位於村頭的小學校,一圈楊樹圍起的院落,一拉溜七、八間平房。這時太陽已往上升起,光芒透過楊樹梢頭射進院子,暖洋洋的。這夥穿軍官制服的病員三三兩兩坐在屋前臺階上曬太陽,有的躺在教室裡用課桌拼成的床鋪上,哼哼卿卿,滿臉的苦相。高田軍醫首先讓院裡的病員脫掉鞋襪,給蘇原診看。蘇原做出查看的樣子,俯下身,盯著一隻只腫得紅亮的腳。此時他對病情已明瞭於心,當他站直身子,高四軍醫詢問要否再去兵士病員宿地診看,蘇原說沒有必要,見一知百。於是他們重返祠堂。
這時北野已離開祠堂,據勤條兵說旅團長親自去通信班接收上面發來的電報。其實是無需他親自去的,通信班每回收到電報都是跑步送來。看來情況有些異常。過了一會兒,北野回來,臉色十分難看。他與蔔乃堂嘰哩哇啦講了一通,蘇原聽得的意思是上面責怪他的先遣隊行進遲緩,鑒於這一帶諸樣不平安因素,第十一旅團滯留于遼寧海岸的大部隊暫按兵不動。這一局面對身任旅團長的北野來說無異是一個巨大的打擊。卜乃堂向他報告了蘇原醫生去病員宿地診看的情況,北野問結果如何?蔔乃堂說還須旅團長親自詢問才是。北野遂點點頭,轉向蘇原一笑,笑得十分勉強,說蘇原君為部下診治,不勝感激,請問此奇異足疾可用何方何藥治療?待卜乃堂翻譯之後,蘇原答:日軍將士所患足疾甚是蹊蹺,以前在書本上和臨床醫療上對此種病例聞所未聞,見所未見,因此難斷病因,更難下藥醫治。蔔乃堂將這番話翻給北野聽,之後又加上一句自己的見解:我看他說的並不可信。蘇原聽得明白,因此在心裡對蔔乃堂無限痛恨:北野顯然是贊成蔔乃堂的,繼續對蘇原說:蘇原君之言難圓其說,難道你們本地老百姓的腳是鐵石所鑄,從來不生病疾?惟獨我們外來的日本人註定倒楣不成?蘇原聽了心裡格登一聲,心想倒真叫這個不懂醫學的北野言中,這種足疾確是一種外鄉症,實由水土不服引起,本地百姓自然不是鐵石之足,也生足疾,但不是這一種。對比起來,這由水土不服引起的足病倒不難醫治,他的父親便有十分奏效的藥方。他說北野先生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人生天地間,俱吃五穀雜糧,俱經雨雪寒暑,哪有不生病疾之理。問題是對病疾的態度大相徑庭。我們中國人崇尚養生,崇尚自然,注重以自身的精血來抵抗病疾的侵蝕,許多情況都是不治而愈。我以為這並不意味著是不尊重科學,而是更貼近醫道本質的一種超然態度。北野聽了蔔乃堂的翻譯後,冷笑一聲,說,想不到身為醫生的蘇原君竟倡導什麼不治而愈,滑稽之至。如真是這樣,像你蘇原君幹醫道行的人不早就在中國絕跡了嗎?話說回來,你們中國人怎麼想怎麼做是你們自己的事,我不感興趣,可我不能叫我的部屬躺在地上等什麼「不治而愈」,我要前進,要完成使命,你懂嗎?你必須大大地為皇軍效力,你懂嗎?!蘇原不再說什麼,心想這個北野俊太郎可有點不好對付。
當蘇原與北野的對峙接近尾聲,北野以異乎尋常的方式向蘇原攤牌。他讓蔔乃堂給他好好翻譯,他口氣平和卻殺機顯見,他說道,蘇原君,從總體上我理解你的心理,豈只是管世上人人都希望生活于理性與道義之中。在中國,在我們日本,』關於教導人如何認識如何行為的金科玉律如出一宗,如同地上的高山河流平原湖泊在太陽底下顯現得清清楚楚。可是蘇原君你不要忘記一點,太陽不會永遠不落,真理也不會永遠放光,人告誡自己該做什麼不該做什麼,雖一切都明明白白。可在理性的法則面前人們又不知所措。蘇原君,你知道人實際上是生活於什麼中間呢?是選擇。人除了親生父母不能選擇之外,其餘的都可以選擇,如求學、求親、求職等等無不存在於人的選擇之中。就以我為例,高中畢業我選擇了武學堂,進入陸軍後我選擇了安堂知子做了我的妻子,戰爭之後我選擇進入中國派遣軍而不是日本大本營……是選擇決定了一個人的生活道路,決定了人的命運。人有時候面臨兩種選擇,有時候又面臨多種選擇,而最困難的選擇是生還是死。我現在要指出的是你此時此刻面臨的選擇,不言而喻,你的選擇將是由我強加於你,這種強加事實上也是我自己的選擇:我必須讓你給我的部下治療,別無其他。那麼我將怎樣地強加於你,這就是你此刻最為關注的問題。如果在和平時期,我的強加或許會有所節制,比如讓我的士兵抽你一頓鞭子,趕走了事。可現在是戰爭時期,戰爭使目的變成唯一,又使選擇變得極端。這沒有辦法。下面我將開誠佈公地指出我將強加給你的幾種選擇,當然前提建立在你仍然拒絕為皇軍效力的基礎上。我將階梯式實施如下:一,著人強姦你的妻子,對此我的士兵將樂此不疲。二,完事以後便一點一點肢解她的身體,看她是否如你所說會不治而愈。三,當著你的面將她活埋入土。四,我將命我的十名士兵從不同角度將刺刀刺進你的胸膛。蘇原君請你原諒,即使我有耐心也沒有時間,如果時間充裕,我會給你提供更多更多的選擇,但是不成,我確實沒有時間,這你知道。現在請你蘇原君聽清也請你相信,作為大日本帝國一名將領,我決不食言,我將依照剛才所說的順序實施,不得到你改變主意的答覆,決不中止。
當蘇原將自己的治療方法說給北野,北野瞠目結舌,爾後又勃然大怒,說蘇原「惡劣」的藥方是故意侮辱大日本皇軍。他決不接受。蔔乃堂趕緊相勸,說中國諸多民間偏方十分玄妙,有的也確實「惡劣」,但偏方治大病無庸置疑。蘇原只是聽著,不加任何解釋。他倒希望北野拒絕用他的藥方治療,那樣他就不用擔為日本人效力的壞名聲。細想想,他供給的藥方當屬北野所認定「惡劣」的那一類。不是別的,是當地男爺們兒的一泡熱尿,將尿直接淋在患者的腳上。在民間,尿歷來被視為一劑藥物,童子尿自不必說,莊稼人在地裡收割,一旦有了創傷,便立刻往傷口上撒尿,可止血,也可消炎。北野部下的足疾既然是外鄉病,那麼當地人的尿自然便算得一味藥了。身為日本人的北野對這些孤陋寡聞,自然會懷疑蘇原是不良用心。事實上蘇原在說出這個藥方時心裡確充滿報復的意願。
蔔乃堂的話總算起了作用,北野從暴怒中平靜下來,他在心理權衡,或者說選擇,他萬萬不曾想到在自己強制蘇原做出選擇後不久蘇原又以另一種方式強制他進行選擇:要麼拒絕治療(後果是他的部隊繼續陷於癱瘓);要麼接受治療(後果是他和他的部屬無論其肉體還是精神都將浸泡在中國人臊臭的尿液中)。這種選擇對堂堂大日本帝國的一名將領來說不能不說是十分艱難的。
北野做出接受治療的決定這一刻,心裡升騰起對蘇原無以復加的仇恨。「治不好死了死了的!」北野咬牙切齒的話用不著卜乃堂翻譯蘇原也聽得明明白白。
日本人採集「藥方」的過程使村子的百姓再度隱人驚慌中。昨夜的戰事剛過,儘管村裡人確實沒有參與對日本人的偷襲,但還是挨家挨戶被搜查了一遍,許多男人被打,許多女人被強姦,最終日本人還覺得不解氣,又硬是指定了幾個「嫌疑犯」,將他們關押起來,凶古未蔔。
日本兵將村裡所有男人一齊趕進離河不遠的學堂裡。
整個治療過程由高田軍醫負責,他讓所有患足疾的軍官和士兵在學堂院子裡站成一排,命他們脫下鞋襪,綰起褲角。關於治療的方法,事先已在他們中間傳開。這正應了中國一句俗語:有病亂求醫。儘管他們嘴裡罵罵咧咧,可還是乖乖地赤腳站著,等中國百姓往上面撒尿。
然而卻沒有人告訴這些被驅趕來的莊稼漢們究竟要做什麼,他們確實只像一味藥那樣任人擺佈。日本兵惡聲惡氣地吆喝他們,叫他們怎樣怎樣,動作稍為遲緩,便拳腳交加。陣勢總算擺成了,日本赤足兵與村裡的男人面對面站成兩排,後者被這奇怪的陣勢弄糊塗了,再加上頭一遭和兇神惡煞的日本鬼子靠得這麼近,心裡咚咚地直敲鼓。
高四大聲向村裡的男人宣佈:「大家都照我說的做,脫褲子,往皇軍腳上撒尿!」
村裡的男人聞聲驚呆了,以為是耳朵出了毛病,不約而同地望著那個向他們發話的日本人,卻沒一個人照他說的做。
「撒尿!往皇軍腳上撒尿!」高田又喊。
這道他們是聽清楚了,俱嚇得心驚肉跳。狗日的鬼子躲還躲不及呢,還朝他們身上滋尿,這不是自己找死咋的?這沒准是狗日的日本人設下的圈套讓他們鑽。有人開始朝後倒退,許多人又跟著退,隊形立時亂了。
一名值日軍曹從腰裡拔出手槍,嘴裡哇裡哇啦吼個不止。
卜乃堂趕緊翻譯;大家別動,都照皇軍說的做。皇軍說哪個敢不往皇軍腳上撒尿就斃了他!
聽說不尿就斃倒真的有人尿了,不是尿在皇軍的腳上,而是尿在自己的褲襠裡,尿順著褲筒往下淌,在腳下地面注了一大汪。
「八格呀嚕,死了死了!死了死了!」這沒逃過軍曹的眼睛,他怒不可遏地將槍口指向那個將尿抛灑光了的中年漢子。
一直默默站在一旁的蘇原見狀急了,忙向大家喊:「鄉親們聽我說,日本人腳長了病,在上面淋一泡尿就治了。大夥都知道蘇家泊有個蘇子熙老中醫吧?這是他留下的藥方。我是他兒子蘇原,大夥只管放心尿,別害怕,尿完了各回各的家。」
蘇子熙老中醫的名聲很大,四鄰八疃哪有不知道的。這當中許多人還讓蘇老中醫看過病。又聽這人說是蘇老中醫的兒子,大夥心裡的石頭便落了地,想既然不是日本鬼子設的計謀,就尿他個娘的。日本鬼子在中國橫行霸道,騎在中國人頭上拉屎,今個咱掐著雞巴往這群王八蛋身上盡一遭,也算替中國人出了口鳥氣。
「尿他娘,尿他娘。」像互相鼓勵,又像互相壯膽,這群莊稼漢子便迅速行動起來,一人選中一個目標,湊到跟前,然後解開腰帶,從褲襠裡掏出那玩意兒,精神抖擻地朝日本鬼子猛滋一陣,刹那間,尿聲如瀑,臊氣沖天,日本兵腳底像開了鍋……
這是一個無比壯麗的時刻,以至許許多多年之後村裡人提起這事便感到迴腸盪氣,而那些往日本兵身上滋過尿的男人更是以抗日英雄自居,豪情永存。
北野沒到現場看中國老百姓給他的部屬治病,可他想像得出那是一幅怎樣的畫面。不僅如此,他甚至感到那洶湧奔騰的尿水從祠堂上空鋪頭蓋臉向他傾注下來,將他淹沒,令他窒息。直到通信兵又有電報送來,他才從這種幻覺中回到現實。電報的內容令他震驚不已:大本營根據瞬息萬變的戰場形勢以及北野所帶領的新編十一旅團先遣隊行動不利,決定仍滯留于遼寧海岸待渡的十一旅團大部隊放棄渡海計劃,改由陸路乘火車經山海關進入華北,然後沿津浦線南下。為便於部隊行動,大本營重建了第十一旅團的指揮系統,任命古本豪少將任第十一旅團旅團長,率領部隊入關。同時大本營命令北野旅團長將先遣隊帶至萊陽城與當地駐守日軍匯合。鑒於駐守日軍大隊的山谷大隊長不久前在一次掃蕩中負傷,仍在醫院治療,暫由北野少將代其指揮,負責全部軍務。
一紙電文如同雷從天降,炸得北野呆若木雞。
行伍出身的北野自然清楚這道命令對他意味著什麼,這是一種變相的罷黜,是對他指揮不利的懲罰。他深知陸軍部那些軍閥們的一貫做法,他們對旅團長一級的指揮官向來不當回事兒,只要他們效力賣命,戰場上稍為失利,便立即給以顏色。北野曾多次為他的那些失寵同僚不平,今天卻輪到了自己。
他憤怒,恨他的上司,也恨給他製造麻煩的中國人。這時,他眼前又顯現出一群中國百姓得意洋洋地往他的士兵身上撒尿的情景。這更叫他氣恨難平。
不知不覺天色已近黃昏,陰影從祠堂四周的圍牆下一點一點向中間收攏。天空又出現了烏鴉的陣列,「哇哇」地鼓噪不止,刺耳擾心。北野再也按捺不住,「唆」地從腰間拔出手槍,對向天空。他一向有射殺飛鳥的嗜好,見了便情不自禁。此時,在他即要扣下扳機時。卻冷丁收住,連他本人都覺得異常。然而只停滯了瞬間,他便豁然醒悟,什麼才是他此時此刻最迫切的心願。
行刑地點在村外河邊,開闊而有依託。負責現場實施的尖下巴少尉,嘴裡哼著綿軟的家鄉小調。時間尚早,太陽從河對面的堤壩上剛剛露出,霧氣使它顯得很大,很紅,邊緣模糊。
少尉抬頭向太陽看看,覺得這異鄉的太陽與他家鄉的太陽毫無二致,是那樣鮮豔。
太陽再升高些,蘇原和他妻子牟青被幾名日本兵帶到河堤前面的一塊平地上。起初他們不明白為什麼要帶他們來,在那塊平地上站住後,便發覺這裡是日本人設置的刑場,即將被槍決的幾個中國人已被帶到堤上。蘇原不知道他們的身份,也看不見他們的面目,他們被一字捆綁在河堤的楊樹下,背對著同樣一字排開的持槍日本兵。那時刻的太陽開始強烈,光線在這些將死的人光亮的頭頂閃耀著玉樣的亮點。四周無聲無息。蘇原兀地感到透心的恐懼,他向妻子身邊靠靠,發現妻子的身體在暗自顫抖。他想日本鬼子為什麼要讓他和妻子來到這刑場?北野要一併殺死他們嗎?他想不會。昨天下午給北野部下的治療很快便有了效果,在尿液的浸泡下,日本兵腫脹的腳迅速消腫,不再疼痛,有的症狀完全消失,可以像正常人一樣行走。當傍晚時分回到北野住的祠堂,高田軍醫如實向北野報告了治療情況,北野還假腥腥向他表示感謝。在這種情況下,北野還會下毒手嗎?他把握不定。他有生頭一次體驗到人面對死亡時的感覺。作為醫生,他的職業是同生死打交道,他曾無數次目睹生命是怎樣一絲一絲進入死亡,這種合乎自然猶如瓜熟蒂落的死亡,早已被他的職業心理所接受。在醫院的病室裡,面對逝者家人悲痛的號啕,他能夠平靜以對,而眼前這種將一個活生生的人在頃刻間予以毀滅的現實,卻是他萬萬不能接受的,不論別人還是自己。
蘇原感到眼前懸在堤壩上空的太陽失去了顏色,天地間陰森森,冷颼颼。
北野、蔔乃堂、高田軍醫以及另外幾名日軍軍官隨後來到行刑現場。
北野的出現給蘇原心靈更增添幾分壓迫。一般說來,像北野這樣的高級將領是不必親赴刑場監殺幾個普通中國人的,除非有什麼特殊目的。蘇原在直覺中將北野的出現與自己聯繫在一起,與自己也包括妻子的生死聯繫在一起。北野的出現不啻是死神的降臨。他感到渾身癱軟無力,不由抓住妻子的胳膊。
走來的北野神情淡淡,他甚至沒看蘇原一眼,站定後只看著前面的河堤。負責現場的尖下巴少尉,跑步到他面前,敬禮,報告一切就緒。他沒說什麼,無言在此時此刻便是一種指令。少尉便跑開,直跑到行刑槍手一側站定。這時蘇原的心幾乎要跳出胸口,他知道只要少尉將腰間的指揮刀拔出舉起再揮下,堤上的幾個中國人將于頃刻間血染黃沙。奇怪的是少尉久久不動,行刑槍手也保持原來的狀態。蘇原正詫異間,又看見高田軍醫向前走去,繞過槍手,一步一步走上河堤。蘇原大張著眼。高田走到一個被縛的中國人身後,盯著他的背後看了一眼,然後伸出手在上面摸摸按按,像在尋找什麼。之後,蘇原又看見高田從衣袋裡掏出一塊什麼東西,在那人後背左側描畫著,很快描畫出一個核桃大小的圓圈。啊!這是心臟的部位。蘇原立時感到毛骨悚然,一股寒氣穿透全身骨縫:這是高田軍醫在為槍手指示射擊的彈著點。在這之前他曾聽說過日本鬼子行刑是射擊心臟而不是射擊頭顱,卻完全不知道還須事先描示出心臟的位置。這是日本人萬事尋求精確的刻板,還是完全將殺人視為一種遊戲?蘇原無從判斷,他兩眼直勾勾盯著那黑色脊背上的慘白的圓圈,似乎清晰地看到在那個死亡白圈的前方有一顆鮮紅的心臟在噗噗跳動,爾後這顆心臟便爆裂開來,眼前噴出一片漫漫血幕,血幕將他全部的精神籠罩,使他難以掙脫。直到他妻子的一陣更為劇烈的顫抖,才使他沖出這堅韌的血幕,太陽重新出現在頭上的天空,他又看見白楊如走的河堤以及那一排被捆綁的黑色軀體。高田軍醫依次在這些軀體上進行自己的工作,無一遺漏地在那個致命的部位畫上了白圈。這些白圈連接成一根白色的鏈條,在陽光下猶如一串亮晶晶的珍珠。
蘇原內心油然生出對高田軍醫的無比憤恨。
事畢的高田已轉過身來,向這邊望望,然後繞過行刑隊列到原先的位置。這時少尉舉起了指揮刀,行刑的日本槍手同時舉槍向前方瞄準。
這瞬間,蔔乃堂一步邁在牟青前面,用自己的身體擋住她的視線,幾乎就在同時,一排清脆短促的槍聲在她耳畔炸裂開來。
那一刻蘇原曾強制自己將雙眼閉合,不使自己看見這慘絕人衰的屠殺,可是不行,他無法將眼閉合,如同那不是自己的眼睛,他大睜著眼,連眨都不眨,於槍響的同時他看見堤上中國人像同時接到口令一齊將頭歪向一邊。他們完了。完了。蘇原心中只凝著這單一的意識。
緊接便是高田軍醫的一聲沉啞呼叫,行刑的日本兵聞聲向河堤奔去,快捷地將剛剛被他們槍殺的中國人從樹上解下,放在準備在一旁的擔架上,抬著向駐地村飛奔而去。高田軍醫緊隨其後。
蘇原驚愕不已。
由於蔔乃堂的遮擋,牟青沒有看見堤上中國人被殺的情景,她眼前很久都是一片土黃,那是蔔乃堂的後背,當這片黃色移開,她眼前的河堤就變得空空蕩蕩。可她清楚兇殘屠殺並沒因她沒有目睹而不存在。她移開目光,不由看了眼站在側方的蔔乃堂,她覺得蔔乃堂那白胖模樣很像一個剛從地裡拔出來的白蘿蔔。
該論到自己了,蘇原不由轉頭向北野望去,正碰北野投向他的目光。他又立刻低頭回避。
北野開始對他說話,聲音很高,卜乃堂翻譯的聲音也很高:蘇原君,我讓你再做一次選擇,是跟我走,還是留在這裡?
蘇原愕然。
我是說永遠留在這裡。北野補充說,抬手指指剛剛殺過中國人的河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