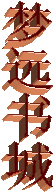
高曉聲文集 魚釣
江南的黃梅天。
大雨嘩嘩下著,像有千針萬線,把天地密密實實縫合起來。
世界一片水汪汪。
漆黑的野外,伸手不見五指,空間像狹窄得僅能容身。各種水的響聲——雨點打在爛泥地裡的叭噠聲,落在水面上的蔔篤聲,碰在闊葉樹上的撒啦聲,以及田水歡騰地經過缺口沖入河裡去的轟轟聲……像一支永遠演奏不完的樂曲。
江水還在倒灌進來,它從一條筆直的小河裡奔騰向南,一路潑啦啦打著漩渦,沖進那十多丈寬的大運河裡來,氣勢洶洶,一直撞到運河的南灘;然後大翻一個身,回旋著隨大流滾滾東去。
就在這丁字河口偏旁的運河岸沿頭,雨點響著一樣嗒嗒窸窸的聲音,好像滴落在硬物上,同時又滴落在軟物上。
原來那兒站著一個穿戴著蓑衣笠帽的人。一眼看去,像個不成形的怪物。他面河而立,不動也不響,好像凝神關注著什麼。
不久,他傴下身子,伸出手拎起一根竹竿,用力把竹竿的另一頭往上提。原來是一口網,他在扳魚。
魚網提出水面,空空如也。他一鬆手,岡又沉入水裡。
「×娘的,」他悻悻地低罵一聲「今朝碰到鬼了!」說著,在衣襟上抹幹了手,伸進懷裡去掏出一支香煙,熟練得幾乎隨手一拋就叼在嘴唇上,喀嚓一聲燃亮了打火機,湊到煙頭上去。火光照出了一張輪廓清晰的長方臉,正皺著眉心吸煙,使那烏黑發亮的眼睛、隆准的鼻子和尖起的嘴巴都湊緊在一起,變得難看了。
像呼應一樣,運河對岸,火光也門了一下,燃出了一個亮點兒。原來那兒也有人,被惹上煙癮來了。
在這樣的雨夜裡,不知有多少人被勾引到河邊來,散落在各自認為合適的地方捕魚。因為這時候河裡的魚多起來了。一部分是隨著江水湧進來的;而運河裡原有的魚本來伏在河心的深水裡,如今發大水,沿岸被太陽曬乾了的泥土和嫩綠的草葉,沒進水裡,散發出誘惑的芬芳,吸引它們遊到岸邊來覓食、來產卵、來嬉戲……然後便輕率地當了俘虜。上刀山,下油鍋,葬身於人腹。
「潑啦啦、潑啦、潑啦啦……」分明又是一條魚落在對岸網裡了。接著水聲消失,魚已脫水上岸。手電筒亮了一陣又熄滅。想像得出,那條魚已被繩子穿住鰓口,就像蘇三上了枷,系在木樁上,國養在河裡了。這樣,明天上市場賣活魚,價錢大。
「什麼魚呀?」北岸的人忍不住問了一聲。
「鰱殼子。」[注]南岸的人回答。
「多大?」他真想跑過去看看,可惜附近沒有橋。
「斤把。
「賊說賊話!」北岸的人罵道:「聽聲音就不止!」
南岸的人不再答話,嘿嘿笑了。
這笑聲,刺傷了北岸人的心。他生氣地低聲罵道:「老子扳魚敗在你手裡,除非鬼摸了頭!」
沉默了一陣。南岸的漁人顯然興致很高,耐不住寂寞,他喊道:「賊王,賊王!」
嘿,這嚇人的稱呼!
北岸人不答。
南岸人不肯歇,又喊起北岸人的真名來:「才寶,才寶!劉——才——寶——!」
劉才寶生氣了:「叫什麼魂!」
「今天怎麼啦?」南岸人的口氣有點揶揄:「聽不見你網裡有聲音哪?!」
這是賊王劉才寶前兩夜嘲笑南岸人的話,現在人家回敬過來了。好大膽,在捕魚這個行當裡,居然有人敢爬到他姓劉的頭上拉屎!他忍住氣,不屑地哼了一聲,反唇相譏道:「喲,聞著點腥味就神氣啦?老子提過的魚,比你吃過的米還多呢!」
「嘿嘿嘿嘿。」對方並不反駁,但那笑聲裡,顯然奚落的味道很濃。
劉才寶也不再說下去了。他今天一直很納悶。他在這裡扳了三夜魚,前兩夜幾乎網網不落空,可是,今天晚飯後到現在,兩、三個鐘頭了,該死,他一共只扳到一條鰻魚,一隻烏龜。一個是舉世聞名的滑頭,一個是盡人皆知的臭貨。按照漁人的迷信,這是今夜不會再捉到魚的先兆。是倒了黴了。但是,劉才寶天生不是疑神疑鬼的人,要知道他不是一般的漁夫,而是這一行的狀元。他精於這個行當,他一貫來靠自己的過硬本領捕到比別人更多的魚,所以決不相信什麼命運。難道他的命運有誰能主宰嗎?難道他當狀元是河神的恩賜嗎?否。假使真有迷信,那麼,河神又算個什麼東西呢?無非是和土地菩薩一樣大小的職司罷了。而狀元則是天上的星宿,河神能管得了嗎!況且自己的銜頭早已不止是狀元,已經封了王了。雖然王之上冠了個「賊」字,難聽而不協調。但一個人的技能精到狀元的程度,如不配以賊心,怎麼能發得了財!豈非胸無大志!王而不賊,不乘機撈一把,才是呆子!滑頭的鰻魚和臭貨的烏龜捨命來投,憑哪一點能算晦氣?滑又怎麼樣?老婆從前做姑娘時,還不是嫌原來的對象老實才嫁給自己的麼!一個人活在世界上,難道應該渾身長著把柄讓人捏在手裡,而不應該像一粒玻璃珠那樣光溜滾園嗎?至於烏龜身上的臭氣,也只有放過屁才聞得到。那麼,請問誰的屁是香的?誰又是不放屁的?區別無非是有的放了屁不賴,就成了屁精、臭貨;有的矢口否認,甚至放了夾屎屁,聞得人噁心,都還像煞是乾淨的。做賊又怎樣呢,難得做一次,被捉出來了,人家會大驚小怪,說什麼「好端端的人怎麼去做賊!」像自己這樣偷慣了又從未被捉住的,成了王,還臭到哪裡去!清官誤飲一杯酒,有人罵他變了質;貪官長享萬民膏,有人說他本領大。兜肚裡有錢,照樣有人眼紅。頂多背後給罵一聲「娘的,偷發財的」
就是了。凡事只要看穿,好官、好賊就都可以「我自為之」的。劉才寶早經深思熟慮,決不因鰻魚、烏龜而上當受騙,他要堅持下去,設法扭轉局面。
但從烏龜落網以後,確實再無來者。除開那迷信的傳說,要另找原因,頗費斟酌。劉才寶研究來研究去,最後認定是烏龜就擒之時,在網上放了一個臭屁,污染了這塊地方,惹得遊魚不肯來了。
「嘖!」劉才寶不禁咂起嘴來。在這種嚴重的形勢面前,真有點棘手。當然,他並不是不會動腦筋的人,起先他打算換一個地方去扳;但一想到那屁臭是粘在網上的,網到哪裡,臭到哪裡,搬也無用。因此不禁惱恨起來,咒駡那河裡的烏龜心不齊,為什麼一隻放了屁,別的竟不放?全體龜族若能同時放起屁來,把一河水都搞臭了,那麼,遊魚也就無可選擇,網臭也不會礙事了。左思右想,沒有別的辦法,只有耐心等待流水把網臭慢慢沖洗乾淨,才能東山再起了。不想等了好久,也不曾有半點起色。劉才寶好不焦躁。一個人的耐心最好,也總有個限度。他不禁又咒駡起來:「×娘的,今朝真碰著鬼了嗎?」
「潑啦啦、潑啦啦……」又是一條魚落在南岸網兜裡。電筒光亮了一陣,那魚又被繩子系住了養人河裡。
劉才寶雖然剛滿四十三歲,卻有二十四年捕撈的經驗。他毫不懷疑他選擇的這個落網地點要比南岸那個地方好得多。前兩夜的捕撈實踐也證明他選得正確。為什麼今夜兜底起了變化,把全部優勢轉到南岸去了呢?難道烏龜那個屁真能決定局勢嗎?也不見得。臭氣固然難聞,但劉才寶明明曉得,魚類中也不乏「逐臭之夫」;鰱魚就愛食人糞,未見得會拒屁於千里之外的。現在為何一反常態,它也專去南網作客呢?
在劉才寶看來,世上得意事,莫過於自己捉到魚,別人捉不到。而最惹氣的,莫過於自己握不到,眼睜睜看著別人捉。他是個得意慣了的人,現在弄到這步田地,如何忍得住。時間越長心越暴躁,終於動搖了。不想繼續守株待兔。他提出網來,向了字河口移近了約一丈,把網落入激流中去。
網還沒有沉入河底,突然網杆竹被猛烈地擊撞了一下,憑經驗知道撞上了一條大魚。好傢伙!劉才寶的手腳真快,幾乎在同一秒鐘之內,就迅速把網提了起來。但是來不及了,「轟隆隆」一聲,那魚吃了一驚,騰空躍起,落在網外幾尺遠的河裡。
劉才寶一楞,網還不曾放下,懊悔還不曾結束,「南岸卻連續響起了「轟隆隆、轟隆隆……」的聲音,分明就是剛才那條大魚,落入南岸網裡了。
劉才寶恨得把手一松,任網落下去,眼睛盯著南岸。那邊手電筒亮了很長一陣,隱約看見那條魚有半人來高,被抄到河邊養起來了。
「這條魚本來是我的。」他咬咬牙說。恨得好像是別人從他手裡搶走了魚。
他重新去提網,發現網被沖得翻了一個身,歪在旁邊。他吃了一驚,打亮電筒仔細察看,這才看到今夜的水流太急了,網都停不住。劉才寶的心一沉,他確實從未碰到過這樣的激流,他沒有經驗,他無能為力。他第一次失去了把握,他猜想在這樣的激流中魚也存不住腳,只能被一直沖到南岸去。這大概就是今夜顛倒錯亂的原因。那麼,除了鰻魚、烏龜他將一無所得,他這條大船要翻在陰溝裡,落得個笑柄遺留在眾人嘴裡了。
「嘿嘿。」他忽然冷笑了。心裡想:「我的魚竟被他捉得去!唔,提得去就算了嗎?老子……老子不會讓你爬到頭頂上去屙屎的!」
他把右腳伸到河裡去,猛然劃了幾下:「轟隆隆,轟隆隆……」真像有條大魚落在網裡。
「娘的,你到底來啦!」他裝得快活地說。還亮了片刻電筒。
「什麼魚呀?」南岸人信以為真。
「不識得。」他裝得不屑回答。
南岸人不願再問了,卻更相信它是一條大魚。
過了片刻,劉才寶又如此做了一次。不過把水踢蹬得更響些,似乎又捉著了一條更大的魚。然後,他安然在濕地上坐下,燃起一支煙,悠悠地抽起來。
他無聲地笑著,顯得很開心。因為他覺得自己擺脫了無把握的狀態,正在幹著非常熟悉而有豐富經驗的勾當。
這時候風輕了一點,雨也小了一點,周圍的一切雜聲,似乎都想停下來,默默地注視這位狀元、這位賊王的藝術表演。
劉才寶看了看手上的夜光游泳表,已經十點五十七分。照前兩夜的規矩,大約不用過半點鐘,南岸那位老兄應該回去吃半夜餐了。不過今天也許興致很高,會忘記或推遲。必須自己帶頭引導一番;同時也是避免嫌疑的一著棋。想罷,不再停留,打亮了電筒,爬上了岸頭,晃蕩晃蕩,故意閃動著電光,朝自家村上走去。一路還唱著動情的山歌。他唱道:
黃梅落雨妹發愁,
情哥捉魚在外頭;
深更半夜不回來,
餓壞肚皮要短壽。
黃梅落雨妹發愁,
情哥捉魚在外頭;
深更半夜不回來,
小妹怕他軋姘頭。
…………
歌聲越唱越遠,電光越打越暗,劉才寶煞腳停住,「咕咕」一笑,便熄了電光,輕手輕腳摸黑回頭往河邊走來。
他還沒有回到原來的地方,就看見南岸也亮起了電筒,走回去夜餐了。
劉才寶看到一切盡在意料之中,十分適意。加快步子到了河邊,迅速把身上脫得赤條條一絲不掛,悄然滑下河去;順著水勢,很快就到了南岸。然後沿灘摸去,尋找囚魚的所在。目標就是那條大魚。本來是他(逃脫)的,竟被別人捉去了,當然應該收回來。
他先摸到了樁。樁上系著好幾條繩頭。他把每一條繩都拉一拉,試准了抗力最重的一條,然後順繩摸下去。他摸著了那條魚。真精,一接觸,就知道是條草魚;從頭到尾一摸,就吃准重量在十二斤到十三斤之間。他隨手從樁上解下繩子,把魚像牛一樣牽在手裡。
目的物到手了,一切如他幹過了的千百次一樣,平安無事。
現在,只要把這條魚拿到北岸,這趟生意就算成功。
但是,運河上沒有橋。
對於劉才寶來說,這次整個行動,不過是無數次戰役中的一次戰役;如何把戰利品運回去不過是打掃戰場中的一個細關末節。即使是真正指揮百萬大軍的英明統帥,對這樣普通的技術問題,也難免偶或忘之。若評歷史功過,又焉能涉及若是之末端!所以,精明如劉才寶,也難免犯千慮之一失。沒有橋,是極簡單的事實,劉才寶決不想臨時造一座。他從北岸下河伊始,從未想過要爬上南岸。他偷的是水營,劫的是水寨;只要得了手,就打算帶著俘虜遊回北岸去。這裡面顯然並不存在什麼困難,無需認真考慮。應該是輕而易舉,可以馬到成功的。可是,現在將魚牽在手上,劉才寶卻感覺到了這個俘虜在水中游竄的力量。
「該死的,它還真有點勁道呢!」劉才寶嘲笑地想,覺得那魚強得有趣。他興奮起來,他的自負心是很強的。他是個捉魚精、是狀元、是賊王;二十多年的打魚生涯,他經歷過無數艱難險阻,也練出了一身本領,網、叉、釣、罩,十八般武藝件件皆精;魚、鱉、蝦、蟹,千百種習性無不洞悉。他能把它們玩於股掌之上,玩得輕巧離奇,神出鬼沒。甲魚很兇猛,伸頭要咬人,他能一下子揪住它的頸脖;鱠魚渾身刺,張開便傷人,他能一把握牢它的肚皮;鰻魚最滑溜,雙手都難捉,他能用三個指頭夾得它脫不了身;七八斤重的黑魚,即使上了岸,平常人雙手也揪不住,他能用兩根手指捏著它的眼窩從水裡拎出來……至於青、草、鰱、鱅,不過是些普通角色,一旦被他捏著,便如粘在手上,再也逃不脫的了。他早就把魚類看作他可以隨意處置的馴服臣民。他平生提到的魚比別人吃過的米粒還多,這給他帶來財富,帶來出人頭地的名聲,帶來精神上的愉快。他真是「與魚鬥爭,其樂無窮」,只要有魚可捉,哪管病在床上,也會奮然躍起,執戟上陣。看著那水裡的畜生被自己逼得亂蹦亂竄,慌不擇路,拼命掙扎,終至無路可逃,束鰭就擒,他會興奮得冒出一身大汗,把傷風病治好。他是個嗜腥如命,樂此不倦的人物。如今面對著一條十二斤重的小小草魚,若把它看成是一個勁敵,豈不是天大的笑話!
他並沒有多想,就決定牽著魚泅渡。
但是,剛開始浮游,那只牽魚的手就被魚拉住了不得自由。劉才寶不得不重新站在河邊水中。他想了一想,就把繩子打了個葫蘆結,把左腳穿進去,讓繩子勒緊在腳踝上,騰出雙手,便於劃水。然後毫不猶豫,一蹬腳,向深水中游去。
他從未想到有什麼危險,因此根本不覺得這行為的勇敢。他只相信自己強有力。
他一鼓作氣前進著。他確實是個強者,在那樣的急流裡,腳上綁著巨大的抗拒力,遊出三四丈遠,方向筆直,一點沒有歪斜。
只是,他覺得他的手必須劃得快一點,更快一點,才能夠壓制住那股拉力。於是他開始喘粗氣。
那條魚一忽兒拉著他往斜刺裡去,一忽兒拉著他往水底下沉。他游得很吃力,有時偏離了方向。
「它居然還想拼一拼呢!」他在心裡罵那魚。想起去年秋天有一次在內灣裡釣魚,一條八斤七兩重的青魚吞了鈞子,拉著鈞線往河心裡鑽。他怕線斷,不肯硬拉,就沿著河岸任魚牽著自己跑。糾纏了近兩個鐘頭,把沿岸菜畦上的作物都踏光了,那青魚才力乏,終於任他釣上岸來。
是的,他同魚拼過不知多少次,從未失敗過。他習慣了勝利。他是有毅力的。
現在的情形很像那次釣魚,又是魚在拉著他兜圈子了。
他仍舊沒有感覺到危險,他搏鬥著,在河心的激流裡連連打轉。困難已經非常明顯,情況顯然和釣魚有所區別,現在是魚在河裡,他也在河裡,雙腳離開了堅實的土地,他的勁使不足。
草魚拼命掙扎著,把繩子拉得急騰騰。箍在劉才寶腿肚子上的葫蘆結,越抽越緊;勒得他越來越痛。劉才寶忽然想到,自己都痛了,魚嘴勒在繩子上能不痛嗎?他高興起來,使勁把腳伸縮,要讓魚嘴痛得不敢再拉他。可是,那魚也像鬥出了性子,竟吃得住痛,一步也不讓。
經過這一番搏鬥,劉才寶力乏了。他馬上後悔不該白花這麼大力氣。他喘著,為了省力,他把仰出水面的頭顱沒到水中去,只是在透氣時才抬出來。
他被魚拉得沉下水去的次數越來越多,他真正感到了危險。他動搖了,覺得犯不著同這畜生爭勝負,他決心要解開繩子。把魚放開,饒它一條命。
草魚卻不想求饒。它要鬥爭,它拼命直竄,把繩子拉得像一根鐵棒,沒有一點鬆動,劉才寶解不開那個結。
連續三次,劉才寶憋住氣,任魚拉著走,他一手拉住繩,讓腳和手之間的那一段繩子鬆弛,另一隻手去解結。但是時間來不及,一口氣憋不得那麼長,只得放開手,再拼命掙扎著泅上水面換氣。
這個企圖,終於徹底宣告失敗。他劉才寶和這條魚,結下了不解之緣,不是人死,就是魚亡。
劉才寶看到了這一點,真正的決戰開始了。他很堅強,一點不後悔,他根本看不起這個畜生。別說是魚,就是人,他也不放在眼裡。在無數次偷魚活動中,他不是沒有碰到過危險。人們發現了他,像逐浪似的叫喊著追趕他,他也從未慌張過。他腰裡繞著一張絲線結成的大眼撒網,等到別人追近來,他就解下撒網撒出去,把成群的人裹纏在撒網裡,使他們跌跌撞撞,滾成一團。自己則從容離開。誰也近不得他的身,誰也沒法縛住他。何況是一條魚!
他咬緊牙關,使出絕力,發瘋似的揮舞著雙臂,把河水拍拉得轟轟直響。但是,前進不到五尺,他沉下去了。
他覺得出了汗,又覺得徹骨涼。
他又一次拼命泅上水面。然後又沉下去。又冒出來……
他張嘴喊救命,卻吞了一口水。
他的腦袋保持最後清醒的時刻,想到的並不是他竟死在魚嘴上,而是後悔自己竟不曾拋得開這畜生,以至人們最後終於要把他連同贓物一起捉住了。
之後就開始昏迷。他似乎覺得身體發脹得難受。這感覺帶著他迷迷糊糊記起了流傳在漁人中的一個老故事。據說鱠魚善於裝死,它翻轉白肚皮,朝天躺在水面上,水蛇看見了,悄悄遊近來,迅速把它繞住。這時候繪魚活起來了,它輕輕動了動身體,水蛇馬上用力箍緊,不讓它逃走。於是鱠魚就鼓足氣,讓身體發脹,奮力展開利刺,一下子把水蛇劃成幾段。然後從從容容,把蛇體吃個精光。
於是,劉才寶覺得發脹變得舒服了,箍在腳上的似乎不是繩子,是一條水蛇。
他想像著要拼命脹一脹。但是,刺呢……
198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