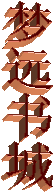
雪 駒 第十六章
歌者說,這應該是幻滅的一章。
我回答,本應該是這樣。布音吉勒格的慘遭不幸,理應擊碎我那馬背上的夢。要知道,我一貫把這巨人摔跤手的今天當做自己的明天。一而現在?今天躺倒在血泊中了,又何從談起明天?
歌者說,但你卻還在往下走著。
我回答,是的!但這僅僅是一種慣性,多年來幻想衝擊留下的一種慣性!雖然說,布音吉勒格之死已使我朦朦朧朧地看到了什麼,但作為一個孩子我已很難控制自己了。更何況,客觀情況也在推擁著我,使我很難及時收韁。
歌者說,你不知日本人還在謀算你的馬?
我回答,知道。往事歷歷在目,我清清楚楚知道豬塚隊長仍在做著那祝壽獻馬夢。據多年後我對有關史料研究的分析結果看來,豬塚隊長這個人是極狡詐兇殘,但也絕不乏認真、頑強、絕不服輸的另一面。是個典型的追求「盡善盡美」的偏執狂。比如一旦決定獻馬,便遭同僚嘲諷也絕不更改。甚至反譏笑對手為「文化的沒有」!「象徵的不懂」!進而又修改為不但要獻「奇異的蒙古馬」,而且是要奪總第一的「奇異的蒙古馬」!
歌者說,這使你暫時逃脫了厄運。
我回答,是的!我尚不知他又有了這樣新的「追求」,竟然把我也納入他那
「盡善盡美」的計劃。我頂多只能意識到,他們只是因雪駒尚未到手才暫時放過了我。而絕對不會想到,我作為「蒙古民族的未來」,也將被進貢給他們那位「天皇陛下」。人、馬,還有未來,多麼「盡善盡美」的野心勃勃!
歌者說,你還需經磨歷劫!
我回答,完全正確。須知,我只是豬塚隊長計劃中的一個小小細節。幾乎與此同時,他正在向整個那達慕張開慘絕人表的網。且莫忘記了那些為布音吉勒格伸冤而被抓走的牧人們,他們將首先成為血的祭品!而我早已自覺或不自覺地陷入了這場災難,不經磨歷劫是很難徹底清醒的!
歌者說,大瑪力嘎的帶你「見識見識」或許就是你又一次磨難的開始。
我回答,準確地說,是要在我迷惘之中,再給我套上一條繩索。使我即使在絕望之後,仍然可由他們隨意牽著而走。但更大的痛苦也極易刺激人的反向思維。我終於又撲向了我的雪駒,開始向它傾述我對叢莽健兒的深深思念。磨難,又使我寄期望於他們!
歌者說,那你就從這兒說起吧!
我回答,是時候了……
我心頭滴著血,我哭了……
我不知道在我身後又發生了什麼,更不知道自己是如何撲出王爺府的!石獅子又被遠遠地拋在身後,我不顧一切地一直沖出了那達慕賽場!
雪駒!雪駒!我只有向你傾述……
應該說,我和我的駿馬才分開了一天一夜,但驟然間我卻覺得是這麼漫長。似一月,似一年,或許似更長時間。總之,我變得急不可待了,悲痛中只想儘快地見到我的雪駒。
一個孩子無法承受的「見識見識」
恍然間,我又看到了小瑪力嘎。他似很後悔一時的魯莽,又像一條忠實的狗尾追上來了。回想剛才,我不由得對他更加憎惡了!他也曾讓我「見識見識」。雖說和大瑪力嘎的「見識見識」風格不同,但卻更能撕裂一個孩子的心!
離開王府,我便不再畏懼他了……
我知道他尚不敢開槍,尚不敢得罪豬塚隊長。更何況,我已經在人群中跨上了那匹馬,一個樓裡藏身便向著草原深處疾馳而去!絕對地令人眼花鐐亂,致使小瑪力嘎帶著眾爪牙手腳失措了。擬追,馬背上不見人影。不追,我卻又在馬背上閃現了。幾經反復,他還是率眾跟上來了。而在此時,我卻早已隱身一個翻滾,甩脫馬匹隱沒在深草之中了。只任小瑪力嘎追著那空鞍子馬,擦身而過地向著那迷茫的遠方馳去!
我終於又和雪駒相會了……
前面說過,一天一夜不見,就像經歷了漫長的歲月。我猛地就摟住了它,把臉緊緊地貼在它的面頰上。親不夠,吻不夠,摩娑不夠。而雪駒等了我一天一夜,也仿佛是擔心了一天一夜。激動地噅噅叫著,也在親昵地吻我,嗅我,舔著我。
我的馬啊我的馬!我還能向誰敘說?
索布妲姨媽似為躲避那根特殊的套馬杆,像永遠永遠消失了。只見那土頭上腦的旅蒙商已經回來了,她卻遲遲不見蹤影。
雖說珊丹也曾解釋過,但我不信……
再說那巨靈神般的摔跤手。胸懷同樣博大,把我真誠地當做朋友。是有什麼話都可以對他說,但卻永遠永遠倒下了。
只留下血泊,還有我的淚……
更重要的似還有叢莽好漢!從塔拉巴特爾,一直到多嘴多舌的單巴。一個個都是那麼可親可敬,定然能從他們那裡討得更好的主意。但誰讓自己不辭而別地沖下山了呢?情況緊急,他們又離得那麼遙遠。
只有痛惜,只有思念……
我和雪駒貼得更緊了,摩拿著它的毛悲哀地說:雪駒!雪駒!只好和你商量了!
它彈了彈蹄子,似說,我明白!
我說,茫茫的大草原上只剩下了我們倆,你說到底該怎麼辦呢?
它動了動耳尖,似說,我在聽!
我說,你知道嗎?豬塚隊長今天又讓我「見識見識」到什麼?
它搖了搖頭,似說,不知道!
我說,阿爸、珊丹、王爺和美女,還有瘋瘋顛顛的喇嘛爺……
它昂起了脖子,癡癡的,這回似在看!
我也不說話了,也在張望遠方。
似也正在看著一幕幕往事。
在眼前恍恍惚惚閃過。
這就是那「見識見識」。
撕心裂肺的……
大瑪力嘎老態龍鍾,卻對我這樣一個孩子絕不失謙謙長者之風。一言一行,頗為尊重,就不該把我帶向不該去的地方。
王府大院深宅重重……
雕樑畫棟,奇花異石,曲徑回廊,亭臺樓閣,他並不引我「見識見識」,而是
「不辱使命」地偏把我直接帶到土牢跟前。一般來說,王府後院為內宅,前院為登堂議事之處。既然兼有審訊之功能,當然前側小院必將設有關押人犯之處。而王府越加豪華,此處也越往往慘不忍睹。溫都爾王府尤為反差強烈,土牢絕對可以稱得上是人間地獄!
打開了一重重古典式的牢門……
大瑪力嘎站住了,似只顧得回頭向我微笑了。略帶歉意,卻又稍顯無可奈何。我起先還不知為什麼,但向內一望我卻失聲地慘叫了:阿爸……只見牢籠內緊鎖著我的阿爸。蓬頭垢面,鬍子長得老長老長。骨瘦如柴,渾身的衣服早已被鞭子抽成條條縷縷了。還沾滿了膿血,上頭竟拱著蛆。除了那雙眼睛我幾乎就要認不出他來了,而那雙眼睛卻目空一切是僵直的。癡癡呆呆,宛若兩隻死羊眼。
「阿爸!」我又慘叫了一聲。
陰森森地絕無回應,是像呼喚他人…
「阿爸!阿爸!」又是兩聲。
淒慘慘地絕不動轉,還是不見反應……
「阿爸……」我倒地大哭了。
直勾勾地望著遠方,依然置若罔聞……
「孩子!」大瑪力嘎終於顫巍巍地出面了,「是呀!是呀!老朽也為你感到寒心!可、可這也多虧了豬塚顧問官……」
「豬塚顧問官?」我冷不丁打斷他的話。
「是呀!是呀!」他忙不迭地應承。
「他?」我突然間大哭大叫地總爆發了,「他是一條咬人的狗!吃人的狼!喝人血的惡鬼!早該下地獄的魔王!」
「天哪!」大瑪力嘎嚇得趕緊捂住我的嘴。
「他!他!」我掙扎著還要喊。
「小爺爺!」沒想到他的手勁兒竟這麼大,「你不想活了?不想讓老朽活了?也不想讓你阿爸活了?」
「阿爸……」我又只剩下失聲痛哭了。
「別喊!別喊!」大瑪力嘎還很惶恐,「要緊的是救你阿爸的命!據老朽所知,此乃悲憤交加所致。只要心氣得舒,治癒傷口自不在話下。有救!有救!這要全看你的了!」
「全看我的……」我似也癡了、呆了。
「對!對!」他仍在循循善誘地說,「只要你奪得草原賽馬的冠軍,只要你順應豬塚顧問官的心意,他答應過老朽:立即放人!大王也發過話:布音吉勒格所留下的一切,從蒙古包到畜群,通通地也全歸你了!」
「布音吉勒格……」我又失聲慘叫了。
「嘿嘿!」大瑪力嘎卻說,「布音吉勒格死了,而你阿爸卻還活著……」
「啊!」我幾乎撲倒了。
大瑪力嘎連忙喚人,及時地把我從陰森森的土牢內拖了出來。真可謂點到為止,似就看我有悟性沒有了!
我心如刀絞……
但這卻只是「見識見識」的前半程,而還有更令人心悸的後半程!
那就是我又見到了珊丹……
還是老態龍鍾的大瑪力嘎帶著路,來到了前大院的一間西廂房。看得出王爺絕不屑于光顧此地,充其量只不過手下人處理日常事務的打雜屋。但大瑪力嘎今天卻顯得格外尊重,不用下人竟親手撩起了門簾。
我看見了什麼?
驀地一怔,便見得一個滿臉橫向的惡漢在我眼前閃現了。禿頂、黑牙,大約四十多歲。個子不高,似只向橫裡發展。從頭至腳都像是在油缸裡浸泡過似的。肥膩膩的,渾身都散發出一股令人作嘔的怪味。一看那身打扮,不用說就知道是從那更加荒遠的漠北來的。好像還是貴族,服飾頗具特徵。
叫我看他幹什麼?
大瑪力嘎笑而不答,而那禿頂怪物也似對我視而不見。兩眼淫邪,好像只顧了盯著對面牆旮旯的什麼。我正在門外,當然不知他為何如此激動了。
「大少爺!」大瑪力嘎似只能喚醒他了。
「頂好!」那人卻仍目不轉睛,「頂好!只不該稍嫩了一點……」
「那就算了吧!」大瑪力嘎說。
「不不!」仍然垂涎欲滴,「這筆買賣就算成交了,我就挑准這一個!」
「滿意了?」大瑪力嘎問。
「可,可,」來人仍死盯著說,「我還得脫光了看看,是不是那能生娃的好坯胎子!」
什麼?我猛地感覺到不祥……
似一種本能的衝動,我不顧一切沖進去了。再回頭一看,果然是珊丹正抖抖瑟瑟蜷縮在牆旮旯裡。臉色慘白,似只剩下了一雙充滿恐懼的黑眼睛。
「珊丹!」我哭叫著撲過去了。
「滾開!」那肥膩膩的惡漢大喝了,「他媽的!哪來的小要飯的?」
「珊丹!」我卻置若罔聞地只顧摟緊著我的童年小夥伴。
「敖特納森!」她也似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似的,哭叫著緊緊摟住了我。
「找死啊!」眼看那惡漢要衝過來了。
「且慢!」大瑪力嘎竟然出面制止了,「大王有令,這女孩子暫時不賣了!」
「留下自己用?」惡漢怒吼了。
「不!」大瑪力嘎還是那麼沉穩,「如若真有此心,待那達慕結束再來一看。你能否得到此美女嬌娃,就全看這位小老弟的了!」
「什麼?!」惡漢似大惑不解。
「什麼?!」我卻全部聽出這弦外之音了。
「敖特納森!」但珊丹卻在死死摟著我哭叫了,「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啊……」
「珊丹……」我的心頭滴血了。
應該說,布音吉勒格之死已夠使我悲憤欲絕了,而眼前這一切正猶如雪上加霜,傷口裡探鹽,就更使我難以忍受了。我詛咒蒼天,我詛咒大地,甚至開始詛咒我那馬背上的夢!但好像一切都晚了,阿爸的慘狀,珊丹的命運,恰似兩條無形的繩索使我掙扎不得,似乎只有乖乖俯首就擒!
但我卻又多麼不心甘情願……
這時,珊丹還依偎在我懷裡心有餘悸地啜泣著,卻猛聽到王府大門內外一片忙亂的響動。隨之便傳來了一聲聲吆喝:王爺回府了!王爺回府了!王爺回府了……
大瑪力嘎驀地一驚,便忙出外迎候去了。我也驚訝王爺的突然歸來,忙憑窗向外望去。
難道是那惡漢剛才跑去告了狀……
看來不像。只見他沉甸甸地坐在四人抬輿上,似只顧得望著陪伴左右的兩個美女嬌娘。至高無上的色迷迷,急不可待的色迷迷,垂涎三尺的色迷迷,目中無人的色迷迷,總之,是一種難以言傳的色迷迷!
而且為他開道的是小瑪力嘎……
「大王!」大瑪力嘎顫巍巍地擋駕了,「大王身為『政府主席』,理當與民同樂,為何提前回府了?」
「嗯?」似自己也難以解釋。
「好狗不擋道!」小瑪力嘎卻挺身而出了,一反常態,驟然變得兇狠起來, 「大王累了,想歇就歇,想走就走,你管得著嗎?」
「嗯!」似滿意這種回答。
「大王!」而大瑪力嘎卻忠心耿耿,「大王可知,當今眾王紛爭,齊謀『眾王之王』之位!大王輕離『主席臺』,豈不是讓查幹王爺等有機可趁嗎?須知『主席』
不在將由『副主席』代理之!我王切不可言累,更不可輕信而擅離啊!」
「嗯?」似也覺不乏有理。
「老不死的!」小瑪力嘎似已完全恢復了昔日的蠻橫狡詐,「大王這就想嘗嘗查幹王爺的『精誠團結』,就連豬塚隊長也連挑大拇指喊:喲唏!喲唏!你這老不死的竟敢公然敗壞大王的興致,還敢大膽跳出來進行挑撥離間!不看在今天是王爺大喜的日子,老子這就向皇軍告你去!」
「這……」大瑪力嘎頓時為之色變。
「來人呀!」小瑪力嘎乾脆大肆操辦開了,「張燈結綵,準備酒宴,鼓樂齊鳴,大放鞭炮,這就先點燃洞房花燭!」
「大王!」兩個美女也歡叫了。
「唱啊!」小瑪力嘎還不失時機地吩咐著,「小福晉奶奶!新福晉奶奶!唱啊!唱啊!」
「嘻嘻……」《何日君再來》頓起。
「送入洞房!」最後是小瑪力嘎拉長聲音的一喊。
亂了!亂了!一切都亂了……
但一切都隨著肥胖的王爺湧進了豪華的內宅,前庭裡頃刻間又變得冷冷清清。似只剩下了瞠目結舌的我,抖抖瑟瑟的珊丹,還有突然被冷落了的大瑪力嘎。
洞房?恰和我一次次悲慘的遭遇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強烈的反差!
悲憤間,一個偶像開始在我心中坍塌了!
布音吉勒格死了,他卻又人洞房!
同樣的兩個女人,昨夜?今天?
流淌的血,速成的婚禮!
這就是至高無上?
原來溫都爾王爺!
全無心肝……
「作孽呀!」大瑪力嘎也在對天長歎了,「辜負了老朽的一片苦心!天滅我曹!天滅我曹啊!」
霎時,我也感到了一片絕望……
「你!」他卻突然老淚縱橫地對住了我,「好自為之!好自為之!眼看著查幹王爺就要陰謀得逞了,我得面見豬塚顧問官長!」
他走了,只給我留下了對未來的恐懼……
「救救我!」珊丹又緊緊地拽住了我,「敖特納森!我怕!我好怕……」
「我,我也怕……」我說。
「我,我們,」她又一下摟緊了我,「我們該怎麼辦呢?」
「只有等雪駒……」我只好說。
「可阿媽說……」她吞吞吐吐地提示著。
「阿媽個屁!」我一聽就來火了,「不要你了,不要你了,跟著個死老頭子跑了!」
「不!不不!」她慌忙分辯。
「還不呢?我親眼看見的!」我說。
「不是的!」她更急切了,「阿媽臨走時來看過我,還悄悄對我說,不要聽別人胡說八道,她就會回來的!她就會回來的!」
「我沒聽見!」我還在賭氣。
「可她對我說了!」她說,「要是你犯混萬一跑下山來了,讓我一定要告訴你:千萬回去!千萬回去!」
「那你呢?」我悲哀地說。
「我?」珊丹更傷心了,「阿媽只關心你,她就讓我耐心等著。我怕!怕等不到那一天了……」
「能!我還有雪駒……」我猶疑地說。
窗外死一般寂靜,但我也只能戰戰兢兢地等著。沒法逃脫,似只能等待著豬塚隊長再讓我「見識見識」更可怕的慘景。
抖抖瑟瑟,兩個相擁的孩子……
也難怪!豬塚隊長總在發狂般地追求「盡善盡美」。在他那張巨大的網收攏前夕,他不但還在「盡善盡美」地玩弄各位王爺,使他們不知大難將要臨頭。而且也不忘「盡善盡美」地玩弄大小瑪力嘎,使他們忽起忽落疲於奔命。至於我,只不過是他所有陰謀中的一個小小句號。但也絕不忘「盡善盡美」畫圖了。他說,這也是一門「藝術」。
而不該我當時心頭只剩下了一種失落感。
突然間,前院又突然熱鬧起來,只見小瑪力嘎率領眾人又從後宅湧現了。顯然是溫都爾王不讓打攪他的洞房好夢,人們只能聚在這裡大說淫詞浪語了。更不該是那瘋瘋顛顛的喇嘛爺也驟然出現了。在一片挑逗笑鬧聲中竟又怪聲怪氣地吟誦起他那怪歌了:
九百九十九個小美人啊,
就差一晃便成老太婆了;
九百九十九裡的山彎啊,
就差一步便上那西天了……
吼的聲可真大!尤其落在「上西天」一句,更是聲嘶力竭力求婉轉。但絕對揭不過彎來,致使人們都聽得渾身發涼。雖後宅久久不見反應,而小瑪力嘎卻惶然出面阻止了。開口還算客氣:喇嘛爺!你這是嚎什麼?誰料這位也回答得出奇:我看見眼前有個惡鬼!後果可想而知,僅一巴掌就使喇嘛爺口鼻流血栽倒了。老人家畢竟救過我,隨之我便推開珊丹沖到屋外了。
「喇嘛爺!」我驚叫著忙去扶他。
「啊哈!」他卻一驚一乍地大聲嚷嚷了,「生瓜!生瓜!大的一個剛被拍碎了,小的一個還在到處亂滾!」
「我是生瓜……」我竟恍然應承了。
「滾!滾!」他更瘋瘋顛顛地喊叫得來勁兒了,「給我快快地滾,遠遠地滾,抱著腦袋滾,捂著屁股滾,夾起尾巴滾……」
「哼哼!你沒瘋!」小瑪力嘎冷笑了。
「不瘋!不瘋!」老頭子竟樂了,「嘿嘿!誰說我瘋了?是一條齜牙的狗瘋了!天靈靈,地靈靈,有條瘋狗要咬人!哈哈哈哈……」
「來人呀!」果然小瑪力嘎呐喊了。
「喇嘛爺……」我驚叫一聲忙去護住。
「小雜種!」誰料小瑪力嘎沖著的卻是我,「玩弄我?沒門!軟的不吃咱們上硬的!來人呀!大刑伺候!你給我跪下!跪下!」
「你?你?」我後撤著。
「我?」他惡狠狠地步步逼近著,「我要讓你跪下對這老不死的說,你服了!老老實實地服了!你心甘情願地要給大日本天皇獻上你的馬!你服服帖帖地甘願為豬塚隊長奪第一?說!說!氣死這個裝瘋賣假的老東西!」
「啊!」我大叫一聲,心如刀絞……
「生瓜!」這時卻只見喇嘛爺猛地躍了起來。老樹枯根一般,也不知道哪來那麼大力氣,驀地就把小瑪力嘎緊緊纏抱住了。還不等我緩過神兒,就聽見他又在怪叫了:「生瓜!還不快滾!還不快滾!」
我似被一股神秘的力量推擁著!
猛地便向王府大門外沖出去!
身後傳來了喇嘛爺的慘叫!
還有珊丹失聲的驚啼!
為了不可恥地下跪!
我拼上一切了!
奮不顧身!
往外跑……
往事歷歷在目,恍然間便——過去了。身邊又只剩下了雪駒,卻仍似很理解地在靜靜等待著我。
我該怎麼辦?我該怎麼辦?
是的!我不服!我不下跪!我絕不心甘情願為天皇獻出我的馬!我更不心甘情願為小日本奪第一!
我跑了!我不顧一切地沖出了王府!
但下一步呢?……
茫茫的大草原啊!海海漫漫,遼闊無垠,卻似乎再沒有一個孩子和一匹馬的藏身之地。現實無情,像莽莽蒼蒼的田野也在逼我做出抉擇。
我的馬啊我的馬……
我又把雪駒摟緊了,摩娑著毛向它絮絮叨叨地傾述:至高無上的溫都爾王沒有了,剩下的只是個荒誕無恥的糊塗蟲。布音吉勒格為了他的榮譽倒在了血泊之中,他卻全無心肝地又撿起那兩個美女大白亮天人了洞房。馬背上的夢幻再沒有了,只馱著抹不盡的血和淚。我那巨人朋友並沒有把「今天」和「明天」連起來,反而使我看到自己那嚮往的「明天」有多麼可怕!偶像坍塌了,夢該早已結束了!
雪駒點點頭,似表示同意……
那就該回去了……或許再回到那原始的山野深處將是我惟一的出路。篝火、歌聲,還有那在光焰中一張張閃現的臉。多麼豪邁,多麼親切,多麼感人!就連那猴裡猴氣的小單巴,在回憶中也似乎變得格外可愛了。在自己身邊跑來跑去,在自己耳旁「夥計!夥計!」地叫著……尤其是那塔拉巴特爾,沉默中透著威嚴,無語中透著親切。他曾為我讓人打過小單巴的尼股,這回我偷跑了他該親自動手抽了吧?多委屈小夥伴……啊!不對!他似正指著自己大喊:牧人的胸懷裡能馳騁九十九匹駿馬,可就拴不住一隻蝨子!娃娃家……是的!是的!自己過去心上就是只拴著一隻蝨子——那個夢!啊!不對!他好似根本忘卻了自己,正在對著一個個叢莽好漢呐喊:看准方向撒韁的駿馬,是九十九頭牤牛也難拉回頭的!夥計們,給我沖啊……
自己似變成了一個多餘的人,不值得一顧的人。雖然說,就連狠心的姨媽也曾留下過話:千萬回去!千萬回去!可已經不辭而別了,人家還會要我嗎?
雪駒搖搖頭,彈彈蹄子,似不以為然……
不會嫌棄?那這兒又該怎麼辦呢?豬塚隊長早讓我「見識見識」過了,就像在我淌血的心頭又掛上了兩個鐵鉤。阿爸是被解押回溫都爾草原了,但卻看得出他在日本警備隊受盡了非人的折磨。一個驕傲的牧馬人就這樣癡了。傻了,任蛆蟲在身上拱湧著。大瑪力嘎說還有救,並說「全看你的了」!條件是「順應豬塚顧問官的心意」,奪得「草原賽馬第一」。而我那從小長大的珊丹,命運就更似維繫在我的身上。才十二三歲,就死死被個「汕頭豬」盯上了。不但要「脫光了看是不是生娃的坯胎子」,而且還要被賣到終身再難看見的大漠以北去。是死是活,大瑪力嘎對
「汕頭豬」說得明白:「全看這位小老弟的了」。不言而喻,條件同前:還要讓我賽馬!還要讓我奪冠!而這一切仿佛對我來說是輕而易舉的:我已初露鋒芒,我身懷賽馬絕技,更重要的是我有所向披靡的雪駒!
雪駒昂首長嘶了,給以充分肯定……
但那不是等於自己應了小瑪力嘎的威逼,自動當著眾人在王府大院裡跪下了嗎?
向日本天堂,向豬塚隊長……
這不僅僅是要氣死瘋瘋顛顛的喇嘛爺,也是使整個草原跟著匍匐跪倒啊!恍然間,仿佛有一個巨大的身影在我眼前出現了。啊!布音吉勒格!即使為了家鄉的榮譽,也要在威脅利誘面前傲然挺立!而我這是面對著整個草原的榮辱,我又怎能輕易下跪喊服了呢?似那身影更鮮明了,鐵打銅鑄一般,好像正在目光炯炯地對我說:老弟!你做得對!
但他的大仇又怎能不報呢?
那些無辜被抓的牧民又怎能不救呢?
疏不通,理還亂!不知為什麼,思緒又從這裡牽走了。陡然間,豬塚隊長的聲音又在我的耳旁響起了:「只要你第一第一的,大管家死了死了的,牧民的通通放了放了的!」對對!不僅僅是阿爸和珊丹,還有好多好多好心報信的鄉親們呢!
亂了!全亂了!我怎麼想著想著又從這裡繞回來了呢?
天哪!我到底該怎麼辦呢?
我又只有和雪駒絮絮叨叨了。我說:是的!我該當站立,可我又得去救阿爸、珊丹、好心的牧人們!我不想下跪,可我又必須為了豬塚這壞蛋奪得賽馬的第一!我的馬啊我的馬,你來出出主意!
雪駒一直乖乖地聽著……
這時卻開始躁動不安了。時而不停地刨動著蹄子,似急於表達什麼。時而噅噅直叫,又像也找不到恰當的辦法。
也不知過了多長時間……
我再不願折磨我這無言的朋友了,但紅日西斜似也容不得我再這樣優柔寡斷了。我該怎麼辦?我到底該怎麼辦?驀地,我又想起了雪駒降生時給我留下的那個夢:一條潔白的哈達從天而降了。飄飄忽忽,後來又在我的夢境中多次出現過。莫非……
刹那間,一個典型的孩子氣決定形成了!
我親昵地吻了吻它,一躍而上馬背!
我說:雪駒!一切都交給你了!
由你馱著我,或東或西!
一切聽任命運安排!
潔白的哈達啊!
助我吉祥……
雪駒顯然激動了,它向著那蒼茫茫的遠山接連就是三聲長嘶。看得出,它的意向已定,是奔向那原始的荒野,是奔向那叢莽的健兒!或許是它知道了好漢們會原諒我,或許是它明白那裡才有真正的救星!
我一閉眼睛,準備聽天由命了……
但就在這時,它卻一揚前蹄猛地又停止不動了。似有更大的干擾轉移了它的注意力,竟默默地調轉頭靜靜地傾聽起來。耳尖不時地抖動一下,明顯地是在捕捉來自那達慕會場的訊息。而這一切似乎漸漸壓過了它對遠山的嚮往,它竟又重新焦躁不安地彈動了蹄子。到後來我才知道,不但人關心人類的命運,馬也一樣關心著同類的命運。但當時我並不理解,只聽得它又是三聲淒厲的長嘶,便毅然載著我向那達慕會場奔馳而去了!
深感驚訝,但我或許更願這樣……
事實證明,駿馬也會有衝動的時候!
但已無可挽回,只能隨之奔騰!
夕陽下,會場已隱約可見!
火燒雲似飛濺起來的血!
映紅了茫茫的原野!
我將面臨著什麼?
槍聲乍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