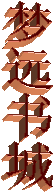
雪 駒 第二章
歌者說,從此,你成了個有馬的奴隸。
我回答,是的!隨著也有了個新的夢。
歌者說,當個傳奇般的騎手?
我回答,這是每個奴隸兒子的夢寐所求。只要能為自己的草原爭得第一,或者王爺一高興就能還你全家自由!
歌者說,希望寄託在馬背上……
我回答,是的!只不該當時我是那麼的幼稚,天真的眼睛裡似乎只剩下了我的馬。要知道,隨著那場暴風雪的席捲,日本鬼子隨之便出現在草原上了。表面上仍把王爺高高捧在王位之上,實際上卻是想利用這個傀儡讓牧民忘記自己是中國人。為此,整整六年過去了,小馬駒也已經長成了一匹矯健的駿馬,我卻仍渾渾噩噩地把希望放在馬背上……
歌者說,這是一首悲哀的歌……
我回答,但並不是所有的人都在唱。我早就聽說,在遠山深處活動著一支特殊的「響馬」——一群頗具傳奇色彩的叢莽好漢。神出鬼沒,來去無蹤,越戰越強,經常打得鬼子首尾難顧。只有我在眷戀我的小馬,仍在孩子氣地迷惘唱著。並且為了對母親的深深懷念,我還給我的小馬起了個意味深長的名字:雪駒!
歌者說,雪駒?
我回答,名副其實!潔白如銀,渾然似雪,奔騰起來就像那當空飛舞的哈達!雖然尚流傳著一些有關它污穢的私語,但我堅信佛爺是保佑著我的!雪駒只會當著王爺面拉屎蛋子,而絕不會禍及為救它而失去母親的小主人!
歌者說,夢不醒的孩子……
我回答,是的!如果沒有那一天!
歌者說,那你就再從這天說起吧。
我回答,是時候了……
那是一個風和日麗的早上。
倒場的馬群在新的牧場上安頓住了,我便匆忙騎著馬來看索布妲姨媽。我長大了,雪駒也長大了,索布妲姨媽家的破氈包也仿佛使我們更依戀了。
須知,小珊丹也長大了……
姨媽對我和雪駒的慈愛是溫馨的,但對我來說更有吸引力的還似乎是這個小丫頭。說來也奇怪,男孩子快十三歲了似仍很難擺脫孩子的陰影,女孩子快十三歲竟出脫得像個苗苗條條的小大人兒了。陣子似水洗過一般,臉龐透出淡淡的紅暈。更讓人感到驚訝的是,原先平平板板的身子上竟隱隱閃現出一些迷人的線條兒。
我跨著雪駒急匆匆地趕著路……
沒有什麼不祥的預感,心頭只有這從小一起長大的小夥伴。一種說不出的誘惑力,使我總想天天和她在一起。小時候有多好呀!我倆常常過家家玩。她當新娘,我當新郎,還唱著喜歌學大人一樣迎過親昵!玩足了,鬧夠了,就擠在一件大皮襖下嘰嘰喳喳個不停。索布妲姨媽常為此發出甜甜的歎息,小雪駒也因此嫉妒得在氈包外噅噅直叫。
怎麼會長大一切就變得複雜了呢?
現在她也好像渴切地盼望我去。一見到我,她會眼睛驟然發亮,長長的睫毛也會驟然抖動起來。面頰上的紅暈會更動人,只不該再不像小時候那樣歡呼雀躍了。挺文靜的,再不和我嬉笑玩鬧,還讓我要像個大人似的。當時我真不明白,難道我還不夠大嗎?要不然就是她也準備和姨媽一樣嫁根套馬杆!
真是少小不知愁滋味兒……
要知道,這是對人性極端殘酷的一種摧殘。王府為了不讓女奴外嫁或其他原因,常把她們嫁給一根套馬杆、一根頂門棍、一塊拴馬石等等。索布妲姨媽還似乎有其他罪名,她不該少女時接受過一位台吉少爺的愛。貴族子弟,從京城讀書剛剛歸來,怎麼能讓一個卑賤的女奴糟蹋呢?於是溫都爾王便匆匆把索布妲姨媽嫁給了一根套馬杆。從古制,儀式還特別隆重。據說,那貴族少年竟因此遠道而去。有人說他落腳于天南,有人說飛往那地北,從此便渺無蹤影。
王爺嚴禁提到他的名字……
但我並沒有在意這些。王爺曾經饒恕過阿爸的罪,我還得到了王爺賞賜的小雪駒。阿爸說過,王爺對我們有恩,天生就不應該打聽這個。我不打聽,只顧做著那馬背上的夢。但隨著我的長大,還是潛移默化地受著影響。首先我覺得草原變小了,再不是世界的中心了。溫都爾王府也絕非名副其實地高高在上,在它上頭還有著日本人。
只有奴隸還是奴隸……
馬群終於安頓在新的牧場了,我又終於可以跑來見珊丹了。視遠方那耷拉的膏藥旗不見,只想告訴我那兩小無請的小夥伴一個好消息:我的雪駒太神了!昨天在倒場途中遇到一處深澗,我剛想到能飛躍過去該有多好啊!雪駒就一聲嘶叫騰空而起了。白色閃電一般,眨眼便落到了深澗的對面。它完全能捕捉我的每個心思了,將來也完全可以圓了那馬背上的夢!
我要告訴珊丹,絕對用不著嫁給套馬杆!
我早想好了,今年我的雪駒就可以參加一年一度的那達慕盛會了。風馳電掣,我一定會為溫都爾草原奪得第一。王爺也會像上次那樣對我開恩,賞賜我和阿爸成為自由民。第二年我還要為王爺喜上加喜,讓他成為草原上的王中之王。這次我就可以向王爺磕頭求賞了:尊貴的王爺!金銀珠寶我都不要,只求王爺把套馬杆的女兒珊丹賞給我吧!還有給我姨媽自由……
我是帶著這樣的夢到來的。
索布妲姨媽近來在王府當苦役,那破爛的氈包只能就近紮在附近。背水、馱柴、拾幹牛糞,成天疲憊地伺候著王爺和他那同樣肥碩的胖福晉。六年過去了,姨媽仿佛換了個人似的。我也搞不清為什麼她能在牧民中有那麼高的威信,好像大夥兒都很願聽她的。我只知道她很愛我,尤其喜歡看我和珊丹在一起嬉戲。
這其間或許寄寓著她的一個夢……
但這一天卻不一樣,不見了珊丹,索布妲姨媽也似乎只顧得憂心忡忡了。即使見了我和雪駒的到來,也似乎失掉了平常那份驚喜了。只是匆匆吻了吻我的額頭,便又不安地外出去打聽什麼了。四周彌漫著一片神秘的氣氛,使我陡然也緊張起來。
莫非是珊丹也要嫁給套馬杆?
我惶恐極了,當即扔下了雪駒便也去王府四周打聽天哪!沒有這回事兒!原來是小瑪力嘎不久前抓到個特殊的『響馬」,一直被鐵鍊鐐銬鎖在王府的地牢裡。為了進一步討功邀賞,今天就要親自押送給日本警備隊。聽說是在草原邊上的一座老城裡,那兒還有個日本人說了算的什麼什麼「政府」。
我開始替這位好漢擔心……
長大後我才知道,為了肢解中國,這是鬼子裹脅著幾個王爺成立的一個傀儡政權。但王爺們平時均分住在各自的草原上,這裡的一切完全由日本「顧問官」說了算。現在的「顧問官」是原先日本警備隊的頭頭,人們仍習慣地把他稱為豬塚隊長。這傢伙兇殘無比,陰險狡詐,殺人如麻,落在他手裡肯定是有死無生的……但又有什麼辦法呢?似乎我也只能擴大著我臨來時那幻想。如果我的雪駒能現在就爭得第一有多好?那我就可以一併請求王爺說:快去讓小日本放了他吧!他是咱們蒙古族的叢莽好漢……
馬背上的幻想是無窮無盡的!
我回到了索布妲姨媽的蒙古包裡,珊丹還是不見影。但我這回放心多了,只要不嫁給套馬杆就好辦!索布妲姨媽終於又回來了,好像又變得很興奮,還夾雜著幾分不安。這回輪到我安慰她了。我說:
「姨媽!您放心吧!」
「放心什麼?」她一怔,似很驚詫。
「珊丹有我呢!」我一拍胸脯說。
「啊!」姨媽松了一口氣,嗔怪我了,「好大的口氣!」
「不大!」我直截了當地回答,「我還有雪駒呢!」隨之,我便開始向她傾述我那少年騎手的夢。
「傻孩子!」姨媽卻打斷了我,把我緊緊摟在懷裡。
「姨媽!怎麼了?」我不解。
「草原上,」她竟像是在自言自語著,「多會兒才能拔掉那膏藥旗呢?……」
「那有什麼關係?」我多嘴,「聽阿爸說過,王府前頭還插過黃龍旗、五色旗、青天白日旗呢!」
「好糊塗!」姨媽當即戳了一下我的額頭。
「糊塗?」我不服氣,「那有什麼不一樣呢?」
「傻孩子!」姨媽緊緊盯著我的眼睛回答,「插那幾種旗,我們還算得中國人!插膏藥旗,我們就成了亡國奴!」
「亡國奴……」我不大懂。
「記往!」姨媽卻特別強調說,「千萬別忘了:你是中國人!」
「姨媽!」我還是不大明白,只是問,「您今天這是怎麼啦?」
「你要忘了,」姨媽不再解釋了,竟又吻了一下我的額頭說,「長大了,姨媽就不把珊丹嫁給你!」
「我有雪駒,我向王爺去求!」我說。
「可珊丹也不會答應!」她說。
「我記住了還不行嗎?」我竟忘了這是在逗我,馬上連聲喊道,「我是中國人!我是中國人!我是中國人……」
「小聲!」索布妲姨媽趕忙捂緊了我的嘴。
今天這是怎麼了?要知道,姨媽平時只是影影綽綽提示我和珊丹,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鄭重其事。但正因為事出意外,從此「我是中國人」便深深烙在我的心靈深處了。我隱隱約約感到有些蹊蹺,莫非是因為王府大牢內那特殊的「響馬」?潛移默化,我竟對那膏藥旗越來越憎惡了。
索布妲姨媽今天的舉止是有些奇怪……
「敖特納森!」她竟莫名其妙地對我說,「假如姨媽今天出了什麼事兒,你就把珊丹趕快帶到馬群裡去!告訴你阿爸,立刻起場,遊牧到越少人煙的草場越好!」
「為什麼?」我還想打破砂鍋問到底。
「別問這麼多了!」她看了看蒙古包外對我說,「還不快去!今天一大早我就讓珊丹到芒凱老阿奶的羊群那裡去了。在西草灘!」
「西草灘?」有珊丹就令我激動。
我呼喚雪駒了……
我絕想不到這是我決定命運的一天!
是的!絕想不到。少年人對夢幻的追求永遠是執著的,而往往會把複雜多變的現實拋在腦後。當我一跨上雪駒,心裡便又只剩下了對未來憧憬的激動。
王府森嚴的陰影漸漸消失在馬蹄後了……
雪駒仿佛和我一樣渴切見到珊丹,歡快地嘶鳴不已,奔騰起來就像一團輕柔的白雲。眼前又只剩下了初夏的茫茫草原,海海漫漫,無邊無垠,到處都蕩漾著一片新綠。遠處,有幾座白色的蒙古包。極目望去,就像浩浩淼淼的綠色海濤中飛濺的幾朵浪花。
啊!西草灘到了!
我一眼就望到了珊丹,正在翠坡上代老阿奶放牧著羊群。她身穿著一件破舊的蒙古袍,但在一片蔥蘢映襯下卻格外顯眼。一點紅,真是萬綠叢中一點紅。我當即激動地縱馬呼喚了:
「珊丹!我來了……」
果然,她一見我跳下了馬背,眸子便驟然發亮了,睫毛也在輕輕抖動著。臉龐上的紅暈更好看了,手也幾乎要伸出來了。但剛等我要撲過握住時,她卻說:「去!還不規規矩矩坐下……」老毛病又犯了,頓時變成了個小大人兒似的。只便宜了同樣激動著的雪駒,竟任它親昵地聞著。嗅著、伸過嘴巴噅噅地叫著。
真氣人!
「我今天可不是找你玩的!」我說。
「那來幹什麼?」她問。
「姨媽呀——」我故意拉長聲音,「讓我把你載到馬群上,送到好遠好遠的地方去!越沒人煙越好,放到我家的蒙古包裡!」
「幹嗎呀?」她問。
「大概是給我當媳婦吧!」我回答。
「你胡說!」她不高興了。
「真的!」我馬上就舉例說明,「姨媽今天還稀罕地又告訴我,你是中國人!」
「奇怪了……」她自語了。
「怎麼啦?」這回該我問了。
「阿媽她,」珊丹不安地回答,「今天也稀罕地對我這樣說……」
「這大概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件事!」我猜測著。
「說過後,」她說,「就背著人把我送到了芒凱老阿奶這裡,還讓我無論發生什麼事,也不要離開老阿奶,除非是大叔和你偷偷來領……」
「這就對了!」我竟只顧著驕傲了。
「對什麼?」珊丹顯然嫌我不動腦子。
「我有雪駒呀!」我還是惘然無知。
「如果我阿媽出了事?」她怪怨地說。
「我有雪駒呀!」我還是這樣回答。
「雪駒!雪駒!」她不高興了。
「就是嘛!」我開始滔滔不絕給她講述自己那個夢了。
雪駒獨自在翠坡下悠閒地吃草……
女孩子總是柔順的,好像也很滿足於我的突然到來。珊丹開始小模小樣聽我說了,明媚的眸子裡很可能只留下個小猴子亂比畫亂動。但我仍很不自覺,也就更當仁不讓地唾沫星子飛濺起來。
當然,主要的話題還是我那雪駒……
我不但向她講了那個「心靈感應」的飛越深澗的故事,而且重點講述了雪駒不甘落後的強悍野性。真的!只要馬群奔騰起來的時候,它就像霎時著了魔一般,非風掣電閃般跑到最前頭不可。有沒有主人都一樣,絕容不得自己眼前再有任何駿馬。野著呢!烈著呢!身後急驟的馬蹄聲只當是給它擂起了戰鼓。只能拋得再無一點聲息了,它才會猛地躍起前蹄長嘶一聲停了下來。真不愧是遠天借來的種兒,更無愧惡草叢中那烈性的原始野馬。第一!第一!天生就是奪第一的料,絕對是老天降給我的吉祥的哈達!
信心的源泉,成功的保證!
隨之,我便向珊丹公開了我的「兩年計劃」:頭一次那達慕盛會上我將獲得自由,第二次那達慕盛會上我將要求賞人……致使珊丹聽後驚叫了:
「那也不能這麼小就娶媳婦呀!」
「沒關係!」我說,「咱們先過家家玩!」
「過家家玩?」她說。
「對!」我答,「玩膩了,咱們再拿套馬杆子當新郎,我再當專唱喜歌的迎親人!哦……哦……我的嗓子可好呢!」
「你也讓我嫁套馬杆?」她當真了。
「別哭!別哭!真娶你還不成嗎?」我真怕女孩子落淚。
「我不嘛……」她說。
正在此時,卻猛聽得王府方向一片槍聲炸響了,把草原的寧靜霎時炸了個粉碎。我猛地一怔,便本能地把珊丹撲倒了。一同隱伏在茂草叢裡,只顧目瞪口呆地望著遠方。
隨之,便由遠及近傳來了急驟的馬蹄聲!
又是幾聲槍響,還有惡煞煞的呐喊!
煙塵翻滾,近了!近了!
王府追擊的馬隊!
追逐著一個人……
我這時才想起了為雪駒擔心。它正漫步著吃草,悠閒地竟一步一步走遠了,正對著那股席捲而來的煙塵。
槍聲、呐喊聲、馬蹄聲!
更近了!更近了……
但雪駒卻根本對我稚弱的呼喚置之不理,卻似乎反而被那急驟的馬蹄聲深深吸引了。野性勃發,蠢蠢欲動,似就是要和這滾滾煙塵一比高低。只顧揚起前蹄,興奮得噅噅直叫。
一切都來不及了……
說時慢,來時快!就在我焦慮萬分的時刻,那股滾滾的煙塵已經席捲過來了。看得一清二楚,是兇殘狡詐的小瑪力嘎親率馬隊正追擊著一條馬背上的好漢!
小瑪力嘎!又是這個小瑪力嘎!
前頭說過,這傢伙是王府的西協理。如果說過去他和人瑪力嘎被稱為王爺的左膀右臂,現在投靠日本人已可算得一手遮天了。他把王府過去的馬隊都改編成了偽軍,只不該牧民們仍習慣地稱之為「親丁」。而日本人也似乎並不完全買他的賬,除了把精銳的兵員抽走親自掌握外,還把餘下的一半兵權交給了老邁年高的大瑪力嘎。這使他一直深深引以為憾。
至於前面那個被追捕的人?
我看不清楚,他始終垂首俯身在馬背上揚鞭急馳著。只看得出,這也是個駕馭駿馬的好手。緊踏馬橙,身軀仿佛和馬背焊接在了一起。任駿馬的四蹄飛騰,他竟能隨勢起伏紋絲不動。即使在夾雜著呐喊的馬蹄聲中,也顯得臨危不懼,遊刃有餘。
霎時,我幾乎又看呆了……
小瑪力嘎惡吼:「別開槍!給我抓活的!」
親丁們呐喊:「抓活的!抓活的!」
前面,單騎飛馳,似無後顧之憂!
後面,馬隊窮追,果然不開槍了!
驀地,一聲冷槍炸響了!隨之,便是小瑪力嘎陰險而又得意的狂笑!
怎麼?他不是真的要抓活的?
我親眼看到了,他不但打人還向馬開槍!
一個趔趄,那馬便猛地栽倒了,緊接著那馬背上的好漢也被拋落在草灘上。
一個、又一個帶血的翻滾!
完了!完了……
但猛然便聽到一陣不平的噅噅叫聲。雪駒!是我的雪駒!它怎麼還不懂得快快離開?
但為時已晚……
只見那跌落馬背的好漢,聞聲便就勢一串翻滾。帶著傷,但身手仍是那麼矯健。剛剛挨近雪駒,便一躍而起,飛身抓住了銀白的馬鬃,再看,已騰空跨上了馬背。迅雷不及掩耳,只是在驚回首間留下一張永生難忘的面孔。
天哪!這是一張什麼樣的臉?
只見得在一雙鴉翅般的濃眉下,天生一雙鷹隼般的眼。黑黑的絡腮鬍子中,難掩那張剛毅的嘴巴。尤其令人難忘的是,從額頭直至左面頰的刀疤。閃電一般劃過,格外醒目。
稍縱即逝……
他的消失也像閃電一般。又見得雪駒揚起前蹄長嘶一聲,便像在綠海中卷起一道白色波濤似的,向著那更荒、更野、更加充滿原始氣息的遠山奔去了。我知道雪駒那性烈如火的野性於,它正巴不得有機會一試蹄腿呢!
顯然,小瑪力嘎也和我們一樣驚呆了……
但那僅僅也是片刻!一聲惡狠狠的「追」!槍聲、呐喊聲、馬蹄聲便又急驟地響了起來。追著那小白點兒,朝著那遠山,排成了扇形馬陣包剿了過去。
只留下了滾滾煙塵。
隱去了我的馬,
我的雪駒……
驀地,我恍若驚醒了。伸著雙臂、發狂似的就要追下翠崗。
是誰拉住了我?
猛回頭,芒凱老阿奶。
她說:「雪駒是在為你行善積德!」
什麼……
偶然,純屬偶然。
後代的一些回憶錄裡,把這一幕描述為精心的安排。不!作為一個當事者我完全可以證明:純屬偶然!
但每一個偶然都可以徹底改變一個人的命運,這卻是無可懷疑的。
這一天啊!這一天……
現在回想起來,如果這一天我不意外地遇到所發生的這一切,命運展現在我眼前的很可能是另外一條路:雪駒很可能年年奪得第一,我很可能成為最出色的御用騎手,珊丹也很可能成為溫都爾王獎賞給我的妻子……
但是結果呢?
要知道,騎手、射手、摔跤手,大多沒有什麼好結果。稍有閃失,很快就被拋棄遺忘了。更可怕的是,在王爺們的明爭暗鬥中,他們往往首當其衝成了犧牲品。說到命運最好的,也頂多重新淪落為一個逆來順受的牧人。
但在當時,我卻只能看到榮耀……
我失掉了朝夕相處四年的雪駒,只覺得馬背上的希望霎時都化為泡影了。但任我百般掙扎,我還是被芒凱老阿奶拉回她那破爛的蒙古包裡了。絕不是因為老人家力氣大,要知道珊丹眸子裡溢出的淚水就像根柔情的繩子似的。
我萬般無奈,我不知如何是好……
誰料,暫時失掉了雪駒,我卻得到了個馬背好漢的傳奇故事。原來,他就是被小瑪力嘎押在地牢內那特殊的「響馬」!率領著一批馬上健兒,常年出沒於遠山深處那原始叢莽中。絕不打家劫舍,卻專和日本人作對。隨著抗戰進入第七個年頭,他們已打得鬼子龜縮在據點不太敢恣意妄為了。為了擴大影響,為了爭取上層,他們竟神出鬼沒地在溫都爾王府門頭公然刷下一行大字:別忘了!你也是中國人!王爺嚇得進退兩難,這才有了小瑪力嘎設計誘騙前來「談判」之舉。不是不知道暗藏詭詐,只是為給王爺宣傳抗日還是大義凜然來了。對這次舉動,後來是有不同評價。有些人甚至談到了好漢們豪放質樸和幼稚。但當時確是滔滔不絕,句句是理,只說得在王爺身旁笑口常開的乃登喇嘛都落淚了。誰料,小瑪力嘎早私下串通了日本警備隊,酒宴上竟突然擲杯為號。據說,就連王爺和大瑪力嘎當時也驚得目瞪口呆,但這條好漢還是落入魔爪了。
為了讓茫茫的草原上響徹一個真理……
我似乎突然明白了,索布妲姨媽今天稀罕提到的:我是中國人!很可能就是那地牢裡不屈的聲音在牧人間的回蕩。至於這位好漢是怎樣臨危脫逃的,傳說頗多,也仿佛不僅僅是姨媽一個人為他不安,為他興奮,為他激動!聽說,僅就大牢旁倒在血泊中的那個獄卒,自殺?他殺?尚難有定論。但那面帶冷笑的神情,卻頗有點好漢做事好漢當的氣魄。出力者肯定不是一個,就不該線兒至此也斷了。總之,好像日本人那「以夷制夷」的美夢徹底破滅了。雖然說有幾個日本兵還穿著蒙古袍冒充王府的親兵,但還是讓他神秘地逃脫了!致使「顧問官」豬塚隊長聞訊趕到,竟在王府內揮臂惡吼:「蒙古人的心通通的壞了!大大的壞了!」
我當時尚不知道……
「孩子!」但老阿奶卻對我說,「你的雪駒是在為你行善積德!」
「阿媽也會高興的!」珊丹也說。
「可我的馬?」我仍很遺憾。
「真正的好馬,」老阿奶安慰我,「就是跑到天邊也不會忘記主人的。老年間,咱們草原有一匹棗騮馬作為貢物被送到了北京。那有多老遠呀!可它硬是躍過宮牆翻山越嶺回到了咱們這片草地。瘦得只剩下一把骨頭了,為的就是能回來見到舊日放牧它長大的牧馬人!」
「你的雪駒呢?」珊丹也馬上問。
「我的雪駒……」天哪!我怎麼忘了我的雪駒不但是匹野性子馬,而且也是一匹特別有良心的馬!要知道,它仿佛深得那灰色母馬的遺傳。犯倔、高傲,也常常離群孤芳自賞。和它那母親一樣,似乎也在時時等待著蠻荒深處的野性呼喚。兩歲那年,它竟像著了魔一般尋著那無聲的呼喚走了。整整三天不見蹤影。我對阿爸說:
「快套住它!抓住它!拴住它!絆住它!圍住它!關住它!」阿爸回答我說:「沒用!收得住籠頭收不住心,真正的馴馬手從不把駿馬當畜生,朋友!是朋友!」雖然後來阿爸對雪駒的態度漸漸變了,但從此我卻像突然明白了什麼,雪駒也好像漸漸明白了什麼。它無論追蹤著蠻荒的氣息走得再遠,只要我的內心為它一動,它准會驟然噅噅歡叫著神奇地出現在我眼前。
「那你試試!」珊丹聽後立即對我說。
「不能!」老阿奶慌忙阻攔說,「就讓它行善行到底,積德積到家!」
「讓誰?」門外傳來了問話聲。
「阿媽!」珊丹迎著聲音歡呼了。
「姨媽!」我也像有許多話要說。
「讓誰?」老阿奶迎進了索布妲姨媽,說,「還不是敖特納森那匹好雪駒!」
「我都聽說了!」姨媽一下便把我攬進懷內,激動地親著吻著。
「是我的阿媽!」珊丹嫉妒了。
「氣死你!氣死你!」我偏偏要占著姨媽的懷。
「不!我就不!」珊丹也鑽了過來。
「瞧瞧!」姨媽只能一邊摟一個,甜蜜地歎著氣對老阿奶說。
「長大了,」老阿奶卻在搖頭,「就不會這樣爭你了!」
「爭誰?」姨媽故意問。
「誰也不爭!」老阿奶笑了,「小兩口只顧著頭頂頭說私房話呢!」
「呵呵!」索布妲姨媽笑著把我倆摟得更緊了。
「我才不理他呢!」珊丹說。
「我理!」我竟一點也不害臊。
「呵呵!」大人們笑得更加歡暢了。
破舊的蒙古包裡,絕對少有的。
我沉浸在一片甜甜的溫馨中。
暫時忘了我的雪駒。
眼前只有珊丹,
沒有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