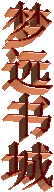
將軍鎮 第十二章 哈巴癩痢
一
李芙蓉從小鎮調到縣上之後,接替她當鎮長的是個從外地調來的癩痢。鎮上的幹部們就有情緒,私下不叫他「鎮長」,叫他「哈巴癩痢」。「哈巴」同癩痢連著,不是乖巧,而是戇和霸蠻的意思。
當時的鎮革委會是很革命的,就在鎮口的大路邊上,先前是李八碗李氏宗族的祠堂,多年失修,破爛不堪,四牆裂了縫,已經歪斜了,屋頭上長了草,衰敗成灰色。祠堂改成辦公室後開的窗子上,沒有玻璃,蒙在上面的是包裝化肥的透明塑料袋。「文革」時候才在滿牆刷了紅漆黃漆,不是為了維護屋子,是為了寫語錄。紅紅黃黃的顏色像在一張蒼老的臉上化妝,不僅是難看,簡直是猙獰。屋子裡幾乎沒有一樣完整的東西,桌子要互相靠著才放得穩,椅子要靠了牆才敢坐,會計的算盤和圓珠筆上都包紮著醫院用的膠布。鎮上原本就窮,再經了幾年革命洗禮就更清白了。不過,再窮也有窮開心的法子。哈巴癩痢到小鎮上任,開第一次鎮革委領導班子會,就領教了這開心。
鄉鎮上從來沒有按時開會這一說。人總是先先後後參差不齊。等人的時候,先到的人就講笑話打發時間。領導幹部又主要講的是跟領導幹部有關的笑話;上級來了一位領導,大會上作報告,首先宣佈來意:「我這回,是專門來搞婦女,」頓一下,才說「計劃生育工作的」。接下來就自謙,「我是個大老粗,有多粗呢?你們婦女主任知道,昨天晚上,我跟她摸了一下,一直摸到下半夜……」等等。在這類笑話裡,開心的對象總少不了婦女主任。說多了,就覺得是老套子,沒有新意。這一天,有人出了個點子,對另一個人說,我們莫總是圖嘴巴皮子快活。今天不來素的,要來就來點葷的。你平日跟婦女主任眉來眼去,今天敢不敢當大家的面,在她胸口抓一把,也給我們開個眼界。
大家就起哄,一致說:「好!」一片山響,如同誓師。
婦女主任是六八屆下來的知青,很積極能幹。下來不到一年就入了党,成了知青模範。鎮革委籌辦婦代會時被抽上來,以後就留下來當了新生的婦代會主任。鎮上的知青有「五朵金花」,最好看的兩朵都進了鎮革委。一朵是鎮廣播站的播音員;一朵就是這婦女主任。婦女主任是工農兵型的,很豐滿壯實,胸脯特別高,讓許多人垂涎。
被提議的那另一位是鎮革委副主任(也就是副鎮長),婦女主任就是由他發現推薦上來的,兩人的關係自然也就不一般。私底下有人問他跟婦女主任是不是有事,他總是反問:你看呢?分明是得了手的神氣。只是大家還沒有看到公開的證明。
婦女主任總是最後一個到會。一是因為來早了,會讓這些臭男人沒頭沒腦地打趣;二是因為當了幹部,又碰到場面上的事,一個女人上下總要收拾得光鮮些。那天她穿了件短袖衫,那衫子很薄,其實遮掩不住什麼,裡面肉色的胸罩遠遠看起來跟沒戴一樣(這其實是鎮上人的看法,婦女主任的穿著還是很得體的,只是因為帶著些城裡人的趣味,鎮上人覺得有些惹眼就是)。
婦女主任高聳著那似乎沒有戴胸罩的胸脯,大踏步地走進來。她走路的步伐和聲響,跟她說話做事一樣,都是很轟動很壯烈的。相反屋子裡倒是顯出格外的安靜。一向高聲大氣的男人們都凝了神,似乎在深思國家和世界的前途。這使婦女主任有些意外,有些奇怪,又有些洩氣。回回她總是最招人注意的,這回卻遭了冷落。
「出什麼事了麼?」
她不由得放輕了腳步,走到副鎮長身邊推推他的肩。
先前悶頭抽煙的副鎮長慢慢地把吸剩的煙頭在一塊西瓜皮裡撳滅,忽然一扭頭,伸出那只粘著瓜汁的手,一把抓住了婦女主任的一隻乳房。
屋子轟地一聲像是突然坍塌了。先前一個個做出深沉樣子的男人們一齊爆發出哄笑,有人笑岔了氣,連同椅子一起仰翻在地上。
婦女主任並不示弱,劈頭蓋臉地同副鎮長揪打起來,一片「死鬼、畜牲」地亂罵,臉漲得通紅。但聽起來,只有三分惱怒,卻有七分快活。
終於平靜下來,副鎮長宣佈開會。鎮上先前的鎮長李芙蓉調走了,一直由副鎮長主持工作。
副鎮長原以為自己這回填鎮長的空是沒有疑義的,沒有想到縣裡又派了新鎮長來。
「今天的會,就是歡迎新鎮長。」
副鎮長懶洋洋地說,瞟了一眼在對面角落裡坐著的一個人,又懶洋洋地舉起手帶頭拍巴掌。好像他剛剛想起來屋子裡還坐了一個鎮長。底下的巴掌跟著響了幾聲,稀稀拉拉也是懶洋洋的。副鎮長是本鎮人,從讀書到工作,一直沒有離開鎮子。鎮政府裡也大都是跟他一起共事或由他提拔起來的熟人,大家都看他的眼色行事。在他上面,鎮長換了好幾位,都呆不長。但是上面也絕,寧可走馬燈似的換人,就是不給他轉正。他也就立了志鬥法。縣裡要調他走,他就是不走。又抓不到什麼大錯,他在上面也有幫忙說話的,就這樣僵持著。對這一回新來的鎮長,他自然也是不在乎的了。
新來的鎮長不但沒有可以讓人在乎的地方,反而是很讓人看不上眼的。一個疤痕累累的癩痢頭——那疤痕顯然是剃頭佬的傑作,粉紅間以灰白。這累累瘡疤之間,偶有幾綹稀毛,像沙漠上的草。臉很黑,滿是粗糙的皺紋和紫色的小瘤子。這樣一個人來做鎮長,實在是對全鎮的一種蔑視。
這歡迎會,不過是個例行公事,顯示副鎮長大度。因此他們該說什麼說什麼,該做什麼做什麼,全然不顧及新來的鎮長會有什麼態度。哈巴癩痢也一直安然地笑著,帶著一種憨憨的新奇看著眾人。眾人笑,他也跟著笑。眾人笑完了,他也就不笑,只不說話。等到副鎮長宣佈了請他說話,他才開口。
他說他今天並不是頭一回到鎮上來。縣裡決定調他到鎮上來之後,他已經在鎮上各處轉過幾回,鎮上七七八八的情況,他是曉得一些的。
他的話一出口,大家就聽出他的中氣很足,嗓門也大,只是他克制著。他的話聽起來很和緩,但其實很硬紮,沒有一句客套,也沒有一點要請教的意思,甚至沒有一點隱諱:「今天的會不必開長。這樣的會開長了也沒有意思,歡迎不歡迎我反正都得來。我看這樣,辦公室下個通知,開個兩級幹部會,把全鎮下屬各單位的負責人都集中到鎮裡來,鎮革委所有負責人都參加。報到時間就定在下個星期一。」
哈巴癩痢說完就宣佈散會,隨即就起身走出會議室。既沒有問副鎮長有沒有什麼補充,更沒有徵求任何人的意見。會議從正式開始到結束,前後不到十分鐘。
其他的人一時呆在座位上沒有動。大家面面相覷,覺得這回有點「來者不善」。有道是「十個癩痢九個哈(音ha)」,這回恐怕是遇上一個難剃的癩痢頭了。
副鎮長臉色鐵青。跟鎮長的這頭一回交手,他明顯是輸了。哈巴癩痢毫不客氣輕易地就把會議的主動權奪了過去,等於把他晾在那裡。末了他冷冷地一笑,他對自己在鎮上的絕對地位還是有信心的。
哈巴癩痢第二天上班就坐在鎮革委辦公室,一直看著辦公室主任把會議通知起草,油印出來,又分裝信封郵寄出去。然後又吩咐要一個一個打電話,保證不能缺漏一個人。電話要做記錄,他回頭要核實的。
二
又是公函,又是電話,應到的人全部到齊。其實不這樣,人也到得齊的,除非哪個遭了天災人禍。鄉鎮幹部指望開這類會,就像伢兒指望過年,說的就是:口裡沒有味,開個幹部會。
但這一回副鎮長卻有了別的心思。會議後勤,由他具體負責。他通知辦公室主任,新鎮長來了,要有新的作風,開革命化的會,會議伙食按最低標準辦。以往都是在財務規定的範圍外再增加一筆開支。這筆開支跟規定的經費比,是大頭,出處最後都分攤給下屬各個單位。各單位的頭都來了,分享了這開支的結果,他們都很樂意,因為理由很正當。副鎮長這回不增加這筆開支的理由也很正當。辦公室主任心領神會,但心裡有些打鼓:副鎮長這一手很絕,明擺著是要坍新鎮長的台,卻讓你恨得想咬他也找不到地方下牙了。
哈巴癩痢聽彙報的時候卻說,要得,就要這樣。聽口氣不像是反話,倒似乎是正中下懷。哈巴癩痢後來又讓把租用的客棧退掉,把鎮革委的辦公室都騰出來鋪上乾草,讓參加會的人全部打地鋪睡在這個老祠堂裡。廂房不夠,哈巴癩痢自己帶了鎮革委機關的幹部就睡在堂屋裡。好在這祠堂有些規模,參加會的連工作人員一起不足半百,勉強擠得下,只是吃和拉有些問題。祠堂做了鎮革委機關後,在屋後加個院子,建了食堂和廁所。先前主要是供機關的人使用,現在一下子加了許多人,自然就難以滿足需要。鎮長說,革命化麼,就化徹底些。這樣的困難有什麼大不了的,尿就滋在牆腳上,拉屎和吃飯,分批。凡事婦女優先。
大家覺得新鮮,倒沒有幾個有怨言。報到的當天夜裡,一屋子男女嘻嘻哈哈,葷的素的,笑話不斷。
第二天起來大家都變了臉色。不曉得從何時起,祠堂外布了崗哨,背了真槍實彈的民兵,不准一個人出進。屋子裡的幾隻搖把電話也都搖不出聲音,明顯是有意切斷了線。大家你看我,我看你,不曉得出了什麼事。正要鬧,哈巴癩痢一下從什麼地方站出來(他夜裡不曉得什麼時候出了祠堂),身後跟了兩個武高武大的帶槍民兵。他清了清喉嚨,壓低了聲音說,大家不要亂,哪個作亂莫怪我不客氣。老子今日就是來專政的。你們這班傢伙,共產黨叫你們當幹部,你們一件好事不做,不是執灰就是弄烏。把男人轟出去上水利,自己就去操人家老婆女兒。鎮上我是來了些時候的,你們各人做的好事一樁也瞞不過我。這回我讓你們自己交待,老實交待了沒有事。哪個要打埋伏,我拆他的骨頭。現在都去吃早飯,吃完了,回到各人鋪上寫交待。交待一個出去一個。一日不交待,一日不准出這祠堂門;一輩子不交待,我就讓他坐穿牢底。莫想帶口信,莫想串供。兩裡路外我就派了崗,除了雀子跟老鼠,哪個也過不來。
這些年,大家什麼莫名其妙的事沒有見過做過。自己對別人做得,別人也就對自己做得。理是沒有講頭的,哈巴癩痢將來時,大家就聽說是有些來頭的。倒不是做了什麼驚天動地的事業,是因為縣革委主任看重他。
縣革委主任是「三結合」後從軍管部隊留下的,又是剛成立的省革委主任的直接下級。說是說強龍不壓地頭蛇,但也還有一句話:「好漢不吃眼前虧。」
不滿三天,大多數人都寫出了交待。那三天裡頭,整個祠堂裡死氣沉沉。哈巴癩痢派了民兵,輪流在各人的鋪前來回巡視。堂屋和廂房裡只有一片輕輕的翻動引起的禾草的窸窣聲和筆尖在紙上的劃拉聲,偶爾夾雜著一兩聲咳嗽和歎息。有人放屁引起了嗤笑,但立即就止住了口。夜裡,才有人做惡夢,從地鋪上跳起來,鬼哭狼嚎。值夜的民兵,嘩嘩地拉動槍栓,又壓抑下去。
白天,哈巴癩痢在食堂的倉庫裡清出個角落,等著一個接一個來送交待的人。他不看,讓交待的人自己念。他閉起眼睛聽。那個人念完了,他才睜開眼,說:「行,材料放在這裡。你可以回去聽候處理。」三天后,祠堂裡只剩下鎮革委機關本身的幾個人。副鎮長一直咬緊牙,黑了臉,仰在自己的地鋪上用無言表示最高的輕蔑。婦女主任和辦公室主任也都沒有動靜。鎮長並不跟他們打照面。到第四天上午,他讓民兵把婦女主任帶到食堂倉庫裡來。好長時間,他一言不發,一心閉著眼睛。婦女主任則隔了桌子坐在他對面,低頭撚自己的衣角。這幾天她也沒有認真梳洗,披頭散髮,面色蠟黃。先前的風騷勁一點看不到,像一棵霜打的菜。
哈巴癩痢終於開口,說:「別的我都不想問,只問你一件事,有一回你開婦女會,講計劃生育,動員大家上環,有人擔心上環出事,難受,你說,你就上了環,一點事沒有。你一個大閨女,上環做什麼?」婦女主任抬起頭,愣愣地看了一會鎮長,忽然「哇」地一下哭起來。這幾天,因為副鎮長的頑抗,她也一直硬撐著。現在,她實在撐不住了。
婦女主任隨後就交待了自己的錯誤事實。鎮革委沒有幹部宿舍,家不在鎮上的幹部要在鎮上過夜就睡辦公室。婦女主任沒有成家,就只有住在鎮婦聯辦公室。在床鋪和辦公桌中間掛張簾子。副鎮長的家在鎮下面的生產大隊。他平時很少回去,也在自己辦公室搭了一張床。逢到別的幹部都不在的時候,他把祠堂大門一關,同婦女主任就做成了夫妻。婦女主任起先不肯,到底受了他的培養,卻不過情分。他說,這是對她最好的再教育……
哈巴癩痢打斷她的哽咽,說:「你不必講那麼細。不要前言也不要後語,把剛才講的這段寫下來就行。」
婦女主任剛出門,辦公室主任一頭撞了進來。他已經在門外等了多時。他兩隻腳索索抖著幾乎要跪。哈巴癩痢讓他坐,他坐了幾次也沒有坐穩,屁股老是不得落實。他牙齒「格格」地打著戰,結結巴巴地求鎮長高抬貴手。他說他膽子小,做不成什麼事情。年輕時冒失過一回,到如今一想起來就心驚肉跳。他把那次冒失寫在了紙上,作為交待:那時候他剛到鎮上,做民政工作。有一回,一對在他手上打了結婚證的新婚夫婦來找他,說是圓房三天了,就是成不了事。那時正是正月裡,鎮政府很多人都沒有來上班。中午他在鎮上的一個親戚家裡喝了很多酒,膽子正是麻的。他就突然心血來潮,對那男的說,你在這裡等著,我給你老婆檢查一下,就帶了那女的進了自己的宿舍。那時候的人百分之百的相信政府幹部。相信幹部,也就是相信政府;相信政府,也就要相信幹部。那男的也就老老實實地等。那女的也就老老實實地讓他檢查。他檢查的辦法很實在,就是把那事做一遍,算是試驗。試驗結束,他大汗淋漓地把那女的帶到男的面前,說,沒有問題,通了。過了一個月,夫妻二人居然帶了禮來謝他,說是他們那回一回去就果真成了事,現在懷上了。他漲紅了臉不敢看他們。他是罪該萬死,利用了革命群眾對政府的信任,應該讓革命群眾打翻在地,踏上一千隻腳,一萬隻腳。
哈巴癩痢耐心地聽辦公室主任念完了自己的交待,睜開眼睛,沒有像對待先前的那些人那樣讓他把交待留在桌上,倒是隔著桌子,伸手把辦公室主任手上的那疊紙接過來,扇扇子似地搖了搖,然後拿過桌上的打火機,點著了那疊紙。火舌沿著那疊紙的下角往上舔,一片一片燃燒後的碎屑蟲子似地飛起來。一直到快要燒到手指了,他才鬆手。又看著那點紙屑燒完,收縮成一團,打了個旋飄起,才抬起頭,對辦公室主任說:「這件事就到此為止。」
辦公室主任一直驚恐地睜大的眼睛裡淚水一下湧出來,一直想跪沒有跪成,現在「咚」的一下跪了個扎實。
哈巴癩痢笑了笑,說:「行了。以後注意,要跟路線,不要跟人。」
辦公室主任說:「我曉得的,曉得的。你就是路線。」
以後的日子,哈巴癩痢就帶了那一摞交待一個單位一個單位去落實處理。自然並不是每個單位的負責人都有偷雞摸狗的劣跡,但這些人也都搜腸刮肚地寫了些平時吆五喝六,好吃懶做的事來湊成交待,鬥私批修總之很徹底,只求儘早出那祠堂門。鎮長一津拿了對付辦公室主任的方法如法炮製,當了各人的面燒了各人的材料。他說,他要看的是各人的態度,各人今後的工作。至於過去的賬,一筆勾銷了。
但有一個人,他沒有放過。他把婦女主任的交待作為揭發報到縣革委。全國上下都正在落實新發佈的最高指示,檢查知青工作,就等著要一個典型。副鎮長剛好撞到槍口上,問了個姦污女知青的罪,抓起來判了重刑。依縣革委主任的意思,要殺頭的。好歹副鎮長在縣裡有些根基,許多人冒險說情,才保住性命。
婦女主任自然在鎮上呆不住,回城去找了個工人下嫁,隨後就調去了丈夫的那個燒磚瓦的工廠。
三
然後是哈巴癩痢一生中最輝煌的一段日子。
省革委主任是個極有雄心也極有膽略的人,抓工業抓農業都有許多驚世駭俗的創造。哈巴癩痢的真正發跡,就得力于把這創造部分地變為了現實。為了貫徹落實省革委主任「大搞八字頭上一口塘」的戰略部署,哈巴癩痢召開了全鎮大搞八字頭上一口塘動員大會。哈巴癩痢說,搞不搞是態度問題,搞成了什麼樣,是水平問題。沒有山,建不了塘,機耕道總可以修的,新村總可以建的。
一散會,就讓人按事先畫好的機耕道,新村規劃圖打石灰線。線一打出來,就讓人動手,邊拆舊屋,邊做新屋。那個農業大隊一時雞飛狗跳,煙塵滾滾。卻有一個村子沒有動靜。這個村子還恰恰緊挨著規劃圖上的機耕道,是非拆不可的。
這村人所以這樣膽大,不怕做反革命,是因為一個寡婦做了他們的盾牌。這寡婦的屋子立在這村子的最前沿,而且壓著那條按規劃圖打出的石灰線。寡婦是新寡,男人害病,沒有錢住醫院,在家裡拖了幾個月死了,給寡婦留下了六個兒子,最小的還在懷裡吃奶,最大的剛剛挑起一擔糞。
哈巴癩痢聽說居然有人敢對抗,便帶上民兵跑了來。寡婦面對氣勢洶洶的鎮長和把槍端在手上的民兵,全無懼色。幾個兒子都擠在她身邊。她一手摟著吃奶的兒子,一手擋定了自己的屋門,說,橫直是死,你們有種就把老娘一家人連屋子一起拆!
一村子男女都圍上來,看哈巴癩痢怎樣唱這台戲。
哈巴癩痢的癩痢頭漲得通紅,眼角很有力地彎下來,射出凶光。
「真不走?」
「不走!」
「還是走吧。」
「不!」
「那就怪不得我了。」
哈巴癩痢咬了咬牙,後退一步,示意民兵上前。幾個民兵圍上去,把寡婦一家一個一個的從屋門口扯開。寡婦一家人殺豬似地嚎叫起來,罵聲哭聲驚天動地。寡婦滿地打滾,「畜牲」「癩痢」罵個不休。圍觀的人中,幾個年輕的血性湧上來,齜牙咧嘴地想要衝出來排命。哈巴癩痢喝道:哪個敢動,動就開槍!年紀大些的趕快靠攏把幾個年輕人擋了起來。哈巴癩痢回頭,向一台早已停在那裡待命的拖拉機揮了揮手。
馬力很大的「東方紅」轟轟地冒著黑煙,履帶沉悶地格拉格拉響著,好像是從每個人的胸口軋過。寡婦的那幢茅草蓋頂的土坯屋幾乎聽不見聲音就塌成了一堆土。
一村人一轟而散,曉得是再沒理可講了,都回去搶自家的東西。想讓一個哈巴癩痢發善心,除非日頭從西邊出來。
哈巴癩痢並沒有讓拖拉機繼續推下去。他對生產隊長說,去,叫他們莫慌,不作對就行了。先去清新村的地基。
寡婦一家人則被關在生產隊的倉庫裡。寡婦已經聲咽氣短,依舊掙扎著要尋死覓活。哈巴癩痢讓人把她的手腳捆住,系牛一樣系在柱子上。跟寡婦一樣捆住的,還有她那個可以擔起一擔糞的大兒子。
先是組織全縣各公社負責人到小鎮來開了現場會。縣革委主任把這裡的經驗總結後又專門報告了當省革委主任的老首長,引起了老首長的極大興趣。接著又在小鎮開了全省的建新村現場會。省革委主任帶了隨員、記者以及全省各縣的革委會主任浩浩蕩蕩幾百人到小鎮來,把鎮裡鎮外壓得塌了三寸。哈巴癩痢先是成了省勞模接著又成了全國勞模。省報和全國的大報都登了他的大幅照片。那顆疙裡疙瘩的癩痢頭經過很巧妙的洗印處理,竟反而有了幾分藝術效果。
但這回的現場會差點惹出大禍。
四
原說是視察了新村、在現場會開始時作完指示就到市里去的,但講話的時候,話筒突然沒有了聲音。省革委主任摜下話筒,回頭就要發作。正在主席臺後側照應擴音器的鎮廣播站播音員趕緊跑出來,抓過話筒拍了幾下,仍是沒有動靜。她很尷尬,一時慌了手腳。整個會場的氣氛也一下僵住,似乎是等待著一場戰爭的爆發。
省革委主任的臉色卻不知為什麼重又容光煥發起來。他和顏悅色地對可憐巴巴的播音員說,小鬼,下去吧,我講話本來不需要擴音的。接著他就大了聲講起話來,並且越講越有興致,幽默風趣,妙語連珠,不時引起滿場的笑聲和鼓掌。
吃過飯,省革委主任竟不走了,對哈巴癩痢說,讓廣播站的那個小鬼來,我想跟她談談。
讓人敬畏的省革委主任在位不久,全省各級領導就曉得了他的一個極有個性的嗜好,就是每到一處就要找些好看的女孩子進行革命教育。他雖然年過半百,但精力旺盛得嚇人,白天不論怎樣辛苦勞碌,這教育還是要通宵達旦的,一點不知疲倦。他抓這教育同他抓革命、促生產一樣都是極有魄力的。就有了種種傳言,就是省革委主任到了哪裡,哪裡的母雞都要趕緊穿褲子。都說這是階級敵人用心險惡的攻擊,但私底下大家都把這險惡的攻擊一遍又一遍用心不險惡地重複,還加了一個形象的描繪,說是「大搞八字頭上一口塘」。
哈巴癩痢說,那太好了。省革委主任要在小鎮過夜,要對播音員進行革命教育,無疑是小鎮廣大革命幹部和革命人民最大的光榮,最大的幸福。我馬上去作安排。哈巴癩痢欣欣然、躍躍然。
然後他就陀螺一樣在鎮革委的院裡院外轉起來。收拾省革委主任一行過夜的房子和床鋪;吩咐準備保衛省革委主任一行的民兵崗哨……省革委主任很感動地說,你歇著吧,忙活一天了,把那小鬼給我叫來就行啦。
「好的,就來了。」
哈巴癩痢一邊雷厲風行地調度,一邊幹練地應諾。
但是哈巴癩痢再次出現在省革委主任面前的時候,仍是一個人。
「小鬼呢?」
省革委主任顯然有些不悅了。他迫不及待要做一個女孩子的工作,結果卻老是這麼一隻可惡的癩痢頭在他面前進進出出。常常有這樣的情況,許多下級幹部以為只要自己忠心耿耿,盡心盡責就能討上級領導喜歡,卻因為總是搔不到領導的癢處,使得種種殷勤,種種辛苦都成為一場白忙。更嚴重的甚至招致了領導的怨恨。因為領導的有些意圖是要靠下級去領會而不便明確指示的。一個下級幹部乖巧不乖巧,能幹不能幹,要害和標誌常常就在這裡。
哈巴癩痢自然不是不乖巧、不能幹的人,只是這一回,他實在無能為力;他去找鎮廣播站播音員的時候,才聽說,僅僅在約五分鐘前,播音員搭了一輛拉貨的便車,匆匆趕去了城裡搭火車。當時她剛剛接到從上海老家打來的電報,祖母病危,讓她速歸。她甚至來不及向鎮長當面請假,寫了張假條連同電報一起讓人帶給鎮長,就哭哭啼啼地跑到公路上搭車去了。
哈巴癩痢現在帶來的,就是這張電報。他請示省革委主任要不要過目。那上面還留著一個上海女孩子到什麼時候什麼地方也免不了要用的護膚脂的溫柔氣息。
省革委主任銳利的眼睛靜靜地看了一會哈巴癩痢,什麼話也沒有說,徑直從哈巴癩痢身邊走過,走到門外,喊了一聲什麼人,就逕自走到了鎮革委的院子裡。
幾輛從省城開來的吉普車很快就轟轟地吼起來,雪白刺眼的車燈橫掃著鎮革委的院子。隨後車隊就向鎮外的黑暗風馳電掣般地撲去。
被省革委主任拋下的鎮革委的一院子人都呆了,弄不清省革委主任為什麼忽然作了戰略轉移。來的時候轟轟烈烈,小鎮一時間福星高照;走的時候陰陰森森,小鎮似乎要大難臨頭。這樣的跌宕起伏,反差實在是太大太猛了。小鎮人見的世面、經的事少,受不得這樣的驚嚇。
哈巴癩痢倒是很安然。說,首長就是這樣火爆的性格,工作作風一向潑辣,這在全國都是很有名的。真要有什麼事也是我擔著,沒有你們的事,各人回去吧。
後來果然也真沒有什麼事。哈巴癩痢和小鎮依舊是全省的先進典型,上了《全省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偉大勝利成果三百例》。哈巴癩痢後來還是依舊多次出席了全省、全國的各種表彰會、講用會、經驗交流會。省革委主任也沒有因為那天晚上的事對他生出什麼隔閡。證明是,哈巴癩痢後來還特地從省城帶了一張省革委主任在一次會議上單獨接見並同他親切交談的合影的放大照片回來。那照片用鏡框鑲了,掛在鎮革委會議室領袖像的下邊。不過,再後來,這又成為哈巴癩痢上了反黨賊船的鐵證。
哈巴癩痢的輝煌很短促,像掃帚星劃過小鎮的天空。
先是中央的副統帥,接著是省革委主任,接著是縣革委主任,接著是哈巴癩痢,一個一個地被押上歷史的審判台。就像他們當初理直氣壯地把別人押上歷史的審判台一樣。據說,他們竟是串通好了謀反的。省革委主任大搞八字頭上一口塘,是戰略工事的一部分。他那回來小鎮,主要是來看地形的,計劃在小鎮修一個地下指揮所。那天晚上說住下又突然撤走,就是為了保密。總之事情很嚴峻,很可怕。大家這才曉得,一個哈巴癩痢當初能那麼不可一世,原來竟有這樣的背景,也就激起大家無比的痛恨,聲討起來一個個義憤填膺。
但哈巴癩痢卻滿不在乎,開批鬥會的時候,他依舊像先前做鎮長時一樣神氣活現。
一上臺,他跪下一條腿,另一條腿伸著,兩條手臂平展著。主持人喊:「你起來,我們不搞體罰。」他說:「我自己罰自己,跟你沒有關係。」主持人說:「你這樣子是什麼意思?」他說:「你這還看不出來?我沒有文化的都認得:一個頭,兩隻耳朵,平伸兩隻手,伸條腿,跪條腿,這不是個『光』字麼。不過不是光榮的『光』,是光卵一條繩的『光』,如今我光卵一條繩,什麼都不是了,甘心情願接受批鬥。」大家聽了,又看他怪模怪樣,想笑又不敢笑,就開始揭批。
鎮食品站的站長黃帽子上去說:「你當個鎮長,專搞特殊化,回回買肉,精的不要,肥的不要,專要豬頭肉。鎮上一個月才供應幾頭豬?一頭豬有幾兩豬頭肉?你回回只要豬頭肉,別個吃什麼?要是讓你這樣的人篡黨奪權的陰謀得逞,勞動人民不重吃二遍苦,重受二茬罪,才怪呢。」說著狠狠地跺腳,高呼:「我們是一千個不答應,一萬個不答應!」
在台角上的哈巴癩痢疑疑惑惑地瞟了瞟黃帽子,說:「你是表揚我還是揭批我啊?世上哪有不吃精不吃肥只吃豬頭肉的人?我是窮得沒有法子啊。你要喜歡,二回我拿豬頭肉跟你換精肉肥肉,你只莫加收我的錢就是。免得你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黃帽子給他說得噎住,一時不曉得怎樣回復。主持人就及時地喊:「下一個上來。注意,這是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要說大是大非問題,敵我矛盾問題。」
「我來!」
下面一個人奮勇地應了一聲,挺身而出。是鎮革委辦公室主任。
辦公室主任先前是跟哈巴癩痢跟得最緊的一個。大家人前人後叫他做「鎮長的吊刀」。他並不惱火,反而樂意,說是「跟路線」,一臉的自豪。哈巴癩痢也是少不得他的。哈巴癩痢走到哪裡都喜歡講話,講話便少不得稿子,稿子都是由辦公室主任寫。寫得好不好,主要就看厚不厚。拿到手上,先掂掂分量,再看看頁碼,好幾十頁,就說要得。
但是,其實再短的稿子哈巴癩痢也念不完的。他放牛放到十幾歲才去上小學,上了沒有幾年,家裡沒有口糧了,就又回去種田。他膽大。他那個山裡沒有學校,他居然敢辦學,一個人當校長、當老師——當老師又教語文、又教算術、又教畫畫、又教體育——當夥頭、當打鐘的。當了幾年,教出些什麼桃李自然是天曉得,倒是他自己出了名,被調到公社做幹部。「文化大革命」,他那個公社造民最早。司令自然是他。把公社機關所有的公章用麻繩串成一串,當褲腰帶系在腰上。大約是因為大家都曉得十個癩痢九個哈,居然當地沒有人敢另立山頭跟他對抗。有幾個人背後嘀嘀咕咕過幾回,想想還是覺得惹不起哈巴癩痢,便死了心。因此,「文化革命」了幾年,別的公社都犧牲了人,他那個公社連武鬥也沒有發生過。哈巴癩痢也就因此顯得出類拔萃。然後就成了鎮革委主任。唯一可借的是字依舊認得不多,跟鎮長的身份遠不相稱。但是他決不肯因此跌價,稿子總要有一定厚度的,因為那是鎮長權威的體現。至於念不全,他有法子解決。
那法子很簡單,就是將稿子複寫成兩份,他拿一份,另一個字認得多的人拿一份。他作報告的時候那個人就站在他身後,遇到有他不認得的字(預先看一遍做好記號),就給他提詞。本來這不失為一種可靠的保障,但他性子急,有時候報告作到興頭上,他就顧不得聽人提詞,依舊信口開河地念錯。好在他不伯出醜,別人要是糾正了,他馬上就改回來。比方,他把「赤裸裸」念成了「赤果果」,後邊提詞的人趕緊輕輕地糾正:不是「赤果果」是「赤裸裸」。他聽見了,就放下手上的報告稿扭回頭大聲問:「不是『赤果果』?」「不是。」「是『赤裸裸』?」「是。」「那好。」他回過頭,對台下黑壓壓的一片人說:「我剛才念錯了,不是『赤果果』,是『赤裸裸』。」對他念錯別字,大家開頭常笑,後來見他坦白得可愛,就笑不起來,反而覺得他人實在。他的坦白就像他對待自己的癩痢。別的癩痢六月三伏都想方設法捂著,他則一年四季從不戴帽子,就那樣暴露著,炫耀似的。
辦公室主任走上台的時候,哈巴癩痢並沒有什麼驚訝的表示,事情原本也是意料中的,「文化革命」了幾年,這種人見多了。
辦公室主任的揭發主要圍繞著哈巴癩痢作過的報告裡的黑話,都是些大歌大頌「林彪反黨集團」及其爪牙的話。這些話都是有文字根據的,出自某年某月某日在什麼會上的報告。辦公室主任說得有鼻子有眼,一清二楚。
哈巴癩痢起先一副滿不在乎的神氣,聽久了,好像有些煩,就說:「那些話都是你寫的,我不過就是念念罷了,還念不完全。要是有罪,你總要擔當一半,莫往我一個人頭上栽贓,莫牆倒眾人推麼。」
辦公室主任給他說得尷尬,站在臺上臉紅一下,白一下,憋了好久,突然聲嘶力竭地喊:「你作威作福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到如今你還敢強辯,你有幾個腦袋!」
哈巴癩痢低了頭,咕噥說:「我有幾個腦袋?我要有幾個腦袋,還會要這個癩痢頭麼!」
雖然是咕噥,但聲音大家都聽得見,不由哄笑起來。主持人趕緊抓起話筒喊「嚴肅些,嚴肅些」,卻自己也忍不住笑了。
對哈巴癩痢的處理沒有批鬥時以為的那麼嚴重。到底只是個基層幹部,紅是紅過,卻同上面的那些大人物沒有什麼非法的組織上的瓜葛。但已經批鬥成敵我矛盾了,總不能一風吹,就下到蔬菜大隊去勞動。鎮長自然不當了,但工資還在鎮上拿。先掛起來再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