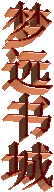
將軍鎮 第六章 李欣
一
才一個夜晚,雪就把田飯都覆蓋住了。田阪變得比先前好看了。先前的嶙峋,裸露,涸竭,先前的凋敝,破爛,傾頹,全都被覆蓋得柔和了,潔白了。天和地變得單純了,卻也更沒有生氣了。穿著一件黃色軍大衣的李欣在沒有邊際的雪裡棲惶地蠕動,遠遠地看去,讓人心痛。
李欣已經追了二十幾裡路了。昨天,他終於打聽到桑葉最近幾天上門做裁縫的屋場,並且弄清楚了桑葉會在哪一家過夜。今天吃過早飯,黃帽子上公社商量工作組的總結,李欣隨後也離開了大隊。他出去,並沒有引起特別的注意。自從下雪,工作組和大隊就佈置了,讓幹部們分頭下去檢查耕牛越冬情況。牛要凍死了,明年春天還要不要生產,要不要過日子呢。只是下去的時間沒有強求統一。大隊幹部住得分散,各人又都有各人的情況,只要掌握了情況,有問題能及時發現,幫著解決就行了。
桑葉做裁縫的那個屋場(那次批鬥會之後,桑葉不能再在大隊開裁縫鋪了,只能做散工。好在她的手藝在當地有了些名氣,約她上門做事的不斷索),離大隊上十裡,並不屬李欣檢查工作的範圍。但他顧不得許多了。那裡沒有住工作組,也就幾乎沒有什麼人認識他。下雪的天,來了一個幹部,找人有事,如此而已。
那一家門關得緊,拍了半天,拍不開。李欣退下臺階,看看屋頂,屋頂上的煙筒冒著淡淡的藍煙。證明屋裡人正把火燒得旺。一條狗圍著他轉,在他身前身後亂蹦亂跳。叫得厲害,不斷威脅地齜牙咧嘴,讓他膽戰心涼,但他還是重新走上了臺階。狗終於失去忍耐和怯懦(鄉村的狗原也有些怕幹部的),撲了上來,咬住了他的大衣的後擺。他閉上眼睛大叫一聲。那一聲在寂寥的下著雪的鄉村的早上聽起來,真是慘絕人寰。這才驚動了屋子的主人。開了門,喝了狗,問了來意,卻給了一個失望。
桑葉剛才讓別人家接走了。那家人不在這個屋場上,遠倒不遠,出了屋場,過了前頭那個坎,再過去兩個大隊就是,二三裡路吧。你要趕,趕得腳印子上的。
李欣看看那個人手指的那條路,遠遠地臥在迷蒙的雪幕的後面。沒有一個人影,腳印是早沒有的了。鄉里人告訴別人行程的時候,永遠只說:「不遠,二三裡吧!」
李欣心裡升起一種悲壯感。他微微佝了腰,恨不得跑,卻跑不了。直是跌跌撞撞,磕磕碰碰,腳不是踢上裸露在地面上的銳利的石尖,就是夾進雪下面的石塊中間。他曉得好幾個腳趾頭已經傷了,在流血,卻一切顧不得了。他走得氣喘吁吁,背上流的卻是冰冷的汗。
「桑葉,桑葉,這都是為了你!」
李欣無所顧忌地大聲喊叫起來,口裡噴出大團大團的白氣。面前跳躍著桑葉美麗的臉、美麗的肩,乳房、腰肢和腿。他相信她對殷道嚴的逢迎只是對權力的屈從。審問她的時候,她說跟殷道嚴頭一次發生關係,就是那個民兵會的下午。殷道嚴到她屋裡來,問她想不想當民兵。她說想,就怕當不了。殷道嚴說,當是當得了,就看你表現。她問怎樣的表現。殷道嚴直截了當地說,你給了我就是表現,不給我就是不表現,那我現在就讓民兵來捆你走,說你想拉攏腐濁我。她笑了,說,那我就給你吧,只不過,給了你,你莫又說拉攏腐蝕你,這可是真的拉攏腐蝕啊。殷道嚴說誰敢說,就動手……黃帽子當時拍桌子制止了桑葉的交待,說她誣衊。李欣知道她不是誣衊,每一句每一字都是真實的。那些話將永遠像一些喊喊喳喳上下起落的刀子切割他的神經,他身上「騰」地一下熱起來。為了桑葉讓他付出的這麼沉重的代價,他真想一到目的地就強姦了她。
前面不遠的茫茫雪地上,終於可以看到兩個隱約在雪霧裡的黑點。
「該死的!」
李欣忽然感到委屈,似乎是桑葉愚弄了他。這些日子,他像是瘋了,就為了這麼一個女人,一個叫做桑葉的地位下賤又並不乾淨的鄉下富農的女兒。他站住了,把棉襖的領子豎起來,點了支煙,狠狠吸了一氣。又狠狠地把煙擰碎,然後就大踏步地朝前奔去。
實實在在的桑葉重又站在他面前了,不再是虛幻縹渺。這些日子她就像妖精一樣折磨他。她赤裸了自己,引誘他,挑逗他。他撲上去,她又飄開了,然後又站在一個他可以真真切切地看清她的地方,喘息、扭動,千般媚態,萬種風情。
不遠的地方已經看得見一個被雪覆蓋住的屋場的輪廓了。一堆一堆的屋在雪裡睡著。一叢一叢的樹在雪裡支撐著。有狗在村口躍動。那個給桑葉挑著縫紉機,顯然是東家的人猶豫地看著桑葉,拿不定主意是站下來等著還是走開去。李欣很不耐煩地說:「你先走吧,我只跟她約個日子,她隨後就來了。」李欣最討厭鄉下人的這種惡習:只要見一個到鄉下來的城裡人,就牛似地瞪大眼睛,憨憨地站著看你。
「躲我?」
桑葉的從裹緊的頭巾裡露出的臉很紅,有雪花落在眼毛上,就停在那裡。李欣一伸手就可以把她攬到懷裡來。他想揉碎她,想把她按倒在雪地上。但是那個鄉下人頻頻回頭。
「為什麼躲你?」桑葉很恐懼地閃閃眼睛,「我要做手藝,我要活命。你們工作組還不肯放過我麼?」
「我說的不是這個。」
「那你說的是什麼?」
「你真不曉得?」
「我怎麼曉得?」
李欣抬起手。那鄉下人在不遠的地方大聲咳嗽。
「我也會殺人的。」
「真嚇人,你要殺哪個?」
「殺你!」
「平白無故殺我做什麼?」
「你曉得。」
「那……隨你。
「你莫走。」
「……」
「桑葉,我是真心真意的。桑葉……」
桑葉走得很遠了。風雪越益大了。桑葉很快就變得模糊了起來。李欣身上發軟,一下子沒有了力氣,很想在雪地上蜷下去。他摸出煙,但手一直厲害地抖著,怎麼也不能把煙點著。他抬起頭,讓雪落到臉上。融化的雪水沿著脖子流下去,稍稍地讓他冷靜了些。他想:她是個什麼東西!但這樣想,反而更想佔有她。他於是又想:她走不脫的。至於怎樣的「走不脫」,他卻不得要領。
二
小敏見到李欣時,臉一紅,一白,淚水一下就湧了滿眼。嘴唇很厲害地翕動著,半天說不出一句話。
她正隨一群女勞力在倉庫裡搓草繩,預備明年春天捆麥把和油菜把的。見李欣來,老表嫂們互相擠眉弄眼。沒有出嫁的女子們偷偷地拿眼睃李欣,盡是對小敏的羡慕。
女人們起哄:
「快起吧,小敏早熬不住了!」
「鬼話,李同志就熬得住麼!」
「秤桿離不得秤砣,老公離不開老婆!」
鬧得兩個人很窘,卻又動不得身。其中就有仗義的高聲喝喊:
「放正經些,草狗!你們騷得,城裡人騷不得,人家臉皮子薄。」
喝喊的是小敏的房東。她男人不在了,一個兒子當兵,兩個女兒都嫁了人,縣工作組就小敏一個女的,正好給她做個伴。住了些日子,就把小敏看成了自己女兒:
「敏兒,還不快接李同志去屋裡坐。」
李欣和小敏就在一片哄笑聲中脫身。
小敏低下了頭在前頭走得飛快,到了前後不見人的地方還不肯放慢腳步。李欣在後面連連喊她,她只是不理。
「你急什麼,我不是來了嗎。」李欣笑得很乾澀。
「哪個急了,鬼才急了。」
已經進了院門了,小敏突然停下來,不進屋。
「你怎麼回事?」
「莫碰我,不理你!」小敏扭了一下肩膀。
李欣卻更緊地抓住了小敏的肩頭。
「走吧,你真是的。」
他努力說得溫存,聲音卻很空洞,好像是從另一張嘴裡說出來的。
小敏又掙扎了一下,沒有掙脫,咬著牙,在李欣抓住她肩頭的手背上狠狠擰了一下,罵:「該死!」
底下的腳卻移動了。
李欣有些日子沒有來看小敏了。他已經不在八隊蹲點了,去那邊的機會自然就少。等到昨天,縣文工團工作組有一個傢伙到這個大隊來找熟人散心,小敏的影子才漸漸地在李欣的眼前清晰起來。
先前遮擋在小敏影子前面的,是桑葉的影子。從最早那次見到桑葉,李欣的心裡就老有一種異樣的興奮。沒有油腥的菜,不再覺得難咽(也不再打瞎拐那缸豬油的主意),覺也不太睡得著(更不要說白天裝病賴床了)。屋子裡總不太呆得住,有事沒事就跑到外面的公路上去,走路總是昂首闊步,想唱歌,像只隨時要撲母雞的小雞公。大隊小學離大隊部一箭之地,隔著公路相望,這邊要唱歌,那邊是聽得清的。大隊小學實際就是一排臨著公路的平屋。公路和平屋之間是一小塊空地,就是操場。屋背後面是一道高坎。做屋的時候,為了讓屋前有塊空地,把坡劈陡直了,屋就坐落在那個劈陡直了的馬蹄形中間,再沒有圍牆。最使李欣遺憾的是,學校兩邊至少二三十步之間,跟哪個也不挨不靠,沒有人家,也沒有店鋪。「要有個煙攤多好啊。」李欣在心裡歎息。實在忍不住了,他就作散步狀。在學校前的公路上走過,每到快走到學校的時候,心口就不知為什麼緊起來,走過去了,後腦勺上又一陣一陣發熱,好像真有什麼熱辣辣的眼光射在上面了。其實走過來,走過去,學校那排平屋始終跟後坎上的墳墓似的靜無聲息。桑葉做裁縫的那間屋子,門倒是開的,但有時或許見到人影一閃,有時連人影也見不到。桑葉並沒有像他常常出現的感覺那樣含情脈脈地倚門而立。現在桑葉是永遠也不會出現在那小屋裡了。那扇小門關著,並且上了鎖。那把鎖小小的,卻有力。就像桑葉小小的手,一把鎖緊了自己的胸口,似乎是一種堅決的拒絕。
李欣很難把持往自己。他在縣城裡一向春風得意,喜歡他以至很明白地追他的女孩子很多。他也就在縣城上一幫平庸的女孩子中高視徜徉,來者不拒地同她們虛與委蛇,小地方的女孩子見識有限,吃了虧上了當往往自認命苦,想想也就過去了。他也便成了常勝將軍。小敏就是他同人打賭打來的。小敏在臺上跳白毛女,跳大春的那個傻大個當著觀眾就抑制不住對小敏的一副饞相。坐在前排看戲的李欣不由冷笑。旁邊同來的幾位就起哄,說,你怎麼知道人家是癡心妄想?李欣說,不信可以打賭,我只要一封信,白毛女就保證為我剪窗花。就真的打了賭。而李欣就真的贏了。李欣的信寄出一個星期沒有收到回信,大家天天逼李欣認輸。李欣有把握,說,決不會出兩個星期。第十天的樣子,回信果然來了。小敏是68屆初中生,實際等於沒有上初中課,字寫得很糟,歪歪扭扭不成樣子,但意思是清楚的,同意跟李欣面談,時間和地點由李欣定。顯然小敏遲回信並不是女孩子的抬高身價,而是不曉得怎樣回信好,怕李欣笑話,乾脆給了個簡單明瞭的回答。李欣就在接到信的當天晚上,在縣城邊的河灘上吻了小敏。「還幹了什麼?」第二天大家訛他,他很曖昧地說:「沒有什麼。」大家就有些鄙夷地說:「小敏臉模子不錯,可惜身子單薄了。」李欣馬上搶白說:「你們曉得個屁!」大家轟然笑起來:「到底交待出來了。」笑歸笑,對李欣的服氣甚至妒嫉還是由衷的。
小敏喜歡發小脾氣,常常莫名其妙地就翻了臉。剛認識的時候,頭一次見面她就讓李欣得到意外收穫。可是第二天李欣以為可以長驅直入的時候,她卻又罵他「流氓」。罵完就走,卻沒有走回縣劇團,反而走到城外坡上沒有人的林子裡來了。來了,依然是執拗著,發著小脾氣。折磨得李欣心裡那股邪火快要熄滅了,她卻又忽然來了激情,軟軟的像只懶貓,聽任李欣擺佈。這樣的脾氣多發了幾次,李欣也就消去了先前以為她不可捉摸的神秘感,曉得只要多一點耐心,讓她多少得到一些她在他心裡不是一點分量沒有的證明,一天的雲也就散了。
但是今天,他卻忽然想,他有什麼必要必須鼓起這種耐心呢?小敏發脾氣的樣子他曾經覺得另有一種味兒,現在他卻忽然發覺了做作、扭捏甚至有些醜。
剛進堂屋,小敏就一下轉過身,把頭抵住李欣的胸口,兩隻小拳頭在李欣身上亂捶。每回,這都是很容易激發李欣的。李欣也就像每回一樣,把她橫抱了起來,任她一邊蹬著腿,一邊罵著「流氓、流氓」,然後就縮緊身子,然後他的頸根那兒就感到一股觸電似的溫熱。但是今天卻沒有了觸電感,只剩下了溫熱。那溫熱讓李欣覺得貪婪,覺得膩。他甚至清晰地感覺到那溫熱留下的一團濕潤。那濕潤讓他感到不潔、有異味,直想沖洗。
每次都是小敏讓李欣給她脫衣服。
「我才不服侍人。」她每次都說。
「我服侍你。」每次李欣都說。但這一次他卻沒有說,動作則很粗魯。
「不來就老不來,來了又急成這副憨樣。」
小敏很甜蜜。
李欣很專注。他忽然發覺小敏的皮膚是一種有些病態的黃色。沒法跟桑葉比的,給自己脫衣服的時候,他想。
「怎麼回事?」
小敏有些迫不及待。
「過了一回。」李欣含含糊糊地咕噥。
「這麼想,為什麼不早些來?」
「不是來了麼。」
李欣閉緊眼睛,抱緊了小敏,極力把身子下的小敏想像成桑葉。
小敏忽然驚叫了一聲,就長一聲短一聲快活地呻吟起來。
每次事後,小敏就再不說「我才不服侍人」,總是軟軟地但是細心地撫弄他。
李欣靜靜地仰面躺著。屋子裡很昏暗。從用塑料紙袋蒙的窗戶上透進的夕陽的微弱光柱裡,飄浮著塵埃。陳年的家具和潮濕的土牆散發著濃濃的發黴的氣味。
小敏在耳邊絮絮叨叨地說劇團副團長(就是那位演大春的人),怎樣有事沒事總是尋了來,有時坐到很晚不走,手腳也沒處放,眼睛也老是發直,很怕人,她就大聲喊房東來,討問鞋幫繡花的樣子。她還真的給自己做了一雙鄉土氣十足的繡花的布鞋。
「快收工了吧?」李欣擋住小敏的手。
「快了!」小敏喃喃地說,很留戀。
「那就起來?」李欣問,卻不等小敏回答,坐了起來。
小敏還賴著,把臉貼在他的大腿中間。
李欣輕輕地但是很堅決地抽出身子,翻身跳到床下來。
「我的衣服有人脫,就沒人穿了。」小敏在他身後嘰嘰咕咕。
一切都是既定的程序,只是心情不同。李欣想。
就聽到屋外面柴門的響動。
房東死活要留李欣「過夜」。在當地人的話裡,「過夜」有兩種意義,一是夜飯,一是夜宿。房東的挽留一併包括了兩種意義。
「空屋有的是,床、被窩也是現成的。你難得來。要不是路教,要不是敏兒,我請都請你不到。」
「讓他死走,死遠些,有什麼了不起的。」小敏很氣的樣子。
房東也就更不肯讓李欣走了。
吃飯的時候,小敏容光煥發,像是一盆受了旱的花,一下子澆足了水。
李欣則沉默著,儘量不去看她,靦腆之態可掬。
房東看看這個,又看看那個,說:
「真好!天生一對,地設一雙。」
房東一去廚房,小敏就站起來,在李欣臉上狠狠印了一個濕膩膩的印子。
「裝什麼憨樣!夜裡不要走。」
「要走的。」
「你敢!」
小敏做出溫怒狀,她相信他不會走。
李欣不做聲。
小敏從下邊端了他一腳,一咧嘴:
「你會走?饞貓。哼!」
小敏一點也沒有覺察李欣的心思。這使李欣覺得自己有些狠心。但等到飯後,幾個人閒聊了一會,房東知趣地說累了,要早些睡。她走後,小敏對房東安排給李欣注的那間房努了努嘴說:「你先過去,等一下摸過來。」
李欣卻斷然說:「我今晚一定要走的,工作組有事。」
小敏這才看出來,李欣是執意要走的。呆了一會,變了臉色,卻嘴硬:
「你走,你只管走!」
李欣起身就走。
小敏一跺腳,哭起來。
李欣不回頭,一直走出屋門,走到院子的柴門那兒,小敏追到屋門,很悠長、很壓抑地喊了一聲:
「你回來,求你……」
李欣拉柴門,一直走進黑暗裡面。接著屋場上響起了此起彼伏的狗叫,淹沒了小敏的啜泣。
三
工作組離開之前,桑葉失蹤了。沒有發現自殺的跡象,也沒有發現任何出走的跡象,卻沒有人曉得她的去處。
桑葉的消失,使李欣先前的風流變成了頹廢。這頹廢竟使他同李月娥發生了糾葛。
李月娥跟一首名歌《養豬模範李月娥》裡的主人公同名,但她不是養豬模範,倘若讓她殺豬,她倒有可能成為模範。
李月娥不是本縣人,據說是一個偏遠山區縣的回鄉知青,後來同一個已經有妻室的人生了一個女兒。那人在縣上有些權力,為了把事情遮掩過去,便托本縣的一個同樣有權力的人把她安排到鎮上做臨時工。她一個人帶著個女兒在鎮上過,正張了網要捉一個人去填空的,李欣自己一頭撞了進去。他父親在小鎮糧管所做事,休息日子和逢年過節他常回到小鎮來。不知怎樣讓李月娥纏上了,竟有了身孕。李月娥比他整整大七歲,還拖著油瓶,婚姻的事,做夢也不該想。
哪裡曉得李月娥卻是懷了雄心壯志的。縣革委幹事既入了她的彀中,她也就志在必得。給他打過幾次電話,沒有結果,她便公然在大街上攔阻他,並豪邁宣佈他們之間感天動地的已經有了結晶的偉大愛情。「偉大」云云,原是李欣的語言。床第之間,快活的時候,他曾對她戲言:燕妮比馬克思也正好整整大七歲的。他在師範學的那點文化大都用在這上頭了。
李欣完全沒有思想準備,惶惶如被當眾拿獲的竊賊。李月娥極柔媚卻極有暗勁地拖住他的一隻胳臂,讓他當街發佈要娶她的宣言。他真希望此刻天塌地陷,卻又不得不支吾其詞,以求脫身。回去便立即廢了剛才的承諾——他本來也沒有打算實行的承諾。
李月娥卻是守信義的。到了李欣那天當街答應的日子,她租了單位裡的一輛爛吉普車,自己用紅綢子紮了朵大紅花掛車頭上,帶上嫁妝(也就是隨身的幾件行李)奔赴李欣的家。
雖然這婚姻很難說怎樣美滿,但李月娥把一切的禮行儀式還是操持得一樣周到。送親的、挑魚肉酒罈的、抬腳盆馬桶的、吹喇叭的、放炮仗的,應有盡有。最具幽默意味的是哭嫁。哭不僅是表示惜別,表示難以割捨,更重要的是表示女兒的身價。娘家人哭得越厲害,女兒就越有面子,好比是離了豪門大宅。然而這卻成了一種職業,是有人專司其事的。兩個女人,一個做娘的角色,一個做女兒的角色,隔一陣子就來一段母女對唱。自然是哭腔哭調,卻沒有眼淚,只是對哭聲的模仿。唱詞更讓人莫名其妙:
母:前邊火把熠熠起,
後邊火把熠熠光,
中間扛個臭瘟喪。
女:前邊火把熠熠起,
後邊火把熠熠光,
中間扛個秀才娘。
母:前邊敬天地,
後邊火燒書。
女:前邊敬天地,
後邊樹華堂。
母:三朝死公婆,
滿月死丈夫。
女:三朝公婆做生日,
滿月丈夫中狀元。
送親隊伍到了院門口,門閉著,李月娥便讓司機猛按喇叭,以示鳴炮,仿佛當年奉行炮艦政策進攻閉關鎖國的大清王朝的西洋強盜。哭嫁的隨著吹吹打打的反響,哭得更其熱鬧。
鎮上幾出得門來的人都出來圍觀。他們議論的是哭嫁,心裡卻是對李欣的幸災樂禍。
李月娥是不達目的,誓不收兵。
縣革委幹事一家只好妥協投降,開門揖盜。
後來這家人的日子是可以想像的。終於到了忍無可忍的程度,李欣娘老子請求法律的救援,解脫這樁要命的婚姻。
李月娥堅強不屈。法庭調查期間,她揚言要以老鼠藥與縣委幹事一家同歸於盡。嚇得他們除了單位的飯菜茶水,家裡的一切可供食用的東西皆不敢入口。她又威脅法庭,誰敢承辦這樁離婚案,她便跟誰全家拚命。法庭傳喚,她堅不到庭,一連幾天閉門不出,一聲不響地實行絕食抗議。法庭怕她真的尋了短見,便派人前去窺探。她住的那間房子窗戶都掛了窗簾,只有房門插頭被她忽視了。前去窺探的人用板凳墊腳往裡看去,她正很悠哉地在床上躺著,瓜皮果殼糕餅盒子棄了一地。一發現房門插頭上的人臉,她便一躍而起,大喊「捉拿流氓」。
一時間,舉縣無人敢近。縣革委幹事李欣一家只好舉家逃亡,另擇他居,任她鳩占鵲巢。